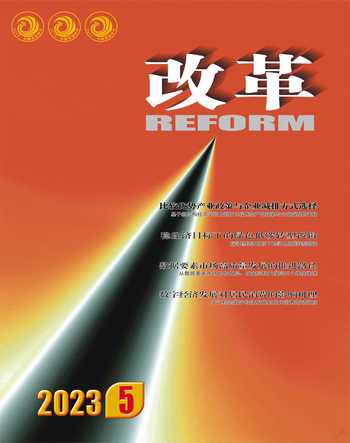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2023-06-13贺唯唯侯俊军
贺唯唯 侯俊军



摘 要:将居民消费问题纳入数字经济的分析框架,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理论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流动性约束等手段影响居民消费。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和手工查找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2011—2019年我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增加本地人均消费支出,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城市层级等层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支付便利性、流动性约束以及家庭不确定性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机制;基于城乡不平等视角的扩展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且有利于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
关键词:数字经济发展;居民消费;城乡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05-0041-13
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尤为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生产力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地快速渗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增长新引擎,将生产力发展推向全新高度。数字经济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供需衔接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有助于诱导人力资本投资,刺激创新活力;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扩大产业链分工边界、促进技术跨行业渗透,加快传统产业转型与技术革新[1];数字经济通过对海量信息进行整合、处理与投送,显著降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使市场供需衔接水平大幅提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发掘数字经济潜力对于助推高质量发展[2]、促进共同富裕[3]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够更为有效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长尾化需求,引发消费内容、形式乃至理念的新变革和消费倾向的结构性变化,居民消费格局亦随之发生转变,尤其是“十三五”期间电商向农村市场下沉,带动农村网络零售发展,实现了农村网络零售规模跨越式增长,更是为中国经济增长扩展了消费新空间[4]。钟若愚和曾洁华指出,数字化浪潮下的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5]。相关典型事实为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研究的展开指明了方向。
那么,这能否说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作用?如果该作用得到证实,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遗憾的是,目前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较为有限。既有相关文献集中于理论阐述[6-7],以及探讨互联网或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规模[8-10]和不平等[11-13]的影响。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并未针对数字经济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结合相关研究梳理与中国现实背景对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提出
既有涉及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互联网发展与数字金融两个维度展开。在互联网层面,既有研究认为,互联网发展将提升居民消费信息获取能力,进而扩大消费。黄卫东和岳中刚、向玉冰均指出,互联网技术应用能够推动线上线下渠道深化融合,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增加居民消费[9,14]。张永丽和徐腊梅基于微观农户样本分析后也认为,互联网兼具“扩大消费规模”与“优化消费结构”的双重作用,因而有助于引导农村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实现消费升级[15]。在数字金融层面,相关研究指出,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有效需求,因而对带动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结合CFPS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的居民消费效应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确实有助于带动居民增加消费[16-18]。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设1: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作用。
既有研究对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主要集中于支付便利性、流动性约束、家庭不确定性三个维度。首先,数字技术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直接带动居民消费。刘湖和张家平、张勋等均指出,数字技术发展有效提升了居民购物的支付便捷度,有助于引导居民增加消费[8,11]。其次,数字金融通过增加流动性供给的方式改善了金融可得性,成为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推手。易行健和周利、尹志超和张号栋经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放松了流动性约束,使得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10,19]。最后,数字经济背景下家庭不确定性逐渐降低,为居民扩大消费提供了风险保障。何宗樾和宋旭光、Li等强调,除互联网支付、增加流动性之外,数字保险业务的全面铺开能够增强个体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使居民更敢于消费[16-17]。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提升支付便利性、放松流动性约束、降低家庭不确定性是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
二、实证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consumptionit=β0+β1digitalit+λDit+μi+δt+εit(1)
式(1)中,consumptionit与digitalit分别为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i在t年的城乡居民消费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为地区控制变量集合,μ、δ分别为地区效应和年份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居民消费(consumption)。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数作为反映本地居民消费规模的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常住人口比重)。
2.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igital)。本文参考赵涛、张智、梁上坤的研究方法[20],选取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五项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化指数进行测度并用以反映数字经济水平。在数据测度之前,本文对上述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具体方法为:处理值=(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在实证分析时,本文对测度的数字化指数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反映数字化水平,具体为:digital=ln(数字化指数×100)。
3.机制变量
本文选取支付便利性(payment)、流动性约束(constraint)以及家庭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考察数字经济带动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分别对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数字支付指数、数字信用指数以及数字保险指数取对数作为度量指标。
4.控制变量
产业高度化(structure)。产业升级有助于提升供给质量,进而提高供需衔接效率、带动消费,本文选取产业高度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反映地区产业结构。收入水平(income)。收入水平对消费具有直接决定作用,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万元/人)的对数反映居民收入水平,具体计算方法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ln(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人口比重)。经济发展水平(gdp)。本文选取人均GDP(单位:万元/人)的对数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力资本(hc)。人力资本对于增加财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均具有正面影响,本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测算,计算方法为:人力资本=(高校在校学生数×16+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12+小学在校学生数×6)/地区总人口。公共医疗供给(medicine)。增加公共医疗供给、减少居民医疗负担对于带动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地区人均医院床位数(单位:床/万人)反映本地公共医疗供给规模。公共交通(vehicle)。公共交通水平提升有利于降低居民出行成本,进而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选取人均公共交通车辆数(单位:辆/万人)作为反映地区公共交通水平的指标。环境规制(regulation)。环境污染会通过加快健康资本折旧的方式增加医疗成本,这可能对居民消费造成不利影响,本文根据叶琴等[21]的研究方法,采用人均废水排放量(单位:吨/人)、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吨/万人)以及人均烟尘排放量(单位:吨/万人)构造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规制指数并取其对数以衡量本地环境规制力度。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于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数据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且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在2019年后缺失較为严重,因而本文将研究时间确定为2011—2019年,并剔除了研究时间内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以及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行政面积等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的直辖市,获得了包含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进一步地,本文对各地历年的数字化指数进行测度,并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带动作用。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乡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均来自中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余数据则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检验结果
基本模型结果如表3(下页)所示。列(1)展示了仅控制年份效应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大体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列(2)在列(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地区效应,可以发现数字化水平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正面带动作用。列(3)则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各项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此时数字化水平每提高1%,居民消费就增加0.052%。
就基本模型各控制变量而言,产业高度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产业升级有利于改善供求衔接效率并带动居民消费。收入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收入提高会引导居民增加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经济水平提升同样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支出。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是居民消费增加的原因之一。人均医院床位数、人均公共交通车辆数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现阶段公共医疗服务、公交交通服务供给增加对于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刺激消费的作用较为有限。环境规制的系数不显著,表明现阶段环境规制不是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
(二)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检验。测量误差、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因素可能导致模型出现潜在内生性问题,对模型进行系统的内生性检验以排除上述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干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使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列(1)所示。本文参考黄群慧等[22]的研究思路,选取2004年邮政设施历史数据作为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对基本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一方面,数字技术是传统通信的新型技术延伸,邮政设施作为传统通信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当期规模会通过产业基础、使用习惯等路径对当地后续数字技术应用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传统邮政业务使用频率随着新型通信技术发展而逐步减少,邮局作为传统邮政通信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降低,故呈现明显的排他性特征。鉴于选取的工具变量原始数据为截面数据,无法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内生性检验分析,本文参考Nunn & Qian的研究[23],通过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方法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本文以时间年份与2004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每万人邮局数量构造交互项,作为该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
表4列(1)结果显示,对于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的统计量p值为0.000,小于0.01的临界值,故显著拒绝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30.820,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以上结果表明,选取历史上各城市人均邮局数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作为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就模型检验结果而言,经工具变量处理后的数字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基本模型结果一致。
(2)系统GMM检验。表4列(2)展示了经过系统GMM方法处理内生性后的模型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此时Hansen值为0.453,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系统GMM模型中数字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经过该内生性处理后数字化发展仍然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与基本模型结果类似。
2.稳健性检验
基本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增加了居民消费支出,即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进一步地,本文针对数字经济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系统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列(1)展示了解释指标替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本文选取数字化水平的滞后1期替代原当期指标进行检验发现,数字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基本模型检验结果一致,表明此时数字化仍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作用。
列(2)给出了被解释变量替换的检验结果。本文参考董直庆和王辉[24]的研究方法选取地区人均居民储蓄(单位:万元/人)的对数(saving)反映地区居民消费潜力,并替换原被解释变量开展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水平的系数经被解释变量替换处理后依然显著为正,与基本模型检验结果类似。
为排除因控制变量选取遗漏而造成的结果偏误,本文进一步采用各控制变量滞后1期替换原控制变量进行再次检验,结果如列(3)所示。经过控制变量替换处理后,数字化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与基本模型结果无明显差异。
由于部分城市城镇化率极高、本地农村人口样本过少,可能会导致农村居民特征难以统计,故本文在基本模型实证部分假定上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再对该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计算。事实上,即使城镇化率为100%的地区仍可能存在少量农村居民,本文对上述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的处理可能导致结果偏差。为排除这一潜在风险,本文剔除了城镇化率为100%的样本,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列(4)所示。结果表明,此时数字化水平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基本模型结果保持一致。
综合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因而假设1成立。
(三)异质性检验
前文系统检验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带动效应。事实上,中国区域间经济基础、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发展政策、文化风俗等均存在明显差异,就数字经济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开展异质性检验,对于全面刻画数字经济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十分重要。本文主要从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城市层级三个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6(下页)所示。
就地理位置而言,本文根据所属省级行政区将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子样本以开展地理位置异质性分析,相关结果如列(1)—(4)所示。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的系数在东部、中部地区均显著为正,而在西部、东北地区不显著。换言之,数字化发展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强于西部、东北地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以信息传递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东部、中部地区人口密度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经济基础好,当地居民依托数字经济所获取的收益更多,因而消费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就城市规模而言,本文参考袁冬梅等的研究[25],将年末总人口大于500万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划为大中型城市,其余为小城市,并以此开展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结果如列(5)—(6)所示。可以发现,数字化水平在大中型城市、小城市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大中型城市系数值略大于小城市。也就是说,大中型城市居民消费受数字经济发展带动的效果稍强于小城市。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可能在于,小城市相较于大中型城市在信息、物流、人口规模和密度等传统消费条件上均存在劣势,导致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渗透的效果有限,因而限制了居民消费进一步增加。
就城市层级而言,本文将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作为中心城市,其余则划为外围城市,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城市层级异质性,结果如列(7)—(8)所示。结果发现,数字化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外围城市。原因可能是,中心城市信息化程度高、物流通畅、消费品供给丰富,居民消费能力已经得到较好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对于进一步刺激本地居民增加消费作用不足。而对于外围城市,数字经济能夠通过提升供求匹配效率、拓宽消费渠道、丰富产品种类等方式有效弥补当地消费市场的诸多短板,有利于加快市场下沉、带动本地居民消费。
四、作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讨论数字经济带动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具体如下:
interit=β0+β1digitalit+λDit+μi+δt+εit(2)
consumptionit=β0+β1digitalit+β2interit+λDit+μi+δt+εit(3)
其中,inter为机制项。本文分别从支付便利性(payment)、流动性约束(constraint)以及家庭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三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带动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机制检验结果如表7(下页)所示。
表7列(1)—(3)给出了数字经济对各机制变量的实际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水平对数字支付指数对数、数字信用指数对数以及数字保险指数对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支付便利性、扩大流动性约束、降低家庭不确定性。
列(4)—(6)展示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列(4)中数字化水平与支付便利性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支付便利性,进而增加了居民消费。列(5)中数字化水平与数字信用指数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换言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放松流动性约束的方式带动居民消费。列(6)中数字化水平与数字保险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数字化水平有利于带动数字保险发展、降低家庭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居民消费。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放松流动性约束、降低家庭不确定性等途径对本地居民消费形成带动作用,因而假设2成立。
五、进一步扩展分析:基于城乡不平等视角
前文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也存在明显区别。理论上,不同收入群体在消费支出规模、产品流向、边际倾向等维度的差异将导致消费出现群体分化。就支出规模维度而言,高收入群体明显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就产品流向维度而言,高收入群体往往偏向于高品质、高价格、享受型产品消费,中低收入群体则更多是增加日常用品消费。就边际倾向维度而言,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低于中低收入人群。此外,数字经济发展使得群体间消费差异出现新特征。首先,数字经济对产品消费的带动类型存在群体差别。数字经济对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带动作用在智能电子耐用品、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休闲等的消费中有集中体现。就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更多聚焦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盲目消费,以及增加服装、日用品、食品及普通耐用品等消费。其次,5G通信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在群体间分布不均,加剧了居民消费间的数字鸿沟。再次,参与数字经济活动受到终端设备成本的限制,这导致数字终端在不同收入群体间接入程度不一,可能放大居民消费的不平等问题。最后,不同群体之间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存在差异,这将进一步导致居民间消费出现分化。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全面铺开,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22年的65.22%,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以加速驱动产业现代化的方式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然而,由于不同群体间消费行为、习惯等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居民内部之间消费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这不仅会对居民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造成直接阻碍,而且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在带动居民消费的过程中,兼顾实现“效率”和“公平”将成为扩大内需的有力推手。事实上,中国于2008、2021、2022年分别围绕“家电下乡”“改善物流”“家电更新”等主题,力求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内需、全方位释放消费“红利”,这与“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发展内涵高度一致。
鉴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可能存在群体差异,那么对于二元结构特征突出的中国而言,数字经济背景下城乡居民消费有何特征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系统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结果如表8(下页)所示。
表8列(1)—(2)分别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数的影响。数字化水平的系数在列(1)—(2)中均显著为正,且列(2)系数值大于列(1),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高且边际消费倾向更小,数字经济引导城镇居民进一步增加消费的难度更大。而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市场供需效率的方式推动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农村居民盲目消费的概率,继而更快地带动了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列(3)—(5)则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公平”问题的实际影响。列(3)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对城乡个体居民消费比(consumptionratio)的影响显著为负,即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直接缩小城乡居民个体相对消费差距。列(4)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了本地城镇人口比重(urbanization)。原因在于,数字经济通过海量信息投放、放松居民流动性约束、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扩大就业等手段加快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进而加速本地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地,本文构造城乡消费基尼系数(consumptioninequality)作为考察城乡消费“公平”问题的度量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为:城乡消费基尼系数=城镇居民总消费占城乡居民总消费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数字经济对城乡消费基尼系数的影响如列(5)所示。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显著拉低了城乡消费基尼系数。综合列(3)—(5)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公平”具有积极影响,且该影响通过直接缩小城乡居民个体相对消费差距,以及引导农村居民“进城”并实现消费的跨越式發展两条途径实现。
接下来,本文以居民食品支出为切入点,结合“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由于中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度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资料系统公布的城乡居民食品数据绝大部分截至2015年,因此本文将考察范围确定为2011—2015年。数字经济发展的居民消费升级效应检验结果如表9(下页)所示。
表9列(1)—(3)基于“规模效应”视角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人均非必需支出对数的影响,其中人均非必需支出=人均消费支出-人均食品支出。结果发现,数字化水平的系数在列(1)—(3)中均显著为正,且在列(3)中数值更大,即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居民非必需品消费,且对农村居民的增加作用更大。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通过扩大非必需支出规模的方式促进居民扩大非必需品消费,进而带动消费升级。
列(4)—(6)则给出了“结构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其中恩格尔系数=人均食品支出/人均消费支出。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明显降低了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且主要是降低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必需支出占总消费比重的方式提高非必需支出比重,这也会对居民消费升级形成积极影响,且该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地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向国民经济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地快速渗透,如何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文将居民消费纳入研究框架并探讨其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现状及演变规律,以期在我国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为各地助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借鉴。第一,本文对既有研究开展系统梳理后明确指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交易便利性、放松流动性约束、减少不确定性等途径对居民消费形成正面带动作用。第二,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加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经过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控制变量替换、不可观测樣本剔除、工具变量法以及系统GMM等方法处理后,结果具有稳健性。在异质性检验中,数字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大中型城市以及外围城市强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小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第三,本文从交易便利性、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带动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支付便利性、放宽流动性约束、降低家庭不确定性是数字经济带动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第四,基于城乡不平等视角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扩展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较好地维护了城乡居民消费“公平”。数字经济一方面直接带动农村居民群体消费更快增长,从而缩小城乡居民个体消费差距,另一方面又通过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流向城市,实现转移劳动力群体消费的跨越式提升。此外,数字经济对于本地居民非必需支出规模增加和比重提升均具有重要作用,且相关效应在农村地区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居民消费。鉴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行为发挥的关键作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带动居民消费、助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快数字要素市场建设,全面激发数据要素潜力;二是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平衡数据隐私保护与开放共享,并防止数字垄断;三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积极引导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并致力于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人力资本体系;四是加强对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设计软件等数字核心技术的重点攻关。
第二,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特征,推动居民消费“效率”和“公平”相统一。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现象在中国较为突出,这不仅对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张造成了直接阻碍,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割裂,衍生诸多社会问题。扩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科学有效地治理城乡消费不平等问题,需要打破二元结构和数字鸿沟的桎梏,加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经济参与能力;扩大数字金融普惠供给,增强对农村居民的金融支持,提升农村地区消费潜力;加大数字技术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城乡居民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第三,科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综合治理体系。鉴于数字经济背景下居民消费的实际变动规律呈现复杂特征,构建科学而全面的综合治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优化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引导个体消费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统筹消费规模与结构治理,在推动消费规模扩大的同时积极引导消费升级,多维度提升居民消费福利。三是提高公共交通、医疗、教育等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参考文献
[1]杨慧梅,江璐.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J].统计研究,2021(4):3-15.
[2]王小明,邵睿,朱莉芬.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究[J].改革,2023(3):148-155.
[3]师博,胡西娟.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J].改革,2022(8):76-86.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大力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J].求是,2022(2):15-21.
[5]钟若愚,曾洁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3):31-43.
[6]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财贸经济,2018(9):5-22.
[7]马香品.数字经济时代的居民消费变革:趋势、特征、机理与模式[J].财经科学,2020(1):120-132.
[8]刘湖,张家平.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与区域差异[J].财经科学,2016(4):80-88.
[9]黄卫东,岳中刚.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性创新与消费增长[J].中国软科学,2016(5):163-171.
[10]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11] 张勋,杨桐,汪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0(11):48-63.
[12] 张李义,涂奔.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化影响——从消费金融的功能性视角出发[J].财贸研究,2017(8):70-83.
[13] 程名望,张家平.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7):22-41.
[14] 向玉冰.互联网发展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4):51-60.
[15] 张永丽,徐腊梅.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基于甘肃省1 735个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9(2):42-59.
[16] 何宗樾,宋旭光.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财贸经济,2020(8):65-79.
[17] LI J, WU Y, XIAO J.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86(3): 317-326.
[18] SONG Q, LI J, Wu Y, et al. Accessi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0, 53(7): 101213.
[19] 尹志超,張号栋.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8(11):188-206.
[20]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65-76.
[21] 叶琴,曾刚,戴劭勍,等.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115-122.
[22]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23] NUNN N, 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 1630-1666.
[24] 董直庆,王辉.城市财富与绿色技术选择[J].经济研究,2021(4):143-159.
[25] 袁冬梅,信超辉,袁珶.产业集聚模式选择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来自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9(6):4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