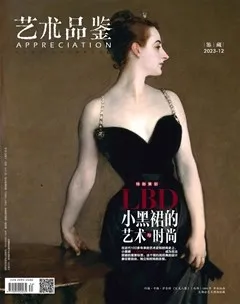戏剧表演理论对舞蹈表演中角色塑造的借鉴价值
——以芭蕾舞剧《花木兰》为例
2023-06-11李时潮唐山师范学院
李时潮(唐山师范学院)
我国戏剧界把戏剧表演大致归纳为“三大表演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布莱希特的“表现派”以及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事实证明“三大表演体系”无法完全运用于舞蹈表演中的角色塑造,也不足以构成舞蹈表演的理论基础。罗伯特·科恩博士曾将控制论、信息论等某些原理和方法运用于表演艺术中,进行了新的探讨,其中内容有助于解释舞蹈表演中角色塑造的原理,比如,演员通过“意图”分析角色,在规定情境中根据信息进行调整不断调整,直至命中角色的真实行为,并且将信息输出给其他角色和观众,与周围一切进行相互关系交流,形成循环不断的情感环路,塑造多层次表演等,启迪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关于舞蹈表演中角色塑造的问题。
“舞蹈表演”是以演员的身体为表现载体,运用身体语言将编导的艺术构思呈现出来,演员通过二度创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反映社会生活。当前“舞蹈表演”大都停留在“只能意会”的实践操作层面,需要对“舞蹈表演”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深入解析,实现“舞蹈表演”理论与实践的合一,这将有助于科学地阐释“舞蹈表演”的特点与规律,关乎“舞蹈表演”生态圈的良性发展态势。
谈起表演理论,大都会提到斯氏体系的“体验派”与布莱希特的“表现派”,按斯氏体系来说,它最重要的追求目标是将演员的自我转变为角色的自我,要求我“是”角色,而不是我“演”角色,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角色,认为在这种情况演员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角色。但体验派强调的“进入角色”与“忘我”,是舞蹈演员所做不到的,技术性毫无疑问是舞蹈演员身体表现力的前提条件,规范性作为身体表现的基础,融化在演员的表演中,融化在角色的塑造中,融化在技术技巧的训练表现中,只有将身体技术性、规范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才能使舞蹈表演的身体表现力达到一定境界。
那么就算是一个技艺熟练的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对技术的控制也不能达到完全下意识的程度,无论是不注意规范还是忽视动作的规格都会对美造成破坏,同时在高难技巧上,稍不注意就会发生纰漏,甚至会给舞蹈演员造成无法逆转的伤痛,所以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并不能完全地沉浸于角色中无法自拔达到“忘我”的程度。当然,既是一种表演,就不能完全是“理性”活动,演员要塑造角色,要把自己的身心融入角色上去,这种矛盾现象,构成了舞蹈艺术的特有的美。
令人惊喜的是,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罗伯特·科恩博士提出了一个与斯氏体系不同但更符合广泛表演艺术的理论,他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对表演艺术进行研究,拓宽了戏剧和其他表演艺术原理的认识。控制论讲的主要是根据所接收到的信息,不断地和自动地进行“自我矫正”,最终命中目标。这一理论的指导意义更接近于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并没有把演员与角色混为一谈,而是根据所发出的和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控制和调整,这对于舞蹈表演中角色塑造来说具有借鉴价值。
一、演员不断自我校正,直至命中角色
首先,人物不是角色,人物是作者以文字形式在剧作中所刻画的形象,它只活在剧本中,若要成为角色,需要经由演员的身体表演出来,赋予人物直观性,才能使角色复活。其次,演员也不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本我,而角色是演员幻我,但这并不代表二者之间没有关系,演员借助角色而存在,但没有演员的扮演,角色也始终会沉睡在剧本之中,可见演员是人物成为角色的关键。因此,可以得出角色的定义,角色就是演员所扮演的剧中人。最后,关于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不应该在舞台上表演,而应该在舞台上生活,应设身处地“化身为角色”,不要脸谱化,而要性格化。但在布莱希特那里,演员与角色之间存在着水火不容的“间离效果”。演员在扮演角色时,并不宜过于冲动,也不必过于逼真,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理智的或批判的态度。罗伯特·科恩对于二者的关系并没有绝对的观点,他只是将控制论、信息论等原理运用于角色塑造的阐释中,认为演员的角色塑造其实就是在输送和接受一系列信息,并根据信息来调整自己的方向,直至命中角色的真实行为。
控制论是在20 世纪40 年代由诺伯特·维纳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种控制系统连续不断地需要和处理信息,并根据它所接收的信息来调节它自身,最终“导向”它们的既定目标或目的地。例如一个装有恒温计的控制炉,它被规定保持一定的温度,如果恒温计规定在70°,那么当温度降低到69°时,炉子就会打开;当温度达到71°时,炉子就会关闭,这说明它是在连续不断地自我校正,这对任何一种控制系统都适用,它们会着眼于自己的目标,不断调整自己的方位,根据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自我校正,直到它们最终命中目标。罗伯特·科恩认为这一原理准确描绘了信息流动的实际情况,同时也符合演员表演的实际。
例如,在芭蕾舞剧《花木兰》中,木兰出征前演员使用轻盈活泼的肢体动作配合柔软且充满活力的身姿形态进行舞蹈表演,展现出木兰儿童时期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童面貌,更加立体地塑造花木兰在从军前灵动活泼、碧玉宛影的少女形象,而在木兰出征的片段中,演员一身戎装,步伐沉重,眼神中的牵挂和坚定纠结在一起,回头望着家的方向跪拜父母,最终径直奔向战场,这个过程中舞蹈演员所流露出的表情复杂,眼神毅然决然,与肢体动作相配合,动作幅度又明显加大,奔向战场时步伐坚定而有力。在这两个阶段的角色塑造中,演员根据剧情信息的不断调整,在规定情境中做出了符合角色社会身份的真实行为,在无形之中饱和了角色的性格,也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替父从军前后木兰的成长和变化。通过演员不断自我校正,将花木兰这个人物角色高度立体展现了出来,将整个舞蹈表演作品进行了充实和升华。
二、传入输出信息,形成反馈环路
罗伯特·科恩谈到控制论简单地将外界对系统的影响概括为“输入”,而将系统对外界的影响概括为“输出”,由控制系统所发出的和接收到的信息叫作“反馈”。控制系统输出的信息作用于被控制对象后,不断地反馈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最终完成全部控制,无论在生理的层次上和心理的层次上,控制论和反馈已大量运用于对人类的研究。科恩认为反馈基本上是一个不断输送和接收信息的过程,它是一种交流形式,在这种交流中,得出了我们所应遵循的行为。
在舞蹈表演过程,这种无数次的反馈形成了无数次的反馈环路,大致归纳为三方面的主要环路:①舞蹈技能环路;②角色情感环路;③与对手交流的环路以及其他环路(如音乐、舞美等)。其实舞蹈表演就相当于规定了一个情境,只要角色处于情境当中,情境对角色就会有要求和规范,同时角色自身也成为情境的一部分。舞蹈表演和人类的任何创造行为一样,都是以创造主体的心理活动为基础,在角色塑造的过程需要多种要素构成心理运动,牵涉到认知、记忆、情感、理智、想象、直觉、才能、悟性等要素来支配身体表现力,只有靠这些要素构成的综合心理运动形成反馈环路,演员才能更好地支配肢体表情,面目表情,舞蹈语言表情,达到规定情境中的热情与真实。同时规定情境也会给角色输入信息,演员就会在塑造角色的过程根据内部反馈环路和外部反馈环路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将信息输出给其他角色和观众,形成循环不断的情感环路,呈现最好的表演效果。
舞剧《花木兰》将这一女性角色的情感、意志、坚韧等内在张力进行诠释,使观众可以解读到剧中女性角色所处的特定人物关系与人设境遇。如花木兰这一人物角色在出征前的几个舞段,则是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着不同思绪和心理状态。
特别是在父亲老态龙钟,多次开弓不济,而国家又在危难之际的这一情境下,作为女儿,花木兰清楚地明白父亲因年岁已高无法出征,演员通过自我心理活动形成反馈环路,然后根据与家人之间的爱与不舍形成角色情感环路,最后通过反馈进行调整,毅然选择替父从军,参与到保家卫国的队伍中去。在故事情境的变化和推进中,演员接收信息再传输信息,形成反馈环路,完成了角色的个性塑造和情感表达,同时作品背后矗立的人物精神也在舞蹈表演中得以强化,从而放射出花木兰极为朴素的角色魅力和极其伟大的家国情怀。
三、意图来自未来,以结果分析行为
罗伯特·科恩认为控制论既然是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反馈来自未来而非过去,那么它对演员来说是一种分析角色的最好方法。
他用一幅画(图1)来举例说明:一个男人由于狗熊的追赶正在往一个带有门的房子奔跑。这时“狗熊”是“起因”,“逃跑”是结果,如果我们是那个正在逃跑的男人,肯定想的是我正在往一个安全的地点跑,并不会想狗熊怎么碰巧在那,只会集中精力思考怎样安全跑到门口,怎样打开门,万一门打不开又该怎么办等等问题。

图1 “动力”与“意图”(图片来源:《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由此可见,这个男人是在向前看,在那一刹那,他想象着有可能实现的和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捕捉能帮助他实现意图的任何信息。
所以角色是被所想象的预期结果拉着走的,那么在塑造角色时,演员必须清楚地懂得,动力和意图绝不是同义语,实际上它们是恰恰相反的两种观点。两者都是解释行为的,但“动力”是来自过去的观点,而“意图”则来自未来的观点。“为了什么”问的是未来,要求的是一种预期的结果。“你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意指“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预期的结果你才做这件事?”而“为什么”则与过去有关,“你为什么做这件事”要回答先前的动力和原因。对演员来讲,通过这个分析途径可以从理解一个角色过渡到扮演那个角色,从而进入到角色的思想。
有三个关键的提示将会使演员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一过渡上:
第一,寻找你的角色行为的目的,而不要寻找你的角色行为的起因;
第二,不要问“为什么。”而要问“为了什么?”;
第三,角色要被未来“拉着”走,不要被过去“推着”走。
舞剧《花木兰》中,关于木兰这一角色的出征有两个意图,第一阶段是为了维护家庭、守护亲人决定替父从军,此时,演员进入角色的思想应该围绕着个人情感,塑造出对家人的不舍、牵挂与爱。第二阶段将木兰的成长历程与情感经历相互有机的交织打通,凸显角色丰富的内心世界,此时角色思想从“为了家庭”进阶成“为了国家”,将亲情与爱国情怀化二为一。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一位勇敢机智、坚韧不拔、有情有爱、有血有肉的角色形象,塑造出由儿女亲情升华至为家、为国的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角色内心,彰显了从平民成长为英雄的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花木兰这一角色所演绎的内容,也是许多其他战士的心路历程,她坚定为国而战的决心也是许多战士心境转变的缩影,通过剧中角色的目的就会清晰地明白为何战士们都拥有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无法抗拒的英雄气概。
四、相互关系交流,塑造多层次表演
罗伯特·科恩认为表演角色的情境意味着同另外一些人在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就是沿着一条反馈环路在进行,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呼吸、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形体动作都在传递着意义。可见行为是一种交流过程,在表演中,演员与同台演员们的交流正是剧本中角色之间的相互交流。由于交流是个持续不断的、正在发展的事件,所以可以说相互关系交流是一个持续不断重新规定一种相互关系的过程。“潜台词”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的一个术语,它涉及了相互关系的交流,但是也涉及了许多别的东西;“潜台词”,从字面上看意思是指“台词下边的”或“几段台词之间”的东西,然而,相互关系交流既可通过台词,也可通过潜台词来进行,并且它还可以完全不考虑台词。
相互关系的交流并不只限于说话者,我们所有的动作几乎都是交流,或者说,至少它们具有交流的功能。比如对人微笑、用某种步态走路、皱眉蹙额、扬起眉毛、抿嘴笑、点头等等,为的是向某人传递某种信息,抑或是反复练习怎样向某人传递某种信息。这一切交流联系其实都是“有目的的”,不管它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大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去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交流和相互作用,两者都是正在不断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单一的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时,就会出现一个反馈环路,当这个环路存在时,相互作用和交流无论在意识层上和无意识层上都是持续不断的。
那么在舞蹈表演的角色塑造中,演员与角色、角色与角色、角色与观众、观众与演员之间等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进行交流,再通过交流输入传出信息,演员根据信息形成反馈环路从而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呈现出多层次的表演效果。
舞剧《花木兰》中角色的思想、性格、情感等都塑造得格外鲜明,同时许多角色与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交流也使得观众共情。
例如,第一幕中,在极富人间烟火的田园气息中,演员用民间舞跳踢步融入芭蕾等腿部动作,将中国古代大家闺秀的灵巧乖闲和美貌娇姿,儿童纯真欢乐的表情、灵动俏皮的眼神,以及情境意态中的婀娜舞姿和百般灵巧,表现得惟妙惟肖。
在这个过程中演员以角色的思想去感知周围,演员与角色进行了交流,充分展现了花木兰孩童时期天真烂漫的样貌。而后木兰与父母一起喝茶,给父亲捶肩,向母亲撒娇等角色与角色间的相互关系交流输出给观众,观众的反应再反馈给演员,这种反馈环路可以使演员在之后的角色塑造中进行更加有效的构思。
包括舞剧尾声部分,花木兰与战友们共同杀敌,将军为保护木兰不幸中箭,两人相互支撑着,互相搀扶着,最终花木兰用将军递来的弓,击败了敌军。此时悲壮的音乐生动刻画了高尚家国情怀的战士角色,最后的赞歌将战士们的爱国精神冉冉上升到云端,又融进每一位观众的心底。在丰满花木兰这位女性英雄角色的同时,对于角色与角色之间心理、情感空间的相互关系交流更彰显出“英雄”的崇高感,多方关系之间不断相互交流,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角色,使舞蹈作品更有思想内涵和感染力。
五、结语
如今我们都处于信息高速运转传播的时代,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智能工具深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许人们认为这些高科技与表演艺术并无关系。
但如果我们脱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或是挣脱其他什么表演体系的束缚,把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高科技原理与表演活动进行对接时,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很多内容也会豁然开朗。罗伯特·科恩深层探讨了有关控制与反馈的原理,将这些内容运用于表演艺术之中,这对于演员分析构思角色来说,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角色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在近十年的芭蕾创编中,无论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敦煌》《红楼梦》,还是辽宁芭蕾舞团的《铁人》《花木兰》,抑或是苏州芭蕾舞团的《西施》《唐寅》,以及上海芭蕾舞团、重庆芭蕾舞团和广州芭蕾舞团等,都体现了各自“独特性”追求,而这种“独特性”追求无疑是形成未来中国芭蕾风格的重要前提。在急需建构中国芭蕾学派、求索中国芭蕾道路的当下,分析研究中国芭蕾舞剧表演中的角色塑造十分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戏剧理论中能够解释舞蹈表演现象的内容进行研究,从而分析舞蹈表演中角色塑造的原理,进一步拓宽舞蹈表演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