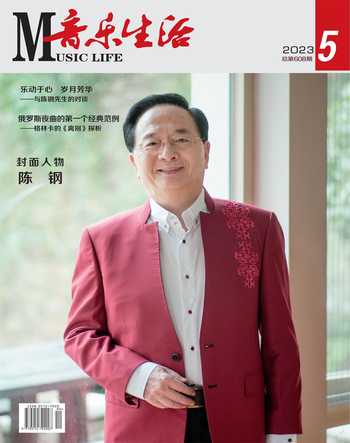琴声虽可状 琴意谁可听
2023-06-10章怡雯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浩瀚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古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獨特文化符号之一,它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乐器,绵延千年,亘古未绝。古琴作为一个乐器而言,现存三千多首古曲,音乐遗产极为丰富。而更为奇特的文化现象是,在中国历史上,古琴的主要传承群体并非专门的音乐人士,而是以文人雅士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精英群体。几乎历史上所有文化名人都爱好古琴,孔子、嵇康、欧阳修、朱熹、陶渊明……历代的文人墨客多以古琴为生命之所寄,留下了无数与古琴相关的人文逸事和历史记载。所谓“士无故不彻琴瑟”“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君子以琴书自娱”。古琴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已与传承文化历史使命的“书籍”具有同等的地位。放眼世界音乐文化史,中国古琴历史之悠久、文化内涵之深厚、历史文献之丰富、绵延之久远、承载文化功能之多样,实未能有与之相提并论者。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古琴于2003年11月7日被列入联合国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古琴艺术在我国开始全面复兴,古琴学会、琴馆、琴社等团体和机构纷纷成立,学习古琴、喜爱古琴、研究古琴的人越来越多,使古琴的社会认知度和普及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绝大多数古琴演奏和教学还是单纯地把古琴作为一个普通的演奏乐器,主要关注音乐表演本体的内容,如指法、强弱、起伏、顿挫、音色、内容、节奏、节拍等,对于古琴艺术中蕴含的深厚博大的文化传统的挖掘至为缺失,导致古琴艺术在弘扬民族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培养人文素养、修为自我品格等方面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以为,古琴文化内涵挖掘和传承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一、古琴之创制文化
有关古琴的创制,在《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中有伏羲、神农、皇帝等“削桐为琴、绳丝为弦”的记述 ,传说是由历史上的这些上古圣人明君创制,非同凡器。古琴的创制之理,包含了古人对天地万物法理的认识和寄托。朱长文《琴史》中说:“圣人之制器也,必有象,观其象则意存乎中矣。”[1]在古琴的形制里,每一处都有象征的意义:琴面圆形,象征天;琴底方形,象征地;琴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琴徽十三个,十二徽分别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而居中最大之徽代表闰月;琴宽六寸,象征六合;琴尾四寸,象征四时;前广后狭,象征尊卑;舜作五弦,内合五行,金、木、水、火、土,外合五音,宫、商、角、徵、羽,象征君、臣、民、事、物五种社会等级;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以合君臣之序;周文王加一弦,称“少宫”,周武王又加一弦,称“少商”,和前五弦合起来象征七星。琴身各个部件的命名也很有讲究,琴面上的“岳山”,象征崇山峻岭,可以兴风起雨;琴腹之“龙池”“凤沼”如江河大泽,可以海纳百川;“雁足”象征凤凰来仪;而琴额、琴颈、琴肩、琴腰、琴尾的称谓则更是把古琴视为有生命有灵性的乐器……仅是古琴创制的外表,就蕴含了古人对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社会人文的种种奥妙与意象,是古人认识论中天地宇宙观的缩影,古琴实为天地之灵物也,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厚的人文内涵。
二、古琴之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想。儒家是入世的哲学,认为人生面对种种现实的问题时,要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来灵活处理各种事项。首先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集体性和团结性,提出“仁”这个观念,同时更注重人伦,即重视家族血统和尊卑关系,而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儒家的观点看来,好的艺术具有助于教化人伦的现实人生作用,艺术中首要的是“善”,美只是第二位的,所以《乐记》中才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说,德是精神的追求,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艺术才能达到“至上之境”。对艺术的评价是要放在“仁”的内涵中进行,因此特别注重“中正、平和、庄严、温厚”等观念。“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汉·《白虎通》)古琴作为承担“禁止于邪,以正人心”的道德工具,其音乐已入中正平和之境,“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汉·《琴操》)这种观念在古琴音乐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曲式类型。传统古琴曲式类型分为畅、引、操、弄四大类。这些曲式类型并不是如西方音乐曲式概念以乐曲段落结构不同分类,而是以乐曲所表达的内容来区分。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特质,以期用音乐来成就完美的人格,因此古琴曲大多数是抒情淡雅的文曲,而激烈澎湃的武曲很少。“畅”是兼济天下的和畅之乐,其意为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如天人共畅的《神人畅》;“引”犹如诗歌之兴,应物起兴,大部分为个人遣兴之作,如《思归引》;“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操守,如君子之慎独,君子不欺于暗室等,其意为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如孔子赞叹兰花独茂其香而作的《猗兰操》;“弄”为性情和畅、抒写胸臆的抒情小品,如取意与雪,言雪清洁无尘之志的著名古琴曲《嵇氏四弄》之《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

二是,五声音阶。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特征是五声音阶的运用,有别于西方音乐的七声音阶。常用的五声音阶为宫、商、角、徵、羽。而(fa)和(si)的半音由于音响效果比较尖锐,不够和谐稳定则很少使用。因此,古琴曲也是这样,绝大部分都是以五声音阶作为旋律的主要骨干音,(fa)和(si)常在作为旋律的经过性、辅助性和装饰性的乐句中使用。以五声音阶创作的音乐听起来平稳抒情,音响效果和谐统一,而(fa)和(si)的半音音色不稳定,给人以不和谐、阴郁、怪异的感觉,为标榜正统的儒家文化所排斥。
三、古琴之道家文化
儒家和道家,一个倡导“有为”,另一个倡导“无为”,或者说一个是让人“入世”,一个是让人“超世”,是中华传统哲学的两大主要流派,千百年来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脊梁。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中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本法则,天地万物各不相同,气象万千,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道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无为”“道法自然”,崇尚顺应自然,提倡遵循客观规律,强调无为而治。道家文化在音乐上的理念主要是追求音乐的质朴、简约、超脱、空灵,最高的音乐理想是“大音希声”“无乐而乐”。道家文化观念在古琴音乐中的体现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琴曲中有大量体现崇尚自然山水和超脱现实等道家思想的曲目。此類歌颂大自然生活的琴曲有《樵歌》《渔歌》《渔樵问答》《山居吟》《醉渔唱晚》《流水》等,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纵情于山水,追求怡然自适、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是反映了在专制政府的压制之下或对于现实不满而隐匿超然于世外桃源的士人风骨。此类乐曲有《广寒游》《逍遥游》《羽化登仙》《列子御风》《八极游》《庄周梦蝶》等。再有一类是体现道家无为而治、注重自我修养等思想的古琴曲,如《玄默》《招隐》《坐忘》《鸥鹭忘机》《静观吟》等。
二是,追求清微淡远、虚实相间的音乐风格。从精神层面来说,虚是神,实是形;虚是我,实是物;虚是情,实是理,二者不可分割。虚代表无限,实代表有限,艺术中运用虚实手法,目的在于希望能从有限通向无限,寓无限于有限之中,从而达到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中国音乐尤其是古琴音乐强调“韵味”,古琴演奏中所谓“韵”,实际来自于左手的滑音和延长后的余音,属虚音,主要通过古琴的“吟猱”指法来演奏。古琴左手丰富的作韵技法形成了琴乐中独特的疏空的结构和变化无穷的运腔,表现了疏朗的空灵和阴柔之美。中国传统艺术强调留白的重要性,利用留白处使气韵生动,意在于尽量用越少的外在物质来表现越多的精神意境,使留白处成为欣赏者精神自由畅想之所,给人以意犹未尽、耐人寻味的美好期待,即道家之“无为而为”思想的体现。吟猱通过力度、速度、幅度的变化,改变了旋律音线的震动形态,使音乐线条产生了明暗、虚实的变化,产生隐约飘逸、淡雅优美的音乐魅力。
四、古琴之佛家文化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入世”,道家文化是“超世”,那么佛家文化就是“出世”。佛家的观念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充满名利情欲诱惑的滚滚红尘世界,另一个是无欲无求的生命本真世界。佛家认为在尘世中,人被先天的情欲和后天的物质追求所桎梏,忘了人性原本纯真的一面。人生一切的痛苦都来自于情欲,情使人留恋,欲使人起贪念,情和欲不能得到满足时便感到痛苦。佛家就是希望把人们从这个尘世中挽救出去,回归到无欲无求的生命的真我初始状态,从而摆脱尘世的痛苦。明代著名琴学大师徐青山在《溪山琴况》之“雅况”中说:“惟真雅者不然,修其清静贞正,而籍琴以明心见性。”[2]“籍琴以明心见性”一语道出了古琴中的佛家思想。心性者,乃宇宙人生之真实,明心见性,乃生命之觉悟。古琴音乐清微淡远、庄重肃穆,听后使人庄严身心、内心平和,六根清净,与佛家道义颇为相合。传统琴人操琴前须沐浴、盥手、焚香、静虑,演奏时身体必须保持端正,目不斜视,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以外在的行为规范来达到内心的宁静一致,这过程与佛教的打坐、冥想进行佛教修行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琴书中对哪些场合适合弹琴,哪些不适合弹琴也作了规定,适合弹琴的场合包括: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而不宜弹琴的场合包括:风雷阴雨、日月交蚀、在法司中、在市廛、对夷狄、对俗子、对商贾、对娼妓、酒醉后、夜事后、毁形异服、腋气噪嗅、不盥手漱口、鼓动喧嚷。以上可见,古人认为只有在脱离尘俗的环境下,才能有平和、宁静的心境,方能奏出与意相合的美妙琴音。弹琴环境的选择与佛家庙宇的选择高度重叠,缘起于思想理念的一致性。从唐宋诗词中亦可知历代琴家中有众多佛教僧人,北宋有夷中、良玉、知白、义海、则全、照旷等著名琴僧。明代有空尘禅师之《枯木禅琴谱》,顾名思义,以三尺枯桐可与佛禅相通。清初心越禅师著有《东皋琴谱》,传入日本,影响甚巨。近代著名琴僧有大休和尚、月溪法师等。在古琴众多琴曲中,与佛教有关且广为琴家喜爱的琴曲是《普庵咒》。该曲使用了不少撮音,描写了庙宇里钟磬铙钹唱诵之声,节奏平稳、庄严肃穆、宁静意远,有古刹闻禅之效,听之使人身心俱静。
五、古琴之标题文化
中国文人士大夫强调借物咏志、有感而发,文章、诗歌、绘画、音乐等都是如此。郭楚望见天光云影,而作《潇湘水云》;屈原悲愤抑郁,而作《离骚》等,几乎每一首琴曲都有其创作的缘由。为了让听众方便了解乐曲的内容和思想情感,就加了各种文字性的标题来进行说明。在古琴的曲目中,绝大多数琴曲都有文字性标题,或说明乐曲的创作缘由、历史沿革;或解释乐曲的音乐内涵,极富诗意和文学性,有些甚至就是一首精美的诗歌。琴曲中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小标题和解题三种。篇幅较大的琴曲往往有总标题和各段落的小标题。总标题是琴曲内容的浓缩和概括,提示了作者总的内容和方向;各段落的小标题犹如长篇小说的章回目录,更详尽地向听众提供了明确的细节发展和更具体的音乐内容;解题则大部分是文学性的描述多于理论性的分析,点出乐曲的意趣所在,有些也会叙述琴曲创作的历史背景。如描述蔡文姬归汉的著名琴曲《大胡笳》,全曲和原诗均为十八段,在《神奇秘谱》中各段落小标题为:(1)红颜随掳;(2)万里重阳;(3)空悲弱质;(4)归梦去来;(5)草坐水宿;(6)正南看北斗;(7)竟夕无云;(8)星河廖落;(9)刺血写书;(10)怨胡天;(11)水冻草枯;(12)远使问姓名;(13)童稚牵衣;(14)飘零隔生死;(15)心意相尤;(16)平沙四顾;(17)白云起;(18)田园半芜。全曲哀怨凄凉,沉郁顿挫,《五知斋琴谱》解题为“篇中如诉如泣,如怨如慕,为古今之离别调也”[3]。这些标题都是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文字优美,极富文学性,与同时代的历史命运和文学形式紧密相连,在阐明乐曲的音乐内容、风格、美学思想的同时,也使得古琴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紧密相连,留下了鲜明的文学历史烙印。
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琴艺术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国传统音乐,古琴文化浩瀚无垠,博大精深。除上述几方面涉及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的最根本性文化内涵之外,还有更多的是琴学、琴论、琴艺、琴道、琴趣、琴曲、琴人、琴派、琴器等古琴本体文化,每一个方面都是价值巨大的古琴文化宝库。在古琴音乐逐渐为大众所欣赏、喜爱,日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寄托的当下,我们在古琴的宣传、推广等各种活动中,都要更加重视古琴文化的揭示、挖掘和引导。在古琴的教学和传承活动中,除了古琴演奏技法的练习和提高外,无论是古琴教师还是古琴学生,或者更多的古琴爱好者,都要了解和认识古琴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努力做到琴技与琴论、琴道等琴文化相得益彰,内外兼修,齐头并进。
“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这是欧阳修的千年之问,也是古琴艺术的当代之问。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古琴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宝藏,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为目标,将古琴深厚文化底蕴全方位融入到古琴演奏艺术中,使古老的中国古琴艺术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艺术魅力!
注释:
[1][宋]朱长文:《琴史》,中国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
[2][明]徐青山:《溪山琴况》,《琴曲集成》第十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3页。
[3]査阜西编撰:《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24页。
章怡雯 浙江音乐学院古琴教师
(责任编辑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