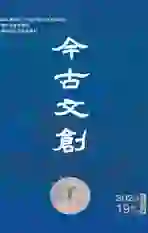《无名的裘德》中“小时光老人”异化特征解读
2023-06-09钟依伶
钟依伶
【摘要】 《无名的裘德》是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其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完成该著作后哈代便转向诗歌创作。在哈代笔下,主人公历经社会变革,在新旧思想冲突中饱受折磨,不同程度的异化特征在不同人物身上均有体现,本文旨在探讨分析小时光老人在文本中的异化特征,解读其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异化;小时光老人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9-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9.008
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的托马斯·哈代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哈代一生中笔耕不辍,自1865年发表处女作《我怎样为自己盖了一栋房子》以来,他创作了数十部长篇小说,作为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著作,《无名的裘德》与姊妹篇《德伯家的苔丝》共同构成了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中集大成者。“性格与环境”小说这一称呼来自哈代,他将《卡斯特桥市长》称作“性格人物”小说,将《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分为“灵”与“肉”人物,足以见哈代对其作品有着独特的写作意图[9]18。
哈代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名为“威塞克斯”的自然背景,在此背景中农村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逐渐受到资本经济的冲击,通过描绘自然风光与人物情节发展,哈代以独特的笔触展现了不同人物在19世纪英国社会的真实生活,探讨了人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哈代有关人物在道德、心理上的困境的思考引发了众多讨论,他对人物性格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也使得其也被广泛视作现实主义作家。然而首发于1895年的《无名的裘德》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着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品不同之处,即“异化”这一主题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无名的裘德》中小时光老人等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化特征,本文试图从“小时光老人”的异化特征出发,探讨《无名的裘德》中的异化主题,从而更深层次了解哈代对于人物性格与环境的理解,加深对该作品的理解。
一、自我异化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讲述了一对年轻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有力抨击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揭露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也展现了普通人物在面临压迫后的异化现象。异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之一,身处于高度物化的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异化给人以孤独感与被遗弃感[5]27。作为一个广受关注的概念,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alienus,在德语中被译介为entfremdung,该词最早出现于哲学和社会学概念中,指人与社会、组织或自我之间的疏离,异化也是现代生活的主要条件之一,时常作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作品中的中心主题之一出现[1]1。《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异化,以裘德为例,殷企平指出裘德身上存在着两种异化现象,分别以孤独感和异化劳动为特征[8]150。而小时光老人(后称时光)所展现的异化现象与裘德有着相似之处。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提出“选择的自主”,即人“由自己决定去要求”[7]587。萨特强调自由选择,倘若人不能按照个人意志选择,那么人与“自我”则会逐渐疏远,甚至失去“自我”,成为一个异化的形象,这种异化也即自我异化,体现为人物无法改变事物状况的无力感。前文提到,心理层面的社会断裂感、疏离感使得时光在面对外部环境压力时无能为力,然而在面对自我时亦是如此,时光的自我异化表现为他时常无法控制事件的走向,从而产生的深深无力感。在裘德与淑决定变卖家产带时光离开奥尔布里坎镇之际,淑一时心软放走了自己的鸽子后不禁感叹“互相屠杀,为什么必须是自然的法令!”[4]400因受世人所不容忍而不得不离开此地的事实对时光来说无疑是互相屠杀的自然法令的真实再现,他急切想从淑的口中得知这一法则的真相,而淑则在情绪激动的非理智状态下给出了肯定答案,这对于时光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一种无法控制事件的无力感盘桓在时光心头,为后文的悲剧做下了铺垫。
时光的自我异化还表现为一种“自我否定”,即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自毁的倾向。自离开奥尔布里坎镇后,裘德与淑带着时光辗转多年后重回基督寺,即使是天降大雨裘德仍坚持观看游行队伍,不顾淑多次提出寻找住处的请求,而后二人带着孩子四处碰壁被人拒之门外的经历催化了时光对于家境贫寒、孤苦无依的懊恼,无家可依的窘境加深了时光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和无力感,始终萦绕在时光心头的自毁倾向促使他向淑问道“待在这个世界上不如离开这个世界好,是不是?”此刻的淑并未意识到时光所处的自毁边缘,她以“差不多可以这样说”的消极的话回答时光的疑问,从而加剧了时光对毁灭生命的念头,他不由得情绪爆发向淑说道“我在澳洲,是那儿那些人的麻烦,在这儿,就又是这儿这些人的麻烦。我压根儿没出生就好了!”[4]432而淑对时光的回答是新孩子即将到来的现实,贫寒的窘境所带来的无力感使得时光认定这是毁灭的前兆,从而掀开了悲剧的序幕。正如萨特所表明:死亡即是自由的界限,也是自由的构成性要素[7]164。淑对于时光的回答使得他确信自身的存在是麻烦,而他对此的解决办法就是死亡,在萨特眼中,死亡构成了自由,时光的死亡即是他的自由选择。
二、心理异化
在杜克海姆有关社会调节和控制体系的区别的作品中,杜克海姆以“anomie”一词来指代社会层面的不正常状态,在心理层面这种不正常状态则被视为个人的主观体验,而Anthony Davids将异化定义为一种人格综合征,由自我中心、不信任、悲观、焦虑和怨恨组成[1]2。简言之,异化指人在面对困境时的焦虑不安、孤独绝望等体验。而在生活的压迫下,时光的心理层面的异化特征十分突出。例如,在时光初次登场的火车一幕中,当其他乘客都被小猫逗笑,时光想到“一切的笑,都是由于误解而来。天地间的事物,正确地看来,就没有一样可以使人发笑的”,面对火车乘务员的搭话,时光木讷地回答一声“啊”,在哈代的笔下,他是“老年的本体而硬装扮成童年的模样,但是装扮得并不好,所以時时由衣缝里露出了本相”[4]357。在裘德与淑的眼中,时光“喜欢不言不语地静坐”,他的脸“古怪、苍老”,带着“生硬死板”的样子,而他的眼睛总是盯着无实体的事物上,淑甚至将时光的脸比作迈尔帕米尼的悲剧面具——隶属于悲惨和恐怖[4]361。以常人的目光来审视时光的描述,未成年的孩子拥有年老的脸无疑是荒诞的,时光荒诞的矛盾形象正是异化在普通人身上的体现,描绘时光时,哈代并不像其他人物(如裘德、淑)那样进行细致入微的语言、心理描写,与其他人物相比,时光少了几分真实,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时光在情节发展中的突兀感、失真感,哈代以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失真的时光,显现了异化对人的巨大影响。
作为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黑格尔坚持“绝对者是精神”的唯心主义命题,绝对精神从绝对理念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成为对自身而言陌生的他者,从而认出自身的存在便是异化的过程[6]34-35。在这一从自身到他者的过程中,人物必然会经历孤独感,作品中的人物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孤独感:时光儿童时期缺失家庭关爱,最终选择杀死弟弟妹妹后自杀,其一生无疑是孤独的。始终存在着的孤独感使时光和他人、社会之间无法融为一体。自出生起,时光被母亲丢弃,被外祖父嫌弃,这显然让他明白自己是不受欢迎的。而在初次与裘德、淑的见面中,淑看着时光与裘德相似的外貌便心生嫉妒转身离开,目睹这一幕的时光从此更加深了“他便是不受欢迎的孩子”的印象。而在学校里,时光同样受到了同龄人的孤立——别的孩子问他的父母、说他的闲话,而裘德与淑对此的补救使得一家人更不为他人所容忍,时光的孤独感在环境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下一步步加剧。
被家庭、社会孤立所带来的孤独感逐渐造成时光的文化疏离现象,即Seeman所提出的异化形式——“拒绝社会中普遍持有的价值观念”[2]93-94。同裘德夫妇二人在展览会上参观时,时光仍旧对一切漠不关心,没有一样能引起他的兴趣,面对淑喜爱万分的鲜花,他只能失落地想到鲜花枯萎的样子。当裘德带领一家人重回基督寺后,裘德仍对基督寺念念不忘,天降大雨也没能熄灭裘德观看纪念日的热情,而与一心将基督寺奉为“圣地”的裘德不同,时光眼中的基督寺更像牢笼,他问裘德“那些大楼都是监狱吗”,更表达了自己不愿在基督寺学习的观点,从这可窥见时光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此处既是时光对基督寺的点评,同时也是哈代对宗教的怀疑态度,这无疑是哈代极具批评意识的观点之一。时光对婚姻制度的观念也是不同寻常的,在裘德与淑成婚的前夜,“一种低微的声音,从壁炉旁的暗处慢腾腾地发出,好像从地里发出来一样。‘要是我是你,妈,我就不和爸爸结婚!” [4]365第一次见到淑,时光询问淑是否真是他的母亲,因为淑看起来深爱裘德,裘德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一对受到法律所约束和保护的夫妇不应该彼此相爱,足以证明时光的观点与众不同。
三、劳动异化
以异化劳动为特征的异化则是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改造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人在社会中首先与他的劳动相分离,其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人与社会产生断裂,此时的人便可称作异化的人,人不再是完整的概念,而是“抽象物”——孤立于社会整体的因素[3]164。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迅速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冲击着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文中哈代写道,“许多房上开着窗户的草房都铲平了,许多长在绿草地上的大树也都伐倒了;除此之外,原来那个有驼背房脊、木头尖阁和古怪隅栋的教堂,现在也拆掉了。”[4]6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使主人公身处于高度物化的世界,人的劳动及劳动成果不受自身控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使人与人、社会甚至自我相割离,金钱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之一。
劳动异化的后果之一便是金钱作为劳动的产物反过来控制住劳动的所有人,无论是艾拉贝拉还是她的父母,劳动异化对他们的影响也间接深刻地影响着时光的生活。对于时光来说,金钱是他一生中所历经的磨难的关键因素。艾拉贝拉远赴澳大利亚后生下时光便将其扔给自己的父母抚养,因为他显然是艾拉贝拉寻找新的婚姻路上的绊脚石。婚姻对艾拉贝拉意味着财富,她与裘德的两次婚姻都建立在艾拉贝拉追求金钱的基础上,艾拉贝拉两次选择裘德皆是为了他所能为她带来的财富,为的是裘德“有赚钱的精力,决不愁给她买不起衣服和帽子”[4]70。而艾拉贝拉的父亲也将金钱看得比自己的女儿更重要,他将艾拉贝拉视作包袱,急于将她嫁出去,称裘德与艾拉贝拉间的交往为“情人之间搞对象”。在外祖父母的家中,时光从未体验过被爱,外祖父母视他为累赘,仅仅是为了节约钱财便不给时光进行洗礼,当被裘德问起他的名字,时光回答“小时光老人。他们老这样叫我。这是个外号。”[4]361“无名”的状态时刻提醒着时光——他的存在对他人来说是累赘。在时光与裘德夫妇二人生活的日子里,“活人的秘密”如同“死人的丑闻”,街邻的漠视和鄙夷以及经济上的困难迫使时光不得不跟随裘德夫妇离开此地,在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时光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最后与淑一块在肯尼特桥镇上摆点心摊,而时光每每都得在火车站叫卖点心,但是劳动并未给时光带来物质上的富足,反而使他对于金钱有着更深刻的执念,当淑告知时光家中经济状况时,他终于感到经济上的窘迫几乎压垮自己,从而选择了死亡。总体来看,时光的异化劳动不仅没有改善他的生活状况,反而加深了时光物质生活的困窘,最终导致了时光最后的自杀之举,可见物化社会所带来的异化劳动是时光自杀悲剧的根源之一。
四、结语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创造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特征,使得《无名的裘德》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品有着不同之处。该作品中人物的异化特征与哈代本人所拥有的敏锐作家意识和所处时代是分不开的。作为横跨两个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哈代的独特创作意识使得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世纪之交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扭曲和异化现象。哈代通过《无名的裘德》展现了19世纪英国现实社会对人的扭曲和压抑。主人公们在不同程度的异化过程中不是走向死亡就是皈依宗教,尤其是时光这一独特人物,他时常思考自己是存在还是毁灭,被社会和他人排斥、拒绝的感受和无法改变生活困境的无力感几乎贯穿时光短暂的一生,时光精神上的异化是新时代来临时人类的典型精神特征。时光身上的异化特征从多方面向读者们展现了异化对人毁灭性的影响,心理异化将人置于精神孤岛之中,而自我异化则将人与“自我”疏离,人由此彻底游离于社会整体之外,而劳动异化则使得人在物质社会中也难以生存,物质与精神的异化共同造成了人的死亡悲剧。时光的悲剧反映了物化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是异化的必然结果。通过书写裘德、淑和时光等人的生活,哈代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工业发展对人的压迫,也展现了作品中的异化特征。本文从异化出发,解读了小时光老人的异化特征,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对该作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
[1]Barakat,Halim.“A Process of Encounter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0,no.1,1969,pp.1-10.
[2]Seeman,Melvin.“Alienation Stud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1975,pp.91-123.
[3]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M].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托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6]大卫·E·科珀.存在主义[M].孙小玲,郑剑文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7]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8]殷企平.《无名的裘德》的异化主题[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4):150-156.
[9]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