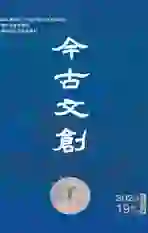精神分析批评视阈下的苏轼《前赤壁赋》文本解读
2023-06-09杜秋蓉
【摘要】 苏轼的《前赤壁赋》是一篇千古美文,写出了苏东坡对于天地、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的思考,文章事理结合、情景交融,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本文采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精神分析法,从“本我”“自我”“超我”的角度,对《前赤壁赋》一文进行解读和赏析,力求挖掘苏东坡情感起伏变化背后的深层次根源。
【关键词】情感变化;精神人格;本我、自我、超我;主客一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9-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9.003
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夜,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近三年的苏轼前往赤壁矶,面临浩浩大江和皎皎明月,感物抒怀,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一传诵万古的散文名篇。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历代文人对《前赤壁赋》的评价极高,他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文章进行了精辟独到的解析,得出了丰富多样且极具个性化的认识和结论。基于此,本文拟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其弟子荣格的精神分析这一文学批评方法,探寻苏轼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一、“蘇子”与“客”的关系问题
《前赤壁赋》出现了“苏子”和“客”这两个人物的一问一答,以对话的方式将各自的观点和情感表达出来,从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林语堂、康震等人所写的苏轼传记,都把《前赤壁赋》中的“客”看作是苏轼的好友道士杨世昌。而《教师教学用书》则认为“客”是虚指,与“苏子”构成苏轼的一体两面,主客问答、辩论,更便于表达苏轼的思想,同时这也符合赋体文的撰写体例。本文比较赞同的是《教师教学用书》的说法,虽然在文章当中,“苏子”和“客”是两个人,且各自表达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但这只是文章显性层面体现出来的信息;通过仔细、深入地剖析,便可发现文章中的“苏子”和“客”其实就是一个人,即苏轼本人,何以如此?
从文体形式上讲,“主客问答”这样的文体形式并非苏轼独创,中国古代的“赋体”文章基本上都有“主客问答”这一写作框架。如汉大赋的代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有“子虚先生”“乌有先生”“亡是公”之间的相互问答;标志汉赋正式形成的枚乘《七发》,其中就有“楚太子”和“吴客”之间的相互问答;魏晋时期曹植的代表作《洛神赋》中,有“余”和“御者”之间的相互问答;与苏轼同时期的欧阳修的《秋声赋》,其中也有“欧阳子”与“童子”之间的相互问答。在这一系列的“主客问答”中,“主”和“客”都不专指某个一人,都可以将其视作是作者在文中的自问自答。由此可见,苏轼《前赤壁赋》中的“苏子”和“客”也并不一定就指苏轼和他的好友两个人,从“主客问答”这一赋体特点上说,“苏子”与“客”就是苏轼本人,是苏轼这个人的“一体两面”。
从苏轼的创作背景分析,“苏子”与“客”正是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真实心情和两种人格极具冲突的写照。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写了《湖州谢上表》被诬上“诽谤朝廷”之罪并被押至监狱,险些问斩。后经多方救助,于当年十二月出狱,被贬为有名无实的黄州团练副使。这于正值壮年得志、春风得意的苏轼而言,“乌台诗案”不仅差点断送自己的性命,也使得“西北往,射天狼”壮志凌云迅速沉落下来。在狱中,他曾写诀别诗《别子由》: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手雌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在狱中阴风凄凄的夜里感到辗转难眠、胆战心惊。回忆自己短暂的一生,种种不幸使他痛苦无奈,于是向苏辙指明了自己的葬身之所——曾经为官的杭州。出狱后,他曾在一封写给好友的信中道: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也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由此可见,苏轼落魄后,亲朋好友对其唯恐避之不及,在黄州孤独闭塞的日子里,他的内心透露着无法消解的苦闷与寂寞。随后两年,他的心态逐渐趋于从容淡定。某天因山间遇雨,触发了苏轼的感慨: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竹杖芒鞋”摆脱了对“马”的依赖,反而觉得身心愉悦。“风雨”一语双关,作者在大自然的风雨中吟啸徐行、坦然处之,体现了苏轼面临人生风雨时超然物外,傲然不屈,不以外物萦怀的胸襟和气度。
苦闷和旷达两种心境,都是苏被轼贬黄州后内心的真实写照。《前赤壁赋》中“苏子”与“客”两种对立的状态和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客”之口抒发自己遭遇人生挫折后苦闷、矛盾的情感世界。他面对天地、大江、明月等自然景物的永恒,对比人类个体的渺小与虚无,发出了对功名仕途、人生短暂无常的叹息。但另一个超乎物外的精神人格,又引导着苏轼站在宇宙天地“变与不变”的视角,看到了“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有何羡乎……”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人格,其实就是苏轼内心另一个“我”对痛苦绝望的“我”的劝慰,“客喜而笑”标志着另一个“我”终于释怀。黎明的出现,仿佛“苏子”又回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起点,但实际上此时的他已经达到了此行赤壁的目的——实现了自我的蜕变,去到了超脱混沌、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之境界。
综上所述,“苏子”和“客”的两种对立的状态和观点,其实就是苏轼本人纠结、矛盾、挣扎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二、苏轼内心世界的“精神分析”
在《前赤壁赋》中,“苏子”与“客”的主客关系所流露出作者的多重人格,可以根据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将其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重境界,这样,从新的视角出发更有助于分析苏轼内心复杂的人格心理。
(一)苏轼内心世界的“本我”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精神结构的第一个层次是“本我”,所谓“本我”就是人的潜意识,它只受自然规则即人体生理规律的支配,满足于人最为原始的、本能的欲望,遵循“快乐原则”行事。主要就包含了人的欲望、器官的快感等内容。
在《前赤壁赋》一文中,第一段的描写体现的就是苏轼“本我”的彰显。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是夜,在浩瀚的夜空中,一轮明月在东山之巅缓缓上升,明净的月光与斗牛星辰交相辉映,寂静的大江之上,清风吹拂,水波不起,白茫茫的雾气笼罩弥漫着整个江面,水面和天际仿佛都融为一体。苏轼就是在赤壁的绝美雾景之下泛舟大江,游目骋怀,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他已然沉醉于眼前的景色,于是开始吟诵起《诗经·月出》的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俏兮。”这里将明月形容为身态曼妙的女子,并期待着她从远山处徐徐升起。“少焉,月出于东方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在苏轼的期盼下,月儿缓缓升起,温柔的月光照耀在江面,也照在苏轼身上,她久久不肯离去,似乎也对游人有着无限的眷恋……此情此景,使得苏轼心胸开阔、心驰神往,不由得“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仿佛自己乘坐小船在江中凌空驾风,随心所欲地遨游,这种飘摇游荡的感觉就像是自己生长出了一对羽翼,送他飞翔到远空中去。
显然,此時的苏轼是快乐的,美丽的自然景物刺激着东坡的眼、耳、鼻、舌、身等多重感官,使他暂时忘记了目前遭遇的所有痛苦。在这个美妙的夜晚,苏轼已然忘却了自我,与天地融为一体,达到了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苏轼精神结构中的“本我”占据了他的大脑,正在起绝对的支配作用。
(二)苏轼内心世界的“自我”
根据弗洛伊德学说,人的精神结构的第二层次便是“自我”,所谓“自我”就是指人的意识,它指引人们清醒地认识现实,并遵循“现实原则”行事,取代了在“本我”中无限制占据主要地位的“快乐原则”。当人们进入“自我”的精神结构后,人们就会调整自身,压抑“本我”,从而实现和社会的一致。也就是说,虽然人心中存在遵循“快乐原则”的趋向,但由于它会遭遇其他某些外力或者各种因素的限制,在自我生存的影响下,“现实原则”会取代“快乐原则”。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在短暂的欢愉和欣喜之后,苏轼也摆脱不了自身精神结构中“自我”的束缚,从“本我”向“自我”,在文章的第二段和第三段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段讲“苏子扣舷而歌之”,歌唱什么呢?“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意识中,“香草美人”中的“桂”“兰”谕旨诗人高尚的品德,“美人思念君王”暗示有才的贤臣君王的思恋和被赏识与重用的渴望。作为“苏子”人格精神的另一半的“客”当不会不懂这层的深意,所以“客倚歌而和之”,吹奏的洞箫声自然也就“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哀转久绝,催人泪下。
而在文章的第三段,“自我”意识体现得更加明显。“苏子”回忆起了赤壁大战中的曹操,遥想当年,曹孟德叱咤风云,野心勃勃,他率领庞大的水军船队想要横扫六合,鼎定乾坤。文章写道:“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不过,随后笔锋一转,“而令安在哉?”一句话道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苍凉。曹操这般雄才伟略,权倾朝野的人尚且成了历史的过去时,更何况此时被贬黄州、仕途坎坷的“我”呢?历史的沧桑感和现实的失意落寞,使“苏子”从“本我”的愉悦世界中苏醒过来,上升到“自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美长江之无穷。”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昙花一现;人,亦是浩渺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尘埃。这种“自我”意识使得“客”陷入以自身有限的生命主体,去面对恒定不变的山川、日月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自然的定数,生命的虚无感和对未来的茫然使得苏轼哀从心生,悲从胸来。
(三)苏轼内心世界的“超我”
按照精神分析学说,人的精神结构的第三个层次是“超我”,所谓“超我”就是指人理性化、道德化的自我。如果说“自我”是人与现实世界的统一,“超我”则是指人理性化、道德化的自我,其功能是监督和指导“自我”去管制“本我”的非理性冲动,它按照“理想原则”行事,其境界和层次比“自我”更高。
换言之,因为赤壁美景而沉醉的苏轼是处于“本我”状态中的,因为自身仕途的失意而感到悲哀的苏轼是处于“自我”状态的,这两种状态反映的都是苏轼内心非理性的冲动。而当进入到“超我”状态的苏轼,就不会再“因物而喜”,也再不会“以己而悲”了。那种感性的,情绪化的状态会被超我状态下的理智思维和冷静思考所战胜,从而使苏轼进入到一种新的生命境界。
这种“超我”的状态就集中表现在文章第四段。既然“自我”的意识使“客”陷入一种个人无法改变客观现实的痛苦与矛盾中,那么就换一个视角来审视问题。在这一段中,苏轼开始从“物”“我”合一的角度来探讨“大江”与“明月”。
首先,苏轼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做出了概括性的描述。文中的“苏子”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大江虽然流逝,但水还是水;月亮虽然有阴晴圆缺,但明月还是明月。同理,人世虽然历经沧桑,但历史的发展也仍然有规律可循。
接下来,“苏子”的言论极具辩证主义的色彩,他从“变”与“不变”的角度阐述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世的关系。“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如果人们从“绝对运动”的视角来观察世界,那么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中,既然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没有人能够把握得住变化的规律,那么生命的远逝、历史的沧桑又有何值得悲叹的呢?“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如果人们从“相对静止”的角度感悟生命,虽然世间万物的具体物质形态终会消亡,但同时它又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留存,因此人可以得到永生,那么人又何必羡慕“大江”与“明月”的永恒呢?
最后,“苏子”言:“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在他看来,自然风光是天地赐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个人的一时得失、祸福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显然,此时的苏轼已经超然俗物外,寄情山水间,进入超我之境了。
所以,当苏轼进入了“超我”的境界之后,他经过复杂而质朴、激烈而冷静的思考,清晰地认识到了生命的真谛,完成了自身精神世界的升华和洗礼,实现了从消极落寞的人生状态到释然旷达的华丽转变。
三、主客关系与三种人格的艺术融合
弗洛伊德的精神结构理论认为,一个人要保持自我的和谐关系,就必须调整自我、本我、超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陷入精神混乱的痛苦之中。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借用主客问答形式,调节了精神人格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呈现出精神人格与主客关系的高度融合的写作艺术。
这种融合同样体现在文章的第五段。既然从“变与不变”的角度来看,物与我都是一样的存在,那又有什么好羡慕的呢?不妨快意享受此时所领略到的明月与清风吧。于是,“客喜而笑,洗盏更酌”,一“喜”一“笑”,表明“客”终于从自我忧恨和怀抱封闭中解脱出来,“洗”去的是此前满怀愁绪时饮的残酒,更是苏轼内心矛盾痛苦的精神人格,旧有矛盾解决了,当然要重新痛饮一番了。
最后,文章以“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作为收束,引发了人们无限的遐想:遥远的天边渐渐地泛白,两位白衣仙人在江雾弥漫的小舟之上共枕酣眠……一时之间,已分不清谁是“苏子”,谁是“客”……黎明暗示着苏轼的新生,在实现“超我”之境的转变之后,他的人生看到了黑暗之后的曙光。至此,一场精神人格之间的殊死搏斗落下帷幕,苏轼内心世界中的三种人格回归和谐。
四、结语
统而言之,运用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方法,围绕苏轼内心世界中“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境界对苏轼的《前赤壁賦》进行剖析,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在泛舟时内心思想情感的变化与起伏,也符合精神分析法对于人格精神的三重划分。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这一视阈,发掘主客关系背后的苏轼精神人格的转化,便能更好地感悟这篇千古妙文的思想与主旨,体察苏轼微妙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陈日亮.如是我读[M].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朱志荣.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
[4]袁海军.赤壁赋情感的转换[J].课程教育研究,2012,(21).
[5]董鸥.悲喜皆因水月生——浅析《前赤壁赋》中苏轼情感产生的外环境[J].语文教学通讯,2008,(03).
[6]严爱军.高峰体验理论观照下的精神宴游——透视《前赤壁赋》中苏轼的情感特征[J].中学语文,2014,(16).
[7]陈群玉.源于大自然的人生启悟——苏轼《前赤壁赋》情感寻迹[J].语文学习,2017,(12).
作者简介:
杜秋蓉,女,汉族,四川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研究方向: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