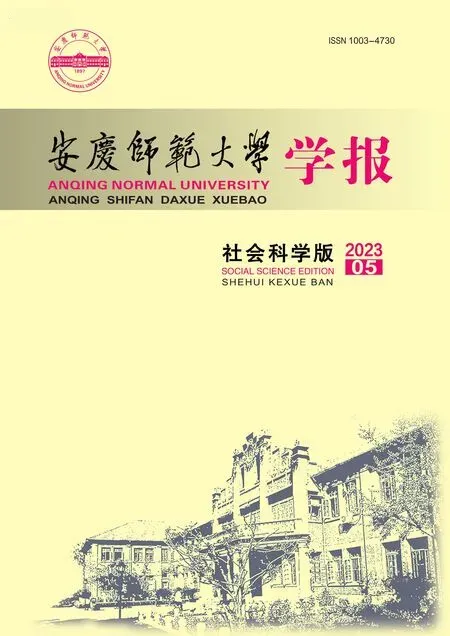方东树《书林扬觯》论
2023-06-07程蒙
程 蒙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方东树《书林扬觯》的价值久被忽略,清人或褒或贬,皆粗笔带过。典型如姚莹和皮锡瑞,前者以为:
植之尝为《汉学商兑》矣,以近世汉学诸贤妄毁宋儒且诬圣道,故力申考辨,而圣道以明。又尝为《书林扬觯》矣,以无识之人妄事著书,故详言古人不肯苟作与夫不得已而有作之旨。是二书者,可谓精于立言矣[1]311-312。
后者则说:
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2]。
近期有学者专题讨论《书林扬觯》之“建白”①参见史哲文《论方东树〈书林扬觯〉之“建白”》一文,此文从著述体例、行文态度、时代影响力等角度阐释《汉学商兑》与《书林扬觯》之关系,又博论方东树在此书中的“建白”,再以学术史的视野观照此书的价值,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和解读此书。,但也许囿于讨论重点和论证体系,还有很多重要问题尚未讨论,鉴于此,本文继续进行探索。
一、理念寻绎与体例选择
《书林扬觯》书承《汉学商兑》,《汉学商兑》是方东树担当卫道、奋力抗争汉学之作,尽管《书林扬觯》成书时间与其有接续性,但是两者著述理念已然有着明显区别,《汉学商兑》一书激愤斥责汉学家乱经叛道、挞伐汉学空疏无用、贬斥汉学家泥古株守,其目的是不遗余力捍卫程朱之道;而《书林扬觯》则门户之见较为和缓,彼时作者深刻洞察到时人轻事著述的弊端,又进一步从古今著述体例展开深入思考,着眼文事,旁征博引,有独到的识见。两书在著述体例的选择上相似却有不同,虽然均是先引用他人之言,再加以评论,但是《汉学商兑》中作者大多列举汉学诸家之言,紧随以按语形式加以批驳,接着阐明自己的观点;《书林扬觯》中先节选宋明理学鸿儒语录,在此基础上阐扬自己的主张,驳斥汉学家的言论虽散见其中,行文态度却偏于理性。作者选择语录加以立说或是对汉学家大力讥讽宋儒语录类著作的无声对抗,意图消解“语录不文”之病。
方氏在此书上卷主要阐述著书立论的宗旨和原则,针对当时学界存在只重考据、不重现实学风的状况提出质疑和批评,阐扬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作者在书中深刻表现出对其时学问与现实社会有着巨大断裂的担忧,以及对于世人轻易著书不良风气的劝诫。通过阐明著书之因、追溯著述源流、指摘时人轻事著书的现状及弊害等,多角度论证这一理念。关于著书缘起,方东树在卷上开篇有言:
两粤制府阮大司马既创建学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首以“学者愿著何书”策堂中学徒。余慨后世著书太易而多,殆于有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3]1。
陈澧亦云:
阮文达公总督两广时,桐城方植之客幕府,文达谓桐城人学问空疏(此语余闻之曾勉士先生),当时方必闻之。文达课学海堂士策问堂中人愿著何书,方遂著《书林扬觯》一书[4]。
事实上,方东树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赴粤东,道光四年(1824)和五年(1825)授经于阮元幕府,在此期间,方东树兼阅学海堂课文,可见此书一方面是为了学海堂的教学而著,另一方面则是方氏有志挽救乾嘉时期滥于著书学风的弊端,劝诫学者切勿轻事著述。
方东树追溯著书源流,又将真正经典著作分为圣人、贤人、儒人之书,强调其重要性如布帛菽粟,古今天下不可一日无,提出了“人当著书”的立论:一是著书须有宗旨。首先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放言高论、夸大自矜,在此基础上再追求言论恰当、可信、有用。由此引发“君子之言”的概念,即能够阐明事理、洞察是非。他说:
君子之言,如寒暑昼夜,布帛菽粟,无可疑,无可厌,天下万世信而用之,有丘山之利,无毫末之损。以此观古今作者,昭然若白黑矣[3]13。
二是著书要立意高远,言之有信,而后才能经久不衰。因此发出经典的论断:
学者著书,要当为日星,不可为浮云。浮云虽能障日星,蔽太清,而须臾变灭,倏归乌有。今日之浮云,非昔日之浮云也,古今相续不绝,要各自为其须臾耳,而日星虽暂为其所蔽,终古不改[3]13-14。
他慨叹世间为浮云者居多,深觉世人著书轻率以及随之产生的流弊,慷慨陈词地强调著书必须要有宗旨。
既然人当著书,而现实又存在轻事著书的流弊,其原因何在?方东树洞若观火,他分析世人轻易著书的重要原因,即急于求名,导致的结果是作品支离穿凿、错漏百出。方氏大力肯定和推崇古人先贤发愤著书的传统,坚信心志专一,才能精思深微。又从著书和传书两个维度加以观照,强调此两者都不可轻易为之,以免无知者道听途说、随意相传。无知者尚且无害,乱道妄说则会造成流传疑误,使得书未通行而先在人心中产生妨害。方氏极力主张要有独立思考、刻苦求学的过程,方能够领悟学问的真谛。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辩论学术的传统和作用不可小觑,但争辩的立足点应该是明是非、匡正义、救民众、行大道。其不耻近世学者因为显名而刻意辩驳以争胜的行径,遂引用吕叔简之语阐明当今学术风气:
而今讲学,非为明道,只是角胜[3]62。
方氏认为著书的重要作用在于阐释经典,他说:
著书说经,最是大业[3]67。
梳理古今书籍,讨论经的著作浩如烟海,义博旨深,古人作传注来解释经典,今人却假托经典来争辩传注,不顾经典的义理内涵而一味立论著书,对经典诠释越多,往往导致偏离经典所蕴含的大道越远,方氏由此批判汉儒过于重视考据训诂,反而错失其要。
作者在此书下卷重点强调著书体例的规范性与重要性。《语录著书》一章中方东树对汉学家讥讽宋儒以佛经语录形式发展宋学极为不满,他描绘此现状:
宋儒以来以语录著书,因于释氏,俚而不文,世争讥之[3]77。
方氏义正言辞为之辩白,他指出宋学家论道以语录传世,此传统上可追溯至孔子,以《论语》及圣人之道为标榜。又说:
语录诚不文,然当审别其所录之语为何如,不当论其迹也。若剿袭雷同,肤剩浅近,虽文之如子云,亦无取。若是言言心得,质之先圣而无疑,俟之后圣而不惑,虽谚何伤[3]78-79?
一方面他认为语言俚俗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只要内容精当深刻,表达形式其实无伤大雅,但也表明不能过于俚俗。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著书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是否真有所得,语言上的通达明晓实则有助于道的传扬。接下来的《说部著书》一章又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指出:
著书为文,好承用古字句,此最为陋恶[3]84。
承袭古字句并不等同于真实可信,方氏对于汉学家考据的标准与可信度提出质疑:
近世汉学考证家好引杂说以证经,辄言其时去古未远,或其人相及,其地相近,执此以为确据,而不知事之有无当断之以理,不在年代之近远,人地之亲疏。世固有子孙言其父祖,弟子言其先师,错谬失实者多矣,安在时、地、人相近而即可信乎[3]85-86?
其认为说部对于考据而言不可轻信,从而以此诘问汉学。
方氏对于著作的凡例别有强调,他说:
凡著书欲先定凡例,凡例既定,其书乃有条理可观,虽商榷长短存乎其人,以视伧俗妄作陋恶不辨体裁者有异矣[3]89。
首先指出后世著书取法经典,以其体例为依据,又随时代的变化做出相应改变。他说:
律生于礼,盖是事物当然之用,例亦犹是也,可以义起,而后人著书,必云用某家某书例,依于古人,述而不作,取尔雅也[3]89。
其次提出“例生于义”的主张,指出凡例的定立不得与文章大义相违背,否则便是以凡例作为个人任臆诠释文章的工具。再次归纳出具体细微的的条目与准则,如“著书大例在先,细例在后”“著书不言名称氏”“著书不避家讳”“著书文字有当跳行另起处”等。最后尤其强调严格规范引用体例:一是要凡引必注,他引用《日知录》之语来表明这一观点:
《日知录》云:“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则两引之,不可袭为己说”[3]97。
二是凡引用前人之言,必定要引原文,切忌改窜杜撰、纰缪陋妄,三是规正注释体例,应当引用原初文献,且需注明作者书名、某篇某卷,以便检校。除此之外,方氏关注到近世伪书泛滥,由此引发对校雠与版本的阐述:
校雠者,两本相对,覆校如雠[3]99-100。
编定论次,今则兼须辨别板本缮刻之异同得失,固非浅闻末学所及也[3]100。
综上可知,方氏高度重视著书旨趣和体例,文本立足点在于著书立论,批驳当时轻事著述的学术风气,明正学人何以著书、如何著书,他提出的著书必有宗旨、著书不贵多、著书不足重、著书伤物等主张操作性强,对学人的审美认识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都有重要启发。
二、价值取向与文学审美
此书不仅彰显方东树在著书之法上有独特识见与深入思考,字里行间又充溢着作者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正如管同在题辞中所说:
所论虽专为著书而发,实则穷理格物、行己立身之道悉贯乎其中。学之不讲久矣,读植之书,如在齐闻《韶》也[3]题辞。
姚莹亦有相似评价:
心平论笃,识精指微,洵卫道之干城,救时之药石。事关千古,岂徒启蒙发秘而已[3]题辞?
桐城派文人致力于将理学与经世、事功紧密联系,展现出鲜明的实学济世思想与修齐治平的人生主张。姚莹说:
夫志士立身,有为成名,有为天下,唯孔孟之徒道能一贯[1]233。
刘开用一生实际行动践行了
负大志,区画世务,体明用达[1]107。
一为朝廷重臣,一为布衣,但他们的经世主张高度相合。方东树在此书中也反复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其有言:
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3]113。
可见他讲求独善兼美、重视经明行修,认为士人君子肩负道德重建与济世匡时的双重重任。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们的经世思想不仅只限于口头和书面上的表达,而且在个人经世实践中取得卓著成效,如姚莹在经济和边疆史地、“夷情”防务研究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方东树强调文必关乎实政,深刻认识到著书应当有实用价值。他说:
君子先务为急,本末先后,要自有不可倒者。如典章名物固是实学,若施于时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禄田、考工、车制等,不知何用,则又不如空谈义理犹切身心也[3]32。
作者推崇古人将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当作著述的首要目的,恰如孔子所重“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在理性省思基础上创作了《读禹贡》《治河书》《劝戒食鸦片文》《化民正俗对》等救时济世之作。
方东树有意将文章与著书相区别,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说:
文章与著书相等而不同。文士以修词为美,著书以立意为宗[3]101。
又有
古人有言:“文士如漆,虽无质干,而光泽可爱。”吾以为文士如凤麐,虽不常见,而于世无损,亦唯盛世而始见之。何义门云:“名士如珠玉象犀,初无用而不可少。”此亦如谢玄“芝兰玉树”之意耳[3]101。
由此可见,方氏认为以审美为目的的文章与以实用为目的的文章不同,他极力肯定追求审美为目的的文章之美,且引用欧阳修、谢玄、何义门等名家之言来阐明此类文章可贵难求。方氏深具洞见的文学审美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文的创作与发展,也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构提供新的活力。
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方氏提出著书作文,贵有新意,不可陈陈相因。其言:
凡著书及为文,古人已言之,则我不可再说;人人能言之,则我不屑雷同。必发一种精意,为前人所未发,时人所未解;必撰一番新辞,为前人所未道,时人所不能。故曰“唯古于词必己出”,而又实从古人之文神明变化而出,不同杜撰。故曰“领略古法生新奇”。若人云亦云,何赖于我[3]104?
又结合自身创作体验说:
维瘠思善,有获必新。理本大同,心有先得。削其雷同,务绝剿说[3]109-110。
此论极其透辟。在此基础上方东树又进一步提出著书为文应追求言简意深,含蓄蕴藉而余意未尽。综观方东树的诗学观和古文观,崇古和求新的立场始终是并行不悖的。方氏大力提倡学古而自成面目,他说:
历城周编修书昌论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世人坐先不能真信好古,不知其深妙而思取法,唯以面目相袭,浮浅雷同,何况于变[5]。
又强调:
凡吾所论文,每与时人相反,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方其专思壹虑也,崇之无与为对,信之无与为惑,务之无与为先;扫群议,遗毁誉,强植不可回也,贪欲不可已也。及乎议论既工,比兴既得,格律音响即肖,而犹若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无愧也。于是委蛇放舍,绵绵不勤,舒迟黯会,时忽冥遇,久之乃益得乎古人之精神,而有以周知其变态[6]。
可见他提倡创作主体善于学习古人,从经典中寻求理论资源,但极力反对因袭前贤,要求言必己出,求变出新。他总结出文章创作的要义,即风格应似人面而各有不同。行文创作可以摹仿和汲取古人文章的精妙之处,但须得展现自己的独特感受与寄托。倘若文章一经写成,雷同百家,全然不见作者之真面相,此文章便无足轻重。
方东树的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实践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他从文章的实用价值出发,大力主张文事要适应现实需要,充分发挥文辞言弊救世的功用。他强调文无古今,学者文人不仅是以此修身养性,更要通达世务,为文思想是探求实理,寻绎社会及事物发展规律,使学术成为于民生有利的实学。他说:
天下皆言学,而学之本事益亡。本事者何?修己治人之方是已。舍是以为学,非圣贤之学矣。古者修己之学,学处贫贱而已,学处患难而已,学处富贵而已,学处死生而已[7]。
他着力提倡为文写作需揭示其时之弊,明正治世之道,以救裨当世。另一方面又以审美价值观照文学,强调文学作品存在的独特内质同样重要。方东树在书末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无论处于何时何处,凡有读书心解、触事开悟、随事有获遂记录一二,其目的则是:
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以备他日考验学之进退[3]109。而非著书矜名。其作品蕴含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他推崇前贤孜孜不倦、潜心典籍的精神,以及坚持将文事作为一生唯一信念的品质,参悟经典,他立志归诸实践、反诸身心,努力为善,实现价值。
要之,作者注重实用、穷理格物的理念贯穿全书始终,他从多个层面完整清晰地诠释了这一理念。又发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独立价值,提出求变创新的文学创作原则,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很好落实。因此,方东树受到后人的推重:
姚门弟子,多闻推方植之,深造推梅伯言。植之之学不纯乎文,而其论文去肤存液,有非拘学浅夫所能圈者[8]。
三、思想倾向与理论局限
《书林扬觯》中对《汉学商兑》已提出的“数十家递相祖述”的著书泛滥之风以及当时学界整体态势提出意见并开展讨论[9],两者在著述上一定程度存在着接续关系,但不可仅仅将前者视为后者的补充,应认识到《书林扬觯》的独特价值,也自当正视其中存在的不足。
在此书中汉宋之争的影响时有显现,方氏也多次毫不含蓄地指摘汉儒一味重视考据之弊端,但其态度较《汉学商兑》中的言辞激烈、情感激昂已渐趋缓和。方氏无疑是一位坚定的宋学言说者与护卫者,然而在其实际学术发展过程中对于汉宋两派实则是兼采和融合的态度,在此书中存在大量体现这一观点的言论。如:
凡著书若非不能已于言而徒欲搏名,无一是者。虽择题而为之,终外强中干,如考订经义最为大题,然非精诣,卓有独见,则亦陈陈相因,剿说贩稗而已。讲论义理,亦为大题,然呆衍宋儒语录,多拾前人绪余,不出里塾拘墟之见,则亦老生学究腐谈[3]33。
此处将汉宋统而言之,说明急于搏名、轻事著述并非一家一派之病。尽管他存在大量针砭汉儒考据之风的文字,却也认为考据注疏对宋儒之学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辩的,他赞成刘静修之言:
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中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论耳。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得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3]70-71。
后世学者认为方氏一味贬抑汉学、肆意谩骂,如皮锡瑞所言“诋及黄震与顾炎武”,持论或有不公。方氏在此书中多次引录并肯定顾炎武《日知录》之语,称赞其“盱衡今古,意甚高远”,又引顾氏强调所成之书必得有所增益之论,发出“呜呼。是皆先得我心矣!”的感慨,可见在此书中方氏能够反躬自省,主张二者应兼蓄并重,不可偏废。
汉宋兼采、唯务折衷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其实多有呈现。在《为姬传先生请祀乡贤公启》一文中,方东树说:
其为学也,考览六经,囊括百氏,钩深探赜,测突研几。收斯文于在兹,拯微言于未绝。发明周孔,和调汉宋[10]。
虽为评价其师姚鼐之言,却是作者内心倾向汉宋兼综的表征。作者在《汉学商兑》一书中固然激愤批驳汉学、护卫宋学,但也存在主张两者合流之论:
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轾,盖时代使然也[11]。
不唯如此,方东树也不期然采用考据的方法撰述此书,旁征博引,以证己说。
该书运用严密的文献考辞,驳斥考据学者的主张[12]。
这无疑是方东树兼采汉学的例证。由此可见作者此时的学术心态相对客观,思想倾向趋于兼采并蓄。
嘉道之际,桐城派对汉学进行批评的不乏其人。如梅曾亮、管同、刘开等均以辟汉为己任,尖锐批评汉学末流的弊病,阐明各自的学术主张。但他们和方东树一样,尽管对汉学展开批评与表达不满,却并非全然否定汉学,而是展现出会通融合的学术取向。如刘开说:
道无不在,汉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废也[13]201。
取汉儒之博而去其支离,取宋贤之通而去其疏略[13]203。管同也认为:
大抵汉儒之言,虽或附会而有本者亦多矣,未易卒弃之也[14]。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学日过中天之时,不仅宋学派在指摘其弊病上众口一词,汉学名家如凌廷堪、焦循、王引之等均对当时的汉学之弊有所披露,焦氏痛斥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不足,他说:
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15]。
由此推重“通核”而贬抑“据守”,主张融会贯通,兼蓄众说。而严汉宋之壁甚笃的阮元,此时也奉行“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主张,充分展现出折衷汉宋的倾向。实际上此时学者已清晰认识到两家均存在明显弊端,也已不再确守己见,在静观争鸣的同时不自觉吸收两者的优点,这一时期学风呈现渐趋融合之势。正如方濬颐所言:
后之学者当两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树其闲,决其障。晓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著。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为卿相[16]。
尽管文本的思想倾向与作者具体实践大体上是相互耦合的,不可否认的是此书确有明显不足。
首先,表现在尽管对汉学家的批评已不似《汉学商兑》般激烈,书写语言也较之平缓了很多,但书中针锋相对、出言无状者不乏其辞。方氏多次称汉学为诐淫邪遁之说,认为其论轻妄无知,又公开指责杨慎、焦竑两家言论浅谬轻肆,悉数他们文章作品中议论程朱之言,全部批驳为忿设诐邪。他将汉学称为浅学,认为汉儒忌嫉盛名、横诬丑诋,加之抨击其说流害人心,将其追随者称为流俗庸鄙之夫,未免过激而失真。
其次,在于书中部分论断矛盾不自恰。其言:
取人贵宽,论义理自有极至不易之则,前贤固当取,究不可指为圣人之道义止于此而已也[3]49。
认识到论义理极至不易,主张应吸取前贤的先见和精华之处,由于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所以不能说圣人之道止于此,此论可谓公正有识。但他在实际论说中独尊朱子,将其说置于至圣地位:
三代以后,数千年以来,止有此一种人品,此一种议论,尊为极至,假使有议之者,则众共斥为轻妄无知[3]49。
则知朱子非刻于论人,而凡訾朱子者,皆出于妒惑诐邪无知而狂暴也[3]49。
他又提倡著述立论,应当辞气和平,昭明义理,而不能任臆逞情,呵斥诟詈,但在其实际讨论过程中痛诋汉学,从政治层面攻讦汉学为“异端邪说”,甚至对汉学家的批判多有推测与妄加的成分,可见其未能达到自己提出的标准。
最后,是对于程朱之说的绝对尊奉。他指出汉唐以降,儒者论道确有见地,但存在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偏而不全等现象,及至宋代程朱出现,才使孔子的述作主张得以光显:
五经《语》《孟》所载宏纲大用奥义微辞,发挥底蕴,始终有序,进则陈之君子,退则语于公卿,或酬酢朋游,或讲之及门,其著述所传,精深高远,斯文不坠,后学有宗,所以继邹鲁而明道统也[3]47。
凡有不利于程朱之言方氏辄为之辩白,凡于朱门有异论者则贬抑之,认为程朱之学无有误疵,将其作为寻求经世之道的理论资源,似乎有失偏颇。
阅方植之(东树)《书林扬觯》。持论近正,然所举皆汉学所主而宋儒所未达。于宋儒扬之恐不升,于经生则抑之恐不沉,矫檠过中。吾则曰,汉学诸公在山过颡,亦有以召之[17]。
尽管书中主张大多持论相对公正,从修己接物、明德正心、镜观古今等方面加以观照,《书林扬觯》之言至今仍颇具重要价值,但作者所针砭的问题是汉学存在却也是宋儒没有完全克服的。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发展至清代中期业已呈式微之势,方东树意图从程朱理学处寻求经世之道也收效甚微,难以解决现实问题。
四、结语
清代中叶汉宋并立,学人热衷矜名著书,方东树则慧眼独具,论及清人轻事著书造成诸种弊端,又以通观古今、概要旨归,在著述体例方面提出规范标准和严格要求,昭明学人何以著书,如何著书,以期纠正时人之风。《书林扬觯》虽为应阮元之命而著,不仅蕴含了作者独善兼济、明体达用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着力讨论了著书立说的法则、文学创作的原则。不唯如此,此书折射出汉宋之争的余续,可见桐城派后期优秀学者能够跳出派系之藩篱、去除意气,从而展开理性思考,从经世致用角度兼采汉学,进一步发扬了桐城派经世传统,推动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学术转型,开拓了晚清理学发展新路径。尽管此书存在明显缺陷与不足,但瑕不掩瑜。深入掘发此书,不仅能够弥补方东树研究之不足,而且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当时学术生态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