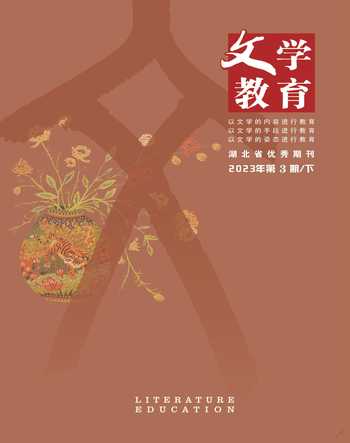鲁迅《阿Q正传》与蹇先艾《水葬》比较
2023-06-07肖银珠
肖银珠
内容摘要:鲁迅和蹇先艾分别在他们的作品《阿Q正传》和《水葬》里塑造出两个相似的人物形象:阿Q与骆毛。蹇先艾受鲁迅创作风格影响,其笔下的骆毛与鲁迅笔下未庄的阿Q都承接了作者对社会、对个体的批判与希冀。剖析“刑场”这一特定叙事空间中的人和事,有助于展现作者对“谋杀案”背后国民性的深度思考,探究在旧中国刑场文化背后,作者如何揭露国民性以召唤人类心灵深处的“爱与诚”。
关键词:鲁迅 蹇先艾 《阿Q正传》 《水葬》 看客
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写于1921年,而蹇先艾的《水葬》于1926年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仅相隔五年。这两部不到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因为人物共有的死刑命运而显示出作家创作的共通处。因《阿Q正传》中的刑场空间集中于后兩章,本文主要以《阿Q正传》后两章与《水葬》进行对比分析。
一.悲剧人物“背后”的创作动机
一百年前孙伏园在《晨报副刊》创办“开心话”栏目,鲁迅应约稿后开始写《阿Q正传》。此时鲁迅已经有为小人物作传的思想准备,可以说,阿Q的诞生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鲁迅酝酿许久的一个影像。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取自当时的社会,而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承担着“引起疗救的注意”[1]149的使命,阿Q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刻在当代人心中,他的诞生也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果。辛亥革命失败让鲁迅意识到拯救国人灵魂的必要性。
鲁迅曾承认阿Q被枪杀的结局是“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2]208,而他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把最后一章起名为“大团圆”。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解释安娜的死:“总的说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事。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我希望他们做的事”[3]3。鲁迅也说过:“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2]208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他们的情感投射,这些人物身上蕴含着作家的人文关怀或情感厌恶,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但在某些时刻,作家笔下的人物脱离作家本人设计的命运,开始向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这便是作家尊重人物设定最初意义和忠实于典型环境的表现。即便鲁迅在文中加入了诙谐幽默的氛围,阿Q的结局也没能和“开心话”像应和。鲁迅笔下的阿Q逐渐往死路上走,这是鲁迅尊重阿Q命运的写法,也是阿Q这一人物在当时历史境遇下的必然结果。
1935年鲁迅先生把蹇先艾的《水葬》和《到家的晚上》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蹇先艾作为贵州乡土文学作家代表人物,与鲁迅的交集从青年就开始了。“进步的青年们总是追随着他,乐于接受他的循循善诱的教导,而且他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学风、文风往往就发生巨大的变化。连校外的青年也纷纷写信给他,要求拜他为师。”[4]蹇先艾从贵州来到北京,也是为了向鲁迅求教。蹇先艾师从鲁迅,他笔下的骆毛与阿Q极其相似,尤其是骆毛身上体现出的精神胜利法。
鲁迅被看做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他认为作家用自己的眼光描述自己的故乡便是“侨寓文学”,“侨寓文学”后来也被看成“乡土文学”代名词。对于蹇先艾这一描写贵州地域特征的乡土作家,鲁迅曾做出客观地评点:“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的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一贵州很远 ,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5]8
蹇先艾的《水葬》写出了偏远贵州的落后习俗,展现出愚昧无知的乡村地区残酷的刑罚。但他的文本中不只是灰暗与凄凉的底色,而是试图将人世间最无私、最无条件的爱加诸其中。正如鲁迅的评价,《水葬》文本中不仅有贵州乡间的冷酷习俗,更昭示了人类情感中一种伟大的爱——母爱。鲁迅在创作《呐喊·自序》写提到自己创作的“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没有梦见儿子。蹇先艾在《水葬》中在结尾也以“曲笔”的形式赞颂了母爱:在《水葬》尾段描写骆毛的母亲——一个拄拐的老妇人。老妇人对儿子的爱使她一直站在风中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儿子。水葬刑罚的冷酷与人世间温暖的母爱交织、对比,更体现出蹇先艾文本中呼之欲出的悲怆与爱。
二.刑场空间叙事与谋杀案
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对艺术时空体进行定义:“空间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历史的运动中,时间则浓缩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6]206小说文本在进行叙事时必须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时间在空间中流动,汇集成可见之物。在鲁迅和蹇先艾的小说中,叙事艺术的时空性在“刑场”这一特殊场域体现出来。
刑场,即为囚犯执行死刑的空间。阿Q和骆毛的悲剧宿命结束于刑场,这场谋杀案的收尾也只能是刑场。阿Q的死是“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1]552,而骆毛却是“他狠心把眼一闭,他老母的慈容仿佛在目前似的一样”[7]30。他们两个人不同的行刑方式指向的都是同样的宿命——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刑空间并非封闭的,除了肉体的湮灭外,精神的毁损更为深刻。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中陈述酷刑对人类群体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凌迟,而阿Q在变成“替死鬼”前的游行示众,也是这一酷刑的表现——人在死前有着较强的求生意识,但因对死亡的结局无法改写,恐惧感会更加强烈。鲁迅在行刑过程进行独特的“阿Q叙事”——在“被看”的逻辑里,作为死囚的阿Q也因自己的特定位置审视着周围的人们。鲁迅在阿Q的眼中将刑场这一空间的时间拉长,随着“被看”的进行,阿Q的“看”也在进行。人丛中“喝彩”的人们成为阿Q眼中的“饿狼意象”:在行刑前,示众带来的屈辱感和威慑感会使得他“先死一次”。骆毛在行刑前始终处于一种向既定空间前进的状态,他接受着周围看客们的鉴赏,在他的世界里,这些“不讲理”的人是整个桐村的权威代表。“‘那不行!尔妈民国不讲理了是不是?……他几乎要哭出来。”[7]27骆毛对死亡的恐惧使他开始怀疑现存的乡村秩序结构,他用“民国”这一权力词汇来进行一种徒劳的反抗,显示出辛亥革命并未改变偏远乡域的落后民风,刑场依旧设立在传统习俗规训好的场域内。在走向死亡的路途中,骆毛想起自己的母亲,他“坚强的意志渐渐软化下去”[7]30——他内心的忏悔与痛苦只能通过想象中的母亲形象建构起来。骆毛与阿Q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有人牵挂的“儿子”。骆毛的死无疑是对偏远贵州落后地域无法律、无道德的私刑的控诉与批判。“水葬”这一习俗下的行刑场域,也比传统的刑场更神秘和恐怖。
鲁迅和蹇先艾笔下的这两个小人物都在特定的刑场空间行刑,但二人的死亡本质上都是一场沉默的谋杀案。阿Q想革命,却成了抢盗赵家财物的“鬼”。阿Q的认知错位使他成为画押认罪的“革命党同伙”,实际上他到死都未意识到自己是个被拉出来粉饰太平的“替罪羊”。现代文明制度中,死囚行刑前有知情权,而阿Q却作为一个并未犯罪的普通民众,在一场貌似公允的审判程序中毙命。阿Q经历的这场“错杀”本质上也在讽刺中国官场的腐败与无能:官员与族群中的权力人物直接操纵着个体的生死,“革命”也成为驱除异己的重要工具。
在传统宗法社会中,村长是村庄这一文化区域的权力代表,负有监管正义和程序定罪的职能,但骆毛生活的桐村并没有设置村长等名目,村长这一职位的缺席潜在意义上将审判的权力交由群众。骆毛犯偷窃罪,罪行的衡量标准无从考证,但处以传统习俗中的“水葬”死刑,是整个群体默许的。因违背群体道德规范而被强制执行死刑的落后习俗,无疑是对文明和法律的挑战。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场全村人共同举办的“私刑”中,未有任何一个村民试图反抗这一“隐形”的奖惩结构,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这一传统规训法则。因此,这是文化与道德承袭的结果,也是一场由历史策划好的“谋杀”。
三.国民性的“魂灵”
鲁迅自谈创作阿Q这一人物形象为的给沉默的国民“魂灵”画像,阿Q这一人物身上所负载的生命意义也时时更新,被进行着多重解读,但阿Q身上所体现出的“国民劣根性”和未庄人的“看客心理”一直是解读《阿Q正传》绕不过去的共识。蹇先艾《水葬》中的骆毛作为阿Q的后来人,其文化根基生植于偏远贵州的乡间习俗。作为一个处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常人,他不可避免的因袭着具有普遍概括意义的“国民劣根”,而他生活的桐村,也培育出中国大地上无主意识的“杀人团”。
阿Q一向是自轻自贱的代表,他通过精神胜利法来转移未庄人对他的凉薄与讥笑,当阿Q叫着“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1]519时,桐村的骆毛也重复着这一行为:“哎哟!你们儿子打老子吗?”[7]29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人性弱点,在必要时甚至发挥着一种积极作用——通过自我神经的麻痹来回避眼前的苦难。鲁迅和蹇先艾一方面看清了这种“精神鸦片”的恶性,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怜悯与同情。阿Q和骆毛自然是专制制度下的“愚民”,但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胜利”和“甘愿做奴隶”,才更加使得这些吃人的封建社会专制制度得以存在。可以说,愚民的存在稳固了腐朽的统治。周作人曾表示阿Q是中国一切‘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8]
“看客”一词最早出自鲁迅的《呐喊·自序》,后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写照。看客心理是几千年中华文明遗传下的病症,鲁迅的作品中曾多次写出这一人类群体间的冷酷与麻木。阿Q在被处刑时,发现人群里有他熟悉的吴妈,喝彩的人们咀嚼着他的痛苦,甚至认为枪毙不如杀头有趣,阿Q的胆怯使得他们没能听一出“好戏”。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提到一种“醉虾论”,对于这些麻木的看客而言,阿Q便是这“人肉的宴席”上的“醉虾”。人们因为长久的刑场文化浸染,不自觉的对残害生命的刑罚产生出一种冷漠的敬畏:看别人被杀是有趣的,听死刑犯唱戏是按惯例的,不遵守现行社会制度的异端是必须被杀死的。阿Q的死激不起人们的同情与悲伤,甚至在舆论上阿Q的死成为他“坏”的证据——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人性中的阴暗处合理化:“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1]552
骆毛在实施水刑前看客群体也一直环绕在他周围,为他持续施加凉薄与苦刑。这一大群看客行列,包括男女老幼、邻村的闲人,都来看这出“死人”的传统好戏。蹇先艾将观看行刑的人群写为“看热闹而来”,而看热闹是中国历史语境下的特殊产物。“看热闹”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并非只在桐村这一偏远落后的地域显现,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有观赏“杀头”“死刑”的乐趣。这些麻木而缺乏人类群体之爱的行列里,也包括天性纯正的孩子。一个人先天生存的环境中显露出的文化习俗确实能够将其整个人生浸染。鲁迅曾写道:“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9]93中国的看客文化是从个人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培养的,因而它带有强大的基因,它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中,并以传染病的形式浸染封闭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鲁迅和蹇先艾都意识到了人性的冷漠与隔阂的可怖之处,并将这一可怖通过阿Q与骆毛的行刑展现出来。
四.现代性的“呼唤”
鲁迅和蹇先艾这两篇短篇小说,都蕴含着相同的主题:召唤人类中的“爱与诚”,启蒙庸众,以达成“立人”的目的。“现代性”意味着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自觉的、文明的、新的精神力量,它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为价值前提。“现代性”也要求人们以史为鉴,拥有“爱”与“诚”的能力。
《阿Q正传》与《水葬》中的“角色之死”都展现了百年前刑场的可怖。私刑的看客来自受刑者熟悉的环境,而公共处刑的观众则开放的多。但无论是未庄还是桐村,看客群体的存在始终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痼疾:环境与群体造成的人性异化。当个体隐匿在群体中时,被同化的冷漠、自私和麻木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古来中国社会已有的“袖手旁观”“置身事外”等都可算做“看客心理”的前身,而现代社会中这种看客心理仍然存在。尽管“看”与“被看”相关联,“被看”的人在进行“看围观者”的行为时,他们也无法像看客群体一样拥有压倒性力量。可以说,“示众者”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势单力薄的存在。鲁迅和蹇先艾在各自设定的刑场区域里详细的刻画出这些看客群像,在严厉的批判这些看客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示众”历史进行反思。
在被看客群体鉴赏的同时,阿Q与骆毛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现实的顺从与逃避。阿Q和骆毛被“非正义”的审判和处死,无人为他们发声,无人正视他们的痛苦,这群麻木不觉的庸众,化身为冷漠的看客群体。鲁迅与蹇先艾在看清这一现实后,通过阿Q和骆毛这两个人物来展现个体与群体身上不同的“劣根”,他们的真实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想借由文字的力量来呼唤理性精神,传达启蒙思想——人民只有在经历思想开化后,不受传统伦理道德人观的束缚,才有可能能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个体。“爱”与“诚”呼喚的便是人类群体之间的体恤与关怀,对弱小、不公进行反抗,以及对自我、对社会抱有真诚。
阿Q与骆毛在刑场中遭受到的旁观与鉴赏,一方面体现出人类群体的麻木,另一方面也展现出私刑、酷刑的可怕之处。远离文明与仁爱场域的庸众,如何成为超人,靠的应当是爱与诚。
在鲁迅和蹇先艾分别写下阿Q与骆毛的百年后的现代社会,“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看客”等词仍常被人们提起。蹇先艾是鲁迅的传人,他的文学创作深受鲁迅文学风格影响。《阿Q正传》与《水葬》文本中共同蕴含的主题引发了后人对自我和社会的思考:要正视国民性格中的奴性因素,学会摒弃自欺欺人的虚假判断,在群体中坚持自我与理性的思想,关怀个体的生命。这两场百年前的谋杀案,带给我们的反思应当被珍视。
参考文献
[1]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
[2]鲁迅著.华盖集续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
[3][俄]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
[4]蹇先艾:《鲁迅与文学青年》[J].《山花》1981年第9期.
[5]鲁迅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2003.
[6]俄]M.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M].《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蹇先艾著.蹇先艾文集一[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8]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J],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见: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联系研究论文选(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9]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