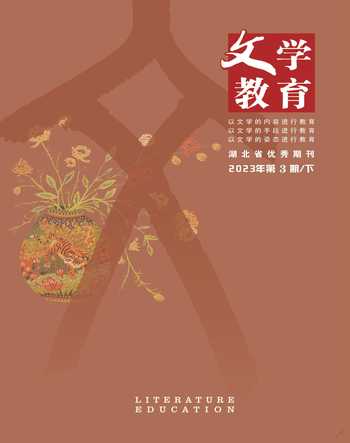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蛙》的释梦分析
2023-06-07朱迪
朱迪
内容摘要:在文艺作品中,梦境往往能夠反映主人公无法直接言说的“潜意识”,抵达一种间接的真实。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人潜意识的呈现,马尔库塞则认为文艺作品是人的一部分“基本压抑”的释放。在莫言《蛙》这部作品中,戏剧作为文艺作品,反映了“我”潜意识层面的“真实”,而主人公们的梦境,则体现了“本我”的真实诉求。
关键词:莫言 《蛙》 梦境 戏仿 忏悔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梦被张清华老师赋予新的注解,其认为林道静的梦体现了她内心的真实诉求,即希望恋爱对象的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这种以“梦”映照现实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给我们研究其他文本的参考。谈到梦必然离不开弗洛伊德的理论,《青春之歌》的释梦正是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个“恐水症”少女的案例与姑姑的情况较为相似,少女始终不肯喝杯子里的水,是因为小时候看到他人向水杯里吐吐沫。这种记忆尽管长大后忘记,但潜意识还保留着这种恐惧的心理情绪,《蛙》中可以很明显发现莫言受佛洛依德影响的痕迹。
一.魔幻或是梦境
莫言《蛙》一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姑姑”醉酒晚归,在洼地中被一群青蛙攻击、撕咬的场景。而对于此处描写,人们往往用“魔幻现实主义”去阐释,认为此为莫言对福克纳以及马尔克斯的模仿。不可否认,两座“文坛高炉”的辐射下,莫言难避“影响的焦虑”,作品中潜匿着魔幻现实主义因子,但此处的文本或许有另一种阐释方式。
姑姑因为年轻时期强制执行计划生育而导致无数婴儿的生命消陨,这使其内心柔软之处永远承受良心的噬咬。在清醒之时,她或许可以用外界原因来为自己辩解,诸如“使命”、“责任”、“有助于社会发展”等。然而当其真正面对自己内心,面对曾“扼杀”过无辜生命这一事实时,罪恶感还是侵袭而来,使其无法安生。被蛙撕咬、生病这一故事是姑姑自己向他人讲述的,当天晚上她处于醉酒状态。“那晚上我喝醉了——其实我喝得并不多,是那酒不好……可他娘的那是瓶假酒,我只喝了半茶碗就头晕眼花、天旋地转了”。i
而正是在这种迷糊不清的状态下,姑姑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一片洼地里,这洼地隐伏着无数的青蛙,处处是蛙鸣。通常情况下,喝醉后的人意识会处于混乱状态,甚至在第二天醒来后,有断片的情况,而姑姑“本来”是……,可是“不知不觉”……,这一“不知不觉”可以看出其受到潜意识的支配,跟随者类似娃娃哭声的蛙叫声来到了洼地。蛙与娃同音,具有强繁殖能力,充满了生殖的隐喻,自然让姑姑联想到孩子而触及内心的痛楚。因为假酒晕头转向的姑姑还能够飞奔跑气,看到了千万万万的青蛙向自己涌来,它们叫跳着、拥碰着、奔涌着,如同一股无法躲避的浊流,带来无尽的恐怖感……
姑姑之所以会看到这种幻想,是因为姑姑认为蛙是娃娃的化身,是对自己的报复。她认为蛙是为了复仇而来,因而激起了内心最深层的恐惧。她嫁给了郝大手之后,捏足两千八百个泥娃娃,也是一种赎罪的方式。
处于醉酒状态的人,其言语并非完全真实可靠。如果将姑姑的话语当做真实的发生,则将此次视作为“魔幻现实”无可厚非,然实际上,不仅此处,很多地方姑姑的话都值得怀疑。比如觉得泥娃娃的长相像曾经毁掉的两千八百个孩子的样子、给小狮子“听诊”……人总会赋予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予意义,而叙事自我经过意识加工,便成为姑姑口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姑姑所讲述的醉酒后发生的事,更像是她做的一场梦。
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进行层次划分,按照他的理论,人的意识包括多个维度: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意识时能让主体认知到的部分,时刻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深层次的潜意识则因为“检查机制”:个体本能压抑或道德约束不被认知到,在睡眠时、醉酒时,超我的检查松懈,潜意识或者躲过检查机制变成意识ii。
姑姑醉酒后的奇幻遭遇则正是潜意识中防御机制弱化引发的罪恶感侵袭。蛙的复仇即为姑姑内心的罪恶感和忏悔。这些罪恶感和忏悔感,醉酒后侵入姑姑的意识之中,使其产生了梦境,梦中曾经被压抑的罪恶终于得到了报应。
二.《苍蝇》和《脏手》
《蛙》中活在负罪感中的不止姑姑一个人。
小说采用独特的叙事方式,通过向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讲述故事。故事也包括“我”和“姑姑”两个主体iii。
起因是杉谷先生要在大年初二来到“我”的故乡,并打算在县招待所礼堂做名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以鼓励小镇文学爱好者进行创作。“我”受到启发想要创作以姑姑为原型的、如“《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这里提及到萨特的《苍蝇》、《脏手》。这两部作品就像钉在作品上的“果壳”纽扣,里面藏着小的完整的宇宙。
萨特的《苍蝇》的主题是“忏悔的释解”。阿伽门农被谋杀后,阿耳戈斯人民在无穷无尽的忏悔中“以慢动作飞舞”:也就是说,他们互相指责告发罪行的时候变成了苍蝇。由此也能够看出莫言的借鉴:姑姑最后被蛙的梦魇缠绕,便是无数潜藏在内心深层的愧疚感和罪恶感作祟。
而“我”也始终处于愧疚感之中。正如阿耳戈斯的苍蝇。
在《苍蝇》中仇人埃奎斯托斯不愿因罪恶躲躲闪闪被杀。厄勒克特拉则开始怀疑复仇的正义性,感到恐惧、仇恨。俄瑞斯忒斯则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责任,终于成为化解仇恨、消灭“苍蝇”的勇士iv。
而在《蛙》中,“我”因前妻之死而有愧疚感、娶了小狮子对王肝有愧疚感、让陈眉成为代孕者而有负罪感,我在写信时反复提及到赎罪: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v”
杉谷义人勇敢地承担了父辈的罪过责任,并愿意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代替赎罪,这是自我批判、反思历史的重要途径。负罪感、愧疚感是个人想象自己的行为与良知、道德观念相悖,即为“超我对本我的批判”,根据马尔库塞的理论:父亲的统治变成了全社会的统治时,推翻这种统治的罪恶感也就变得非同小可了。文明为了压制死亡本能产生了罪恶感。心理防御机制作用下,自我进行行为美化,美化方式包括压抑、合理化、补偿、升华等等……vi
姑姑赎罪的方式是通过将她曾经“不得不”扼杀的那些婴儿,通过一个个泥塑再现出来,仿佛赐予那些未见天日的灵魂重生,以此来弥补看似“正义”行为所带来内心始终无法推脱的亏欠和歉疚,尽管这场扼杀行为并非她个人主观行为。
至于“我”自己,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赎罪,通过诉说、写作来忏悔自己的罪行,以期减轻罪过,获得心灵的宁静。这一句式很有力量:“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vii”这种将自己内心完全暴露在公共地带的忏悔方式,也提供给特殊时代内心冲突的“犯罪者”们一个抒发灵魂颤栗的出口。惩罚的目的在于避免错误的再次发生,将这种“罪”与“罚”的发生发展及结果广而告知,具有警醒世人的效果。
三.朦胧地带的书写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如是说:“……把所有的人,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去定性的朦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viii”
《蛙》中人物的塑造,很生动地体现出文学家对此朦胧地带所施展的才华。文学正是展现人性冲突与命运无常的舞台,莫言的确操纵了已出精彩的“皮影戏”。为什么收信人是“杉谷义人”先生——一个日本医生的儿子——这其中包含着对于战争的反思。“您勇敢地把父辈的罪恶扛在自己的肩上,并愿意以自己的努力来赎父辈的罪,您的这种担当精神虽然让我们感到心疼,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当今这个世界最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ix
为什么“我”最后记忆混乱,或者说是故意隐瞒,将陈眉所生的孩子说成是小狮子所生?“我”讲述的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假?我在所谓的“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之后的行为是否仍然“愚蠢”?
细读文本不难看出孩子自然是陈眉的,蝌蚪在书信中暗示的信息始终是“孩子是陈眉的”,现实中他们联合上演了一场大戏,获得了孩子的所有权。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的讲述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此即为对于实际情况的隐瞒。
最终“我”不得不承认,用诉说的方式忏悔自己犯下的罪,以达到减轻罪过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我”无法在写作、赎罪的过程中,保持“真诚”。
“因为我妻子小狮子是超高龄初产妇,所以,连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里那些据说是留学英美归来的博士们也不敢承接。这时候,我们自然想到了姑姑。姜还是老的辣。我妻子唯一信任的也就是我姑姑。她跟我姑姑接生过数不清的婴儿,自然见过我姑姑遇到危急情况时的大将风度。x
”而随后在小狮子“生产”时,“我”同样用一个梦带过。
在梦中王仁美顺利地生下了孩子,而我也心安理得地将孩子视为自己的骨肉,自称“我们给予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文本中的价值观导向与创作主体之间并不一定一致。叙述主体“叙事自我”美化,而文艺作品作为内心中真实欲望的呈现,则代替主体给出了真实的答案。剧本《蛙》中为了自身地占有孩子,“我”不惜放弃自己的良善,做出泯灭人性的事情。人成为在欲望与道德之间徘徊的皮影人偶,无法逃脱时代带来的痛苦挣扎。这是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命运之手的操纵与无法终止循环的宿命。这关系到人类行为上的终极质疑,人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正当与否之后,是否能够真正忏悔,这种忏悔是一种满足读者对于作者道德要求的计谋还是内心真正的愧疚?在忏悔之后,犯错者是否必然会纠偏改正?还是在面对相同的情境时会重蹈覆辙?
四.杉谷义人的设定
逻辑上,将人物选为与姑姑有关的“日军指挥官杉谷”的儿子,构建人物关系网络,形成一种自圆自足的闭环。
姑姑的工作导致无辜的生命消逝、无数家庭破裂,尽管有程序正义性,合法、合理,但却不合情。因而其无法摆脱自己内心的煎熬。杉谷义人的父亲和姑姑行为本质是一致的,作为国家机器,坚定地服从指令。
但随着时间流逝,当时代发生了改变,姑姑如同厄勒克特拉一样,开始怀疑复仇的正义性,感到恐惧。《脏手》中贺德雷说:“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xi——恶的行为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也可以被看成善的。姑姑前半生始终坚守这一理念。但晚年时,她的神经出了问题,成为所谓“疯人”。然而我们知道“疯癫”不过其实是另外一种本能释放的形式。由此可见,曾经坚定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在“蝌蚪”的戏剧中,虚构与真实交织,意味着发生的事件有一定的真实性。
在戏剧中,姑姑说:“后来,报纸介绍了“蝌蚪避孕法”,让排卵期女人,在房事前,喝十四只活蝌蚪,即可避孕。但结果没有避孕,那些女人,都生出了青蛙!”如此荒谬的理论竟然源于报纸,权威性刊物严肃性的消解,也暗示了姑姑心中“组织、单位等自己给自己捆上的绳索”的松绑。姑姑帮助帮助小狮子掩盖假怀孕生子之事,亦可见组织至上向人性至上的转变。xii
通过最后蝌蚪和姑姑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姑姑实际上对陈眉是有愧的。她不像蝌蚪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美化自己的行为,从而产生心理释脱感。
蝌蚪用各种借口来为获得孩子提供正义支持,他说:“陈眉是疯子,而且是个严重毁容、面貌狰狞的疯子,我们将孩子交给她抚养,是对这孩子不负责任!当孩子母亲神志失常、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的情况下,孩子由父亲抚养是天经地义的事……”xiii
姑姑却始终在辩解:“也许我们把孩子还给她,她就好了呢?母亲和孩子之间,那是可以产生奇迹的……”
高梦九断案一幕是戏仿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灰阑记》中双母夺子,夺到孩子的母亲被认定是更爱孩子的。而布莱希特对血缘和伦理进行反思,布莱希特认为相较于更看重孩子所有权的亲生母亲,与孩子有着深厚感情的养母,会因担心孩子受伤害而不硬夺孩子。但在《蛙》中,无论结果如何,孩子都会被判决给小狮子和蝌蚪,外部力量—十万元赞助,超越了伦理、血缘。
回到萨特的《苍蝇》和《脏手》,蝌蚪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心理状态随着事情的发展发生不断的变化,总体上是负罪感—赎罪—仍然无法消解内心的负罪感,这种心理状态也暗示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莫言对萨特创作思想的反思:“人在主动采取赎罪行为之后真的能够将自己心里的重负放下么?”
或许如姑姑所说:“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xiv。這一点在蝌蚪的最后一封信中也有暗示:“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先生,我期待着您的回答。”
蝌蚪同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杉谷义人先生那里获得一种心理的安慰。正如李手“组织绳索”的一席话让他决定留下陈眉的孩子,现在他希望通过未来到的另一席话来减少心中的负罪感。
《蛙》的文本和其建构的意义空间呈现一种相互映照的形式。文本是表象,作为本质的意义空间的真实性,需要透过逻辑推断完成,这是作品的艺术张力所在。文学同样可以为玄学与科学交织的地带。至于作品通过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分析,还是用魔幻现实色彩去解释,对于伟大意义的传递均无影响。《蛙》的意义不仅在于向我们展现一个时代的存在与意识,同时指向人性的终极命题,让读者在阅读中反思,并在参与现实建构时融入更多文艺带来的温情,而这种以梦境投影主人公内心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为研究者解读其他文艺作品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i高子晴.论《蛙》中万心的个体罪恶意识与虚妄忏悔表达[J].现代交际,2020(10):99,98.
ii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iii石转转.父权制下"强者"的生存与"弱者"的毁灭--解读莫言小说《蛙》中的人物形象[J].文化学刊,2019(4):79-82.
iv范吴喆.莫言作品《蛙》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剖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6,29(7):49-50.
v[8][10][11][14][15]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vi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vii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viii林建法主编.讲故事的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01.
ix莫言著.莫言文集 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
x莫言著.莫言文集 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
xi伏爱华.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07.
xii兰鲜凤.莫言小说《蛙》的矛盾性探析[J].学理论,2014(17):136-138.
xiii莫言著.莫言文集 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
xiv莫言著.莫言文集 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