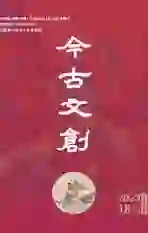现代女性的困境
2023-05-30陈培佩
陈培佩
【摘要】《杜兰葛山庄》是安妮塔·布鲁克纳从艺术家转型为小说家后的第四部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浪漫小说作家埃迪斯·霍普被放逐到瑞士的度假酒店后,她開始审视并尝试改变自己的经历。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杜兰葛山庄》中主人公埃迪斯探索建构主体性过程,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以埃迪斯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女性即使努力却仍然很难找到自我,从而导致她建构主体性的失败。现代女性仍处于各种困境,可见女性主义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杜兰葛山庄》;现代女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8-002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8.007
20世纪是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工业化、战争、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削弱了以往的安稳现实。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化和陌生化,这使得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自我,但同时也让他们无法在这个社会找到自己的定位。面对这些剧变的现代人,他们不知不觉中被孤独地困在这个复杂动荡的世界里。
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1928年出生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949年获得伦敦国王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1953年获得伦敦大学考陶德艺术学院艺术史博士学位。之后布鲁克纳一直从事与艺术史相关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出版了《未来的天才:法国艺术批评研究》(1971)、《格鲁兹:十八世纪现象的兴衰》 (1972)和雅克·路易·大卫(1980)等法国艺术批评书籍[1]。1981年,她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安妮塔·布鲁克纳的小说都把女性描绘成聪明而敏感的主体,在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努力应对复杂的工作现实、婚姻、人际关系和伦理困境。布鲁克纳时常描绘着一种悲观的人生态度,她在大部分小说中描写了中年女性在遇到不适合自己的浪漫男人后所经历的孤独,且越来越感到与社会的疏离感。她还擅长刻画角色性格和细节,在小说中她描写了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根状态,描绘了人们因焦虑、丧失自主性和真实性而产生的身份危机和不安全感,从而表达人物的欲望和情感。
《杜兰葛山庄》是布鲁克纳转型成为作家后的第四部作品,她也正是凭借这部作品在1984年获得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杜兰葛山庄》中的女主角埃迪斯·霍普是一位三十九岁的未婚作家,在她的生活处于混乱状态时,她被周围的人“驱逐”到一家瑞士酒店以便“长大”后“做个真正的女人”,好为自己的错误赎罪。埃迪斯来到酒店发誓绝不改变自己,然而酒店沉默的魅力和她对酒店客人的观察都在迫使她审视自己是谁。在酒店里,她观察着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普西太太和她的女儿詹妮弗对彼此的爱,以及她们过着灿烂的生活;博纳伊夫人被她的儿子从庄园赶走后住在这里;还有莫妮卡,她答应了丈夫的要求来到酒店调养身体。当内维尔先生向埃迪斯求婚时,她考虑过嫁给内维尔会给她带来一种被世人所认可的生活,但当最后她发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花花公子时,她最终拒绝了他的求婚。这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她再一次鼓起如逃婚那时的勇气,决定自己掌控一切,最终离开了杜兰葛山庄。
目前国内外一些研究对埃迪斯的探讨倾向于赞美她作为独立知识女性具有自主选择权,而把她的困境只归因于父权制社会,但埃迪斯并没有真正独立,她没有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从未有真正的自我,从始至终言行不一。埃迪斯总说自己是龟兔赛跑中的乌龟,其实她何尝不想在现实中当一只兔子呢。这也从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布鲁克纳的女性主义观点,即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女性主义,但现代女性仍难以建构自己的主体性。
一、主体性的缺失
埃迪斯主体性的缺失在于一方面是她没有真正的自我,她的自我是虚像。拉康表示主体的自我意识始于镜像阶段,婴儿依靠镜中影像形成对自我形象的最初认同,而这种认同本身就是一种“误认”。建立主体性得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但她的自我为了克服匮乏,用凝视将镜中一个完整的形象强加于己,她认为自己是乌龟赛跑中的乌龟,“现如今,我可是只彻头彻尾的乌龟了”[2],因此她的主体性建立于非真实的虚像乌龟基础之上。埃迪斯的形象是散乱的,她的经纪人认为她“真像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布隆斯伯里俱乐部的一员”——即弗吉尼亚·伍尔夫,后来又赞叹她“不愧是教授的女儿”,再后来又被普西太太认为像安妮公主,自我的不统一导致埃迪斯没有主体性。
埃迪斯总是欲望着他人的欲望,却都不是她自己本真的需求,这也从另一方面导致了她主体性的缺失。在拉康的哲学视域中,人的欲望总是虚假的,你以为是自己有需要,而其实从来都只是他者的欲望。人的欲望就是一种无意识的伪“我要”。[3]作为一个作家,她按照传统的男性文本主题写作,欲望着的是男性的欲望。她的小说中总是乌龟这样的弱者获胜,而类似的情节如同《格林童话》一样的男性文本,总是男强女弱,女性永远处于被保护和待拯救的状态。《格林童话》中的女性被动、沉默、勤奋,得到的回报是财富和一个支持她们的男人,而男性角色注定要去冒险,并把被动、沉默、勤奋的女性作为他们的回报。在埃迪斯这个年代,女性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她享受着独立赚钱、纳税的生活,却依旧没有摆脱从属的地位。埃迪斯标榜自己写的小说要跟当代女性不一样,却囿于男性所定下的写作规范之中,执着于灰姑娘等待心上人出现般的古老爱情神话,于无形中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变相地复制着男性的文本。
作为一个女性,埃迪斯同样欲望着男性的欲望(这里的男性特指情人大卫)。埃迪斯满脑子都充斥着对大卫的思念,她给大卫写了六封信,读者也正是从信中才了解到埃迪斯与其他几名客人相处的细枝末节,她无时无刻都期盼着大卫也能给她写信或者打电话,结果到最后才发现埃迪斯自始至终都没有寄出任何一封信,大卫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关心问候她。她热切地祈盼着大卫也在想她,她欲望着大卫的欲望。
欲望着其他女性的欲望,还不如其他女性。最开始,埃迪斯自恃清高,瞧不起其他女性整天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并打扮得花枝招展,后來随着跟普西母女与莫妮卡的深入交流,她才发现这些为了取悦男性精心打扮自己的上层阶级女性就是她理想中的“兔子”。她开始动摇自己原本不在乎自身形象的想法,于是跟着莫妮卡一起逛街一起做头发,买到漂亮的裙子也想着要展示给大卫看,就如同普西太太一定要等全场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时才会踏入酒店,最终埃迪斯还是欲望着女性的男性的欲望。
二、建构主体性的努力
正因为埃迪斯面临着种种孤独和焦虑,所以她试图想要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杜兰葛山庄》的时代背景设定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期,而是在与这本书出版年份一致的1984年,埃迪斯在1984年拥有独立的收入、公民的所有权利,唯一没有的是社会地位。她作为女人是隐形的,她只能去适应别人,被别人可怜,因为她显然是“不被男人需要的老女人”。与杰弗里·朗结婚本可以改善这一状况,但要失去的东西太多,因为他“不赞同已婚女性工作,说她把太多时间耗费在写小说上了”[2]。所以当她坐着出租车绕过街区去登记处时,她意识到她将无法写作,她将失去她珍视的生活方式,她生活中的小乐趣和她目前所拥有的身份突然显得更有价值了。如果她成为一个妻子,她将要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保持一座房子的整洁,维持一种社会地位。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决定保持自己的身份,她选择不去改变原本的生活。她不愿意被婚姻束缚,她追求自由,追求自己眼中的浪漫爱情,逃婚意味着她不愿沦为传统的女性,不甘做“房间里的天使”。然而这一行为激怒了她的亲朋好友,邻居兼好友的彭尼洛佩·米琳如同狱警将她押送至杜兰葛山庄,待其改造成一位更成熟理智的女人才能原谅埃迪斯。
埃迪斯来到杜兰葛山庄后,作为一名作家,善于观察是其特点,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人物看似是用眼睛普普通通地“看”,实际上却是凝视,而凝视(gaze)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物时,不单是在“观看”(looking),它同时也是探查和控制。[4]凝视是埃迪斯构建主体性过程中关键性的行为,女性凝视关注并表达自身欲望,建立女性的主体性,当她意识到凝视的力量时,她企图用自己女性凝视力量冲破传统的男性凝视,她向欲望主体发起挑战,并消解其他女性的主体性。埃迪斯观看并评价着其他女性们的穿着打扮和身材,贬低她们肤浅而自恃清高。
我思故我在,有思想有思维才算一个人。思考这一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也是为建构主体性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她通过思考来揣度他人,当她遇见每一个人都会如同写小说般为他们设定年龄和身份,比如一进来酒店看到博纳伊太太,埃迪斯猜测她“像是哪个比利时糖果大王的未亡人”,猜测莫妮卡“八九不离十是个跳舞的”[2]。她也有对自己的认识,她认为自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并从穿着打扮都模仿着伍尔夫,连她的笔名瓦妮莎·维尔德(Vanessa Wilde)都与伍尔夫的首字母缩写一致。
三、建构主体性的失败
全文以埃迪斯这样一个聚焦人物的眼光对其他人和景物进行“看”的行为,而小说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酒店老板胡伯先生,他才是小说中观察所有人的角色,当埃迪斯入住酒店时,他奇怪于“一位英国女士怎么会起这样的名字”,继而猜测“或许,她祖上不是英国人;或许,不是什么正经女人。”[2]埃迪斯并不知道这位默默观察所有人的先生就是胡伯,“餐厅里还有位圆滚滚的年老长者,埃迪斯不知道,其实这就是胡伯先生。胡伯先生一边吃着饭,一边留意身边的一切,将人生的两大乐事融为一体。”[2]看到莫妮卡出门向咖啡馆的方向走去,埃迪斯跟在身后,胡伯先生的眉头微皱了一下。[2]杜兰葛山庄若是伊甸园,那么来到酒店的所有女性将酒店视作天堂,她们都是来避难的,却没想到胡伯先生就是上帝,那些来到酒店的男性散客即为天使,男性权威无所不在的审判目光如同美杜莎般的凝视。他看埃迪斯时表现出鄙夷的态度就像上帝审判的目光,当埃迪斯用凝视的力量试图建立主体性时,胡伯先生对她的观察同时如同美杜莎的凝视消解了她的主体性,在希腊神话中,被美杜莎凝视的人都会被石化,而被胡伯先生凝视等于埃迪斯主体性的死亡。埃迪斯只知道自己在看,不知道别人在看她,致命的看。如同拉康讨论过的小汉斯·荷尔拜因的名画《大使》,在这幅图的最下方有一件古怪的东西,从右下角某个适当的角度,可以看到那是一颗头颅。人们推测,这张画像是悬挂在丹特维尔宅第中的一面对着楼梯的墙壁上,从走上台阶的人,只要一抬起头,就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这固然是画家在卖弄技巧,但是没有主顾的特别要求他也不会这样做。研究者认为,这张照片反映了丹特维尔的一种“记住你终有一死”(Memento Mori)的神秘主义。《大使》中的历史和文化阐释拉康将观看对象的视角称作“眼睛”,而“眼睛”则是观看的主体,当他“看”客体目标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到,他所观看的目标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他的视线从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移开,也就是被观看的客体会以他的方式对观看主体发出“看”的目光,这种折返性目光就是凝视。
另外,埃迪斯作为一个有洞察力的作家,却老是把别人的年龄和身份猜错,她一而,再而三地将普西母女的年龄猜错,最后发现事实的她大为吃惊。同时,她对自己的认识也不清晰,她以为自己打扮穿着像她的偶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可以被所有人认为是伍尔夫,却不然,胡伯先生看到她第一眼认为她不是什么正经女人,普西太太也觉得她像安妮公主,这些与她想象中不一致的形象,也是她主体性建立失败的例证。凝视必然包含主体化和客体化的过程,这种行为“将目光的暴力加之于他者身上,使之成为主体化与客体化的一个粘合区”[5]。埃迪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徘徊,其主体性也不能得到建构。别人对她的凝视给她带来了负面影响,让她不自在地想要改变自己,她试图打破传统的男性眼光,向欲望的目标发起挑战,但她的凝视却是失败的。她三番几次揣度周围人的结果是错误的,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基于她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她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自然无法确定自我,她对别人和自己的思考都被他人和事实一一否定,从而也就无法建立主体性。
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掌握了话语权以此建立起主体性,这样的房间无疑包含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含义。来到杜兰葛山庄的女性都是不自由的,包括埃迪斯,也是被迫来到杜兰葛山庄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女人。她为情所困,脑子里整天都是大卫,这个人占据了她的精神空间,而现实中亲人离世、朋友疏远,她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伊迪丝的经纪人哈罗德曾提及过爱情小说的市场正在怎样发生改变:“现在流行的是职场女强人的性奇遇,到处都是手提公文包的年轻小妞”。伊迪丝本人似乎是一个复古的人:她写的是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浪漫故事,而不是讽刺的故事,这也是作为她固执地相信的愿望实现的形式。她的人生如同她目前这本在酒店仍未完成的书一样,仍没有遇上自己理想中的浪漫爱情,于是她选择了回归(returning)而不是归家(coming home),又回归到以前那种漫无目的的“孤女”状态。
四、结语
安妮塔·布鲁克纳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女性主义,因为女性主义是要反凝视,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而埃迪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她既不传统也不超前,在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中根本没有对自己形成清晰而准确的认知。她在凝视别人的时候,角落里还有酒店老板胡伯先生凝视着她,也就意味着她的主体性不可能成功建构。
即使在女性运动发展的后期,以埃迪斯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作者不承认这是一部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或许基于她所描绘的人物并不是理想中实现女性主义的模样,而是现实中女性处于危机的真实形象,她作为一名“清醒”的作家用文字道出了女性主義任重道远的事实。
参考文献:
[1]Malcolm,Cheryl Alexander.Understanding Anita Brookner[M].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2.
[2]安妮塔·布鲁克纳.杜兰葛山庄[M].叶肖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3]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4]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张德明.沉默的暴力——20世纪西方文学/文化与凝视[J].外国文学研究,200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