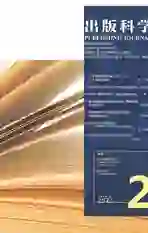数字智能时代的知识秩序与出版范式转型探析
2023-05-30刘欣袁也
刘欣 袁也
[摘 要] 出版的本质是知识生产的公开化实践。在互联网的媒介物质性作用下,数字智能时代的知识秩序以链接、多重拼贴、生成性和混杂性为主要特征。一方面,颠覆了印刷时代对“知识”的定义,由此带来知识生产空间的极大释放。另一方面,随着“被动的”读者转向“能动的”用户,图书出版也由传统的知识产品生产者转为知识服务提供者。在万物互联的网络社会中,一种对出版的新的想象由此打开:数字智能时代的图书出版通过跨媒介叙事进行内容生产,搭建贯通线上线下的新型知识服务空间,打造具有公共文化属性的知识服务平台。
[关键词] 图书出版 数字化转型 媒介变迁 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 G2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2-0056-05
Knowledge Order and Publishing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Liu Xin Yuan Y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BPG Digital Media Center,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Beijing, 100120)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publishing i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wide dissemination.Under the media materiality of the Internet, the order of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s mainly characterised by linking, multiple collage, generation and hybridity.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rint era has been overturned, the space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has been greatly released. On the other hand, book publishing has shifted from being a traditional producer of knowledge products to a provider of knowledge services, as the passive reader shifts to the active user. In a networked society where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a new imagination of publishing is opened up: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produces content through cross-media narratives, builds a new knowledge service space that connects online and offline, and creates 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with public cultural attributes.
[Key words] Book publish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dium change Knowledge production
出版是承載、传播人类知识与文明的重要活动。出版的发展与技术、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息息相关,也在这个意义上,出版的发展、变革有着自身的科学规律。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ilel Kuhn)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断地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范式革命—常规科学”这样的循环[1]。数字智能时代,出版业面临的危机更深层次的是一场范式革命,而这场范式转换与作为出版本质的“知识”生产息息相关。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知识”的秩序与内涵在不同媒介环境下的变迁,揭示不同时期的出版形态应和着怎样的知识生产需求,以此探寻数字智能时代的出版范式及数字化转型路径。
1 媒介变迁视角下的出版活动与人类知识—断裂与重构
出版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并将其以一定介质形态进行公开化的社会实践[2]。在不同的历史媒介环境下,知识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相匹配的出版活动也随之改变。若想探寻数字智能时代的图书出版有着怎样的可能性,首先需追问当下的“知识”的本质特征发生了何种变化。
1.1 印刷时代的知识:文字、出版与现代性
出版活动诞生之初就与文字、印刷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弗洛克(Havelock)曾指出,文字或字母作为一种“概念技术”,是我们今日熟知的西方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基础[3]。文字使说话者与其所说的话相分离,促使概念性论述成为可能。人们开始用线性的方式推理、将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现代意义的“知识”由此诞生,并以一定介质记录和流传。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出版活动能够一直延绵不绝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原因也在于出版与发行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手段。
当我们把“知识”的概念放入媒介变迁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时,也需要回应来自20世纪哲学家和媒介学家对线性文字造就的“知识”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抨击。这也是打开“知识”在媒介融合下新的意义与想象的契机。以麦克卢汉(McLuhan)为首的学者认为,拼音文字以效率、实用、理性的名义使意义与对象相分离,人类的沟通脱离了象征和感知的视听系统。拼音文字和书面文化在放大了理性的同时,也割裂且萎缩了人的感觉,“是进步也是灾难”[4]。拼音文字使人类古往今来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分离成了一致而连续的单位,应用型知识从中被提炼而出,影响和重塑着社会的生产和组织结构,一个韦伯意义上“合理”的社会由此诞生,这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1.2 口语时代和电力时代的知识:感官平衡与“重新部落化”
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将文字出现以前知识的传播形式描述为“部落的百科全书”。知识传播的主体是诗人,他们为传统社会中的年轻人提供了实用智慧和忠告[5]。本雅明(Benjamin)也认为这是一种与共同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这一传播过程需要讲者和听众之间“经验的同化”,这是一种通过相互陪伴、面对面的互动才能获得的过程[6]。不论是麦克卢汉、哈弗洛克还是本雅明都向往着口头文化时代人们交流方式带来的感官平衡。当广播、电视等媒介普及后,麦克卢汉高呼“重新部落化”,本雅明也将注意力放在现代传播技术如何能够像口头文化中所体现的那样,引起多感官的沟通[7]。与人类感知结构适配的“知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一种理性与情感的“混成体”[8]。
1.3 互联网文化中的知识秩序与知识内涵
互联网、5G、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技术带来的是一个万物互联、瞬息同步、虚实重叠的世界。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穿梭在光纤信号之间的信息和意义流动构成了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线索。“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 即信息时代。”[9]媒介技术改变着人类的时空观,使人的眼睛和耳朵再度回归到感知平衡的状态,麦克卢汉和本雅明希冀的多感官卷入的沟通已成为可能,那么知识的形式和载体也再次被打开。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秩序,是链接而不是容器;是多重拼贴下的意义,而不是单向度的意义;是未竟的(unfinished),而不是确定的;是混杂的,而不是清晰秩序的[10]。
印刷时代的“知识”对应着传统的图书出版模式。其知识生产是对精英文化的肯定、提炼、加工和传播,对知识生产的主体有一套既定的评判体系。互联网时代,在新媒体赋权下,个体的生命经验也同样可以被作为知识并释放而出,以一种显现的方式摆放至互联网平台上,完成“观点的自由市场”下的优胜劣汰。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内涵,不仅包含了印刷时代离身的、抽象的、理性的知识,也包括了借助网络的视听手段可达成的具身的、具象的、感性的经验。随着知识内涵的扩展,数字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空间被极大释放,也推动着文化产业的疆域拓展。
2 出版业发展的范式革命:知识服务转向
2.1 转向的内在逻辑及外在要求
如胡泳指出的那样,“一页印刷品对我们有用,是因为它包含了知识;而一个网页的有用性却不仅仅在于它包含了什么,而更多地在于它指向了什么”[11]。这种指向背后隐含着个体对知识的主动探索、选择、拼贴和组织,而非印刷时代的被动接受。在这个知识超载的社会里,“被动的”读者变成了“能动的”用户,受众的主体性重新显现[12],这也使得知识生产需要围绕人的需求进行重组,出版也从传统的产品导向转向服务导向。出版企业相应地从产品生产者转为知识服务提供者。
服务型企业的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不可分割[13]。这也就要求图书出版企业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将有形的出版产品与无形的出版服务融为一体。知识服务与受众消费同步,在客观上要求着一种时空同步,即一种贯通线上、线下新的消费服务空间的敞开。这种新的空间或场景,应和着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内涵,将知识从线性的文字和平面化的纸张中解放出来,知识生产者的个人魅力、知识守门人的思考、知识的细节、受众的反馈等向度再次被激活,重新回归到人类的知识传播活动中。
2.2 转向在实践中的分野
在我国的出版实践中,知识服务平台最早并不是由传统出版业生发出来的,而是互联网企业,其中的典型是“知乎”。作为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并不生产知识,而是由用户生产并分享知识、经验和观点。知乎通过搭建资源聚合的平台,将知识的传者与受者连接。从这个角度看,知乎和传统出版业做的事情一致,都是在连接作者与读者。但知乎做了而传统出版业没有做的那部分才是揭示知识服务的关键,这也启示着传统出版转型的道路。
首先,知乎搭建的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资源聚合型平台。多元主体互动意味着多个主体会以各自的需求和利益出发,在平台的快速互动中相互博弈,以求最大化自身的诉求。相比之下,传统出版业搭建的是单一线性的资源链,互动的缺失直接导致讨论难以形成。一方面,读者的社交等其他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能转向书籍以外的其他知识产品;另一方面,作者也感知不到反馈,作品的影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或者被淹没在知识超载的社会中。除此之外,知乎也对社区中的知识进行提炼和整合,并利用多种媒介打造知识综合体,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多重需求和体验。知乎相继推出了优质用户回答和专栏文章整理而成的电子书“知识盐系列”、以“课程、书、训练营”为矩阵的“知乎大学”、直播和语音交流为主的 “知乎Live”等产品。
2.3 数字智能时代出版业的范式革命
“知乎”产品的逐步拓展也让传统出版业意识到图书出版活动正在和其他知识行业逐渐融合,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融合出现的根源在于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内涵得到了拓展。传统出版业无法避免地将面临与“大知识产业”的竞争者们争夺用户注意力的局面 [14]。传统出版业所面临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版业科学革命的契机[15]。
数字智能时代的出版业面临的危机由知识秩序和知识内涵的变化引发,现有的图书出版范式已无法满足知识生产的内在需求,当新的可能性范式,如知乎这样的互联网企业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后,与传统的图书出版范式产生碰撞,在不斷地探索、学习合作与竞争中,能够满足数字智能时代知识内在需求的新型出版范式也终会达成。
3 数智时代出版范式及转型构想
3.1 跨媒介叙事中的内容生产
媒介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出版活动和知识的传播。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来强调媒介强大而无形的塑造力。媒介环境于人就如同水和鱼的关系,“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16]。当人们从印刷媒介“移民”到电力媒介,才恍然惊觉新旧媒介于人的影响和意义。而如今,我们身处一个“万物皆媒”的全媒介世界,互联网不仅连接了个体,重塑了社会组织结构,互联网也连接了从古到今的一切媒介内容和形态,从声音、文字、影像(静态和动态),到口语、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直播、全息投影等。跨越媒介的叙事成为可能,媒介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基于此提出了“跨媒介叙事”的概念:一个跨媒介的故事横跨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一个媒介平台都有新的文本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的、有价值的贡献。每一种媒介都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17]。跨媒介叙事已然成为数智时代内容生产的趋势,但出版实践中如何运用跨媒介叙事理论进行内容生产,需要重新回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这一视域中。麦克卢汉强调一切媒介均是人感官的延伸[18],启示着出版人去理解和甄别每一种媒介形态唤起的感觉和知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利用和开发。
听觉—声音。声音在当下的数字出版实践中,以有声书作为最主要的产品形态。声音作为媒介,调动起人的耳朵,给人带来比“冷静的眼睛”更浓烈的情感。以声音作为媒介形态的内容也应与之相符。具体而言,如虚构类的小说等文学作品,相较理论性的学术著作等更适合以有声书的形态来传播。在针对微信听书用户的调查中,用户收听有声书的内容以文学类书籍为主,尤其注重内容的感性价值,专业性、学理性较强的书籍收听状况不理想,呈现极度“重文轻理”的态势[19]。
在人工智能技术下,有声书的声音分为真人语音和AI语音两种。二者的优势和劣势同样明显。真人语音比AI语音更让人共情。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声书会邀请演员、主持人等知名人士参与创作,献声主体也为有声书增加了新的叙事维度。但真人语音在制作上面临人力成本高、制作周期长、转化效率低等现实困难。AI语音使听众情绪参与度变小,但AI语音的优势也在于制作周期灵活、生产速度快、成本低等。随着AI语音技术的逐步成熟,AI语音也会占据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真人语音并不会消失,反而会以更加精准的策划、更加优良的制作服务于一些更具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的项目。
视觉—影像。人首先是视觉的动物,通过眼睛把握外部世界。相比声音,影像更有利于观者进入具象的空间中去把握意义。同时,影像也刺激着人的互动反馈机制。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移动技术的推动下,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视觉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6.9个小时,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44亿,较2020年12月增长1707万,占网民整体的93.4% [20]。更进一步而言,以网络视频为首的影像形态已成为当代人视频化生存的重要内容、形式和场景。我国的图书出版实践如何把握、利用好影像的力量,是迈向融合出版的关键。
我国目前的出版实践中,对影像的运用多停留在营销层面,利用“直播”和“短视频”等形式为新书做宣传,目的是增加图书的销量。在这个意义上,影像的运用并没有进入图书出版的内容生产环节,而是停留在销售环节。融合出版的实现首先要求知识生产主体对知识的内容进行多媒介形态的开发,以文字、声音和影像作为叙事的延展,形成与特定媒介所匹配的内容。除此之外,对影像的利用也应突破既有形式的想象。具体而言,除了直播、知识类短视频、纪录片等已经应用于出版实践的影像类型以外,还应结合新技术利用VR、AR等技术开发更多形态的影像类型。第三,对于影像的理解也应在虚拟和真实的各种媒介中不断穿梭,打破时空的想象,将线下的视觉内容变成线上的影像进行传播。
3.2 公共文化属性的知识服务平台
互联网、物联网、移动终端等数字智能技术将人、货、场连接起来。这也使得图书出版活动,在内容生产方面走向跨媒介叙事,在传播渠道上多种媒介渠道融合展开,受众层面也在社交媒体等平台接收和反馈信息,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数字智能时代的图书出版必将走向全场景时代。具体而言,图书出版活动以场景为纽带、以体验为核心,通过构筑新的关系网络,完成图书出版向融合出版、体验营造、关系生产和社群服务的转向[21]。
“平台”隐喻着一种资源的聚合场域。传统出版业在搭建资源平台时,首先应注重多元主体的互动,调动多方的积极性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聚合效应。第二,应关注用户的体验与反馈,及时了解用户的需求,通过跨媒介叙事满足用户的多重体验。公共文化属性则强调知识生产的社会效益。用户进行知识生产时的差异化选择以及平台企业的逐利性势必导致公共属性的部分流失。这时传统出版业在知识生产上的专业优势便可凸显。要求出版人立足自身的专业优势,发挥“知识守门人”的社会文化责任,积极变革出版理念,吸纳新的出版范式。只有出版人的理念产生转变,新的出版范式才能真正付诸实践。
注 释
[1]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6
[2] 孙玮,李梦颖.数字出版:超文本与交互性的知识生产新形态[J].现代出版,2021(3):11-16
[3][9][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05-578
[4][5][8][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著;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8-367
[6][7][韩]康在镐著;孙一洲译.本雅明论媒介[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9:27-29
[10][11] 师曾志.生命传播:自我·赋权·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46-347
[12] 刘欣.互联网时代重提异化的主体性:以生命传播的视域[J].台州学院学报,2022(2):67-72
[13][14] 方卿,王一鸣.论出版的知识服务属性与出版转型路径[J].出版科学,2020,28(1):22-29
[15] 师曾志.网络环境下出版理念的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13-118
[16][1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52
[17]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YU Press,2006:105
[19] 姜澤玮.内容、形态、场景与满足:移动新媒体有声书的用户使用研究—以移动应用“微信读书”与“微信听书”为中心[J].出版科学,2021,29(5):31-40
[20]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2-06-02]. https://cit.buct.edu.cn/2021/0925/c7951a157922/page.htm
[21] 马廷魁,刘岩.场景、体验、连接、社群:图书出版3.0的新进路[J].中国编辑,2021(3):86-91
(收稿日期:2022-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