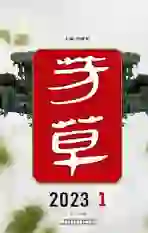说到文学批评,我只是一个迟到者和晚熟的人
2023-05-30何平
何平
我们做文学批评的前史是文学青年,不是做论文的专家学者后备军。我生于一九六八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的文学前史大多数是文学青年。我的文学青年期是蹩脚的诗人加拙劣的先锋小说仿写者。上个世纪末进入文学批评之前写杂七杂八小东西的十几年,这里包括曾经作为中学生、大学生“文学社诗人”和一个失败的先锋小说仿写者的学徒期。我高中念的是后来大众传媒聒噪得很厉害的县中样板海安中学。那是一九八五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历史时刻。电影《妖猫传》里空海说:“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八十年代好像也差不多吧。从高中开始写诗,一直写到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今天看也就是一个混文学社的“文学社诗人”而已。
作为应试教育的获益者进入大学中文系,我只是一个没有多少外国文学阅读经验的文学“小白”,不可能像资深的外国文学读者那样轻易识别出他们各自的母本。于是,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成为我八九十年代小说写作尝试最直接的范本——依样画葫芦写出了自己的一批所谓先锋小说。如果像后来研究者所指出的,八十年代先锋作家们往往都有他们的外国文学母本,无疑我只是一个更拙劣先锋“国潮”的仿写者。至今还记得我模仿格非的《褐色鸟群》写了一篇题目叫《三路车通向》的小说。三路是南京一条环形公交路线,沿途会经过大学、精神病医院、教堂、商业区和民国街区等等,这些城市地标在我的小说都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其实只是一层所谓形而上的浮沫。这篇小说后来被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本科同学拿过去,据说发表在他们学校的研究生刊物上。显然,马原、残雪等的先锋小说“正品”依然在场,我的这些当场复制的赝品不可能获得多少发表的机会。
应该说,同时代写作者,我不是个例。去年,写一篇邱华栋的文学批评,得以读到他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早期小说,我发现这个中学时代的文学“发小”,也有类似先锋小说的仿写阶段。事实上,我最后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也没有学成一个小说家。但是,这十几年横冲直撞的瞎读瞎写,或者是你说“野蛮生长”和自由写作,对我后来的文学批评生涯至关重要。我,或者复数的“我们”并不像现在很多的年轻写作者在文学学徒期就明确地要做一个小说家、诗人或者批评家。
再说我的个人阅读史,青年时代的阅读也不是为了写一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以也读得很“野蛮”。尤其值得说是,我们八十年代并没有一个特殊的读“儿童文学”的阶段,也没有谁要我们一定要读规定的经典。印象中,从初中开始的十四五岁,就读同时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最初的就是张贤亮、张洁、王蒙、铁凝、贾平凹那拨人。同时代作家对我们的精神成长,是日常生活的、人性的、审美的,包括青春期爱与性的启蒙也是从《小月前本》《祖母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这些小说获得的。
我的本业是在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教书、做课题和写论文是我的日常工作。一九九八年,在写了十几年杂七杂八的小东西之后,我在如皋师范同事、批评家汪政的鼓励下试着转到文学批评。这个时间不长。二〇〇二——二〇〇五年,在毕业十年后,重返大学读书,博士论文做的是史料和文学史研究。从我在职读硕士学位开始,我的导师朱晓进教授就说,我知道你会写文学批评,但你现在先把文学批评放一放,你我做文学史研究。前后六年的纯学术训练对我影响特别大,再做文学批评时,我会把它放在一个更宏观视野和历史维度中间去观察。博士毕业之后有两三年,也想再拾起文学批评,但恢复得很慢。直到二〇〇八年,我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做文学批评。这是一次“批评的返场”,发生在四十岁的年龄之上。
文学批评参与到文学生产和公共生活是我的文学批评理想,感谢为了这个理想和我结伴而行的同路人。从二〇一七年第一期开始至今的六年三十六期,我在以先锋和探索见长的《花城》杂志主持“花城关注”。我把主持这个栏目的实践定义为“文学策展”。其间得到前主编朱燕玲的《花城》编辑团队的全力支持。作为支持的体现,六年来,我策划了三十六个专题全部按我的设想完成。也是从二〇一七年,我和复旦大学金理教授共同召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至今已经五期。工作坊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得出什么结论,而是一种讨论文学的态度和风气。二〇一八年开始,译林出版社的原创文学出版团队参与到我的批评实践,和我共同编辑“文学共同体书系”和“现场文丛”,并且和中国作协、南京师范大学一道共建世界文學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暨出版中心。正是这些介入文学生产的实践使得我理解的当下文学是过程性的,也使得我有可能真正扎根在文学现场,从而有可能不断拓殖中国文学版图,同时捕捉时代审美动向。
新世纪前后文学期刊环境和批评家身份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刊物会自觉组织文学生产。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思潮,甚至每一个经典作家的成长都有期刊的参与,但当下文学刊物很少去生产和发明八九十年代那样的文学概念,也很少自觉地去推动文学思潮,按期出版的文学刊物逐渐退化为作家作品集。与此同时,批评家自觉参与文学现场的能力也在退化,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几乎等同于论文写作。“花城关注”从艺术展示和活动中获得启发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学习,更为自觉地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对我来说,栏目“主持”即批评。通过栏目的主持表达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臧否,也凸现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审美判断和文学观。“花城关注”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念,这样短时间可能会博人眼球,但也会滋生文学泡沫,而是强调批评家应该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一定意义上,继承的正是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实践精神。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每年召集作家、诗人、艺术家、编辑、翻译家和出版人等与上海和南京“双城”青年批评家共同进行主题性的研讨。五期工作坊的主题分别是“文学的冒犯和青年写作”“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以及“文学和公共生活”。工作坊不局限于文学,也非狭隘的同人沙龙,而是一个聚合青年力量研究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一个开放、协商和对话空间。除了“花城关注”和“双城文学工作坊”,我这些年还和译林出版社合作一个三十五岁以下青年作家出版的长期支持计划“现场文丛”。金理曾经说过这三个项目之间的关系:“花城关注”以沉浸于第一现场的姿态发现新人、新论域,“双城文学工作坊”对新人、新论域出场过程中的症候性问题予以理论研讨,“现场文丛”则为经受了出场考验的文学新人提供长线支持。
今年在做一件事,给《小说评论》杂志主持“重勘现象级文本”栏目。一起做前期准备工作的博士生问我,怎样才能算得上现象级文本?我的想法是,虽然现象级文本有这样那样的指标,但最基本的指标肯定应该包括公众认知度。当然,我们不是以读者多寡来论文学成就。考虑到国民的普遍审美水平,如果把读者多寡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排名靠前的作家,可能并不能代表我们时代的文学成就。但意识到国民审美出了问题,更加要思考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我们在确定这四十余年来的文学现象级文本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九八〇年代是文学现象级文本最多的时代,越到靠近,现象级文本越难找。这里面当然有文艺生活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学在今天很少主动地参与公共生活和国民审美建构,也不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还记得二〇〇二年春天的某一天中午,我走进颐和路的江苏作协大院,那是我第一次和作协有了关系。这一天下午,我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入学面试。也许这是一个暗示,正是这一天大学和作协在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交集。从此,大学和作协成为助力我文学批评的两翼。这二十年,我一直生活在南京。在南京做文学批评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南京作家群充满活力且可持续生长;以大学和作协为中心的批评家群落互动互渗形成代际承传的南京文学批评传统;文学教育资源丰富;作家和批评家相互激发共同成长;市民日常文学生活参与程度高,是作家做文学活动的重要到达地,可能还要包括政策扶持和常态化的文学批评奖项设置等等。如果像选宜居城市那样,选宜文学生长的城市,这三四十年来的南京应该算一个。在南京做文学批评,南京是一个城市文学含量高的城市,我的文学批评是南京这座文学城市的批评传统滋养出来。
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真正的江苏批评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一九九二年从南师大出去工作,十年后,又回到南师大读书和教书。生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和同一个代际的批评家相比,我是一个迟到的进场者,一个文学批评的“晚熟的人”。一九九八年,我开始尝试做文学批评的时候,我的同代人都已经是成名的批评家了。举一个例子,《南方文坛》有一个坚持多年的栏目“今日批评家”,二〇一〇年一月,我是這个栏目推出的最后一个六〇后批评家。一个迟到者和晚熟的人,一直得到很多前辈和老师的鼓励和帮助,比如我的导师朱晓进教授和他们同时代的学者,比如作协的文学生产的组织者——他们许多就是我的前辈、兄长辈和我同时代的批评家,比如刊物的编辑。说到刊物的编辑,我的文学批评其实就是和一个个编辑老师的相遇,做文学批评的这些年,许多编辑老师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予过我无私的帮助,我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那些让我回忆起来就心生温暖的人和事,我特别要提到《名作欣赏》的解正德、《当代文坛》的黄树凯、《文论报》的李秀龙、《南方文坛》的张燕玲和《钟山》的贾梦玮等老师,他们的帮助都是发生在我做文学批评的起步阶段,一个晚熟的人,也是一个无名者。而今年五月刚刚去世的林建法先生,从二〇〇八年和他认识一直就是人和文的引领者。我在《批评的返场》后记里说,这本书曾经想用的书名是《有文学的生活》以纪念这些年赋予我丰富文学生活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爱与热情。
(责任编辑:宋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