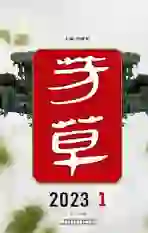我们村的百岁老人
2023-05-30李传锋
我们村的钟伍生老太太去年成了百岁老人,儿孙一百多人从各地赶回村来给她祝寿。五世同堂,寿衣寿帽大蛋糕,她坐在堂屋中央,长子长婿儿女分列,各率子孙一批批给她拜寿,其乐融融,政府还专门派人送来了寿礼,全村家家都来人致贺,一时传为美谈。
我国现阶段以六十岁以上为划分老年人的通用标准。六十到八十九岁为老年期,我们称老人;九十以上为长寿期,我们称长寿老人;而一百岁以上则称百岁老人。健康长寿是人生的美好愿望,但真能活过百岁者寥寥矣!
一个偏远山村的老太太能活过百岁?她有什么特别的长寿秘诀吗?钟伍生老太太的长寿是否另有诀窍?这便是我想采访她的动因。
鹤峰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南角。在东经110°和北纬30°神秘交叉点上。上六峰村则处于鹤峰县的东南角,往西走十几公里是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湾潭镇,翻过东边的山就是湖南省的石门县,这里海拔接近一千二百米,森林覆盖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四面环山的平地,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显然是一个十分宜居的地方。
百岁老人的长媳陈次英带着我去看望钟伍生老人,陈次英也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老媳妇负责照顾百岁老婆婆的起居生活。这是一栋陈旧的木房子,大门开着,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大门边打盹,夏末,她还穿着红花夹袄。这就是钟伍生老太太,五月份过了一百零一岁生日。陈次英对她大声说:“山边李家的老幺来看望你!”陈次英说了两遍,老人一时没弄明白。也难怪,我离开村子已经五十年了。陈次英递给她一杯白糖水,她喝了一口,认真望了我几次,还示意我走近些,她看了看,还是想不起来。她开始讲话,声音洪亮。她把我当成了政府派来看望她的“工作同志”,她说她的“后事都准备好了,不会麻烦政府。”老人的生命之旅已经走到了天堂的门口,她很坦然地关注着自己的后事。我沿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见堂屋墙边停放着一副棺木,这副棺木做得很气派,刷了几遍生漆,油光水亮,那是老人死后要长眠的房子。
第二次来,又只有陈次英一个人在家,她丈夫钟福兴上山摘簝叶去了。我们又聊百岁老人,陈次英对我说:“我婆婆没读过书,生的孩子也都没读好书,大儿子钟福兴只读到三年级,弟弟妹妹最多也都只读到小学。”这些情况我知道,那些年,钟伍生正上伢儿滩,不想生也没办法,就一个接一个生,一般家庭很难顾及孩子的学业。尽管政府一再强调要上学,但农村家庭认为孩子能认几个字,能算账,就算有了文化。
在陈次英印象中,钟伍生一生没生过病。她说:“去年,她满了一百岁,喊不舒服,我们急忙把她送到走马坪医院去检查,医生检查之后说她没什么病。在这两年疫情期间,我们几姊妹轮流守护她,两个人一班,守了几个月,她日夜没有瞌睡,要烤火,一个冬天烧了几万斤柴。”
陈次英负责给老人弄饭吃,我问老人吃些什么?陈次英说:“现在,她每餐吃点米饭,一碗和渣,一两坨肉,昨天还吃了几个小洋芋,每天一杯白砂糖水是一定要喝的。”
我問:“老人家一天吃几餐饭?”
陈次英说:“一般都是吃两餐,夏天日间长,就吃三餐。”
我问:“现在生活改善了,还是只吃两餐?”
陈次英说:“是的,习惯了。现在,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弄什么。前些天,她说她做梦吃粽子,我就给她包,她也只吃几口就不吃了。”
我说:“陈姐,我想问一个不好问的问题,老人五十多岁就守了寡,伢儿又多,她就没再找个帮手?”
陈次英说:“我婆婆儿多母苦,走了三个男人,不想再找,就一个人拼命做,想办法把小的养大。”
在一个下雨的日子,我终于见到了钟福兴。他是百岁老人的长子,我们熟。我一九七〇年在生产大队当书记时,喊他大钟,因此,我们的谈话无拘无束。老两口精神矍铄,我说我想了解有关长寿基因的问题。大钟告诉我,他爷爷死得早,婆婆眼瞎,双目不见,名叫廖四姐,是燕子坪瓦屋场人。钟家在上六峰这边有一庄地。他说:“我妈九岁就和我婆婆两娘母过来安家,那也就是逃难。我婆婆活到七十多岁,那时候的人算长寿,是我养我葬的。”
我问:“你妈最远到过哪些地方?”他说:“最远只到过县城、湾潭、南北墩。”他说的这些地方我都走过,到县城一百二十里山路,要走两天;到湾潭四十五里山路,要走半天;到南北墩三十里山路,十五里下坡,一天可以打个回转。
他说:“我婆婆爱唱歌,那时候生产队白天下苞谷,打夜工撕苞谷,还专门把我婆婆请去给大家唱歌解闷。”
我问:“你妈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吗?”他说:“我妈从小就爱吃糖,一直到老,不吃蜂糖,不吃红糖,只吃庆糖,庆糖就是苞谷熬的糖,后来才吃到外面来的白砂糖。我前年接手赡养她,前后称了百把斤白糖,她吃饭都要掺糖。”
我问:“你们家喝的水是哪里来的水?”他说:“都是吃的大沟里的水,我们从前挑水吃,后来才改成自来水。我们这一条山边,家家吃的都是大沟里的水。”他说的大沟,是他屋旁一条几里路长的山沟,没有人烟,大山含蓄的山水慢慢渗出,形成很多山泉,汇成一条小河流出。我想,吃这条水的长寿老人比较多,肯定和这水有关系。
我当回乡知青时,钟伍生是队里的强劳动力。那时候,妇女五十五岁就下劳动册,男人六十下劳动册。我就问:“你妈做工夫做到什么年纪才歇?”其实,农村人无所谓退休,在劳动册的必须出工在集体做事,下了劳动册,可以不出工了,又在自留地里干。自从分田分地责任承包,那就一直干,干到干不动了才能歇。
他说:“我妈九岁过来就开始做事,八十多岁时她还上后山砍竹竿,还和媳妇比赛,九十五岁她还种地。她喜欢吃白苞谷,就自己种了一块。她九十九岁还下地扯草,满一百岁了,还能从柴屋里自己抱柴烧。”
我认为,一个农村妇女,生了十个儿女,对身体伤害一定很大,就问:“能谈谈你妈的几次婚姻和你的兄弟姐妹吗?”
他说:“我的亲生父亲叫陈国安,是下洞后坪人,生我和家福两弟兄,因为父亲有外遇,后来离婚了。父亲是七十多岁病死的,我还去看过。第一个继父谭冬林,湖南慈利匣儿桥人,是打三棒鼓上来的,生了三个,桂英、三秀、登高。继父以挑力为生,后来在湖南受了伤,不久就死了。第二个继父闵远成,下六峰湖盔人,生了珍英、梅英、伏英、申英、国志五个。闵家爹后来是吃蜂糖中毒死的,还只六十多岁。他的死对妈打击很大,从此没再结婚,独自把未成年的儿女抚养大。”
陈次英在旁边补充:“婆婆说过,一窝伢,只有老头儿生,没得老头儿养!”
大钟说:“生活所迫,我妈个性很强,死命地做。”
村子里也有人说,钟伍生爱噘人。我们村的地方话,噘人就是骂人。谁惹了她,她就骂,乱骂,子女惹了她也骂。我想,骂人虽然不大文明,但在农村,妇女、弱者,特别是孤儿寡母,骂人是一种自卫的方式,也是一种情感释放。但她这人爽直,骂了,吵了,就算了。
钟伍生没有能力把十个孩子送上学深造,但她严格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她的子女,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很能干,一个个都是种田的好手,是理家的好手,这在村里是被公认的。
我对大钟说:“请你谈谈自己。我看你也要活过百岁的。”
他笑起来,说:“我九岁就开始割草喂牛,十二岁开始打转工。今年冬月满八十五岁,搞了一辈子生产。现在,子女都不在身边,和堂客还种了三亩地,主要是种苞谷,养了三头猪。”一谈到猪,他就神采飞扬。说个好玩的话,他一生除了和人打交道,再就是和猪打交道,欠下了无数条猪命。他不无骄傲地说:“我从二十六岁学杀猪,是跟着寇家老爹学的。师傅后来把全套工具都送给了我。我一直杀到八十岁,八十岁过生那天,我在去大山坡猪场一天杀了十三头。”他说:“我一生爱好赶仗打猎。赶到七十多岁了,政府收了枪,我才没搞了。我曾经喂过两只好猎狗,打猎我都不用进蓬,两只狗就能把猎物咬住。我有时清早上山割一担牛草,还要挑两个猪獾子下山。我有步枪的时候,一连打过两头野猪,一个人硬搞不下山。”
宋代大诗人苏轼曾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有诗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多么惬意,多么豪迈。我们山地民族的男人没有不爱赶山打猎的,因为赶山打猎除了好玩,更可以锻炼勇武,可以保护庄稼,还可以改善生活。现在,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生态,不准再伤害山里的动物了,男人们就只能通过回忆打猎来打个精神牙祭。
我想到抽烟喝酒有损健康的问题,就问:“你抽烟喝酒吗?”他说:“我抽烟、十多岁就抽,那时只有叶子烟,喝酒不多,我爱吃辣椒。”一说到吃辣椒,他不由得又进入了豪迈回忆。他说:“骆同鹤跟我打赌吃辣椒王,如果我能吃三个就给我一百块钱。当我吃第四个时,他就不搞了。哈哈,我就从没遇到过辣的!”他也有遗憾,“我没读好书,只跟着祥先生读过二年私塾,跟传发在唐祖伦家读过冬学。”他说的祥先生是我爷爷,旧社会的私塾先生,他说的传发,是我二哥,教冬学那还是一九五一年底的事。我想,爽直而能干的大钟,如果多读些书,肯定是个出众的能人。
我问:“你除了爱吃辣椒,还喜欢吃什么?”他说:“我爱吃苦瓜蒌叶,从前是没饭吃,摘来当菜吃。我妈上山做工夫,扯一背篓回来煮了我们当饭吃。我现在还特别爱吃,我妈现在也还爱吃,野菜是百草药。”我们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把苦瓜蒌引栽在屋前屋后,春天夏天秋天都有,特别是夏天,每天喝一碗苦瓜蒌叶做的汤,能消炎解暑。”
“请问你当年多大结婚?婚姻幸福吗?两口子打过架吗?”
他说:“我二十二岁才结婚,陈次英十九岁。我脾气毛,我们一生小吵嘴是有的,但没大吵,没打过架。”说到这里,他给我唱了一曲老歌:“心肝肉儿我的妻,要我打堂客是万不能的。各人(自己)的堂客是屋上的瓦,人家的堂客是瓦上霜,太阳出来一抹光。”他两眼望天,唱得情深意切,声情并茂,陈次英就坐在旁边眯眯笑。
我问:“你唱歌是跟你婆婆学的吧?还是跟你妈学的?”
他说:“都不是的,我妈不唱歌,我是跟村里陈本善、张次英几个会唱歌的人学的。”我问:“你们夫妻生了几个孩子?”他说:“我们生了五个,现在还有三个在。七个孙子,重孙都有了。儿孙们都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现在身上穿的,吃的不用买,都是儿孙们给弄的,吃不完,穿不完。”
“你认为长寿的原因主要是什么?”他说,“我听说遗传很重要,但我们的家庭穷狠了,子女又多,必须要做,一直在做,拼命在做。这里气候好,冬天不是很冷,夏天不是很热。粗茶淡饭,这些应该也是重要原因。”大钟虽然没读过书,但他接受新知识,一个遗传基因,一个热爱劳动,一个生活环境,说得很有道理。
过了几天,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没搞清楚,就再次拜访大钟。
我问:“你妈妈从前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有睡午觉的习惯吗?”他刚从山上劳动回来,洗了手,给我倒茶,坐下来就说:“我妈一生都早睡早起。忙完家务就睡,天一亮就起床,有时天还没亮就起床做事,也不允许我们睡早床,必须起来做事。老人一生就没有睡午觉这一说。”
我问:“你妈妈每天做饭吗?她做家务和种地如何兼顾?”
他说:“我妈也做饭,但很多时候是我爹做饭,继父做饭,她主要是引孩子,里外安排,做地里山上的功夫。”
“那你继父死了,家里谁做饭?”
“我大妹、二妹、三妹,她们长大了接着管做饭。”
我问:“你妈吃过补药一類的东西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吃过,她也不喜欢吃药。”
我问:“你妈妈平时吃盐多吗?”
他说:“我妈不吃咸盐,家里穷,舍不得多放盐的。”
“你妈的牙齿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她牙齿一直很好,只掉了几颗。”
我问:“你们当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一年能吃几次肉?小时候有零食吃吗?”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陈次英,我要再印证一下。
他说:“旧社会、刚解放那些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饿饭的,吃不饱,吃草,子、鱼腥草、葛米子都吃过。我妈跟别人做事,别人把一点糠,拿回家,从山上摘些苦瓜蒌叶,调了吃。家里经常借粮,很少吃到一餐光饭。原先地就不多,土改时分了二十多亩,产量低,还是不够吃。谈不上一年吃几次肉,没粮食喂,我记得那年杀一个猪,只五十多斤重。弄肉吃还要掺些包包菜,来了客,弄点肉,妈就把我们赶到山上去玩,怕我们围着看。我们也没零食吃,别人家炒苞谷花儿吃,我们家没得多余的粮食炒来吃。”
我问:“那你们现在吃肉多吗?”
他说:“嗨!现在,天天吃肉,哪天没弄肉还好像缺了什么。”
我问:“你妈妈一生害过重病吗?受过哪些伤?被蛇咬过吗?被狗咬过吗?”
他说:“她一生就没得过大病,没有受过伤,没有被狗咬过,也没有被蛇咬过。”
我又问:“我知道你爱打猎,打猎是为了好玩,还是为了吃肉?你打过哪些猛兽?”
他说:“我们打猎主要是为了护秋,我当过民兵连长,发了步枪,成立打猎队,赶野猪,保护苞谷,当然也图个好玩。”他说:“野猪,麂子,熊我都打过,老虎只碰到过,没敢打。那一次,我想打金鸡,进大沟我站在一棵大树下听,一只大老虎突然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朝我嗅了嗅,出的气都快喷到我的脸上了,我被吓懵了,只知道后退,没敢打。”我也想起读中学时在山路上几次遇见过老虎,但隔得远,没他这样惊险。
我挖根到底,再问:“你妈妈爱卫生吗?刷牙吗?爱洗澡吗?多久洗一次?”我们村在没有安自来水之前,无法洗淋浴,只能烧了水,用脚盆洗,很麻烦的。他说:“我妈很爱卫生,每天都要烧水洗澡,冬天都洗。妈到晚年才开始刷牙,原先没这个条件。”
有人说,性爱也是长寿的原因,是多好还是少好?我不便问她妈这方面的问题,我就说:“钟哥,问一个不很好问的问题,你夫妇现在还有性生活吗?”
他立即说:“早没有了,没那个意思了,七十岁以后就差了。”
我只好转换话题:“你妈最爱吃的蔬菜是什么?最爱吃的野菜有哪些?”
他说:“我妈一生就是吃我们这里出产的青菜、萝卜、茄子、辣椒、黄瓜、包包菜一类。困难时期,油盐又少,我们吃苦瓜蒌叶、春天吃刺包坨、秋天捡核桃、板栗、洋桃,还要挖葛打蕨。”
说到挖葛打蕨,他给我讲了一件难忘的事。大约是一九五八年,家里缺饭吃,就挖葛打粉。乡长王万里看见了,说在大路边摆场子挖葛打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要张广清去把粉缸给掀了。张广清去了,看见廖婆婆母女在艰难地推磨,一次只用手往磨眼里放上几粒苞谷籽,慢慢地磨,穿的裤子都破了洞。一听说要掀她家的葛粉缸,廖婆婆腿一软就糯下了地,长声吆吆地哭。张广清是本村人,自己家也挖葛打蕨,就没掀缸,而是帮她把打葛的场子移到了湾里,放在大路上看不到的地方。廖婆婆母女千恩万谢。张广清是我表姐夫,我找他核实此事,他说这事千真万确。
我又问:“你妈有最爱穿的好衣服吗?她爱打扮自己吗?”
他说:“她当女儿时很穷,没有特别喜爱的好衣服,她一生十分节俭。最困难时候,我妈挖了宿旦去白果坪街上卖了,扯几尺白布,顺路背一块煤黑石回来,把白布染了,给我们做单衣。她到老了,特别这一二十年来,生活大大改善了,儿孙给她买了新衣,她都不肯换,说怕把新衣弄脏了,攒着。”
有人说,多吃腌菜不好,我就问:“你家里平时吃些什么?常做腌菜吃吗?”
他说:“我们家平时就是吃包裹粉子钣,和渣汤,每天都是这个,现在买米吃。从前,我们这里没有大白菜,主要是大叶青菜,萝卜菜,冬天就吃干萝卜菜煮豆儿。我们一直不大吃腌菜。”
我问:“你家是谁来腌制腊肉、薰炕腊肉?”
他说:“从前,我们家腊肉不多,有一点,腌和炕也主要是我爹做,后来是我继父做。弟妹们长大后,劳动力多了,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改善,每年都杀大年猪,但我妈还是很节俭。前些年,她杀了猪,把肉收到柜子里舍不得吃,结果都长了虫,烂了,不能吃,我们只好给她背出去扔了。”
“你妈平时锻炼身体吗?”我想到村子里的老人现在爱跳广场舞,走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问题。大钟愣了一下,笑起来,说:“她不锻炼,村子里当年搞什么气功、喝神水、打鸡血、甩手,她都不搞,就是早睡早起,搞劳动。劳动了一辈子也就锻炼了一辈子。”
大钟说得很有道理,锻炼身体是有闲人的专利,对于农民来说,劳动就是锻炼,区别只在是为谋生而劳动,还是为健康而劳动。我很想打探到一点特别的东西,就再问:“你妈妈会熬庆糖吗?家中经常熬糖和做甜酒吃吗?”
他说:“我妈会熬庆糖,从前只有过年时才熬一点,庆祝一下,又舍不得粮食,一人一小碗,尝尝。糖糟还不能给猪吃,要做粑粑当饭吃。我们家也很少做甜酒吃。”
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们家有十姊妹,都姓钟?为什么没一个孩子跟爹姓?”
他也笑起来:“是啊,很多人也问过我,你家三个爹,为什么十个孩子都姓钟?因为我妈是坐堂招夫,再加上我妈做事有些跋扈,不让孩子跟爹姓。”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爹和妈离婚之后,有一次我爹过来把我弟弟引走了,人都走到磨石垭了,我妈得信后追赶过去,硬是把我弟弟拉了回来。”
钟伍生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勤劳的双手,下决心要把孩子们养大,命运之神帮助了她,就在她生第四个孩子时,迎来了新中国。
正在这时候,门口公路上传来一阵叫卖声:“新鲜大米、猪肉、卤肉、鹅肉、鸡翅、鸡蛋、炸豆腐、生姜、粑粑、老干妈,还有苹果、好吃的柚子呀……货郎车上的喇叭一連串报出了二十多种货名。
说到现在的农村,大钟十分激动,他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哇!从来没这样好过。国家不收我们一分钱,还给我们种田补贴,样样都给我们照顾得周周到到,你看,过去赶个场难上难,现在公路修到家家门口,你想要什么都给你送上门来,孩子们还在手机上买东西。”
我问:“那你们什么时候才过上不焦不愁的生活?”
他说:“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重新分了山分了地,良种、化肥、地膜,搞多劳多得,收成就好了。再说,弟弟妹妹们慢慢都成了家,侄孙辈有好几个都参加了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现在都修了新房子,日子越来越好了。村里很多人家都买了车,出个门,赶个场,上医院都方便得很。你看,货郎车从门口一天跑无数趟,想吃什么买什么。”
是的,百岁老人虽然不能坐车出门了,也很少买东西,但每当她坐在家门口,看着山村的振兴和变化,心中无比的高兴。家边只隔一个围墙就是上六峰小学,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下课之后的欢笑声时时传过来,让老人感到无比的欣慰。
“政府对老人家进行特别照顾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九九六年我们县里开始有高龄补贴政策,每月补助几十元,后来几百元,我妈成了百岁老人之后,政府加大了照顾,还有低保、医保、护理费等等。”
钟老太太的大女婿田登进是退休教师,他也是过了八十的老人,还帮岳母管过一段账务,在钟家是很受器重的人,我想听听他对钟老太太长寿的见解。
在一个下着细雨的下午,我到了田老师的家,他正在和两个年轻人打上大人,见我登门,就散了场。听了我的来意,他略微思索,就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很启发人。
田老师说:“老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结婚之前一段,很穷;养育孩子階段,很苦;进入老年阶段,无忧无虑。”
钟伍生大儿子钟福兴今年满八十五周岁,这么推算,钟伍生就该是十五岁结婚,十六岁生孩子。这一阶段,处于旧社会。她做少女时就随母亲来上六峰村安家落户,孤儿寡母,她的少年是很短暂而艰难的。第二阶段,是她的青春岁月,却早婚早育,时值旧社会的末期,兵荒马乱,新中国的初创期,百废待举。一九五四年发大水,后来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吃食堂,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国民经济大调整,日子稍有安稳又是十年动乱。这一阶段,三次婚姻,养十个孩子,其艰难窘况可想而知。第三阶段,她进入老年,国家迈进改革开放新阶段,脱贫致富,这时候老人才真正歇下来,过上不愁吃不愁穿安居乐业的日子。
田老师说:“进入老年之后,社会安定,生活无虑,精神上不再有什么大负担。而所谓营养品,她都不吃,过怪了穷日子,儿孙给她买的水果、糕点她都放着,攒着,结果放烂了。她一生粗茶淡饭,不暴饮暴食,即使后来生活条件大改善,她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所以,身上就不存在吃出来的那些病。”
“儿女个个都好,热爱劳动,和睦顺利,没有让她怄气。她和亲戚们的关系也都很好,还教育儿女孙子们要孝顺,要立志。她的孙辈中有很多个上了大学,有了不错的工作,这让她很满意。”
我说,老人操劳一生,前半生吃尽了苦,终于赶上了好时代。她的前半生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拼命劳动,她的后半生还坚持劳动,那是习惯性热爱劳动。
我对百岁老人从来没害过病持怀疑态度,就问田老师。田老师说:“农村把头痛脑热,皮肤发痒,劳累酸痛不当病,她还是生过病的,但没生过什么大病。现在村里有了卫生室,刘医生时常上门服务,我有时也去给她拿点药,但我岳母娘没有什么严重的养身病。”
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现在已经不灵了。上六峰村的老人绝大多都能超过了七十岁。这日子过得快,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怎么一眨眼就过了七十岁!”
是的,上六峰村的老人们迎来了好日子。全村九百人,六十岁以上的有两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岁以上的有八十九人,八十岁以上的有二十四个。我们数了数,先后故去的长寿老人,就有十几个。
同样是这个村,同样自然环境,同样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从前,他们为什么就“人生七十古来稀?”而现在有了很多长寿老人,还有百岁老人?我发现,社会对人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除了自然环境因素,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大变。从前,社会动荡,在贫困中挣扎,人生充满焦虑和不安,生命的蜡烛就燃烧得很快。如今,人们终于摆脱了贫困,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服务的加强,人们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居乐业,温饱无虞,有了慢生活,才得以谈论养生长寿。
大众长寿,已经成为我们新中国标志性社会概念。解放初,我国人均寿命五十多岁,短短七十多年,我国人均寿命已提高到近八十岁。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长寿老人也会越来越多,百岁老人也就不稀奇了。
(责任编辑:王倩茜)
李传锋曾任《今古传奇》主编、编审,原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小说曾两次获得全国民族文学“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