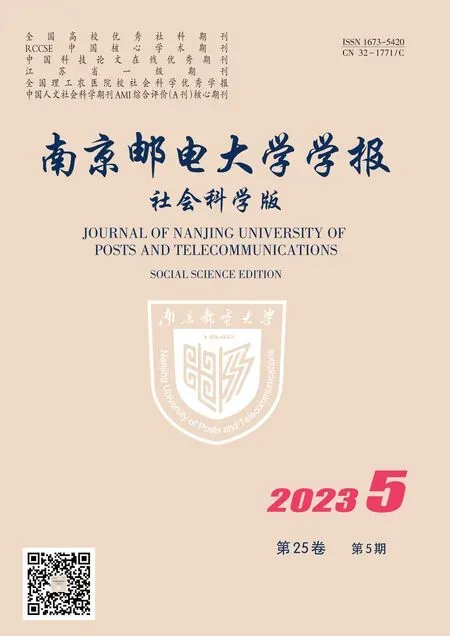出版、销售与邮政发行:清末新式官报传播体系的形成
2023-05-15程河清
程河清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为了推行新政,袁世凯率先创办了《北洋官报》,在直隶地区开展官方办报活动。此后,全国各省接连筹办地方官报,共同构筑了以官报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渠道。新式官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部门公开发行的报刊,专载政治文牍,借由官方邮政发行,成为清廷宣传网络的重要环节。
既有研究探讨了官报传播体系在内容层面上的形塑与宣传,认为其通过话语实践维护官方立场,开辟了传递各类新学、新知的窗口。朱荫贵认为,《商务官报》对世博会的介绍与相关报道体现出中国努力观察、探索世界的积极态度[1]。杨莲霞提出,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介利用改变报章书写文体、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都海虹等人指出,《北洋官报》对清末新政的大量报道,维护了清廷的官方立场,强化了价值认知[3]。刘琼分析了清末官报与邸报传播内容之差异,认为新式官报的时政信息传播开辟了官方信息传播的新局面[4]。上述研究较多关注的是文本内容与传播体系之间的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传播体系在物质层面的建构,尤其是报纸的出版、销售与邮政发行。事实上,一个高效的传播系统无法离开外部环境中发行、交通、运输环节的物质支持。基于此,本文试图深入探讨构建新式官报流通网络的物质性因素,并认为这些决定了一个传播体系是否畅通。
一、公开出版:及时刊布政治信息
新式官报是政府公开出版发行、面向大众的官方媒介,这是其区别于邸报的重要特征。此前,政府不对外发布朝堂新闻,传抄邸报一度被视为违法事件。1851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大规模出版邸报,却遭到咸丰皇帝申斥,“若令其擅发钞报……不但无此体制,且恐别滋弊端”[5]92-93。这表明官方不愿公开官员奏折,认为邸报无须传入民间。
清廷宣布实施新政后,各省政府首次以定期出版物的形式,面向民众发布政令,宣布政情。新式官报成为公布官方信息、政治新闻的权威渠道。第一批成立的官报由地方督抚操办,《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佼佼者。报纸分设谕旨类、奏折类、文牍类、函电类、法令类、论著类、记载类、调查类、表式类、图书类、广告类等栏目[6],以皇帝谕旨、臣僚奏章文牍为主。地方新闻是各省官报特色,可以及时传递本地政事。譬如,《秦中官报》称“秦中政治故秦中属吏所宜详”[7];《南洋官报》“以两江奏牍为主,而宁省督辕批牍尤为扼要”[8],较多关注本省新闻。
地方政府逐步公开信息之后,中央政府顺势成立了《政治官报》,旨在公布与“预备立宪”相关的一切奏章文牍。至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创办了新式官报,官报传播体系正式形成。1907年,御史赵炳麟上奏呼吁中央政府公开改革信息、国家大事,“凡一切立法行政之上谕及内外大小臣工折件,无论准议、议驳,皆由军机处另缮副本,交局发抄”[9]1060-1061。随后,清政府责成考察政治馆研究这一提议。考察政治馆认为赵炳麟的奏折不无道理,1907年4月17日,该馆请奏专办政治官报,拟定每日发行,建议发抄军机处各件,清廷后批准。同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这意味着一个自上而下、自中央到地方的媒介格局基本搭建完毕。
除了中央、地方政府外,其他官僚机构也筹办了报纸,宣传自身方针、传达各部门政策。这些专业型官报多点开花,涵盖教育、商业、农业、司法等领域,不断拓展官报传播体系的深度和广度。譬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旨在“发表商部之方针、启发商民之智识、提倡商业之前途、调查中外之商务”[10];贵州学务公所创办的《贵州教育官报》旨在“收罗关于全国学务及本省教育之事件,以便教育界中人有所考查及取法”[11],传播专业资讯。种种类型不一、内容多样的官报确保在每个重要部门都建立了发声渠道,是传播组织的纵向延伸。
在发布官方文牍、时政新闻方面,官报具有绝对的渠道优势,民间报刊往往以其为准。通常来说,政府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省城公牍由各衙门局所文案随时择要选出”[12],由书吏抄送至官报局,后登报公开。正因官报能够获取一手信息,《申报》《时报》《大公报》等民间报刊经常转发官报的政治新闻。如,1903年9月,《申报》刊登了袁世凯、张之洞请求递减科举名额、专注学校的奏折,并载明了来源于《北洋官报》,“此折见北洋官报,篇幅甚长,容俟明日续录”[13]。此外,官报文字可信,不像民间报刊语多失实。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北洋官报》对战事的报道准确、及时,成为其他官报的信息源。南洋官报局指出,民间各报多传风闻之事,惟《北洋官报》真实可信,“因北洋冰冻函件阻滞,各处电传动多歧互,仍未敢以风闻之事,草率付刊,现阅北洋官报日俄战纪,语颇详备。北洋文件最近所纪,当可征信”[14]。综上,新式官报的官方立场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高是其有别于民间报刊的重要标志,也因此具有权威性。晚清都察院御史陈善同在参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奏折中提及,“臣阅官报内载:‘本月初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片奏委应德闳署理藩司’”[15]142。可见官报新闻报道准确可靠,是官员们的主要信息来源。
新式官报出版后,刊载政令文牍、宣传改革法律,公开面向民众发行,因权威、真实的新闻报道而受到了广泛关注。辛亥革命前,中央、地方政府、官僚机构已建构起以新式官报为核心的信息流通渠道,向不同读者群体传播时政新闻。中央官报侧重公布朝廷改革的信息;各省官报偏向发布本省公牍与新闻,强调地域性;专业性官报报道各行各业的政策法令。
二、派销为主,代销为辅的销售途径
新式官报以派销为主,凭借行政指令销售至全国各地,体现出官办性质;以代派销报为辅,主动走进读者市场。通过派销与代销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官报流向政府官员、学堂学生、军营将领等读者群体,实现了报纸发行区域的全方位覆盖。
(一)自上而下的垂直派销模式
派销,即由上级政府指定下级政府订购一定数量的官报,利用行政手段,层层分派报纸。新式官报的派销分为两种:(1)上下级派销。中央或地方官报创办后,官员饬令“本省各署局、公所、学堂、军营以及绅商两界”[16]59订阅官报。(2)平行派销。督抚之间互相派销官报。如《河南官报》开办后,巡抚部院除了在本省札发官报外,还将报纸寄送江苏省督抚,希望其饬令派销。两江总督周馥随即应允,要求下属订购《河南官报》[17]。
派销模式体现出两种特征:第一,借助行政手段实施,基层部门、官员将订报作为政治任务,售报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律,而是依照官方命令。处于官府管辖范围内的机构,都须将订购官报作为政治任务执行。譬如,“预备立宪”后,许多省份开始实行地方自治,相继成立了一些自治机构。吉林省督抚称“正宜藉官报以为之先导”,要求这些新办的半官治半自治机构“一体认销”官报[18]。第二,将资金压力转移到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要求学堂、官署等共同承担报费,最终形成中央政府/部署—地方政府/部署—基层府州县—学堂、官署、士绅的派销链。地方政府根据各县规模大小规定各州派销份额,如四川省要求全省大县每期订阅二百份《四川官报》,中县一百份,小县五十份[19],将报费负担转移到基层行政机构。地方学堂、官署处于传播链底端,必须缴纳上级分配的摊派费,如上海县曾强制学堂绅董购阅《南洋日日官报》,由县派人收取报价“每月大钱三百文”[20]。
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派销模式,报纸发行网络延伸至全国各地。中央官报基本覆盖了省城及边疆枢纽,《内阁官报》的派销范围涵盖了清朝境内二十二省及特殊政区,绥远城将军、伊犁将军、青州副都统等偏远地区的官员都能收到派销的官报[21]。与此同时,省级官报很好地填补了中央官报空间分布的缝隙,将报纸发行区域延伸至各府州县。
(二)横向流动的代销模式
派销使用行政手段销售报纸,代销则仿照商业报刊售报模式,将报纸发行业务承包给私人。代销,指的是在本省或外省设立铺保,一般是由商务局、书局、报馆、学堂来销售报纸。没有官报局颁发的执照,代派处不得擅自设立分局。许多官报局积极招徕代派处,邀请各局与之合作。外地记者也可以代销报纸,如《南洋官报》申明,“本局外埠访事各友愿为代销亦可承认”[22]。
一方面,代派处根据销售量多寡赚取提成,刺激商贩推销。《南洋官报》代派处称,“本埠销报五十分以上,外埠三十分以上,于报价内酌提二成作为经费”[23];《吉林官报》规定,“按日代派册数在五十册以内者,照报价扣二成,五十册以外扣两成五,一百册以外扣三成,邮费不扣”[24]。另一方面,官报利用代派处的广告宣传扩大影响力。为了推销报纸,代派处会为官报设计广告,大肆宣传。北京琉璃厂有正书局为《北洋官报》撰写了广告词,指出“首录宫门抄、上谕……实与各报风闻记录者不同,且卷首用新法续印照相一页,专印各处风景,此亦本报特色之一端也”[25]。这条广告中,有正书局特意强调《北洋官报》的特色,认为该报贵在记录真实而非有闻必录,使用最新照相技术印刷各地风景,凸显它与其他报纸的区别,希望吸引读者关注。
通过全国范围内代派处的销售,新式官报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大城市大多设有多个官报代派处。上海的申报馆、农学报馆、中外日报馆等处可以购买到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商务报》[26]。天津城内的城隍庙两等官小学堂、乡祠南李茂林售报处、锅店街文美斋、锅店街宜阑堂、机子胡同同文仁、北马路东亚公司、东马路教育图书局等地都设有《直隶教育官报》的代派处[27]。海外书店甚至也代派官报,位于日本东京神田南神保町七番的古今图书局售卖《商务官报》[28]。该局由华商创办,声称与内地书局联系密切,能够及时寄发杂志,“凡中外关于祖国各大报馆,本局立有特约,各种杂志新闻尽先寄卖”[29]。
派销模式偏重自上而下的覆盖,代派模式则很好地填补了派销模式在发行区域内的疏漏。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设立了不止十处代派点,极大地促进了报纸在同一空间的横向流动。北洋官报局因原址狮子林“地势偏僻”,“诸君多以往返不便为憾”,特在天津市北马路北海楼西路南设立分局,以便在市内繁华路段销售报纸,扩大影响[30]。
概言之,新式官报在销售层面形成了空间上覆盖全国的传播网络,确保政治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群。其一,新式官报被派销至各省、府、州、县和行政机构、军事枢纽,及时传递到每个政府部门,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网络。其二,借助商业市场,通过各处代派点推销,新式官报的发行网络进一步扩大,形成同区域内的横向传播网络,甚至延伸至海外。两种不同的销售方式连接了省-府-县及其他偏远地区的传播节点,促进了新式官报在空间上的全覆盖。
三、邮政发行:新式官报的主要传输方式
无论如何销售,报纸都需要借助交通工具送达最终目的地。新式官报大多经邮政运输,外省口岸、铁路沿线城市依靠新式邮政传送报纸,交通不便之处通过传统驿站收发。新式交通和传统驿传共同保障着官报运输,确保信息传播的最后一环节顺利实现。
(一)依托邮政发报
新式官报诞生时,便与邮政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北洋官报》是中国历史上首份邮发合一的报纸,邮政既负责运输报纸,又连带售报。新式官报的发行、拓展有赖于新式邮政系统。
第一,邮局采用邮发一体的方式推销官报,减免运费,令其在价格上占有优势。1903年,北洋官报局与天津邮政局签订协议,申明“邮政局情愿承寄官报局各报,分送各处邮局转发,并不取资”[31]553,邮政局如在官报内登各项告白、示谕,官报局亦不收费。1904年,镇江海关税务司雷乐石下发指令,称“南京官报(即《南洋官报》)像现在允许《北洋官报》那样,在寄送和分发上,给以同样的特别待遇和便利”[32]59,继续保持与官报的合作。此后,许多官报承诺,“凡由邮局订购者不取邮费”[33],各省各埠邮政总局分局均认定代派官报,官报与官方邮政紧密地联结起来。
第二,新式邮政决定了官报发售系统的深度,邮局分布点与官报发行区域基本吻合。截至1910年,邮局几乎遍布全国,“行令乡僻无关紧要之处所,及夫绵远未经入手之边疆,一律推广无遗,以期普遍”[34]687。通过邮政点对点均质传播,地方官报的影响力不单局限于省城中心,还辐射至县级区域。根据《南洋官报》在江苏省省内的发行区域[35],除了桃源县、安东县、清河县、新阳县、昭文县、元和县、太湖厅、娄县、金匮县、荆溪县、阳湖县、镇洋县这十二处没有邮局的地方之外,其他各府县皆有邮局,且都能收到《南洋官报》。可见,报纸发行区域与邮政驻点基本保持一致,江苏省境内绝大多数县既有邮局,又能接收到《南洋官报》。邮政与报刊相结合后,形成了一整套传播链。
第三,与传统驿政系统相比,新式邮政能够保证发行效率。辛亥革命以前,境内邮局已克服种种困难,加强组织整顿、增加发班次数、缩短程期。例如,张家口市原本无邮局,商民信函皆由标局递送,“资费既重而每多迟滞舛误遗失”,设立邮政分局后,“转运妥速,无不称便”[36]。新政后期,官报多由邮政寄送,“除未通邮政之处,仍照前寄外,其余均已改归邮局经递以省周折而免迟延”[37],省时省力,卓有成效。
(二)使用火车邮路传送报纸
现代邮政主要依靠铁路传送官报,时效性较高。以《南洋官报》为例,该报在发行条例中指明,南京市内下至镇江、上海一带,上至芜湖、安庆、鸠江、汉口一带,皆可当日寄发;外府州县出版次日寄发[38]。邮局规定,发往长江上游的信件每日晚间八点封发,发往长江下游的信件在每日早上七点半、中午十二点、下午一点、晚上八点均有一次封发的机会,通过沪宁快车、专车或慢车寄出[39]。参考沪宁铁路时刻表,南京开往上海的慢车于早上八点二十发车,当晚五点十五分便能抵达上海[40]。这意味着,来自南京的邮件基本当日内可抵达沪宁铁路沿线城市,如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以此类推,当日发行的《南洋官报》最迟在第二天能够到达口岸城市,新闻的时效性得到了充分保证。
直隶地区,随着铁路网络的迅速铺设,官报借助铁路网形成了官方传播系统的扩散圈。未与邮政合作之前,《北洋官报》按期包封汇寄,分发至州县,再由府州转发,各属收报迟速不一,“偏僻之处,甚有逾月始到,且挤压至十余期者”。北洋官报局与邮政合作后,利用关内外铁路在北方地区运输报纸。凡是北洋官报局发报,“从速以火车递送”[41],报纸在当天内可发往铁路沿线城市,“本埠及京城、保定、正定、塘沽、山海关铁路可通之处,皆当日寄发”[42]。可见,《北洋官报》的传播范围与关内、外铁路网的铺设关系密切。
交通的通达与运输工具的便利,促进了报刊读者共同体的形成。铁路开通后,将所经城市、乡镇、村庄连成一条直线,缩短了各地之间的距离。火车最快能在当天将官报发往沿线城市,让人们尽快了解最新国家大事、政治动态,“空间的缩小(其实是运输时间的缩短),通过把新的区域合并到运输网中来……国家收缩成一座大城市”[43]59。由浙江留日同乡会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浙江潮》曾刊登读者来信,称“乃今阅本年八月十五日《北洋官报》,则谓其以矿产抵作银二百五十五两”[44]443,表明官报成为海外读书人的重要信息来源。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南浔人刘锦藻在日记中写道,“阅官报,悉湖北革党起事”[45]73。由此可见,较为便捷的交通推动了官方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使得阅读官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由邮政运输,尤其是分别以电线、蒸汽为动力的电报、火车代表的现代邮政运输,新式官报在可达性层面建构了“实在”的官方信息系统。首先,现代邮政运用技术扩展了信息流动空间,使官报的分布与邮局的分布基本保持一致,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尤其是铁路运输与轮船运输的出现,纵向推动了官方在偏远地区、内陆地区搭建传播网络,官报开始从都市、省城向地方县、厅扩展,这也是官方传播系统大众化的体现。其次,现代邮政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将处在不同地区的读者汇聚成了一个庞大的阅读共同体,在接受层面建构了稳定的物质网络。
四、结语
从信息流通层面看,新式官报改善了邸报制度封闭、发行时效低的缺陷。现代邮政出现后,以电线、蒸汽为动力的现代邮政逐渐取代了以蓄力、人力为动力的传统驿政,铁路、轮船等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改变了依靠驿传制度流转邸报、公文的传统传播体系。早期,提塘抄录本章奏折后形成邸报,交付驿传递送,向各行省散布信息。19世纪末,驿站成为效率低下、斥资靡费的官僚机构。提塘制度耗费数金,百姓苦受其害,时人称“便于国而不便于民,利于公而不利于私”[46]676。驿站效率低下,“不以驿务为重,以致迟延,遗失诸弊层见迭出”[47],导致信息传播深受阻滞。新式官报出现后,与传统邸报的传播方式、途径、效率截然不同,其所运用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远胜于依靠人力、畜力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
新式邮政提升了报刊传播效率,回应了新政改革需要及时传递政令法规的新诉求,在物理层面上建立了规范化、效率化的发行机制,推动了官报传播体系的形成。在与邮政合作送报的过程中,新式官报逐步奠定了报纸“邮发合一”之传统。“邮发合一”是一种将邮政与发行业务相结合的制度,利用邮政通信网的优越条件,将报刊迅速、准确地送到读者手中[48]。民国时期的政府公报延续了官方报纸与邮政合作之传统。公报大多派销至政府机关,“本省行政、司法、议事各机关及军营、局所、学堂,均有购阅公报之义务”[49],兼有代派处销售报纸。公报仍由邮局递送,并在报纸上加盖公文章印,享受公文待遇。可见,近代邮政奠定了民国公报发行、传输的基础。
得益于晚清邮政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技术变革,清末新政实施后,政府以公开、大众化的媒介传播方式发布新闻、传递政令,打破了传统官民之间的信息鸿沟,标志着官方国家治理途径的现代化。邮政技术在物质层面建构起横、纵结合的传播体系,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可达性,为此后建立官方信息传播渠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网络。正如有学者指出,“甚至最新技术的有效性依旧可以说最终取决于物质基础设施”[50]。这也提醒着我们,在讨论传播甚至政治制度建构时,除了聚焦思想、观念、符号层面上的影响,更应该考虑物质层面的发展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