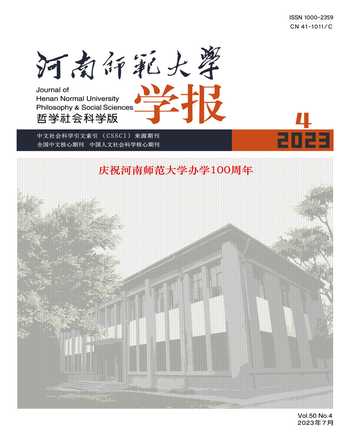晚明士人李贽的英雄观
2023-04-29李竞艳
李竞艳
摘 要:“英雄”一词在李贽的著述中多次出现,“豪杰”“侠”“好汉”等描写英雄人物的词语也被频繁使用,彰显了李贽浓厚的英雄情怀。作为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赋予英雄观念以识、才、胆、忠、义、真等多种优秀文化内涵,认为英雄应该重见识而兼才胆、重忠义而为他者、重真心而不矫作、重个性而不从众。在他看来,只有做到向死而生、真心学道、践义履道,方可成为真正的英雄。其本人也以此为目标,不断践行着英雄的精神,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在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李贽的英雄观对当今我们学习英雄、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晚明;李贽;英雄观
作者简介:李竞艳(1977—),女,河南安阳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4-0093-07 收稿日期:2022-02-13
古今中外,“英雄”都是人们常谈常新的话题。“英雄观”作为人們对英雄的看法和态度,包含了如何判断英雄、如何成为英雄以及如何对待英雄等诸多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文化思潮的转换,人们的英雄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晚明社会是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多元文化激荡交融,李贽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其英雄观既继承了前代的思想传统,又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不仅对明清社会的英雄观及人物品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何为英雄、如何践行英雄精神也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贽的英雄观曾引起当今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李贽“尚侠”,“有强烈的英雄豪杰心理期待和信仰景仰”,“侠之骨、侠之气和侠之精神对其思想个性有重要的支配作用”何宗美:《李贽与“侠”略论》,《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也有学者指出李贽孤傲、率真、敢作敢为的性格造就了他独特的“英雄”情怀朱志先、张霞:《由李贽的性格特征探析其“英雄”情怀》,《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然而,李贽英雄观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成为英雄的途径又是什么?对待英雄景仰问题应该持什么态度?诸如此类的问题尚需进行深入发掘。
一、李贽英雄观的思想内涵
“英雄”一词在李贽的著述中多次出现,但何为“英雄”,李贽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品评人物时所作出的评价。如项羽在乌江战败后发出“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慨,李贽认为项羽的这种真情流露“真是英雄语”。再如,当许多人认为是张居正杀了何心隐时,李贽为张居正辩护说:“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答邓明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页。李贽认为何心隐和张居正都是英雄,两雄不能并立而产生误会。我们知道,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和作为思想家的何心隐,二人思想和行为具有很大不同,社会上对二人也是褒贬不一,李贽同以“英雄”来评价二人,为我们抽绎李贽英雄观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帮助。此外,李贽还常用“豪杰”“侠”“好汉”等概念指称英雄。在他看来,“豪杰”“侠”“好汉”等都具有英雄的某种特质,从某些方面而言,都可称为英雄。
细绎李贽评价英雄人物或英雄行为的言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出李贽英雄观的内涵:
(一)重见识,兼才胆。李贽重视见识的作用,认为见识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英雄的重要条件。在见识的基础上,一个人的才和胆方可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李贽用“识、才、胆”阐释孔子的“智、仁、勇”:“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就是说,有了很高的见识就不会困惑,在见识的影响下,有一定的才能便不会忧虑,勇敢而为便不会恐惧。而且,“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如果有二十分见识的话,五六分才也会变成十分才,四五分胆也会变成十分胆。由此李贽发出“天下唯识为难”的感慨。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是见识占了上风。“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而“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但这并不代表才和胆不重要,而是进一步强调见识的重要性。而“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二十分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6页。。也就是说,仅有才能,而无胆量,则会因为胆怯而未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空有胆量而没有才干则会成为盲目乱干之人。所以,只有在识的基础上,才、胆相济,方可成豪杰之事。
李贽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是英雄,但却从“识、才、胆”的角度暗称自己是英雄,“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二十分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6页。,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也唯有此,才使得他敢于单枪匹马地与众多假道学家们决斗,批判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续焚书注》卷二《三教归儒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认为那些假道学家们口头上说学“道”,实则是为了追求富贵,表面上温文尔雅,而真正的品行连猪狗都不如。对假道学家们进行如此猛烈的抨击,如果没有相当的胆识,是很难做到的。李贽也是凭着这些超人的胆识,成为晚明思想界的一名勇士。
(二)重忠义,为他者。李贽称《水浒传》中敢作敢为的人物为“英雄”“豪杰”。他指出《水浒传》为“发愤之所作”。因何“发愤”呢?李贽认为:“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养已矣。” 宋室衰微,面对外敌入侵,甘于屈膝称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这不仅仅是《水浒传》作者个人泄愤,实则是在替水浒中之英雄泄愤,表达忠义之情。这里的忠义不是忠于某人、义于某事,而是忠于国、义于民。为了国家和人民,“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尽显英雄“忠义之烈”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忠义水浒传〉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1、302页。。同样,李贽赞扬大忠大义之人关羽,“忠义贯金石,勇烈冠古今”,认为关羽正是秉持这种大忠大义精神,“虎视中原,夺老瞒之精魄,孙吴犹鼠,藐割据之英雄,目中无魏、吴久矣”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关王告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浩然之气充塞天地。所以大忠大义是李贽判断一个人是否英雄的重要条件。
李贽认为从他人安危出发,而非沽名钓誉地重义,是一种英雄气概。“李陵降虏,陇西之士皆耻出其门下,马迁独救之,非独枯木寒灰,无势位之可附,亦且负不忠不义之名,救之而无以自解于清议者也。无恩无名,而又有不可测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于意气,非后世矜重名义之流可比。”厦门大学历史系:《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页。司马迁不为任何名利,还面临着不可预测的祸罪危险,挺身而出,慨然为李陵辩护,李贽称其为“天下大侠”,认为这种侠举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义气,而非沽名钓誉之矫揉造作。
重义也是一种担当。真正的英雄是为国为民为他者,而不为一己之名利。“为他者”就要有“庇人”的担当和勇气。李贽说:“未有丈夫汉不能庇人而终身受庇于人者……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凡大人见识力量与众不同者,皆从庇人而生,日充日长,日长日昌……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于人处识取。”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别刘肖川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1、142页。凡是能真正为他人而且能够终身为他人考虑的人皆可称为英雄。
(三)重真心,不矫作。李贽认为“童心”即“真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是判断事物真假是非的标准,是判断是否真性情的标准,一旦掺杂了“道理闻见”,便会失却真心、真性情,人便变成了“假人”。这种“童心”“真心”“真性情”本来是人人具有,自然而然的事情,“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读律肤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5页。。但在当时“满场是假,矮人何辩”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童心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的社会里,许多人丢弃了“真心”。那些敢于从自己真心出发,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者,便可被视为英雄。所以,李贽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丈夫汉喜则清风朗月,跳跃歌舞;怒则迅雷呼风,鼓浪崩沙,如三军万马,声沸数里。”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豫约·早晚守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9页。大丈夫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做扭捏之态,“欲杀则走就刀,欲打则走就拳,欲骂则走就嘴,只知进就,不知退去”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续焚书注》卷一《与周友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页。。可见其率性自然,毫不造作。李贽不仅自己如此,对古人的率性之举也极为赞叹。如对项羽在乌江战败后慨言无颜见江东父老之举,大呼“真是英雄语”李贽:《藏书》卷二《世纪·英雄草创·西楚霸王项羽》,中华书局,1959年,第23页。。公孙述不降光武帝时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李贽称之“亦雄”李贽:《藏书》卷三《世纪·乘乱草窃·公孙述》,中华书局,1959年,第47页。。苏轼常常直抒胸臆,率性而为,嬉笑怒骂流露于外,李贽认为其“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始可称万夫之勇”李贽:《藏书》卷三九《儒臣传·词文儒臣·苏轼》,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李贽天生不想被人束缚管制,说:“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历观从古大丈夫好汉尽是如此,不然,我岂无力可以起家,无财可以畜仆,而乃孤孑无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勢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续焚书注》卷一《与耿克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5页。宁可一死,也不想违背自己纯洁的本心。
(四)重个性,不从众。李贽笔下的英雄,无论是学道者还是出世者,都个性卓然,出类拔萃。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答耿中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自己的英雄之路。如在对待出家还是在家问题上,李贽认为出家和在家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但在真正求道方面,孔子未出家是英雄、圣人,释迦牟尼出家同样也是英雄、圣人。
英雄卓然的个性往往使他们坚持真道,不趋炎附势,不从众献媚。所以,李贽认为,被假道学家们视为大盗的林道乾,不仅不是大盗,反而是英雄豪杰,原因就是当“举世颠倒”,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时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因记往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9页。,英雄不为权势所屈,挺身而出,宁可被世人误解,也不耽于自己的纯净个性。
英雄往往不被一般人理解,所以英雄往往知己者少,显得孤独高洁。李贽感叹道:“若为学道计,则豪杰之难久矣,非惟出世之学莫可与商证者,求一超然在世丈夫,亦未易一遇焉。”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续焚书注》卷一《答骆副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9页。罗汝芳少而学道,却被俗儒批为不肖,李贽却称他为英雄:“近老(罗近谿)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学道,盖真正英雄,真主侠客,而能回光敛焰,专精般若之门者;老而糟粕尽弃,秽恶聚躬,盖和光同尘之极。俗儒不知,尽道是实如此不肖。”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答周二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真正的英雄不仅不会因为别人的不解而放弃自己心中的理想,反而会越挫越勇,独占时代思想鳌头,哪怕被污为“异端”也在所不惜。所以素有英雄情怀的李贽自言道:“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六《读书乐(并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当然,李贽彰显个性、不从众,并不代表其故意不与人同,而是不屈于权贵。所以他说:“余性好高,好高则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势仗富之人耳;否则稍有片长寸善,虽隶卒人奴,无不拜也。余性好洁,好洁则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趋势谄富之人耳;否则果有片善寸长,纵身为大人王公,无不宾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高洁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李贽容不下那些偏激狭隘、阿谀奉承之人,对于真心行善的人,无论社会地位低下之人还是王公贵族,都以礼相待。因为真正的英雄不问出身、只重品行。
二、成就英雄之道
李贽一生向往英雄,不断实践着英雄之道。所以,如何成为英雄也是李贽思考的重要问题。李贽认为成就英雄之道主要包括向死而生、真心学道、践义履道。
(一)向死而生,直面生死。探究成就英雄的道路要从根本处着手,李贽认为这个根本处即是“生死根由”,认为只有对生死有了一个彻底的了悟,方能坦然面对世间的林林总总,方能在世俗间寻得出类之道即英雄之道。他说:“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所以,“勿伤逝,愿伤生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伤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8、439页。。这种看似消极的生死观,其实是一种极具张力的达观的人生态度。所以当李贽面对当局迫害,有人劝其躲避时,他大义凛然,宁死也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李贽心中的英雄都是向死而生者,因为,“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五《王半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4页。。正如其在《五死篇》中所言:“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第一等好死”乃是英雄之死,程婴、公孙杵臼、纪信、栾布、聂政等为报答知遇之恩和知己,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者。屈原为了自己的国家,用生命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此时国家就是自己最大的知己。奸臣当道,知己蒙冤,自己用死去抗争就是对知己(国家)最好的报答。李贽说这些为报答知遇之恩、为知己而死的义烈行为是“大买卖”,而“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认为敢于死于不知己者同样也是“英雄汉子”。所以李贽对貌似知己者不无讽刺地说:“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五死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4、435页。这种英雄浩然之气其实是对不知己者的无情控诉。
向死而生的英雄之道还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它是英雄对生和死的辯证认知,就像对待事物的存与亡一样,理性而达观。所以李贽称赞元代“视亡若存”的秉忠为“真英雄豪杰”,“世祖方得天下,而即问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为不祥,侃然致对。视亡若存,真英雄豪杰,诚不同于时哉”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又与周友山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生死同待,不惧死亡,唯有此,才敢于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搏斗,乃为真正英雄豪杰。
(二)真心学道。李贽认为,“人伦物理”即是“道”。遵循于人的现实生存需求和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保持“真人”状态,即是“道”的真谛。然而常人往往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迷惑,而真正的英雄因为学得了道的真谛,而在常人中脱颖而出。
李贽认为,只有真心学道,才能看透人世间的虚像,才能够摆脱名和利的束缚。主流社会对门派、社会身份、性别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李贽认为这些都是极其错误和可笑的。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知,他从具有平等、自由精神的“道”出发,论述人人皆可学道,皆可为英雄。他认为,不同门派学道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其本质却无差别。就像饥者求饱一样,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填饱肚子,所谓“食之于饱,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羡也。然使两人者易地而食焉,则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犹稻黍之于南北也,足乎此者,虽无羡于彼,而顾可弃之哉!何也?至饱者各足,而真饥者无择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子由〈解老〉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儒家和道家的真心学“道”者就像“真饥者”一样“无择”,当然也没有必要选择,因为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持“真心”,求得真道。李贽认为,不仅儒、道两家是这样,儒、佛之间也是如此:“孔子之于鲤,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尝为子牵也。鲤未死而鲤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尝为妻系也。三桓荐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视富贵如浮云,唯与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晋,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虽名为在家,实终身出家者矣。故余谓释迦佛辞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诞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书黄安二上人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3页。释迦牟尼和孔子无论辞家还是在家,其本质都是超脱世俗的出家,最终都成为大英雄,甚至圣人。
真心学道不仅不分门派,也不分性别。李贽说:“夫薛涛蜀产也,元微之闻之,故求出使西川,与之相见。涛因走笔作《四友赞》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贞元杰匠也,岂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子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4页。被唐代诗杰元稹钦服的女诗人薛涛,进入极乐世界的庞婆、灵照,都可被称为英雄。所以,李贽认为学道不应“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进而赞叹“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昆仑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6页。。充分体现了其追求平等的启蒙思想。
同样,英雄不问出处,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只要真心学道,都可成为英雄。被李贽赞为“真英雄”者的王艮,“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但当他“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王阳明),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卒业焉”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王艮学道心切、心诚、真心,造就了其“气骨”刚毅,终成“真英雄”。
门派、性别、身份都不是区分英雄与否的条件,因为“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真心学道练就自己宏达的心智,在真正适合自己心性的地方成就英雄之举。
(三)勇于践道。真心学道可以练就宏达的心智,培养忠义的情怀,但能否最终成为英雄,还需要将所学之道付诸实践。
李贽曾将立言分为“先行之言”“可行之言”“当行之言”三类。他最推重“先行之言”,认为“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当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先行录〉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由此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主张言行合一,学道践道相统一。由此他批判耿定向口头上“专志道德,无求功名,不可贪位慕禄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贪货贪色,多买宠妾田宅为子孙业也”,而实际行动上却追逐功名利禄的虚伪丑陋。
当然,践道往往会遭受身心磨难,如“何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谿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李贽不禁感叹:“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孔子践道,曾遭削迹伐木,绝陈畏匡,“几死者亦屡,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为得正而毙矣。不幸而死,独不曰‘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者乎”。所以李贽称其“为出类拔萃之人,为首出庶物之人,为鲁国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万世之儒一人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何心隐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5页。。
践道,也往往会遭遇不被知遇之苦,但英雄哪有不孤独的?李贽说:“既学道不得不资先觉,资先觉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独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属徒有家乡之念,童仆俱有妻儿之思,与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则难留,是以尽遣之归,非我不愿有亲随,乐于独自孤苦也。为道日急,虽孤苦亦自甘之,盖孤苦日短而极乐世界日常矣。”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答刘晋川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李贽认为,眷属、童仆各有他志,遣散他们,自己雖有暂时的孤苦,但为了学道、践道,也心甘情愿。
三、关于“英雄景仰”问题
李贽作为晚明“英雄”形象的建构者和实践者,“有强烈的英雄豪杰的心理期待和信仰景仰”何宗美:《李贽与“侠”略论》,《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我们不禁会想,李贽为什么景仰英雄?景仰英雄的什么?是英雄事迹本身还是其所折射的精神?怎么才能够做到合理地景仰英雄?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对李贽的英雄观有更加全面的认知。
(一)为何景仰英雄。英雄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英雄的作用会更加突出,英雄的形象会更加耀眼,它像一盏明灯指引着人类向着更加光明的方向前进。英雄往往是一群出类拔萃之人,非“异人”不可成英雄。正如李贽所言:“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类。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与焦若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页。不同时代产生英雄的“异人”群体有所不同,在魏晋之后,英雄观念从主流的士人阶层、知识阶层逐渐下移。晚明时期,“异人”群体进一步下移,逐渐到了日常百姓。前文有述,李贽英雄观的理论基础是“真心”“真情”,而且人人都曾具有“真心”。既然人人都具有“真心”,则说明人人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但这似乎只能从理论和逻辑关系上成立。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更多人受到假道学家们“闻见道理”的影响,“童心”(真心)极易“遽失”:“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童心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只有那些不肯“效颦学步从人脚跟”者,不被假道学家的义理迷惑者,保持“童心”不失,超脱名利束缚,出类于常人,拥有独立精神者,方为真正学道践道的英雄。所以,英雄是“大人者”“庇人者”,是引领社会向上向前而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思想胆力无与伦比者。社会发展需要英雄,不同时代都需要学习英雄、景仰英雄,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发挥自身在社会中应有的那份力量。
(二)如何景仰英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景仰英雄是学习、景仰英雄精神。生活在晚明的李贽,虽然有些思想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但在对待英雄景仰这一问题上,却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即认为对待英雄时,不能局限在其行为本身,而是要学习其重忠义、讲真情等英雄精神。就像人们往往以仗剑天涯来形容英雄的侠肝义胆,剑术精湛会为英雄的高大形象增色添彩,但李贽认为,景仰英雄贵在其精神而不在其剑术:“夫剑之有术,亦非真英雄者之所愿也。何也?天下无不破之术也。我以术自圣,彼亦必以术自神,术而逢术,则术穷矣。曾谓荆卿而未尝闻此乎?张良之击秦皇也,时无术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术者,立为齑粉矣。故黄石老大嗔怪于圮桥之下也。嗣后不用一术,只以无穷神妙不可测识之术应之。灭秦兴汉,灭项兴刘,韩、彭之俎醢不及,萧何之械系不及,吕后之妒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术之有,况剑术耶?吾是以深悲鲁勾践之陋也,彼其区区,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盖真侠者也,非以剑术侠也。”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四《昆仑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6页。剑术对于英雄而言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英雄之根本是“堂堂大道”之英雄精神。
孔子和释迦牟尼都是李贽特别景仰的英雄、圣人,但他景仰的不是他们出家或在家之事迹,而是其学道成道之精神:“故苟有志于道,则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释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学佛者,非学其弃净饭主之位而苦行于雪山之中也,学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学孔子者,非学其能在家也,学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复邓石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页。李贽虽然尊孔子为英雄、圣人,但对其并非顶礼膜拜、盲目崇拜。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答耿中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认为孔子只是众多英雄、圣人中成就较高者之一,但不是唯一,认为他与老子、释迦牟尼在学道成道方面只不过是发力点不同而已,“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所以孔、释、老三人各有特色,不分伯仲。
(三)真心景仰英雄。李贽的思想体系中始终贯穿一个“真”字,主张真心、真情、真道,反对假道学家们的言行不一。他认为那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家们“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答耿司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2页。。对待英雄景仰,更要有真心,不能将英雄景仰作为自己获取名利的工具。为此,他批判耿定向说:“公今既宗孔于矣,又欲兼通诸圣之长: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圣人之所以继往开来者,无日夜而不发挥,又于世人之所以光前裕后者,无时刻而不系念。又以世人之念为俗念,又欲时时盖覆,只单显出继往开来不容己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己处也,是正念也。”耿定向口头上说宗于孔子,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最终目标是获取高官厚禄。这与孔子重道之精神背道而驰。孔子认为“鲤死则死矣,颜死则恸焉,妻出更不复再娶,鲤死更不闻再买妾以求复生子。无他,为重道也;为道既重,则其他自不入念矣”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一《答耿司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7页。。但世上有几人能够真正懂得孔子重道之真谛?更多人“一生学孔子”,“以博名高,图富贵,不知孔子何尝为求富贵而聚徒党乎”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二《与焦弱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李贽不禁为这些人感到可笑。
真心景仰英雄,要从根本上汲取英雄精神之营养,而非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李贽谈到《忠义水浒传》时说:“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李贽著,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忠义水浒传〉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李贽认为《忠义水浒传》是那些真心景仰英雄者必读之书,纵然身份不同,但只要真心景仰英雄,便都可以从中培养忠国义民的情怀,切勿像好事者那样只是“资其谈柄”而已。
李贽的思想是复杂的,身后饱受争议王记录:《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李贽的批判:兼谈早期启蒙思想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但李贽的英雄观打破了门派、身份、职业等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英雄观念的平等性和实践性,缩小了理想和现实间英雄形象的差距,不至于使英雄只活跃在中心文化的边缘,避免了汉魏之后英雄最终走向虚名化。“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否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专运阴谋,狼顾狗偷,品格更下。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汤用彤:《读人物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页。在英雄形象塑造上,李贽克服了将英雄神化的局限,在人格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创造出一种融合儒、释、道思想的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使中国学术史上反复论证圣人人格权威并代圣人立言的现象得以缓解,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为英雄这一人类亘古永恒的话题赋予了新的含义,也为解决如何定义英雄、如何学习英雄等社会实践问题提供了借鉴。
Abstract:
The word “hero” appears many times in Li Zhi's writings, and words describing heroes such as “person of exceptional ability”, “knight-errant” and “chivalrous man” are also frequently used, which shows Li Zhi's strong heroic feelings. As a famous thinke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 Zhi endowed the concept of heroes with many excelle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such as knowledge, talent, courage, loyalty, righteousness, truth, etc. He believed that hero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knowledge and courage,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for others, sincerity without affectation and personality without conformity. Moreover, he regarded how to become a hero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is view of heroes, and thought that only by living to death, sincerely learning Taoism and practicing righteousness can he become a real hero. With this as the goal, he constantly practiced the heroic spirit and became a banner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 at that time.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eclined, but it shone brilliantly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Li Zhi's view of heroes is significant for us to learn from heroes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heroes.
Key words:the late Ming Dynasty;Li Zhi;view of heroes [責任编校 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