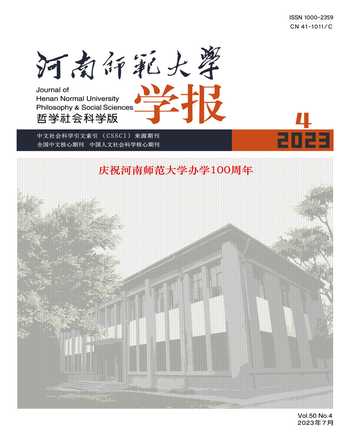五臣李善王逸三家序“骚”之比较
2023-04-29力之吴晓云
力之 吴晓云
摘 要:《文选》“骚类”的各序/解题,李善注的乃节录王逸《楚辞章句》相应之序文而冠以“序曰”,“五臣注”的则虽“另起炉灶”而实多暗袭《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以为之,二者多有不同。五臣、李善二家注均往往漏了王逸序文之精华而有所未逮乃至大为逊色,尤其是李氏的。合观序注,可知李善节去《离骚经序》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以下文字,与其是否欲“摆脱文学依附经学”如何毫无关系。将五臣李善二家序“骚”与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作比较研究,对深入了解五臣李善二家对相关作品的整体把握如何,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忽略。
关键词:五臣;李善;王逸;序“骚”;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力之(1956-),男,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前文学与文献研究;吴晓云(1991-),女,广东湛江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ZW061)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4-0115-10 收稿日期:2023-01-08
关于《文选·骚》之李善注,四库馆臣云:“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8,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7页下栏。“全用”云云,就仅用其注文而不加“善曰”言,那是没有问题的。“逸注”,乃李善所用“旧注”中之最早者,而且几可以说对其唯一“不复加证” 李善在《招隐士》的“刘安”下有注(参佚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页),然此盖因昭明太子改“淮南小山”为“刘安”所致。即实际上,李善确对王逸注“不复加证”。(李善于《毛诗序》的“郑氏笺”虽亦“不复加证”,然此“笺”太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以忽而不计);然李氏所用“逸注”之各篇序 关于《楚辞章句》各篇之“序”的作者问题,参见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第35-62页。,则均为节文(详后)。故于此,“全用其文”或引起歧异 参见力之:《〈文选〉骚类李善注引〈楚辞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辨:兼与王德华先生商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力之:《〈王逸招魂章句考辨〉商兑》,《中国诗学》,2008年第13辑。。当然,注文亦时或有删 尤其是《离骚》的。如其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注,即被删去了其中的“德合天地称帝”“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二处共21字(以《唐钞文选集注》与《楚辞补注》比观)。,只是较之序文,所删比例要小得多,且不那么一目了然罢了。又,朱珔(1769-1850)自序其《文选集释》有云:“《昭明文选》一书,惟李崇贤注号称精赡,而骚类只用旧文,不复加证。……未免于略。” 许逸民:《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第15册,广陵书社,2013年,卷首。就全部李善所用“逸注”言,“未免于略”者仅《卜居》《渔父》及《招隐士》与部分《九辩》之注,而其余的《离骚》《九歌》(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六首)《九章》(仅选《涉江》一首)与《招魂》等之注并非如此。故此“未免于略”云云,未达一间。不过,近人骆鸿凯针对朱氏此序而来之“不知《楚辞》唯宜守叔师章句,不宜纷纭妄说。李氏采王注无所沾益,诚知训诂之精者” 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第104页。又,对骆氏是说,陈延嘉云:“如果说作为唐朝人,李善全用王注而‘无所沾益,表明他自己的理解不能超出王逸,还情有可原的话,到了20世纪,早已有洪兴祖的《补注》、朱熹的《集注》、戴东源的《屈原赋注》,等等,还这么说,就不可思议了。骆氏不可能不读《补注》和《集注》,应该知道洪兴祖、朱熹有不同于王逸之处,但他为了给李善辩护,竟说‘唯宜守叔师章句,岂不令人惊诧?”(参见陈延嘉:《〈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比较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68页。)笔者认为,陈先生此说,亦有商榷之处。因为骆氏显然是就“唐朝人”说的,而就“到了20世纪”论,则未免以今律古了。又,骆氏是说来自乃师黄季刚先生。季刚先生云:“《楚词》唯宜守叔师家法,不宜纷纭妄说。李氏采《章句》,无所沾益,诚知训诂之精者也。”(参见黄侃,黄焯:《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即陈先生未注意到骆氏是说之所自。说,亦未尽然。首先,李善除了用“王逸注”而“不复加证”外,于所用之其他“旧注”均有“加证”;其次,就注之体式言,李善注与“王逸注”甚为不同,而“五臣注”与“王逸注”则十分接近。另外,就序/解题言,李善注的乃节录王逸相应之序文而冠以“序曰” 王德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有云:“《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王德华:《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文選》原本录有”云云,未为得也:以《离骚经序》为例,如王先生所言,何以李善节引、陆善经全引,而张铣竟冠以“《史记》云”“另起炉灶”?又,关于此中之“节引”“全引”问题,参见力之:《〈文选〉骚类李善注引〈楚辞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辨:兼与王德华先生商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五臣注”的则虽“另起炉灶”而实多暗袭王逸序文以为之,然二者多有不同,此其一;其二,不仅五臣、李善二家注间多有不同,五臣与李善所为,亦均往往漏了王逸序文之精华而有所逊色,尤其是李氏的。故此,就五臣李善二家 本文所说之“二家注”专指“李善注”与“五臣注”。即将“五臣”作一家看。注“骚”作比较研究,对了解这二者之同异是难以替代的。不仅如此,将这二家《文选·骚》注与王逸《楚辞章句》相应部分作比观,对相关的学术问题也会看得更透彻。不过,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三家注之“骚”的各篇序/解题部分作比较研究。下面,分为三部分以说之
一、关于《离骚经序》之比较
王逸《离骚经序》曰: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李善节录之《离骚经序》为: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1983年,第778页。又,“流”,《楚辞补注》本作“疏”,然当以“流”为近是。参见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2-13页。
“铣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离骚经序》):
《史记》云:“屈原,字平。”仕楚为三闾大夫,上官靳尚妒其才能,谮毁之,王乃流屈原于江南,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骚,愁也。言己遭放逐,离别愁苦,犹陈正道以讽谏也。上述唐尧,下序桀纣,以香草善鸟龙凤以譬忠贞君子,以灵修美人以喻于君,以臭草恶禽飙风云霓比小人,援天引圣,终不见省,遂赴汨渊而死。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1983年,第778页。又,“屈原字平”之“平”,显非张氏所见《史记》如此,而当为其据《文选》改《史记》而来,即类李善之“改‘毛从‘三家”。参见力之:《〈文选〉李注札记》,《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1期。
比观王逸原序,可知李善如此节录殊欠高明:省了“三闾之职……王甚珍之”,读者不明屈原作《离骚》前之“入”与“出”如何,国君又怎样待他,而这对读者了解作者与作品均甚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当留下“入则……应对诸侯”与“王甚珍之”;省了“屈原执履忠贞……不知所诉”与“言己放逐离别……反于正道而还己也”,读者难明屈原作《离骚》深层原因与屈原之所以为屈原的原因;省了“《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云云,读者便不易把握《离骚》之艺术特色 毫无疑问,“《离骚》之文”是否如王逸所说的“依《诗》取兴”,尚可作进一步之研讨。然无论如何,这均不影响本文之结论。;等等。就后者言,近人游国恩(1899-1978)在其《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一文中说:
屈原辞赋多用“比兴”,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指出。例如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刘勰也承袭着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辩骚》)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他们这些话虽未免挂一漏万,也不甚正确;但所谓“引类譬谕”,所谓“讽兼比兴”的原则却是无可怀疑的。 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5-206页。
“所谓‘引类譬谕,所谓‘讽兼比兴的原则却是无可怀疑的”云云,的然。接着,游先生将“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概括为以下十类:“(一)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二)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三)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四)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五)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六)以规矩繩墨比公私法度”;“(七)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八)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九)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十)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 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6-210页。。屈作之特重“比兴”与“多用‘比兴”,于斯得其概矣。而以此反观李善节录之《离骚经序》,更启吾人之思。
而如果说,李善删去《离骚经序》中之“‘《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和关于道德象征的话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等等”,是“努力摆脱文学依附经学的地位,恢复楚辞文学作品的真实面貌,甚至淡化文学作品的政治道德功能” 熊良智:《选学骚类文献考述》,吴明贤:《文学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0页。,亦显非圆照 由于这一问题涉及注与选等方面的问题而较为复杂,故拟另文详之,兹不展开研讨。。这只要看一下李善所用王逸注《离骚》,便不难明白。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注之“美人,谓怀王也。言天时运转,春生秋杀,草木零落,岁复尽矣。而君不建立道德,举贤用士,则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萧统,李善:《宋尤袤刻本文选》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189-190页。;“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也”注之“言原君务及年德盛壮之时,修明政教,弃远谗佞,无令害贤。改此惑误之度,修先王之法也” 萧统,李善:《宋尤袤刻本文选》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190页。;“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纽夫蕙茝”注之“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贤者。言禹、汤、文王虽有圣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化,非独索蕙、茝,任一人也” 萧统,李善:《宋尤袤刻本文选》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190页。;等等。王立群之“我们在对《文选》局部进行研读之时,脑海中必须要有一个《文选》的整体存在” 王立群:《反思方法 回到起点:〈文选〉成书研究的再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说甚是,而可以例此。此外,李善节引的《九章序》有“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明著也”;节引的《九辩序》有“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也”。此亦崇贤未“淡化文学作品的政治道德功能”之证也。
不仅如此,节去“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复作《九章》……终不见省”,读者(一)或以为怀王“流(《楚辞补注》作“疏”)屈原。原乃作《离骚经》”,而后“遂赴汨渊自投而死”——实际上,屈原“自投而死”在“复作《九章》”后的襄王时;(二)因此,无以知李善节引《九章序》所说之“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故复作《九章》”之“放”究竟是何王时,且极有误以为《九章》作于《离骚》前之可能。易言之,李善之这一节引存在的问题非一,而且均十分严重。又,“铣曰”之“王乃流屈原……乃作《离骚经》……遂赴汨渊而死”与下文“翰曰”之“原既放逐,又作《九章》”二者,其可能造成读者之误解与问题严重之程度均无异于李氏之节引。
再者,若说李善是为了节省篇幅,同样难以成立。因为其注卷41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引《史记》曰: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司徒。博文强志,敏于辞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怀王使原为宪令,原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为也。”王怒而疏之。平病听之不聪,作《离骚经》。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1983年,第997页。
即此处引文篇幅更大。因之,我们恐难以从篇幅大小之角度来为崇贤过多地删节此序寻找到什么理由。另外,在标明作者之前提下,如此简略之节引,似无保留“《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一语之必要(后面的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等同此)。至于张铣之“《史记》云”云云,其实除了开始之“屈原字平”四字外,均来自王逸《离骚经序》。崔富章说:“《离骚经》一篇,张铣作小序(亦采自王逸小序,唯开头增“史记云屈原字平”一句,“字平”乃“名平”之误)。” 崔富章:《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又,“五臣”所为“小序”时或如此。参见力之:《关于〈文选〉五臣注与李善注之差异问题》,《文选学研究》,2018年第1辑。崔先生之“唯开头增”云云,的然。客观地说,对理解作品言,比之李善那样的节录,五臣之张铣所为显然要好些。当然,比之王逸的序文,“铣曰”仍多所未逮。不仅如此,“铣曰”之“王乃流屈原于江南”一句为误接——“流屈原”与“于江南”并非一回事:前者,即王逸之“(怀)王乃疏屈原”;后者,即王逸之“襄王……迁屈原于江南”。概言之,这一误接,将屈原作《离骚》之时地均弄错。不仅如此,如果王逸此序与《史记》或其中的《屈原贾生列传》佚,读者恐均以为此“铣曰”乃本自《史记》。又,今人陈延嘉的“张铣注的绝大部分也出自王逸的《离骚经序》”说,这是符合实际的。陈先生接着又说:
两家注不同的是张铣注中多出“言己遭放逐……终不见省”一段。这一段在《离骚经序》原文如下:“屈原放在草野……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李善在《西京赋》薛宗注下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者,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依此,李善照录王逸注是认为其“是”。但张铣注却增加了上述一段,这说明什么?说明着眼点不同。张铣注多的正是揭示其写法和文学语言特点的部分,而李善却认为不必,说明五臣注在《吕表》三项注释主张的指导下更注意揭示作品的写作特点,更符合注释文学作品的要求。 陈延嘉:《〈文选〉五臣注的纲领和实践:兼与屈守元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又,关于“铣曰”之“《史记》云‘屈原字平”,俞绍初等先生之“盖据昭明意改之,误也”说(参见俞绍初等:《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4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9页),近是。
今按:“言己放逐离别……言己遭放逐……终不见省”一段,乃张氏暗节《离骚经序》“言己放逐离别……终不见省”而来。尽管如此,比之李善注,“铣曰”确是“更注意揭示作品的写作特点,更符合注释文学作品的要求”。换言之,二家之可资者是共同的 当然,其时可供张铣资者尚有班固《离骚赞序》与《离骚序》等。后者,或怀疑乃至否定其为班固所作,非也(另文辨之,兹不赘)。,关键是如何“资”。不过,比之王逸之序,“銑曰”不仅没有任何“新增”,且亦同样有重要之遗漏,乃至严重之误接。于此,特别是其何以同样存在着重要之遗漏,这尤当引起我们更深一层之思考。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今节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相关文字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卒行。入武关……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屈原至于江濱”云云,出于《渔父》(文字之异,盖传写而来)。然学者或因司马迁不加说明而否定《渔父》为屈原所作,乃忽乎就整体考察部分之所致也。即未明“汉人为他人做传时,引传主以他称写己之作,往往当传主的故事来叙述而不注明出处”。参见力之:《〈卜居〉〈渔父〉作者考辩》,《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司马迁:《史记》卷84,中华书局,1982年,第2481-2490页。
以李善节录的《离骚经序》文与五臣之张铣所作解题/小序比较,再将这两者与《离骚经序》比较,进而以《离骚经序》与《屈原贾生列传》比较而综观之,便不难看出,就对《离骚》的总体把握言,李善稍逊张铣,而比之王逸,显而易见,两位后来之唐人均未免“瞠乎其后”了。不仅如此,合观《离骚经序》与《屈原贾生列传》,李善的节引与张铣的暗袭所致之误更为清楚(详上)。相对而言,陆善经全录王逸此序(将其与今传本《楚辞补注》中之王逸《离骚经序》比较,仅有个别文字不同,与《补注》本多“屈原”“也”“楚”“焉”共五字) “陆善经本载《序》曰”云云,参见佚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6-787页。,更为得当。明人焦竑(1540-1620)序汪瑗《楚辞集解》云:“原词谲怪奇诡,非逸章决句断,未可易读,况诸家之说传自汉人,往往参于其中,盖有未可茀废者。” 汪瑗,董洪利:《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非逸章决句断”云云甚是,而其篇义之阐明,则见之叔师相关之序中。
又,宋吕祖谦(1137-1181)《观澜集注》甲集卷1“赋·《离骚经》”所用即“五臣注” 吕祖谦,黄灵庚,等:《吕祖谦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按:标点者误将“仕楚为三闾大夫……遂赴汨渊而死”作《史记》文。又,《新校订六家注文选》标作:“《史记》云:‘屈原,字平。仕楚为三闾大夫……乃作《离骚经》。离,别……遂赴汨渊而死。”(俞绍初,等:《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4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13页。)是亦为偶失。另外,有学者认为《观澜集注》非宋吕祖谦撰,然笔者认为其理由难以成立(另文详之,兹不赘)。。显而易见,就对《离骚经》的认识言,吕氏之识力不仅远非王逸之匹,亦未能拔萃于五臣之张铣。需要说明的是,《观澜集注》用前人之注者,该题注时或添以别“家”说,而此处原原本本。
二、关于《九歌》《九章》《卜居》《渔父》《九辩》《招魂》等六序之比较
(一)关于《九歌》
王逸《九歌序》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
李善节录的《九歌序》为: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乐鼓舞,因为作《九歌》之曲,托之以讽谏也。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1983年,第794页。
“铣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九歌序》):
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乐诸神,原既遭放逐,含怀忧恚,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见黜之情,以讽焉。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1983年,第794页。
稍加比观,便知李善之节录实在并不高明。由于其节掉了屈原在什么背景下作等重要内容,故尽管前面有“屈原之所作”,然读者仍无以从此中得知屈原在什么情况下、因何而“作”此辞,等等。何况,这正如今人潘啸龙所说的,“《序》所言‘昔楚国南郢之邑至‘因为作《九歌》之曲。这部分乃是王逸记述他所了解的传说事实,而非其主观判断” 潘啸龙:《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比之李注,“铣曰”对读者理解《九歌》,无疑要好得多。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说之“以讽焉”以上,除了抄王逸之序外,了无新增;“九者”以下,才异于王说。据“九者,阳数之极”一语,可知张氏认为《九歌》非九首。而关于《九歌》之首数,向来学者辨之夥矣,然迄无定论。至于“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说,则未免牵强附会之嫌——《九歌》乃至全部屈原作品,并无此意。况且,这就“铣曰”言而前后不协。此其一。其二,“九者,阳数之极”盖本之叔师《九辩序》的“九者,阳之数”来。当然,此语乃唐前之“成说”,故张氏亦可能是直接采之。唐前“成说”如徐彦疏“《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引“郑氏曰”之“九者阳数之极”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5页下栏。,张晏注《汉书》卷75京房本传载“房至陕,复上封事曰”之“九年不改”的“九”所说之“九,阳数之极也”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165-3166页。,等等。又,洪兴祖于王逸《九歌序》之“因为作《九歌》之曲”下引五臣此说之“九者”云云为注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宋施青臣《继古藂编·骚篇》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10编第12册,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184-185页。、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8“《楚辞·九歌》” “铣曰”,嘉业堂校刊本作“张锐云”。即误“铣”为“锐”,而今人引此多未之觉。等同样引此为说,明张丑说宋李龙眠《九歌图》“《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郡之邑……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 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之“楚南”以下实亦来自“铣曰”,等等。由此,可见此“铣曰”之影响实亦不小——缘乎“五臣注”,然引者几无注意到其“自谓否极”云云未切于《九歌》之义。
(二)关于《九章》
王逸《九章序》曰: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121页。
李善节录的《九章序》为: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复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2页。
“翰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九章序》):
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义与《九歌》同。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2页。
按:李善节录,节掉了屈原在什么情况下作及“世论其词”等重要内容;然比之李善节录,“翰曰”更为笼统。而就后者言,因此序/题解乃“自撰”,故可资者尚有如王逸《离骚经序》之“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等,其却未用。结果是,据李善这一节录,读者不仅难明屈原“放逐”于何处与其在什么情况下作《九章》,而且亦不易弄清楚《九章》“言己”所指为何、楚人怎样对屈原、“其词”在当时如何流传等问题。概言之,于此五臣不如李善,李善不如王逸。又,“‘九义与《九歌》同”说,恐未的。因为《九章》之“九”,首先当指“八加一所得”之“九”而非其他;而《九辨》《九歌》则否。后者如《离骚》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等。
(三)关于《卜居》
王逸《卜居序》曰: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6页。
李善节录的《卜居序》为: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弃,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4页。
“翰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卜居序》):
原往太卜之家,卜己宜何所居,因述其辞。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4页。
按:三者比观,一清二楚:李善这一节录,可谓主干与枝叶并弃。读之,无法了解“原放弃”之背景与屈原当时之心灵困境如何。而比之李善节录之文,“翰曰”还略为不及——“原”在什么情况下“往”与“其”者为谁,均不明确。当然,这些问题,细读《卜居》便不难明白。不过,看此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无以见一目了然之效。此外,“翰曰”之“因述其辞”一语指向不明。就“翰曰”全句看,主语自然是“屈原”,然说屈原“因述其辞”实不通——《卜居》不只是“太卜”之辞。不错,《卜居》为屈原之所作 力之:《〈卜居〉〈渔父〉作者考辩》,《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然那是另一回事。
(四)关于《渔父》
王逸《渔父序》曰: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页。
李善节录的《渔父序》为: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渔父避俗,时遇屈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5页。
“翰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渔父序》):
渔父避世而隐于渔者也,原因之而叙焉。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5页。
按:这与《卜居序》节录类似,李善此节录,同样是主干与枝叶并弃。读之,难以了解相关背景与“其辞”之所以“传”。而较之李善的节录,“翰曰”更略;不仅如此,比观王逸之序,“翰曰”恐未免有“张冠李戴”之嫌——意引“渔父……遇屈原……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为“渔父避世而隐于渔者也,原因之而叙焉”。
(五)关于《九辩》
王逸《九辩序》曰: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敶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岛,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李善节录的《九辩序》为: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九者,阳之数也,道之纲纪也,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也。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6页。
“向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九辩序》):
玉,屈原弟子,惜其师忠信见放,故作此辞以辩之,皆代原之意。“九”义亦与《九歌》同。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06页。又,陈第《屈宋古音义》卷3《九辩》下“旧注”,即此。
按:李善删去“屈原怀忠贞之性……可履而行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说便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向曰”的情况类此。此其一。其二,李氏节引时,误将接“辩者,变也”之“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一语接在“九者……纲纪也”后,致使此语突兀而莫名其妙——“道之纲纪也”非关“辩者”,而“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非释“九者” 黄灵庚先生云:“据义,《文选》本以‘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字在‘道之纲纪也下者,是其旧本。”(参见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增订本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22页。)“旧本”云云,似未为的。;至于吕向之“皆代原之意”五字,盖约自王逸《九辩序》之“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说来,不过此“代原之意”虽至确,然“皆”却无以着落——而若以《九辩》说《九辩》,则“皆”无异于“枝指”。其后,洪兴祖于王逸《九辩序》之“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下引五臣(“向曰”)此数语为注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未尽恰也。
今人方铭引王逸《九辩序》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后,有云:
王逸之言,对于我们了解《楚辞》一书的编选体例,以及《九辩》主旨,无疑有重大意义。他告诉我们《九辩》的内容是悲悯屈原行为,以述屈原之志;而《楚辞》之书的成名,在于自宋玉以至刘向、王褒,皆悲屈原之文,依屈原之文而作词。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正确理解《九辩》与《楚辞》中大部分非屈原作品所表现出的因袭屈原之作的倾向。 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89-490页。
方先生之说极是。而无论是李善之节引还是吕向的“另起炉灶”,就解读《九辩》言,删去或不用“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数语,问题自然不大;然就《文选·骚》言,李善之节引与吕向的“另起炉灶”均可谓失之远矣。即就此而言,二家均未能体会到昭明太子立“骚”一类之用心。《文选·骚》以《楚辞章句》一书为封域,此乃其特立于《文选》中别的文体之处。
另外,关于王逸何以在《九辩序》而不是在《九歌序》中解“九”的问题,王宏理、龚俅、邵杰之说可参 参见王宏理:《〈楚辞〉成书之思考》,《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龚俅:《〈楚辞〉研究三题》,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7年,第20页;邵杰:《古典研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6页。。
(六)关于《招魂》
王逸《招魂序》曰: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7页。
李善节录的《招魂序》为: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厥命将落,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也。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10页。又,《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66“作”前有“故”,参见佚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
“翰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招魂序》):
玉哀屈原,忧愁山泽,魂魄飞散,其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于君,冀其觉悟而还之。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10页。
按:就序文/题解言,李善节去了“忠而斥弃”云云,“厥命将落”给读者之震撼感便大为减弱;节去了“外陈”两句,读者便不能在第一时间知其主要的写作特色如何;节去了“以讽”二句,读者就无以一下子了解到宋玉何以作此辞。至于“翰曰”,其虽是暗袭王逸序而来,且同样不明“忠而斥弃”一语之重要而未采,然其此“曰”实远优于李善所节。
三、关于《招隐士序》之比较
王逸《招隐士序》曰:
《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伎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
李善节录的《招隐士序》为:
《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也。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17页。
又,李善于刘安下云:
《汉书》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数千人。后伍被自诣吏,具告与淮南谋反,上使宗正以符节劾王,未至,自刑煞。” 佚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页。又,俞绍初等先生认为“此节”非“李善注”,而“当是善本所存之旧注”(俞绍初,等:《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4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0页),可参;然笔者仍认为此乃“李善注”。不过,无论如何均不影响笔者之说,故兹不赘论之(详后)。
“向曰”(此可视为五臣注本之《招隐士序》):
《汉书》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数千人,后谋反自杀。”《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辞赋,以类相次,或称大山、小山,犹《诗》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伤屈原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之赋,以章其志。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817页。
按:“又怪……似若仙者”数语对读者理解《招隐士》之性质殊为重要,而李善节去;“向曰”之“《招隐士》者”以下,乃来自王逸序,即吕向以王逸序文接于《汉书》语,而其所引《汉书》盖本之李善所引 力之:《关于〈文选〉五臣注与李善注之差异问题》,《文选学研究》,2018年第1辑。。同样的,吕向亦忽略了“又怪……似若仙者”数语。此其一。其二,“向曰”的“《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乃五臣注《文选·骚》唯一暗用王逸序之“××者,××之所作也”这一格式者;而通观《文选》全部五臣注的题解,如王逸序的“昔淮南王安……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这样之背景者,五臣是不太关心的,而李善则每多重之,然这里正好相反。另外,如果王逸此序与《汉书》或其刘安本传佚,我们恐均以为此“向曰”乃全节引自《汉书》。
仅限于上述《文选·骚》各篇之序文/题解言,如上所述,“五臣注”实际上主要是节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序文而为之。从客观层面说,“五臣注”与李善注各有长短,而就说“文心”角度言,则五臣略胜。问题是,比之王逸相应之序,这二家均大为逊色。
余论
通过上文之比较可知,就对《文选》“骚”类各篇作品的整体把握言,无论是李善还是五臣均远逊于王逸,尤其是李善节引的《离骚经序》何以如此忽略“文心”,更是值得我們深思。于此,笔者注意到,学者或“从李善的注释体例以及这一体例起到的对‘旧注的保存来看”,而认为“李善注本中的‘王逸注非出自李善注引,也就不存在李善节引的问题,后人认为是李善节引,往往是因对李善注释体例不明所致” 王德华:《李善〈文选〉注体例管窥》,中国文选研究会:《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738页。。然仅就“李善注释体例”云云考察,是无法证明“‘王逸注非出自李善注引”的。又,黄灵庚疏王逸《离骚经序》开头之“《离骚经》者……为三闾大夫”有云:“李善引序,节约其要,非其全文。……古人引书固不甚缜密,未可执一本为依据,宜乎求其同,存其异。”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卷1,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这是恰当的。不过,黄先生又云:“李善标言‘王逸注,然多所删芟。《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云:‘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何本已佚,未详旧貌。盖以章句繁芜,故删而约之。李善所称‘王逸注,抑何氏删本也欤?”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卷1,中华书局,2018年,第11页。是说恐非。首先,《隋书·经籍志》此条自注之“宋何偃删王逸注”后,尚有一“亡”字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5页。;其次,综观《文心雕龙·辨骚》《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与李善注例的“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49页。说,仅据“多所删芟”是难以推测“李善所称‘王逸注,抑何氏删本也欤”的——这一推测实难界“可备一说”之域。另外,并非各篇均“多所删芟”,如以《唐钞文选集注》与《楚辞补注》比观,“删芟”《招魂》注远少于“删芟”《离骚》注,而《招隐士》注则无所“删芟” 唐钞本《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注无“违偝旧土,弃室家也”二句,非李善所删,而显为钞者钞漏。首先,尤刻本、明州本、奎章阁本均有此八字(“偝”作“背”);其次,唐钞本《招魂》“独秀先些”前漏了“《激楚》之结”句;《离骚经》“贯薜荔之落蕊”句注,李善仅删其中的“累香草之实,执持忠信貌也”,而钞者却漏了其前后之“而生蕊实也”“言己施行常揽木”;等等。。简言之,迄今为止之否定或怀疑“李善注本中的‘王逸注非出自李善注引”而是“李善所见《文选》原有之旧注” 俞绍初,等:《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4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9页。的理由难以成立。退一步说,即使能证李善于此是用“旧注”而非其节引,亦毫不影响笔者之说。即其失之“重”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减轻。
总之,就这里的李善何以如此忽略“文心”言,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说李善注之“述作之由,何尝措翰”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卷首。虽未免过于夸张,然亦不无缘由。而就李善注与五臣注之“骚类”各序/解题言,后者虽略优于前者——这主要体现在《离骚经》《九歌》与《招魂》的序文/题解上,然比观王逸相关序文便不难明其距吕氏上揭文所说的“作者为志,森乎可观” 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卷首。之境实亦非近;至于从作为“小传”看,李善节引的《离骚经序》存在问题之严重远超乎想象,五臣注的相应处之失亦然。此其一。其二,“骚”类作品共八序/题注,而五臣注一将非出司马迁之文接《史记》,一将非出班固之文接《汉书》,引文之其他问题者,李善注虽亦存在,然五臣注为多。
王齐洲说:
《楚辞章句》将屈原的生平和创作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知人论世”,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屈原生平事迹的了解,也加深了人们对其作品的认识。例如他说:“《离骚经》者……乃作《离骚经》。”“《九歌》者……而广异义焉。”……这些序言,不仅清晰准确地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事迹,而且具体翔实地交代了屈原作品的写作背景,有些背景材料还是前人未曾言及的,对理解屈原作品极有帮助。这些材料当然不是随意罗列,而是作者研究后的慎重选择,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尽管后来也有人对王逸的某些说法表示怀疑,但王逸厘定的屈原生平和创作的基本线索和背景材料,一直是人们理解屈原其人其作的重要基础。 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41页。
这可谓得其大者矣。当然,由于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页。,可知其为《楚辞章句》有着非凡的“原动力”,加之是时可参的文献多,故其所撰的这些序超乎后来的李善与五臣注,那是非常自然的。问题是:李善仅仅是节引王逸之文,而时或弃其“要”;五臣则几乎全是暗引王逸之文,而可以“新增”处却未能有使读者眼睛一亮之“新增”。
俞樾(1821-1907)《程一夔孝廉〈选雅〉序》云:
李善之注《文选》也,所采用之书,自经史以下及乎诸子百家,都凡千有余种。求之马氏《经籍考》,存者己不过十之二三。至于今日,崇山坠简矣。又其所载旧注,远则服子慎、蔡伯喈,近受则郭璞、韦昭,皆两汉绪言,经师旧诂,片言只字,珍逾球璧。余尝谓《文选》一书不过总集之权舆,词章之輨辖;而李注则包罗群籍,羽翼六艺。言经学者取焉,言小学者取焉,非徒词章家视为潭奥而己。近代诸公喜求古言古义,如慧琳、玄应《一切经音义》,皆梵氏之书,而寸珍尺宝,往往有得,况李氏此注乎? 俞樾,赵一生:《俞樾全集》第15册,《春在堂杂文》卷9,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98页。
就清民二代言,俞氏是说甚具代表性。即后人之重李善注,非仅仅缘乎“词章家视为潭奥”者也。此亦吾人所当加意焉。至于五臣注之特色及其對“文心”之重视度如何,通过与李善、王逸二家之比较,我们自然看得更为透彻。
总而言之,跳出五臣李善二家序“骚”而将之与王逸相应之序比观,才能使我们深切地看清五臣李善二家序“骚”之情形。而这一角度,乃考察五臣李善二家把握其所注诗文“文心”程度如何之最为独特而殊佳者。然目力所及,迄今为止,这尚未引起学界应有之关注。
Abstract:As every preludes/topic explanation of the part Sao of Wen Xuan,Li Shans interpretations extracted corresponding preface of Wang Yis the Songs of Chu Chapters and Sentence and named it prelude saying,while five ministers actually lifted the Songs of Chu Chapters and Sentence in secret though making a fresh start. As a result,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of them. However,neither of them skimmed the cream of Wang Yis preface or as well as it ,and even be much inferior to it,especially Li Shans. Combined with all of them,there is nothing to weather Li Shan wanted to get rid of literature and depended 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or not ,when he cut out the following words of Li Sao Jing Xu that Li Sao depended on The Book of Song to select to be roused.There is irreplaceable and special meaning by comparative study both five ministers and Li Sans preface of part Sao with Wang Yis the Songs of Chu Chapters and Sentence when penetrating into five ministers and Li Shans how to overall grasp related works,which the academia always neglects of.
Key words:five ministers;Li Shan;Wang Yi;Sao prelude;comparative study [责任编校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