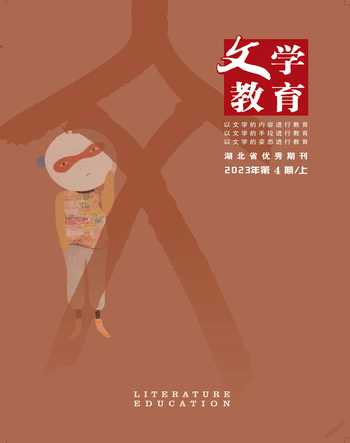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东阳夜怪录》的驿舍遇怪叙事及文学蕴含
2023-04-27陈晨
陈晨
内容摘要:《东阳夜怪录》作为驿舍遇怪的典型叙事,表现出驿舍设施对于小说叙事的重要作用。小说中出现的驿舍,作为叙事空间,通过层层转换与推进,成为推动小说叙事与发展的线索。同时,驿舍作为故事空间,既有外部空间所具有的的特殊性,成为渲染小说悬疑与恐怖内容的底色,又有内部空间自身独有的文化内核与特定作用,发展充实了小说自身情节与内容。驿舍遇怪下的叙事环境与空间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内在逻辑。这一叙事模式也呈现出驿舍遇怪叙事下的多重文学蕴含,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叙事 空间 文学 《东阳夜怪录》遇怪
《东阳夜怪录》为《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所收唐传奇,载唐元和中秀才成自虚佛舍遇怪事。前人研究多集中在成自虚于东阳驿南佛寺中所遇精怪之虚实变形以及精怪诗,对其中驿舍之于小说的叙事作用却提及甚少。在小说叙事当中,古时具有通信、住宿等功能的驿舍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说明,此处的驿舍,是对驿站旅店的统称。现以驿舍为视点,研究其遇怪故事叙事空间及文学蕴含。
一.叙述空间的转换递进
《东阳夜怪录》中所记驿舍的遇怪事,在小说结构上呈现出驿舍环境的转换,从中可见小说驿舍遇怪叙事层次的层层递进。
第一层:举子相逢,宿于逆旅。
在《东阳夜怪录》的叙事中,小说先为其营造了第一层外围环境,即云王洙暮次荥阳逆旅,遇秀才成自虚所述异事。此处的逆旅即私营旅店,晋唐多称逆旅。唐朝开科举取士,这成为文人获取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而在进京赶考返乡的长途跋涉中,投宿逆旅便成为一件寻常不过的事。王洙进京赶考黄昏投宿,成自虚因家事不能参加科考返乡,二人恰好相逢荥阳逆旅。看似偶然的巧合,实则也是诸多举子赶考途中的普遍现象。夜幕降临,萍水相逢的文人在旅馆中谈起科举路上往复的艰辛,便拉近了距离。谈到深处,借着夜晚的黑暗的氛围烘托下,那些真伪难辨的怪事异事成为了饭后的谈资。唐小说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李公佐《庐江冯媪传》载,元和六年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高钺、赵儹、字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公佐为之作传。此处的传舍,也是驿舍,亦是当时供往来官吏休息食宿之地。私人旅店作为小说《东阳夜怪录》的叙事缘起,为小说设置了合理的叙事场所。由此来看,文人间相逢相识,驿舍作为这样一个群体住宿交游的外开放空间,众人“宵话征异”,不仅可通过此活动来排遣长夜寂寞,又在无形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另一种交际的方式。
第二层:僮仆辎重,旅店俟宿。
从成自虚谈及自己元和八年所遇异事,小说的叙事环境即进入第二层。成自虚经渭南县,与县宰饮酒,命僮仆辎重先于赤水店住宿。这里的赤水店亦是私营旅店。“唐代的驿站对于接待对象有严格的身份规定。凡非因公出使的官员和民众,都谓之私行人或私客,不得占宿馆驿,只能入住私营客店。同时,使人如以家口相随,则须于村店安置。”对于成自虚这样的携带家眷的举子而言,无官无职,就只能入住村店,城外的赤水店就成为成自虚及随行住宿的场所。但作为遇怪事件本身而言,故事发生的主人公多是独身一人,人多则失之神秘,会破坏这种遇怪遇异的悬疑氛围。成自虚因恃所乘驴,便令僮仆先去赤水店,待酒饮完,其时“阴风刮地,飞雪霿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无从辨路,行人已绝,寻不到村店,只能投宿佛舍,因而遇怪。如此看来,如赤水店這样的村店的存在,就去除了小说叙事中不必要出现的人事,为主人公独身迷路遇怪的情节提供了一个合理理由和绝佳环境。而在后文成自虚自天亮明白遇怪之事后,即策马奔回赤水店。这时的村店又成为主人公从怪异返回到现实的安身归所,发挥了映照现实的作用。
第三层:东阳驿南,佛舍论诗。
小说叙至成自虚迷路后投宿东阳驿南的庙宇,遇怪情节由此展开。此处的叙事空间,实则意味深远。所谓东阳驿南,即将东阳驿作为秀才成自虚遇怪的地理坐标轴中心,用以区分佛寺方向之所在,这也是小说叙事的潜在空间。而东阳驿虽有其名,不见其实,也是因为驿站的特殊性。东阳驿地处唐京兆府渭南县,是长安与洛阳重要的交通驿站。根据唐朝律令,对于行人出行,除办理发兵、授官、差使、追征等公事者,私人出行则仅允许五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国公以上爵投驿止宿。边远地区和其他无村店之处,可适当放宽入驿标准,但仍有严格规定。开元以后,虽有放宽,但是也仅限于官员。对于成自虚这样的无官无职的读书人,是不能住宿于官驿之所的。所以小说以“东阳夜怪录”为名,并非实指驿站之内,而是把东阳驿作为成自虚“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远,略辨佛庙”这一寻路过程中一个显著的坐标中心来出现的。因佛庙不知其名,而以驿附近代称,所谓“东阳夜怪录”,意在说明此为成自虚于东阳驿附近夜晚遇怪的传录。而投宿佛舍论诗,才正式展开了小说的遇怪故事情节。
二.故事空间的内外渲染
驿舍在古时,虽为过路公私行人通信食宿之用,但因为其特定的职能,再加上唐时宵禁制度严格,因而大多驿站往往设置于城外。其地所处,虽常为大道要冲或依傍江河,但也不乏荒凉幽静之处。加之驿路并非坦途,充满了险阻。唐代长安至巴蜀驿路、长安至荆南驿路北段,从秦岭山脉中穿过,很多路段都在深山密林中溪涧中蜿蜒伸展,林深路曲,光线幽暗,行旅苦之。两京驿路所经亦多山足云之区。若是少见行人,则更显阴森可怖。驿路与驿站周围,就共同构成了一个荒凉恐怖的骇人氛围。再加上驿路上驿馆中本就多见行路死亡的官民,有些因当时客观条件限制甚至死因不明。在唐人的鬼神观念中,正是这样的场所及周围,往往会生成鬼怪游魂。至于有鬼怪成精作祟,也在常理之中,而成自虚便恰好投宿在东阳驿不远处的庙宇当中。此处的庙宇荒芜,还未曾收拾,但夜晚风雪之际,仍可做投宿之用。再者,唐代寺院向来有作为旅舍供行人香客住宿的传统,“唐代的寺院旅舍源于宗教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是除宾馆、驿站、商业旅馆之外的又一重要而特殊的旅馆表现形式。”中晚唐,馆驿制度逐渐宽松,再加上部分时期,馆驿制度的混乱与废弛,驿站往往也可提供闲杂人等使用。但是,由于驿站要求严格且馆驿容量有限,行人数量庞大,供不应求,因此驿站附近常有私营旅店和佛寺旅舍常作为补充,来满足旅人的需要。佛庙的出现。便为成自虚入庙遇怪谈诗论诗提供了合理场所。佛寺适逢其时地出现在郊野,容留逆旅投宿,此成为成自虚遇怪故事的外部空间。而故事的内部空间,即具体遇怪的情境,则在佛庙之内。佛舍虽破败,但内部的空间仍然完备。唐代驿馆内部建设有公共活动区、住宿区、堆放杂物区与牲口饲养区,寺庙业已荒废,但是基本住宿区仍在。小说虽描写不多,但从字句中可见端倪。庙内“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空屋较多,昏暗不明正为下文精怪出场,尤其是卢倚马所变人形隐隐约约间显露的形貌与驴的本相之类做了铺垫。同时,寺院旅舍空间谈诗论诗,也让遇怪故事有了文化内核支撑。唐承隋制,自初唐时期就建立了州别一寺的密集的寺系网络。除了国家营建、认可的大寺院,各地村庄和深山之中还分布着众多民间营建的佛堂、兰若。这些佛寺为文人提供了不少聚会的机会,大历以后至唐末,文坛盛行流寓佛寺、诗文酬唱的风气,相识或不相识的文人士子常数人共寓一寺,把盏夜话,诗文酬唱,称“宿会”或“会宿”。另外,唐代文人出游多投宿寺庙,往往于寺庙之内吟诗或作诗,部分题或刻于寺庙院墙柱子之上,成为庙内的景观。因此,文人在佛寺中主要活动围绕诗文展开,当成自虚佛寺借宿时,所看到精怪的社交活动形式便是品评诗歌。但又不止于此,寺院作为旅舍,其佛寺文化的渲染为小说的内容增添了佛教的旨趣, 整体上为《东阳夜怪录》营造出一种神秘的佛教文化氛围。动物异化成人后,所吟所谈诗歌带有佛教色彩,这与常见的遇怪故事有异。但从反面看,也恰恰反映了驿舍空间的特殊性对于小说内在的强大作用力。
风雪夜晚,东阳驿旁庙宇配合着内部幽暗的光亮,就为叙述的故事本身营造了两重空间。如此,东阳驿南与佛寺旅舍的两重空间交融,至夜晚来临时,诸多因素催发,促使动、植、器物产生异化。成自虚所遇精怪的变形即来自佛舍周遭动物,它们借着夜晚,幻化成人形,在佛舍谈诗论世,天亮时又回归其本来面貌。小说叙事的多层情节与环境,遇怪的外部与内部两重空间,都通过驿舍来连接起来,从而构建起一个严密细致的叙事模式,这也体现出唐小说“叙事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在这种叙述空间转换的层层递进与两重故事空间的交相辉映中,我们也能窥得唐时驿舍的风貌与小说创作的审美倾向。
三.驿舍遇怪的文学蕴含
《东阳夜怪录》中驿舍的多次出现,创造出唐传奇多重的叙事空间,在文学中有着内在的角色扮演和独特属性。
首先,这一故事,体现出驿舍作为志怪传奇故事情节和诗歌生成场所的典型性和独特作用。驿舍作为《东阳夜怪录》的叙事线索和叙事空间,是小说行文叙事的内在逻辑结构。馆舍空间是公共性和私密性的统一。驿舍作为公共空间,将过往行人与精怪聚集在一起,这也就造成过路举人王洙和成自虚有机会在驿舍中交谈行旅所遇异事,各类精怪亦可在夜间东阳驿旁佛寺旅舍内谈诗论诗。如此,驿舍即成为一种文学生成的典型场所:前者生成小说,后者生成诗篇。这是驿舍所催生的文学产物,促使文学发展进入新的叙事场所,此其一。其二,驿舍又有其他环境所不具备的独特作用,影响了文学的生成风格。驿舍是古时赐死、兵杀、病死、暴毙的多发场所,《旧唐书·玄宗纪》就记载了回纥部落杀王君于甘州巩笔驿以及驸马都尉薛鏽长流瀼州,至蓝田驿赐死事。按照古人观念,鬼魂常常会在此处聚集,驿舍成为鬼怪出没的符号象征。在驿舍的背景作用下,小说往往带有神秘特色。成自虚所述异事即是如此,那些夜间在东阳驿旁佛寺评诗的人,原来竟是幻化成人的动物。因此,结尾处发出“自虚慨然,如丧魂者数日”之叹。
其次,基于此,就形成“驿舍多怪”的叙述方式和志怪传统,实际上反映的是小说创作审美传统。驿舍之创设,由来已久。先秦时,就已经出现旅馆。秦统一后,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在各地驿道设驿站、邮亭,供宿过往的官吏、驿使和商旅。秦代“亭”遍布城乡。汉承秦制,在秦驿道基础上,建立了更广阔的交通网,设置有各种供宿备膳的场所。隋唐以后,亭制取消,但馆驿制度承之,得到空前发展。不论驿亭还是馆驿旅舍,都是古时重要交通设施,承担着广泛的交通职能,见证了人在旅途的生活境况,这就为史传和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史书记载自不必说,魏晋志怪小说如干宝《搜神记》亦记载了大量亭中遇鬼遇怪故事,形成“亭多鬼怪,不可止宿”的文言志怪傳统。唐以来,小说承汉魏六朝亭中遇鬼传统,在馆驿制度发展完善的同时,逐渐形成“驿舍多怪”的叙述方式和志怪传统。宋郭彖《睽车志》卷四明确记载“驿舍旧多怪”,洪迈《夷坚志》也有关于驿舍怪“一物毛而四足如猪状”的记载。明清小说中记载驿舍遇鬼遇怪之事更是俯拾即是。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即有台湾驿使宿馆舍,夜半有鬼魅掷片瓦于枕畔事。卷二一有寺院旅舍遇鬼一事,记叙“余”在前明古寺十刹海馆舍宿,其处气冷如冰,灯黯黯作绿色,封闭室中有人语,至天晓死一轿夫,后方知为十刹海鬼找替身,且寺中鬼尚多,不止一二。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有某生夜宿孤馆,四无邻,与狐女交欢,致狐惊痛,穿窗而去。卷四有邹平将宿驿亭,而前驱言“驿中有怪异,宿之必致纠纷”……凡此种种,莫不反映出传统小说驿舍多怪的创作审美传统。
最后,多重叙事空间下的虚实结合,构建起古代文言小说的美学传统。构成小说叙事线索的驿舍有三部分,但整体看,可分叙述空间和故事空间两类。具体到《东阳夜怪录》,小说的“叙述空间”即荥阳逆旅。唐传奇文本中和“叙述空间”有关的文字尽管和主体故事关联性不强,但揭示了故事讲述的场合(空间)、故事的口头叙述性质及笔录过程,因而是重要的。而故事空间则具体为东阳驿旁佛寺。两类空间一为实有,一为口述。荥阳逆旅作为公共场所,所以王洙与成自虚相遇所谈,可见于现实之中,有事实根据。而佛舍境况实际是成自虚讲述自己所遇异事,从头至尾,所有精怪都只在他一人眼中,却没有他人见证,这就有了说话人夸大事实,变异情节的嫌疑。从结构看,也就构成一实一虚的特点,使唐传奇逐渐脱离史传与六朝志怪的藩篱,体现出有意虚构情节环境的特点。荥阳逆旅中“说话人”成自虚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话本的形成。而叙述空间和故事空间两者所构建出的距离感,使小说具备了与中国传统建筑相似的艺术特征,从而构建起小说的美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中,根据空间需要和文化内涵,往往呈现出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的建筑形式美法则。投影在《东阳夜怪录》中,荥阳逆旅在前,佛寺旅舍在后,两类空间一实一虚,又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和实的有机联系和有序结合,互相叠套,构成小说的情节。在驿舍环境的渲染和空间建构中,为遇鬼遇怪叙事披上了一层恐怖外衣,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含蓄蕴藉的美学传统。
参考文献
[1]鲁迅.唐宋传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9:43.
[2]李德辉.唐宋馆驿与文学[M]上海:中西书局,2019.
[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0)[M]北京:中华书局,1961:4023.
[4]肖鸿燚.唐宋时期旅馆业研究[D].河南大学,2006:31.
[5]李艳茹.唐代寺院故事中佛教寺院的叙事功能[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06):105-109.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
[7]张健.唐小说中的馆舍书写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9:22.
[8]郑向敏.中国古代旅馆流变[D].厦门:厦门大学,2000:31.
[9]龙迪勇.叙述空间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J].中国文学批评,2021(04):98-109+157-158.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