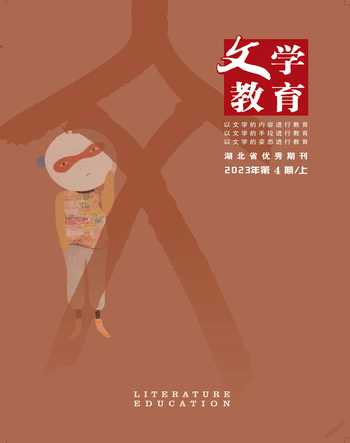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服饰描写
2023-04-27孙欣
孙欣
内容摘要:作为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在小说中,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符码,伴随着摩尔一生中诸多重要的节点,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之中。服饰不仅承载着一定的贵族象征意义,更承载着摩尔对于上层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讽刺的是,摩尔对于服饰的极度向往却催化出了其一系列的变质行为,又从根本上摧毁了摩尔的理想人生,迫使其走入无限的堕落与忏悔之中。
关键词:丹尼尔·笛福 《摩尔·弗蘭德斯》 服饰 贵族理想 堕落
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不仅标志了英国小说的发展,还为英国文学引入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女性角色[1]。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说,“《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的名字至少应该像笛福的名字一样被深深地刻在纪念碑上。它们是为数不多的、无可争议的可以被称为伟大英国小说之一的作品”。有鉴于此,这本书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陈栩早在“论《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易装”中指出,《摩尔·弗兰德斯》借助服饰这一叙事元素呈现了摩尔的独特存在。复杂多变的服饰建构了一整套为服饰主体生存和个人利益服务的话语系统和规范[2]。在“以衣行事:《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服饰叙事”一文中指出,《摩尔·弗兰德斯》中服饰意象的流变成为演绎个人身份诉求、性别话语规训,以及帝国殖民想象的多维舞台。服饰作为被广泛关注、重视的主要生活元素,可以折射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时代精神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生活写照,可以被视为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形式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3]。此外,摩尔·弗兰德斯的一生——从少女到人妻,到情妇,到小偷,再到最后成为流徙的犯人——服饰布料更是贯穿在整个故事的叙述情节之中,成为摩尔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在小说中,服饰不仅昭示着摩尔·弗兰德斯的“贵族梦”,更承载着摩尔对于上层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讽刺的是,这一为摩尔所珍视、所追寻的贵族象征却成为助推她一次次不道德行为的催化剂,促使摩尔一步步走向堕落与忏悔之中。而且,摩尔·弗兰德斯的名字也与服饰布料有着某种暗含意义上的关联,弗兰德斯与英国一盛产蕾丝花边的城市同名,这一城市因为大批荷兰妓女的出现,后以“最好的妓女”在英格兰声名远扬。由此,弗兰德斯、蕾丝花边、荷兰妓女,三者似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摩尔·弗兰德斯这个名字本身就与布料载体和妓女身份相关联。但是,根据查阅发现对于《摩尔·弗兰德斯》中服饰布料描写的研究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服饰描写承载的贵族理想
十八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异军突起,主导了消费模式的发展,服饰开始从伦敦式的便宜、流行服装模式,转向巴黎式的昂贵、专有时装样式[4]。服饰是金钱地位的象征与标志,是一种社会价值最外在的显现。所以说,在《摩尔·弗兰德斯》整个故事中,摩尔对于服饰的喜爱亦代表了其对上层社会理想生活、对金钱和地位的向往与追求。服饰作为一种承接载体,承载了摩尔·弗兰德斯一生的信仰。
在较为纯真的童年时代,摩尔对于贵妇人的定义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用出去服役的人,就是一位贵妇人”[5](6),由此摩尔想通过纺纱,缝补衣物来养活自己。当许多贵妇人让摩尔去帮忙“缝衣服、补花边、做帽子,还将孩子穿小的衣服送给她”时,摩尔便发出 “我这时真是个我所理想的贵妇人了”的感受[5](8)。后来摩尔成为拥有数百金镑的小偷,她依旧没有放下缝纫这门手艺,她白天为贵妇人缝补衣物、被褥等,晚上出去寻找合适的偷盗“机会”[5](160),所以说,无论或贫或富、或年幼或年长摩尔对于服饰都有着极强的追求欲和敏感度。当她与第二任丈夫扮成贵族去往牛津时,虽然小说中对摩尔自己的服饰只字未提,但是对于其身边仆人的描写却细致入微——“两个穿着最讲究的制服的仆人,一个骑在马背的跟班,还有一个帽子上插着鸟羽,骑在另一个马上的侍童”[5](47)——种种细节就足以侧面佐证出摩尔也必定身着豪华服饰,被称为“伯爵夫人”的摩尔第一次如愿体验到了上层社会的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一次的牛津之旅于无形之中深深加固了摩尔对于服饰的沉迷、对于金钱和地位的珍视。
服饰还出现在摩尔生命中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每当她失去一任丈夫时,她就开始细数自己的财产,财产里往往包括了金钱、衣料与衣服,她经常带着亚麻布、蕾丝花边和天鹅绒到任何地方去。“我在世界上所有的一点财产全是现款,除了像前面所说的,一些金银器具,一些衣料和我的衣服。”[5](103)“我现在还剩下大约四百六十镑,一些十分华丽的衣服,一块金表,几颗并不很值钱的钻石,还有三四十磅没有卖出去的布料”[5](59)。在当时的男权社会背景之下,摩尔失去了唯一依靠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只能通过物质财产来反复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说在《摩尔·弗兰德斯》中,服饰描写的重心主要就在于财产和地位的象征,而非款式样式。在摩尔因为盗窃未果被当场戳穿而闹上法庭时,由于她的花言巧语再附加随身携带了一定数额的钱财,让她成功塑造了被诬陷的受害者形象。她在法庭上向店主索要赔偿,得到了一百五十磅和一件黑色绸缎衣服,她本可以只索要更高的金钱赔偿,但是摩尔却乐于接受黑色绸缎衣服的赔偿。在故事的后半段,摩尔在与历经波折才与荡妇妻子离婚的一任丈夫在旅馆结婚时,为了向旅馆主人表示感谢,她送给旅馆主人的女儿“当地最好的镶花边的衣服,又买了一块骨花边送给旅馆女主人做帽子用[5](148)”。骨花边是当时各种花边中价格比较高昂的, 是指以鱼骨为别针,扎在垫子上,然后以羊脚骨为绕线管,所制成的花边,后来又称绕线管花边。精美昂贵的骨花边也体现了摩尔对服饰布料的讲究和看重。在小说的结局,摩尔对于服饰的毕生追求更是得到了印证,被流放的摩尔和丈夫杰米一路开垦荒地、料理田地,收获颇丰。在到达弗吉尼亚之后,摩尔立即为自己订购了“羊毛衣服料子、布呢、哔叽、帽子”等标榜贵妇人生活的衣物,还为丈夫买来“两条好材料的长假发、两把银柄的剑、三四杆漂亮的鸟枪、一只精致的马鞍、很好看的手枪和皮套子、红袍”等绅士配饰[5](273),这件红袍是小说中最后一件被精确描述的服饰。在近代早期,英国传统的服饰颜色有特殊的象征含义,从蓝色到土褐色就如同从蓝天到褐土一样,代表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变化,一般的大众是不能穿紫色、深红色和蓝色的服饰的[6]。直到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普通大众才有资格按照自己的喜好意愿挑选一些色彩艳丽、图案精美的服饰。“红袍”是传统意义上贵族的象征,那么这也就是摩尔对于“贵族梦”的追求的最终印证。此外,对于布料的颜色,当后期摩尔盗窃时,她穿上粗布衣服,普通长布衣,绿色围裙,戴上一顶草帽,以女仆身份到发生火灾的富人家骗取钱财。在十八世纪,服饰的颜色以褐色最常见,其次便是绿色。所以装扮为女仆时,穿了一件绿色围裙是再合理不过的。当摩尔在第一个主人家里做工时,家中的大少爷在诱奸摩尔时,摩尔本是有抵抗意识的,直到大少爷拿出了一个里面装有一百磅的金丝钱袋,摩尔才开始默许两人之间的逾矩行为[5](19)。虽然一百磅本身的数额就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金丝钱袋的出现绝非偶然,其象征的是摩尔渴求的高品质、高阶层的生活。
由此可见,小说故事情节中虽然对于服饰描写着墨不多,但服饰的每一次出现都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笛福通过对服饰布料,服饰颜色,服饰花样等不同层次的多角度描写,将摩尔对于服饰的珍视与看重予以呈现,服饰承载着摩尔对于贵族阶级的向往与追求,承载着其对于贵族生活的极度渴望,这种极度渴望也为摩尔后期的堕落倾向做了铺垫。
二.服饰沉迷致使的堕落倾向
服饰虽然承载了摩尔的贵族梦,代表了摩尔对美好生活的積极向往,却也于无形之中扭曲了摩尔的道德观念,瓦解了她的理想人生。在小说中,摩尔·弗兰德斯多次通过服饰构建不同人物身份,她带上圆软帽和草帽,即可以女仆的身份看望生病的第四任情夫[5](95),服饰为她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但这个身份却被用来处理一段不正当的感情。而且对于圆软帽和草帽,十八世纪之前,圆帽主要在平民中流行,之后由于时尚服饰的双向度影响才流行于上流社会。服饰还让摩尔成功的跨越性别进行伪装。在后期偷盗过程中,为了方便盗窃行事,她佯装成为男性和一个年轻男人合伙进行偷盗,但事情暴漏,年轻男人当场被抓。可是因为摩尔在两人合伙期间一直以男性身份自居,未曾吐露真实性别,所以年轻男人最后上了绞刑架而摩尔却毫发未伤[5](174)。以上两套服饰,虽都并不属于贵族服饰,但是若将服饰看作整体载体,的确为摩尔的不道德行为提供了便利途径,让摩尔得以掩藏真实身份,游走于建构的虚拟身份之间。但是,这种通过服饰建构不同人物身份的社会现实也是在十八世纪才得以实现。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对于服饰有严格的等级要求,不同阶级的服饰有不同的材质和颜色。只有贵族才有能力和特权购买、穿戴丝绸、天鹅绒、貂皮等质地很好、价格昂贵、色彩艳丽的服饰,而普通大众主要穿着厚重的粗呢绒和坚硬的皮革制成的服装,色彩单调沉闷[6]。直到十七世纪,服饰阶级才开始被渐渐打破,人们才可以跨越阶级购买原只属于贵族的那些精美时髦的服饰。尤其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快速增长,大众物质生活变化显著,服装消费的增加更为明显,下层和贵族之间的服装差距也快速缩小。除了日常工作的普通服装,他们还可以像贵族一样在节日里穿漂亮时髦的衣服。十八世纪初,服饰阶级的淡化与物质文化的冲击为摩尔建构不同身份提供了基础条件,服饰等级制度的没落也为跨越阶级的小说情节提供了社会现实基础。
但是,服饰等级制度的没落,并不代表服饰不再受人关注。相反,由于效仿贵族风气的普遍流行以及昂贵专有时装样式的出现,服饰成为了竞相追逐的物质消费类别。服饰仍然是财富和贫穷的分界线,棉衣的价格并没有低到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程度。摩尔曾穿上她最难看的、最肮脏的衣服,试图装扮成讨饭的女人到街上去寻找偷盗目标,但是这种服饰外貌让她“感到行动起来比穿任何衣服都更不自如”,这也再一次激发了摩尔对于服饰的执着追求与深沉热爱。当莫尔偷窃时,她也更喜欢衣服,摩尔第一次偷到的物品是一件镶有花边的、材质很好的小孩衣服[5](155),这成为诱导她开始偷盗生涯的导火索。摩尔捡回其他小偷被发现、追赶时扔掉的赃物,里面是黑色丝绢和天鹅绒,这又无形中加剧了她的侥幸心理[5](158),以这种手段获取了不菲的财产。她也喜欢偷盗典雅时尚的服饰及布料,“包里没有钱,也没有金银器皿同珠宝,却有一身非常好的印度花缎衣服,一件长褂和裙子,一些非常好的弗兰德斯花边做成的帽子和袖口,这些东西的价钱我是很清楚的”[5](194)。印度印花棉布是十七世纪末英国最时尚的服饰材料,进口量由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万匹增加到十七世纪末进口一百二十五万匹,占据英国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6]。这件带花缎的印度服饰即象征着十八世纪英国的服饰主流,又象征着高阶级的社会地位。此外,不得不指出的是,摩尔的盗窃生涯中多次盗取了花边布料,这似乎也再次佐证了弗兰德斯、蕾丝花边、荷兰妓女三者之间暗含的关联意义。摩尔·弗兰德斯与花边在小说中的最直接接触的一次事件是:摩尔发现一大批违禁的弗兰德斯蕾丝花边,在得知蕾丝花边的货物总额和藏货地点后,为了从中获取利益,摩尔向海关人员进行举报。在缴获这一批禁品之时,摩尔“设法悄悄地将其藏在身上一些,能藏多少就藏多少,藏了将近三百金磅的花边”[5](169)。最后摩尔索要的举报赏金也包括了价值八到九金磅的花边和五十金磅。在十八世纪时穿戴绣有银丝并有蕾丝花边作修饰的丝绸或者天鹅绒的外套是英国贵妇人服饰的典型特征。所以说,摩尔对于花边的执着一方面是其追逐贵族理想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花边作为最具代表性贵族服饰之一也见证了摩尔离她渴求的人生理想逐步远去的堕落历程。
综上,摩尔通过自己极为珍视、喜爱的服饰元素一次次成功进行伪装,一次次成功逾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又全身而退。服饰不仅是象征性目标,更成为了一种媒介,但这种媒介并未推动摩尔朝着贵族理想目标迈进,却将其拉入无底线的堕落之中。
从服饰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小说通过不同的服饰勾勒出了摩尔一生传奇的贵族奋斗史。摩尔的服饰既是迷惑观众的道具,又是自我保护的绝佳策略,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演变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符码。摩尔将对于贵族生活的向往承载于服饰之上,从明眸的少女到流放的罪犯,摩尔一直执着于自己拥有几件服饰、几件衣料。可是这种极度的向往却催化出了变质的行为,摩尔为之崇尚的贵族生活又从根本上摧毁了她的理想人生,迫使其走入无限的堕落与忏悔之中。
参考文献
[1]McCoy, Kathleen. “The Femininity of Moll Flanders.”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7(1978):413-422.
[2]陈栩.“论《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易装.”《云南农业大学学报》,7(2013):115-118.
[3]陈栩.“以衣行事:《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服饰叙事.”《新西部》,7(2019):99-108.
[4]陆扬.“身体与空间:18世纪英国小说中女性的衣着分析.”《外国文学研究》 42(2020):52-59.
[5]笛福著,梁遇春译.摩尔·弗兰德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6]王洪斌.“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世界历史》6(2016):15-30.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