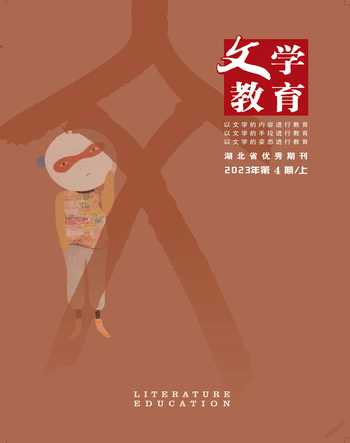从“格拉斯家族”的书写看塞林格创作的禅意修行
2023-04-27丁笑俪
丁笑俪
内容摘要:格拉斯家族是J·D塞林格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群像家族,从《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三部作品中可以窥得格拉斯家族中诸人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其角色命运与塞林格本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所接受的佛教禅宗思想彼此糅杂、互为补充,形成了塞林格后期创作中独特的禅宗世界观与自我救赎、自我超越思想。
关键词:塞林格 禅宗 格拉斯家族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是美国二战后最具声望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于15岁时进入一所军事学院学习,1942年开始从军,在四年的军旅生涯后,于1946年选择退伍,转身投入文学创作。1951年,他发表了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作品的发表引起了世界性轰动,小说受到各国读者的追捧,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然而,借此震惊文坛的塞林格却在此时选择了隐居,直至2010年去世前,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在此期间,塞林格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九故事》(1953),中篇小说《弗兰妮与祖伊》(1961)《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1963),也正是在这四部作品中,塞林格勾勒出了其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群像家族——格拉斯家族。
塞林格何以在初露头角之后就选择遁世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问题,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内华达大学的教授约翰·昂鲁说:“塞林格决定不再发表作品,这是受了他的佛教信仰的很大影响。他希望尽可能不被人注意,放下他的自我。”[1]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的创作映证了约翰·昂鲁教授的说法,“放下自我”也成了塞林格书写“格拉斯家族”时的中心思想之一。
格拉斯家族共由9名成员组成,包括父亲莱斯、母亲贝茜、长子西摩、次子巴蒂、长女波波、双胞胎沃特与维克以及最小的两位孩子弗兰妮与祖伊。在《九故事》中,长子西摩、长女波波以及双胞胎之一的沃特分别于《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在小船里》三部中出现,其余成员则在剩下的几部中篇小说中依次揭露。从创作时间上看,自格拉斯家族的第一个成员出现至该家族成员初具规模共经历了8年的時间跨度,而在此期间,其中部分角色的定位与性格也发生过微妙的改变。在《西摩:小传》中,塞林格就曾借叙事者巴蒂之口承认,在《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中的西摩实际上更像是巴蒂,而对于熟悉格拉斯家族的读者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巴蒂是整个格拉斯家族中与塞林格本人有着最高相似度的角色:
这位年轻人,所谓的“西摩”,在我早期的那个故事里又走又说还开枪的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西摩,相反,奇怪得很,他倒是像极了另一个人——哎哟,你还别说,就是我本人。[2]
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塞林格有意将一以贯之的性格赋予格拉斯家族中的角色——这并非只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某种井然有序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在于格拉斯家族中各个角色的形象与性格直接联系着塞林格对于禅宗接受的不同阶段,其中甚至包含着他对于美国后世读者对于禅宗接受的预测。
禅宗思想与塞林格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最早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我们就可以轻易捕捉到禅宗思想的显形。其中最为经典的是霍尔顿在出租车上与司机所发生的关于鸭子的对话。面对霍尔顿提出的“鸭子在湖结冰后会去哪”[3]的问题,司机答非所问地告诉他“鱼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老地方,那些鱼,就待在破湖里边。……(鱼和鸭子)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4]这段角色间的对话是一种典型的“禅悟”体现。鱼和鸭子虽然并非同样的物种,但它们却是相似的永恒存在。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是最先尝试通过禅宗进行自救的角色,他是特立独行的、反叛的,然而这种反叛中却又夹带着一丝对孩童的温情。从故事的结局看,霍尔顿的自救并未成功,他最终陷入了某种模棱两可的精神困境。或许正是这片困境给塞林格以启发,到了创作《九故事》时,塞林格作品中的禅学意味更加明显,他直接将《禅宗公案》中“双手击掌之声人尽知,只手击掌之声又若何?”一句置于《九故事》的扉页,以这句话来对其中的每篇故事进行注解。然而,与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所不同的是,格拉斯家族中诸成员不再表现出如霍尔顿一般的激进与反叛,一份细若游丝的温情裹挟着困顿中的格拉斯一家,愤世嫉俗的青少年形象最终被具有盎然禅意的成年智者引导着走出心灵的迷宫。
在创作格拉斯家族时,塞林格并非对每一个角色进行细致刻画,而是对人物及其功效进行详略得当的安排。在格拉斯家族中,塞林格对于父亲莱斯、母亲贝茜、长女波波以及两位双胞胎沃特与维克的着墨较少,而对西摩、巴蒂、弗兰妮和祖伊则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这两组角色中,前者成为了外部世界背景的铺垫,而后者则是内心世界困境的表征。这两组角色各司其职,为读者描摹出塞林格禅意世界的雏形。
维克与沃特是格拉斯家族的一组双胞胎,维克是原先是一名四处游走的记者修士,后选择入世修行。有学者认为维克形象的原型是一九六三年发表了《天主教禅》的黑衣教团修士格雷厄姆。[5]沃特出现于《九故事》中的《康涅狄克州的威格利大叔》篇,他是一个爱说冷笑话的美国大兵,在母亲贝茜眼里,他是格拉斯家族唯一快乐、真正正常的孩子,而他最终却死于二战。波波同样出现于该短篇集中的《在小船里》一篇,故事讲述了一个敏感的小男孩莱昂内尔因听见女仆说犹太人父亲的坏话而离家出走,最终被母亲波波哄回家的故事。塞林格对上述三个人物的经历书写无疑与二战后的美国背景挂钩。世界性的战争宣告着人类乐园的解体,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人们长久以来建立的精神世界逐渐崩塌,人类的残酷暴行宣告着上帝的死亡,现实世界的无序同时反映着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个得以解救精神危机的新出路,因此,异域文化在此时此刻进入了塞林格与其笔下角色的视野,这也成为了他禅意修行的开始。
如果说波波、沃特与维克分别代表着外部世界的混乱,那父亲莱斯以及母亲贝茜则更多地象征着内心世界的喧嚣。母亲贝茜是格拉斯家族中“正常人”的代表,此处的“正常”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与“庸碌”互换。她是二战后心灵空虚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精神世界的匮乏令她不得不以现实中的忙碌来自我填补,因此她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孩子们身上,然而,身为母亲的她面对早慧孩子们的困境无计可施,因而只能成为某种使人厌烦却又无可奈何的“噪音”的展现。对于早慧的格拉斯的孩子们来说,庸碌的父母并不能为自己指引生命的方向,毋庸说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圆满。因此,担任起家族成员指引者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大哥西摩的身上。
对于格拉斯一家,尤其是巴蒂与早慧的弗兰妮、祖伊而言,大哥西摩乃是他们真正的精神指路人,而在故事中,塞林格似乎也有意将西摩的形象与得道的禅宗大师形象联系在一起。西摩是个才华出众的早慧青年,他从小喜爱中国和日本文化,在十四岁时就进入了大学。因其出色的智力、感受力、敏感性与爱的能力,因此这一角色对于禅宗有着相当深刻的体悟。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中国佛教“禅”的基本教义是将将印度的佛学理论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而创立的,随后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在《抬高房梁木匠们》中,就出现过西摩打着手电给妹妹弗兰妮念《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中的伯乐相马的故事。这是西摩最喜欢的道家故事之一,由此可见西摩所受到的禅宗思想之浸润。然而,西摩对于禅宗思想的信仰与当时以基督教文化为尊的美国社会却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就令西摩处于一种极大的矛盾之中,使他成为了一个另类的智者。他对着周遭的一切人怀着深切挚厚的爱,但这种爱与随性却常常使他显得特立独行,使他作出逃婚与越过婚礼直接与妻子进行蜜月旅行等看起来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径,而这无疑引发了妻子母亲的质疑与厌恶。世俗的阻碍与隔阂是塞林格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难题之一,对于西摩而言,这也是他所欲克服与超越的困境,而他超越困境的最终方式则是死亡。禅宗的终极目标就是开悟、解脱,就是在自然自在中对终极存在的洞悉。[6]通过超脱的死亡,西摩克服了一切障碍。
在《弗兰妮与祖伊》中,这两个从小受到西摩与巴蒂教导的早慧孩童也正是通过西摩式的禅意得到最终的解脱。作为格拉斯家族的一员,他们自小体味着一种格拉斯式困境——因早慧而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无法沟通。这让弗兰妮感受到由衷的痛苦:
“我只知道我快疯了,”弗兰妮说,“我受够了自我,自我,自我。我的自我和所有人的自我。我受够了所有想去某个地方的人,想做出点成就的人,想讨人喜欢的人。真恶心——就是恶心,就是。我不管别人说什么。”[7]
弗兰妮对于自我的厌弃,实质上是来自于精神上的孤獨与焦虑。男友赖恩试图给予弗兰妮安慰,然而只遭受到她更剧强烈的拒斥,因为赖恩的安慰仅仅是在弗兰妮困境的外部徘徊与周旋,却始终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即因理解力的差异而导致的深切的孤独。弗兰妮试图寻求宗教的帮助,然而,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祷告所求的乃是逃避,而非真正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正是这个时候,弟弟祖伊出现了。他拨通了打给弗兰妮的电话,在电话中,祖伊假扮成西摩,带弗兰妮回忆起小时候的故事。多年前,早慧的二哥巴蒂曾而录制“智慧儿童”节目。上台前,西摩要求巴蒂把皮鞋擦干净,巴蒂极不情愿,因为对于他而言,录音棚里的众人都如同白痴,何必为了他们擦皮鞋呢?西摩则劝说巴蒂,不管怎样擦擦皮鞋吧,为了那个“胖女士”。祖伊告诉弗兰妮,此处的“胖女士”正是耶稣本人,体悟到这一点后,弗兰妮顿悟了,她的精神危机也就此解除。
胖女士的故事向来是塞林格作品中的著名意象,对祖伊来说,耶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具备着佛禅的慈悲与智慧,其中表达出了作者塞林格试图将东方智慧与西方宗教融入在一起的意图。西摩的“胖女士”故事中其实内含着一种宗教救赎式的宽厚与博爱,即对于身边的人充满包容之心,不因见识的差异而对他人抱有偏见,否则这终将导致弗兰妮式满是自我的困境。弗兰妮与祖伊在此刻成为了典型的禅宗弟子与大师的意象,而西摩则是禅宗的象征,借助禅宗中的宽恕与大爱思想,弗兰妮成功解除了自己因早慧而造成的危机。祖伊——唯一一个因西摩的死亡而愤怒的孩子,也通过此事对西摩之死感到释然。
最后一个被重点刻画的格拉斯成员是二哥巴蒂。他是《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的主要叙事者,研究禅宗的大学老师,也是最贴近塞林格本人形象的人。倘若说西摩是一个虚幻的禅宗形象,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巴蒂则是对于西摩思想的活注脚。在《弗兰妮与祖伊》一篇的开头,他寄给祖伊一篇长信,其中谈及了他与西摩从小对弟妹进行禅宗教育的原因:
……然而关键的关键在于,西摩当时已经开始相信(而我也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认同他的观点),教育这个东西,如果根本不以追求知识为起点,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教育都会芬芳依旧,也许是更为甘甜。铃木博士在哪里说过,处于纯意识的状态——satori[开悟]——意味着在上帝说“要有光”之前便同上帝在一起。[8]
在这段文字中,塞林格借巴蒂之口直截了当地展现了他本人所受的禅宗影响,而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在这段文字中,也隐含着巴蒂本人的困境。教育应不以追求知识为起点,而身为大学教授、自小早慧的巴蒂,却没有办法做到抛却“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对自己有着深度迷恋的祖伊有着相似之处,这便是巴蒂的困境。因此,在给祖伊的信中,巴蒂这样说:
这一次我玩的全知全能的把戏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笑,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应该对我体内自作聪明的那一部分表示尊敬,那就是你。几年前,在我还是个准作家的最初也最混乱的日子里,有一次我给S.(即西摩)和波波念了一篇我刚写好的小说。等我念完了,波波不动声色地说(但她的眼睛看着对面的西摩),这个故事“太聪明了”。S.摇摇头,远远地冲着我乐,他说聪明是我永远的痛,聪明是我的假肢,让大家意识到我的聪明是最大煞风景的事。祖伊老兄,我这个老瘸子敬告你这个小瘸子一句,我们应该惺惺相惜才是啊。[9]
对于西摩而言,他内心的一切不平静并非出于愚钝,而是因为太过聪明。这种聪明使得他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普通人的立场,也令他失去了鉴赏未经雕琢的自然之美的能力。他倾向于使万事万物臻于完满,而这份完满中充斥着大量的人工痕迹,这是巴蒂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作家的危机,同时也是包括塞林格在内的众多小说家的危机。在巴蒂之前的回忆中,他曾提及西摩教自己的打弹子的技巧——不瞄准的瞄准,这即是告诉巴蒂如何克服“聪明”之弊端,其中也暗含某种“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创作思路。正如《九故事》扉页禅宗公案里的“独手击拍之音”所暗示的那样,这段话的真谛在于告诫读者放弃一直以来用于拘束自己的理性规范,从世俗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品味本真的世界,消除一直以来与俗世的对立态度,借此获得生命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方式”异曲同工。只有摆脱了精神的桎梏,才能彻底实现自我救赎与生命超越。
通过对格拉斯一家的书写,塞林格完成了自己的禅意修行,波波、沃特与维克是二战后混乱阴鸷的时代背景,父亲莱斯与母亲贝茜是环绕在耳畔关切却喧嚣的杂音,西摩是得道的拯救者,他在这样的社会中将不可逆转地步入死亡,正如在《九故事》《泰迪》篇中的那个先知小男孩儿一样,剩下的巴蒂、弗兰妮和祖伊则是在这种精神危机中挣扎与自救的人。格拉斯家族的经历不仅仅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更是塞林格心中小小的禅意世界。在他的行文中,不光有晦涩的“布道”,更怀抱着对笔下人物乃至整个世界的悲悯之情,这使得塞林格的作品常常体现出一种东方的物哀之美。其诗意的语言,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坛来说是罕见的,在他的影响之下,垮掉派中的若干成员也走向了对于禅宗的品悟,但他们对于禅意的诠释却迥异于塞林格。
二十世纪前,禅宗还只是东方的智慧。一九二七年,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在英国伦敦出版《禅佛教文集》的第一卷,禅佛教首次面对西方进行自我表述,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将“禅”混同于“神秘主义”和“静默主义”(Quietism)的西方想象。[10]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对禅宗的接受出现新的转机。二战让西方知识分子对神学观念乃至基督教产生了怀疑,西方旧有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被逐步消减并重塑。恰逢此时,研究意识活动与心理状态的心理学引起了广泛注意,并就此登上历史舞台,用于解决“人”的种种问题。禅宗思想也由此进入西方视野。他们认为: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神观修行能导致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不立文字,不起分别”的禅宗最强调直观自悟,不太注重禅理的研究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人的心态。[11]禅宗在美国盛行一时,得到众多美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精神病理学家的追捧,塞林格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修习禅学,接受禅宗思想。区别于后世垮掉派代表人物凯鲁亚克与艾伦·金斯堡所表现出的张扬自我、放荡不羁的“达摩之狮”式禅意,塞林格对禅意的接受与吸收更注重其深幽清远的旨趣、适意洒脱的境界及身心自由的超越精神,而这些精神体现在其文章中,便形成了独特的塞林格式人情味。
自《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塞林格对于事物的体味多了一分冷静与沉着,也多了一分同情与悲悯,他对这个世界的反抗不再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更表现于角色人物的精神危机与自我拯救中。这种对于纯正的“禅”的捍卫,令他的作品一反西方自希腊文明以来的酒神式疯狂与太阳神式理性的轨道,延伸出了颇具东方特色的沉重哲思与哀而不伤的意蕴,而这正是隐藏在塞林格笔下创作的禅意修行主题下的生命超越。
参考文献
[1][美]J.D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2][美]J.D塞林格:《九故事》,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3][美]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4][美]J.D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5]房定坚.塞林格与中国文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17-19.DOI:10.13971/j.cnki.cn23-14
35/c.2004.04.006.
[6]赖庆沅.塞林格的“中国情结”[J].青年文学家,2010(03):7.
[7]卢睿蓉.禅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渗透和发展[J].名作欣赏,2010(36):123-124
+127.
[8]卢一欣.矛盾、见证与治愈:J.D.塞林格《笑面人》中隐蔽的“中国”[J].中国比较文学,2019(04):168-179.DOI:10.16234/j
.cnki.cn31-1694/i.2019.04.012.
[9]罗四鸰.抛开塞林格,洗钵盂去——从西方早期禅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J].书城,2009(06):98-102.
[10]马文净.弗兰妮的自我救赎——从禅学角度解读《弗兰妮与祖伊》[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04):45-48.
[11]孟湘.塞林格的“生命超越”与中国的“禅”[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7(04):25-29.
[12]任媛.超越情怀与诗意建构的结合——从与金斯堡的比较看塞林格对“纯正的禅”的捍卫[J].中国文学研究,2017(03):124-128.DOI:10.13399/j.cnki.zgwxyj
.2017.03.022.
[13]任媛.焦虑中的禅意之思:贾宝玉与塞林格笔下青少年之比较[J].明清小说研究,2019(01):154-167.DOI:10.13674/j.cnki.32-1017/i.2019.01.011.
[14]任媛.塞林格的禅意叙事[J].世界文化,2018(12):26-29.
注 释
[1]任媛.塞林格的禅意叙事[J].世界文化,2018(12),第26页。
[2][美]J.D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3][美]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4][美]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5]罗四鸰:《抛开塞林格,洗钵盂去——从西方早期禅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J].书城,2009(06),第102页。
[6]任媛:《塞林格的禅意叙事》[J].世界文化,2018(12),第28页。
[7][美]J.D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8][美]J.D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9][美]J.D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6页。
[10]罗四鸰:《抛开塞林格,洗钵盂去——从西方早期禅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J].书城,2009(06),第99页。
[11]房定坚:塞林格与中国文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第17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