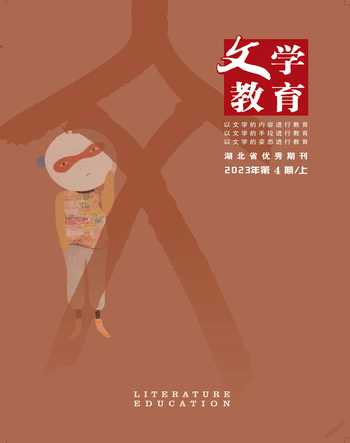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人羊》中羊的象征意义
2023-04-27沈骏楠
沈骏楠

大江健三郎(1935-)是日本战后社会派作家的代表,也是当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大江在大学中广泛接触法国文学,并在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影响之下对存在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借由怪异的性表现形式,大江深刻描绘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封闭与日本民众的恐慌情绪。继第三新人之后,他与石原慎太郎(1932-2022)、开高健(1930-1989)并称为日本“新世代作家”。
《人羊》是大江健三郎批判战后日本社会的代表作。战后空间中的监禁状态和美军霸权下的身体政治在小说中得以凸显,这些关键词也反映出中日学界对《人羊》研究的重心。史忠秋(2014)以大江健三郎小说《饲育》和《人羊》为中心对小说中的身体叙事的深层含义和小说主题进行分析,因此含有大量关于小说《人羊》中身体政治的分析。高桥由贵(2011)通过小说中的身体、言语描写分析公交车中日美之间权力关系不对等的状态以及公交车中象征战后日美关系的表现。陈汝倩(2022)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以及安保体制构筑为背景,运用多重理论并尝试从身体规训、精神管制的视角切入小说《人羊》,并借此揭露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权力操控。董悦(2020)主要圍绕小说主人公“我”上车与外国士兵下车两个叙事结构为核心,探究历史视域下日本战败后美国霸权主义暴行和日本战后空间及其国家隐喻,探究了小说中美军权力凌驾于日本社会的现象。
另一方面,《人羊》的先行研究中,还有不少对“羊”这一动物意象的含义进行过探讨的内容。比较典型的研究有,江口真规(2015)总结了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观念中“羊”的词汇意义的变迁,并提出“羊”在小说中象征了男同性恋或兽交行为中的被支配者,具有弱势地位。除此以外,霍士富(2013)认为,以“我”为代表的战后日本人如同“羊”一样温顺地忍受着美军士兵的飞扬跋扈的行径,并提出“‘羊那‘温顺有余的、任人宰割的奴性”实际上是暗示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另一弱点”。
通过梳理先行研究可以得知,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对《人羊》文本中体现的空间叙事与身体政治的分析。虽然其中也有关于小说中“羊”的意象的讨论,但是关于这一意象的研究多集中在小说中明确出现的“羊”的意象当中,没有深入挖掘小说中未明示的“隐羊”。因此,本文以小说中“羊”意象的象征意义为核心,通过考察小说中明确出现和未明示的“羊”的意象以及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成立的特殊慰安组织,从权力构造、精神管制以及身体规训等不同角度,揭露在日本的政治权力受到美国占领军操控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政治家妄图牺牲国民、成全自身利益的野蛮行径。
一.小说中三次明确出现的“羊”
通读整篇小说,我们可以得知,“羊”这一意象在小说中明确出现一共有三次。
“羊”这一意象第一次出现是在外国士兵对以“我”为首的后排乘客施以暴行的时候,外国士兵口中的“羊”。
打羊,打羊,啪,啪!
他们用地方腔调很重的外国话劲头十足地反复唱着。
打羊,打羊,啪,啪!
一个拿着刀的外国兵朝车厢前部走去。其他几个外国兵也去给他助威。……
打羊,打羊,啪,啪!
这样一来,每当汽车晃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和前面职员那有着褐色斑点的冻得僵硬的瘦屁股撞在一起了。(大江健三郎,2000:7)
在外国士兵的话语描述和视线中,日本乘客如同基督教中容易迷失、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感化的人。外国士兵把日本乘客视作“羊”的举动,是一种夹杂着身体规训和精神管制的“凝视”,充分反映了美国占领军对日本人支配和改造的野心。(刘玮莹,2018:61)在这里,温顺的“羊”与强大的外国士兵形成鲜明对比,并且“羊”与士兵们的力量反差也构成了一种权力不对等的图示,被压缩进了公交车这一象征战后日本的权力空间中。
“羊”这一意象第二次出现是在小说主人公“我”叙说故事时提到的“羊”。“我”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多次用“羊”来称呼被外国士兵扒下裤子的日本人。例如:
被当成了“羊”的人们都慢吞吞地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又返回到座席上。“羊”们垂着头,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浑身颤抖。于是,没被当成“羊”的人们,反过来却用手指托着血往上涌的脸颊看护着“羊们”。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
接着,所有坐在前部座席上的被兴奋烧红了脸颊的男人们也都走了过来,和教员们站在一起。他们拥挤着俯视着我们这些“羊们”。
……
站着的乘客围着我们义愤填膺地说着,就像围猎时追赶野兔的一群猎狗。我们这些“羊们”温顺地垂着头坐着,一声不响地听凭他们数落。(大江健三郎,2000:8-9)
在“我”口中的“羊”表达了对占领期间臣服于美军士兵的日本人的无奈。当麦克阿瑟带领的美国占领军踏上日本领土之时,日本人展现出了高度顺从的态度。这种恭顺态度既有战后日本民众希望利用美国的庇护保障日本的自身安全的私心,又有和平主义者希望借美国的力量遏制日本战争狂热倾向和殖民扩张野心的考量。(董悦,2020:80-81)因此,在公交车这一微缩的战后空间里,无论是一开始外国士兵对“我”施以暴行之前抑或是施以暴行之时和之后,日本乘客们大多保持了这种不反抗的态度,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前两次出现的“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战后日本和美国权力关系构图之下所形成的“羊”。第二次“我”口中的“羊”,也是美军身体规训和精神管制延续的象征。
而文中第三次出现的“羊”却有所不同,是外国士兵离开后的“羊”,即日本人同伴口中塑造出来的“羊”。“羊”第三次出现是在教员口中。
喂,你怎么了?教员焦急地问,你怎么不吭声。
我想就那么埋着头走出派出所,可教员却叉着腿堵住我的去路。
喂,你听着。他用起诉一样的声音坚定地说。得有一个人为这个事件做出牺牲。你是想在沉默中遗忘掉它吧,我看你还是下决心为此付出点儿牺牲吧,做一头牺牲的羊!
做羊?我对教员的话很气愤,可他还是努力热心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并且露出了恳切与和善的表情。我还是固执地闭口不说一句话。(大江健三郎,2000:15-16)
教员口中的“羊”有别于前两次出现的“羊”,是一头为起诉美国肆意妄为行径这件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而做出牺牲的“羊”。“牺牲的羊”中隐含着教员强迫受害者“我”为反抗美国霸权而甘愿牺牲的道德意义。在考察文中第三次出现的“羊”的意象时,有必要结合说话者教员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来展开。任雅萱(2019:107)认为“教员这一人物形象是《人羊》这部小说中最为矛盾且复杂的”。在不同读者的理解中,教员既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但总之教员这一形象的政治色彩浓厚。通过对小说中空间象征及权力关系的分析可以得知,教员起初是旁观者中的一员、是臣服顺从于车上外国士兵的乘客之一,并且与外国士兵和“羊们”形成了一种“旁观/加害/被害”的关系;等到外国士兵下车以后,教员逐渐从旁观者中脱离,成为带头引导反抗的人;等“我”和教员前往派出所以后,教员逐渐替代先前外国士兵的加害者地位,反而与警察和“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加害/旁观/被害”的关系;到了最后“我”和教员离开派出所时,教员一直尾随跟踪“我”,目的是要将一切公之于众。公交车上事发之时教员的不作为与事发后教员执意要反抗的转变可以看出,教员从事发之初就没有和以“我”为首的“羊们”处在同一位置上。外国士兵离开以后,教员一直强迫以“我”为代表的“羊们”告发外国士兵,与“羊们”想要忍气吞声的诉求相违背。于是,“羊们”产生了反抗教员的冲动。同时,教员的这种以“鼓励”为幌子的强迫是一种言语暴力和过度干涉,这实际上与外国士兵们的暴行如出一辙。他为了达到自己心中反抗美国的目标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受害者“我”来成全这种目的。
那事我想你不会忍气吞声吧?教员很谨慎地说。别的家伙都不吭声,只有你不想忍气吞声,要和他们斗一斗吧?
斗?我吃惊地注视着教员的脸,薄薄的皮肤下潜藏着重新燃烧起来的情感。那一半是抚慰一半是强迫。
我帮你和他们斗。教员向前跨了一步说。不管到哪儿我都去给你做证。
我暧昧地摇了摇头谢绝了他的建议,教员充满了激励的手腕挎上正要走开的我的右臂。(大江健三郎,2000:12)
这一段教员口中提到的“斗”已经失去了本意,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达成“查明你的名字”这个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让“我”和外国士兵无地自容。即为了不屈服于一方而使另一方屈服。所以,在文中教员用到了“牺牲的羊”这一表达。这种行径其实和战后日本右翼强迫民众的行为相一致,因此教员的形象其实是在讽刺日本右翼政府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日本国民的政治手段。操控民众的野心被披上伸张正义的外衣,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权力者反而站到了道德制高点,在美军士兵走后成为新的“加害者”。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一头没有明示的“羊”。下一节,笔者将就这头隐秘的“羊”做进一步分析考察。
二.小说中的“隐羊”与战后慰安妇
小说中没有明示的“羊”,即外国士兵身上坐着的女子。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到女子的来由,但是结合故事背景可以推测,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二战后日本街头出现的专门为占领军提供色情服务的吉普女郎(パンパン)。
日本战败以后,政府为了防范占领军强奸妇女等暴力行为,着手准备建立面向占领军士兵的“国家卖淫组织”。时任大藏省主税局长池田勇人在拨出筹建组织的资金时就表示:“如果僅靠这点钱就可以挽救日本女子贞操的话真是物超所值。”(千田夏光,1988:214)在这种官方支持的和“官民一致”的推动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成立。1945年8月,首个特殊慰安所“小町园”开业。特殊慰安设施成立之前,日本政府在皇居前宣读了建立声明:“在‘昭和阿吉几千人的人柱之上筑起力挽狂澜的防波堤,力争在此后百年守护民族纯洁之同时,铸就战后社会秩序之根本的地下支柱。”(隅谷三喜男 大野木克彦,1972:1357)
建立声明中提到的“昭和阿吉”本质上是将这些女郎和唐人阿吉联系在了一起。唐人阿吉(1841-1890)是日本幕末时期伊豆下田的造船匠之女,后成为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之妾。唐人阿吉的故事代表了安政元(1845)年日本开国以来嫁给外国人做妾的“绵羊(らしゃめん)”。在日本开国之初,日语中“绵羊(らしゃめん)”一词多用以蔑视嫁给外国人做妾的女性,但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小说和戏剧中却掀起了一股“阿吉热潮”。此时,唐人阿吉的经历在小说和戏剧中成了脍炙人口的故事。这种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卖淫者与唐人阿吉联系起来的举动,为特殊慰安设施的成立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在东京和日本各地方招募慰安妇的时候,政府都以“报效国家”和“效忠天皇”为由劝说曾经的色情从业者加入。勉为其难成为慰安妇的人之中,有不少受到美军士兵的虐待,轻则弄瞎一只眼睛或是打断一条腿,重则在慰安所被杀。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个例,所有服务于美军的慰安妇们都豁出了性命。(台東区史編纂専門委員会,1997:544)特殊慰安设施中的慰安妇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小说中的女子那样为不同美军士兵服务的吉普女郎,另一类是只为特定美军士兵服务的专门娼妓(オンリー)。尽管像这类慰安妇在同行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她们在日本国内遭人唾弃,在美军士兵离开日本后又被抛弃,因此,她们和吉普女郎们一样,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有秩序地投降”和“有秩序地接受占领”而被日本政府所利用的棋子。此后,由于性病泛滥加之美国国内社会的道德谴责,特殊慰安设施逐渐被取缔。解散之时日本政府始终未对其五万多慰安妇做补偿,这些慰安妇逐渐沦为日本街头的洋娼。
小说中写道,坐在外国士兵身上的女子挑逗“我”的举动遭到“我”的反感,而“我”不小心将女子推倒在地的举动惹怒了外国士兵,因此导致了两者的对立。女子是小说前半部分事发的导火索,也是有别于小说中明确出现的“羊”以外的隐藏着的“羊”。通过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及行为举止我们可以推断,她很有可能就是“吉普女郎”,即一头从“绵羊(らしゃめん)”嬗变而来的“羊”。当外国士兵对车上乘客施以暴行之时,下述关于女子的细节描写耐人寻味:
女人自暴自弃般地放开嗓子和外国兵们合唱起来。
打羊,打羊,啪,啪!(大江健三郎,2000:7)
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得知,女子将自己与加害者外国士兵们摆在了同一权力位置上。按照松枝诚(2007:57)的归纳:“她(女子)不单单是一个占领期间被美军支配的形象,在美军面前她是‘羊,在‘东洋人面前她又拒绝承认自己是‘羊,反倒是把自己想成了拥有权力的支配者。”这头“羊”有别于美军暴行下被统治的“羊”,她与外国士兵的关系和公交车空间中日美之间单纯的“支配/被支配”的权力构造明显不同。女子与外国士兵们的视线融为一体,与“羊们”形成一种复杂三元结构下的“支配/被支配”关系,权力构造因此发生改变。
自然,从小说中“我”被挑逗那一刻起,女子的“特殊地位”已经凸显出来。尽管女子也是“东洋人”,但她却和外国士兵一样在权力空间中分配到了较大席位,并且将自己与外国士兵置于同一地位上,如同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专门娼妓一样。但这些为外国士兵服务的慰安妇最终还是逃脱不了骂名,成为世人唾弃的对象。因此在外国士兵下车离开公交车这一“战后空间”以后,她也因此失去了生存空间并被迫离开。川岛高峰(1998:12)提到:
她们(慰安妇们)为了保护民族纯正血统而卖身。如果这样的行为都能被称作是“谨遵天皇之命”的话,这和战前所倡导的“日本妇道”、“家的本义”大相径庭(中略)这样的行为与其本质相背离,如果硬要说与之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这样的决策仍然暗含对自己民族同胞的虐待以及欠缺当事者意识。
作为战后日本国家策略的牺牲者,这些吉普女郎们很可悲。她们被政府所谓的“为国效力”的口号欺瞒,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牺牲的羊”。因此,作者在此借用吉普女郎的两难境地再度讽刺了日本右翼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惜牺牲国民的野蛮行径,与教员口中“牺牲的羊”形成呼应。
本文从小说《人羊》中出现的“羊”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入手,考察了小说中三次明确出现“羊”这一词汇的文本以及小说中没有明确指明的“隐羊”。
通过分析文本中不同文段里出现的“羊”一词的不同含义可以得知,小说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羊”象征着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变态管控以及对日本民众的身体规训。而第二次主人公“我”在叙述事件过程中提及的“羊”,和第一次出现的“羊”一样,也是美军身体规训和精神管制延续的象征。同时,文中第三次出现的“羊”这一意象与前两次略微有所不同,是由同样身为日本人的教员塑造出来的“牺牲的羊”。这里的“羊”暗含对日本右翼牺牲国民换取自身利益的讽刺。
另一方面,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到的“隐羊”隐喻了占领期为在日美军提供色情服务的特殊慰安组织的吉普女郎。这些吉普女郎作为战后日本国策指引之下的牺牲者,被政府提倡的“报效国家”和“效忠天皇”等表面上的积极思想所欺瞒,并被迫将自己出卖给在日美国占领军士兵,从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牺牲的羊”。作者在此处再度披露了日本政治家们不惜牺牲国民成全自我的野蛮行径,这种行径与教员口中“牺牲的羊”构成呼应。
参考文献
[1]陈汝倩.2022.反“霸权主义”暴行的书写——大江健三郎《人羊》论[J].日语学习与研究,(01):52-60.
[2]大江健三郎.2000.叶渭渠译.人羊:大江健三郎作品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3]董悦.2020.从小说《人羊》看日本“战后空间”及其国家隐喻[J].牡丹,(24):80-82.
[4]霍士富.2013.鲁迅与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审美思想比较——以“狗”“羊”与“狼”为隐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02):46-50.
[5]刘玮莹.2018.大江健三郎《人羊》中“羊”的多重隐喻和自由哲学阐释[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8(03):60-64.
[6]任雅萱.2019.浅析大江健三郎《人羊》中的人物形象[J].汉字文化,(02):105-107.
[7]史忠秋.2014.论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中的身体叙事[D].复旦大学.
[8]江口真規.2015.らしゃめんの変容と戦後占領期文学における羊の表象: 高見順『敗戦日記』·大江健三郎「人間の羊」を中心に[J].文学研究論集,(33):25-40.
[9]川島高峰.1998.被占領心理:肉体戦士R.A.A.と官僚的「合理性」[A].河原宏編.日本思想の地平と水脈[C].東京:ぺりかん社.
[10]隅谷三喜男.大野木克彦.1972.東京百年史.第五巻[M].東京:東京百年史編集委員会.
[11]千田夏光.1988.『従軍慰安婦』正編[M].東京:三一書房.
[12]台東区史編纂専門委員会.1997.台東区史.下巻[M].東京:東京都台東区.
[13]高橋由貴.2011.「人間の羊」における沈黙を囲む饒舌[J].日本文芸論叢,(20):53-62.
[14]松枝誠.2007.『羊をめぐる冒険』論:北海道から満州、そして戦後[J].論究日本文学,(86):55-68.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作家。1935年出生在日本南部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57年5月,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获《东京大学新闻刊》“五月祭奖”,1958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短篇小說《饲育》发表于《文学界》,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正式登上日本文坛。1965年《个人的体验》获第11次“新潮文学奖”。1967年发表《万延元年的足球》,获第3次“谷崎润一郎奖”。1989年,荣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1992年,又获得意大利的“蒙特罗文学奖”。1973年,长篇小说《洪水荡及我的灵魂》,获第26次“野间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