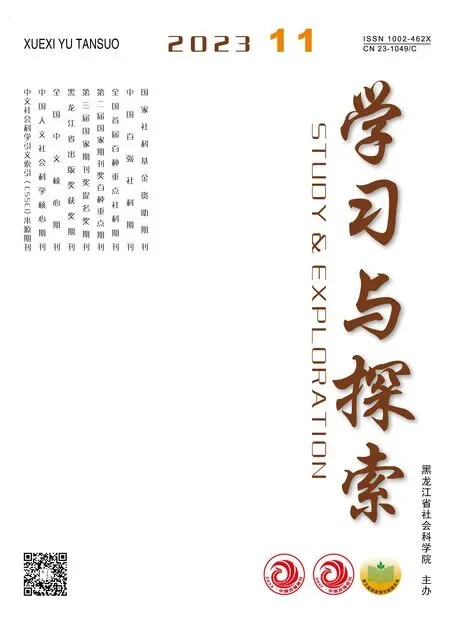模仿: 创意写作的理论渊源与早期实践探索
2023-04-24张永禄陈至远
张永禄,陈至远
(上海大学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上海 201900)
在近年全球兴起的创意写作及其学科化过程中,中外研究者倾向于把“模仿”作为其核心基础理论之一。现代模仿论受到实证主义和认知行为科学的影响,模仿关注的重心不再是模仿对象,而是重视模仿行为,和相似性、重复等普遍现象关系密切。社会学家、传播学家塔尔德就宣布模仿是人类社会的行为和根源。模仿无处不在,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相似性都源于模仿。他把世界运动归纳为三种普遍重复形式,即物理世界的波动(vibration)、生物界的世代生成(generation)和社会活动模仿(imitation),并指出社会模仿行为有三层模仿律:一是下降律,即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二是几何级数律,即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迅速蔓延;三是先外后内律,即个体对本土文化及行为方式的模仿和选择,总是优先于对外域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和选择[1]。塔尔德的模仿律观念为创意写作的模仿方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论基础。创意写作提倡的模仿论理论基础与方法已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模仿说”和模仿方法论,但不能排除古希腊、罗马的模仿说观念及其派生的模仿教学法对今天创意写作的模仿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英国著名创意写作学者大卫·莫利教授就认为创意写作教学起源于亚里士多德[2]19,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黛安娜·唐纳利在《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中指出,“摹仿论或模仿理论的教育学设计以‘艺术模仿表象世界’的概念为前提条件”[3]54,但不加区分地把古典模仿说作为创意写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不恰当的。本文从创意写作的理论视野出发,试图重新考察古典模仿说及其创作教学实践,厘清写作中模仿与创新的关系,以期拓展创意写作理论的历史根源。
一、古典时期模仿观念作为模仿论写作的思想遗产
从词源学上考察,“模仿”一词的希腊语有“模仿品、模仿者、模仿的、模仿行为”等多种含义,后转写为英语mimesis。mimesis主要是指“模仿行为实现的过程”,亦可理解为“模仿”,即mimeisthai动词抽象化后的名词形式。如果进一步品味柯林斯词典中mimesis的四种意涵,(1)(1)[美术、文学]对自然或人类行为的模仿性再现(the imitativ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or human behaviour);(2)任何表现出其他疾病症状的疾病(any disease that shows symptoms of another disease);歇斯底里病人的一种状态,类似器质性疾病(a condition in a hysterical patient that mimics an organic disease);(3)[生物学]拟态, 一种动物(尤指昆虫)与另一种动物的相似之处,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侵袭(the resemblance shown by one animal species, esp an insect, to another, which protects it from predators);(4)[修辞学]在演讲中再现他人的断言陈述(representation of another person’s alleged words in a speech)。现代英语虽然把希腊语中与mimos相关的多种词性和含义混用,但“通过动作或手势而非语言”“戏剧表演法”两大核心内涵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换言之,“模仿”一开始就是一种表演(act),因这种表演去除了言语的因素,就更突出它是一种视觉行为,一种假装的、可视的行动。鲍桑葵则指出:“要把一个对象转变成一种雕塑介质的作品涉及的就不是一个要素,而是两个要素——不仅要考虑到所要表现的对象,而且要考虑另一种介质造成了新的条件,使对象再生的行为具有想象的创造性。”[4]21“模仿”一词的原初意涵重视“行为”以及行为的“手段(介质)”而非仅仅是“对象”的观念,启发了创意写作从认识论而非本体论上发展模仿理论。
模仿说(摹仿说)作为关于艺术起源的古老说法耳熟能详,它经由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镜子说”为中介,转化为“再现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文艺理论。古希腊时代的人们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模仿是人的本能。代表人物德谟克利特指出:“我们从蜘蛛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5]112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思想,模仿的根源和对象是自然界,模仿行为是人的本能。不过从创意与模仿的关系看,我们似乎应该重视的是模仿的结果:“织布”和“缝补”、“房子”和“歌唱”等,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表征。换言之,模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理想的模仿是一种创造。
其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人继承和发展了文艺上的“模仿说”,开创了影响巨大的两大范式。鉴于他们对模仿的具体认识的不同,创意写作界认为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自觉开启了模仿写作。柏拉图从“理式”论出发,认为艺术是模仿自然的,但自然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艺术是对模仿之物的模仿,是“二手仿制品的仿制品”,摹本和模仿者的地位不会高于范本和被模仿者,因而柏拉图拒绝模仿诗人进入理想国[6]22。(2)柏拉图对“模仿”的态度其实是含混的:一方面他从理想国的纯粹性出发,否定诗人的模仿;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中用模仿的方法开创了哲学对话体。有研究者认为,“柏拉图模仿的摇摆意义说明了视觉和声音能力之间的斗争;对诗人的三重排斥可以转化为对语言至上的主张和对形象的一种禁止”。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则是摹本和模仿者的地位可以且往往会比范本和被模仿者高。我们不妨通过分析它们的基本构句形式来领会:柏拉图构句是amA,亚里士多德构句是AMa。(3)在这里,M(m)=mimeisthai(mimesis的动词形式),A(a)=author/artwork(设A的地位比a高)。
在柏拉图的模仿构句中,a是不完满的,A是完满的,反之则无须模仿。因此,一种积极的目的性、一种“崇高倾向”存在于模仿实践之中。柏拉图认为,表象世界模仿理式,而艺术模仿表象世界,因此艺术(artwork)所模仿的表象世界是理式的作品(artwork),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实际上,amA的基本构句形式可以一直连缀下去——例如AmA+——它的方向不会改变;同时,模仿作为一种剽窃式的摹影,它的性质也不会变化(因此是小写的m),m前后两者的地位差也不会改变。A位置上的范本一定是未知的,至少对于模仿者来说是部分未知的,这使它处于一种神秘的幕后——至于幕后之物的存在,本就不是必要的。柏拉图模仿说的构句中,A的位置所指涉的是神圣且神秘的范本及其创造者,永不可能被把握,更不可能通过模仿行为达到。a的位置上则永远摆着赝品和仿造者。既然模仿的是赝品,作为仿造者的诗人在道德和人格上就存在问题,他们对于理想国是有害的,应该予以驱逐。柏拉图模仿说的终点在于触及这层帷幕,福柯对于模仿说的批判正在于此——通过帷幕的现形,揭示出幕后空无一物。既然模仿的对象为空,模仿只剩下了滑稽的“崇高倾向”:毋庸说摹本了,就连范本也是一种make-believe(扮假作真)[7],模仿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欺游戏——福柯的批判力正在于揭示出了词与物的话语实践的真相[8]——模仿所构造的这种稳定关系即便是错位的也是本不存在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构句中,“模仿”一词被赋予了摹本超越范本的可能,以至于摹本的现世就向世界昭示了完满所可能达到的程度。模仿作为获知和超越的手段,是大写的模仿(M),这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尤其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艺的产生来源于模仿的本能,“诗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的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9]47。亚里士多德这一认识是对柏拉图文艺观念的发展,它把文学创作活动归结为人类先天具有的禀赋,从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艺术创造是类个体都具有的能力,模仿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而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自然行为(德谟克利特),也不是复制自然对象的机械行为(柏拉图),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知识(不是与真理隔了两层的“影像”)的来源和文明的开端,这就给创意写作“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平民化的艺术哲学,诗人(即便最优秀的诗人)也不再是柏拉图所称的“被缪斯赋予灵感的人”,而是生性特别敏锐的人,这就把艺术创作从神界拉回了人间,并紧紧与人绑定。由此,艺术创作是人人都具有的潜力,虽然潜力大小有不同,但一种普遍的、本性的表达权经由“模仿”被给予了每一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创意写作全民化是自亚里士多德肇始的。
以今天创意写作实践的认知审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存在着不足,即这种模仿天然带有一种从质料向形式的目的论倾向。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形式因是决定一事物是其所是的原因。艺术模仿现实,就是使作为质料成分较多、形式成分较少的现实向作为形式成分较多、质料成分较少的艺术品进行运动,是现实世界的质料潜能形式化,进而是其所是的运动过程。然而若果真是这样的运动,那么艺术就是作为现实实在成为它自己的目标而存在的,整个运动只是现实世界去实现它的潜能——在这个序列里,模仿者的要素消失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应该是模仿者提炼自然的规则,并用艺术介质表达出来。因此,这里消失的模仿者要素反而应该是最能动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构句中,现实世界的形式化发生了两次位移,即现实世界→模仿者的头脑→艺术品,而目的论序列却省略了最重要的中间环节。范本的实在性和观看“模仿”中所获得的创制知识是由解释摹本的要求所摆置的,这在旁观者(作者以外的“读者”)、艺术批评家等需要解释艺术模仿性的人看来,却被视若无睹了。换言之,但凡依然声称艺术实现的不是模仿者自己的而是现实世界的潜能,声称不是模仿者自己而是观众获得了知识,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构句就逃不开自身的矛盾。后来的莫里茨和康德通过将模仿转化为想象,促进了对创作者的想象力等研究,逐步解开“模仿者”之谜,为创意写作的另一基础理论——创造潜能激发作品作出了铺垫。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开创了“模仿说”的两大趋势。亚里士多德以后,对于“模仿说”的讨论,基本是围绕着两种走势的糅合和对垒展开一系列的论争、阐释和再阐释,可以从中察觉到两种构句形式的析合关系。其中值得特别讨论的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对于“模仿”的理解。在两位神学家看来,模仿的重点变成了行动本身(不是A与a的关系,而是M/m自身),是人像上帝那样去行动。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从空无所有之中创造天地”[10]263,这种创造是无中生有的,既没有先在的材料,也没有先在的形式,甚至没有时间和空间。创造世界使其存在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世界存在的形式。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他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为艺术模仿自然的创造过程。他说:“艺术所以摹仿自然,其根据在于万物的起源都是互相关联的,从而它们的活动和结果也是如此的……艺术的过程必须摹仿自然的过程,艺术的产品必得仿照自然的产品……如果艺术能够造成自然事物,它就一定要像自然那样来活动。”[11]121-122然而,艺术的创造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模仿上帝创世;易言之,“自由”并没有被当作艺术的本性,而是特定艺术行为(模仿)的结果。因此,两位神学家的观点,依然可以划为柏拉图一派,因为模仿者(人)模仿被模仿者(上帝),而人低于上帝,摹本(艺术)模仿范本(自然)而人造艺术终不敌上帝所造之人世。平心而论,抛开宗教信条,他们对于艺术创造的论述,在今日依旧振聋发聩。
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模仿教学方法审视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教育(包括文艺教学)实践中,模仿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后期,随着学校教育结构与形态的改变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才衰落。20世纪模仿理论在社会学等领域再次受到重视并发展,成为创意写作教育实践的重要方法。创意写作重视模仿训练理应要回溯到其古希腊、罗马传统,这种回顾一方面反过来刺激了对模仿教学这种古老教学方法的再认识,另一方面也提醒创意写作需尊重历史,重视对经典模仿理论的再发现。
对古典模仿教学方法的专门研究文献,如伊苏克拉底的《修辞学的艺术》、狄奥尼修斯的《论模仿》等大多遗失或仅存残篇。近年的研究主要有理查德·麦基翁的《文学批评与古典时代的模仿概念》[12]、唐纳德·莱门·克拉克的《模仿:罗马修辞学的理论与实践》[13]、爱德华·科比特的《古典修辞中的模仿理论与实践》[14]以及迪金森与芭芭拉·安合著的《写作过程中的模仿:起源、含义、应用》[15]等。从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古代的模仿教育实践主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一)演说家或教师是学习模仿的对象。古希腊时代以来, 教师/演说家的角色是神圣的,有“通往奥林匹斯山的道路上铺满了演说家的桂冠”之美誉。作为演说家或教师,他们为万人之师,是学生学习的好榜样。这个模仿的榜样,应该具备好公民、好老师和智者这三种身份。首先,作为道德楷模,他们身上无处不在地洋溢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气质,是真理、诚实、正义的化身。因此,这些智者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其次,这些演讲家或教师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演说家,他们做示范性演讲,或者亲自写演讲稿供学生模仿。最后,他们有人性化的教学方法,作为道德楷模的教授或演讲家不仅身体力行地宣扬他们的世界观和政见,还深谙演讲等技巧,并通过言传身教等方式将这些技能传达给弟子们。
当我们谈到古希腊、罗马历史上的优秀演讲家时,一般意味着这三个目标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雅典演说家伊苏克拉底认为,“一位教师必须在自己身上树立这样一个演讲的榜样,让那些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并能够模仿他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演讲中表现出别人所没有的优雅和魅力”[16]17-18。作为模仿对象的演说家或教师很在乎自身形象和行为举止,他们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是文学的审查者,用来传授道德价值观,并指出值得效仿的历史英雄等。成长既需要榜样,也需要引导,古希腊时代的智者教育对教师、演说家的定位,就是所谓模仿得以建立的模仿对象。要求弟子们对老师的模仿,并不必然意味着弟子们会成为没有自己个性的“克隆人”,而是通过对老师的模仿来让自己快速成长,也成为演讲家。学生对老师的模仿,是通过与老师朝夕相处地“观察并做同样的事”以提高自己。因此,伊苏克拉底也鼓励他的追随者们不做自己的小复制品,而是让他们成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一样的杰出者,追随者们在与伟大导师的精神融合中创造新的思想流派。
(二)模仿演讲的风靡。古希腊罗马演讲辩论之风兴盛,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群星灿烂,成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奇观。这些人大多不仅是著名的演讲家和修辞学家,还是精英教师,培养新一代的演说家传承并发扬光大其学术思想流派是他们的神圣使命。有论者指出:“演讲技巧是通过理论、模仿和实践三种方式获得的。技巧指的是一套规则,提供了一种明确的说话方法和系统。模仿刺激我们按照所研究的方法,达到某些说话模式的有效性。练习是口语中刻苦的练习和体验。”[14]比如西塞罗在《论演说家》(DeOratore)中讲道,为了克服仓促的表达和多余的风格,安东尼乌斯敦促苏尔比修斯模仿卢修斯·克拉苏。不到一年后,安东尼乌斯再次听到苏尔比修斯讲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者之间出现了多么大的差异……大自然不可抗拒地引导他走上了克拉苏宏伟而高贵的风格;如果他没有像大自然引导他那样,通过刻苦的模仿来引导自己的努力,他就永远不会在这方面达到令人满意的卓越程度”[13]。西塞罗指出,古希腊演说家连续流派的特点是模仿了一些杰出的当代老演说家或最近蓬勃发展的演说家。在《论演说家》中,西塞罗也讲述了自己模仿许多不同的当代演讲者和演员的经历,并提到了通过模仿教学走向繁荣的学校。
古希腊、罗马的学生如何模仿老师们的演讲呢?大体是模仿演讲词、演讲的修辞技巧和演讲家的风格等。模仿演讲词就是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和背诵导师或古代优秀的演讲词。教师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演讲稿供他人表演,并作为教学修辞艺术的典范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做法。教育家伊苏克拉底就建议教师使用自己的作品以及学生的作品作为范本。事实上,伊苏克拉底的所有演讲都是作为学校教授口才的典范,可以作为模仿学生的作文范本。约翰逊在《伊苏克拉底的教学理论》中指出,最简单的模仿练习是背诵模型;昆体良充分证明记忆是通过模仿学习说话的一种方法[17]。如果孩子们习惯最好的作品,他们的记忆中总会有一些他们可以模仿的东西,并且会无意识地复制他们脑海中印象深刻的风格模式。此外,他们还能掌握大量优美的词汇和短语,这些词汇和短语会在他们内心的宝库中自发地呈现出来。
修辞学习或演讲的技巧在古希腊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演讲家往往是修辞学家,为了让自己的演讲更有气势和力量,让更多的人折服和倾倒,他们非常重视修辞的使用。作为学习实践艺术的一种方法,模仿与模仿对象的这些形而上学概念无关。“模仿作为一种修辞练习,与说话者或作者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他的态度有关。它关心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如何说。”[13]在经典的模仿关系中,学生可以模仿老师的“(1)演讲方法,包括手势、口头技巧、口头表达、演讲的所有部分;(2)写作方法,包括各种写作过程;(3)结合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教学方法;(4)道德、行为、伦理、诚信、人格、古风;(5)示范作品,包括具体的体裁、编排、风格和内容”[15]5。学生对老师的模仿是亲密的师生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中,老师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学生不自觉地模仿老师们的演讲表演特色和技巧,将师长的演讲风格逐渐内化为自己的演讲风格,并镶嵌进连续的演讲和学术流派。
(三)古希腊的模仿教学训练方法。在古希腊的教育中,模仿教学法一直是教学的典范。如果单就创作(古希腊的没有专门的创作教学,文学创作被包含在修辞学中)而言,模仿可以具有多重意味。有柏拉图式的:复制想象中的、理想的艺术形式,并存在于精神完美(真理)的领域;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创造艺术的方法是正确描绘人性和个性,或完成自然界的“部分”创造一种完形的关闭过程;有模仿是学习的过程:通过复制一个例子来获得触觉书写的习惯以及获得掌握符号形式;有模仿演说家或教师的演讲方法、道德和写作模式;有把模仿作为精确写作模式:通过模式内化语言、风格、安排、形式和内容,并通过记忆、抄写、听写、释义、总结和翻译等方法进行练习;是一种生成或模仿写作过程:由模范教师指导,使用专业的、教师的或学生的模型,加上规则、分析、讨论、批评反馈和修改,以生成原创作文的过程等[15]2。对于模仿的写作训练来说,后三种更具有写作操作的意义,而不是前面三类的文艺理论或文艺批评理路。对模仿理解的多样化,也促进了在教学中对模仿的方法不断丰富和细致,从早期对演讲词单纯的背诵、模仿老师等,发展到预习、练习、复述、翻译、释义等各种模仿训练方式方法。这里介绍和当代模仿写作训练模式比较接近的三种形式:仿写、翻译和释义。
一是仿写练习。教师首先选择“最好的模仿模型”(别的优秀作品或教师本人的作品),并事先指出模型中要模仿的优点和要避免的缺点;学生必须在自己的书面或口头主题、宣言中模仿他所做的。这种模仿在20世纪被创意写作重新拾起和发展,发展为比较成熟的模式和操作程序,如精确句模仿[18]185-202和扩增句模仿[19]等,此不赘述。
二是翻译练习。对语言的翻译和古罗马的文化语境有关,罗马文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希腊文化衍生而来的,如果要提升和丰富较低文化的语言,从较高文化的语言到较低文化的语言的翻译是不可避免的。西塞罗就认为通过翻译模仿希腊文学,可以提高拉丁语、罗马人的口才和他自己的风格。在《论演说家》一书中,他承认翻译希腊最优秀演说家的演讲使用了最好的单词,虽然这些是挪用的,但对他的同胞来说是新的。西塞罗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过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译本,这些译本都是他作为练习所做的。昆体良呼应了西塞罗,他赞扬了翻译作为模仿练习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是一种极好的练习,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或将拉丁语翻译成希腊语尤其有用[13]。通过练习,学习者将学习得体的词汇、丰富的数字和有力的陈述,也就是说,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化工,也是一种积极的模仿写作行为。
三是释义练习。将现有作品转换成不同的文体形式,比如从诗歌到散文等。昆体良坚持释义是一种有益的练习。他说:“关于把诗歌变成散文的效用,我相信没有人有任何怀疑。”[13]他觉得适合散文的词不一定比适合诗歌的词更糟糕:因为诗歌的雄辩可能有助于提升散文风格;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诗意的大胆表达转变为适合散文的精确表达。我们甚至可以为诗人的思想增添雄辩的活力,填补疏漏,删减多余的内容[16]。因为不希望释义仅仅是一种解释,而是一种努力,在表达同样的思想时,与原著相抗衡。但事实上,表达一种思想的方式数不胜数,通往同一目标的道路也很多。对于释义练习,昆体良还尝试对既定主题的同一风格和语言基调的改写方式,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模仿写作训练。比如通过阅读和研究一位作家的作品,然后就问题和论点写作(类似于同题作文),比较并仔细权衡自己的陈述和对方的作品(模型),以做出优缺点对比。
综上,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写作上的模仿教学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方法。由于黑暗中世纪的禁毁运动,很多关于模仿写作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的书籍文献不幸失轶,我们只能从后来零星的文献中窥得一鳞半爪。中世纪后期,随着教育结构的转变,模仿和模仿的完整机制开始退化,强调风格和逻辑等教学风尚加速流行开来。文艺复兴的“天才论”等主流思想使想象力和创造性等观念逐渐占据上风,丰富多彩的模仿教学方法被冷落也是自然的事情。
三、从模仿走向创造
古典重视模仿,当代热衷创造。从模仿到创造的古今之变暗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创意写作兴起的历史合法性。据雷蒙·威廉斯考证,英文创意(Create)来源于拉丁文creare,“主要用来描述天神初始创造的世界”,直到16世纪以前,创造都是指向神的,“被创造物本身是没有能力去创造的”[20]92。人作为创造性存在的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产物,起源于意大利。这一时期开始倾向于把诗歌作为创作而不是模仿(即便有模仿,但“诗人模仿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产生他们的东西——上帝的创造能力”),诗人心中创造了一个异类世界,被认为类似于上帝创造的神圣行为。重视诗人的创造性标志其神性的内在化。“模仿说”在16—18世纪上半段的艺术领域是明日黄花,“模仿”意涵也发生了改变,从外在性转向模仿者的内在性,比如在爱德华·杨的观念中,模仿自然的意思就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因为它指的是通过内省实现对自然的个人体验,而不是对普遍形式的客观表现”[21]28。
但“创造力”的概念在18世纪并未取代模仿说并流行起来,因这一时期学界推崇原始天才,更关注天才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创造性的想象力),“通过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运动,想象力被重新塑造成一种创造性的能力,与激情和神性相联系,并优于理性”[21]24。想象力作为诗歌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艺术能力的统治地位,但想象力的神秘性、内涵模糊和重视激情等非理性越来越不适合对戏剧、小说等形式的分析,“直到19世纪后半叶,‘创造力’这个词才开始使用取代了过度劳累和疲惫的想象力,成为对人类崇高能力的描述”[21]28。保罗·道森通过考察后认为,欧洲长期把诗歌作为想象的领域,而文学则是指知识的领域。直到19世纪,文学才逐渐被狭义地理解为“创造性”作品而不是“高雅知识”或“文献”,戏剧、散文、诗歌和小说等先后纳入文学的门类,“这种对文学的专门理解是随着诗歌被浪漫主义者美化为人类创造力的体现而发展起来的,与科学作品相反,因此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形式”[21]35。马修·阿诺德在《当代批评的功能》(1865)中也把作为创造性的文学与作为批判性的评论明确区分开来。雷蒙·威廉斯进一步指出,将“文学”一词的含义缩小到只包括“创造性”作品的专业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普遍的人类‘创造力’的名义,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对新社会秩序的社会压迫和智力机械形式的一种主要肯定回应”[21]39。因此,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面对欧洲影响的焦虑,在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推动下,通过发展一门旨在推动学生联系现实,抒发个人真实感受的写作模式——创意写作教育,提升年轻人的创意素养和能力,让年轻的美国获得民主化与创造活力,也由此必然催生和极大发展了创意写作学科。
从艺术的核心本质看,从古典时代的模仿说到文艺复兴的想象力论再到现当代的创造力,构成了明晰的历史线索及其背后的强大逻辑合法性。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的创意写作视域下重新审视古希腊时代的模仿理论与模仿写作教学方法,既要走出浪漫主义时代持有的模仿是创造之敌的偏见,也要把想象力和创造力自觉加以区分,立足于时代的需求,把握模仿和创造的辩证法,发挥模仿对创造的推进作用,避免学习写作中走不必要的弯路。从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看,至少有两个重要结论需要被认可和加以重视。
一是模仿和创造都是艺术有机组成部分。古希腊、罗马的智者们很清楚模仿的力量,“通过模仿伟大的人,学生不仅可以变得伟大,而且最终可以表现出上帝般的特征”[15]86。模仿优秀的作品,帮助学生明白什么是优秀,并通过模仿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模仿不是成为别人的影子,而是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像亚里士多德模仿了柏拉图,但亚里士德在很多思想上是大大不同于柏拉图了。这恐怕要得益于古希腊的小班授课或理想的一对一教学模式,师生间开始自由、平等和开放的对话,相互辩驳,相互促进。如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大师和学徒之间的问答模式,在柏拉图的《费德鲁斯篇》,西塞罗的《演说家》和《发明篇》等较为常见。这种教学模式是从模仿起步,通过对话促进教学相长,促进和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反观中国春秋时期的师徒教学的语录体模式,古希腊时代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模式对创造力培养的路径值得我们借鉴。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模仿物要低于模仿对象(理念)。亚里士多德承认模仿是本能,但却不认为模仿者一定要比模仿对象低,模仿作为“一种经过精心组织的、以表现人物的行动为中心的活动……艺术模仿(或表现)不仅可以,而且应该高于生活”[9]213。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重心也从模仿对象走向了模仿行为,比如他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9]20。在对模仿行动的分析中,他超越了柏拉图的对话体写作,开创了书面的分析式写作形态(叙事学也由此诞生)。更重要的是,他开创的书面戏剧写作被今天的创意写作研究者认为是创意写作的起源:“创意写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这主要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对多年来接受和使用的创意实践的描述。当然,该书仅仅收集了他用于学习知识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告诉他的学生在诗剧创作中应该寻求什么和避开什么,这些戏剧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目标的实现如何支配戏剧的形式?这个目标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剧作家可能由于什么缺陷而未能实现它。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却走得更远,因为它有一个道德目标,而创意写作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个目标。”[2]20
二是模仿出于实用需要,而非是脱离现实的游戏。古希腊的模仿是服从演讲的现实需要。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爱智风气激发了演讲的传统,演讲和修辞的艺术成为贵族青年们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追随老师学习不是在固定的教室里和书桌上,而是多在户外,在广场上,在宫廷中,在各种公开的演讲和辩论场合。为拥有优秀的口才和辩才,他们不得不模仿卓越的大师和优秀的老师,背诵他们的演讲词,模仿他们的演讲技巧,学习他们的演讲风格,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在现实的演讲中脱颖而出。这个功利目的促使他们更多模仿当代的演讲家、修辞学家,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反之,古典学在文艺复兴之后走向衰落的一种重要因素就是因教育结构与模式的变化,学生不得不坐在教室里,机械生硬地模仿古代作家和作品,和现实的文艺创作、现实生活完全脱节而失去生机和活力,成为干瘪的知识学。也就是说,古典修辞学和语文学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模仿不能脱离模仿者的现实生活和现实需要,修辞学和语文学要重新“活”起来,古为今用。有了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提倡创意写作,并不是要简单否定修辞学学习和传统的作文教学,传统的作文教学和修辞学习为创意写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模仿学习上它们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创意写作的模仿是活态教学法,学习者应该走出“阁楼上的象牙塔”,走向社区,走进各种日常生活场景,开展模仿活动。
自然,古希腊罗马的先哲们关于模仿理论和模仿教学的思想和方法是创意写作宝贵的遗产,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深入,我们一定会有更多新奇的发现。模仿说和模仿方法论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理论场域,作为研究者,在追逐创意写作这个新的学科时,目光何妨向悠远的历史深处打探,借历史之光照亮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