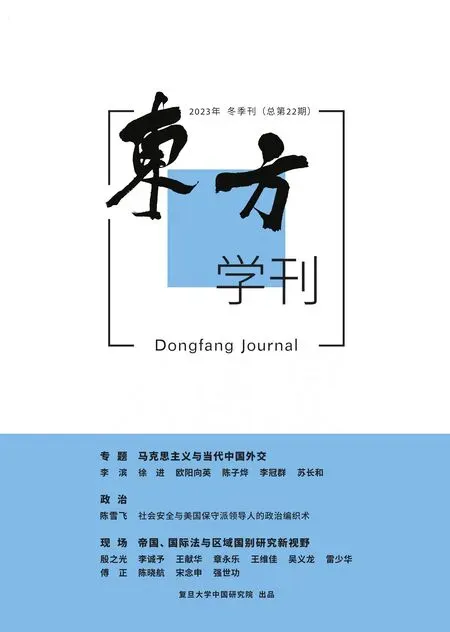国际社会的性质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革
2023-04-17苏长和
苏长和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摆在世界很多国家以及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国际秩序演变的加速乃至发生突然性的急剧变革,全世界学界—自然且必然也包括中国学界—为此做好了什么样的理论准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先进国家在被推到历史潮头的时候,理论界抱残守缺、后觉后行而错失良机的有之;同样,理论界因为先知先觉先行、引领时代风骚的也有之。现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热议的话题。于内,自主知识体系有筑牢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共同思想根基的意义;于外,自主知识体系要面向世界,在人类社会和秩序演进中,中国的知识有何贡献?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大命题中,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如何一跃而升为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理论,这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都是极大的机遇。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应该对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现状有个基本评估。这些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由于长期学术惯性,不少论著还是在英美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下打转,其使用的概念和理论基本还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那一套。在不少高校的国际关系教学中,这一套还是比较流行的。二是围绕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自主学术创新活动,出现一些以本土标识性概念为代表且具有解释其他地区能力的理论流派,如天下、关系、共生、文明型国家等,在国际学术界开始受到越来越多重视。三是全球治理议题、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家安全、国际战略研究的作品很多,这类研究主要还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利,比较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介入得还不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类研究成果的广度,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对国际社会性质和形态的宏观把握以及国际关系历史观的指导,这类研究策论成果虽多但其理论深度受到了制约。四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研究,涉及“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观、全球伙伴关系、中国的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变迁等。
以上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的概括也许并不全面。这其中,关于国际关系理论自主、自觉的创新意识是从1990 年代至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支重要力量、先进力量。类似“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提法及其学术自觉和创造历程,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满,这使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识,要早于、先于国内其他门类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界也是一支独特的力量。之所以如此,部分缘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学者背靠着坚实的国家制度从而拥有独立思考的底气。在学界认识结构上,关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和肯定,也正在从为了得到西方学界承认、迎合英美主办的英语刊物的选题审题习惯的受动规训认识阶段,发展到自我主张、自我设置议程的认识阶段,尤其表现为中国原创标识性概念开始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使用和扩散,显示出较强劲的学术能动创造的趋势。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下的国际社会性质
这种学术自我主张的能动现象,初期的表现是零星的、分散的、不成组织的。然而,要从零星的、分散的、多元无序的、不成组织的学术创造阶段,发展到系统的、整合的、有组织的创造性爆发过程,必然要将这一学术自觉运动转化和上升到聚焦于对研究对象根本性质的认识和讨论上,由此才能纲举目张、自成一体。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方法,对世界的本质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历史和逻辑的抽象,由此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
在关于世界的认识上,过去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英美国际关系理论,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理论,将世界(借用“国际社会”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视为无政府,这个假设在现实主义理论那里,自然推出丛林世界、现实主义以及强权政治合理性那一套学说;而在自由主义理论(某种意义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那里,又自然推出所谓“自由”国家可以干涉“非自由”国家,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对弱小国家霸权和专制的结果。在英国“国际社会”学派那里,将国际社会分为有序和混乱无政府的世界两部分,“国际社会”的进步和扩大,是以后者接受前者的规范和规训来实现的。英国学派的这种认识,同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的华夷秩序观并无多大区别,是现代的西夷秩序而已。直到今天,在英语媒体和学术著作中,当它们说“国际社会”的时候,这个以普遍形式表现出来的概念,实际上主要是指集体西方的特殊概念。
我们恰恰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理论还没有抓住国际社会性质的根本,它们很大意义上是在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捍卫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由此,我们需要就国际社会的历史和逻辑进行剖析。关于国际社会性质的抽象,需要更多地从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推理而得。英美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新自由主义法权理论和国际秩序理论,其基础还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社会”这些概念,回避了进入世界市场时代的国际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阶段这一本质特征。这一特征的揭示,是从社会科学最伟大的作品—《资本论》中经过科学推理而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从国家出发分析世界的,也不是将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简单地划分为两种政治。它是从生产及其属性以及一套生产关系被制度化来分析的,这个在国内造成阶级矛盾,因而需要建立新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国内探讨的主题;而在世界范围,其所揭示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给国际社会各国各民族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制度性压迫,由此产生对这套不公正体系正义的反抗和抵抗直至解放的过程。
这样,我们就看到,所谓的现代世界,或者国际社会,从其一开始形成的时候,既不是用无政府属性可以刻画的,也不能简单地以各个政治单位(后来表现为主权国家)的简单相加来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扩大,使得民族及各国来往从区域扩大到全球,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背后以及之上,形成了世界制度体系,将世界牢牢地锁定为一种控制和从属的结构;在国家之上,愈来愈形成了一套将控制和从属结构予以制度化的法权体系,在过去表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在当代则表现为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这是现代世界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和逻辑,也是我们对国际社会性质进行定义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里定义国际社会的性质还不够。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这种将不平等、从属关系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并不是进步的,它日益制造出否定的正动力量,就是更多民族和地区觉醒以后,努力从这种奴役、殖民、不公正的体系中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解放出来。在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历史中,表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和进步运动。这一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也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关系的自由和民主进步。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它们将制度化的不平等塑造为自由和民主的扩大过程(理论措辞表现几波“民主化”“自由世界”等),但是换一个方面看,过去以来推进世界民主和自由进步的不是集体西方恩赐的,而是由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新兴经济体发展争取而来的。这正是我们讨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动力和逻辑起点。回到这个历史动力和逻辑起点上,我们才能对当今世界的功过、善恶、是非有一个正确的政治判断和理论判断。
三、国际社会运动和进步中的正反力量
关于国际社会性质的认识非常值得学界深入的讨论。这一对国际关系理论根本问题的认识的深刻程度决定了理论的形态、品格和力量,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实践方向。如果在上一视角下定义国际社会的性质,才能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在世界历史及其逻辑发展的阶段上予以更新的认识。在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世纪之问中,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正确一边,以及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至高道义所在。在今日世界的外交话语修辞和辩论中,美西方好用“站在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来压制中国等新兴国际政治力量,而中国外交话语也使用“站在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莫衷一是,但实质很清楚—谁是真正代表世界历史以及国际社会进步的力量?显然不是竭力维持和巩固对大多数民族和国家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那一方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变革中,需要批判和突破英美特色国际政治理论所谓国际社会“无政府”“权力政治”假设的重要意义所在。它使我们直接面对国际社会的本质属性来认识现代及当代世界变革的本源力量,而不是纠缠在无政府属性、“自由世界”、“现代国家 — 前现代国家”这些表象的讨论之中。资本主义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叙事是用“无政府”假设来偷换“不公平不公正”这个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国际社会性质的核心问题,将世道中的功过、正反、是非、黑白、善恶搞颠倒了。这些理论叙事关于自由、民主、非自由世界、专制世界的划分是观念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话语讲是唯心主义的),这套话语将其历史上野蛮的殖民掠夺行为美化为“文明”,将本是对抗式的制度塑造为民主制度并在世界推广,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刻画为中国“威权”挑战西方“民主”,将全球南方追求独立发展的解放力量看作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将改革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进步运动说成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而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将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矛盾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扩张对各国内部及其国际关系发展以及各民族追求自由、独立、解放,直至全人类解放的障碍和阻力。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当今世界矛盾和竞争的根子所在,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种族、民族、经济、国际秩序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深刻认识到代表旧国际秩序的力量为何以及如何竭尽所能压制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国际秩序、人类解放的进步力量的原因在哪里。
四、新型的国际政治文明和新国际关系理论的品格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力量并不仅仅告诉我们一个国内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和规律,它的引申意义还在于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和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21 世纪的世界性问题。世界生产的发展,在其历史最初形态上造就出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社会并不是完美的,其社会形态一度表现为殖民主义宗主体系、资本主义世界制度体系以及世界性的发展与落后、霸权与奴役、帝国的中心秩序与边缘的动荡混乱二元秩序状态。然而历史的演变即便曲折,但终究跳不出逻辑的规律。在其逻辑规律上,国际社会终将向世界社会、全球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发展。世界上各国、各民族、各方力量的觉醒以及这类进步力量的汇聚,从而追求从不公正的旧国际社会秩序中获得政治和经济解放的历程。
我们站在这一历史和理论的高度,才能舍象而穷理,俯视、审视当今世界变局的阶段性意义及其确定的发展方向所在,确保政治定力和理论定力。也只有从这一历史和逻辑运动中,才能真正在学理上讲清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重大学术和政治意义所在。如果不通过历史和逻辑主线知识将世界本质变化及其各类进步因素汇聚起来,形成我们所谓的新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我们关于中国崛起的历史正当性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变革、“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各类世界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学理解说,就只会停留乃至被淹没在分散的、无序的、支离破碎的、不成体系的、缺乏自觉的、没有方向的,甚至有点徒劳无力的知识创造之中。而当我们按照历史和逻辑的主线知识来作用于我们的知识创造的时候,这样的知识创造就从自觉变成自为、自由的过程,人们就容易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倡议和行为,以及世界上各方进步的倡议和行为,从代表着新型国际政治文明发展方向来予以定义和阐释。它并不是今天世界上“去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国际关系”概念,即简单地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成果机械相加,而是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揭示其向文明的秩序演变的道理和方向。这就是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变革的焦点所在。
因而,关于国际社会性质的重新认识,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全球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化,以及可能的进一步讨论,目的在于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视角下,赋予国际关系这门学问以历史和逻辑法则的意义。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首要在于将政治的第一原则立起来,从而站立于人类道义的高点,进而在秩序变革到来之际,按照进步的世界历史观,为人类贡献更多有价值的政治方案。这也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