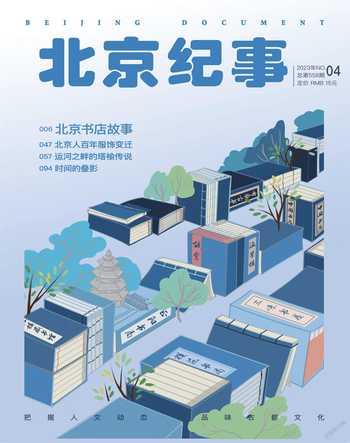半个世纪买书记
2023-04-17元尚
元尚

北京书市由来已久
北京有书市,据记载最早出现在明朝,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即记载了明代北京书市,又记录了书市所在的位置。“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今毛主席纪念堂西)。每会试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也即大明门附近、考市、灯市、庙市。”大凡在北京的图书市场,主要集中在大明门右边礼部大门之外,今天的位置大体上在毛主席纪念堂的西面的位置上,明朝每年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瀚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焉。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日常百货都集中于这几个地方,书市则是其中的一项营生。
著名古旧书学者孙殿起著有《琉璃厂小志》,其中说:“清初书市,移于城南广安门内慈仁寺,今名报国寺。《香祖笔记》云‘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云集,慈仁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此即城南书有市之始。所称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则货源渐稀,秘本难得,可知慈仁寺书市在彼时已步入衰落之境矣。”由此可见北京的书店其源头来自按时节举办的市集中,古代北京的书市主要来自各地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他们是书的来源之一。其次是古代官员大多学而优则仕,从考试而来,其家中书籍众多。一边求书,一边有闲书在家,于是市场兴焉。
当代书市盛况不衰
当代北京书市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书籍开始再版,将近十年的读书饥渴期过去之后,释放出来的读书欲望,用空前盛大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人们坐公交读书,上班读书,礼拜天在家读书,甚至走路时候也读书。一部书再版出来一上市,一抢而光,须知那时的图书印数都是以万计,就是这样买不着的时候都多。
我那时还在学徒,买书的信息是去厂图书馆的“社科图书出版目录”中去找,把书名记在一个小本本上,然后休息天去书店买。那时候我住在北京站口,离王府井新华书店很近,步行约十分钟,就是这样查到的已经出版之书,连续去好几次,才能买到其中之一二。年轻时看书很快,一般的书上班赶上一天没活,差不过就看完了。比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莫泊桑的《俊友》都是一天就看完了。我所在的车间是服务性质的,一线车间不出问题,可能一个月不用干活。当然最好别有事,我们工厂是高温高压的化工厂,不能出问题。书看得快,就总有不解渴的感觉。然而买书那叫一个难。等人去了书店,书卖完了的时候太多了。整个北京的读书人都说买书难。好像记得当时报纸上也呼吁过应该解决这个大难题。
1980年北京市为了解决买书难问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首次新书书市(记忆中这之前没有大规模的书市)。书市云集了各地出版社新书。去书市的那天,真是人山人海,整个文化宫从进门处到大殿前的空场,摆满了书摊挤满了人。围着书摊的买书人里三层外三层。买书跟抢书一样。那时候在书市,真的无法淘书,只要看见有自己想要的,立马交钱拿走。总想多买几本,书市结束后能足足看俩月才好。可惜学徒一个月十几块,买书的钱的确很有限。80年代书市买的都是文学名著。这次的书市留给我的印象是,书几乎上来就没,很少见有人拿着书翻检。
古旧书与时俱进
与首次新书市同时,记得中国书店办了一个旧书书市,在海王屯里面。当时上面还没有封顶,书摊摆在院子里。中间从南到北一溜,东西两侧各有一溜。北面小楼1970年代时是机关服务部,一般读者进不去,要单位介绍信。书市时也开放了随便进。买旧书的人那时也很多,很多珍贵旧书,也很便宜,可惜的是我当年是一个铁杆“文青”,一心只想文学,尤其只追长篇外国古典文学译著,其他旧书再有价值也看不见。一毛钱买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三毛钱买下奥斯托洛夫斯基《来得容易去得快》,五毛五买下他的另一部剧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足足比在文化宫书市得到的书多。
在琉璃厂古旧书市上淘书,一直以来从没有间断过,从1980年开始,直到2000年前后,旧书书市并入北京书市整体市场之后,也总是首先去看旧书,其次才看新书。在旧书书市还真真的淘到不少很有价值的老书。比如:1949年俄文原版普希金文选,俄文我是一点也不认识的,不过对普希金的像还是印象深刻的,这书里有我特别喜欢的原文《叶甫根尼·奥涅金》,这首长诗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一直到现在五十来年过去,还记着他哪。我总想如果能有一册原版书入藏多好,没想到竟然在书市如愿以偿了。书还真就不贵,才五元钱。
书市兴起惠及京城读书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书市都在文化宫举办,后来一年两次,一次春季书市,大约在4到5月间,一次秋季书市大约在9月间。旧书书市与新书书市同期,地点还是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读书热在八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每次书市,人们都是大包小包的装书回家。我是每次书市必到,八十年代前期我出徒后调去厂业务部门跑外,不坐班。看书买书两不误。当时跑业务是按照计划去买设备。一年也有不了几个计划单。所以只要有书市,天天去。不仅春秋两场书市必去,那段时间里东单体育场也有过书市,在那儿买到了中华书局的清代著名学者何义门的《义门读书记》,清代学者于鬯的《香草校书》。后来迷朴学就和收获这两部书直接有关。记得动物园对面停车场也有过书市,在那里买的书最多,因为太远不能天天去,所以一次豁出去买的书装满两个帆布旅行包外加一个大挎包。打了一“面的”回来,太沉了。和我一样北京有很大一批人,每逢书市必到的。冯先生和我三十几年的老文友,最真诚的爱书人,金先生也是迷书迷得不得了,1990年代每次书市他投入买书的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藏书家谢其章也是从不落空,每次在书市碰上他,聊几句,都能让人得到很大受益。这样的熟人还有很多,书市把人们聚在了一起,后来每次去书市,买书都变成次要的了,主要目的在于谁谁可能在里面,又有好久没见,赶紧去准会碰上。跟冯先生几乎每次书市都能碰上,我们从来没有事先约过,然而在书市总会碰上。1990年代我开始做自由撰稿人,逛书市就成了我一年中两次盛大的节日,书市期间不写稿,此时只为书疯狂。
大约是2000年以后,书市搬到了地坛,场地大了,规模也更大了。每次去真得一天时间。所有的爱书人读书人,又在那里聚齐。地坛书市這个时期,买的哲学书最多。它为我退休后专心读哲学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地坛之后,书市转到朝阳公园,这个时期打折书最多。不过每次去,买的书却远远不如从前多了。如今已经不是买书难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