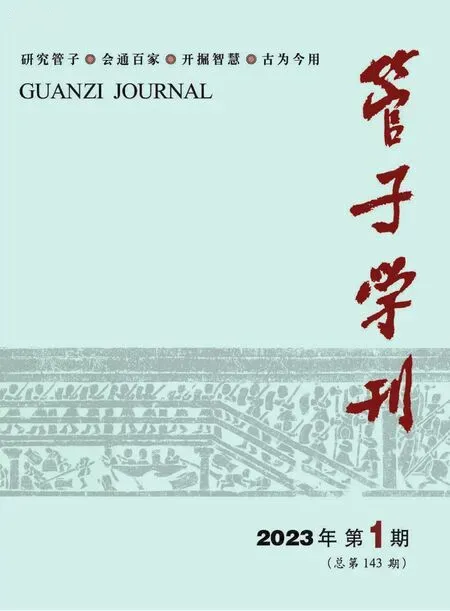“真知”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
——认识论视角下的庄子“知”论解读
2023-04-15何晓
何 晓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般认为,庄子的“知”论与其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境界论问题。如李耀南教授指出:“庄子尽管触及到了认识论的深层问题,但其本意或恐不在探讨认识问题,更不在建立认识论体系(这和《墨经》有关‘知’的客观分析以及对于认识问题的自觉探究有别),而是在追寻有限人生的无限自由时涉及到‘知’,也就是说,庄子的‘知’论是从属于他的人生哲学和整个理论体系的。”(1)李耀南:《庄子“知”论析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30页。这也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从境界论的角度出发,《庄子》中的“知”(知识)被分为两种:“俗知”(2)《庄子》中并无“俗知”一词。“俗知”即世俗之知,是与“真知”相对的、普通意义上的“知”。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使用“俗知”这个说法。与“真知”。多数研究者认为,“俗知”与“真知”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验性的知识,后者是一种形上之思。或者说,两者的认识对象不同:“俗知”的认识对象是形而下的“物”,而“真知”的认识对象是形而上之“道”。因此,也有学者将“俗知”与“真知”称为“极物之知”与“体道之知”(3)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02页。。
本文对庄子“知”论的解读视角则是认识论的。在《庄子》中,“知”的本义是“认识”,大多数用作动词。而作为名词的“知”,不仅可以指认识内容,即“知识”;还可以指“认识活动”本身。而且,《庄子》中关于“真知”的论述只有一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4)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6页。这就为我们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果我们把“真知”中的“知”理解为“认识活动”本身,就会发现,庄子提出“真知”的观念,不是为了彰显某种“体道”的境界,而是为了回答“认识活动之本质”的问题。
一、“俗知”的困境:认识何以可能
既然我们把“知”定义为“认识活动”本身,那么这里要讨论的“俗知”就不同于上文所说的“经验性的知识”,而是指这样一种观点:“认识活动”是“主体—客体”架构下的某种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即是有着“俗知”的人。庄子认为这种理解“知”的方式存在着问题。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24-225页。
庄子指出,人通过认识活动,可以知道哪些是属于天然的,哪些是属于人为的。我们可以使用自己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来达到“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的目的。不过,这种认识活动却存在一个隐患,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认识”,是“有所待而后当”的,而“所待”的东西又是变化不定的。因此庄子就提出疑问:我们如何保证被认识对象的确定性?“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认为的“人为的”不是“天然的”,而认为的“天然的”不是“人为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保证,那么也就谈不上使用这些知识了。
庄子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他笔锋一转,谈论起了“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并非庄子不知道答案,而是不需要回答。因为上述问题不是疑问句,是反问句。庄子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把“知”理解为“主体—客体”架构下的某种活动(即“俗知”),那么就会陷入“无法保证被认识对象的确定性”的困境。在西方哲学中,这种困境被称作“认识论困境”。所谓“认识论困境”,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内在意识如何可能确证外在实在?这是从存在论角度来说的。另外一句就是:内在意识如何可能通达外在实在?这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的。”(6)黄玉顺:《生活与爱——生活儒学简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3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认识论困境”?庄子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有所待”。所谓“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待”,成玄英解释为“对境”(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1页。,也就是“主客对待之境”。庄子指出,“俗知”的观点是,“认识活动”是在主客对待之境下形成的。因此,“有所待”就是造成“认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
为了纠正“俗知”的看法,庄子提出了“无所待”的观念。何为“无所待”?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6-17页。
庄子指出,超越内外之分、荣辱之境的宋荣子是“有所待”的,“御风而行”的列子也是“有所待”,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至人、神人、圣人”才是“无所待”的。徐复观先生解释说:
“乘天地之正”,郭象以为“即是顺万物之性”,即前面所提到的“观化”。“御六气之辩”,郭象以为“即是游变化之途”,即前面所提到的“物化”。人所以不能顺万物之性,主要是来自物我之对立;在物我对立中,人情总是以自己作衡量万物的标准,因而发生是非好恶之情,给万物以有形无形的干扰,自己也会同时感到处处受到外物的牵挂、滞碍。有自我的封界,才会形成我与物的对立;自我的封界取消了(“无己”),则我与物冥,自然取消了以我为主的衡量标准,而觉得我以外之物的活动,都是顺其性之自然,都是天地之正,而无庸我有是非好恶于其间,这便能乘天地之正了。(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逍遥游》讲的是境界问题,徐复观先生的阐发也是着重于人之境界的提升。其中对“无所待”的解读,与庄子认识论中的“无所待”是相同的,都是指超越物我对立,或者说消解物我对立。既然“有所待”是造成“认识论困境”的根源,那么超越“有所待”,回归“无所待”,则是解决“认识论困境”的方法。
当然,“超越—回归”是境界论的说法,对于认识论来说,我们的认识活动是实际存在的事情,所以不论我们如何去理解认识活动,都不会对认识的结果(即“知识”)产生影响。比如,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认识活动是一种主客二分下的活动”,我们通过认识活动而获得的知识(比如对桌子的知识)并不会因此而变化。所以,这里不存在“超越”的问题。只是说,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去理解认识活动的时候,会造成不可克服的逻辑困境,所以我们要改变对认识活动的认知,以消除“认识论困境”。庄子对于“俗知”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克服“认识论困境”,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而庄子使用的方法,就是揭示认识活动的本真面目,即提出“真知”论。
“真知”论的内容,就是认为“认识活动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俗知”是把认识活动放在一个“主客对待之境”中去理解的,而庄子认为,“主客对待之境”并不是认识活动的实情。“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都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换言之,“人”与“物”本身就不是二分的,而是“浑沌”的。庄子用了一个“浑沌”的寓言来描述发生认识活动的本真情境: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309页。
“人”与“物”的本真状态就是这种“浑沌”,既没有认识主体,也没有被认识的客体。直到我们去分析(“凿”)这个本真情境时,一切才开始分化。认识主体生成了,被认识的客体也生成了,但此时的“浑沌”却也死掉了。因此,庄子指出,在主客对待的视域下去理解认识活动,所见到的已经是“死掉”的认识活动,而非认识活动的本真面目。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主客对待的思维模式呢?庄子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之主体意识。要言之,“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出现,都是源自人之主体意识的觉醒。进一步分析“浑沌”的寓言,我们可以发现,“倏”与“忽”并不是有意谋害“浑沌”,而是“谋报浑沌之德”。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凿”“浑沌”,是因为他们发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视听食息”四者,正是人之主体意识的象征。因此,认识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
庄子的“真知”论揭示了认识活动的本真面目,指出认识活动并非主体去认识客体,而是在混沌之境中的领悟。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认识论困境”。那么,庄子为什么把前主体性的认识活动称之为“真知”呢?
二、“真知”:前主体性的认识活动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重点在于如何理解“真”字上。关于“真”的本义,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仙人说”。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真”的解释为:“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段玉裁注曰:“此真之本义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页。许慎认为,“真”指的是仙人羽化登天,这种用法在道教中可以经常见到。比如在《逍遥游》中御风而行的列子,被道家称为“冲虚真人”,而庄子自己也被奉为“南华真人”等。
第二种是“讹写说”。王夫之在《说文广义》中写道:“真,《说文》据会意而言,为仙人化形登天之名,乃古今文字皆用为‘真伪’字。仙人登天,妄也,何得云真!‘贞伪’字自当作贞。贞、真相近,传写差讹,遂有‘真’字。方士假为之说,汉人附会之耳。《六经》《语》《孟》无真字。贞,正也,卜筮者所正,得之爻体也。故为正、为实、为诚、为常、为不妄,而与虚伪相对。考文者废真字可矣。”(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九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29页。
王夫之认为,本来不存在“真”这个字,是后世传抄文献的时候,将“贞”讹写,遂生造出了“真”字。船山之说并非毫无道理。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甲、乙、丙三种版本的《老子》。其中,与传世本《老子》作“质真若渝”不同,乙组《老子》写的是“贞”(13)丁四新:《郭店楚竹简〈老子〉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第三种是“倒人说”。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通过识别金文,认为“真”是“殄”字的古字。他还提出一条音韵学的证据:“真在真部,殄在谆部,真谆音相近。《诗经·小宛》‘哀我填寡’,毛传:填,尽也。陈奂、胡承珙等均谓填读为殄,是其例也。”(14)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而“殄”的本义是“倒下的人”,所以“真”的本义也是“倒下的人”。持相同看法的还有日本汉学家白川静,他也认为“真”的本义是“倒下的人”,并且进一步解释说,“真”之所以有真诚、真正之义,是因为古人相信死后的世界才是永恒的、真正的存在(15)[日]白川静著,苏冰译:《常用字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那么,庄子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真”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庄子》文本中的例子来进行分析。《大宗师》中记载了一个寓言: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16)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64-266页。
孟子反与子琴张将子桑户的死亡称之为“反其真”。在这里庄子为什么把“死亡”称之为“真”?结合上文对“真”字本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庄子所谓的“真”不是“登仙”之义。原因有两点,第一,道教所谓的“登仙”,追求的乃是永生,而非死亡。死亡恰恰是道教所要逃避的事情。第二,“登仙”是通过某种修行而获得的状态,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这也与死亡不同。其次,“真”也并非“贞”的讹写。如果把“真”理解为“贞”的讹写,而“贞”的本义又是“正”,那么“反其真”就是“反回到‘正’的状态”,语意难以疏通。
其实,庄子是在“倒下的人”的意义上使用“真”字的。如果我们以“倒下的人”去解读“真”,那么“反其真”就是“人返回了倒下的状态”。人死了,就是人倒下了,这是一种再形象不过的表述。因此,庄子所谓的“真”即是指“倒下的人”。
另外,从构词法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庄子讲:“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在这里,庄子把“真”与“伪”对称。何为“伪”?伪者,人为也。既然“伪”是人为,那么“真”就是“非人为”。与此类似的还有“假”。“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郭象注曰:“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1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3、241-242页。在这里,庄子将“真”与“假”对称。何为“假”?《说文解字》对“假”的解释是:“假,非真也,从人,叚声。”(1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374页。后面的“叚”是表音的,唯一能够表意的就是作为偏旁部首的“人”。“假”的意象就是一个“挺立的人”,那么作为“非假”的“真”就应该是一个“倒下的人”。
那么,庄子的“真知”为什么就是“前主体性的认识活动”?因为从“倒人”出发,“真”字的含义可以引申为“主体性的消解”。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作为主体的“人”倒下了,人的主体性也就随之消解了,回到了前主体性的状态。庄子在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个引申义。如在另外一处关于“反其真”的用法中,庄子说: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1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90-591页。
牛和马生来就有四只脚,这叫作天然。给马套上辔头,给牛穿上缰绳,这是人为。去除人为,复归天然,这就是“反其真”。“人为”显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反其真”就是回到人的主体性尚未挺立的状态。所以说,庄子所谓的“真知”就是指前主体性的认识活动。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不知”或者说“无知”的问题。为什么庄子将“真知”解释为“不知”或者“无知”呢?从境界论的角度来说,“真知”不同于“俗知”,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所以是“不知”。比如刘笑敢教授指出:“庄子所谓真知即体道之知,即对道的直观体认,但体道必须摒除一般的知觉思虑,所以真知对于常识来说实为无所知,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不知’。”(20)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但是,从本文所说的认识论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不知”是对处在“浑沌”境界中的“真人”而言的。
庄子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知”是与“真人”密切相关的。而庄子谈到“真人”时,一般会冠以“古之”二字。比如:“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21)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26-229页。这是因为,庄子认为,上古之人,就是“真人”的原型,而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无知”: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2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334-336页。
庄子所谓的“至德之世”就是上古之世,因为每当他提到“至德之世”,总是以上古圣王为例,比如“赫胥氏之时”“神农之世”(2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341、995页。等。在上古之世的人,都是“无知”的。但是这里的“无知”并非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物我之分。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2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4页。
“真人”知识的最高形态,就是没有“物”的观念(“有以为未始有物者”)。既然没有“物”的观念,自然也没有“我”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真知”可以说是“无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俗知”与“真知”是两种对“认识之本质”的不同理解。所谓“俗知”,指的是我们通常意义上对“认识”的理解,认为“认识”是主客二分下的一种活动,这就造成了无法解释的“认识论困境”。“真知”则揭示了认识活动的本质,指出“认识”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不存在所谓的“认识主体”,也没有“被认识的客体”,从而消解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解决了“认识论困境”。
三、濠梁之辩:提出“真知”论的一个契机
庄子之所以提出“真知”,否定“俗知”,并非毫无来由。最有可能引发庄子思考“认识何以可能”,从而发现“认识论困境”的,应该是他与惠子之间那场有名的辩论,也就是所谓的“濠梁之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06-607页。
庄子与惠子辩论的本质,就是惠子提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就这个辩论而言,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辩论。理解这个辩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惠子所提出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安知”代表疑问。但问题在于,惠子的疑问是一个反问,还是一个真正的疑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冯耀明教授将之称为是“修辞性的问题”(rhetoric question)还是“真实性的问题”(real question)的区别(26)冯耀明:《鱼乐、真知与浑沌——濠梁之辩的逻辑分析》,《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57页。。如果是“修辞性的问题”(反问),那么惠子的意思就是“否定庄子能够知道鱼之乐”。如果是“真实性的问题”(疑问),那么惠子的意思就是“肯定庄子知道鱼之乐,而询问方式”。
我们来分析一下辩论的过程。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里并不能判定惠子问题的真实意图。然后,庄子回答说:“子非鱼,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不知”二字表明,庄子把惠子的问题理解成了一个反问。那么惠子的观点就变成了“非鱼则无缘相知耳”(2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07页。。如果把这个观点用现代白话文表述出来,那就是“‘我’无法认识‘非我’”。于是庄子就利用惠子的观点反问道:既然你主张“‘我’无法认识‘非我’”,那我(庄子)对于你(惠子)来说,同样是“非我”,你又是如何知道我的想法呢?对于庄子的这种反问,评论者基本持赞同的态度。比如成玄英疏曰:“惠子云子非鱼安知鱼乐者,足明惠子非庄子,而知庄子之不知鱼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问我,亦何妨我非鱼而知鱼,知鱼而叹鱼?”(2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08页。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逻辑推理。
对于庄子的反诘,惠子使用了类推的方式进行回应:“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惠子承认了他所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否定庄子能够知道鱼之乐”,否则,他应该就庄子对自己的误解进行澄清,而非顺着庄子的理解去回应。我们知道,庄子没有对惠子的回应做进一步的反驳,但并不代表惠子的逻辑是正确的。因为当惠子试图回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时,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即我知道你,并且惠子还给出了一种知道你的方法:类推。换言之,在庄子将惠子的问题定义为反问句时,就意味着惠子行为本身(判定作为“非我”的庄子不知鱼之乐)已经与其要坚持的观点(“我”不能认识“非我”)相违背的了,而惠子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帮了倒忙,甚至给出了一种“我”认识“非我”的方法(类推)。
不过,虽然惠子的回应有逻辑问题,但是庄子并没有抓住这一点反驳,而是回答说:“我知之濠上也。”一般认为,庄子的这种做法是诡辩。因为惠子的“安知”是“你是如何知道的”的意思,而庄子回答的“我知之濠上”则是回答“你在哪里知道的”这个问题。按照这种理解,辩论是以庄子的诡辩而结束。
按照上面的分析,这看上去是一场失败的辩论。因为惠子存在逻辑漏洞,但庄子却没有抓住逻辑漏洞进行反击,而是选择使用诙谐的辩论技巧来结束这场辩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庄子所谓的“我知之濠上也”,并不是简单地对“在哪里知道的”回应,而是对“认识何以可能”的回应。
很显然,不论将惠子问题理解为“修辞性的问题”,还是理解为“真实性的问题”,庄子都需要对“‘我’如何认识‘非我’”做出说明。只要庄子能够说明“我”是如何认识“非我”的,那么就既回答了“真实性的问题”,又证伪了“修辞性的问题”。但是庄子似乎没有这样做,至少没有正面回答。不过,为《庄子注》作疏的成玄英却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成玄英疏曰:“夫物性不同,水陆殊致,而达其理者体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鱼之适乐;鉴照群品,岂入水哉!”(2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08页。成玄英试图用“理”和“情”的范畴去解释“我”如何认识“非我”的问题,所谓“达其理者体其情”,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理”,自然也能体会到“情”。但是,这种回答并没有额外地说出什么,很难让惠子的支持者信服。
其实,庄子的确没有正面回答,但并非没有回答。通过前文我们对“俗知”的分析可知,惠子的问题就是在“俗知”视域下所产生的“认识论困境”。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言:“这里惠子所提出的,就是一个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30)陈鼓应:《庄子浅说》,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8页。惠子询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之所以能问出这个问题,其前提条件就是“子非鱼”。“子”是认识主体,“鱼”是被认识的客体。在主客二分的视域下去理解认识活动,必然会产生“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陷入“认识论困境”。
庄子没有正面回应“认识论困境”的问题,是因为他发现在惠子提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时候,其实蕴含着两个问题:其一,将认识活动视为一个主体认识客体的活动。其二,认识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能认识“非我”)。换言之,惠子没有把他的问题作为“认识论困境”(“认识何以可能”)看待,而是直接否定了认识的可能性。所以,庄子一开始与惠子的辩论,是针对惠子第二个问题的。在辩论的前半部分,庄子利用惠子的逻辑去反驳惠子,让他陷入逻辑悖论,从而使他承认认识活动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反驳在庄子说出“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时已经成功,只是惠子并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在惠子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的时候,庄子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反击,而是绕过了这个问题。
在已经论证“认识是可能的”之后,庄子就试图说明“认识是何以可能的”。所以庄子说“请循其本”,就是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庄子先是重申了一下之前辩论的结果:“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你知道“我(庄子)知道”这件事,已经证明了认识是可能的。然而怎么去解释这种可能呢?“我知之濠上也”,庄子没有大篇幅地说明惠子对于认识活动的理解有着主客二分的前提,而是向他展示了认识活动发生的本真情境。这就回到了辩论的开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在庄子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并没有将儵鱼作为被认识的对象而打量,而自己也并不是作为一个认识主体而存在。这就是认识活动发生的本真情境,而这种理解认识活动的观念,也就是“真知”。
结语
要言之,本文所解读的“真知”,并非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对于“认识活动之本质”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本文的视角是认识论的,而不是境界论的。认识论是知识层面的,而境界论则是实践层面的。庄子的“知”论是知识层面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认识活动”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其理解不同而有所改变。举例来说,我们以“俗知”的观点来理解“认识活动”,那么我们“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们以“真知”的观点来理解“认识活动”,同样还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而非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庄子所谓的“真知”与“俗知”的区别仅仅在于,持“俗知”观念的人认为“认识”是主客二分下的主体性活动,而持“真知”观点的人则认为“认识”是一种前主体的活动。庄子的“知”论是对“认识活动”的认识,即“认识之认识”。
那么,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如何理解“认识活动”并不能影响认识活动本身,那么庄子区分“真知”与“俗知”的意义在哪里?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其一是哲学的角度。哲学起源于“惊异”(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页。。既然“俗知”存在问题(“认识论困境”),那么对“俗知”的追问就是有意义的。比如,无论柏拉图是否提出“理念论”,物质世界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这并不妨碍柏拉图“理念论”提出的意义。其二是境界的角度。虽然本文是在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庄子的“知”论,但是如果从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论出发,认识论的问题也可以转化为境界论的问题。冯友兰先生曾经给“境界”下过一个定义:“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3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在这里,我们不必取冯友兰先生关于“境界”的严格定义,仿其大意即可说明问题。冯友兰先生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之不同,会使得人之境界也不同。同理,人对于“认识活动”的认识之不同,也会使得人之境界不同。在《庄子》文本中,以“俗知”去理解认识活动的常人,其境界是比较低的,而身在“浑沌”之境中的“真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其对认识活动的理解属于“真知”,所以境界是比较高的。庄子笔下的修道之人喜欢“坐忘”“心斋”等以“忘”为核心的工夫,其原因就在于想通过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33)至于这种方式是否达到了想要的效果,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参见张立文、何晓:《“真”与“独”:论〈庄子〉中两种不同的最高境界》,《周易研究》2022年第1期,第92-101页。。
总而言之,庄子的“真知”论意在解释“认识活动之本质”的问题,以说明“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避免了“俗知”所带来的“认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