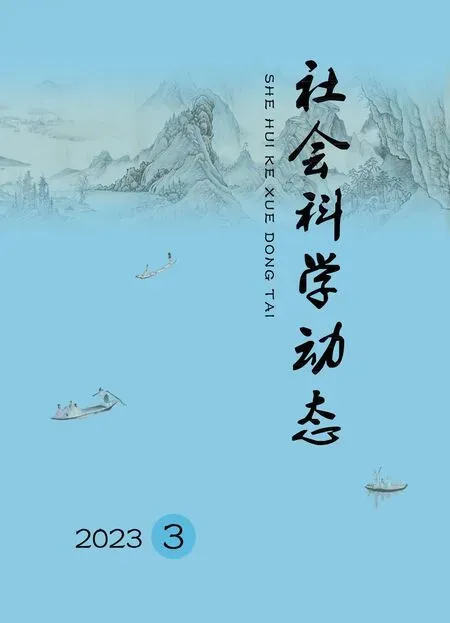从《汉志》到《隋志》:女教的形成与发展
2023-04-15郑植
郑 植
一、引言
《礼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①儒家自诞生之初就对教育怀有最高程度的重视,并在历史演进中建构出了一套以儒家精神为内核的教育体系。而受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观点的影响,长久以来对传统儒家教育的讨论总是习惯于将男性士人定义为唯一对象,而将女性排除在外。实际上这种惯见习知中的观点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儒家教育在封建社会中的辐射范围极为深广,女性同样是儒家教育矩阵中不可忽视的受众群体,只是儒家施予女性的教育较之男性而言,目的、层次、角度均有不同。
针对这一问题,学者高世瑜曾有过阐释:“中国自古便极为重视教育妇女,只是目的不在于让她们学习知识、开发智力,而是要让她们知晓礼法、妇道,成为最符合男权社会要求的贤女贞妇……由于这种观念,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发达的‘女教’、‘女学’。”②可见,儒家教育系统中,在“士教”之外还别有一套“女教”体系。所谓“女教”,即指依儒家性别伦理,如“三从四德”“内外有别”等,对古代女子进行的专门教育。女教的本质,实则是儒家性别观念与社会构想的另一种变体,它与士教是儒家教育体系的“花开两朵”“一喉二歌”,两者在封建社会中双轨并行、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单元。
与士教一样,女教同样有其漫长而曲折的形成发展过程,而其中,两汉到隋唐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点时段,许多学者都将其视为是古代女教的形成期以及第一次发展高潮③。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在《汉志》与《隋志》的儒家类对比中得到直观有力的印证——在子部儒家类,《隋志》较之《汉志》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出现成规模的女教典籍,即《女篇》《女鉴》《妇人训诫集》《娣姒训》《曹大家女诫》《贞顺志》6部女教专著。这一变化相当不同寻常,它引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为什么女教典籍在汉末至隋这一历史大动乱时期得以形成并取得井喷式发展?其二,《隋志》又为何特地给予新诞生的女教典籍以极大礼遇,直接将其郑重收录于子部第一的儒家类?——要知道,颇有声名的《颜氏家训》,在当时都未被《隋志》收录。
在《隋志·儒家》所收录的6部女教典籍中,《曹大家女诫》写于东汉殇、安年间,《娣姒训》作于西晋初年,《妇人训诫集》撰于刘宋时代,《女鉴》成书区间则大致在汉后梁前,而《女篇》《贞顺志》在现存文献记录中首见于《隋志》,其具体成书年代难以考证,一般认为是成于《汉志》之后、《隋志》之前。可见,在《隋志》所新著录的女教典籍当中,一部分创作于东汉中后期,另一部分则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这些研究在客观考据方面有着详实文献支撑,无可争辩,但在主观感知层面又似乎与我们惯常对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两个时代妇女处境的普遍认识有所悖逆。
东汉自章帝盛年而崩之后,女主临朝、外戚摄政成为无法撼动的定局,以至《后汉书》称“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④。魏晋南北朝则更是政治与礼教的双重大变革期,步障解围、新妇参军、风起柳絮等,都是这一时期妇女的典故美谈。而以禁锢女性人格为功用的女教读本,却偏偏在这两个时期落定形成并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这种矛盾悖论之下必然有其深层历史原因,这正是本文所要重点探究的问题。
二、女教形成:儒学发展的衍生
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儒家很早就将目光投向对女性训教的讨论。《仪礼》《孟子》等多部先秦儒典都对此有过论述,如“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⑤“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⑥等等。这些言论虽在社会中流传甚广,但大多还是作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陪衬,或对礼仪规范、社会风俗的单纯记录而存在,往往只是文中的只言片语,并非讨论的重点,更谈不上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或专著。
女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潜伏期”一直维持到了汉代,并在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中真正迎来了转机。“在汉代……女子教育亦进入一个定型时期。女子教育史上的许多重要观念和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出台;从女子教育的内容到形式,从女子人格塑造到行为范式设计,对后世女子教育的影响至深至巨。”⑦先秦萌芽化的女教,在汉代迎来了真正的发展定型,而在其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里程碑式节点:一是刘向《列女传》的诞生,二是班昭《女诫》的面世。学者陈东原曾这样评价:“二千年来关于女子生活的书籍,不仿《列女传》的体裁,便仿《女诫》的体裁,他们的影响,可想见了。”⑧后学但凡探究女教在汉代的形成发展,就无法绕开这两部典籍,而女教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分支变体,要对其发展定型形成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也势必需要将其置于汉代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中,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观照研究。
在汉代,董仲舒系统性地将阴阳五行学说注入到儒家政治哲学之中,极具创造性地将阴阳的概念与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有机结合。严格来说,董仲舒的著述,如《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都未见对女教问题的直接讨论,但他依旧在汉代女教产生及定型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春秋繁露》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⑨他从哲学的高度将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共同确立为“王道三纲”,并且巧妙地将阴阳五行学说融入其中,从神秘主义的角度神化夯实了所谓“王道三纲”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正式建构起汉代新儒学体系的核心骨架,并从理论层面实现了儒家对君臣关系的伦理化和对夫妻关系的严肃化。
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明确而强硬地确立了“阳尊阴卑”观念。“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⑩在这种绝对的“阳尊阴卑”观念统摄下,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严明的尊卑等级秩序,便自然而然地生成落定了——“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⑪。并且董仲舒在对“王道三纲”阴阳尊卑关系的合论之外,还为夫妇之伦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⑫。即男尊于女、女卑于男是恒定的,不随具体情境变化而改变。在董仲舒之前,儒家对“男尊女卑”的论述多是从礼法、举止等方面来规定男女之间的角色差异,相较于“男尊女卑”,更倾向于“男女有别”。董氏这一观点的提出,则彻底将男女、夫妻从本质上划分为贵贱两类,将女子无差别归入贱人之列,在古代社会中算是正式确立了绝对化的“男尊女卑”观念。
自新儒学与政治联姻,董仲舒的理论观念包括“王道三纲”与“男尊女卑”等,作为国家意志在思想领域和社会实践中推行,成为汉代儒学乃至整个后世儒学的底色基石,也为女教的产生起到重要的铺垫作用:夫妻之伦正式由一种受儒家关注的社会关系,一跃而成为与君臣、父子并列的封建社会最高伦理纲领之一,在理论建构层面得到内化和升华,成为儒家教化体系和封建统治秩序的核心之一。这种理论上的肯定和国家意志的规范,促使人们开始从儒家教化的高度来看待妇女问题,逐渐将女性训教作为一个亟待完善的新命题来展开系统化的研究。而“男尊女卑”观念的正式确立,则使得男性主体意识不断膨胀,对女性的训诫和管控欲望不断增强。在这前后两者的遇合之下,女教的形成便在酝酿之中了。
唐代刘知几曾云:“(向)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⑬此言虽系对刘向史学态度的质疑,但也揭示了刘向作“史”的特点。在《列女传》的写作中,刘向的确并不注重对历史真相的把握,有时甚至扭曲原本的历史情景,皆因其创作旨归不在记言记事,而是要完成一个儒学命题,即依据董仲舒所确立的儒家思想来建构起新的性别秩序。在《列女传》的构思与编排中,刘向以汉代新儒学的性别伦理为尺度,借用已有典籍或剪裁、或拼凑出一批具有女性教化意义的历史故事,赞颂严守儒家礼教的贤妃贞女,如“终不更二”的息君夫人、齐杞梁妻,鞭挞违背儒家礼教的女祸之人,如“牝鸡司晨”的殷纣妲己、周幽褒姒等,行文逻辑简洁严密,引导警示并行,试图以此建构完整的封建女性价值评判体系。其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的骨架搭建,可谓大体奠定了后世女教的结构基础和阐发原点。直至清代的女教言说,如李清的《女世说》依旧延续着这一价值准绳和体例模式。
东汉章帝时期,汉代儒学巨著《白虎通义》诞生,其对于女教的发展同样有重要意义。汉代儒学的基本架构和核心理念在西汉就已形成,东汉的博士儒生则主要负责对其进一步总结与阐释,以求将儒家理论构想与王朝政治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白虎通义》正是这一阶段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因此,相较于董仲舒性别思想的高度理论化,《白虎通义》中的论述显得更加详实细致,并展现出更强的现实指导性。
《白虎通义》曰:“妇人学事舅姑,不学事夫者,示妇与夫一体也。”⑭“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也。”⑮“有五不娶。乱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恶疾,丧妇长子,此不娶也。”⑯《白虎通义》在继续夯实“三纲”的基础上,对儒家性别理论进行了权威性梳理与总结。如“妇孝”“妻不去夫”“五不娶”等概念,都在《白虎通义》中得到细化和规范,成为具体的、可指导实践的法则。由此可见,儒家的女教思想在《白虎通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由顶层思想建构向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逐步下沉落实,而这一变化更是直接推动了严格意义上女教专著的出现。
班昭的《女诫》便深受《白虎通义》影响。《女诫》看似闺阁妇人“现身说法”的教女之书,但实则班昭出身累世儒门,结合其家学渊源与生平其他著述,不难发现撰写者有着深厚的儒家学养和典型的儒士人格。《女诫》在承继《白虎通义》“阳倡阴和,男行女随”⑰精神内核的同时,将后者的性别构想进一步具体化与实践化,不但直接将闺阁女性定义为传道对象,更首次将汉儒“夫妇之道,参配阴阳”⑱的性别理论融入日常生活情景,明确对妇女提出“持卑弱”“守敬慎”“专一心”等具体约束要求,还对如何“贞顺夫君”“曲从舅姑”“和睦叔妹”等实际问题进行指导说明,使得妇女在日常起居中更易把握和效仿,真正从现实生活的意义上起到了封建女教的作用,开创了儒家女教的又一经典范式,后世如宋氏姐妹的《女论语》等便深受此体例的影响。
从学术发展视角看,女教在汉代以《列女传》为发端,以《女诫》为标志,根本动力源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儒家的发展。可以说,西汉儒学通过大刀阔斧、开宗立派式的理论革新与体系建构,开辟出了儒学发展新命题,刘向对这一新命题展开探索并为之奠基,正式开启了女教体系化、专著化的进程。而东汉儒学通过引经据典、托古维今式的理论阐释与制度落实,强调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班昭将儒家性别理论规范化地落实到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意味着女教理论在封建社会的正式落成。简而言之,女教的形成并不是一条孤立的线索,它与两汉儒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整个汉代儒学发展新变的衍生成果。
三、加速契机:现实困境的反推
中国历史上女主临朝称制,即儒家所谓“牝鸡司晨”,发生最为频繁的便是两汉至隋时段。汉初便有吕后主政,她虽无皇帝名分却享有至尊实权,故司马迁为其特作本纪。其后,诸吕虽迅速凋敝,但皇室妇女参政甚至主政却作为一种传统被长久地保留了下来——窦氏、卫氏、霍氏、赵氏、王氏及诸多后妃公主轮番登上政治舞台,对西汉政治的格局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及至东汉,这种传统依旧得以延续,《东汉会要》中便有“母后称制”条目,可见太后摄政在东汉不仅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得到了制度承认。
在两汉历史中,许多女性当政者都为王朝的稳定和延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观念古已有之,自先秦以来士人群体针对女性参政主政的污蔑与抨击便从未断绝,这种偏见在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正式具备了系统化的理论依据,并由此愈演愈烈。在汉儒的理论建构中,两性的分工、角色、尊卑被固化为不可变易的法条,任何偏差或修改都会被视为是违背天命的大逆不道。女性参政的现象,无论其前因后果、功过是非,这一行为本身就天然对应着非法、颠倒、灾异等一切不祥的意象。由此,在两汉时期,女主临朝称制的既定现实与儒家的性别伦理、为政观念之间的巨大矛盾,成为当时儒士思想上不得不面对和纠结的一种现实困境。
在两汉儒士看来,这种“以妻制夫,以卑临尊”的乱局必须被纠正,大批儒士投身“匡扶正道”的政治运动。然而,主幼时艰的政治现实,母权孝道的名分优势,加上煊赫一时的外戚势力,都对并无实权的儒士文臣造成了巨大压力。这种进退两难的现实困境,决定着儒士群体很难从正面途径去改变这一格局,在反复探索与尝试之后,他们转而采取一种“扬长避短”的间接干预方式,即发挥汉儒“发愤著书”之传统——由政治直谏走向思想教化。在这一改革路径转型实践中,最为成功的大概就是刘向《列女传》与班昭《女诫》。如前所说,两部女教典籍的根本源流在于两汉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新变,但结合二者具体诞生背景来综合分析,即可发现,它们的诞生同样还有一个现实层面的契机。
先说刘向与《列女传》。刘向在政治上的起复始于成帝即位,《汉书》中称这一历史时期是“政由王氏出”⑲。出于儒生天然的使命感,也出于对成帝知遇之恩的感念,刘向自重新出仕起,便一直在为遏制女主摄政、重整阴阳乾坤而上下求索。成帝初年,刘向曾撰《洪范五行传论》以上奏成帝,此书将当时异常的天象时数归咎为王凤兄弟用事之过,以期利用舆论压制迫使王氏还政于帝。然而,虽然成帝深感刘向之忠精,但却最终未能撼动外戚摄政的局面。此后刘向还陆续多次上书,均以失败告终。经历了长期的探求辗转之后,刘向认为王凤等人本质上是因“倚太后”方得以“专国权”,仅以阴阳灾异警示外戚家族,并不能触及问题根本,要想真正扭转局面,破局之策当是对离统治中心最近的、以太后为代表的后妃宫嫔进行儒家的教化与训诫。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⑳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列女传》具体成书时间是在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㉑。这一年在西汉后期政治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成帝纪》中记录:“夏四月,封婕妤赵氏父临为成阳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㉒。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标志着外戚专权和后宫干政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刘向《列女传》在这一年“应运而生”,可以视作是儒生群体在现实困境倒逼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或“最后一搏”。
再看班昭与《女诫》。东汉立国之初,光武帝就因感叹前汉吕、霍、王、赵之恶果,而对宫中教化颇为重视。其后,孝明帝亦秉持此旨,在“登建嫔后”之事上“必先令德”,形成“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㉓的整肃局面。然自章帝盛年而崩、和帝以10岁之龄即位,原有政治格局便开始解体,太后摄政的循环又宿命般地回到东汉的历史进程中。“和帝以降,窦、邓、阎、梁等外戚家族相继专权,形成东汉中期百年外戚政治格局。”㉔班昭恰好生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并因其独特的际遇得以近距离目睹,甚至参与到和帝、殇帝、安帝三朝宫闱倾轧和政治斗争中。在班昭的主要活动年代,和熹邓太后无疑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位女性政治家扶持少帝、稳定时局的功绩曾得到过儒士的赞颂,但她在临朝称制之后所表现出的政治强势,却也引起了士人群体的激烈反对。司空周章曾在永初元年发动以“诛车骑将军邓骘兄弟”“废太后于南宫”㉕为目标的政变,事败后自杀,牵连者甚众。郎中杜根则在安帝年间与同僚联合上书,直谏太后应还政于帝,太后大怒,以至杜根等人不得不诈死逃窜。太后外戚与士人臣子的矛盾在一场场相互博弈中不断激化,攻讦与清洗频频发生,朝局由此更加动荡不安。
虽然班昭在《女诫》中始终以卑弱的执帚之人自居,但实际上她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缓和这一政治矛盾而不断努力。班昭在和帝年间就曾奉诏入宫为皇室妇女讲授道理,与邓氏尤为相厚,故邓太后临朝之后多向班昭问询政见。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丁母忧,按制应去职守孝,太后执意夺情不允,引发朝臣激议。班昭上疏谏太后曰:“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㉖班昭的劝诫最终奏效,将一场正在酝酿的政治风波化于无形,避免了矛盾继续激化与彻底爆发。结合班昭的家学源流和生平事迹,可知她有着非常典型的儒士心态,在重要事件发生时有着明确的参与意识和政治智慧,这从她上书和帝与直谏邓后等事迹中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和帝钦定的“大家”和续写《汉书》的史学家,对于轮番上演的外戚政治,班昭应该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和独特的思考,凝结其毕生经验思虑的《女诫》之中,除了饱含作为母亲的谆谆教诲之外,未尝没有她作为一位儒门史学家的隐秘思考与劝诫意味。
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主昏瞀和主幼时艰的政治窘境常常交替上演,加上胡汉交融后“先母后父”观念的渗入,导致太后临朝与妃后专制的现象较之两汉有增无减。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一方面,儒家“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㉗的观念根深蒂固,敦促儒生士人继续孜孜用志于对皇妃宫嫔们的教化训诫;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部分皇室妇女对国家政治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惠帝后贾氏之于西晋、宣武灵皇后胡氏之于北魏,莫不对 国家朝政和儒士群体造成 极大的伤害和震撼。于是,在“纲常伦理”与“前车之鉴”共同催化下,魏晋南北朝社会对于妇女德行教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实践动力急剧提升,女教文化也借此契机迎来自身繁荣发展。
由此可见,两汉至隋时期频繁出现的女主专权现象,与儒家壁垒分明的尊卑等级秩序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碰撞,现实的困境压力大大强化了士人群体对于女性教化的迫切度,并加速了女教在汉代的形成和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四、地位落定:重构秩序的需要
东汉桓灵之后,国家溃败,吏治混乱,中央宦官与外戚交替掌权、屡行废立,地方豪族武装割据、起义频发,政治上以臣弑君、父子相争之事屡见不鲜,是故《后汉书》以“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㉘来总结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儒家名教体系的维持亦是危如累卵,《后汉书》中如《符融传》《陈蕃传》等诸多篇章,都揭示了当时社会上“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㉙的荒诞现实。这种普遍的社会状况极大地消解了名教体系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以至民间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㉚的风谣。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在现实冲击下开始分崩离析,一方面为魏晋南北朝多元思想迸发打开方便之门,而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统治者留下秩序“重构”难题。
虽然魏、晋皆以刑名之术立国,南北朝各以兵家之道起家,但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秩序,每个朝代在时局稍定之后,统治者便将目光立即投向儒家体系,诸如祭孔庙、兴太学、修五经等政策举措,在各代都成为践祚之后的当务之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以“三纲”为核心,皇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互为拱卫,想重构现实治理中的儒家体系,势必难以脱离三对核心社会关系。若细究魏晋南北朝历代政治渊源,即可发现,魏与晋、南朝四国、北朝五代,本质上都属于以臣弑君的“不正得位”。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君为臣纲的“忠”观念,只能长期处于含混暧昧的失语状态。如此一来,重振“三纲”的重任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父为子纲”与“夫为妻纲”上,而这也使得魏晋南北朝对于“孝”和“节”的宣传、执行较之前代尤为执着与激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孝”观念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各代统治者在掌权之后都标榜本朝是“以孝治天下”。相较之下,魏晋南北朝社会对于节烈、贞顺的鼓励和追求却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节”与“孝”在儒家教化中是一对同根共生的“连体婴”,两者在同一历史情景下的境遇一般也都相似。东汉之后,频繁的朝代更迭和胡汉混战,使得原有的儒家伦理体系摇摇欲坠,“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的情况在社会基层成了普遍现象,而“贾氏窥帘韩掾少”的轶闻在上层贵族中也并非个例。这种“任情而动”的婚恋方式虽为魏晋南北朝的风流气象增色不少,但这种非传统的、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却绝非为急于重构本朝治理秩序的统治者们所乐见。《晋纪·总论》中记载:“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礼法刑政,于此大坏。”㉛每当社会遭遇危机,统治阶级为整饬社会风气、重构统治秩序,往往会将对两性关系的规范也纳入到国家政治议程之中,而在男尊女卑观念的统摄下,这种礼法规范最终又势必会落脚到对女性行为举止、道德品质的教化、训诫乃至禁锢上,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得尤为显著。
陈东原先生曾说:“世道越不好,贞烈越是提倡,诏旌门闾的事越是盛行。”㉜此言不虚。朝廷奖赏守贞及节烈妇女的事例,早在两汉时期就有零星记载,但这种奖赏真正形成官方化、规模化、体系化的表彰制度,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宋明帝在泰始元年(465)下诏曰:“巡方问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广求民瘼,……贞妇孝子,高行力田,详悉条奏。”㉝北魏孝明帝在正光四年(523)下诏曰:“宜诏百司各勤厥职,……若孝子顺孙、廉贞义节、才学超异、独行高时者,具以言上,朕将亲览,加以旌命。”㉞齐明帝在建武元年(494)诏令天下:“孝子从孙,义夫节妇,普加甄赐明扬。”㉟可见,在魏晋南北朝,为朝廷发掘可供奖励宣传的贞女典范,已成为各级官署重要政治任务之一,且成果直接上达天听,是以“朕将亲览,加以旌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由皇帝亲自下诏褒扬的贞女节妇不在少数,如受封“义姑”的陆郁生、赐号“贞女”的泾州兕先氏,等等。在国家政策的强力号召下,这一时期史册中关于官府下令表彰节妇贞女的记载可谓多如牛毛,且相较于两汉以“赐粟赠帛”为主的物质奖励,魏晋南北朝显然更偏重于“旌表门闾”的精神表彰,这更加凸显出官方表彰行为的教化意味。㊱
与孝经学因“以孝治天下”的国策而大兴同理,在官方意志的推动下,“思想引导”作为与“奖励诱惑”双管齐下的教化手段,自然而然地迎来了蓬勃发展。受统治者重构秩序需要的驱动,当时的中上层文人孜孜不倦于儒家性别伦理在当下的修复与巩固。除上文中提及的多部诞生于魏晋南北朝的女教专著外,这一时期还诞生了近10种《列女传》的不同注本及赞颂,且多出自名士之手,如曹植的《列女传颂》、缪袭的《列女传赞》、皇甫谧的《列女传》6卷,等等。此外,这一时期的文人还十分热衷于以诗歌来吟咏纪念所谓的贞妇、列女,几成为一种文坛的风气时尚,代表作如傅玄《秋胡行》、陆机《为陆思远妇作诗》、高允《咏贞妇彭城刘氏诗》等,都是称颂女子“孀居独宿,守节不移”的事迹以及“妇德既备,母道亦践”的品质。而在学术资源和话语权力高度集中的古代社会,这些创作无形之中也为女教典籍的经典化与再传播添上了一把新火。
及至隋、唐相继建立,“重构”的时代命题仍在延续,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再次催化了统治者重塑礼法纲常的迫切与信心。《隋书·后妃列传》卷首即云:“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归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衅,褒、赵结周、汉之祸。”㊲初唐虽多有胡人遗风,但在顶层思想建构上依旧完整地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性别伦理,将女性的道德优劣与家国兴衰直接联系起来,以示对女性德行教化的重视。刘知几云:“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㊳五代史的修撰就是在唐太宗的直接指导下由文臣编撰而成,统治者本人的意志偏好及编修者的思想态度肯定会对史书编写的形式、内容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具体到《隋书》,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太宗与魏征。唐太宗本人对于女教极为重视,将其视为是实现家国安定的重要一环,这在太宗本人及其身边之人的诸多言行中都有直观体现。《隋唐嘉话》中记载:“太宗令虞监写《列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㊴此条记录中,无论是太宗令人写《列女传》以装屏风的要求,还是虞世南立刻就能一字不差地默出《列女传》的行为,都充分体现了初唐统治者对于女教的推崇,以及女教文化在当时上层社会中的流行。再如《旧唐书》中记载:“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崩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㊵长孙氏以皇后之尊指导编写女教书籍,这一意识与行为本身即体现出了初唐统治者与贵族阶级对女教的重视,而唐太宗“足可垂于后代”的激赏之评又间接将《女则》所代表的女教典籍的历史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另外,《隋书》的首要修撰者魏徵也曾著有《列女传略》7卷,足见魏徵本人亦对女教文化留意颇多。在初唐特殊的时代环境中,“重构”的现实需要、统治者的文化偏好、编撰者的思想取向,三者一经遇合,造就了女教典籍在《隋志》中的经典化地位。
综上所述,汉末至隋唐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期,社会赖以延续的政治体制与思想秩序经历了由“崩溃”到“重构”的探索历程。女教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具象化形式之一,得到历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崇与鼓励,也因此迎来自身发展的繁荣期,并最终随着重构的进程完成了自身的地位落定。
五、结语
从《汉志》到《隋志》,从两汉到隋唐,女教文化以儒家学术的新变为根本动力,因两汉的现实困境而加速孕育,在魏晋南北朝的全方位重构中迎来特殊机遇,最终在隋唐一统后落定地位,成为儒家教化体系与封建统治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教的形成,既是儒家学术发展进程的产物,又是封建社会加固统治的需要,这二者的遇合使它在由两汉至隋唐的历史中应运而生、顺势而兴,但也为它日后逐渐走向僵化与畸形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 郑玄注、孔颖达编撰:《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4页。
② 高世瑜:《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页。
③ 参见高世瑜:《中国妇女通史·隋唐五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张秀春、杨忠:《中国古代女教文献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陈延斌、王丹丹:《中国古代女训论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0年第6期。
④⑱㉓㉕㉖㉗㉘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 书 局2000年 版,第266、1883、265、777、1881—1882、1393、1479页。
⑤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20页。
⑥ 焦循撰:《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7页。
⑦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⑧㉜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6、66页。
⑨⑩⑪⑫ 董仲舒著、苏兴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0—351、324、351、325页。
⑬㊳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6、371页。
⑭⑮⑯⑰ 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6、467—468、488、452页。
⑲⑳㉒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1520、223页。
㉑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0页。
㉔ 陈苏镇:《论东汉外戚政治》,《北大史学》总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㉙ 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页。
㉚ 葛洪著、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3页。
㉛ 萧统编:《昭明文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92页。
㉝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3页。
㉞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8页。
㉟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9页。
㊱ 参见张小稳:《贞节观念历史演进轨迹的重构——汉唐间贞节观念的不断加强》,《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6期。
㊲ 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37页。
㊴ 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页。
㊵ 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