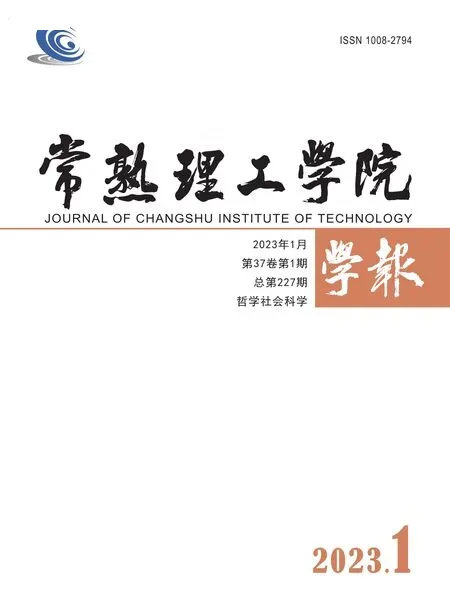南宋言子籍贯落地常熟的学案考察
2023-04-07陈颖
陈 颖
(常熟市文化博览中心,江苏 常熟 215500)
言子作为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后世尊为“南方夫子”。他致力于在吴地传播儒家学说,终成儒家礼学派的宗师。关于言子的籍贯,目前仍有争议①如曹建国在《论传世文献中所见子游及其思想》中仍然认为言子是鲁人,载《齐鲁文化研究》2012年专辑,第122-129页。,因此,对此问题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重温八百年前常熟知县孙应时联手理学家朱熹确证言子籍贯为常熟这一学案,着实是一件颇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一
关于言子的籍贯,学术界主要有“吴人说”“鲁人说”和“南京人说”三种观点。“吴人说”以《史记》为代表,“鲁人说”以《孔子家语》为代表,“南京人说”以《江南通志》为代表。《论语》失记孔门弟子的国籍家贯,故后世就有了关于言子籍贯的不同观点。
最早论及言子籍贯的是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偃,吴人,字子游。”[1]2201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称:“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1]2201。三国魏时,《孔子家语》问世。王肃辑成的《孔子家语》说:“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2]283。孔颖达《礼记正义》也云子游是鲁人。于是,言子又被定论为鲁人。《江南通志·古迹》称:“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县(今南京市)东二十二里’。”[3]31元《金陵新志》说:“言偃,吴人,金陵亦吴也。”[4]55史料中所记言子生平活动事迹,主要是在鲁、卫等中原诸侯国,因此,关于言子的籍贯,相对而言“吴人说”和“鲁人说”在后世影响更大,两说并立,争论持续至今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
从南北朝梁至南宋初期,言子籍贯始终处于吴人说与鲁人说的对峙阶段。王肃等人的鲁人说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质疑者认为,《孔子家语》其文采自秦汉以前著作,任意增损改易,所以书中称言子为鲁人自不足信。唐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反对王肃的鲁人说。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直接否定王肃的“鲁人说”,他还引《吴地记》仲雍冢“在吴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5]1447,力证言子为吴人。玄宗时,张守节研究《史记》极赅博。在《史记·赵世家》中,身为战国七雄的赵武灵王为争霸中原,在周赧王八年(前307),决定移风易俗,实行胡服骑射。他说了这样两段话:“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齒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又说:“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张守节研究赵雍的话后写道:“言吴、越僻处海隅,其民疏诞简易也。而生巫咸、巫贤、太公吕尚、吴季札、言偃,皆秀士也”[6]429。这段精彩的文字,着力铺陈了吴国人才济济,巧妙地表达了言子与吴国的关系,再次佐证言子的吴人国籍。宪宗时(806-820),唐林宝撰《元和姓氏纂谱》载:“言子墓在常熟虞山,其子孙世守之。”①转引自杨载江《言子春秋》,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挑战王肃等人的鲁人说,更多的是来自当时方志对于言子文化遗存的记载。《吴地记》记载吴郡所领各县沿革、掌故及其风物,成书年代上限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前,但原书散失,后世补辑。晚唐僖宗时(874-888),吴郡人陆广微重为撰辑成正文1卷。北宋初,宋人续成后集1卷,并附佚文9目。其中记载的言子文化遗存是:“常熟县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圣井,阔三尺,深十丈。旁有盟,盟北百步有浣纱石,可方四丈。”[7]54②南北朝吴郡人顾野王《舆地志》中,在《吴地记》以上记载之后写道:“梁萧正德为郡守,将石去,莫知所在。”转引自杨载江《言子春秋》,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常熟县桥梁五所:言偃、伩义、文学、庆(?)僊、通泰。”[7]158“仲雍冢,在吴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7]186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命李昉编纂包括天下人文事物类书供他欣赏。李昉等人花了6年功夫,旁征博引,编成含有天地万物分作55门的类书1000卷,初名《太平总类》。太宗日览三卷,历时一年读完,赐名《太平御览》。其中记言子遗存如下:“常熟县北一百九十步孔子弟子言偃宅。宅有井,井边有盥洗石,周四尺”③转引自杨载江《言子春秋》,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同一时期,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撰成考据精赅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200卷(佚8卷),为后世州县志滥觞。书中第91卷有记:“言偃宅。苏州记云:‘周文学孔子弟子言偃宅,在常熟县西一百步。’史记云:‘偃,吴人也,字子游。’又吴地记云:‘宅有井,井边有盥洗石,周四尺。’舆地志云:‘梁萧正德为郡太守,为萧将去,莫知所在。’”[8]1828
宋神宗(赵顼)元丰七年(1084),吴郡朱长文(1041-1098)撰《吴郡图经续记》3卷。他在这部4万字的书中,选入言子资料两条:“言偃宅,在常熟县西北。宅有井,阔三尺,深十丈。井傍有坛,坛北部有浣纱石,方四尺。县有言偃桥,盖得名于此。子游的文学升圣师之堂,吴人好儒术,其有所自哉。”“言偃墓,在虞山上,与仲雍墓并列”。[9]61宋孝宗(赵眘)淳熙十六年(1189),朱长文作《学校记》,再次写道:“吴为东南都会,自泰伯三逊天下,延陵脱屣千乘,言偃的学称……世多显者”[10]614。
虽然自唐宋两代,人们普遍质疑言子为鲁人说,众多地方文献证实言子为吴人,但言子的常熟籍贯依旧无法形成定论。以上即南宋孙应时联手朱熹为言子证籍的历史背景。
二
从现存常熟地方文献看,南宋以前的常熟地方官员对于言子籍贯的争论,未置可否一词。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从开封迁都南京(河南商丘),次年再迁临安(浙江杭州)定都,史称南宋。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平江府拱卫南宋政权的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日盖重要。在平江府所领各县中,常熟为望县,籍贯常熟的言子作为江南文化的先驱,开始受到地方官府的关注,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评言子的历史契机。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言子籍贯的争论出现了新机,吴人说最终否定鲁人说的条件已然成熟。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理学人物孙应时出任常熟知县。孙应时,淳熙二年(1175)三月中进士第,淳熙五年冬,获任黄岩县尉,十年返乡教书,十一年应史浩之请,讲学东湖书院,十二年任泰州海陵县丞,十五年丁父忧,绍熙二年(1191)任遂安县令。其投身于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门下,后又转学朱熹,与朱熹关系深厚。淳熙八年十二月(1181),浙东大旱,朱熹为浙东常平使者,专事救灾;除了赈灾以外,朱熹重视修水利以兴农,当时孙应时主持当地水利工程建设,朱熹与孙应时因水利工程而结识,一见即与定交。孙向学深醇,行谊整饬,理学、经济、文章并著,有《烛湖集》20卷传世,收入《四库全书》。
1.地方文献遗存的搜集
早在赴任常熟之前,孙应时即认同言子籍贯“吴人说”。孙应时即将到任常熟时,曾致信浙西常平使李唐卿云:“常熟属在东吴,昔言游之故乡,今天子之近甸。谓亦壮邑,偏蒙恶声。”[11]551又致书知平江府郑若容云:“惟是琴川之近封,实为弦歌之故里,乃当昭代,独著恶声。”[12]553孙应时到任常熟后即谒言子庙,有《到任谒庙文》传世,曰:“窃迹此邦实惟圣门高弟言游之故里,古今辽邈,风化方传。某受县之始,祗见学宫,心不敢忘。惧力不足,圣贤临鉴,尚佑启之。”[13]383孙应时走访民间,查看古迹,获得了言子籍贯常熟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历史遗存信息:
(1)言子为常熟人,已经成为常熟民众的普遍认知。在常熟有则民间故事,说是孔子晚年到常熟寻访言子,见到一个十来岁小孩在河里摸螺蛳,前去问路。小孩感到在人前赤身露体不太雅观,赶紧后退到齐颈深的水中,有板有眼地唱声诺:“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孔子感慨地说:“这里乡下小孩尚且能知书达礼,难得难得,我放心了。”于是返身回转。[14]343相传吴人“被发文身,裸以为饰”,人称其为裸国。这则民间故事表明小孩懂得礼貌,懂得歌咏,呼应着言子南归传道使得吴地由朴鄙而人文的风俗变化。常熟曾出土两方唐代墓碑,分别是《唐故施府君墓志铭并序》和《唐奚君故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铭文明确写明时间分别是“大中五年”和“大中六年”,即公元851年和852年。前者铭文中有“生兮言偃之侧,没窆虞山之东。独立仰之修竹,三魂悲此飃蓬。”[15]13墓志深为逝者生前居住言宅之侧、死后埋葬虞山之东为荣。后者在序中直接写明:“窆于常熟县言偃乡,买刘野者地建茔,礼也”①《唐奚君故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此墓志铭出土于常熟市福山海城路西北庙前村,未见于任何著录,由常熟市博物馆周公太先生提供。。因为逝者是“颖川人”,墓志强调了“言偃乡”葬地,强调了买地建茔之礼,传达出对于言偃的尊崇之情。以上事例说明对言子的尊崇普遍存于常熟民间。
(2)在南宋以前,吴地官员尊崇言子留下的记载不多,但也并非完全阙如。如在郡城苏州,为纪念言子,在淳熙七年(1180)于学道书院讲堂西始建丹阳公言子祠,祭祀言子。宋元丰初年,常熟知县刘拯在县衙设立县宰题名榜,以勤方来。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知县曾慎改板榜为石刻,“庶为不朽之传”。他在《常熟县令题名碑》中激励来者:“夫儒之效,恺悌及民,福延百里。庶几乎刊石而无也。”[16]165宋淳熙七年(1180),知县陈映撰《常熟县令续题名碑》,表达自己勤政为民的心迹:“今吾邑之人或知映,不敢惰也,率以淳厚简孚,交相为治。”“若夫邑之望,则有巫咸所止之山,泰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龚景材所表之闾,其风俗之美,由可概见。”[17]166由此可见当时常熟官方对于巫咸、泰伯、言偃、龚景材等先贤的尊崇,并强调以先贤为范,推动地方治理和移风易俗。
(3)常熟城内保存着诸多言子文化遗存。南宋以前,常熟保存或新建了诸多彰表言子的遗存。庆元六年(1200),朱熹弟子黄士毅来到常熟,流连于言子家庙北侧文学桥,题刻“文学桥铭”曰:“登桥而思,刻铭述记。期我同心,如水荐至。能令后学,本末易明。伪行不作,踵公自今。”②转引自杨载江《言子春秋》,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在唐以前,常熟没有志书记载言子的文化遗存。明陈三恪《海虞别乘》在“古迹”中追记周代常熟古迹:
吾邑县治南北多先贤遗迹,北有文学桥、子游巷、墨井、言子桥、景言巷,又有孔子巷在景言巷西,疑子游祀孔子处。今南门之内,旧传为阙里坊,则因子游而以义起也。先贤治武城,有弦歌之化。吾邑旧名琴川,以水凡七派,自南门内以至炳灵公庙而止,亦名七弦,今湮其大半。[18]49
这说的是,与言子相关的古迹早就存在于周代,因此唐宋地方志书就有言子古迹的记载。
(4)言氏后人聚居常熟,和睦相处,“青瓜延蔓宗枝茂,丹桂流芳孙子贤”③见明姚广孝《瞻子游遗像》,转引自杨载江《言子春秋》,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西汉武帝时,言氏16世言成大以贤祖武城之政律己,在河南任襄城令时政绩突出,辞官归里,百姓罢市,感恩相送。其归家后著书课子,见言子墓周围凋零,便在周围植树造林。他创修言氏宗谱,世系“自子游始,凡16世”,并有《言氏家箴》和《亲民集》。后世续修家谱,代有传人。言氏后裔世守旧宅,旧宅有墨井,井畔有捣衣石,是为镇宅之宝。南北朝时,太守萧正达巡视常熟,派人索要此石。三十世言正拒之门外,公差翻窗而入,言正躺在石上,对公差喝道:“宁可杀了我,石不可取。”公差强行抢石,言正追骂。太守拿出银子购石,言正扔进河里。失去镇宅之宝的言正从此郁郁寡欢,客死他乡。①言梦奎编纂《言氏家谱》之“人物录”,此谱成于清雍正九年(1731),现存常熟市博物馆。
2.编信史、建专祠的举措
面对大量地方文献和历史遗存信息,孙应时认为言子籍贯为常熟确凿无疑。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言子去世1600多年,其籍贯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即使言子故乡常熟,“郡县之学通祀先圣,公(言子)虽以列得从腏食,而其乡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19]3虽然早在唐代言子即被纳入孔庙正殿从祀,但孙应时认为这还不够,言子作为孔子弟子从祀常熟文庙这是通祀,但其乡没有专祠祭祀言子则是缺憾,而常熟没人能把乡贤言子的事迹说得清楚,更是令人无法接受。面对以上尴尬的现实,孙应时感慨万分,他为确定言子常熟籍贯而奔走。孙应时在为言子证籍方面做了两件重要事情:(1)首编常熟县志,名曰《琴川志》,记载言子事迹,改变言子家乡常熟“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的状况。孙应时搜集散落的常熟文献,在《琴川志》中记录了大量言子文化遗存,包括“子游巷,意即言偃坊”“吴国言公东巷”“吴国言公西巷”“吴公祠”“文学桥,旧名言偃桥”“言偃墓”“弦歌馆”“兴贤坊”等。对于言子历史遗存,《至正重修琴川志》予以具体记载,如关于“兴贤坊”的记载是:“在县南,以县学居其左,故名。本名学道坊,前令王爚建,后令别桷改今名。”[20]4《至正重修琴川志》全文辑录了黄士毅游常熟撰写的《文学桥铭》。(2)始建言子专词。孙应时任职第二年(1197)在文庙明伦堂东偏建成言子专祠,为屋三楹。祠堂建立后,是岁中冬长日之至,孙应时亲自率领邑人、学士、大夫及其子弟公祭言子,并宣读了脍炙人口的《先贤言子赞》:“孔氏以来,千六百祀。大江以南,遗迹能几?猗欤琴川,子游之里。有宅有桥,具应《史记》。弗崇弗彰,为邑之耻。我作斯堂,学宫之旁。与我士民,弦歌洋洋。山川其光,斯文其昌。勿替成之,以念四方。”此赞强调了常熟是“子游之里”,并明确建立言子专祠是要光大子游传统,推行弦歌之治。尤其是,在此赞语中,孙应时正面提出了“弗崇弗彰,为邑之耻”的思想,推动了常熟尊言学言进入到一个自觉的时代。
孙应时在常熟任知县三年多,其为言子常熟籍贯确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常熟人民始终不忘孙应时的这一恩泽,把他列入文庙名宦祠祭祀,虞山书院把他列入子游祠从祀言子。
三
在言子专祠建成以后,孙应时为了使言子籍贯常熟成为定评,就写信给理学大家朱熹,请他为专祠撰写碑记。孙应时在信中说:“常熟实为言游故里,桥巷犹存其名,且载于图经,惜未有表而出之者。已即学宫之侧别为堂以奉祀,匾曰‘丹阳公祠’,念非乞记于先生,犹不为也,不知先生肯特破例下步否?”[21]568然而,朱熹在庆元五年春天回信婉拒,其原因是当时的“庆元党禁”波及朱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信中告诉孙应时,不应称子游为“丹阳公”,而应称“吴公”,因为“子游之封,在唐为吴侯,在政和为丹阳公,而淳熙所颁祀礼,乃为吴公。盖十子皆因唐之旧,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时所加。”[22]4887朱熹此话,其实暗含着认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言子是“吴人”的观点。面对朱熹的婉拒,孙应时即手书长信,再次请求赐记:“某昨书又尝僭乞子游祠堂记,谅关尊抱,区区素不敢事炫饰,妄求品题,以自表见。顾此邑实子游故里,今江浙所无有,不以请先生求一语为信,某之罪大矣,亦望因赐挥染,当留俟他日托人刻之,乞无疑也。”[21]16孙应时鉴于时局,提出另找合适时机镌刻碑文。朱熹由此被孙说动,遂于庆元五年(1199)六月撰记,并在信中对孙应时说:“昨需祠记,本不敢作,以题目稍新,不能自己,略为草定数语,漫录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祸,幸且深藏之也。”[23]4887这就是朱熹的《平江府常熟县吴公祠记》。
朱熹的《平江府常熟县吴公祠记》,是历史影响深远的儒学经典。朱熹充分肯定了孙应时在常熟建言子专祠的意义,即“矧今全吴通为畿辅,文物之盛绝异曩时,孙君于此,又能举千载之阙遗,稽古崇德,以励其学者,则武城弦歌之意,于是乎在。故熹闻其事,而乐为之书。”[19]3这就说明,朱熹同样认为,常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孙应时建立言祠弥补了“千载之阙遗”,具有稽古崇德、以励学者的功绩,也具有推行弦歌之治的意义。朱熹的碑记,主要内容是两大方面,一是为言子证籍;二是论子游传统内涵。
1.朱熹为言子证籍
朱熹在为常熟言子专祠所撰碑记中,首先引经据典,肯定了言子籍贯常熟的正确性。他在碑记中写道:
平江府常熟县学丹阳公祠者,孔子事第弟子言偃子游祠也。按太史公记,孔门诸子多东州之士,独公为吴人。而此县有巷名子游,有桥名文学,相传至今。《图经》又言:公之故宅在县西北,而旧井存焉。则今虽不复可见,而公为此县之人,盖不诬矣。[19]3
朱熹指出,言子为吴人,是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弟子,不仅《史记》有相关史料,而且常熟当地还有言子巷、文学桥等言子遗存。朱熹深知,孙应时邀其撰记,有着请他为言子证籍的意图,因此就在碑记开端态度鲜明地肯定言子为常熟县人,同样认为“其乡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朱熹明确采纳司马迁的吴人说,重在以《史记》和《祥符州县图经》所记作为论据。《史记》是历代官方公认的信史著作,而《祥符州县图经》也是学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祥符州县图经》,是北宋李宗谔、王曾奉敕编纂,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因以为书名。该图经凡记大中祥符年间行政区划;京府二、次府八、州三百五十二、军四十五、监十四、县千二百五十三。序言说,图经之“图”是“作绘之名”,“经”是“载言之别”,合称图经。可见图经即方志书之有绘图、有说明的一种形式。在材料来源上,文献资料与调查访问资料并重;体例和内容方面比较规范和相当完备。其后宋真宗还曾命令各州府修订大小图经,令职方部知照诸州贮备资料,每闰年依本录进,按期绘制和呈送图经形成严格制度。此志编纂过程是:“先由各州县自行搜集资料,自行编订,朝廷惟颁凡例;送进以后,始交官阁学士纂为全书”,然后再颁下诸州县谨藏。[24]因为《祥符州县图经》的基础材料是由各州县自行搜集上报的,因此其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既然《史记》明确言子为吴人,《祥符州县图经》又有言子故宅、旧井的记载,因此,朱熹认为言子“为此县之人,盖不诬也”。
2.朱熹论子游传统内涵
朱熹不仅为言子证籍,而且推动子游传统落地江南,为江南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碑记论子游传统内涵,有四个方面重要内容:
(1)定言子历史地位。言子为孔门十哲之一,列文学首位。东汉永平十五年(72),明帝东巡过鲁,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言子首次列入曲阜孔庙从祀。唐代开始,言子领“哲”字衔配享孔子,并赠吴侯、丹阳公、吴公爵位。对于如何准确定位言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独特的地位,朱熹开辟了新的思路,提出了新的见解:
若夫句吴之墟,则在虞夏五服,是为要荒之处。爰自泰伯采药荆蛮,始得其民,而端委以临之,然亦仅没其身。而虞仲之后,相传累世,乃能有以自通于上国,其俗盖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间,乃能独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身通受业,遂因文学以德圣人之一体,岂不可谓豪杰之士哉![19]3
朱熹把言子功绩放在历史中去考察,具体包括三个时期:一是虞夏时期,处在五服要荒之处的吴地,“德行道艺之教”不行,泰伯周礼治吴,但仅行一世。泰伯卒,无子,仲雍嗣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这也就是《左传·哀公七年》中子贡的话:“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岂礼也哉?有由然也。”[25]2162此说虽有争议,但大致来说,泰伯、仲雍适吴既治周礼,又入乡随俗,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吴俗。二是虞仲之后累世,吴地与中原有了较多交往,文化也有较大融合,如梦寿问礼中原,季札出使上国,南北人才交流,但春秋末期吴地仍是“朴鄙而不文”,即吴地文化仍是质朴鄙陋,缺乏礼仪人文文采,文明进程相较中原落后。三是言子北学中国得圣人一体,晚年南归传播儒家文化,开启了吴地文化崇文重教的基本走向。这就客观地评价了言子的历史性功绩,也肯定了言子的历史地位。
(2)揭言子思想特征。历史上对言子为学特征的评价,就是精于礼乐,以文学著名。那么,如何理解孔子所谓“文学”,如何理解言子“以文学名”,而其得圣人一体的礼乐思想特征又为何?这在朱熹之前是没有明确结论的。朱熹在撰写碑记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其曰本之则无者,虽若见诎于子夏,然要为知有本也。则其所谓文学,固宜有以异乎今世之文学矣。既又考其行事,则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诗书礼乐为先务,其视有勇足民之效,盖有不足为者。至使圣师为之莞尔而笑,则其与之之意,岂浅浅哉?及其取人,则又以二事之细,而得灭明之贤,亦其意气之感,默有以相契合者。以故近世论者,意其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19]3
朱熹通过剖析子游与子夏西河之争,揭示言子重本知本的思想特征;通过剖析其异于今世之文学的内涵,强调言子行事必以诗书礼乐为先务;通过剖析其取人灭明默有相契,强调其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虽然朱熹没有正面说明言子之“文学”的真实内涵,但通过考其行事,即“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诗书礼乐为先务”,已经对此做了回答。这就是现代学者所谓的“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治教化之学”[26]。若把以上“知本闻道”和“礼乐教化”结合起来,就可以准确把握言子的思想特征。为知有本,其本即德行,是内在的仁;敏于闻道,其道即人道,是孔子之道。知本闻道,礼乐教化,这就是“特习于礼,以文学名”的内涵。
(3)说言子人格特征。荀子在《非十二子》中,用“犹然而材剧志大”[27]94-95来评价子游氏之儒。东汉王充在《论衡·问孔》中,称“子游之大材也”,并引《孟子》的话说:“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颜渊具体而微”。[28]329朱熹在碑记中,对言子人格特征的评说是:“今以《论语》考其话言,类皆简易疏通,高畅宏达。”他不仅如此概括言子的话语,且在论子游行事、为人时也紧扣这一人格特征,强调“其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朱熹在诸多场合有着相似的论述。他曾经说过:“子夏是个细密谨严底人,中间忒细密,于小事上不肯放过,便有委曲周旋人且投时好之弊,所以能流入于小人之儒也。子游与子夏绝不相似。[29]1140朱熹认为言子的人格特征,是得南方文化精华的结果。清学者陈祖范在《重修尊经阁记》中说:“ 《隋书·儒林传》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此朱子之言所本也。”[30]209言子思想和人格均得南方之精华,朱熹对言子人格特征的概括,得到后人普遍认可。
(4)期子游传统弘扬。在碑记中,朱熹充分肯定孙应时建立子游专祠之举,并表示“喜闻其事,而乐为之书”,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写作碑记的心意与动机,即乐于推动子游传统落地,在江南推动儒学思想的传播和弘扬。
至于孔门设科之法,与公之言所谓本、所谓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则愿诸生相与勉焉,以进其实,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复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食之讥焉,是则孙君之志,而亦熹之愿也。[19]3
这是朱熹撰记的期望。这里既回应了前文对言子知本闻道、行事取人的评价,又回应了荀子对后代子游氏之儒的讥讽,并正面提出愿望:以进其实,复有如公者出,而避免成为受人讥讽的贱儒。至此,朱熹写作碑记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充分显露。
以上四方面内容,始终都在回应着历史的时代的课题,高屋建瓴,语重心长,具有鲜明的现实性,这就是朱熹在给孙应时的信中所说:“以题目稍新,不能自己,略为草定数语”[23]5157。碑记为南宋以后江南重提子游传统继承、推动江南儒学发展定下了基调。南宋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常熟人民不忘他为言子证籍的丰功,将他列入五夫子祠,每年由地方官致祭。而朱熹撰写的碑记,则被常熟士人先后四次镌刻立碑,前后绵延数百年,数代人持续彰显此碑精神,持续接受此碑恩泽,这是常熟尊言历史传统中值得重彩书写的事件。
四
经过南宋孙应时、朱熹等人的努力,最终奠定了言子籍贯吴人说的坚实基础。与此呼应,南宋端平年间,知县王爚重建常熟文庙,移建言子专祠,形成了新的庙学体制,这就是东庙西学、庙前祠后的格局。王爚在新建文庙中设立“象贤斋”,聚言族子弟其中,县里给予赡养之资,买书延师,朝夕训导,择齿长者主言祠祭祀,又虑岁月浸远,美意难继,则为之节冗费,买田五百多亩庶贻永久。南宋理学家、任礼部尚书的魏了翁撰《重建学宫记》,时间在嘉熙元年(1237),仅是朱熹撰写祠记后的30多年。魏了翁碑记完全赞同朱熹所记,如实记载了孙应时联手朱熹为言子证籍之事:“庆元三年,县令孙应时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学,新安朱子既为证其事。”[31]7记文肯定了言子精于礼乐的思想特征,最后也是对常熟士人的勉励:“我朱子既尝表其事以风厉之,予又何言?独惟山川风气,古今犹夫人也,诵先生之书,服先贤之训,呜呼,其必有闻风兴起,以无负建学尊贤之意者,士当勉之。”[31]7同年,南宋礼部尚书袁甫应王爚之请撰《常熟县教育言子诸孙记》,同样肯定了朱熹的碑记,赞同言子故里为常熟说:“按《琴川图志》,言偃,字子游,旧宅在先治之西。唐追爵吴侯,我朝升为公。庆元间,令孙君应时即学宫建祠于论堂东偏。后令迁其祠,祀事弗饬,有识嗟惋。”袁甫尤其对王爚在学宫中建象贤斋聚言族子孙而教大加赞赏,认为“是举也,可谓知礼也”。[32]17两位在当时都是重量级理学家和政治家,他们共同在朱熹证籍基础上,再次为言子吴人说站台,肯定了在言子家乡常熟建立言子专祠的重要意义。他们两人呼应朱熹期待,精当地阐发言子的礼学思想,强调子游传统的真实内涵,从而把言子导入常熟文化,要求邑人弘扬子游传统,这对常熟的文化发展意义重大。魏了翁和袁甫的记碑同朱熹的记碑均立于常熟文庙,成为言子籍贯常熟的历史见证。
在孙应时和朱熹为言子证籍以后,言子作为平江府常熟人,得到常熟知县、平江知府为代表的官方和后世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认可。孙应时联手朱熹为言子证籍的事迹,也被载入官修的《吴郡志》和续修的苏州府志。南宋光宗(赵惇)绍熙间,平江府开修以府并及所属县份为论述对象的官志,范成大为总撰。绍熙三年(1192)撰成,题名《吴郡志》。这是苏州首次以志命名的地方志书,下限止于绍熙三年。这部经过官方“订伪补缺”的《吴郡志》,把原稿未能载入的庆元年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在常熟所发生的为言子落贯证籍的大事以及有关言子与常熟的史料,无不尽收志书各卷之中,包括全文收载朱熹为言子证籍的重要碑记,认定言子为古吴之地常熟人。如《吴郡志·古迹》载:“言偃宅,《苏州记》云:在常熟县西。《史记》云:言偃,吴人也。《吴地记》云:宅有井,井边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33]98又《吴郡志·人物》中有:“言偃,字子游,吴人。”又载:“今言偃宅,在常熟县西。常熟,世传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说故也。”[34]303-304常熟后世历代志书,均把言子作为乡之先贤予以记载、颂扬。元代以后,常熟地区存在着三处祭祀言子的祠堂,即文庙的言子专祠、书院的言子祠学和家族的言子家庙。常熟在后世逐步建立起以先贤言子为代表的乡贤祭祀格局,建立了以先贤言子为宗的在地儒学道统体系。
在孙应时和朱熹为言子证籍以后,在言子家乡常熟持续地掀起了学言尊贤的文化行动。南宋著名理学家对于“子游传统”的阐释,体现的是思想权威性,而常熟地方官员对于“子游传统”的实践,则体现的是行动示范性,两者结合、上下联手,终于树立起了众人仰慕的历史丰碑,重新阐释了被尘埃掩映的历史传统,唤醒了常熟人的文化意识,开启了常熟尊言学贤的全新历史。常熟尊言学贤的主要内涵是:效行礼乐风教,推进移风易俗,崇尚和谐社会;效行学道爱人,推行弦歌之治,建设小康社会;效行崇文重教,尊师兴教养士,弘扬人文精神;效行知行合一,传承求真实学,培养创新人格。由此而来的是常熟文脉赓续,常熟文化繁荣,常熟崇文重教尚和。到了清代,常熟祭祀乡贤言子得到了朝廷的肯定,朝廷先后六次派员赴常祭祀言子,前两次致祭还有御制祭文存世(言子墓有祭文亭,文庙有祭文碑),常熟尊言学贤由此臻于峰巅,进入到令人自信自豪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言子故里问题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言子故里问题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提出的,绝非单纯的故里之争,理清历史脉络、揭示历史真相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古人的表现。同时,这一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对于当今传统文化研究,尤其是对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江南文化的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