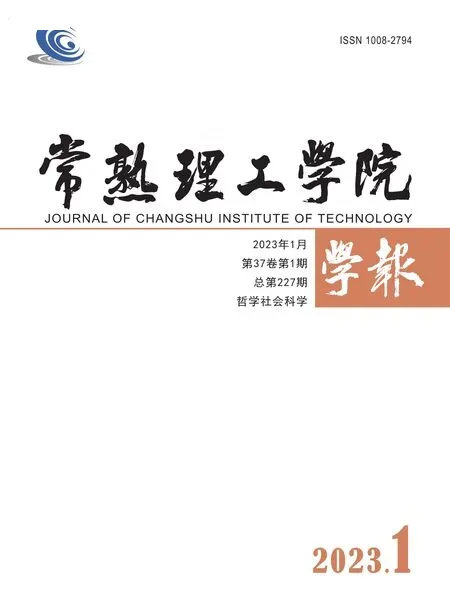《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2023-04-07朱则杰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 310058)
在清代诗歌(包括散文)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世纪之交相继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先生所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两种巨著。两书均为16开三大册,各著录清代作家近两万人,别集约四万种。特别是《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提要》),更可以说是后出转精,代表着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不难想见,涉及这么多的对象,即以《提要》而论,这里面的各种疏忽、缺漏乃至错误,自然也是难以尽免的。并且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一般说来,其难度恰恰也是最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订正和补充,正可以使两书更趋完善。特别是关系到《提要》本身以及日后《全清诗》《全清文》等内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问题①《清人别集总目》虽然按作家姓氏笔画排序,但各家小传也力求注明生卒年。,更是解决一处是一处,完成一家多一家。因此,笔者在日常读书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即随时将它们记录下来,并陆续整理成文,相继分组发表,提供给编撰者以及其他有关读者参考。本篇取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仍旧按照《提要》著录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有些同时涉及《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附此一并予以指出。
一、秦嘉铨(卷六,上册,第117页)
秦嘉铨,《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二册,1728。
按同治年间秦锦等人第八次所修《洞庭秦氏宗谱》,卷三之二“廷彩公派十七世至二十一世”之“十八世”内“秦嘉铨”名下记载:
字存古,号既耕。嘉定邑庠生。著有《既耕堂诗集》,载入郡志艺文、传。生万历庚申[四十八年,1620]六月初九[公历7月8日],卒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六月廿九[公历8月8日],寿七十六。②秦锦等《洞庭秦氏宗谱》,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咏烈堂刻本,第23a-b页。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年6月11日。
这样,秦嘉铨的生卒时间就十分具体了。《提要》介绍《既耕堂诗集》,曾说“诗始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止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这正符合一般的创作规律。
《既耕堂诗集》笔者尚未获读。《提要》提到的卷首第一篇潘耒序,则亦见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八,标题作《既耕堂诗序》,正文有一段叙及秦嘉铨的年龄:
岁己巳,余游石公,始得见先生,须眉皓白,神观超然,年已七十余矣,无几何化去。[2]
这里“己巳”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该年秦嘉铨实际刚好七十岁整;潘耒称其“年已七十余矣”,记忆不是很准确。
附带关于乾隆年间吴定璋辑太湖地区诗文总集《七十二峰足征集》,诗集卷五选录不少秦嘉铨的作品[3]。同卷秦嘉铨之前特别是之后,还收有十来位太湖东、西洞庭山一带的作者,版心统称为“秦氏合编”;其中一部分作者,其具体的生卒时间同样也有可能从该《洞庭秦氏宗谱》中查找得到。
二、瞿有仲(卷六,上册,第135页)
瞿有仲,《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三册,2460。
按陈瑚《确庵文稿》卷十下“诗歌”,有七律《瞿有仲五十》四首,小序说:
吾门瞿子有仲,今之振奇人也。岁在乙卯,为其知命之年。菊月初度,其兄师周赋诗劝酒,词旨辛酸,予为感叹者久之。因成四章,以叙其抑塞磊落之概,并邀同人共作焉。①陈瑚《确庵文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第315页。组诗首数,瞿有仲稿本《焚余集》卷一《祭确庵陈夫子文》说是“赐诗三章”,见《常熟文库》第8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页。
这里“乙卯”为清康熙十四年(1675),瞿有仲五十岁,亦即所谓“知天命”。据此逆推,可知其出生于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具体时间,则在“菊月”即农历九月份。
又同样是《确庵文稿》卷十下,稍前还有五律《钱梅仙五十赠言十首》,为另一门人钱嘏(梅仙其号)而作,小序说:“梅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念其及门已久,赋诗相赠。”时间署款为“阏逢摄提格之岁,律中无射”[4]314,即甲寅年(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诗歌最末第十首,正文云:
门墙多国器,伯仲见钱瞿。
健谷时谈鬼,梅仙只守株。
亭亭天下士,兀兀古人徒。
至竟成何事,嗤他两腐儒。
同时加有相应的自注:
有仲自号健谷,与梅仙交最密,皆不求用于世。明年有仲亦五十矣,故戏而□[及?]之。[4]315
这就是说,瞿有仲比出生于天启五年乙丑(1625)的钱嘏小一岁。这样,瞿有仲的生年能够多得到一次证明,更加可以确信无疑。
瞿有仲的这个生年,曾见近年不少论著有过正确的括注“1626”,但都没有交代依据,猜想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
瞿有仲的卒年,目前仍旧不详。不过,康熙《常熟县志》卷二十《人物·文苑》“明”瞿纯仁本传最末,曾经连带叙及:“孙有仲,读书能诗文,无忝家学,惜早亡。”②康熙《常熟县志》,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刻本,第42b页。可见“中国数字方志库”网站,网址:http://10.15.61.5,2022年6月11日。该县志据卷首钱陆灿序最末所说,“刻始于癸亥岁之五月,而成于丁卯春王正月”③康熙《常熟县志》,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刻本,第7a页。——这里的“癸亥”“丁卯”依次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十六年(1687)——这就是说,瞿有仲即使再晚,也应该卒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以前;并且进一步从“早亡”来看,很可能其享年不到六十岁,亦即卒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以前。
确定这个下限,有时候也能解决相关的问题。例如章文钦先生所作《吴渔山集笺注》,卷六“画跋补遗”内有一篇《溪山雨过图跋》:
《溪山雨过图》。丁亥冬十月,临高尚书法,奉祝仲翁年先生尊阃宋君夫人五十华诞。墨井道人吴历。[5]
笺注说,这里的“丁亥”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仲翁年先生”的“仲翁,疑指瞿有仲,字健谷,亦常熟人”①章文钦《吴渔山集笺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0页。另外关于字号,详见下文。。然而,此时瞿有仲谢世已经数十年,这个“仲翁”显然不会是指瞿有仲,而是另有其人。
附带关于瞿有仲的父亲瞿共美,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曾定其生卒年为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至清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依据分别注为陈瑚辑《离忧集》卷上和今人《江苏艺文志·苏州卷》[6]。检《离忧集》卷上所录最末一家“海外畸人”亦即瞿共美的诗歌,有《六十初度自述,示子八首》,小序提到“丙申六十初度”[7],逆推其生年确实如此。但是,本年“六十初度”,并不等于瞿共美就卒于本年。而已故张慧剑先生《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记载瞿共美生平事迹,最后本年一条恰巧依据这组诗歌,说:“常熟瞿共美在世,作《六十初度》诗。”[8]《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之类的编者可能误解了张慧剑先生的意思,所以才把本年当成了瞿共美的卒年。实际上,就在陈瑚《确庵文稿》内,不仅卷十二“古文”有《瞿叔献六十寿序》[4]364,而且卷七下“诗歌”还有《瞿叔献七十》[4]286,都是为瞿共美(叔献其字)而作,而后者据编年作于“丙午”即康熙五年(1666),说明瞿共美享年至少在七十岁以上。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以及《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关于瞿共美的这个疏误,至少在近年问世的李峰、汤钰林两位先生合著的《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中已经得到更正——其“瞿共美”条既将生卒年括注为“1597-?”,又同时说明“卒年七十余”[9]1016,这样就符合实际了。而更加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刚刚影印出版的《常熟文库》,收有瞿有仲的稿本《焚余集》凡三卷,卷一文类最末一篇《祭确庵陈夫子文》开头叙及:
维康熙十有四年冬十月甲戌,确庵陈夫子卒于蔚村。虞山门人瞿有仲新遭大丧,不克赴。……仲遭先君之变也,苫块之中而闻吾夫子之死,去先君死才二十七日耳。一月之间,既丧吾父,复丧我师;生我成我,同时陨殁……②瞿有仲《焚余集》,《常熟文库》第8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229页。原文“先君之变”衍一“之”字。又同册此后还收有一种钞本《瞿有仲集》凡一卷,作品很少,并且都已经见于稿本《焚余集》,因此本篇祭文不再引用比勘。倒是《提要》提到的常熟市图书馆藏另外一种包含《丁酉集》《戊戌集》的钞本,从时间范围来看明显与稿本《焚余集》不同,不知具体情况如何。
陈瑚(确庵其号)卒于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的十月二十日(公历12月6日),瞿共美早二十七天,即可知其同年谢世,具体时间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历11月9日)。难怪我们在陈瑚的《确庵文稿》内,见不到任何正常应该为瞿共美撰写的悼念诗文,却原来两人挨得这样近。如此,《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关于瞿共美卒年的这个问号,也就能够进一步改补作“1675”;而通计其享年,则为七十九岁,接近八十。
另外,顺带看到《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钱嘏”条,生卒年括注为“1626-?”[9]758,这里的生年却明显比上文所述晚了一年,而变成与瞿有仲同岁了。究其原因,似乎与严熊《严白云诗集》有关。该集卷十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有《钱梅仙五十》[10]84-85,逆推钱嘏生年本来正是天启五年乙丑(1625)。但是,该诗起句云:“与君齐甲子。”而卷十一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第一题《元旦》起句自述却云:“五十今朝是。”[10]87如果读者据此误以为钱嘏与严熊同岁,那就会导致钱嘏也出生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的错误③严熊这个生年,可以参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于是变成了与瞿有仲同岁。
最后再说一下瞿有仲的字号。瞿有仲以及其兄瞿师周,表字均与名讳相同。为此陈瑚专门写了一篇《瞿师周、有仲字说》,收在《确庵文稿》卷二十三之“说”内,开头就明确交代:
常熟瞿生师周、有仲兄弟,乞命字于予。予仿古人子仪、浩然之例,即字师周曰“师周”、有仲曰“有仲”。[4]433陈瑚辑《从游集》收录众门人诗歌,卷上瞿师周、瞿有仲小传也分别说“字师周”[11]650、“字有仲”[11]652。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十分少见①清代比较著名者,有李刚己字刚己,可见拙著《清诗考证》初编第三辑之一百二十七《李刚己表字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1349-1351页。,所以后世读者一般不容易想到这一点,从而生发出诸多疏误。例如上及《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瞿有仲”条称其“字有仲,号建[健]谷”[9]1017,还算正确;同页“瞿师周”条就不详其字,只称“号漆园”。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明遗民卷”瞿师周小传,则称其“字漆园”[12]第二册,1189;“顺治朝卷”瞿有仲小传,又不详其字,只称“号健谷”[12]第四册,2391。而《提要》本条,称“有仲号健谷”,很可能就是受到《清诗纪事》的误导;至于《清人别集总目》称其“字健谷”,则又误同前引《吴渔山集笺注》,只不知道其作俑者是谁。由此可见,看起来似乎很微小的字号问题,也往往牵涉到不少重要著作,因此同样有必要加以梳理。
三、毕朗(卷七,上册,第179页)
毕朗,《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同著录《织楚集》及其《余稿》各一卷[1]第一册,379,而作者仅《提要》有介绍:
朗字昭文,安徽新安人。昆山王圣开妻。明季宫人,甲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后流落燕市。嫁王[圣开]后授徒为生,寄居城南熊家村。善鼓琴,画美人兰菊。
按毕朗相关情况极其复杂,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系统。
第一个可称“ 《明练音续集》系统”。《明练音续集》是王辅铭所辑明代江苏嘉定(或称“练川”,今属上海)的一种县级诗歌总集,包括部分进入清初的遗民作者。据卷首编者《引》,此集编纂历时“三年”,完成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13]301。其卷十“闺秀”倒数第二家为“毕昭文”,选录五言律诗《村居》二首、七言绝句《夜书》《夜饮》《夜画》《夜绣》各一首,小传说:
昭文号少陵。明季宫人,鼎革后流落燕市。遇昆山王某,挈之南下。成伉俪后,以授徒寄居邑南熊氏村。容止修整,善鼓琴,能画美人兰菊,工诗。有《织楚集》。[13]445
这里不详毕朗其名,所以只能直接以表字为称,并且说她是“明季宫人”。
第二个可称“ 《清诗别裁集》系统”。《清诗别裁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是沈德潜等人合辑的一种全国类诗歌总集。据卷首沈德潜《凡例》最末第十八款所述,此集“创始”于乾隆十年“乙丑”(1745),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又复增删镂版,共经十六寒暑”[14]上册,5。其卷三十一闺秀第五家为“毕著”,选录五言古诗《纪事》、七言绝句《村居》各一首,小传说:“字韬文,江南歙县人,昆山王圣开室。”特别是所附两则诗话十分重要,兹不惮其烦,全文抄录于次:
著父守蓟丘,与流贼战死,尸为贼掳。众议请兵复仇,著谓请兵则旷日,贼且知备,即于是夜率精锐入贼营。贼正饮酒,惊骇;著手刃其渠,众溃,以兵追之,多自相践踏死者。舆父尸还,葬于金陵。时二十岁女子也。后来吴中,为昆山王圣开室,裙布荆钗,无往时义勇气矣,白首相庄以没。阅毛太史大可集,载沈列女云英为父报仇杀贼事,与相类,岂世乱时,天故生奇女子不一人耶?抑所传闻异辞耶?[第一则]
韬文诗稿,向见于家来远兄处,序中有云:“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胎弓五石能开。”又云:“入军营而杀贼,虎穴深探;夺父尸以还山,龙潭妥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陇上携锄,可并庞公之偶。”时异其人,钞录五言古、七言绝二章。来远兄没,毕诗遍索不得矣。存此旧录,聊以见其生平。[第二则][14]下册,563这个系统涉及各方面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带标志性的是单名“著”,表字“韬文”。
第三个可称“ 《织楚集》系统”。正如《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所著录,《织楚集》及其《余稿》各一卷,现今还有一种乾隆周秉鉴易安书屋钞本流传于世,收藏在南京图书馆。该钞本笔者目前尚未获读,但从周秉鉴等人合辑的一种镇级诗歌总集《甫里逸诗》可以了解到一部分情况。“甫里”原属江苏苏州府长洲县(部分曾析为元和县),今为甪直镇。《甫里逸诗》据卷首《征甫里逸诗启》、卷末《后序》等②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a-b页、第1a-2b页。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年6月11日。,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至五十八年“癸丑”(1793),分为上、下两卷。其卷上所附“闺秀”内,即有毕朗《织楚集》,所录诗歌共计三十三题七十八首;虽然很可能只是一个选本,但好在卷首、卷末各有两篇序跋,总体框架应该是完整的。
《甫里逸诗》本《织楚集》,卷首两篇序言,标题依次作《织楚集序》《序》,署款分别作:“时在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季冬上浣,古吴伏龙山樵殷铭警斋撰。”“岁在康熙丙辰[十五年,1676]桂月,练川湄浦惕庵主人苏瀜一宗滨氏撰。”①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2b页、第5a页。“苏瀜一”的“一”字疑是衍文。卷末两篇跋文,标题依次作《跋》《又》,署款分别作:“丙申[顺治十三年,1656]献岁人日,书于梅花旧馆。”“时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春日,叔其脉氏名景维识。”②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9b页、第20b页。这看起来作者似乎是同一个人,但正文提及毕朗的丈夫,后者称“吾家阿咸”即侄子,自然与“叔”对应,而前者却称“余甥”即外甥,则对应的应该是舅父,不过其姓名很可能被遗漏了。
《甫里逸诗》关于《织楚集》的作者,只在全书卷首的“甫里逸诗上卷姓氏目录”中出现一次姓名“毕朗”③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a页。,此外没有再添加小传。但《织楚集》四篇序跋,泛称“毕氏”之类者毋论,卷首第二篇苏瀜序一再称之为“昭文”,可见这确实是毕朗的表字。又卷首第一篇殷铭序、卷末第一篇佚名跋,分别说毕朗出自“天都甲族”“新安巨族”④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a页、第18b页。——这里的“天都”和“新安”都是安徽歙县的别称,也就是毕朗的原籍。
毕朗的丈夫,姓王之外,有关序跋以及毕朗诸多诗歌标题都称之为“圣开”。按照古人的称谓习惯,这正如毕朗字“昭文”一样,“圣开”也一定是他的表字,而其名不详。这样严格说起来,我们也只能像前引《明练音续集》一样把他叫作“王某”,必要的时候再加括注“字圣开”。他的原籍是否为苏州府的昆山县,或者具体移居过哪些地方,在目前这个《织楚集》内看不到明确的记载。不过,毕朗有《送圣开归吴门》一诗⑤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6a页。——这个“吴门”是苏州的别称,则至少大范围不会错。又卷末该佚名跋,曾经叙及“吾平洛,鄙乡也……而王子以为可寄一枝”⑥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9b页。;毕朗的诗歌,也一再写到“平洛”。这个“平洛”,是昆山县——雍正三年乙巳(1725)部分曾析为新阳县(两县同城而治)——朱塘乡的一个村名⑦可见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乡都图圩村镇·二》“新阳县”“五都”“藏区(四保)”“一图”“平洛村”,光绪江苏书局刻本,第134a页。可见“中国数字方志库”网站,网址:http://10.15.61.5,2022年6月11日。。而《明练音续集》所说一度“寄居”的“邑南熊氏村”,则自然属于苏州相邻太仓州嘉定县的范围。苏瀜序提到毕朗曾经“和余家《湄浦村居》韵”⑧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3b页。,说明她在嘉定还参加过苏瀜及其从兄苏渊组织的诗人结社活动⑨参见拙著《清诗考证续编》第二辑之二十二《清代诗人结社丛考》第五条“石佛庵诗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下册第822-826页。。
毕朗的父亲是一个武官,最终战死。这在有关序跋和毕朗诗歌中,都一再写到过,可以确信无疑。但其为官战死之地,应该是在湖南、湖北一带。例如殷铭序说他“分阃三湘,总师全楚”⑩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b页。,苏瀜序说毕朗“幼年出入乃翁戎帐之下,督兵荆襄之域”⑪⑪ 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4b页。⑫ 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6a页。;毕朗《夜拣书,得家大人〈长兵五千言〉刻本,有感》一诗,颈联亦云:“心事漫随湘水去,功名曾得楚人传。”⑫⑪ 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4b页。⑫ 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6a页。即如《织楚集》的书名,据苏瀜序介绍,除了字面上借用南朝沈约《郊居赋》“织宿楚以成门”云云以外,还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而这个“楚”字,很可能就同时关合毕朗父亲的事迹。后来正如佚名跋所说,毕朗“常从尊人宦游,之楚之浙”,其丈夫王某也是由于“善[尝]历江汉诸胜,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挈其家涉江越山而东抵故里”的①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9a页。。
以上三个系统,因为第三个还有《织楚集》其书作为依据,所以总体上应该最值得相信。
由此倒过来看第一个系统的《明练音续集》,其他毋论,至少称毕朗为“明季宫人,鼎革后流落燕市”,这就明显属于错误。奇怪的是,据前及卷首编者《引》等等,可以知道王辅铭乃是苏瀜的外孙,《明练音续集》也正是在苏瀜“所辑”的基础上“而增补之”的,前后“相去不五十年”[13]301,然而关于毕朗的介绍,却与《织楚集》苏瀜序大相径庭。此外,前引毕朗该小传,最末曾经提到过《织楚集》;其所录五题六首诗歌,即在《甫里逸诗》本《织楚集》内也大都能够看到对应的题目,只不过正文文字颇多出入。这样看起来,王辅铭当时一方面确实有可能读到过《织楚集》,另一方面即使读到过也明显会是另外的一种钞本——至少这篇苏瀜序,很可能就没有保存,不然王辅铭应该会特别重视。不过,后来嘉定地方的相关文献,所见基本上都是沿袭《明练音续集》的说法。
再说第二个系统的《清诗别裁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毕朗杀敌人、夺父尸的这段事迹,依据大概主要就是所录五言古诗《纪事》“吾父矢报国,战死于蓟丘”云云。这里的敌人,诗歌只是泛言“贼”。沈德潜说是“流贼”,则指定为农民起义军。而另外不少读者,特别在其内心,却认为指清军。甚至像嘉庆前后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三“国朝诗别裁集”条,还进一步具体到所谓“崇德癸未[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饶余亲王伐明,自蓟州入边”云云②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2页。“蓟州”或误作“苏州”,盖由“苏”字繁体与“蓟”字相近所致。。
沈德潜所录毕朗诗歌共两首,据说原来“见于家来远兄处”。这里的“来远”,应该也是其兄沈某的表字,而名讳不详。沈某卒后,“毕诗遍索不得”,这就变成死无对证了。不过,该处录有序言中的三联骈体文字——这正常应该出自《织楚集》卷首第一篇殷铭序,只是《甫里逸诗》本此序,后面两联不见,前一联“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胎弓五石能开”作“芙蓉剑百步取人,梨花枪八面无敌”③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2a页。。同时,《织楚集》卷首第二篇苏瀜序,最末说:
至于昭文幼年出入乃翁戎帐之下,督兵荆襄之域,上马横槊,下马能作露布,如古传修期者,以柔婉女子而能为烈丈夫行,则自有传之者矣,又何必缀于简端?④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4b-5a页。傅永字修期,北朝人。又卷末第一篇佚名跋,也说:
余甥王圣开之妇毕氏……诸父皆掇巍科,尊人为参军,必发愤为烈丈夫事。⑤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8b-19a页。
这两处都提到毕朗的“烈丈夫”之事,但又都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似乎其所针对的也确实是清军。联想到《清诗别裁集》一书,以“贰臣”钱谦益冠首,被乾隆皇帝当作借口,引发大规模的“文字狱”;《织楚集》流传到周秉鉴这个时候,殷铭序原有的“入军营而杀贼,虎穴深探;夺父尸以还山,龙潭妥葬”之类或删或改,这应该不足为奇。
毕朗《纪事》该诗,《甫里逸诗》本《织楚集》内未见。属于这个系统的道光年间张潜之、潘道根合辑《国朝昆山诗存》,卷三十“闺秀”第一家毕朗⑥张潜之、潘道根《国朝昆山诗存》,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读易楼刻本,第1a-5a页。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年6月11日。,也没有选录这首诗。不知道足本《织楚集》内,是否有收。不过,前及《织楚集》卷末第二篇王景维跋,开头就说:“此吾家阿咸圣开妇所制也,亦止录其归侄时新裁也。”⑦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20a页。所以,即使足本《织楚集》同样不收该诗,也不能证明该诗非毕朗所作。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地点“蓟丘”,与前面所说的楚地不合,不知是否故作狡狯(不考虑错别字的可能),有意暗示敌人系清军。而如果确实发生在楚地,那么其时间应该是在清军入关之后的顺治初年。《清诗别裁集》所说“时二十岁”无法用来推算毕朗的年龄,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个“时”实际上根本不得而知。
但是,《清诗别裁集》称毕朗字“韬文”,这从其前后另两个系统来看,肯定属于错误。其所谓“韬文诗稿”,显然也只是普通的叙述之语,而不是真正的书名。由此类推,其称毕朗单名“著”,同样有可能系由前及《织楚集》卷末第一篇佚名跋“ 《织楚集》者,余甥王圣开之妇毕氏所著也”之类牵连而致误①周秉鉴等《甫里逸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易安书屋木活字本,第18b页。。《国朝昆山诗存》毕朗小传最末,甚至明确指出:“长洲沈德潜《别裁集》……讹‘朗’为‘著’,则传闻之误也。”②张潜之、潘道根《国朝昆山诗存》,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读易楼刻本,第1b页。至少与《织楚集》这个系统相比,它只有本身这一个孤证而缺乏“毕诗”的支持,自然也就不如《织楚集》系统可信。
然而,由于《清诗别裁集》其书的巨大影响,这个系统的势力却最为强大,相应地衍生出来的各种错误也最多。例如道光年间恽珠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第四家据《清诗别裁集》选录“毕著”该两首诗歌,所附诗话说:
沈来远序其诗稿,有:“梨花枪万人无敌……”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③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红香馆刻本,第2b页。可见“明清妇女著作”网站,网址: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2022年6月11日。这就明显误读了前引《清诗别裁集》的第二则诗话,把沈某当作了诗稿该序言的作者。又如光绪年间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第二则将《清诗别裁集》有关内容敷演成诗话“歙县毕韬文著,随父宦游蓟丘,父与流贼战死”云云,说:“余读其传而慕之(传为沈来远作)。”[15]这是误把前引《清诗别裁集》的第一则诗话,当作了沈德潜之兄撰写的“毕著”传记。
另外还曾见一种格外复杂的类型。道光《昆(山)新(阳)两县志》卷三十四《列女·四》“才媛·国朝”第三人本传记载:
王氏名昭齐,能诗,年二十五守志。有《织楚集》五百余首,皆自述所遇,音节酸楚。⑤道光《昆(山)新(阳)两县志》,道光六年丙戌(1826)刻本,第22b页。可见“中国数字方志库”网站,网址:http://10.15.61.5,2022年6月 11日。
这篇传记孤立来看,只能猜测毕朗《织楚集》有王昭齐同名著作。但发展到光绪《昆(山)新(阳)两县续修合志》卷四十一《列女·六》“才媛·国朝”,在其后增加第四人本传:“毕昭文……遇昆山王某……著有《织楚集》。”⑥光绪《昆(山)新(阳)两县续修合志》,光绪六年庚辰(1880)敦善堂刻本,第36b页。可见“中国数字方志库”网站,网址:http://10.15.61.5,2022年6月 11日。这样放在一起,就猛然想到,这个所谓“王昭齐”,很有可能也是毕朗的衍生者——其姓“王”,源于“王某”;“昭齐”的“齐”字,则是“文”字的形近之误。至于“年二十五守志”,那当然属于“传闻之误”。
不过,昆(山)新(阳)两县合志系列的这个错误,在前述关于毕朗的三个系统中,应该归于第一个《明练音续集》系统。而像咸丰年间黄秩模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卷四十七第一家与第二家分别选录“毕昭文”与“毕著”的诗歌⑦可见付琼先生《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册第2213-2214页。,则是将第一、第二这两个系统同时放到了一起,误以为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物。
类似三个系统相关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涉及的著作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这几种。即如地方志,除了昆山的以外,就还有嘉定、苏州以及南京地区①例如误作“江宁王圣开妻”或“金陵布衣王圣开室”之类,具体出处从略。,歙县,乃至河北一带的蓟县等等。假如要把这些著作逐种梳理过来,那将需要写很长很长的篇幅,而且还难免挂一漏万,写不完整。
同游者为:茅山月华道人、吴期远,北平何汇吉,会稽金襄、郁文,白岳毕文。时康熙丁丑[三十六年,1697]四月二日也。[17]396
又“诗前集”卷三同年所作,有一首《月沼集会稽金衣田(襄)、郁周尚(文),徽州毕文(晓),效李义山,以鸟兽虫鱼成篇,次文韵》[17]554。这里所说的毕晓,字文;并且“白岳”为齐云山,借指所在地安徽休宁县或者更大范围的徽州府,而府治就在歙县,所以正巧还与毕朗同乡。而既然前述《清诗别裁集》的“韬文”,后世可以演化为“文”,那么倒过来看,这个真正的“文”,也完全有可能引发沈德潜的牵连而致误。
最后再回归到《提要》本条。其所著录的是第三个系统的《织楚集》,却以第一个系统的《明练音续集》小传作为作者介绍的主要依据,这正是错误的原因所在。
附带关于《提要》同卷稍前以及《清人别集总目》共同著录的毕汝霖[1]第一册,381,作者都没有介绍。而其诗集《空香亭集》一卷,以及所附《舫园十二首》《孤馆十韵》各一卷②毕汝霖《空香亭集》,清初刻本。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年6月11日。,内文均署“天都毕汝霖玄牧著”。这就至少可以知道,毕汝霖字玄牧,同样也是歙县人。看来,清初歙县以及徽州毕氏,的确称得上“天都甲族”或曰“新安巨族”。
此外,《提要》毕汝霖该条,曾经提到其诗集有“刘赓、吴自携评”,于是借助“吴赓为江西南昌人,顺治间举人”来大致推测毕汝霖的生活时代。这个方法非常合理,但所谓“吴赓”,本来应该是“刘赓”。《提要》不小心从“刘赓、吴自携”两人那里各取了一个字过来,这恰巧可以佐证我们上文关于“王昭齐”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