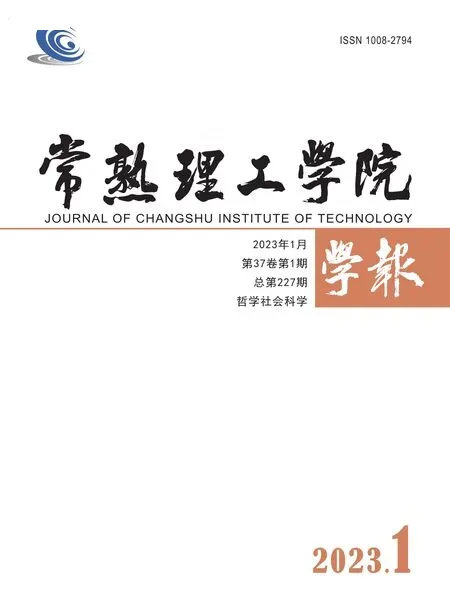杨泗孙致翁同爵翁同龢兄弟信札八通考释
2023-04-07李文君
李文君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100009)
故宫博物院藏有杨泗孙写给翁同爵与翁同龢兄弟的信札8通,系1958年收购入藏,此前从未对外刊布①故宫博物院藏“杨泗孙书札册”,文物号:新00086436。除本文所刊8通信札之外,故宫藏“杨泗孙书札册”内还有杨泗孙作于北京的短札4通,因与杨氏回乡无关,故未论及,特此说明。。这些信札,作于咸丰三年至四年(1853-1854),均是杨泗孙在返乡途中或回到常熟之后写给在京的翁氏兄弟的。这些信札为我们了解咸丰初年常熟籍京官的一般情况,了解在太平军北伐大背景下从通州到江南运河沿途的情况,太平军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以常熟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发生的各方面的变化,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本文以写信时间为序,对其逐一进行考释,以惠学林。
一、两对兄弟
写信人杨泗孙(1823-1889),字钟鲁,号滨石,江苏常熟恬庄(今属张家港)人,杨希钰次子,咸丰二年(1852)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官太常寺少卿。后因病乞休,家居十六载而卒[1]10。杨泗孙的兄长杨沂孙(1813-1881),字子舆,号咏春、濠叟,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安徽凤阳知府。杨沂孙精于书法,以篆书名擅天下。
收信人翁同爵(1814-1877),字侠君,号玉甫,常熟人,翁心存次子,官至湖北巡抚。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声甫、松禅,翁心存幼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晚清名臣,先后在弘德殿与毓庆宫教授同治帝与光绪帝读书。
杨家与翁家均是科第世家。清中叶以后,在常熟形成了不少累世中进士的仕宦之家,有“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的说法。各家族之间,又通过师生与联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师生方面,道光二十八年,已中举的杨泗孙家居读书,“从学于翁心存,晨夕过从,相与敦品励志”[1]37。此时,翁心存为母守制,在籍闲居。因有此重师生渊源,在本文所述信札中,杨泗孙径以“夫子”称呼翁心存,以“师母”称呼翁心存之妻许氏。联姻方面,翁同爵之妻杨氏,为杨泗孙二伯父杨希铨之女[2]14,故杨泗孙在信中以“姊丈”称呼翁同爵。不过,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夫人就病故了。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泗孙与翁同龢一起离开常熟,结伴赶赴京城,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十二月二十六日抵京后,杨氏就在翁宅下榻[1]40。道光三十年会试,杨泗孙落榜,翁心存一度将其留在府中,襄助笔墨文字,后又让翁同爵之子翁曾荣与翁曾翰(杨氏的两个外甥)从学于杨泗孙[1]41。咸丰二年开恩科,杨泗孙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六月,在庶吉士散馆之后,离家近四年的杨泗孙请假回常熟省亲。回乡途中及在常熟居家期间,杨泗孙给在京的翁氏兄弟写了这8通信札。8通信札中,写给翁同爵的有3通,翁同龢的1通,写给兄弟二人一起观看的有4通。在写给翁同爵的信中,杨泗孙也频繁问候翁同龢,基本上将翁家兄弟二人同等对待。杨、翁两家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杨氏在信中无所不谈,无形中使得信札的史料价值得到提升。
目前学界还未见有杨泗孙致翁同爵信札披露,所见杨泗孙致翁同龢信札,也仅有作于光绪十四年除夕的1通。在这通信札中,退居常熟的杨泗孙给在京的翁同龢拜年之余,还为无锡知县吴观乐说项[3],光绪十五年正月廿六日翁同龢收到此信[4]。对杨、翁两家关系的论述,谢俊美的《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一书中,论述了翁同龢与杨泗孙胜似亲兄弟般的关系[5]。张剑的《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一书,亦涉及杨家与翁家的关系。朱新华、黄志刚编著的《杨沂孙杨泗孙年谱》一书,大量利用了《翁心存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的材料。李文君的《翁同龢与〈宝慈话旧图〉》一文[6],部分提及了杨氏兄弟与翁氏兄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学界并无对杨、翁关系或杨泗孙本人的专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信札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信札考释
杨泗孙的这8通信札,内容详尽,多数有时间落款,为信札的考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为醒目起见,据信札的主要内容,整理者为每通信札拟定了一个小标题。
(一)通州荐仆
握别后于七下钟抵通登舟,舟极宽大,今日未行,明日必可解缆。前路据出通利,但舟大行迟,抵家必在中秋时候。所幸同舟诸子谈论娓娓,不寂寞耳。玉甫五兄竟未能言别,殊出意外。早知此刻尚在潞河,惜不稍缓数刻也。怅怅!沈荣人尚勤妥,还望推爱,谋一噉饭之所,至感至感!倚舷泐请叔平六兄世大人箸安,愚兄杨泗孙顿首。
玉甫姊丈同此,不另札。仲渊昆仲及两甥均此道意。席桌围一条,存零用物件,未订箱内,筹甥可取用也。此信于咸丰三年(1853)六月初五日作于通州,主要是杨泗孙到达通州(潞河)之后,向翁同龢推荐仆人沈荣。信尾有大字“送南横街翁六少老爷”,南横街在京城宣武门外,翁宅位于南横街头条胡同,咸丰三年四月十六日至十七日,翁氏正式迁居此处[7]971-972。据《翁心存日记》,咸丰三年六月初五日:“中鲁今日赴潞回南矣,来辞行,予尚未回,匆匆不及待而去”[7]986,可知杨泗孙离开京城赶赴潞河(通州),是在六月初五日。他临行前到南横街翁宅辞行时,只见到了翁同龢,当日赶到通州后,晚间在船上草此短札,让仆人沈荣送到南横街,且一并将沈荣推荐给翁同龢,请其为沈荣谋一差事。翁心存共有三子六孙,长子同书,堂兄弟大排行第三;次子同爵,大排行第五,故杨泗孙称其为五兄;幼子同龢,大排行第六,故杨氏称其为六兄(六棣)。翁同书有子三人,长子翁曾文(绂卿,堂兄弟大排行第一),次子曾源(仲渊,行二),三子曾桂(小山,行五);翁同爵有子三人,长子曾纯(吉卿,行三),次子曾荣(鹿卿,行四),三子曾翰(小名筹儿,行六,翁同龢嗣子)。仲渊昆仲,指翁曾源与翁曾桂,二人本随父母在贵州学政任所,咸丰三年翁同书奉调帮办扬州军务之后,自己只身前往扬州,其妻钱氏率曾源、曾桂于四月二十六日进京,随翁心存夫妇居住[7]977。两甥,指翁曾荣与翁曾翰(下文称“筹甥”“六甥”),均为杨泗孙堂姐杨夫人所出,当时亦随父翁同爵在京居住。
(二)将抵德州
玉甫世五兄姊丈大人阁下:匆匆出都,竟未握别,怅何如之。抵通后有致叔平棣书,令沈荣持送,想早入览。嗣于初九解维,十一抵津门。知丰北新工漫口三十余丈,青、徐之间恐有他变,姑至济宁再探消息。因舟子耽搁,迟至十五日始过关前进。适许星台昆仲先一日到津,遂约同行。许氏共八舟,有李春生及刑部韩某家眷船附焉。十八日将至青县,李春生专足来,因丰工漫口之故,嘱许氏北旋,星台不以为然。二十日过沧州,周莲士(宗濂)在此养疴已四日,是日稍愈,闻欲前进。昨据舟人云,次日即病故,仍回沧州矣。恨过沧时,未及一问其何疾也。卫河水势甚平,两岸麦子青青,可徵丰稔,沿途亦甚静谧。弟等身体俱健,足慰锦注。家信一函,祈附便寄归为要(若无速便,乞加封由局寄归,尤感),容再肃谢。不尽所言,即请升安,弟杨泗孙顿首。廿五日将至德州五里许,大雨如注,草草不庄。
朗甫昆仲、惪生均嘱笔道候。夫子、师母大人前叩名请安;叔平棣台均此不另;宝生、汴生前辈及宝翁、稚侯诸君并道谒怀。
此信于咸丰三年(1853)六月廿五日作于德州,主要是通报从通州到德州的行程。据信可知,杨泗孙六月初九日离开通州,十一日到达天津,十八日至青县,二十日到沧州,二十五日抵达德州。丰北漫口,指咸丰元年八月,黄河在江苏丰县决口,淹没了丰县、沛县、邳州、铜山等处大量土地,济宁以南的运河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许星台,指许应鑅,广东番禺人,咸丰三年进士。其堂弟许应骙,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李春生,指李仲良,广东从化人,咸丰中叶任四川夔州知府[7]1131,同治初相继任常州、镇江等处知府。刑部韩某,似指刑部奉天司主事韩锦云,字紫东,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道光二十年进士[8]。周宗濂,字廉生,号莲士,浙江归安(今湖州)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六月初五日[9],卒于沧州时,得年55岁。
朗甫,指赵曾向,字朗甫,号啬庵,江苏阳湖(今常州)人,赵忠弼之子,赵翼曾孙,咸丰二年进士,杨泗孙的会试同年。另外,杨沂孙的原配赵夫人,为赵起之女,赵翼的曾孙女,是赵曾向的堂姐[1]4。赵曾向精于医术,在京期间,曾几次为杨泗孙[7]943、翁同龢[7]968等人把脉问诊。赵曾向有兄弟六人,他行四,还有两位弟弟赵曾逵(厚甫,同治初曾任浙江慈溪知县)与赵曾采[10]649,不知与其同行的是哪一位。据赵曾向之子赵徹诒等所撰《啬庵府君年状》记载:“咸丰三年四月散馆,一等六名,授职编修”,“散馆后即日乞假归省,时贼氛(北伐太平军)阑及山东,陷直隶,天津府南北道梗”,赵曾向“冒险耑征,至于八月中旬始达,而大母吕淑人已先十日弃养”[10]664-665。此即本文所引第四通信札中提及的“(八月)十二日抵常州,朗甫昆仲已丁内艰。”惪生,指陈亮畴,江苏武进人,咸丰三年进士,此次与杨泗孙等一并结伴回乡,但行至山东德州时,留于其母舅吕公处,未再南下。宝生,指庞钟璐,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庞钟璐的妹妹嫁给杨泗孙之弟杨汝孙为妻[2]20。汴生,指邵亨豫,常熟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宝翁,指张璐,字宝卿,号芝佩(后文称其为“宝卿姻世丈”“芝翁”),常熟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时任刑部主事。稚侯,指葛桐衔,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咸丰三年进士,后官至金华知府。道光二十七年会试落第后,杨沂孙、杨泗孙兄弟曾与葛桐衔结伴,一起从京城返回江南[1]34。道光二十八年四月,葛桐衔与张修府从嘉定赶赴常熟,专门拜会庞钟璐、杨沂孙等人[1]36-37。
(三)舟过济宁
玉甫五兄姊丈世大人足下:六月廿五日抵德州,曾布一缄,并托寄家言一函,想可速达。廿六日陈惪生为其母舅吕公谆留,过夏再行。弟等偕许星台昆仲即日解缆,一路顺平,于昨安抵济宁。适慧秋谷制军带兵二千余名在济,明日即由水路折回扬州。弟等船只,均拟跟帮南下。近日南阳湖一带,颇不安静,乘此机会,定可无虞。抵杨庄后,仍当沿途探听,断不冒昧,致廑绮注也。所过直隶、山东各处,年岁均属丰稔,人情亦复安帖。到济(宁)则灾民乘舟迁徙者纷纷矣。昨闻镇江贼南窜丹阳,经绅民击退,不知近日苏、常一带又复如何。舟中闷闷,惟棋酒可以解忧,大约中秋节前才可抵里。如寄府报,或可将此信略言之。都中光景,想已安顿。宝生、汴生前辈,宝翁、湘翁、稚侯、蓉洲丈诸君,均乞致声。即请升安不具,弟杨泗孙顿首。七月十二日。
夫子/师母大人前请安,叔平均此不另,仲渊昆仲及两甥均道念。朗甫昆仲嘱笔道候。
此信于咸丰三年(1853)七月十二日作于济宁,主要述说准备随慧成所部从济宁南下的行程。慧秋谷,指慧成,满洲镶黄旗人,戴佳氏,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咸丰二年十二月,署四川总督[7]931。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朝廷命行抵陕西的慧成折回,“驰往江南淮扬、徐州一带,会同(漕运总督)杨殿邦防剿”[7]954。为安全起见,杨泗孙等的船只,随慧成所部,从济宁南下。南阳湖,在济宁之南,微山湖最北边的一部分。杨庄,在淮安,黄河与运河的交汇之地。湘翁,指姚福增,号湘坡,常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蓉洲,指王宪成,常熟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时在刑部任职。
(四)安抵常熟
玉甫吾兄/叔平吾弟世大人阁下:别来已及四月,系念至深。德州途中,便致一函,谅经达览。舟行濡滞,七月十一日始抵济宁。湖中不靖,拟由此登陆,而车辆极少。适慧秋谷制军由豫折回扬州,刚至济宁,将于十四日督兵从水路南下,遂跟帮同行。又以飓风大作,击缆于独山下者十余天,波涛之险不必言,其免于萑苻之警者,则慧帅之力也。八月初四抵杨庄,初五渡黄,买舟南下。初八日出高邮湖,至邵伯镇,行三里至六闸,绕东行,过仙女庙、宜陵、白塔河大桥。十一日至中闸口三家营,出江过圌山关,约行八九十里至小河口(在孟河东十五里),进口行四十五至奔牛。此路常州较近,所雇邵伯划子夙谙此处一带,实不如走通州福山之稳妥也。十二日抵常州,朗甫昆仲已丁内艰。弟因亲友俱徙乡间,未曾上岸。又闻上海、嘉定滋事之信,急欲归省,未及觅仆,遂坐原船至无锡,复易舟而抵里,刚中秋前一日也。此行两月有余,身安而心危,亦生平未尝之境,幸一路无恙,家中安善,堪慰遥注耳。
府中自吉卿失偶后,绂卿继逝,闻之不甚骇异。绂卿才名学问,卓越流辈,顾不令竟其志,是亦有气数存焉。吉卿支持门户,实非易易。意欲五兄暂归,未知何如?所寄吉卿大钱廿千,已交楚矣。贼匪蔓延数省,而上海、嘉定各处奸民,乘间窃发。刻下嘉定土寇已除,而上海尚未克复。闽广匪徒,实为始事之人,首逆即闽人李少卿也。夷人在城之货,俱移至城外。夷馆守御甚严,贼不敢犯,夷人有与官兵夹攻之说,实则持两端以观望。近日许抚亲督兵攻剿,尚无好音。撮尔如此,大城可知矣。粤东许星台昆仲一路同行,在袁江分手,渠后由通渡江,为买舟送往余杭。吕星翁闻已到毗陵,而潘补之乔梓及东墅、古廉眷口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药房前辈音信绝少,南下时离大营不远,甚欲进谒,藉悉近事。而同人归心如箭,竟不如愿,歉甚!近知晋擢少詹,益加委任,而简书可畏,维持綦难,不知三城何日克复耳。寄存箱件,费神安顿。如有妥便,望将皮衣箱一只附寄,寄费酌之可也。此肃,即请近安。仲远(渊)昆仲及两甥均问文祉。湘坡姻伯,蓉洲表叔,汴生、宝生两前辈,宝卿姻世丈均此,不另致札矣。愚弟/兄杨泗孙顿首,九月初二日。
此信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初二日作于常熟,主要是通报自济宁到常熟沿途的情形及常熟地区的最新局势。湖中不靖,指济宁以南的微山湖等处,流民众多,社会治安恶化。独山,在今山东微山县独山湖中。萑苻,指水边的盗贼。邵伯镇、六闸、仙女庙、宜陵、白塔河大桥,都在今扬州市江都区境内;中闸口三家营,在芒稻河与长江交汇处,今江都区中闸乡三江营村。因瓜洲与镇江被太平军控制,杨泗孙一行过江时未选择传统的运河渡口,而是选择了从偏东的芒稻河口的三家营渡江。过长江之后,经圌山(今属镇江市京口区,在三家营的对岸)、孟河、奔牛等处,到达赵曾向的家乡常州。经过切身体验,杨泗孙认为:从江都渡江,不如在北岸沿江继续东行,从通州(今南通)渡江,直趋常熟所属的福山,这样更加安全便捷。从六月初五日离开京城,到八月十四日回到常熟,承平时期一个月左右的旅程,杨泗孙一行耗时近七十天才走完。
上海、嘉定滋事,指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上海与嘉定县城。后在江苏巡抚许乃钊(许抚)的主持下,清军及时收复了嘉定。小刀会中有不少福建、广东一带的天地会成员。李少卿,指李文炳,原名绍熙,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天地会成员,早年在上海经商,小刀会起义首领之一。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洋人将县城内的货物转移至县城以北的租界区(夷馆),并加强了租界的戒备,切断了县城内义军的粮米与军火供应路线。洋人先是在清政府与小刀会之间保持中立(持两端以观望),清政府出让海关等部门的利益后,英美等国转而支持清廷。咸丰四年底,在英法美三国租界驻军的支持下,清军攻克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最终失败。
当时,翁氏一家,翁心存夫妇带翁同书之妻、翁同爵、翁同龢夫妇及翁曾源等在京居住,翁同书在扬州江北大营,只有翁同书长子翁曾文(绂卿)与翁同爵长子翁曾纯(吉卿)留在家乡常熟。本年五月,先是翁曾纯之妻病故,到七月,翁曾文亦病故。《翁心存日记》咸丰三年六月三十日记载:“得曾文、曾纯六月初八日书,知曾纯之妇侯氏于五月廿八日未刻产男不育,六月四日巳刻,曾纯之妇忽中暑,延医服药,竟不及,即于未刻夭逝,年甫二十。”[7]991八月十八日又记载:“退直后见五、六两儿(同爵、同龢)来,面皆改色,讶之,不肯遽说也。坐定良久,乃云昨得七月十九日家书,知曾文于七月十四日申时病卒,闻之痛绝。徐取云樵(翁同福,翁心存之兄翁人镜次子)及曾纯书阅之,知于六月廿六日陡患伤寒症,为庸医所误,全用凉药,遂至不起,伤哉。”[7]1001二十四岁的翁曾文去世之后,常熟仅剩年方二十岁的翁曾纯一人支持门户,杨泗孙建议翁同爵暂时回乡,料理家事。不过,翁同爵自己并未返回,而是在咸丰九年八月派次子翁曾荣回乡协助兄长曾纯[7]1457。少詹,咸丰三年,卸任贵州学政,准备回京复命的翁同书北上行至成都,接到驰赴扬州军营,帮办琦善军务的旨意。翁同书让随行的眷属继续回京,自己只身赴任,于“五月初七日驰抵扬州军营”[7]986。当年三月,朝廷擢翁同书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寻转侍读学士,迁詹事府少詹事[7]1859-1860。三城,指南京、镇江、扬州三城,当时均为太平军占领。
袁江,指淮安清江浦,黄淮交汇之处,运河上的重要节点。许应鑅一行,在清江浦与杨泗孙分手,从通州(南通)过江,取道杭州南下。吕星翁,指吕倌孙,江苏阳湖(今常州)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咸丰三年四月七日,放广东潮州府遗缺[7]968,赴任途中,先回家乡毗陵(常州)探望。潘补之,指潘希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潘世璜次子,道光十五年举人;其长子潘介繁,咸丰二年顺天府北闱举人[7]913。古廉,指李清凤,江苏新阳(今属昆山)人,道光十六年进士。东墅,指张修府,嘉定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
(五)常熟近况
前信封就,为寄书人所误,嗣因买櫂东西各乡,回城后始知前信耽搁。日来上海匪徒据城固守不下,官兵颇有损伤,如能即日扫平,乃于运道无碍。征收上下忙钱粮,已设柜于邑廨公局,以捐抵赋,减价限催,黜胥吏而以绅董主其役,苏府皆然,亦一变局也。白茆河工议叙,黄印翁请知州升衔(嘱致代为周方通信时,望及之),张约翁请同知衔,闻已奏请议叙,由工部咨吏部查核,想无驳轻之举,而吏部书吏往往因部费不到,遂遭翻驳,殊不足以鼓励绅董。当此时势,尤所不宜。余容再函,不尽所言,泗孙又启,九月廿八日。
此信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廿八日作于常熟,与九月初二日的信札一同寄出,内容也紧接初二日信札,主要谈常熟的社会情况。上下忙,当时的田赋分两季征收,征收夏粮的田赋,称为“上忙”,秋粮的田赋,称为“下忙”。因受到太平军的威胁,为提高效率,整个苏州地区的钱粮征收,不再重用胥吏,更多的是靠地方绅董来直接张罗。翁曾文的去世,就与以士绅的身份参与常熟事务有关。翁心存在日记中说:“邑中设军需防堵之局,劝捐者成人鲜,遂令年少亦与之,烈日奔波,积受暑热,竟至夭折,可恨也。”[7]1001白茆河工,指疏浚白茆河的工程,白茆河是长江支流,位于常熟东部,是当地的主要灌溉水源,对防止海潮倒灌也有重要的作用。黄印翁,指黄金韶,字子钧,号印山,广西容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时任常熟知县,兼署昭文知县[11]。此次叙功之后,升任海州(今连云港)知州[7]1022。张约翁,指张元龄,字介眉,号约轩,常熟人,藏书家张大镛子,官湖北郧阳府通判[1]28-29,张元龄也参与了白茆河工,他卒于咸丰四年三月廿九日[1]47。河工归工部主管,议叙之事归吏部,吏部办事人员(书吏)习惯索取部费(陋规、好处费)才办事,杨泗孙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面对太平军与小刀会的威胁,朝廷需要地方绅士的大力支持,吏部不应该再借故刁难议叙的绅董,使他们寒心。
(六)江南局势
玉甫姊丈吾兄世大人阁下:九月杪曾肃寸函(内有呈夫子大人信函及致宝翁信),由天顺信局寄京,谅早得邀青鉴。比惟从事贤劳,合第康吉为颂。昨晤吉卿甥,刚接家书,敬悉老夫子大人兼办粮台,诸事丛集,几无片刻之暇。兄及叔平棣台趋公之余,更相入城侍奉,想见近时景况与晤别时大相悬绝矣。湘坡侍御何以冒险南归,闻之不胜诧异。或因同乡诸君劝阻暂缓行期,则大幸也。家兄已于廿七日起身赴皖,由福山渡江西进。幕友季兰舟同往,人极朴实可靠,但皖江全省摇动,到彼须相机而行耳。家乡因三城未复,上海负隅,四乡奸民并生戎心,吾虞东乡有郑氏之事,西乡则惧如家兄,复遭……。俱已接去。常州巡查甚严,有内地匪人勾结镇江之贼,剋日内应起事,幸早发觉,拿获十余人正法,现已安堵。兹闻吉卿甥即发竹报,草此附寄,祗请侍安。叔平棣台均此,不另。仲远(渊)昆玉并两甥均道意,如弟杨泗孙顿首。十二月朔。
老夫子大人、师母大人前叩名请安。同乡诸公均此不另。
此信于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初一日作于常熟,内容不完整,中间有缺页,主要讲以常熟为主的江南地区的局势。兼办粮台,指为应对北伐的太平军,咸丰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的翁心存设粮台于顺天府署,负责供应京城周边防卫部队的粮台与器械[7]1859。湘坡,指姚福增,此时也拟冒险离京,返回常熟。咸丰五年八月初七日,姚福增卒于常熟,“年未五十,上有老母,可伤也”[7]1059。十一月二十七日,杨沂孙从常熟福山渡江,经南通西赴安徽任职,幕友季兰舟随行。此时的江苏一省,东边有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西边有太平军占据南京、镇江与扬州,且太平军不时从镇江向东边的常州一带渗透。受此影响,常熟地面也不太平,不时有小规模的动乱出现。
(七)恳请销假
玉甫姊丈吾兄/叔平吾棣大人阁下:先后奉到手书,备承拳注,浣薇雒诵,铭佩弗谖。昨敬悉老夫子大人简掌夏官,曷胜忭贺。五兄例应回避,未识签分何部,八面之才,正无所不宜耳。弟以北行乏伴,迟迟至今。兹入郡城,晤伯寅侍读,知须今岁起身入都,为明岁试差计。因约同行,较有照应,家严慈亦稍放心。惟伯寅行期尚须略缓,计腊月二十前弟等未必能赶到。兼以豺狼未靖,或恐有阻,绕道前行必需时日,敬恳五兄或六棣印结代为销假,以在至好,用敢渎陈。伯寅亦必奉恳,云:“出月初旬,当有专函到都,嘱先致意。”家兄在庐,一切顺平。聚首匪遥,诸不赘及。俟行期择定,再当泐闻。恐后信或有浮沉,先此奉布,伏祈垂照,祗请升安。世愚弟/兄杨泗孙顿首。十月廿七日。
老夫子大人暨师母大人尊前,均望叩名请安贺喜,仲渊昆仲、六甥等均候。宝生前辈先为道贺,来札已到,另有覆函也。邵汴生前辈、王蓉丈、张芝翁晤时均致意。
此信于咸丰四年(1854)十月廿七日作于常熟,主要是介绍准备北上情形,并请翁氏兄弟代为销假。老夫子简掌夏官,指咸丰四年九月,翁心存从工部尚书调任兵部尚书(夏官)。不过,当年十一月,翁心存就转任吏部尚书[7]1860。翁同爵当时在兵部武选司任主事,翁心存调任兵部堂官,父子同在一部,翁同爵理应回避,需调往他处任职。从后一信“荣调农部”的记述来看,翁同爵从兵部改派到户部履职。郡城,指常熟所属的苏州府城。伯寅,指潘祖荫。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潘祖荫的祖父潘世恩卒于京师,八月,潘祖荫随父潘曾绶扶送祖父灵柩南还,十月回到苏州,十一月,潘祖荫奉父命返京供职[12],即信中所言的“为试差(乡试考官的选拔)计”。因担心不能在腊月二十日封印之前按期回京,杨泗孙嘱托翁氏兄弟代为办理销假手续。家兄在庐,咸丰三年二月,杨沂孙选授为安徽铜陵知县。杨沂孙到安徽之后,铜陵已被太平军攻陷,后又受邀入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府[1]45-48,当时省城安庆陷落,安徽巡抚移驻庐州办公。
(八)预备进京
玉甫吾兄/叔平吾棣世大人阁下:前月由竹报中附递一函,谅经达览,伏维上侍康娱,第祺绥吉,并知荣调农部,新绩幸宣,奚如忭颂。弟与潘伯寅同年偕行入都,前札已曾述及,兹准定本月二十五日由郡起身,单骑简从,兼程而行,唯恐冰雪之阻,致过销假之期,务恳于封印前代为销假。印结各费并恳垫办妥善,至感。弟去岁请迎亲假系五月廿二日,须呈明否?走馆者及长班应给费否?诸费清神酌定。相见不远,未尽所言,专此泐恳,敬请大安。愚弟/兄杨泗孙顿首,十一月初八日郡寓。
老夫子大人暨师母大人尊前祈叩名请安。甥辈并仲渊昆仲并候。
此信于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初八日作于苏州,主要是通报启程入都日期,并再次请翁氏兄弟代为销假。杨泗孙与潘祖荫一行,定于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从苏州起身。咸丰五年正月初三日,杨泗孙到达京城,同行者除潘祖荫之外,还有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太仓人陆增祥(心农)[7]1007。杨氏回乡,请的是迎亲假,当时,杨泗孙年过三旬,还无子嗣,此次回常熟,纳胡氏为妾[2]191。杨泗孙的假期从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始,到咸丰四年底结束。杨氏在腊月下旬封印前赶不回京城,故请翁氏兄弟代为销假,并请他们代为垫付一年应出的印结费用,并询问应否适当给予走馆者(翰林院办事人员)与长班(办事人员的随从)年敬小费。
三、余论
晚清的常熟,文化昌明,传世文献量极为丰富。但要说系统性的记载,还是首推翁心存与翁同龢父子二人的《日记》。二人的《日记》起于道光五年(1825),止于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连续近80年,对常熟的方方面面均有涉及,且记述颇为详尽,是了解晚清常熟社会无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不过,现存的《翁心存日记》,缺少咸丰三年(1853)九月初五日至咸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内容[7]1005-1006。《翁同龢日记》的系统记载,开始于咸丰八年六月。杨泗孙这些作于咸丰三年到四年之间的信札,正好可补翁氏父子《日记》对常熟记载的某些缺失。如在太平军与小刀会的双重威胁之下,常熟社会呈现出某些新的变化:征收钱粮时“黜胥吏而以绅董主其役”“四乡奸民并生戎心”等等,均是当时常熟社会的真实写照。
咸丰初年,围绕着年龄与官阶俱尊的翁心存其人,常熟籍的京官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联合体的中心人物是翁心存,成员除杨泗孙之外,还有他在信中频致问候的王宪成(蓉洲)、姚福增(湘坡)、张璐(宝翁、芝翁)、邵亨豫(汴生)、庞钟璐(宝生)等人。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紧接着组织了北伐,不但使江南局势紧张,也影响到运河的通畅,南北联系受到一定的干扰,家乡常熟的社会变化情况,时刻牵动着这些京官们的心。在此大背景下,杨泗孙回乡,在某种程度上,也担负着为常熟籍京官探听消息的目的。为此,杨氏信札记述得细致入微,将回乡沿途的见闻与感受以及家乡常熟的最新变化,都及时反馈给在京的同乡。
总的看来,杨泗孙写给翁家兄弟的信札,对我们了解咸丰三四年间从北京到常熟等江南地区运河沿途的社会治安状况、太平天国与小刀会双重威胁之下的苏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以翁心存等为主的常熟籍京官心系家乡的情况等,均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