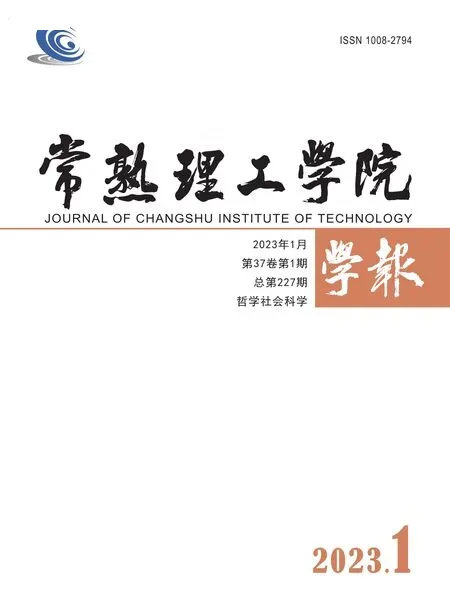赵树理的乌托邦化乡村内部叙事与竹内好的判断
——以《三里湾》为例
2023-04-07刘旭
刘 旭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
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中,乡村一直是文学关注的重点,文学研究中的乡村研究也一直长盛不衰。赵树理文学是乡村文学中独特且重要的一支,对赵树理的重视在共和国七十年历程中始终没减弱过。赵树理的农村想象在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如《三里湾》对于赵树理研究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作品,小说对乡村的描写独具特色,将当时的历史及各种评论和赵树理本人的创作谈做互文性印证,就会发现赵树理的真正立场。赵树理之后有莫言,两人的“互文”之处几乎没被人注意过,但它们对“人类”的文学非常有价值,即莫言虽然表面看从文体和主题都与赵树理相去甚远,但两个作家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对乡村的关注,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有与《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相同的对高度公有化的反思以及对农民的“生存”本身的关注;这还直接导致了两人另一个共同的地方,这是绝大部分被命名为“乡土作家”者所缺乏的:对中国乡村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关注。
竹内好即从这个角度提出了赵树理的“唯一性”:“我认为赵树理恐怕是唯一的一个人了。在这里,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1]74-75竹内好在此非常鲜明地指出了赵树理与“人民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区别。“人民文学”即我们所说的解放区文学,“现代文学”即启蒙影响下的欧化式文学。竹内好在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声誉首先来自他对鲁迅的洞察,他第一个建构了鲁迅的“绝望”系统。而对于几乎与鲁迅毫无相似之处的赵树理,竹内好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使用了“唯一”这样的断语,他看重的是什么呢?——恰恰是鲁迅的反面。如果说,鲁迅代表的是启蒙,那么赵树理代表的是什么呢?
在中国,启蒙的核心即“国民性”问题。“国民性”问题不只是共和国七十年文学的焦点,它还是鲁迅以来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和文学的共同关注点。它一直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直接联系,而且一直被当成中国无法“发展”成现代国家的“内因”。
启蒙体系的存在也造成了相当多的赵树理研究者其实都不真正了解赵树理的乡村理想,他们很容易拿赵树理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不是在说赵树理本人。
实际上,“启蒙元话语”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看似指向精神,实质是经济焦虑的投射,“任何一种估价国民性理论之理论价值的试图,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个理论的前提——民族特性即劣根性——是一种非理性逻辑的假定,它的唯一依据是该民族在经济、政治、物质文明上落后于先进的其他民族”。①杨联芬较早论述到这个问题,她认为“国民性”实际与经济发展无直接关系,是文人在那个时代的臆想。参见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三)》,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只是从“国民性”理论的本身来看,它在今天已是个伪命题,鲁迅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心完全多余,从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来看,“国民性”不但未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相反,它成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民族心理基础——如果鲁迅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精神“现代”的话。②此问题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见本人《想象与现实的悖论:“国民性”阻碍了现代中国的建立吗》,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质言之,很多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就是,启蒙的起点一开始就偏向了。启蒙是精英化且城市化的,这正是启蒙知识分子难以真正为乡村思考的根本原因。人类的权力层和大众层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就是精英和亚精英,精英们正是“启蒙”的传播者和教化行为的实施者。乌托邦的生产是精英化的,赵树理把精英的权力用于思考非精英的问题,是精英退后的思考,即赵树理虽然身处精英的位置,却把乡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看成第一位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赵树理更多地在这句儒家式精英话语的基础上进行文学乌托邦的想象。这个想象,可惜当时即未能被启蒙知识分子接受,反而被当成“反现代派”加以压制。直到今天,赵树理的这种想象实际仍然未被广泛理解。这依旧是启蒙精英的“向西”思维导致的结果。而赵树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是正面的,不是一味地否定,而是扬长避短,积极地继承和发扬,这正关系到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中国文化传统的走向问题。
就是说,一直不被认可的赵树理反而在解放区时代就已经化约了启蒙,建立了一套较符合中国现实的乡村乌托邦系统。
二
《三里湾》是赵树理乌托邦想象的鼎盛,第25章《三张画》里提到老梁画的三张画,即代表着中国新农村发展的三个阶段,象征着中国乡村的现在、明天和未来。三张画第一张是“现在的三里湾”,第二张是“明年的三里湾”,第三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从画的内容上看,第一张是合作化初始的三里湾,第二张是水渠修好后的三里湾,表现的是实现了全水利灌溉后的三里湾,表现出集体力量的强大,因为单独的家庭或某个家族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完成那么大的水利工程,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完成了。重点是第三张画,它应该是当时可以实现的“准共产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张挂在右边,画的是个夏天景色: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器正在锄草……一切情况很像现在的国营农场。[2]302
这一张表现的是很“现代”的公路、汽车、电线杆等,还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集体统一建造的新房、庄稼的大片分区等。其中,庄稼的分区化很重要:“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它意味着在赵树理的想象中,中国农村完全能实现全部机械化作业,类似资本主义下的规模经营。看得出,赵树理的乌托邦想象是以集体为基础的,它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不违背,而且这种乌托邦是非常接近现实的乌托邦,很容易实现,表现出一种“近切”的共产主义想象。这也体现了赵树理以乡村为立场的此在性。
与这个乌托邦相应,赵树理的叙事也独具特色,比如采用了独一无二的乡村内部视点。
一个或几个叙述者对故事的讲述就构成了叙事,而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则构成了叙事视点。赵树理作品的特点即是他的叙事视点一直在乡村内部,这与《暴风骤雨》中党代表的叙事视点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叙事视点等农村外部叙事视点截然不同。赵树理从早期的欧化小说转变为后来的农民化小说,改变的不只是叙事方式,更是作者的思维方式,即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变成农民的思维方式,所以赵树理的作品与同时期的作品相比,并不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857。即使他的作品中有一个外来者(党代表),甚至赵树理本人就是一个外来者,但是赵树理却能将外来者置于农民的视线之内,对其进行淡化叙事,在淡化的同时强化其政治功能:一方面突出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始终将叙事视点放在乡村内部,使外来者与农民的冲突与契合都在村庄内部得以完成,而外来者所隐含的政治性,也只有与乡村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发生作用。
1943年《小二黑结婚》之后的赵树理文学,较多借鉴地方戏曲等民间文艺中的表现方式,让人物自己带动叙事的发展,类似于穿针引线,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全知全能叙事。作为叙述人的作者,与农民站在同一立场,虽然对于故事是全知全能的,但并未站在农民视角之外说话,而是透过故事中的人物来叙述,而且只讲述他所看到和听到的,并不做主观的分析和评价,这也就是赵树理所说的:“写风景往往要从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描写一个人物的细部往往要从另一些人物眼中看”[4]184。赵树理采取了独特的“散点叙事”。“散点叙事”是中国绘画的透视方式。西方绘画不论是风景还是人物,通常会有一个固定的聚集点,画面会相应表现出明显的主次差别,中国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则没有明显的聚集点,像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和《富春山居图》等,任何角度都可能或可以作为中心,与西方绘画视角固定的“焦点透视”相对,中国绘画的透视方式一般被称为“散点透视”。赵树理的叙事视点,非常类似中国古典绘画传统中的“散点透视”,可称为“散点叙事”,即从多个角度表现事物特征和塑造人物,整体上看并无中心人物,从而建构出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的乡村叙事世界。
如《三里湾》开头,仿佛一个东方老人以一种全知的视角讲述了旗杆院的由来,接下来叙述视角转到了王玉梅身上,情节就随着王玉梅的行动而展开,先是旗杆院上课迟到以及何科长住宿的事情,马有翼、范灵芝、王满喜纷纷出场,且性格鲜明;而后随着王玉梅的脚步来到王家,叙述的线索就交给了袁小俊和王玉生。就这样,人物在三里湾这个村庄内活动,并带动其他人物的活动以及事件的发生,不过并不是以某一个人物为主,与《孔乙己》中小伙计那种限制性视角以及小伙计背后作者冷观视角不同,《三里湾》中没有固定的人物视角,不断变换的人物既是事件的一部分,同时又带动事情的发展和情节的展开,引出其他的人物,叙述人就跟着这个人物的所见所听来叙述。叙述人和小说中的人物是同一的,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叙述人的全知与小说中人物的限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但是,无论是全知叙事还是限制叙事,作者都没有赋予其作品人物以一种主动观察的意识,而叙述人的主动意识则隐藏于小说人物的自在状态中。就以王玉梅为例,她穿针引线的功能并不是主动发挥作用的,在文本中,她只是隐含作者展现在接受者眼中的一个角色;但在故事中,她是王家的女儿、合作社的社员、夜校的学员、青年团员、三对青年恋情中的一方,所以她参与的所有事件,既是她日常生活的普通行为,同时又使与她有关的人与事情自然地呈现。其他人物也是如此,他们生活在三里湾这个地理空间中,共享着三里湾不言自明的伦理和行为规范,同时也在推动着三里湾的变动与重组。而在叙述的过程中,隐含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并不存在一种旁观的或外来的视角,隐含作者化身于每一个人物,与他们融为一体。
赵树理小说的叙事视点既没有源自“他者”的“凝视”的目光,也不存在一个内视的目光。叙述者或隐含作者虽是全知的,但是他们附身于故事中的人物,借着故事中人物的限知视角,平静地看着或者说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由于故事中的人物是自然而然地生活于乡村中的,他们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在取消了古典全知视角叙述者的同时,也没有就农村的变化做任何评述。事情的发生与解决、农村的改变和重组是由各种力量的集体作用推动的,同时也使得事情的发生与解决摆脱了外部(包括国家)的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点也决定着小说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暧昧关系,从而将其作品中的乡村呈现为某种自足自在的意义空间。当然,这种自足自在性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暂时的,三里湾并没有完全摆脱外部的干扰,如何科长的外来者身份,只是赵树理尽力弱化其外来者的行为特征,而使他成为第12至15章的线索,并作为三里湾变化进步的一个佐证。虽然他的外视角被弱化,但并不代表不存在,不过这种弱化外部人物的线索式的叙事,使得三里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暂时的自足性,其内与外呈现出一种互动式的和谐,其中蕴含的则是作者对于理想的乡村生存形态的一种想象。
尽管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是跟着故事人物的眼睛走的,但是叙述声音却是叙述者的,这个叙述者又是全知全能的,这就使赵树理的作品既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不是限知视角,因为在其作品中,“谁说”和“谁看”并不总是统一的,即使他们在同一叙述平面上。下面两个叙事片段正表现了独特的散点叙事造成的“不统一性”,同时也体现了赵树理对青年“新人”的定位:
[1]灵芝一走进去,觉得黑咕隆咚连人都看不见,稍停了一下才看见有翼躺在靠南墙的一张床上。[2]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她,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3]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有翼的床头仿佛靠着个谷仓,仓前边有几口缸,缸上面有几口箱,箱上面有几只筐,其余的小东西便看不见了。[2]296
[4]当灵芝走进去的时候,可以坐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别人占了。[5]她见一条长凳还剩个头,往下一坐,觉得有个东西狠狠垫了自己一下;又猛一下站起来,肩膀上又被一个东西碰了一下,她仔细一审查,下面垫她的是玉生当刨床用的板凳上有个木橛——她进来以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吃了亏了,所以才空下来没人坐;上面碰她的原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小锯,已被她碰得落到地上——因为窑顶是圆的,挂得高一点的东西靠不了墙。[6]有个青年说:“你小心一点!玉生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机关!”灵芝一看,墙上、桌上、角落里、窗台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不简单。[2]282
这两个叙事片段分别是范灵芝对马有翼和王玉生的房间的观察,[1]-[3]为中农家庭青年马有翼的房间,[4]-[6]为贫农家庭青年王玉生的房间,从叙事视点来看,都是随着灵芝的眼光写的,透过灵芝的眼睛可看到截然不同的房间,也反映了有翼和玉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及家庭环境,从而为后文灵芝选择玉生放弃有翼做了铺垫。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分属第24章和第22章,故事中的时间距离不短,叙事距离也不算短,但对两个房间的描述,隐含作者采取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叙述方式,甚至连使用的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两个叙事片段都是三大句,中间的第二句都出现了破折号,第二个片段还出现了两个,而且破折号之后附上的解释性话语的功能也完全一致,即[2]和[5]中叙述人和灵芝分离,以全知的视角进行补充说明,前者写出了糊涂涂的精明,而后者在灵芝的视角之外对玉生的房子做了更具体的补充,[6]句的最后三个字“不简单”既是灵芝所想,也是叙述者的评价话语,等于隐含作者的声音,同时还可以是满屋子里人的想法。从接受上看,对两个房间的描述产生的修辞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马有翼是阴暗的封闭的,没有生气的;而王玉生的房间却是明亮的、科技化且充满生机的。但隐含作者的叙述干涉却是很隐蔽且简洁的,他的干涉仅在于对描述对象的选择,即叙述人虽然会不时地以全知的视角做补充说明,但其补充说明的只是人物看不见的部分,或是看到的事实背后的原因,叙述人的立场、想法和故事中的人物依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虽然他是全知的,但是叙述却又始终没有离开故事中人物的眼睛,其叙述的部分也没有超出故事人物的理解和接受范围。这种内化于村庄内部的叙述方式,来源于作者对农村这一乡村共同体的熟悉,赵树理对农村的生活及农民的想法都极其熟悉,“在与农民关系上,他不是从外边扎进去的,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5]5,“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6]120,这种熟谙使得他能更多地关注乡村内部的复杂变化以及农村内部稳定的传统,而不是乡村外部的世界,“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7]83,所以赵树理作品中带着现代思想的外来者,是在农民的目光审视下逐渐与农村融合的,而不是外来思想一下子改变了乡村世界。
这种乡村内部叙述视点指向的农村变革,更多是从乡村固有的传统出发,而外来者只有与农民契合,才能解放农村。换言之,在农村革命的过程中,外来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但农村传统的伦理道德和集体经验,却支撑着农民的行为。这种全知和限知交叉的叙事视点,使得作者的叙事始终围绕着农民的生活,呈现出农民乡村生活的常态,而没有溢出村庄之外。即使是外来者,代表着党的干部,也没有成为叙事的核心。他们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来到村庄,首先接受的便是农民视点的检验,在农民视点的观照下,其与村庄的融合程度恰恰是其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说,外来的思想虽然会对农村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前提是必须要和农村内部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相契合。而外来者虽然没能成为叙事核心,但作用却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外来者的扶持才保证了农民视角的稳定。乡村内部叙事视点,在某种程度上,使乡村在内与外的互动中维持了自足性,很典型地表现了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的独特性。
赵树理这样坚持乡村立场,不可避免地被启蒙知识分子称为“不现代”,再加上过于通俗的语言,解放区的五四式“现代”文学批评家亦对他嗤之以鼻,甚至称之为“海派”,将其与“鸳蝴派”和张爱玲相提并论[8]89,但日本学者竹内好却由此“古”和“俗”看出了赵树理的超越性:
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这里所说的赵树理的不同性质,包括了个性的问题和自我完成的问题。这一点把他与其他人民作家区别开来了。我想,特别提出赵树理的这种特殊性,是会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吧。因为把赵树理与其他人民作家等量齐观的人不少。但是,我反对那种意见。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更明确地说,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1]75
竹内好的判断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他对鲁迅的判断,“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重大判断。进而言之,基于文学的想象也昭示了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的“超现代”性。
三
在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中,乡村仍然是无解的文学乌托邦。文学必然面对社会、面对人类,始终难以摆脱权力和政治,有权力就有弱势群体的存在,作家和研究者都必须面对,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中的作家和文学都深陷其中。很多作家和学者自以为是认真地进行所谓人类前途的思考,实际多坠入文字游戏,甚至在已经完全否定他言说那个群体的前提下,还以为自己在为弱者代言。赵树理的写作从来不是以自娱或自我为目的,从《三里湾》可看出他的“乌托邦”之“近”与意义之“远”,他拒绝抽象的文字游戏,心系乡村的存在与发展,又不乏指向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向度的思考。应该说,赵树理在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特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楷模,他给作家和其他文人树立了一个真正的体察式的思考和“代言”模式,而不是自说自话和自我满足。赵树理的“代言”方式,是融汇中西努力达到东方传统之下的人性的“进化”:“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1]76竹内好说出了赵树理的个体“进化”思路的真谛,即赵树理的乡村进化是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它既是农民个体与乡村集体的辩证,也是现代作家与被代言者的辩证,也是乡村乌托邦想象的“远”和“近”的辩证。竹内好归纳出的个体的进化与“还原”,正是在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对西方化弱肉强食的经济“发展”规则的有效抵抗,它不但能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还能保证人类“为公”的文明特征。
概言之,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对当前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有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即现代的个体性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集体特色相结合,形成一个强大且文明的经济中国和文学中国。或者,我们能由此等待着莫言之后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