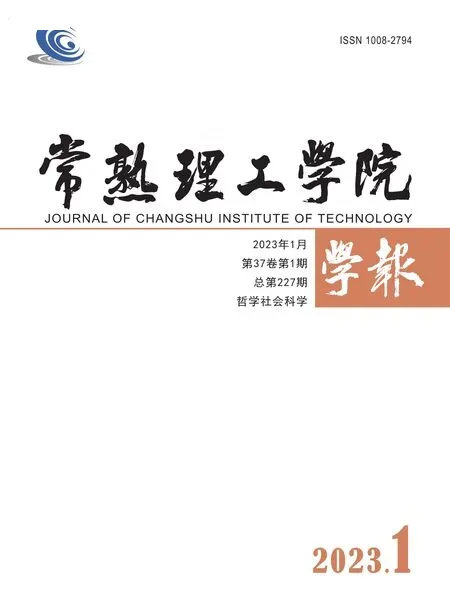立足传统 致力创新 忠于志趣
——品读《韩陈其诗歌集》
2023-04-07高燕
高 燕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诗。从先秦到当代,由《诗经》而唐诗宋词,每个时代都不缺乏独具个性特色的诗歌样式。诗歌如同中华民族的血液,绵延不息地流淌在温润厚重的中华文化中。中国新诗发展百年,各种诗派争相崛起,前有湖畔派,后有窗诗派,他们秉持共同的美学追求:摆脱格律束缚,追求形式自由。然而,新诗发轫之初过分追求“个体自由”,过度抛弃传统格律,渐渐迷失“自我”而产生了散文化的松散倾向和艺术粗糙浅陋之弊端。于是,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有识之士开启了新诗格律之旅。诚然,闻一多先生的“三美”新诗理论为中国现代新诗指明了健康发展的方向,但仍未触及新诗的本质。那么,新诗的本质究竟为何?新诗格律应该如何建构?当今著名学者、人大教授韩陈其先生给出了他的探索与思考。通读《韩陈其诗歌集》[1](后面简称《诗集》),我们不难发现,韩先生直击汉语结构系统和应用系统,在“言意象”的观照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尝试为新诗建构的困境找寻适切的管钥。
一、韩诗新格律之根本:立足传统
从古至今,诗歌且吟且舞,传唱千年,其发展从来都是依托前代的。我国现存文献记载的最早的“诗”是源于劳动的古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2]诗歌语言简约质朴,八字即呈现完整狩猎过程;节奏短促铿锵,匹配狩猎的一气呵成以及情感的欢悦跳动。“杭育,斫竹,嗬哟嗨!杭育,削竹,嗬哟嗨!杭育,弹石,飞土,嗬哟嗨!杭育,逐肉,嗬哟嗨!”[3]这是发现于江苏张家港地区的民间劳作之《斫竹歌》,如果去除拟声词,共十字,五个节拍,形式和《弹歌》略有出入,但内涵一脉相承,疑似《弹歌》的遗存和补充。及至《诗经》时代,诗歌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由两言而演变为四言,间夹以二、三、五言,甚至七、八言,可以说,《诗经》在诗歌语言范式上具有继往开来之功。而《楚辞》变《诗经》四言为六言,或夹以七言。汉魏产生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应是滥觞于《诗经》和《楚辞》。在前代押韵、平仄、对仗、字数和句数理论一步步臻于至善的基础上,唐诗格律体系构筑完成。除排律外,其字句定数,押韵严格,讲究平仄,追求对仗。可见,诗歌形式从来都是代代相传、承继创新的。不仅如此,古代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也逐代渗透,或显或隐于各个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所以,我们无法割裂古今的联系,抛弃古代意味着背叛传统,更意味着践踏诗歌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本性。韩先生认为,中国诗歌要想健康发展,就要节制毫无规则的自由放纵,适当继承传统诗歌元素[4]。
1.继承古代诗歌韵律
音乐性是诗歌的生命。《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5]可见,诗歌配乐可唱,且乐谱须依诗而定。这无疑对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提出了很高要求。因此,节奏自古便是诗歌的内在要素。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诗的节奏也不尽相同。但是,不管节奏形式如何,都会自带旋律的美。相传帝尧时代,政治清明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人们喜欢玩一种“击壤而歌”的游戏,关于“壤”究竟为何,颇具争议,但这种“击壤”的特殊方式形成有节奏的拍子,可以协助所咏之歌的内在意蕴表达。押韵是诗歌音乐性的又一关键要素,从《诗经》到后代诗词,几乎没有诗歌不入韵。这种对诗歌音乐性的深刻体认及自觉追求在唐诗宋词里达到了顶峰。
韩先生认为,汉语诗歌不外乎两大要素:句式及其节律,音乐及其韵律,无论古今,都应是诗歌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对古代格律理论的传承和守望充分蕴含于其《诗集》之中。
从节律角度看,韩诗大多句式整饬,以七言、九言为主。《诗集》后七卷一般七言,唯有第一卷的宽骚体诗几为九言。这遵循着汉语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长度无限,宽度有限,从原始诗歌的两言发展到律绝的五七言足以印证。《诗集》中的宽骚体九言诗主要继承了《楚辞》以虚词“兮”“之”“乎”等作为语音衬字的传统,这是屈原顺应春秋时期语言加长发展需求,并借鉴《诗经》节奏规则的独创。
从韵律角度看,《诗集》四百多首诗歌,非常重视押韵,大多偶句押韵,有的上下句都押韵,有的甚至一韵到底,这无疑是对古代格律体的变通性的继承。同时,为了增强声音的律动,韩先生极尽《诗经》叠字传统之能事,在其宽骚体诗中几乎篇篇可以找到韵律十足的叠字,使这些诗篇读来音韵和谐、节奏铿锵。
由此观之,以传统格律精神与节奏规律为立足点建构新诗格律,是韩先生新诗格律的根本。
2.传承古典文化元素
诗歌是民族的,诗歌创作者如果全然抛弃民族文化的传统精髓,势必会被民族抛弃。只有善于继承先贤经典,作品才能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否则难免流于苍白浅陋。韩先生秉持着这样的创作自觉,巧妙引用古典文化元素,诗中经常出现古代的人、事、景、物以及语言文字,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即其诗作十分善于用典。《文心雕龙》把用典分为两类:举人事以征义,引成辞以明理[6]302,即“用事”和“用辞”,“事”即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史实等,而“辞”则指古人诗文中富有文化内涵的特定文辞。
登我铁塔兮想乎启封,启封拓疆之巍巍仓城!
登我铁塔兮想乎大梁,大梁引黄之济济孙庞。
登我铁塔兮想乎汴州,汴州复元之重重兜鍪。
登我铁塔兮想乎东都,东都转向之灿灿新途。
登我铁塔兮想乎汴梁,汴梁争凑之煌煌汉唐。
登我铁塔兮想乎龙亭,龙亭携湖之泱泱皇庭。
登我铁塔兮想乎吹台,吹台赋歌之悠悠情怀。
登我铁塔兮想乎包湖,包湖明镜之赫赫龙图。
登我铁塔兮想乎繁塔,繁塔媲美之隐隐希腊。
十朝古都兮东京梦华,清明上河之豫豫人家。
七朝都会兮东京梦华,清明上河之漫漫霓霞!
《东京梦华》一诗是一幅开封历史风云的厚重画卷,可谓“用事”之典范。启封、大梁、汴州、东都、汴梁等都是开封的别称,孙膑、庞涓、包拯等是与开封相关的历史人物,龙亭据说是宋太祖坐过的金銮殿,吹台之得名源自春秋盲人乐师师旷,传说他曾在此奏乐抒怀。一个个地名、人名裹挟着历史故事和传说随着开封历史的斗转星移鱼贯而出,扑面而来,诗境如此开阔悠远、大气磅礴,文字的古朴和历史的厚重相得益彰。
韩先生诗中化用古典诗文入诗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江柳舞春》中的“蒹葭青青杨柳绿”化用了《蒹葭》一诗中“蒹葭苍苍”之句,凸显了江柳之美色,“窈窕随心花露浓”活用《关雎》“窈窕淑女”之句,张扬了江柳之美态,如此,柔美曼妙之江边柳树呼之欲出。《女静》篇则是化用《诗经·邶风·静女》,并把“静女”之美展而伸之,赋予今人的审美取向,以“柔、娴、雅、宁、如、明”来盛赞“女静”之美,可谓“用辞”之典范。这些典故装饰了韩先生的诗歌,也美化了我们的心灵,更让古典文化元素焕发出时代的光辉:
女静柔柔兮柔柔静女,婵娟窈窕之微微轻语。
女静娴娴兮娴娴静女,黛娥云鬓之依依心侣。
女静雅雅兮雅雅静女,金粉娥翠之丝丝花雨。
女静宁宁兮宁宁静女,萧娘梅香之萌萌姬虞。
女静如如兮如如静女,青鬟红袖之姝姝飘羽。
女静明明兮明明静女,倾城倾国之洋洋天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静》一诗还继承了回文这一传统艺术形式。陈望道先生认为“回文”是“极求词序有回环往复之趣的一种措辞法”[7]。这种艺术手法充分展现并利用了汉语作为孤立语的独特个性:以单音节语素作为构词的基本单位,以语序作为构句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了顺读和倒读皆可成文的特殊艺术效果,使得诗句获得了语言、音韵和形式的和谐统一的审美意蕴。韩先生在《女静》一诗的序中说:“女之姝,在于静,《诗经》则有《静女》。静之韵,在于柔、娴、雅、宁、如、明。”[1]8为了展现女性静之内蕴,诗歌巧用回文这一艺术手法,诗中“女静柔柔兮柔柔静女”“女静宁宁兮宁宁静女”等句是典型的句内回文,无论正读逆读皆同语共义,一个“兮”字连接了两个由同样语素组合的不同的语言结构,利用不同语序的神奇力量构成了回环往复的语言形式,有利于诗人反复涵泳女之静美。而这种静美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又极具时代意义的。
这种奇巧的回文形式要想达到形式和语义的妙合无垠是极为不易的,但韩先生在“言意象”的观照中深入汉语词汇的内核,探知了汉语词类同词性的特点,他发现在古代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经常不分,甚至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也经常用同一个语言形式(同一个字或同一个词)来表达,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名动同词”“名动形同词”说理论[8]。现代汉语的“兼类词”即是古代汉语“名动同词”这一现象的活化石,而《女静》一诗则是这一理论的完美实践,诗歌利用“静、柔、娴、雅、宁、如、明”等词既有动词的功能、又有形容词的意义这一特点,通过调整这些字的语序,形成了六组动宾结构和偏正结构,最终形成了顺读倒读皆可、形式和语义和谐的回文句式。通读这些诗句,怎能不让人叹服韩先生的闲情逸趣与诗性才情呢!
这些古典文化的元素在《诗集》中无处不在,让我们看到了古典文化传统之于现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更让我们看到了韩先生对古典文化元素的殚精竭虑的继承意识和决心。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指出,诗人有必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精髓,否则只能陷入肤浅内容和粗鄙形式的泥淖中不可自拔[9],这是确论。
二、韩诗新格律之核心:致力创新
从古代汉语转为现代汉语,语音和词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语音的变化最明显莫过于声调的变化。古有“平、上、去、入”四调,今有“阴、阳、上、去”四声,但今之四声已非古之四调,最突出的是古代的入声除了在部分方言中还能找到其遗存外,均已分散到普通话的四声中而失去其形了。词汇方面,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转化,只有少部分单音节词汇保留在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中。而格律诗形成于汉语中古时期,依据的是中古音,因此,今天的新格律诗创作无法也不该生搬硬套古代的格律,而应该结合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和语言系统找寻属于自己的格律范式,新诗格律的建构唯有超越古典模式才能焕发出健康的生命底色。
韩先生对中国诗歌一往情深,四十余年孜孜矻矻、皓首穷经,在找寻和构建现代新诗格律的道路上苦心经营。
1.建构独特的“言意象”理论体系
探讨诗歌和汉语关系的专家学者及其成果不在少数,但韩先生直击诗歌和汉语汉字的本质,摸索出了“言意象”的独特理论体系。这与他多年的学术生涯不无关系。韩先生曾执教于江苏师范大学,躬耕于“言”的领域,是语言文字领域的领军人物,著作等身,这为他创作诗歌并研究诗歌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又在南京师范大学深挖“意”之内涵,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象”之本质以及“言意象”的内在联系,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言意象”理论体系。
《周易·系辞上》曾记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10]孔子早就意识到言、意、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曹魏经学家王弼进一步阐明了言、意、象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11]609,他强调“言以尽象,象以尽意,得象得意,忘言忘象”。而韩先生则进一步深入阐述了“言意象”和诗歌创作及释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言”形成节律,“意”凝聚情感,“象”构筑特定时空,而诗是“言意象”的聚合体。“言”关乎诗之形,现代诗歌必得有属于自己的“形”,这个形必须适合自己的语音系统和语言体系,否则会难以为继。由于古今四声的演变归并,韩先生认为古律中的平仄格律不再成为现代新诗格律的应有之义。[1]诗序,3关于“意象”这一没有定论的大是大非问题,韩先生不但指出其来源,还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人工、精神之“三象说”。其中,精神之象至关重要,其形成包括由印象而意象、由意象而大象的过程,这是一个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的象思维过程。这一过程以言释象,以意筑象,意随象生,由自然、人工之具象生发精神之虚象,再由精神之虚象回归自然和人工之具象,无限往复,至于无穷。所以,汉字的本质是象,汉语的本质是象,诗歌的本质自然也是象。[12]
这样完备而系统的“言意象”理论体系无疑为新诗格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而韩先生也用这样的理论指引自己的实际创作。
2.践行“言意象”观照下的“宽”容诗律
韩先生正视古今语音变化及当今汉语结构特点,根据自己的新诗格律思想,在“言意象”观照下创制了包括齐正律、宽骚律、宽韵律、宽对律、宽异律在内的“五律”宽式格律机制。
(1)秉持齐整方正的基础形式
纵观中国诗歌史,古代诗歌的创制机制是精确到字的,从最初的两言,到后来的四言、五言,乃至七言,至于词,那就更不必说了,词牌就是字数的符号代码,因此,不同字数似乎成为古代不同诗歌范式的标志,这种内在生命气息的短长无形中制约并引领着诗歌的发展演变。韩先生准确体认汉语诗歌的这一内部生成机制,在充分尊重汉字独特的外部特征以及汉语语音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坚持以齐整方正的形式为汉语新诗歌的基础形式,这就是韩氏齐正律。
若包括卷首的《宽骚体·乾坤骚怀》以及诗跋中的小诗,《诗集》共收录了四百二十六首诗歌,其中,五言诗十首,七言诗三百五十一首,九言诗三十九首,十四言诗一首,词十二首,杂言诗十三首,既有符合传统格律诗体系的五七言基础形式,更有适应时代需求的九言乃至十四言创新格律样式,这些诗歌尽管句数不尽相同,但因着每句字数一致而获得齐整方正的视觉效果。即便是句式长短不一的词和杂言诗,也都有其内部规定性而显得整齐和谐。这样的齐正体贴合视觉愉悦的内部机制,有利于对汉语诗歌的创作和吟诵进行调整和释读,更是对现代新诗因放任形式自由而迷失自我的一种救赎。由此可见,韩诗在继承中竭力推陈出新,不断为新诗形式格律建模赋能。
(2)独创诗骚结合的宽骚体式
使用《楚辞》虚字字腰来写现代新诗,这本身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创新。“宽骚长怀”卷三十九首外加卷首的《乾坤骚怀》一首,共四十首,都是韩先生独创的巧用虚字字腰的诗骚结合的宽骚体诗,这些诗歌是韩氏宽骚律的完美呈现。《诗集》中的宽骚体诗一般九言,其中最长为十四言。这种体式吸收了诗骚赋独特的句式并加以改造,或是叠加《诗经》四言和五言句式而成,或是于《诗经》两个四言句式中间嵌入《楚辞》虚字而成,可谓对汉语诗歌宽度的一种变革式创吟独唱。当然,《楚辞》虚字字腰众多,韩先生独钟情于“兮”和“之”字,这是一种取舍。关于“之”字,韩先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立足古人“因物制字”的创字创语理据,认同元人周伯琦的观点,指出“之”的原始本义应为“芝草”,并用“言意象”的象思维来观照“之”的发展演变过程,阐释了“之”的各种意义的产生序列以及各种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拨开了掩盖在“之”字之上的重重迷雾①韩陈其《言意象观照:释“之”》一文认为“之”的发展先有无中生有之象,也就是其作为名词“芝草”的意义;继而有“萌”发之象、“生”发之象和静动互变之象,“萌”发之象和“生”发之象是“之”作为指称代词“此”或者“彼”的意义,静动互变之象是“之”作为动词的意义;最终基于以上诸多“象”而形成了“之”的种种实指、虚指,甚至无指,也就是其作为介词、连词、助词的用法。这篇文章于2021年发表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辑出版的《语文建设通讯》第123期,第2-4页。。“之”字词义发展轨迹足以昭示汉语和汉字“源于象,成于象”的本质属性,这恐怕是韩先生钟情于“之”的原因之一吧。
一般而言,《楚辞》中“兮”字可以位于句中,其前后通常三言和两言,也可以位于句末,前面通常六言;“之”字通常位于句中,前后通常三言和两言,如“抚长剑兮玉珥”“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韩诗宽骚体在《楚辞》节律的基础上做出了变通,“兮”和“之”的前后各有四言,这种革新切合了现代汉语语音的特点。如果声音可以丈量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大部分汉语双音节词的发音时长基本相当,且其中一个音节或重或长,另一个则或轻或短,这是汉语节奏抑扬顿挫的根本。“兮”和“之”前后的四言各有两个音组,形成两个节奏,读来抑扬顿挫,极富音乐的韵律。
宽骚体诗大都上句用“兮”,下句用“之”,但《耀天红月》和《鸡飞狗旺》二首是个例外,这也许是韩先生整齐中求变通的匠心独运。《耀天红月》的结尾四句以“兮”字作为句腰,《鸡飞狗旺》则开头和结尾四句均以“兮”为句腰。
婵娟碧华兮凛凛飞红,玄烛耀天之滚滚尘红。
明明红月兮红月如眉,玄烛照天之娇娇娥眉。
红月明明兮红月如钩,玄烛辉天之晶晶玉钩。
明月红红兮红月如眸,玄烛煌天之柔柔情眸。
红红明月兮红月如环,玄烛烛天之灿灿金环。
月红月红兮如如月红,玄烛光天之天灯红红。
红月红月兮宝华红月,玄烛华天之红红雪月!
婵娟碧华兮玩水弄潮,玄烛烁天兮天海洋潮!
碧华婵娟兮弄潮玩水,玄烛灯天兮冰镜天水!
《耀天红月》是韩先生于故乡宝华镇的望月抒怀之作。他有感于当年南朝宋诗人谢庄曾到此一游,望月怀远,并写下《月赋》名篇,留下千古佳句,遂诗情迸发,一吐为快。如今,此月亮貌似昨日之月亮又绝非昨日之月亮,韩先生以细腻之笔触极尽描写月亮之色、形、质、态,这月亮充满梦幻,如“娥眉情眸”,似“玉钩金环”,若“天灯白雪”,天上、地上、人间,无处不在。但这还嫌不够,结尾的四个“兮”字句从动态角度极写月力之震撼,想必是为了加强对月亮玩水弄潮之自然神奇景观的吟咏叹息。这样的设计使这首诗达到了音乐和语义的双重极致。
除夕除岁兮除岁除夕,喜喜红红兮亲亲戚戚!
鸡飞狗旺兮除岁除夕,春夏秋冬之忙忙急急。
鸡飞狗叫兮除夕除岁,男女老少之双双对对。
鸡飞狗汪兮除岁除夕,东南西北之歌歌泣泣。
鸡飞狗欢兮除夕除岁,喜怒哀乐之零零碎碎。
鸡飞狗笑兮除岁除夕,锅碗瓢盆之点点滴滴。
鸡飞狗喜兮除夕除岁,爱恨情仇之连连缀缀。
鸡飞狗闹兮除岁除夕,江河湖海之潮潮汐汐。
除岁除夕兮除夕除岁,日月星辰之凉凉沸沸!
除夕除岁兮除岁除夕,红红喜喜兮福福吉吉!
《鸡飞狗旺》首尾四句全用“兮”字,或具备音乐的巧美,或具备语义的圆美。如果我们变换角度读一读,就可以把首尾四句变为整饬的两句“除夕除岁兮红红喜喜,亲亲戚戚兮福福吉吉”,寓意亲朋好友幸福和美,这样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构成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回环之美。
(3)坚持宽大为怀的用韵原则
格律诗在用韵上非常严格,因着韵的等距离的合理调配可以构建诗歌形散音聚、腾挪回环的韵律美,且每个韵部都有各自的声情质态,可与文情意蕴互为表里。一般而言,格律诗隔句押韵,偶有首句入韵,只押平声韵,且不能“落韵”,即只用同一韵部之字,而不用邻韵或他韵之字。
韩先生正视现代汉语语言本性,坚持宽大为怀的用韵原则,并在这一宽韵思想的指引下创作了大量宽韵体诗,这些诗歌几乎篇篇押韵,但在继承中努力革故鼎新,注重韵脚的选择和韵位的安排。
通观《诗集》诸篇,押韵不拘平声韵,也可押上声韵、去声韵,甚至可以出韵,或者四声混押,灵活而自由。有时一韵到底,如《寻往》通篇押平声“歌”韵,《野荷白鹭》隔句押平声“阳”韵,《龙翔九天》偶句押上声“有”韵,《驹隙感怀》隔句押去声“宥”韵。有时邻韵相押,《江春潮思》偶句押平声韵,但通押了平声的“先”“寒”“删”三个邻韵中的韵字。还可三声韵混押,《五峰客潮》是典型的上声和平声混押的例子,韵脚是“往、方、翔、港”,其中“往”是上声“养”韵,“港”是上声“讲”韵,“方、翔”属于平声“阳”韵;《京华走游》则是去声“宥”韵和上声“有”韵通押;《春狂》单句都以上声结尾,偶句均以平声收束;《永遇乐·京华上元》则平声韵、上声韵、去声韵混押,事实上,“永遇乐”这一词牌有平韵和仄韵二体,北宋时均押仄韵,南宋时均押平韵。有时两句一换韵,如《鹳鹳歌》;有时任意换韵,《圌心颂》一诗总共二十二句,竟使用了平声韵中九个韵部中的字。或者异字为韵,《诗集》中大部分诗歌属于这种类型;或者同字通押,如《牛首春颂》《渡江》等,而同字为韵则是古代格律的大忌。韩诗既可上下句为韵,宽骚体诗大抵如此;也可偶句入韵,宽骚体以外的诗歌大都如此。这种韵脚和韵位的灵活调配可谓前无古人,后者可期。
(4)热衷追求“象”格的宽对模式
讲究对称美,是中国五千年美学思想的精髓,从古代建筑的设计、生活物品的雕琢,到哲学的阴阳平衡、文学句式的两两相对,无一不是如此。诗歌作为中国文学之源,对称可谓其创作法则。这种对称体现在语言形式的字数、结构、词性以及语义诸方面的一致性上。这也适用不同的对象,如散文、楹联、诗歌等,给人一种健康平和的均衡感和端庄肃穆的秩序美。
韩先生不拘于格律诗的对仗法则,糅合散文、楹联及诗歌之大要,创制了追求“象”格的宽对律,热衷关注“象”的数量、层次、范围、色彩以及“象”与“象”的关联性、协调性和整体性。
一湖碧水万顷云,几条渔舟逐浪追。
青竹白帆翠黛远,蓝天绿水涛声微。
夕照璀璨鸣鸥鹭,树影婆娑钓余晖。
群山绕云太平湖,绿地亲水皇冠徽。
荡桥水人嬉玩天,万缕芳思伴霞飞。
这首《青竹翠黛》是韩先生注重“象”格的典范作品之一。从结构、词性以及语义看,第二、三、四联是典型的宽对,让我们惊叹的是诗中诸多“象”的相生相伴:青竹对蓝天,白帆对绿水,翠黛对涛声,夕照对树影,鸥鹭对余晖,群山对绿地。然而,这些意象并非完全符合结构一致、词性相同、语义相属的要求,如,鸥鹭和余晖的内部结构就有差异,而竹和天、群和绿显然不是一个意义类属,组合翠黛和涛声的单音词的词性完全不同,但这些意象统摄在一个共同的时空里,却是那么和谐完美。首联和尾联的句式貌似不够对称,但其中的“象”却不乏相对相关之处,如碧水和渔舟,游人与芳思。这些意象数量众多,色彩和谐,涵盖自然人工之象、空中地上之物、动态静态之景,既独立,又浑然一体,貌似无关,实则紧密相连。这种注重“象”格的宽对模式涵容了形式的自由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为汉语诗歌新的对仗模式的建构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5)提倡不拘一格的宽异体式
宽异体诗歌是韩先生对汉语诗歌体式的全新尝试,这种宽异律既尊重汉语新诗歌的齐正律,又追求诗歌表现形式的灵活宽泛和不落窠臼之变,如《扇之秋》《鸟花对话》《挂怀》《新元云歌》《旧笑新缘》《善人乐牛》《入泮知命》《古诗杂拌》等,这些诗歌或异于语言形式,或异于语音韵律,都是勇于开拓创新的佳作。
秋
枫红
彩蝶翔
淡云熏风
婵娟霓云裳
参差烟花社鼓
大江奔涌入心窗
抚今怀古北固怅望
吴女尚香万里祭情殇
水漫金山白娘访仙梦乡登高携手更上五峰岗
品茗赏花行酒问月
敢信嫦娥笑吴刚
天街欢声笑语
彩霞飞九江
长河落日
金桂香
清风
秋
这首《扇之秋》就是韩诗宽异体的典型代表,其语言形式别具一格,仿若一把打开的折扇,又似顾影自怜的临水之塔,很有古代宝塔诗的意味,但又有所不同。宝塔诗文如其名,通常塔尖以一言或两言起首,塔身逐层叠加,至塔底以七言收束,如同一个等腰三角形,具备特别形象的建筑美和图画美,是对方块汉字形体特征的巧妙运用。这首诗却是以一字开头,继而逐层叠加一字至第十层而止,此后便每层减少一字直至文末一字收尾,这无疑是对古代宝塔诗的变革性尝试。这种对汉诗形体建设的尝试,既符合人类的创造本能,也贴合诗歌本体的变革天性。
总之,韩氏“五律”宽式体系是韩先生在“言意象”的观照中勇毅笃行、躬耕不辍的结果,这一体系为汉语新诗格律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3.重视观象、取象、立象的象思维
关于“象”,甲骨文中的“象”字像大象之形。《说文解字》说:“长鼻牙,南越大兽。”[13]198可见,“象”最初是大象的借记之词,后引申为“形象”,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甚至精神世界的各种事物和形态。它包括自然之景象,如日月山川、风霜雪雨等;也包括人工之物象,如典型人物、特定场景等;还包括精神之虚象,以自然之景象和人工之物象为原型的引申幻化之象。
中华文化重意尚象。韩先生深谙这一点,他在“言意象”的观照中发现,汉字之形源于象,汉语之韵显于象,汉语诗歌之魂筑于象。诗歌创作即是“言意象”交互作用的象思维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观象应至广、取象应至美、立象应至幻,由实而虚、由有形至大象无形。
销魂夺魄兮子规声声,柳岸残月之春风吻城。
夺魄销魂兮知了哄哄,荷塘清月之夏雨洗虹。
夺魄销魂兮鸳鸯如如,枫亭冷月之秋露含珠。
销魂夺魄兮鸿鹄灵灵,梅岭冰月之冬雪戏情。
春夏秋冬兮天旅匆匆,人海泛舟之云竞苍空。
这首《人海泛舟》意象众多,子规、知了、鸳鸯、鸿鹄、柳岸残月、荷塘清月、枫亭冷月、梅岭冰月、春风、夏雨、秋露、冬雪、白云、苍穹、天旅、人海,既有自然景象,又有人工物象,自然景象中蕴含着人工物象,人工物象源于自然景象,幻化出人生如春夏秋冬的绚烂多姿、如泛舟湖上的跌宕起伏的物我两忘的精神之境象。从取象层面看,春夏秋冬之景众多,但只取最具季节标志以及极富美感和象征意蕴的事物,以视觉为主,融汇其他五觉,动静结合,极富层次。从立象角度看,亦实亦虚、似真似幻,如诗如画,言意象共生。
遍观《诗集》四百多首诗歌,所观之象横贯大江南北,涵盖古今中外;所取之象内涵丰富,意蕴深厚;所立之象意境阔远,语义宏富。正是这样的杜鹃泣血、冰心觅象才有了这么多赏心悦目的字字珠玉、篇篇华璋。
朱光潜先生在《谈新诗格律》一文曾慨叹:“伟大的诗人创造了真正伟大的诗作品,往往也就同时奠定了他或他们那个时代的诗的形式。”[14]韩先生不但孜孜于诗歌创作,还钟情于诗论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二维层面为汉语新格律诗的开拓创新指明了方向。
三、韩诗新格律之灵魂:忠于志趣
《后汉书·蔡邕传》有言:“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15]文人总有文人的志趣。《说文解字·心部》说:“志,意也,从心之声。”[13]217又说:“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13]217《广韵》说:“志,意慕也。《诗》云:‘在心为志。’”[16]可见,“志”和心理有关,是一种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而自觉奋斗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坚定的志向。《说文解字·辵部》说:“趣,疾也。从走取声。”[13]35《广雅·释诂一》说:“趣,遽也。”[17]所以“趣”的本义为快速行走,重在强调行走速度之快,后引申为旨趣,即美好的志趣。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走部》说:“趣者,趋向之义。故引申为归趣、旨趣之称。”[18]品读韩先生光华缤纷之诗作,在言意象的观照中,我们看到了氤氲其中的高尚志趣。在高尚志趣的引领下,韩先生自总角垂髫之时便浸润其诗爱之心,至花甲古稀而如如①如如,佛家语,犹“真如”,谓永恒常在的实体、实性,引申为永存、常在,又引申为恭顺儒雅的样子,这里是永恒存在的意思。诗情腾飞。
诗跋里的一首小诗既是韩先生一生的写照,更是其高尚志趣的集中体现:
少狂迷汉语,
半世探究言意象,
春思一生,
洋洋羡余逸度;
古稀歌韩诗,
一心回归江湖海,
秋望八垓,
靡靡宽骚情怀。
诗歌分为两节,形象地概括了韩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以及其对语言的迷恋和敬畏、对诗歌的喜爱和执着的“致于言、乐于诗”的人生志趣。韩先生少年立猛志,半世勤躬耕,一生守志趣,古稀归自然。而“半世痴迷言意象”“一心歌咏江湖海”的苦心孤诣使韩先生获得了“洋洋逸度”“靡靡情怀”的人格建构。正如韩先生在《诗集》序中所言:“四十余年学术生涯,肇始于‘言’,周旋于 ‘意’,升华于‘象’。言——意——象铺就了我的学术康庄大道,渲染创设了我的诗歌特色,也架构了我的人生哲学观,既不汲汲于时利,更不汲汲乎空名。”[1]诗序,1
“不汲汲于名利”是韩先生人格的底色,也是其诗歌能够独树一帜的根本。
要之,《诗集》四百多首诗歌是韩先生数十年对“言意象”三者关系深入探究之累累硕果,也是韩先生对汉语和汉字内在本质矢志不渝的苦心寻绎,更是韩先生对现代白话诗格律范式继往开来的勇敢践行。缓缓合上《诗集》,浑然置身于“流霞飞虹,星歌云梦”之美妙意境,胸中激荡起“人生蒸腾烟霞正,生命永红彼岸花”的如如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