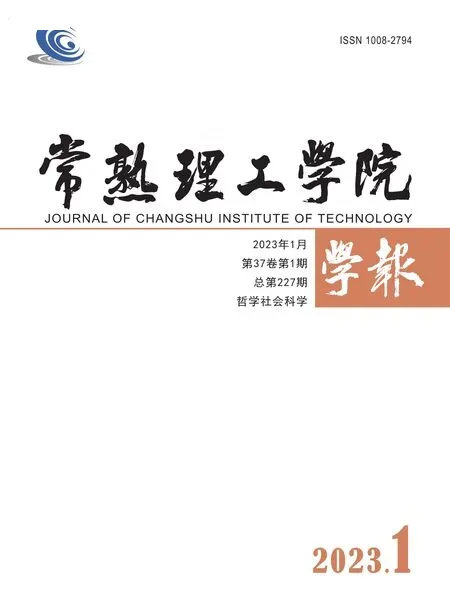言子与常熟乡贤文化
2023-04-07许霆
许 霆
(常熟理工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贤学贤的历史传统,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保证。在传统意义上说,尊贤学贤之“贤”主要是指先贤,包括后世所称的名宦和乡贤。仕于其地而惠泽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常熟把孔门大贤言子,视为常熟文化的始祖,又视其“鲁之宰”是县令起源,因此,言子成为常熟民众心目中兼具乡贤和名宦双重身份的先贤。尊言子与尊乡贤有机结合,这是常熟乡贤文化的基本特征。
乡贤与邑之人望
我国的乡贤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常熟的乡贤文化溯源无考,现存最早论及常熟乡贤文化的是宋常熟县令陈映所撰《(常熟县宰)续题名记》[1]。
宋神宗初年,常熟县令刘拯在县署厅壁创设县宰题名板榜,将太宗太平兴国至神宗元年百余年内的42名县令的姓名,逐一开列板榜,希望后继者不负先贤,刷新政绩。绍兴二十一年(1151),县令曾慎将木质板榜换成石刻,“庶为不朽之传”。淳熙元年(1180),县令陈映撰《(常熟县宰)续题名记》,其中有这样的表述:
今吴邑之人,或知映不敢堕也,率以淳厚简孚交相为治,倘如是愒日,庶乎列名下方其无辱!若夫邑之望,则有巫咸所止之山、泰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龚景材所表之闾,其风俗之美,犹可概见。[1]109
这里所论“邑之望”,即邑之人望,而“人望”即众人所属望或在民众中有声望的人,因此,“邑之望”即“乡贤”的意思。陈映认为,邑之望则有巫咸、泰伯、言偃和龚景材。巫咸,商代太戊时贤相,其子巫贤祖乙时贤相。“吾邑乡贤祠首商相巫公咸及子贤。按《越绝书》,虞山巫咸所出。张守节《史记正义》,巫咸及子贤冢在苏州常熟县西海虞山上。盖二子本吴人也。”[2]209泰伯,商代周人部落古公亶长子,后与弟仲雍奔吴建勾吴国,泰伯为勾吴一世,无子,弟仲雍立,传之后世。言偃,孔子唯一南方弟子,以文学著名,列名十哲。唐龚景材,邑之小山人,五世同居,以孝义称。唐麟德九年,旌表门闾。这是唐代以前的四位邑之先贤。关于“乡贤”,历来“有以德行称者,有以风节闻者,有以文学著者,有以事功显者”[3]之说,无论从哪方面说,巫咸、泰伯、言偃、龚景材都是名副其实的邑之望,是常熟乡贤的杰出代表。乡贤有着多个衡量标准,但首要标准就是德行,因此,乡贤文化的鲜明特征就是人文性,而这种人文性在巫咸、泰伯、言偃、龚景材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常熟乡贤文化史上,陈映首先把四人组合称为“邑之望”。此后,常熟志书大致沿袭这种在地乡贤的表述。现存最早常熟志书《至正重修琴川志》,“人物”所列前三位是:巫咸、言偃、龚景材;最晚常熟志书《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所列前四位是:巫咸(巫贤)、仲雍、言偃、龚景材。由此可见,常熟官员和士人始终把以上四人视为在地最为重要的先贤(乡贤)。
陈映在叙说四位“邑之望”时,都突出他们与常熟故土的特殊关系。说巫咸则是“所止之山”。巫氏家族居常熟虞山北端小山地区,巫咸、巫贤死后又葬虞山。“山虽无峰峦,而蜿蜒起伏,略如卧龙,随处望之,形势各异。”[1]49说泰伯则是“所葬其墟”。其实,泰伯并非葬在虞山,是葬吴县或无锡学界尚有争议。倒是仲雍奔吴后,先在虞地开拓,建立中容小国,并入泰伯所建之国勾吴国,后仲雍接续泰伯为勾吴君,勾吴五世周章与祖仲雍同葬虞山,因此,常熟民众视仲雍而非泰伯为在地先贤。说言偃则是“所居之里”,肯定了言子故乡在常熟,是常熟的乡先生。常熟现存言子故里碑亭,题“先贤言子故里”,左右石柱镌刻题联:“邑里崇名迹,东南钟大贤”。说龚景材则是“所表之闾”,其“闾”是指唐户部奏请所表门闾:敕用厅事夹栏,正门阀阅、乌头二柱,端冒瓦桶,卫以绰楔。左右各建台,高一丈二尺,圬以百垩,赤其四角,广狭方正称焉。[4]1018据龚立本编次的《(崇祯)常熟县志》记载,“龚景材宅,在县西,五世同居,以孝义称。麟德元年诏旌。”[5]112陈映对于四人所在处所的叙说,把乡贤与常熟故土的可视景观结合起来,呈现了由此形成的地方人文景观,使得乡贤具备了在地联系的客观性。这又是常熟乡贤文化的重要特征。乡贤文化具有精神性特征,它必须通过客观显示性才能发挥社会功能,建祠祭祀是显示,人文景观也是显示。这种显示性在乡贤文化传播中意义重大。突显相关景观的显示性和联系性,能够更好地收获乡贤精神传播之效。
陈映在论说邑之望后说道:“其风俗之美,犹可概也”,即借助于巫咸、泰伯、言偃、龚景材之“山”“墟”“里”“闾”,可以概而见到常熟风俗之美。这就是说,这些杰出的乡贤是常熟风俗之美的表征,这种表征性人文景观,是先贤移风易俗、德播天下的结果。这使县令陈映感到欣慰。陈映说:“环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时主客以户计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今五万一千三十八,夏赋金钱为缗二钱八百,其币帛匹合万二千三百,而斛财损其旧二千。”常熟是财赋重地、风俗美邑,环府居其望。但在此同时,陈映也说道:“邑之事,其倍称何如哉!”“资粮巨万,以日馈给。营缮百顷,以时调度。苟有不至,责且乏兴。若民兵之事,由如是。”“比为令者,材若不济,负罪投劾而去者,顶背相望也。”陈映在叙说治邑之难后接着说邑之望,是要表明自己将以邑之望为范,“率以淳厚简孚交相为治”,以德行和功绩,“庶乎列名下方其无辱”。陈映的这种自我表白,提示了彰表乡贤具有敦风俗、美族邦的政治功能。乡贤具有在地亲善性,容易使人产生共鸣,使得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这是乡贤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人文性、显示性和教育性,这是陈映在论邑之望时所隐含的乡贤文化思想,它提示了常熟乡贤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性体现的是乡贤文化的价值选择,显示性体现的是乡贤文化的传播意义,教育性体现的是乡贤文化的教化功能。陈映所论在不经意之间,为常熟乡贤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常熟乡贤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后代在邑之望四位乡贤中,尤其突出的是言偃,次则是仲雍,或是两者同列。基本看法是:“仲雍与泰伯一起,将中原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吴文化的宗祖,常熟也成为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言子与仲雍一脉相承,仲雍是吴文化的奠基者、吴地礼仪教化的启蒙者,而言子则是吴文化的发扬光大者、吴地崇文重教的开导者。”[6]“虞当商周间,不犹然荒服榛莽之区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入而宇内尊虞者,傲然与邹鲁埒。”[7]154尤其是言子这位乡贤,对常熟文化发展的贡献其功至伟。知县王叔杲《重建文学书院碑》说:“勾吴自泰伯端委以治,而尚仍文身之陋。惟子游北学于中国传仲尼之道以归,而大江以南学者莫不得其精华,由是称文献之邦者。盖三千年于兹,其功非亚于仲尼者与?”[8]299常熟是言子的故乡,他晚年南归传道,“文开吴会”,成为“南方夫子”。因此,常熟对于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先贤怀有特殊感情。《至正重修琴川志》就把邑治与言偃紧密联系起来,在卷第一“叙县”中说:常熟公廨是“单父之堂,言游之室”[1]7,王爚易曰道爱;在卷第三“叙官”中说:“乃若治县之谱,在学道爱人格言具在,而邑先贤言游之施于武城者,尚可考,故作叙官”[1]30;在卷第八“叙人”中说:“盖常熟地本荆蛮,前乎此篾可纪矣。自仲雍以礼逊为化、子游以文学名科,而文物彬彬,实表于他郡国。”[1]73“常熟,古壮县,诗书礼乐之地。自言子游亲圣门以来,人才宜不乏。”[1]76常熟志书如此重视言子与常熟的亲缘密切关系,并认为常熟是“虞仲、子游文化之地,不可无纪”[1]1,可见言子等不愧为“邑之望”的代表人物,需要特殊尊崇。
常熟最初的“邑之望”论,确定了乡贤文化建设的特色,后代基本沿此思路推进。如明代在虞山书院选址时,就重视通过形胜古迹来传承先贤文化传统。虞山书院坐落虞山北麓,而虞山是一座东南文化名山,其上就有仲雍和言子两位先贤的墓。张鼐在《地胜志》序中指出:“滨海而国曰虞,其山曰虞山,皆以虞仲传也。或曰:商巫咸居虞山,在虞仲前,虞仲让国居其地,为商逸民。后七百年而言子出,则地之胜又有以言子传矣。嗟乎,桑沧有改,山陵可移,古来灵异之区埋没,莫可记者多矣。而兹山之胜代封而识之以迄于今。”因此,虞山书院能同大贤陵墓比邻,可谓“地胜”。张鼐又说:“令公(耿橘)直欲引其千年来表彰,一念而使人人识其所为,言子虞仲者,以归之于圣人,是令公之祀胜又不在山水灵异之间也,志地胜。”[9]108-109俞汝楫也说:“当虞仲子游两墓间直下三百步许,南为文学里迤,北西入堂室精舍,与言子祠杰然鼎峙。从言子祠出游艺门,北通射圃,南达讲武厅,而中为弦歌楼,楼高三十余尺,山南诸胜始毕献目前。”“盖城内山南一隅,其古迹若亡若在,地势忽高忽平,䟱莽葱郁,泉石祠宇,分奇缀胜,而书院成遂全收诸堂室之中,亦虞山有灵秘,此胜地一开千万年道脉之传也。”[9]111-112围绕着虞山书院,是名城常熟的历史古迹,有虞山、言子墓、墨井、子游东巷、子游西巷、景言巷、景言阁、子游阙里坊、文学桥、吴公祠、言氏家庙、莞尔亭、致道观、观德堂、弦歌馆、兴贤池、读书台、影娥亭、巫咸祠、清权祠、六先生祠、尚湖等,这些人文古迹呈现着常熟先贤的精神内涵。虞山书院的选址,充分利用了乡贤文化的人文性、显示性和教育性特征,使之成为激励后人追踵前贤、化民导俗的精神家园。乡贤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通过有形显示性来潜移默化的。张以诚在《虞山书院志》序中说:“学不在诵读而在此勃然瞿然者也。此勃然瞿然者又必有触而动,故君子欲移天下之心志,必先正天下之见闻,欲正天下之见闻,必先道之以礼乐。”“今河间耿侯来令常熟,慨然以表章先贤兴起后学为己任,考故址而鼎新之名曰虞山书院……足使人闻且见之而勃然与瞿然化者矣。”[ 9 ]102-103景行于前哲,场景触动极其重要,它能使君子“勃然与瞿然化者”,达到“移天下之心志”。
乡贤与入祠祭祀
建祠祭祀乡贤,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因此它是乡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对名宦和乡贤的区分原则明确,但早期人们往往不去严格区分,这就导致了范围边界不很确定的先贤祭祀。相传周代就有“祀先贤于西学”之制。郡国名宦乡贤之祀在宋代已经普遍,元人就有“古乡先生没,而祭于社。乡先生之德,乡人心悦而诚服者,其秩于祭,宜哉”[10]之论。常熟乡贤祭祀同样如此。明代以前,常熟建祠祭祀往往以先贤概之,且地域要求不严。宋先贤祭祀有记的是:言子专祠,南宋庆元年间创建;商相巫公祠,祀商相咸及子贤,宋祀于言子祠夹室;五夫子祠,祀先贤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六先生祠,祀周濂溪等理学家;张尉旭祠,祀草圣张旭,在庙学土地祠内;王爚生祠,在庙学以内。元乡贤祭祀有记载的是:常熟知州卢侯生祠、二戴祠(祀戴德、戴圣)、庙学三贤堂(祀宋诸儒)等。明代初期,教谕傅著建先贤祠于吴公祠东,祀范仲淹、胡瑗、王爚;明代前期,巡按御史命知县祝献将言子祠移至文庙东(先贤子游祠),祠之两庑列祭祀多位乡贤。
明初,朝廷推动各地庙学建立名宦祠和乡贤祠,地方官也以改建或新建名宦、乡贤祠为己任。其具体过程是:(1)正面提出先贤祭祀附学。洪武二年(1369),在整顿各地祀典基础上,推动乡贤附学。“庙以尊圣贤,政教之所由出也;学以养士子,政教之所由行也。”[11]学校作为教化之本,包括教学与祭祀二途,士人所习乃是孔子之道,而崇祀先贤也是作孔之道。(2)诏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洪武三年(1370),又令天下学校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春秋仲月,亦得附祭庙庭。这仍是承袭旧制,乡贤与名宦“同堂合祭”,即一祠左祀名宦,右祀乡贤。(3)令天下学校分设名宦、乡贤二祠。弘治九年(1496),祠祭郎中王云凤请天下府州县学校悉立名宦、乡贤祠,遂为定制。此后地方学校新建或改建的名宦、乡贤二祠,位置多于孔庙宫门外左右。弘治九年(1496),知县杨子历稽乡贤所当祀者,祀商相巫咸于西夹室,宋陆绾、钱观复、钱佃、周容、冷世光、崔敦诗、周虎、邱岳、陈元大、钱俣,列吴公祠西壁;张洪、吴讷列吴公祠东壁。弘治十三年(1500),杨子器重修庙学,充拓庙址,重建礼殿五间,东西两庑各七间,戟门三间,左乡贤祠、右名宦祠各一间。这就有了两祠分设的空间条件。据《[嘉靖]重修常熟县志》(1538)记载,列入乡贤祠的祭祀对象是:
商贤臣巫公咸子贤;宋和州防御使周忠惠公虎,尚书职方郎中赠中散大夫陆公绾,朝散郎赠金紫光禄大夫钱公观复,江西路转运副使中奉大夫钱公佃,孝子周公容,殿中侍郎御史冷公世光,翰林院权直赠中奉大夫崔公敦诗,龙图阁学士封东海郡侯丘公岳,温州府儒学教授陈公元大,福建路提举朝请郎钱公俣;明工科给事中黄公钺,翰林院修撰止庵张先生洪,都察院作副使御史谥文恪吴公讷。[12]
嘉靖中,移地新建乡先贤巫公祠,专祀巫咸及子贤,因此,巫咸父子移出文庙乡贤祠祭祀。后文庙乡贤祠祭祀名单有所扩充,这一名单在《[万历]常熟县私志》(1617)和《常熟县儒学志》(1610)中相同,均为51名,位次如下:
宋:周容、陆绾、翟汝文、钱观复、冷世光、钱俣、钱佃、崔敦诗、周虎、丘岳、王万、陈元大;
明:黄钺、张洪、吴讷、鱼侃、程式、章格、程宗、杨集、徐恪、桑瑾、李杰、瞿俊、陈喆、陈易、沈海、周木、王宗锡、卢翊、丁仁、时中、蒋钦、陈播、王槐、唐天恩、陈察、邹武、陈寰、王舜渔、陈逅、邓韍、钱泮、严讷、瞿景淳、陈瓒、邵圭洁、陆一风、赵用贤、蒋以忠、王之麟。[13]
明万历以后,常熟乡贤祠明代入祀名单又有新的增加①如龚立本《(崇祯)常熟县志》记:“乡贤去留无常,弘治初惟吴文恪、张修撰洪存。知县杨子器历稽所当祀者,祀商相巫咸于西夹室,而宋陆绾、钱观复、钱佃、周容、冷世光、崔敦诗、周虎、丘岳、陈元大、钱俣,列吴公祠西壁,修撰文恪列吴公祠东壁,位号载桑《志》,其并入今祠,未详所始。益以咸子贤及翟汝文、王万、黄钺,凡十七人,而御史章珪且不与焉,严可知已。嘉靖中,巫公父子议立专祠,春秋祀以少牢,而周孝子容遂首列。后有鱼侃、程式、章格、程宗、杨集、徐恪、桑瑾、李杰、瞿俊、陈喆、陈易、沈海、周木、王宗锡、卢翊、丁仁、时中、蒋钦、陈播、王槐、唐天恩、陈察、邹武、陈寰、王舜渔、陈逅、邓韍、钱泮、严讷、瞿景淳、陈瓒、邵圭洁、陆一风、赵用贤、蒋以忠、王之粦、瞿汝稷诸公相继在列。”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61-62页。。
民国初编纂《重修常昭合志》,记录了自宋至清末入祀乡贤祠的总体名单,共105名:
宋:周容、陆绾、翟汝文、钱观复、冷世光、钱俣、钱佃、崔敦诗、周虎、王万、丘岳、陈元大、王坚、王安节;元:褚不华、褚伴哥;
明:黄钺、张洪、卫浩、吴讷、鱼侃、程式、邓彦章、陆懋、章格、程宗、杨集、桑瑾、陈易、李杰、徐恪、桑悦、沈海、瞿俊、陈喆、周木、王宗锡、时中、卢翊、陈播、王槐、蒋钦、唐天恩、丁仁、陈察、张文麟、邹武、丁奉、陈寰、邓韍、王舜渔、陈逅、张文凤、钱泮、严讷、瞿景淳、邵圭洁、陆一风、查光述、陈瓒、严澂、瞿汝稷、王嘉言、蒋以忠、赵用贤、陈国华、王之麟、陈禹谟、翁宪祥、陆重科、徐待聘、宋懋中、顾大章、龚立本、魏浣初、许士柔、王梦鼎、王梦鼐、杨彝、孙永祚、赵士春、蒋棻、归起先、钱永达、项志宁;
清:钱朝鼎、王曰俞、王澧、李临、蒋伊、周庆曾、翁叔元、归允肃、汪惟时、汪锡爵、席启寓、程云蛟、严虞惇、归宗敬、蒋廷锡、蒋溥、归宣光、陈祖范、张敦培、张大镛。[4]308
以上名单并不尽善尽美,恰如《重修常昭合志》所说:“将后贤之济济,迥倍前贤耶?抑前贤之子姓所为表彰先烈者,会不若后之切耶?有识者所宜参观也。”[4]308但这些人物相继在列,还是呈现了常熟乡贤文化传承的精神谱系。
乡贤祭祀附学,是在府州县儒学里建立乡贤总祠,集中奉祀本地的乡贤,这就开启了乡贤祭祀的新模式,改变了各地乡贤祭祀多且散的状况。庙学建立乡贤总祠后,祭祀对象众多,地点集中,时间有常,费用保障,行礼简便,易于坚持,各地庙外乡贤专祠因此相应减少。但是,还是保留或新建有专祠,这样就形成了庙学乡贤总祠合祀、庙外乡贤专祠特祀的状况,常熟也是如此。据《重修常昭合志》,庙外乡贤专祠大致包括:巫公祠,祀商相咸及子贤,有司春秋致祭;泰伯祠,祀勾吴首任国公,地方官致祭;清权祠,祀虞仲,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地方官致祭;虞溪书院,祀虞仲,始建于明弘治中,春秋致祭;五夫子祠,祀宋理学家,地方官致祭;黄忠臣祠,祀明给事中忠节钺(黄钺);程公祠,祀明刑部员外郎式(程式);蒋忠烈公祠,祀明御史赠光禄寺少卿钦(蒋钦);唐公祠,祀明叶县赠光禄寺少卿天恩(唐天恩);钱公褒忠祠,祀明江西左参政赠光禄寺少卿泮(钱泮);顾裕愍公祠,祀御按察副使赠太仆寺卿大章(顾大章);瞿忠宣公祠,祀明大学士临桂伯式耜(瞿式耜);王忠壮公祠,祀宋宁远节度使坚(王坚);王忠惠公祠,祀宋太常少卿万(王万);陈北山先生祠,祀宋温州教授元大(陈元大);吴文恪公祠,祀明副都御史讷(吴讷);张修撰祠,祀明翰林院修撰洪(张洪);崇勋祠,祀明大力寺卿章格;程尚书祠,祀明工部尚书宗(程宗);桑渊静先生祠,祀明处州通判瑾(桑瑾);思玄先生生祠,祀明通判桑悦;瞿副使祠,祀明按察副使俊(瞿俊);李文安公祠,祀明礼部尚书杰(李杰);徐公祠,祀明工部侍郎恪(徐恪);张公祠,祀明建宁知府文麟(张文麟);严公祠,祀明封大学士恪(严恪);严文靖公祠,祀明大学士严讷;邵北虞祠,祀明德清教谕圭洁(邵圭洁);瞿文懿公祠,祀明礼部侍郎景淳(瞿景淳);赵文毅公祠,祀明吏部侍郎用贤(赵用贤);许公祠,祀明国子监祭酒士柔(许士柔);双相祠,祀清蒋文肃公廷锡、文恪公溥(蒋廷锡、蒋溥);严太仆祠,祀清太仆寺少卿虞惇(严虞惇);归昭简公祠,祀清工部尚书宣光(归宣光);瞿氏先贤祠,祀明文懿公景淳、太仆寺少卿汝稷、布政参议汝说、忠宣公式耜;等等。以上庙外乡贤祠,有的不久即废,有的存续较长,有的属公建,有的属私建,有的是家祠。但这里的人物,大多列名庙学乡贤祠。虽然记载也有遗漏,但由此可见常熟建祠祭祀乡贤风气之盛。
祭祀,是发挥乡贤文化教育教化功能的重要方式。乡贤祭祀,包括一系列的礼仪,加上陈设、祭品、仪品,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使人对乡贤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神圣体验。《常熟县儒学志》在《祭仪志》中规定,首先是“斋戒”:正祭前三日,献官并陪祭官、执事人等沐浴更衣,散斋二日,各宿别室,致斋一日同宿。常熟祭祀仪式中诵读的祝文是:乡邦俊彦,后学斗山,风教敦俗,时祭是虔。这里阐明了祭祀对象受祀的原因,表达了参加祭祀活动的情感,揭示了祭祀活动的社会意义。
乡贤与江南儒学
言子身后1600余年,南宋理学家朱熹郑重地向常熟士人发出了振聋发馈的吁请:“孔门设科之法,与公之所谓本、所谓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则愿诸生相与勉焉,以进其实,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复有如公者出。”[14]3到了元代,学者黄溍说:“常熟故吴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已若夫为弟子而藏修息游于斯者,皆生于子游之乡,而得其风气习俗之美者也,苟无辜乎。居之安,食之饱,而必有事,将见其处也,必无愧乎。子游文学其出也,必无忘乎。”[15]289学者陈基也说:“子游往矣,其嘉言微行,见于孔门师友之问答,千世之下,四海之内,读其书皆知其有所兴起,况生乎其乡者乎,况弦歌其文学以教其子弟者乎。”[16]307以上学者,皆从先贤与后贤关系的视角,对常熟士人学子提出殷切期望,希望言子故乡后学以前辈乡贤言子为范,学道知本,成为如言子那样的乡贤人物。
随着常熟尊言学贤活动的推进,常熟学人不仅普遍认同言子这位孔门大贤,而且从在地视角把他视为“乡贤”“乡先生”。“先贤”的本义是先世的贤人,特定情形下也指“先世的乡贤”。明常熟乡贤严讷撰《文学书院记》,首句说:“先贤言子,吴产也,尚矣”[17]131。他强调言子是常熟乡贤,并把言子与县令王叔杲联系起来,揭示了他们同官同政:“公治先贤所产之邑,而首崇先贤,以风乎邑人,是与先贤同官而亦与先贤同政,斯于吏道,实为得之,而视夫斤斤簿书者,不同年而语矣。夫武城小矣,且服先贤文化,而有弦歌之声。公之化即先贤文化,而吾邑方幸被之,将于文学盖茂进焉,而弦歌云乎哉。”这就使昔时武城宰言子和现时常熟令王叔杲产生了亲缘关系,使言子形象变得可亲可爱。由“先世的乡贤”,常熟又生出“乡先生”“先师”的称呼。明王鈇《重修儒学碑》中有“子游言公,邑之乡先生也”之句。明杨一清《常熟县重建吴公祠记》中,有“先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祀,故乡先生没则祭诸其社”句。明洪武间县学教谕傅著在《子游像赞并序》中说:“星辰之昭明,河岳之流峙,将愈而益彰焉,其先师子游氏之神乎?”不但称言子为先师,且称其为先师之神。以上称呼表明,常熟士人官员普遍认同言子是邑之人望(乡贤),也就是说,言子这位孔门先贤与后代常熟先贤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特定的师承关系,言子是一位同常熟后世乡贤有着“先师”“乡先生”关系的先世乡贤,这就在常熟构建起了一个前贤后贤相继相续的精神谱系。
基于以上状况,常熟乡贤文化构建的言子与后代乡贤之间的特殊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特殊的师生关系,即强调言子是常熟学子的先师。如明常熟教谕许成器说:“古者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先贤犹如鼻祖,大宗亘古。今孔子尚矣,乡党一篇,以身教万世。子游非海虞之先师耶?其受先圣之传,惟礼为兢兢,实与颜曾称南北宗。”“二三子之尸祝先师,非一日矣,岂其不望以为趋,而随俗厝趾?”这就从先圣与先师的关系,从孔门子游与海虞学子的关系,阐释言子是常熟学子的先师,学言可达先圣之道。许成器认为,以言子为先师,最高境界是相契言子心斋密藏,其次是成为言子武城弦歌嫡派,再下则可以成为行不由径、私不谒室的澹台式人物。[18]135吴人徐有贞认为:“盖子游之学之道也,仲尼之学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之道也。”“吾愿与二三子省之,由子游以求乎仲尼,由仲尼以求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于道也,若溯流而求源,由一心而运之天下,小试而为弦歌之治,大行而成礼乐之化,庶几哉其古若尔矣。”[19]69这就勾勒出一条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言子,再到常熟学子的师承线索。而常熟士人认言子为先师,愿踵其迹。陈察列祀常熟乡贤祠祀,他在《重建昭明读书台亭记》中动情地说:“虞仲清权,德高千古,子游礼乐,道契圣心。二公遗芳孔迩,过祠则式,经墓则吁,不假外求,得师也已。虽然,学何常师。宅心砥行,吾从至让;学道爱人,吾仪丹阳公博文;缮性敏政,吾兼资不遗乎昭明。食实采英,敦本该末,主善协一,归成吾美,夫何不可。是则斯举固君子所不废也。”[20]41陈察认为自己所学,不假外求,愿以乡贤为师,君子不废。
二是特殊的从祀关系,即强调言子是常熟在地的儒宗。基于言子在儒学道统中的特殊地位,也基于言子在江南发展中的特殊贡献,常熟在南宋即建立言子专祠,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移建于文庙东。这次言子祠移建的意义在于:言子祠移至学东,扩大空间,自成轴线,从而形成了常熟文庙南北三条平行轴线,殿宇三大建筑群落,即中为庙、西为学、东为言祠。这时正值朝廷积极推进乡贤、名宦附学之际,其意是把乡贤、名宦逐步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和政教系统。朝廷对于附学祭祀者有着明确规定:凡有功于圣门者,始得从祀。附学乡贤出处、事业虽有不同,但都是孔子之道的践行者。乡贤由此获得了儒学的浸润,完成了乡贤祠祀的儒家正统化改造。这对于言子在常熟文庙祭祀中的地位变化有着直接推动意义。乡贤附学,是使乡贤成为孔庙祭祀系统中的次级层次,乡贤附食圣贤之列,实质是孔庙祭祀延伸的一种附祭。而常熟文庙又有言子祭祀轴线,这就有个恰当处理孔子与言子以及其他乡贤三者关系的问题。常熟文庙所取方式是其他乡贤从祀言子祠。明天顺三年(1459),知县唐礼重修吴公祠,以乡贤从祀吴公。乡贤李杰撰记认为,“是邦才俊继出,见用于世,文章政事,后先争光,遂为诗礼文物之薮,未必不因子游之风而兴起也”;因此,“唐侯又以乡之后贤,如范文正公诸位神主,从祀于内,俾是乡之人益有所观感而奋励焉,其有关于风化大矣”。[21]71这就指明了言子先贤与乡之后贤的关系,也揭示了后代乡贤从祀先贤言子的可行性。成化二十二年(1486),言子祠东移重建后,正殿三楹祀先贤言子,两庑以范仲淹、张洪、言信、吴讷、徐恪、周木从祀。明弘治九年(1496),杨子器宰邑,始例举乡贤、名宦所当祠者附庙祭祀,名宦列于文庙戟门东西夹室,乡贤均列于文庙吴公祠东西壁。后杨子器重修文庙,建成乡贤祠和名宦祠,即把乡贤名单中宋诸公俱入乡贤祠,独留张洪、吴讷两公,益以徐恪、周木,总四公从祀言子。后又调整从祀乡贤为六人,即宋范公仲淹、明张公洪、吴公讷、徐公恪、周公木、言公信,此一从祀名单延续到清末。[22-24]常熟文庙通过从祀方式,呈现了先贤言子与后来乡贤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其本质是呈现在地儒学道统的师承关系。
特殊的师生关系,特殊的从祀关系,揭示了言子与其他乡贤之间的非凡关系。在此基础上,明万历年间,耿橘等复兴书院,建立虞山书院,试图通过整体空间布局和祭祀格局建构,把这种关系固化起来,建立一个在地的儒学道统谱系。耿橘和顾宪成对此的叙述是:
书院讲堂,镌孔圣大像,为会众所瞻依,表所宗也。言子祠,土塑言游大像,乡贤故重之尔。讲堂四周,精舍十五,各镌一小像于中。孔门之颜、曾、思、孟,汉之董,宋之周、邵、程、张、朱、陆,本朝之薛、陈、胡、王咸在。尚友之藉,思齐之感,不可或遗矣。子祠后,书楼之前,经房六,各镌一小像于中。如易之伏羲,书之尧舜,诗之文王,春秋之孔子,四经之祖宗,学者之日月,无待言矣。惟礼、乐二经,自昔不传。汉人集诸古文为记,今人亦谓之经,而记中颇录言游氏之文。如《礼运》诸篇,其钜者也。用是两房皆像言游。(耿橘《耿令公宗像赞引》)
颜其祠曰:“言子”,亲之,亦尊之也。配以游寓梁昭明太子统,名宦宋县令孙公应时,邑贤明修撰张公洪、都宪吴公讷、侍郎徐公恪、别驾桑公悦、大忝周公木、孝廉邓公韍、县幕朱公召、布衣邹公泉,从舆望也。又为之溯厥渊源,颜讲堂之前曰:“愿学孔子”。……旁建精舍,颜曰:“友颜”“友曾”“友思”“友孟”,而汉之董,宋之周、邵、二程、朱、陆,我明之薛、胡、陈、王诸先生,俱次第列焉。是子游之所后先,二千载之间相与奔走,作孔子羽翼者也。(顾宪成《虞山言子祠记》)
这个祭祀体系设计颇具匠心。(1)孔子与言子的关系。虞山书院用“愿学孔子”标识二者关系,耿橘认为孔子是大宗,镌孔圣大像,言子则是小宗,土塑大像。耿橘认为,“匹夫而承五帝三王之统者,孔子一人而已。故孔子以前,五帝三王之统,天统也,非人也。孔子以后,秦汉唐宋之统,人统也,非天也。”“夫大江以南,得孔子之天统者,言子一人而已。”[24]297言子愿学孔子,北学圣门,精于礼乐,得圣人之一体。(2)言子的在地儒宗地位。虞山书院建筑群落,居中的是子游祠,东侧是学道堂,西侧是弦歌楼。学道堂祀孔子,周围有15个精舍。言子祠前左右有王叔杲和杨子器两位的名宦祠。弦歌楼为藏书楼,两边各三经房分别镌小像,礼经房和乐经房刻子游像。此空间格局,是把言子作为在地儒宗祭祀,“亲之,亦尊之也”。张鼐认为,祀以报本,本者,一也。“邑自言子出而斯道大明。言子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在南国。言子上有功于孔子,而下有恩于海虞千百世。故祠祀言子,报本也。”[25]150孙慎行认为:“孔门之传行于东南,实自言游始。况以虞山之人,师虞山之贤,以虞山之令,弘虞山之道,固其所也。”[26]154(3)言子与师友后贤的关系。学道堂周围十五个精舍,分别颜友颜、友曾、友思、友孟、友董、友周、友邵、友程、友张、友朱、友陆、友胡、友薛、友陈、友王,并分别镌刻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董仲舒、周濂溪、邵雍、伊川二程、张载、朱熹、陆象山、薛敬轩、陈白沙、胡敬斋、王阳明小像。这表明以上十五位先贤,有的是言子的同门师友,有的则是言子的后学,但他们都是平等相接的朋友,都是孔子的羽翼。(4)言子与常熟乡贤的关系。虞山书院言子祠中从祀者共十人①据《万历常熟县私志》,虞山书院从祀言子名单的确定,是在文庙言子祠从祀四人(张洪、吴讷、徐恪、周木)的基础上,县令耿橘益昭明太子统、宋县令孙应时及邑人桑悦、朱召、邓韍、邹泉,总计十人。,即萧统、孙应时,张洪、吴讷、徐恪、桑悦、周木、邓韍、朱召、邹泉。除名宦孙应时外,余为乡贤。顾宪成认为,选择十人从祀是“从舆望”。张鼐这样说:“从之祀者,有孙公应时及诸名人,凡十余人。诸名人本言子,言子本孔子,孔子之真血脉,至今在海虞。”“识得此本,便为言子真正弟子,为孔子的骨孙。”[25]150
虞山书院构建的空间结构和祭祀体系,明确了言子作为在地儒宗的地位,也明确了言子与在地乡贤的特殊关系,这是常熟乡贤文化的重要特色。
乡贤与文化传承
在常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乡贤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常熟著名乡贤,或致仕在外,或退居乡邑,都能关注并参与乡邑建设,尤其是乡邑的文化建设。由于乡贤在民间颇具舆望,其人之德行风节、文学事功、遗风余烈洽于所见所闻多传闻者,所以他们的参与对于常熟文化建设贡献至大。
首先,乡贤阐释子游文学传统。南宋接引子游传统落地以后,常熟官员和士人不断地阐释子游传统,正是在此阐释中,子游传统得以生根开花结果。而在此阐释进程中,很多时候或关键问题是借助乡贤实现的,这里以常熟书院数次变更复建为例说明。
元代至顺年间,常熟创建“文学书院”,命名取义言子习于文学。元至正年间废,明宣德间县令郭南改建,更名“学道书院”。乡贤张洪撰《学道书院记》,阐明书院改名初衷:
以子游为邑人,北学于中国,圣师目其所长,故曰文学。及为武城宰,施其所学于民,故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形莞尔之笑,有牛刀之戏。而子游以学道为对,言君子学道,应推己以及人,故能爱人;小人学道,知职分之当为,故亦易使。然则弦歌者,学道之具,非以道为弦歌也。
诗以兴起前,乐以涵养于后,故以弦歌为学道。但昔子游之学道,本末兼该,重在小人,故以之为教于邑中。周公学道,先用力于根本,重在君子,故以之标名于书院。[27]55
张洪揭出了子游文学的真谛,即学道爱人,弦歌之声的内涵,即本末兼该,其要义是社会教化的善治德政。因此,书院之名改“文学”为“学道”,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子游传统,重在要求君子用力根本,深求学道,同时也寄望地方大夫学道爱人,以为出治之本。
学道书院“年久颓废”,邑人周木、孙楼等提出复建,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县王叔杲改建于虞山下,名文学书院。其考虑是:“兹固先贤吴公之乡也,国家方以文学造士,今仅有祠而书院不立,造士之制无乃缺诸。”乡贤瞿景淳对此深表赞同,撰《重建文学书院记》,说明了恢复“文学”命名的深层意义:
余独念今之以文学名者,或有异于吴公也。吴公之文学盖笃其实,非徒饰空言者。若今之文学,徒饰空言,为干禄之资尔,无乃有异于吴公乎!世有豪杰之士,必有不安于科举之习,而以操履为重者。矧至吴公之乡而依其门墙,可图浮华是竞以忝吴公乎?[28]130
瞿景淳借机阐释子游文学的涵义,强调其特质是“笃其实,非徒饰空言者”,“以操履为重者”,并对时人错误理解提出批评。这实际上是在恢复孔子教育的本质,即培养能够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豪杰之士。与此同时,乡贤严讷也在《文学书院记》中阐释“子游文学”:
武城小矣,且服先贤之化,而有弦歌之声。公之化,即先贤之化,而吾邑方幸被之,将于文学益茂进焉,而弦歌云乎哉。虽然子游以文学称,而其闻诸夫子者,不过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然则其所谓学者,学乎道也,而文亦文此而已。[17]131
严讷的阐释,同样由现象到本质,揭示了子游文学的特质是教化,同时也对“今之所谓文学者,殆异于是”提出了尖锐批评。瞿、严的阐释,对于准确理解子游文学意义重大。
万历初毁天下书院,文学书院仅存祠。三十四年(1606),知县耿橘重修,名虞山书院,乡贤周木在《请复建先贤子游祠院疏》中,对于言子的思想和功绩做了明确的概括:
子游学宗大成,产由常熟。夫常熟素号荆蛮,诗书礼乐焉能家喻户晓,自子游特起,得圣道精华,倡教于东南。如论学必崇本抑末,为政以学道率人,论丧贵其致哀,取士务其正大,规友戒其难能,得圣一体,列名充科,东南籍以移风易俗。而常熟尤为耳濡目染,迄今士行彬彬,民重廉耻,弦歌雅化,恍然可挹。[ 29 ]308
周木突出了言子文学教化的特质,强调其崇本学道,得圣人一体,如此,东南得以移风易俗,常熟则得以士行彬彬,民重廉耻,弦歌雅化。
以上诸位乡贤,借着书院变更连续阐释子游文学传统,其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这种阐释恢复子游文学的真实内涵,直击子游文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子游文学的传承路数。它持续端正了书院的办学思想,对于常熟继承子游文学传统,形成崇文尚和风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乡贤推进弦歌之政。地方官员尊重乡贤,乡贤则参与地方建设,这是常熟历史上乡贤与地方互动关系的基本状况。乡贤张洪阐释子游文学要义,归结为“吾邑之大夫当深求学道之意,以为出治之本可也。”官员周驰则说:“子游在圣门以文学著名,而其宰武城则能以学道爱人为先务。常熟,公故里也,凡官于此者,当以公为则。”[30]33乡贤相互呼应,在常熟推行弦歌之政中协同合作,这是常熟弦歌之政的重要特征。明嘉靖年间,东南地区经常受到倭寇侵扰,为抗击倭寇,知县王鈇决定重修城墙。这就有了乡贤邵圭洁的《筑城议》、严讷的《东南寇灾请蠲恤疏》等,也就有了王鈇动员民众集资重修县城之举。王鈇募集民勇,抵抗倭寇,大败敌人,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误中埋伏,与敌奋战,受创死难。常熟民众怀念忠烈,建祠纪念。乡贤陈逅有《褒忠祠碑记》,陈瓒有《赠太仆少卿常熟知县王公墓表》,邵圭洁有《祭王苍野母子文》,严讷有《赠太仆少卿县令王公墓铭》等。官员和乡贤在保卫家乡中互相配合,官员殉职后乡贤纷纷表达崇敬感情,令人动容。
武城弦歌之政,其理政思想是学道爱人,施政目标是惠民教民。其惠民,即发展生产,造福民众;而教民,则兴教办学,礼乐教化。常熟历任官员崇文重教,乡贤对此充分肯定,并撰碑记予以彰表,阐发意义。如明正统年间,常熟县陈澄新、郭南两任知县,捐俸为倡,官民合力,鸠匠市材,建成“尊经阁”,以储藏儒学经典。邑贤吴讷撰《常熟县儒学新建尊经阁之记》,结尾说及写作情形:“愚也年登八十,杜门待尽,笔砚久废,故是阁之记,五年之间屡辞邑官之请。今则弗克终辞者,盖欲因是尽悃愊以告乡邑后进,俾勿悖先圣贤之训也。若夫本武城弦歌之政,推广学道爱人之心,此邑之令佐当自勉,以求无忝其职者,然亦耋老之深望云。”[31]59吴讷撰记,是为了推动邑治的弦歌之政,其言其行令人感动。尊经阁后有多次修葺,乡贤也有撰记,如沈应魁在明嘉靖间有《重修常熟县学记》。清乾隆十七年(1752),乡贤陈祖范又撰《重修尊经阁记》,强调“吾邑独以言子故里,独占南华之号,讵不美哉?”[32]209要求“吾乡子弟”三复朱熹告诫,“百世之下,复有如公者出”。常熟乡贤普遍肯定地方官员兴教办学的功绩,如李杰在《直隶苏州府常熟县重修庙学记》中,先说常熟为姑苏上邑,沾被文明之化最深以久,士之育才于学,而登贤科致仕者,独盛于南畿诸郡;后赞扬巡抚刘廷瓒重修庙学:“庙自圣贤像以及礼殿两庑,戟门、棂星门,焕然维新;学自师生舍馆,会馔之堂,习射之圃,以及碑亭坊表,翼然加饬。经始于甲寅之春,不五阅月而告成。于是阖学师生谓予宜有言以纪成绩。”[21]75这里具体记载了常熟重建庙学成绩,成为常熟文庙发展信史。
常熟地处江南河网地区,水旱灾害频发,农民苦其甚也。因此,常熟知县一般都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造福百姓。在常熟现存碑刻中,保留了相当数量乡贤记述官员治水政绩的碑文。如张洪《修浚七浦塘记》、管一德《开横沥湖漕等河记》、管一德《邑侯赵公议浚横沥塘碑》、管一德《议浚横沥赤沙碑》、陈寰《白茆港水功记》、陈瓒《浚奚浦记》、赵士春《瞿侯理漕流爱碑》、严讷《浚治白茆塘记》、严讷《白茆塘新建石闸记》、陈国华《重开三丈浦记》、沈应科《重浚盐铁塘碑》、管一德《重浚福山塘记》、翁宪祥《杨侯德远塘记》①以上所列,仅据邵松年辑《海虞文徵》所载文献,广陵书社2017年版。等。邓韍《渐斋先生王公碑》,记载知县王纶救灾为民的形象:“县连水旱,往时县官坐廨宇,受民所报而不核,公拿小舟遍历田野,虽雨涂沾体不为止,得其灾,为牍以告于上官。比户部文至,民税得免,或不免,盖于公于民无不得也。”[33]121吴讷《重建惠民药局记》,记述知县郭世南“捐俸赀以为众倡”,吏民协勤相助,重建惠民药局的动人事迹;张洪《济农仓记》,记述郭南扩建济农仓增加储粮,“居人过客瞻望者,啧啧载道”;张洪《义役仓记》,记述郭南仿效古制,建立义仓,减轻百姓役费。[34-36]知县郭南的惠民举措得到乡贤肯定,郭南入祀常熟名宦祠。
由上所列可见,常熟在推行弦歌之治时,乡贤与官员融洽合作,推动社会发展。对于乡邑治理中德政显著的名宦,常熟乡贤不吝笔墨予以铺叙、赞扬,这就有了一组常熟官员德政的碑记。如陈察《重修何孝廉祠碑》(何子平)、邓韍《渐斋先生王公碑》(王纶)、桑瑜《邑侯杨公像记》(杨子器)、瞿景淳《常熟县令永嘉王公去思碑》(王叔杲)、邑人《知州张公叙绩碑》(张允同)、龚立本《赠宫保前邑杨忠烈公》(杨涟)、赵用贤《常熟县三先生遗泽碑》(刘文诏、吕尚古、汪元臣)、魏浣初《邑侯杨公漕政碑跋》(杨鼎熙)、顾云程《耿侯去思碑》(耿橘)、顾云程《潜白黄公去思碑》(黄家谋)、陈祖范《重建于公祠记碑》(于宗尧)、翁贤祥《赵侯去思碑》(赵国琦)、翁宪祥《本石李先生遗泽碑》(李维柱)、许士柔《常熟县令严陵守侯去思碑》(宋严陵)、翁叔元《永平杨侯去思碑》(杨振藻)、翁叔元《江南布政使刘公墓表》(刘鼎)、翁叔元《城守林公德政碑》(林介石),等等。乡贤对于常熟名宦的肯定和赞扬,表达了深厚的乡情,期望家乡更好发展。
再次,乡贤德高望重激励后学。从舆望的乡贤是本土人才的杰出代表,他们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或兼而有之。明万历间管一德《皇明常熟文献志》,记载了诸位乡贤事迹,呈现了乡贤形象。如明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进士严讷,历进官职,其在吏部时:“严饬约束,远隙苞苴,能使长安中金贱而士贵。并用三徒振拔淹滞,而搜剔岩穴之士殆尽尽,岁余与兴化李公并召直西苑,加太子太保,俄并进武英殿大学士,仍管吏部事。始公为学士时,上特赐鹤袍,后益赐麒麟飞鱼服,以至绣蟒。”这是立功。后告辞回乡,“二亲尚无恙,据乡则恭谨益甚。虽少年书生与之讲钧礼出,遇鲜衣怒马,狼跄而来者,辙匿舆之,有以缓急告者,靡不饱所欲而去。尝置义庄以周族人。”这是立德。死后“所著有文靖公集十二卷,春秋国华十六卷。”这是立言。[37]24尤其是,乡贤寓居故里,都能严于律己,成为乡民楷模。如明英宗四年(1460年),吴讷告老返里,居室简陋,巡抚周忱拟帮助翻建,被谢绝。其平时生活淡泊,常布衣食蔬。乡贤有着激励后学追踵前贤的示范作用。因为乡贤乃乡人,耳闻习见,乡人对乡贤功德事迹的熟知,自然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盖人心有感发之机,天下有风动之理,使官于斯者皆有志名宦,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38]这就是乡贤对于乡里学子的激励、感动作用。这种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乡贤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
常熟重视乡贤文化的示范、导向作用。明万历间,侯先春撰《虞山书院弦歌楼记》,批评近世文学趋于章句,而不知经纬天地,弥纶忝赞之术,去文学之真精神益远。如何纠正近世文学之弊,侯先春主张向乡贤学习,具体说是向乡贤严文靖(严讷)和瞿文懿(瞿景淳)学习。瞿景淳的文章是“以其调之皆古”(严讷),即文章有本而根深叶茂;而严讷则是“以文学入筦机务,参大政者”,即文章通神明,可以治天下。这都同近世文学迥异,是得言子礼乐文章之真传。因此,侯先春明确地说:“吾愿邑之良子弟,由兹洗涤今时所习,竭力以求言氏之真精神。言氏之言,尽载《论语》《檀弓》,苟能因肤及髓,即未能非一旦媲美先贤,而侦如靖、懿两文公者,不将接踵起乎?”[39]296乡贤邵圭洁也是文界杰出人物,《皇明常熟文献志》介绍其文:“公制举义,匠心独妙,名彪映天下。策论尤奇拔古练,雅攻古文词,不斤斤绳削而清婉凄切”[37]34。这给了科举学子以范本,学子纷纷向学门下,虽其仕途不顺,但在乡里却受到普遍尊重。在他逝世以后,其私淑弟子推动地方官为其建专门坊祠,并议谥号为“文远”。推动建祠纪念的均为地方后起之秀,一同署名的有十六位,其中进士三位,举人五位,未有功名的有九人。后邵圭洁入祀常熟乡贤祠。瞿景淳、严讷、邵圭洁是明嘉靖后常熟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乡贤。耿橘复建虞山书院,意在传承言子“治邑以道,取人以节,论学以本”思想,建立新机制培养崇尚其实、以操履为重的国家有用人才。因此,在科举时文教学中,他反对“道自为道而文自为文,文与道二”的做法,强调为文致真,文章与道理不相为二的关系,认为“夫文之真者,谈理必晰;理之彻者,为文必超”。为达此人才培养目标,耿橘把瞿景淳、严讷、邵圭洁三位乡贤作为学子学习的榜样,以三位文章作为学子写作的范例。耿橘还邀请三位乡贤的子孙或门生参与虞山书院的教学、编志等工作。如邵圭洁门人孙森担任《虞山书院志》共十一卷的编次或校阅;瞿景淳孙子瞿汝稷撰《虞山会语跋》(卷九);瞿汝说撰《虞山书院有本室会艺序》(卷十);严讷儿子严澂担任数卷《虞山书院志》校阅,撰《虞山读书台记》(卷九);邵圭洁孙子邵濂是《虞山书院志》三卷的校阅者;邵圭洁门人钱时俊、翁宪祥、翁应祥等也参与其事。耿橘充分利用乡贤资源,推动了虞山书院教育思想的落地。以上以瞿景淳、严讷、邵圭洁三位乡贤为例,说明了乡贤文化直接影响着常熟文化传承,乡贤文化推动了常熟文化发展,这也就是常熟文脉得以延续、子游传统得以弘扬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