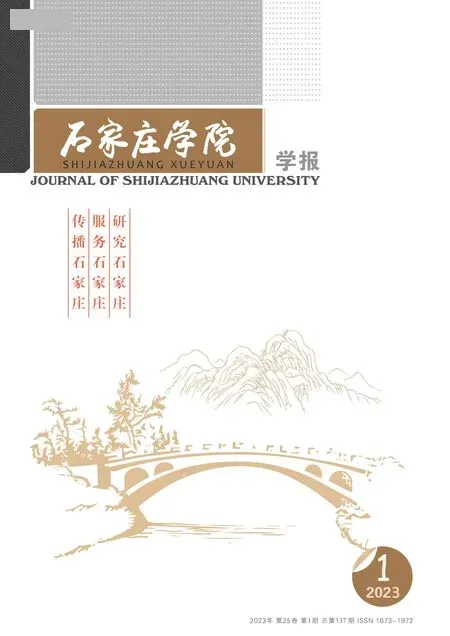启蒙的回归:张爱玲《五四遗事》中的男权问题
2023-04-07王栋亮
王栋亮,陈 珺
(1.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1;2.唐山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1]1-19的论断,意图从文学视角强调“现代性”意识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连续性,以阐明五四时代所呈现的现代性面貌是晚清以来量变累积的结果。这个论点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和逻辑性,是引导学界反思“五四”的切入点。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五四”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发展的界标,无论是从文学史、思想史还是政治史来审视它,其重要性都不言而喻。五四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知识界从思想启蒙转向了社会改造,以此作为现代转型的着力点。反过来,借助社会转型状况的分析,也可以成为我们透视、反思五四现代性广度和力度的镜子。正因为“五四”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时人在其后不久就开始纪念与反思,并在多个领域形成了平行的五四叙事体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它们共同构筑成了“五四解释学”。
在五四叙事构成中,五四文学又是不可或缺的领域,它起源于启蒙,而又反思、深化了启蒙本身。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间接记录与反映,属于抽象之真的史料,有时能更加深刻地反映社会现状,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2]399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①文中未标注《五四遗事》中的文献,均出自张爱玲的《张爱玲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是后五四时代的五四叙事,具有一定特殊性。作为知名的现代女作家,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领域,侧重于小说文本的解读,当然也有人独辟蹊径,关注张爱玲姓名的文化史研究②详见张小虹的《本名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具体到该作品的研究在于剖析“五四”与现代性的关系,如有研究者认为,作品是张氏个人情感史的镜像,其接续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题旨,又可与《伤逝》构成对话。[3]还有人认为,作品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五四”的现代性,但并不影响作者对其总体评价。③详见布小继的《阐释与建构:张爱玲小说解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26页;相似的成果还有冯黎明的《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上述成果主要以“文本细读”方式剖析作品的特色,品读其中映射的各种现代性隐喻,而对于作品中男主人公从观念到生活的蜕变缺乏深入解读,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剖析五四现代性特质的重要着眼点。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张爱玲对“五四”有何观感?这对包括《五四遗事》在内的文本的文风如何产生影响?从女性意识出发,她又如何展现其中蕴含的男权特质?这种特质与男主人公从“自由恋爱”到“三美团圆”婚姻蜕变有何逻辑关联?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有助于深化对于张爱玲及其时代主题的认知。
一、五四反思与文本的创作
张爱玲作为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传奇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进而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并形成了“张爱玲学”。她的代表性作品基本都受到了学界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其作品“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4]111。故而其小说的基调是“荒凉”,这是一种悲观的、带有女性敏锐细腻的感叹。与鲁迅作品“荒凉”的基调相比,鲁迅着重鞭挞社会对于个性的压抑,而张爱玲的作品则着重刻画挣扎于男性权力结构下的“新女性”,即“人的挣扎”。[5]12
张爱玲的作品很少直接描绘国家、革命等宏大主题,而是将它们浓缩于家庭生活。在她看来,日常平凡男女的悲欢离合、跌宕曲折才是生命的底蕴。她的小说正是透过这生命的底蕴,来反映时代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她声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6]84即人在恋爱的时候,缺少战争或革命的强迫或者约束性,更能表达人的率真,反映人的社会性烙印。正如胡兰成所评论的那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回到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7]。实际上,张爱玲并非不关注政治,只是更习惯于以具有韧性的日常生活去映射政治,同时也是她崇尚的个人主义的表征。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她的个人主义“超越了‘个人对抗社会’的五四模式,而将个人主义问题向内开掘,挖掘出现代个体在总体虚无中闪现的‘本真性理想’,从而使个人主义问题在心理深度上有了迈进”[8]70。这是理解、剖析张爱玲小说的重要切入点。
追寻、塑造现代自我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从而形成了她对小说文本中女主人公“个人主义”洞察和批判的思想来源,这也是她五四反思的重要立基点。对“个人主义”的追求,既与新思想的熏陶有关,又是其特别人生经历形塑的结果。纵观张爱玲的一生,父亲的冷漠、母亲的多次离弃、继母的苛待与教唆、弟弟的麻木与隐忍,这些变异的亲情让她看到了人性的冷漠、世俗的肮脏和无情。她在变得敏感、冷漠、孤傲的同时,也培养了她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和赖雅在美国结婚后,生活极为拮据,但从不向生活低头。[9]66-67追求爱情的纯粹和人格独立、自我认同,既是她生活的态度,也是她文学创作的主题。
既然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主题,而这自然离不开性别议题,《五四遗事》也是如此。该小说是张爱玲中后期的作品,其写作风格由前期的绚丽苍凉逐渐转向了平淡自然、内守持中,于平淡无奇中生发出特别的内涵,但“虚无”指向的基调并未发生改变。从严格意义上讲,中文版的《五四遗事》是该小说的第二次创作,因为它改写于英文版本。小说的英文版1956年第一次发表于美国双周刊杂志《记者》,中文版经过改写,于次年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台湾《文学》杂志上。英文小说的标题可译为“失却生命活力的伴侣们——爱情莅临中国时发生的短篇故事”,这个题目有助于深化解读中文篇名。中文小说描写了男主人公罗文涛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的周折反复,在“五四”后近二十年的时间最终收获“三美团圆”的结局,在主旨表达上与郁达夫的《沉沦》有异曲同工之处。小说以令人艳羡的“团圆”喜剧收尾,而实际上表达的仍是具有“虚无”特质的社会悲剧。以罗文涛为代表的新青年,其婚姻行为从现代向传统的回归,实际上是从日常生活层面映射了“五四”社会变革深度的乏力。
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旅居海外的“流亡”生活促使她以一国经验对照另一国经验,加深了对于母国文化的理解,触发了她对于母国文化的反思,推动了她对传统的对接,《五四遗事》就是这一思考的体现。[10]237按照上述理解,中西文化的体验和对照,加深了张氏的文化自觉,乃至有了小说的创作。其实,这一理解不能说不对。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该小说创作的主题和手法与她之前的作品并无本质不同,即反思“五四”与新女性塑造之间的内在紧张,因此对于研究者所作的上述判定的限度要有所警醒。
张爱玲对“五四”的观感是复杂的,她有三次谈到“五四”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作者第一次直言不讳谈“五四”大约是在1944年的《谈音乐》中,其中谈道:“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4]164-165在上述畅谈音乐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最恐惧的是个人主义或者自我认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逐渐模糊、消失,表达了其抗拒五四左翼文学的态度。
1955年11月,当张爱玲携外籍好友炎樱拜访胡适先生时,发现好友尚未认识到胡氏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故而感慨道:“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11]347-348在这里,“民族回忆”显然是一种值得薪火相传的集体经验,张爱玲用平淡的语言高度评价了“五四”的思想价值,肯定了其在现代转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1975年在《世界作家简介》中的英文独白中,作者再谈“五四”,提及了新文学运动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她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不遗余力地鞭挞了“吃人的礼教”。中国文学素有写实传统,而因国耻之故使这一传统得到强化,使其文笔更加锋利。在中西文化的跨越与比较中,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受到的五四新文学的影响。[12]428-429这次表述表明作者的创作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回应了文学界对其五四文学创作非主流的质疑,申明自己的作品其实就是五四现代性与个人经验的结合体。
在现有成果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有三种“五四”的表述。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三种,不如说是两种:其一是作为个人生活经验的“五四”,其二是作为近代思想史意义的“五四”。作者在1975年对“五四”的表述,笔者以为其实是前两种“五四”的结合,既表明了自己延续五四新文学的正统性,又暗指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体验和文学风格。
现代研究成果表明,作为历史的“五四”,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传递场域和影响力,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张爱玲对“五四”的理解同样具有多层次性,并主要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社会意义的解读具有即时性特征,就是要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中去衡量“五四”的功效;历史意义则以后来者的眼光,在近现代中国转型的长时段中去评估“五四”的价值。正因为如此,这两种理解在作者的观念中并行不悖。作者对“五四”现代转型的肯定着眼于思想史、政治史的视野,这并不妨碍她在日常生活史视野中消解“五四”。正是继承、反思“五四”的个人体验,塑造了张爱玲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五四遗事》的创作看,作者在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同样也在日常的婚恋生活中消解了“五四”。对“五四”的继承具有某种客观性,这既是五四现代经验向社会传递的结果,也是张爱玲作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无法逃避的过程,毕竟她曾经是喜欢五四新文学的。至于她对“五四”的消解,可能与其观察和切身的生活体验有关,如作为五四新女性的母亲的离家出走[13]、自己的情感波折等等。再者,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是革命,由此而产生的救亡式启蒙使“五四”政治化,它由个人觉醒转入了革命的集体行动;再加之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解了她所尊崇的“个人主义”,使它在中国社会只能是昙花一现。[14]这就意味着,体现个体主体性或者说女子主体性的个人主义,很难作为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在个人意识中扎根,自然难以成为指导人生的伦理根基。因此,以“个人主义”视野来审视“五四”,必然会对她造成某种程度的消解。“个人主义”被消解,而民族主义视域下的个人发展路径又为作者所不喜,这就意味着她笔下的“新女性”难以找到新生的道路。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专题演讲中所提到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5]。因此,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必然处在“人的挣扎”的尴尬境地,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无”的荒凉调子。
二、文本中男权特质的剖析
应当说,张爱玲的五四反思是独特的,其中充溢的情感是复杂的。五四启蒙效力传播的层次性,决定了思想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存在,反映在性别关系上亦是如此。“新女性”作为张爱玲小说重点剖析的对象,在性别张力之间的生活状态无疑是小说的描摹焦点,《五四遗事》正是如此。
小说首先将爱情的发生地置放于西湖这样一个时空场域中。西湖秀丽的风景、多样的景致对文人雅士有着超强的吸引力,故而是艳遇颇多、才子佳人盛行之处。别样的风景容易激起人的诗情画意和爱情想象,在小说中,诗意的西湖是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催化剂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二人的婚姻结合地和诗意生活的栖息地。
不过,作者在定制这个独特时空场域的同时,做了特别交代,其中描述说:“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如果说作者以“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湖水来隐喻传统的存在,那么前朝名妓洗脸水的比喻描写,则以水至柔至刚的巨大穿透力进一步揭示传统的韧性和阻力,以此暗示主人公爱情、婚姻、命运的多舛,为结局的出现作了铺垫。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在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积淀了相对稳定的伦理规范和婚姻传统,其“古老性的本身就被确认为是合乎规范的”,“并能够用以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16]220五四时期,新思想风云激荡,影响了广大青年学生,但传统社会结构依然稳固,传统伦理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必然意味着新旧冲突异常激烈,爱情婚姻还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
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果将其赋予性别属性,其无疑具有强烈的男性特质,它是在父权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性别秩序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特质体现在文本的方方面面,如外貌的描写既是如此。文本对于男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极为简略,“身材较瘦长的一个姓罗,长长的脸,一件浅色熟罗长衫在他身上挂下来,自有一种飘然的姿势”。虽只有寥寥数语,却把清代以来塑造的男性特质勾勒出来,正如高罗佩所揭示的那样,风雅秀致、身材瘦削、多愁善感、脸色苍白的知识男性,恰是女性的理想爱人;而密斯范“静物美”的气质和瘦尖的鹅蛋脸型,正是清代以来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貌。[17]282性别身体与文化和语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这番外貌的描述,无一不是在烘托着男性特质。
体现男权特质的还有职业身份。文本中交代,男主人公罗文涛的职业是中学教员,这足以表明其知识分子的身份,既与女性理想的男性身份相符,又赋予了其“文”的特性①按照澳籍学者雷金庆的解释,“文”是指经历、接受了主流文化教化而表现出的男性特质,参见《男性特质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宗法血缘性,其不言自明的男权特质在各方面都有明确体现。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其内容中女性的缺席就意味着男性特质伦理关系的建构。在传统官方主导的社会生活中,“文”的领域是拒绝女性参与的,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文”的疆域是男性的公共用地,自然拥有规训女性的权力。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之时,虽不乏保护女性的策略,但整体上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权力格局。因此,男性特质体现为“最终决定权”,女性特质体现为“最终赞同权”。[18]21传统的坚韧在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深邃穿透力,必然会影响着处在转型时期的人的观念。
不言自明,“决定”与“赞同”体现的是性别权力关系,且是或隐或现的男性权力支配关系,这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都有明确体现。正如文本中的女主人公密斯范,“她依旧保持这秀丽的面貌,他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微妙的妥协。他永远不要他改变,要他和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模一样。……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女性迎合男性精英对其形象身份的塑造,只是为了内化其形象,使自己更迷人,更适合消费,这与女性的主体性构建毫无关联。正因为这样,密斯范才令罗文涛特别着迷,不惜倾家荡产、两次离婚,以追求自己心目中神圣的恋爱。换言之,女性形象的塑造,取决于男性的审美标准。1923年,《妇女杂志》策划了“我之理想配偶”的征文活动。分析结果表明,在男性眼中,同时具备新知识和旧道德的女性最受欢迎;女性对浪漫爱情的向往,甚至表现得比男性还要积极和热烈,但在潜意识中仍希望寻求男性的庇护。[19]女性潜意识中庇护权的寻求,实际上就是向男权的靠拢。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绝大多数具有“新思想旧道德”的特征,恰是对于当时新女性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所谓“新”是指她们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旧”是指她们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依然遵循传统老路。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并无清晰、坚定的精神信仰和自我认同,而是以“爱”和“自由”的名义,用个体行为回应了“新文化”话语的召唤,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20]这个结论对于密斯范是准确的,也能够代表当时一部分“新女性”的精神状态。“密斯范”只是个时髦的姓氏称谓,与“罗文涛”清晰的冠名相比,具有普遍性和不确定性,喻示着女子主体性的模糊。对她们而言,由于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和自我认同,其接受教育的主观动机就是“得一富女婿”[21]。实际上,对于她们来说,包括新教育在内的时髦包装只是在新形势下规划人生道路的跳板。自由恋爱的结合迎来的可能就是如传统女性般的回归家庭,即婚姻依然是她们人生的最终归宿:“她们在家不必如旧式妇女的执畚帚扫地,不必上灶做菜,只要弹弹钢琴,高兴的时候做做蛋糕,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一个快乐的主妇;因为丈夫有名望,她的声名也煊赫起来了。”[22]时人对此说,“她们看到鸡吃糠极不满意,以为吃蛋粉是令人羡慕的,殊不知其被人豢养是相同的”[23]。密斯范婚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慵懒生活状态,再次表明她缺少性别主体性,进而抽空了新女性的内涵,使启蒙知识界的国家建构缺乏个人根基。
失衡的性别权力格局必然影响着婚姻关系,如在离婚问题上就充斥着鲜明的男权特征。离婚在明清社会被视为不名誉之事,无论男女离婚都极为不易,离婚法则以有无“过失”作为判定是否离婚的主要根据,这种传统延续到了五四时期。正因为如此,当罗文涛两次提出离婚时,女方都以无过错而拒绝,从而使其离婚之路困难重重,两次离婚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可以看作五四时期湖南浏阳学生左天锡的离婚之路在文学中的映射[24]。离婚自由在五四时期被启蒙知识界构建为女性解放的必要手段,而事实上,很多女性尤其是社会中产家庭的女性,都将离婚之路视为畏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女性不从事社会性劳动,经济上难以自立,不能独立谋生;另一方面是贞节观念的束缚。[25]430因此,离婚进而演变为“男性的离婚”,即男性主导下的离婚。罗文涛的两次离婚都由他主动提出,如果说第一次离婚是为了弥足珍贵的爱情,那么第二次的结婚、离婚都表现为男权的恣肆。而如密斯范般的新女性显然毫无察觉,仍旧义无反顾地迈入男权编织的温柔陷阱中。面对这种性别权力格局,女性为自己维权的空间很小。作为新女性的密斯范,面对“三美团圆”的变局,定然是心不甘、情不愿,虽“哭闹着声称要自杀”,但这番虚张声势的表演显然无法影响罗文涛的决定,她只得以“大妇”的身份出面张罗相关事宜。正是“豢养”的依附性地位,使密斯范丧失了反抗夫权的勇气,由自由恋爱之“妻”变成了“三美”之一。
总之,文本无论是在烘托时代氛围,还是对两性生活轨迹的描述,无不渗透着浓厚的男权特质。传统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影响着五四青年的思维意识。男性特质依然决定了女性的精神风貌,规划着女性的人生轨迹,掌控着两性生活的基本节奏。因此可以说,男性特质是张爱玲对五四时期婚姻生活特征的本质性认知。
三、启蒙的回归与男权的反噬
如果搜寻五四时期知识界思想启蒙的关键词,婚姻自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词汇。它向当时的知识青年描绘了一幅全新的两性生活图景,引起了众多青年人的追捧。因此,追求自由恋爱、塑造新的家庭生活成为不少年轻人的追求。罗文涛和密斯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顽强地展开了他们的恋爱生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恋爱生活并没有能够组建核心家庭,而是以“三美团圆”的讽刺喜剧收尾。张爱玲就是以五四婚姻的憾事,从生活视角来指陈五四启蒙的限度。
从启蒙的视角看,知识界播下的龙种,在现实当中收获的为什么往往是跳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因为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态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权的表征,同时也是男权荣光的重要体现。从自由恋爱到“三美团圆”的传统回归,表明启蒙视野中的婚姻与男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婚姻在古代中国从来不只具有生活的意义,它更是家族主义以及伦理政治生发的起点,故《易》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26]313构建在家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中国,呈现家国一体特征,政治、社会的一体化必然使得伦理、政治融为一体。正因如此,正婚姻、正家庭就取得了政治上的意义,从而使婚姻、家庭受到国人的特别重视。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推动着国家的现代转型,引发了知识界思想文化的更新和价值体系的重建。在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文化是具有贯通性的连接枢纽,而伦理文化的改革是重塑政治、社会新一体化结构的关键,婚姻恰恰是社会人伦关系的源头,故而以婚姻变迁推动伦理改革,进而实现一体化结构的重塑,就成为启蒙知识界构建新话语体系的思维逻辑。五四时期“人”的意识觉醒,增强了青年人的自由意识,恋爱被视为婚姻成立的根本要素。[27]这为青年人打破包办婚姻,实现自由结婚提供了新的道德依据。接受了新理念的年轻人勇于追求浪漫的爱情,并在五四时期形成了自由结婚的热潮。按照知识界的逻辑预设,以恋爱为核心的自由结婚是组建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贞操是自由恋爱的结晶体”[28],它是“人生的一种态度,使恋爱能够伟大的工具”[29]。换言之,自由结婚指向的是充满人生趣味的两性生活。
从普遍意义上看,婚姻与性别权力格局紧密勾连在一起。马克思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30]52母系与父系社会之间的更替,意味着性别权力的转换。中国自西周建立了基于血缘的封建宗法制以来,逐步确立、强化了男性的社会主导权。从唯物论视角看,男权社会建立于男性对社会财富的掌控基础上,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维护男权秩序的意识形态,如文化的垄断、礼仪的调整、法律的制定,通过上述架构的创建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权力组织体系,来保障“男尊女卑”的两性权力格局。如上所述,政治、社会的一体化使得伦理、政治融为一体,且呈现男权化特征。
五四婚姻变革以思想启蒙为基础,那么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否置换了传统文化的内核?金观涛、刘青峰在深入分析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利用新概念建构意识形态的模式时发现,“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并没有改变自己正当性论证的推理结构”[31]69。这实际上是上文提及的政治、文化的一体化结构造成的。毋庸讳言,中国既有的文化结构和心理意识都带有强烈的男权色彩,以此思维结构构建的启蒙框架并没有削弱这种色彩。学者高彦颐指出:“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时期,有着落后和依从的女性身份,一直是一个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紧迫问题。当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时,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被男性强权‘强奸’和征服。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也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来说,女性启蒙成了一个先决条件。”[32]《绪论》1-2从以上文化心理和既有社会结构出发就不难明白,民族危机所引发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实际上是利用现代性重构男权的过程。因此,从女性启蒙发端的社会根源看,其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权的烙印。
为什么女性启蒙成为解决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先决条件?启蒙知识界认为,传统女性无法清醒地认识和承担自己作为国民的责任,男性有义务为女性代言,代替她们争取权益。[33]知识男性由此获得了启蒙导师的资格,继续行使编织性别意识形态的权力,并陆续预设了“国民之母”“妇女主义”等女性角色。在文本中,作为知识男性的罗文涛与同事郭教员,恰恰就是女性启蒙导师的化身。当他们四人相聚于西湖之时,两位男性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两位女性朗诵雪莱,这一举动有意无意地指向了其启蒙导师的身份,而作为受众的两位女士听到激情澎湃、荡气回肠之处,则会激动地握紧彼此的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在《创造季刊》《小说月报》《文艺杂志》《文艺先锋》等杂志,广泛译介、评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雪莱追求民主的启蒙精神,鼓舞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反抗旧制度、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勇气。雪莱作品的译介与受欢迎程度,说明中国的现实呼唤雪莱式的人物。正是在此过程中,启蒙者与受众达到了精神的共鸣,在反抗包括旧家庭、旧制度层面达成共识。不过,雪莱的浪漫主义启蒙,在作者看来可能是女性启蒙乌托邦的隐喻。
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释放了青年人追求浪漫爱情的欲望,罗文涛与密斯范马拉松式的爱情则是极好的写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通过研究认为,浪漫的爱情对于女性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将妇女放在‘她们的地点’——家中;而另一方面,浪漫之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主动的激进的同‘男性化’的现代社会的婚约”[34]《导论》2。对于第一种影响,要是置放于五四时期则要做具体分析,毕竟中英之间的历史文化有不小的差异,第二种解释则与当时的境况基本吻合。
国内学者刘慧英通过梳理清末到五四时期女性启蒙的路向发现,在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框架下,女权启蒙使女性变成了被民族国家话语任意编织的“场所”;五四时期《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等人提出的“妇女主义”,其中虽包含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欲望想象等多重因素,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对妇女的想象,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的建构。[35]57-61,192她的研究观点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由此可见,清末以来“女性”的构建被限定于民族国家话语之中,其主体性正是在这一层面得以体现,而非置放于性别权力关系层面的主体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就容易理解安东尼·吉登斯的论断了,恋爱作为被启蒙构建的女性解放神话,女性对恋爱的渴望和追求往往表现为对男权的回应和强化。
《五四遗事》的文本在平淡自然的叙述中,对上述问题都有清晰的呈现,足以表明张爱玲深邃的洞察力。以此来审视罗文涛的婚姻,就会发现从自由恋爱到“三美团圆”的婚姻蜕化历程,有着同质的男权意识作为深层的心理支撑,从而保证了蜕化过程的自然、顺畅。简言之,“自由恋爱”和“三美团圆”,只不过是男权架构下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化身,深层的男权意识是沟通二者的桥梁,从而能够保证男性在二者之间畅快的游走。
除此之外,《五四遗事》的文本中还提及了男权被反噬的境况,它的出现与性别权力和家庭经济的复杂联系有关。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决定了婚姻的目的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36]1416,通俗来讲就是“重人伦,广继嗣”[37]451。母权到父权的权力转移,改变的不仅仅是各自的地位,还有他们所承担的角色。正如英国的格里康夫人(C.G.Hartley Gallichom)在其名著《关于妇女的真理》中所说:“在父系制度下,男子对女子的呼声只在她的性,而她的工作价值,他们是不记及的。然而这样错误观念的罚已降到男子身上了。女子还转来的要求,遂专在要求男子能供养他们的能力,而男子的性的价值,正如女子的工作价值一样不重要了。”[38]这番概括是对传统社会婚姻的本质性描述。在父系权力框架下,女性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生育,如若不能为男性家族诞育子嗣尤其是具有继承权的男性,那么她的家庭地位会受到冲击,甚至有被休弃的可能。反之,女方同样有权力要求男方的经济供给能力,正如民间谚语所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表明,男权荣光的实现要以相对充分的经济供给作保障。
传统家庭中的夫妻双方承担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相互弥补中维系着家庭的基本运转。传统观念认为,“妇与夫一体也”[37]486。细读文献不难发现,这种一体性主要表现在“敬祖承嗣”意义上。也就是说,在维系父系家族的绵延上夫妇是利益共同体,但社会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因角色功能失调,仍存在紧张的可能,甚至会侵蚀夫权。文本中的罗文涛虽有让时人艳羡的“三美”,但供养大家庭的巨大经济压力让其非常狼狈,这样的窘境显然降低了他在家庭中的威信,又因过多干涉密斯范的日常生活而时常受到其“无能”的讥讽。另据《右仙台馆笔记》记载,何氏女因丈夫黄氏不能供养自己,主动要求丈夫将自己卖给姑家表哥为妻。黄氏虽十分不情愿,但因生活所迫也只得被迫应允。[39]8两则案例的发生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即黄、罗两位男性都无法享受家族的荫蔽,个人承担的养家糊口的重任又力不从心。当作为“夫”的男性无法在经济层面尽到自己的供养义务,夫权就要失掉既有的荣耀光环而受到侵蚀。近代上海开埠后,附近进城佣工的妇人,因视野的开阔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就出现了不少弃夫姘居的现象,当时的舆论多以“乾纲不振”为主题作报道。[25]93
从社会进化的整体看,从母权到父权社会的转换,确立的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权,又因性别权力体系的组建而形成稳定的社会性结构。其实,在社会生活层面,性别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夫妻在“敬祖承嗣”层面结成同盟,共同维护社会的男权特质,而在其外的日常生活中夫妇之间权力的消长则具有弹性。除了上述事例外,明代的“悍妻”现象也是重新审视夫权的切入点[40]。总而言之,作为男权特质的父权与夫权,值得从日常生活层面去研究其弹性和实践张力,这是认识传统社会的重要面向。
四、小结
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五四”,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史学领域,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因此,对于“五四”的阐释、纪念和反思在五四时代既已展开。在拓展五四影响力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轨迹。在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张爱玲,同样深受“五四”的影响,并深刻认识到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引导作用。不过,具有个体生活体验的张爱玲,习惯以个人主义视角,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五四”作为思想运动的穿透力进行反思,故而时常在作品中消解“五四”的现代性。这表明,在政治史或思想史层面的“五四”,与作为日常生活的层面“五四”之间存在着张力。
文本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即女性建构与女性体验,思想启蒙与男权蜕变之间的张力,这是作者据以言说“五四”的问题意识,所要表达的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复杂缠扰。传统不仅仅是制度性或社会结构性呈现,而且日益积淀为社会深层的心理意识,具有强大的时代穿透力,并不因时代鼎革而随之烟消云散。张爱玲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作品时常从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的视角去反思,剖析挣扎、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性别心理意识,深刻反映了近代启蒙所具有的性别特质。女性对于启蒙的回应或参与,同时也在强化着男权特质。知识界的文化推演结构决定了启蒙建构的男权特质,使得女性解放或启蒙中的主体性构建先天存在不足,其自我认同意识定然模糊不清,势必导致她们挣扎、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使其个人主义具有“虚无”的特征。这一特质,使得男子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退有余,表达了启蒙现代性追寻的某种暧昧性。在张爱玲看来,启蒙的男权特质影响着其在日常生活的下潜深度和影响的力度,也就削弱了转型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喻示着中国现代转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