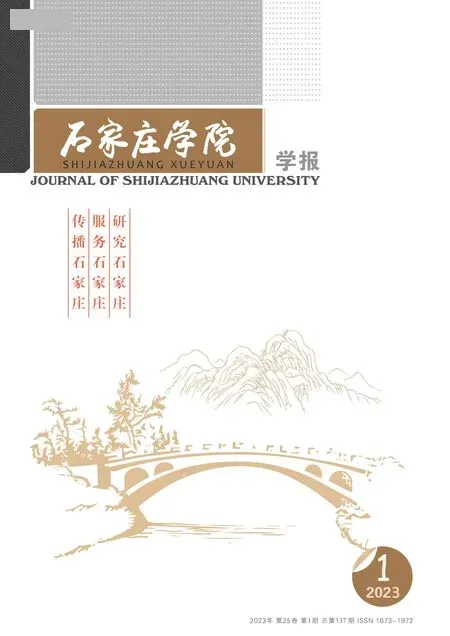古典诗词多元阐释的可能与限度
2023-04-07王昕
王 昕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历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关于诗词的阐释问题,大体来说学界存在三种观点:作者原意说、作品本体说、读者接受说。传统阐释学寻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努力在“文本语言的多义性的解释中确定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释”[1];英美新批评认为诗是自足的存在,其意义在于作品本体;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强调读者所领悟的意义,更关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活动及生成的意义。作家原意说、作品本体说都坚持阐释意义的唯一性;而读者接受说则肯定阐释意义的多样性。这样看来,关于诗词阐释一元还是多元问题都不能通融。但实际上,作者表意和读者释意都借助语言媒介进行,而诗词语言比其他文体更富有张力,古典诗词的多元阐释,我们从诗人创作意图、诗词文本、读者感受都能找到根据。不过,由于诗人意图、诗词文本的限定,读者的多元阐释也有一定的限度。
一、诗人表意的困惑与追求
诗人创作时,都有一种或清晰或模糊的主观欲望,即使有时创作带有突发性甚至迷狂性,诗人即兴而作、挥毫而就,也不能否认创作时的意图存在。但是,诗人在写作中能否做到运用语言确切表达原意?作品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诗人的意图?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先清楚言与意的关系。
(一)“言不尽意”的困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言与意的关系。孔子指出语言在表述深奥思想上的局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需要借助“象”来表达,“圣人立象以尽意”[2]171。刘勰从文学创作层面发挥了“言不尽意”的观点,“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言远不能及意,“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3]369陆机进一步强调表意之难,“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4]2013。文学创作中,语言表达某种意义常常要借助物象,而物象与意义又并非清晰、确定的关系,因此“文不逮意”似乎成了必然。
西方学者更强调语言在表意上的无能为力。黑格尔(G.W.F.Hegel)认为,“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①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6页。。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语言符号“不是个别事实的复制或模拟,而带有某种模糊、抽象的普遍性,但又不是概念”②参见周春宇《西方美学的历史构成》,敦煌文艺出版2002年版,第258页。,在有效表意方面具有局限性。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明确指出文学语言表意的无力,“语言表现无论如何都不够准确,需要再推敲,而且必然地总不能充分地表情达意”③参见张隆溪《诗无达诂》,载《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从严格意义上讲,语言用来表达复杂微妙的思想意识总是不尽人意的。
“言不尽意”是诗词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诗词体制短小,语言要比一般文学体裁更简洁、精练,而古典诗词创作往往还要考虑平仄、押韵、对仗等格律要求,从表意确切的层面上来看无疑难度更大。刘禹锡曾倾吐语言未能尽意的苦恼,“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视刀环歌》);贾岛真切表述“苦吟”的不易,“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先流”(《题诗后》);方干也诉说锤炼诗句的痛苦,“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贻钱塘县路明府》)。诗人对语言的推敲和追求,其实不仅仅是形式方面的执著,也是希望用有限的文字更好表意的反映。
(二)“言外之意”的追求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语言表意的局限性也正是其优势所在。刘勰意识到“言征实而难巧”,同时也发现语言能形成“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3]495梅尧臣明确主张:“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5]1952可见,“言外之意”是古人评论诗歌的重要审美标准。
从诗词创作来看,“言外之意”主要从深度和长度两个维度展开,由此形成两个创作传统:一是重视语言的“深意”,强调语不直露,言在此意在彼;一是重视语言的“余味”,强调语不说满,言有尽而意无穷。
古代诗人充分发挥语言的模糊性、隐喻性的特点,形成了含蓄婉曲的表达方式。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或以史论今,使诗歌语言不仅具有表层意义,还往往具有深层意义。刘勰谈到“隐”的复义时举例:“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3]496陈子昂提出“兴寄”说,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强调“兴寄”的重要性。司马光推崇“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认为“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6]201-202,并以杜甫之《春望》进行具体分析。《春望》以诗人所见之物,寓感时伤世之悲,不过诗旨意还比较明确。“意不直露”最典型的要属李商隐的“无题”①李商隐“无题”系列的诗包括诗题为《无题》的诗和取自篇首两字的诗,《锦瑟》属后一种。系列诗,李商隐自谓其诗“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但是具体所指莫衷一是,“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正是叶燮所谓的“诗之至处”。[7]584
古代诗人还充分利用汉语语词富有张力的特点,追求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含义。诗人通过跳跃省略、虚实结合等方式,使诗歌有限的语言包孕着无穷的余味。刘禹锡因为语言不如人意而遗憾,又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8]237为追求;苏轼大力提倡“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9]681;姜夔又进一步指出,“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9]681。为达到诗歌具有“不尽之意”,古人还提出具体的方法,如五言绝句当以“咫尺有万里之势”为第一义、填词时“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等。②参见王夫之注、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由于语言表达未能完全表达作者的心中所想,读者又希望通过语言去了解作者确切的创作旨意,语言的双重偏离,使诗歌阐释的多元性具有它内在的根据。而且,优秀的诗人能超越“言不尽意”的局限,充分利用诗歌语言的简约性和表意的模糊性,从而达到意蕴丰富、韵味无穷的表达效果,也为诗词意蕴的丰富性和多解性提供了可能。
二、文本语言的阐释空间
西方新批评主义者反对作者的“意图谬见”,也反对读者的“感受谬见”,坚持用“细读”方式去关注“诗本身”[10]257;贝蒂(Emilio Betti)、艾柯(Umberto Eco)等诠释学家也认识到作者原意实在难以企及,逐渐将目标转向了文本意义。但是,当我们尽力摈弃干扰主观意图或感受,回归诗歌本体时,由于语言表意的非确定性,特别是“诗家语”的多义性、隐喻性和非逻辑性,尽可能客观的阅读也可能出现分歧。
(一)词义的多解性
诗词阐释建立在对词义理解的基础上,词义理解的分歧直接造成诗意解读的不同。诗词用语,不仅具有一般词语约定俗成的概念义,还多具有表达诗人情志思想的负载义。概念义虽然固定,但汉语词语多数有一个以上的概念义,而且语言演变导致古今词义多有变化;负载义没有明确的指向,甚至可能会根据读者的期待而改变旨意。由此,概念义和负载义的理解都有可能出现多样化的结果。
1.概念义的歧解
汉语词语中,一词多义比较普遍。在特定的情境下,诗人表达某种内容的时候,一般来说是用其中一个概念义。后人阅读时可能与作者原意一致,也可能误解为不同的概念义,如果这些解释在诗中都能大致说通,而又无法知悉作者原意,就会出现多元阐释的结果。
苏轼《记子美〈八阵图〉诗》记述梦中杜甫谓《八阵图》诗被“误解”情况:
《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11]2101
梦中所谓杜甫之言,实表达苏轼个人意见,是他在结合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并以此质疑世上所传说法。苏轼与世人之说不同,关键在于诗中“失”字的多义性。“失”可以解为“失败”“失策”等义,世人认为的“恨不能灭吴”,“失”应解为“失败”;而把“失”解为“失策”,符合苏轼所谓的遗恨“蜀有吞吴之意”。
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诗中“床”一词,古代可表示多种含义,由此产生了“卧具之床”“胡床”“井栏”“建筑物底部”等不同说法。又如“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白居易《惜牡丹花》),诗中“残”通常被解“凋残”“残败”,萧涤非即认为“晚来只有两枝残败”用以表现惜花之情;而蒋绍愚认为“残”应解为“剩余”,即“在晚上看到阶前的红牡丹只剩下两株”才与诗意相合。①具体参见蒋绍愚《唐宋诗词的歧解和误解》,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再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只是”通常被解为“不过”“但是”,表示转折义,依此,诗句反映诗人“消极”的心境;周汝昌认为“只是”应解为“正是”“就是”,诗句就表现了诗人“满足”或至少“慰藉”的心情。[12]1154
2.负载义的多解
诗歌中的词语,不仅具有约定俗成的概念义,也往往作为情感、志怀、观念等的载体,“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13]6。相对而言,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概念义比较明确,而其所负载的意义一般不明确说出,需要读者根据诗中提供的信息去领会和体悟。如果对诗歌词语负载义的指向和深度理解不同,自然也会造成诗义阐释的多样化。
诗人经常借用一些具体的物象含蓄表意,“意象”化词语成为诗歌基本的表意符号。诗歌意象尽管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常见意义,但是这些意义既不唯一,也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诗人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常会赋予“意象”独特的意义。读者对“意象”之“意”的理解,由于立足于不同层面,会出现多个结果。如“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杜甫《江汉》),“落日”“秋风”均是表示时间的自然事物,分别作为“心犹壮”“病欲疏”的时间状语,可解为“落日时分”“秋风起时”;“落日”“秋风”又具有情感意蕴,可分别喻指诗人“已近晚年”和“经历坎坷”;再进一步说,“落日”“秋风”也可分别象征“社会衰落”和“时代动荡”,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又如,“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陈与义《牡丹》),“牡丹”是一种美丽华贵的花,概念义明确;洛阳牡丹一向为天下之最,陈与义是洛阳人,故“牡丹”又成为“故乡”的代称;此诗前两句为“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诗人国破家亡后流落异乡,这样“牡丹”又成为“故国”的象征。
诗人还会利用借代、用典等技巧,使词语负载更多的意义。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菊花”,既指自然界的花,又可作为“高洁”“隐逸”的象征;还可借指为“菊花酒”,寄托诗人重阳饮酒祛灾祈福的希望。再如,“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咏柳》),“碧玉”,字面义是碧绿的玉,诗中用“碧玉”来比喻“嫩绿的柳色”;“碧玉”还是晋汝南王宠妾的名字,汝南王为其作《碧玉歌》,其后“碧玉”多指“妙龄少女”,这样来看,“碧玉”又有把柳树拟作“少女”之意。
应该指出的是,词语的概念义歧解和负载义多解造成的诗歌多样化阐释具有本质区别。词语的概念义是约定俗成的,具有普遍的限定性。诗人运用多义词,通常指向一个义项,因此,歧解的概念义至少有一个是误解,且多表现为互相排斥的关系。词语的负载义是诗人独特创造的产物,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负载义通常不能离开概念义而独立存在,不过与概念义的联系可近可远;而且一个概念义还往往会生成多个负载义,有的负载义甚至超出诗人原意。读者对负载义的理解,或情感指向不一致,或有深浅层次的区别,情感指向不同的负载义一般来说互相排斥,而不同层次的负载义可以共存。
(二)句法的特殊性
诗词与散文在诗句的构成与组合上不同。散文词句之间要求逻辑清晰,语意连属,其意一般明白晓畅。而古典诗词中省略、倒置、凝缩等手段被普遍运用,这就给理解其意带来一定的困难,诗词阐释也常会出现歧解情况。
1.省略与“填空”
古典诗词常省略一些表意成分,使得句子的弹性增加,“可是弹性增加以后,则文句意义的迷离性、游离性也随着增多”[14]59。诗中的省略成分引发后人去想象和“填空”,也会呈现出多样的阐释结果。如下:
昨日山有信,只今耕种时。遥传杜陵叟,怪我还山迟。独向潭上酌,无人林下棋。东溪忆汝处,闲卧对鸬鹚。
——岑参《还高冠潭口留别舍弟》
诗中关于来信之人未具体说明,又省略“潭上酌”的主语,读者根据自己理解填补而出现分歧。如明人谭元春认为诗言杜陵叟寄来信,“末四语就将杜陵叟寄来信写在自己别诗中”,“‘忆汝’‘汝’字,指杜陵叟谓岑公也”;周振甫赞同“潭上酌”者指“杜陵叟”的说法,但对“来信人”质疑,“是信里传杜陵叟的话,似不必说成杜陵叟来信”;张桂丽坚持“潭上酌”者即岑参,“是诗人设想兄弟分别之后自己的孤单无依”,而“汝”即“舍弟”。①参见周振甫《诗词例话》,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张桂丽《岑参还高冠潭口留别舍弟重读》,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6期。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此诗后两句,有“豪语说”“苦语说”两种相反的说法,而又分别言之成理,以至清人沈德潜谓“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倍有意味”[15]647。其实造成此诗的不同理解,除了“终”字的意义含混外,主要在于诗歌省略了一些成分。试想,在“不还”间增加能愿动词,如“不肯还”“不能还”;或增加关联词,如“只要不破楼兰就终不还”“因不破楼兰而终不还”,那“豪语”“苦语”自会明确。正是由于诗句省略了一些可以表意的成分,意义阐释多元化就不难理解了。
2.倒置与还原
倒置,又称倒装、颠倒、错置等。诗词句子成分经常会出现倒置的情况,解诗时要把倒置成分还原为正常语序。仅为押韵、平仄、对仗需要的倒置,只要我们了解一些格律知识,就可以较清晰地判断其意义。但是,如果句中还省略了一些成分,在还原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分歧。如下: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李颀《送魏万之京》
两句总体上倒装,这比较好理解,但因“初渡河”主语省略,故“初渡河”是否跨句错置,还有争议。如清代方东树认为:“《送魏万之京》,言昨夜微霜,游子今朝渡河耳。”[16]392此谓“渡河者”为“游子”,语序还原当为:“昨夜微霜,(我)朝闻游子唱离歌,(游子)初渡河。”这样的话,两句为错综倒置。而今人姚奠中解释:“一开首,‘朝闻游子唱离歌’,先说魏万的走,后用‘昨夜微霜初渡河’,点出魏万前一夜渡河来的景象。”[12]113-114此谓“渡河者”为“微霜”,诗人用拟人手法,语序还原为:“昨夜微霜初渡河,(我)朝闻游子唱离歌。”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
——苏轼《西江月》
第二句为倒装没有异议,还原后为“隐隐层霄横空”,而首句是否倒装有不同观点。如胡云翼注为:“月亮照彻旷野里水波动荡的小河。弥弥,水盛貌。”[17]52即以此句为正常语序,但是省略了主语。钟振振认为此句为倒装句,和下句一样构成对仗,还原正常语序为“浅浪(主语)弥弥(状语)照(谓语)野(宾语)”,或者“弥弥(定语)浅浪(主语)照(谓语)野(宾语)”。[18]
3.凝缩与断分
诗词用语凝缩、简洁,通常一句就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解释时往往需要再分成较小的语言单位。诗句内部断分可根据语音节奏和词语搭配,有时其中一成分断为前或后似乎都能说通,这就会造成诗意理解的分歧。如下: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
后人有两种断分方式:一是“不薄/今人爱古人”;一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前者是动宾结构,“不薄”的宾语是“今人爱古人”,即对于当时人推崇古人表示认可;后者是并列结构,“不薄”谓语是“今人”,“不薄今人”与“爱古人”并列,即评价诗歌不论“今人”和“古人”。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断肠人在天涯”也有两种断分方式:一是“断肠人/在天涯”;一是“断肠/人在/天涯”。这两句停顿方式,从情感和语意上都略有区别。“断肠人/在天涯”,主谓结构,描述“断肠之人远在天涯”的情景;“断肠/人在/天涯”,倒装结构,强调因“人在天涯”而“断肠”,而且“断肠”的主语可以是旅人,也可以是家人。结合整首曲的意境,似“断肠人/在天涯”为好;而如根据曲子前几句两字一顿的节奏,作“断肠/人在/天涯”也未尝不可。②具体参见王恩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中的“悬案”刍议》,载《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三)修辞的婉曲性
为了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诗人在创作中往往用采用婉曲的表达方法,诗词语言更具有隐喻性、模糊性,使诗意向多项度呈现,也带给人们更自由的阐释空间。下文仅就比兴与用典举例说明。
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借物寄情,因事托意,使诗歌不仅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而且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不过,寄托之意因不明说,也带来了阐释的困难。诗歌是否有所寄托,寄托之意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同,是古典诗词的阐释多元化的主要原因。如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首先,“山”“水”所指。受周济的“惜水怨山”说影响,人们多把“山”“水”作敌我双方,如邓小军认为:“清江水既为行人泪之象喻,则东流去之江水如有所喻,当喻祖国一方。无数青山,词人既叹其遮住长安,更道出其遮不住东流,则其所喻当指敌人。”[19]1505也有人认为“山”“水”就是常见的表达情感的意象,“强调的是作者思念故国和壮志未酬之忧愁”[20]。其次,“鹧鸪”寓意。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曰:“‘闻鹧鸪’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21]22此述有歧义,后人据此纷纷解说,如:邓广铭推想,“盖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遂行”;夏承焘分析,“恢复之事由于当权者不敢抗战,所以困难还很多”;刘逸生直谓,“鹧鸪之声应该是指投降派的叫嚷”;而任二北对鹧鸪指“恢复之事”质疑,“特谓鹧鸪之唱乃指恢复之业行不得,则又未免臆断”。①关于“鹧鸪句”争议,详见张玉璞《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探隐》,载《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诗词用典,以精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可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含蓄性,收到言简意丰、耐人寻味的效果。“典故”是解诗的难点,后人对典故的意义、用典方式的理解不同,会造成诗意阐释的分歧。如韦应物《长安遇冯著》:
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
“采山”“买斧”是否用典大致有三类看法:一是没有用典,如周啸天认为“采山”谓“采樵”,即上山砍柴,比喻归隐山林;“买斧”指买采山斧,即为采山备取条件,比喻通过求仕获取俸禄以归隐。二是用两典,如倪其心认为“采山”语出左思《吴都赋》“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即谓入山采铜以铸钱,比喻谋取仕途;“买斧”化用《易经旅卦》“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之典,意谓“旅居此处做客,但不获平坦之地,尚需用斧斫除荆棘,故心中不快”,寓意为“谋仕不遇,心中不快”。三是用一典,如认为“采山”用典同上,“买斧”没有用典,为了采山而买斧暗指为求仕挣钱“想好了谋取的办法”。②参见周啸天《唐诗鉴赏辞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58-959页;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3页。
从诗词文本的语言运用来看,无论是词义、句法,还是修辞方式,都有可能造成理解的分歧。这一方面容易引起诗词含义的误解,另一方面也为诗词含义的丰富性提供可能。
三、读者阐释的差异与限度
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生命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22]24。由于不同读者的个体差异性、读者与作者的审美逆向性,读者阅读往往打上了个性化阐释的烙印。读者阐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过度阐释的借口,“诗无达诂”应有一定的限度。
(一)读者阐释差异的必然性
在作品的阐释活动中,作者、作品、读者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交往结构。读者与作品或作家构成多对一关系,读者又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间接的对话。由此,古典诗词意蕴的多元阐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不同读者对诗词意蕴理解的不同,二是读者对诗词意蕴理解与作者原意的不合。
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文学阅读中的读者都是具有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观念结构的独特个体。刘勰认为,读者的解释分歧主要在于“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个体的知识能力的局限性和性情兴趣的差异性,使读者倾向于选择性地解读评价,故“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3]592西方现代阐释学认为,读者阅读作品时,既无法摆脱历史传统、时代社会、文化习惯等通过语言对自己的预先占有,又不可避免地融入性情、阅历、知识等要素形成的“前见”,因此,不同的读者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对作品的理解不同。实际上,个体的气质性情、年龄阅历、学识水平、文学修养、审美趣尚、阅读心境等的差异,读者的解读方法、理解能力、情感态度、选择偏重等的不同,都会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可以说,不同读者阐释的差异具有必然性。
读者阐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弄清诗词字面意思外,还要通过涵咏、体会等方式明白诗词所包含的深蕴和意味,最后还要把自己对作品的独特的理解和感受用语言进行表达。在某种程度而言,读者阅读阐释是在作者创作成果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因此,从绝对意义上讲,读者与作者通过作品进行的沟通也不可能完全相合。梅尧臣以欧阳修为“知音”,欧阳修也“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然两人所“得意处”并不相同,故欧阳修感慨“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5]2196。更何况今人阅读古典诗词,“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15]1,读者对于主旨思想、情感色彩、内蕴深浅等方面的理解与作者出现差别更在情理之中。
(二)过度阐释的倾向
尽管我们承认读者阐释差异存在的必然性,但并非意味着一切随意的阐释都是合理的。如果把读者的主体性任意放大,过分强调读者创造阐释的权利,势必会导致随心所欲的“过度阐释”。这不仅存在于注重读者体验过程的有意为之的创新阐释中,在努力探求作者或作品的本意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倾向。下面我们以“比兴附会”为例简要说明。
是否运用比兴手法是评论诗词的重要角度。自王逸指出《离骚》“引类譬喻”的比兴特点后,后世逐渐形成了“香草美人”的批评传统。如清人毛先舒评《古诗十九首》多比附君臣关系,认为《行行重行行》“谪宦思君也”,《青青河畔草》“怨不得其君也”,《今日良宴会》“遇时明良,思自奋也”,《西北有高楼》“悲有君无臣,思自效忠也”,等等。[23]95《古诗十九首》大多诗篇以女性口吻抒发闺怨、相思之情,在不能确定作者及相关背景资料的情况下,一味挖掘政治寄托,难以令人信服。
解诗者不仅重视诗歌的“内外之意”,甚至逐字逐句落实。如杜甫诗《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颔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续金针诗格》解为:“‘旌旗’,喻号令也;‘日暖’,喻明时也;‘龙蛇’,喻君臣也。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也;‘风微’,喻政教也;‘燕雀’,喻小人也。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24]497-498这种认为字字均有所喻、物物皆有所托的解释,没有可以信赖的文献支撑而曲意比附,其结果是以损伤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为代价。
读者解诗时,往往不满足于诗词的字面意思,而致力于去挖掘词句所蕴含的深层寓意。但是,一个作品是否有寄托、其寄托是否具有政治性,既不能妄加推断,也不能按照一个模式机械套搬,应该结合作品语言、创作本事、作者情况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从文学创作层面对诗歌的比兴手法、寄托之意过度阐释,可能导致以讹传讹,这毕竟仅属于审美批评观点或态度的分歧;而有些解释却建立在政治打压的基础之上,专门从诗歌的字眼中找出多义的字词,有意歪曲诗人创作意图,不仅超出人们的接受限度,甚至由此兴起“诗案”“文字狱”之类的迫害行为,这种“过度阐释”实在是危险。
(三)多元阐释的限度
谈到古典诗词的多元阐释,人们通常通常引用“诗无达诂”来作为理论根据,不过“诗无达诂”并非没有限度。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载: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5]94-95
董仲舒反对古文经学家的注释方式,倡导根据现实需要来解读《诗经》,但前提是要把握“从变从义”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承认经学和诗学多元阐释的合理性。
“变”意味着承认文本是开放的、具有无限可能性,并且肯定读者在阐释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创造性作用。“义”却规定着读者不能仅凭阅读感受随意发挥,必须从文本出发,必要时还要参照作者创作时的相关背景资料。对于这些问题,艾柯也有相近的论述:
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说一个本文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26]27-28
“从变”“从义”的辩证关系,我们在理论层面上较容易接受,但在实际操作时仍会遇到不可避免的难题。由于诗词语言的间接性、隐喻性、不确切性,对其文本之“义”的理解也有可能出现不同甚至对立的结果,更不用说读者有意去“变”了。因此,确定文本之义首先需要辨析“义”的不同理解的原因,进而通过分析考证、综合比较以选择较合理的解释。
由于词语概念义造成的歧解,我们应尽可能细致考察语言的发展变化、词语在同时作品中运用、诗词的具体语境等,判断词语的含义。钟振振提出的古典诗词文本解读的两大步骤很有参考价值。首先是“顺向推衍”,把文本可以“‘引发’出的各种不同解读,无一遗漏地分析、罗列出来”;然后是“逆向删存”,通过多种方法检验“不同的解读是否能为该具体作品的诠释空间所‘容受’”。[27]尽管“逆向删存”目的在于寻求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解释,但从其阐释的顺序和具体方法来看,能有效避免阐释得过度或错误。不过,如果歧解都能自圆其说,又不能充分断定某种解释更合理,不妨存留不同的阐释。由于修辞手段、表达技巧等引发的关于诗词意蕴的歧解,我们应在正确理解文本字面意义的前提下,参照诗词抒情言志的传统,并通过作者情况、创作本事等的考察,进而确定比兴、双关、借代等深层的意蕴。如果文本没有提供其寄托之意的线索,而文本之外也无可靠的佐证材料,应避免凭藉猜想而妄加比附;即使根据相关资料可证有寄托之意,也最好不要具体落实。省略导致的歧解,如是省略某个句子成分,应依据创作规律、上下文语境等,判断解诗时所增加的相应句子成分的合理性,从而更好地还原诗意;如是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创造的想象空间,读者可以在“义”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填补,阐释的多样化也更进一步说明诗词的多重意蕴和含蓄蕴藉的审美价值。
诗词阐释实际上是读者运用语言媒介来解释自己对文本语言所反映的对象世界的理解,语言符号表意的间接性、不确切性和可塑性,为作者自由创造和读者个性理解提供了基础,因此从作者、文本、读者三个层面,我们都能找到古典诗词多元阐释的根据。但是,承认多元阐释并不说明诗词都无法“达诂”,也不说明所有的阐释都是合理的存在,而是希望在避免对文本进行过度诠释的前提下,发掘出多种有价值的理解,通过综合比较、去伪存真,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鉴赏古典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