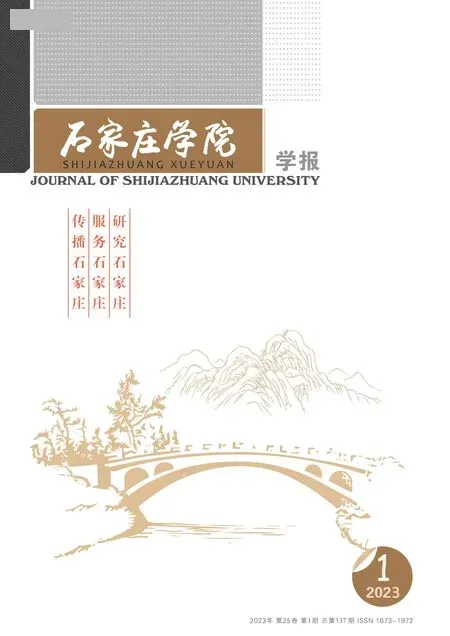《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元遗产案”识微
2023-04-07文霞
文 霞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政法系,广东 广州 510303)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地下出土资料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加快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出土简牍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料,不仅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不同时期的文书、制度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元”遗产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我们试图以此案例为中心,重建他们创造历史的具体场景与想法,观察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与制度的特点。
一、“元”遗产案的内容及时间考证
根据《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整理成果,有3枚简牍涉及该案,兹录于下:
妻以元所有大婢婴送纳,纳为世产男石。后何卖民,直钱九万五千。以其五万买大婢 侍,空地一所直八千。自驾起居。其中复买粢肆一孔,直二千四百。元本有豉肆一孔,后纳(CWJ1③:325-4-25)
永元是汉和帝刘肇在位时的年号,永元十一年是公元99年。“珠”在永元十一年左右出嫁,按此推算,珠可能出生于汉章帝建初(76-84年)或元和(84-87年)年间,在建初后期或元和、章和年间(87-89年)大概四五岁。如果是出生在建初年间,“珠”的出生时间应该不早于76年,不晚于84年。按出生于公元76年算,永元十一年应该23岁了,适婚年龄偏大。按出生于建初中期(80年)推算,永元11年大约为19、20岁,对女性而言也是较大的结婚年龄。按出生于84年算,永元十一年大约15、16岁。如果出生在元和年间,公元99年“珠”应该是12-15岁。汉代女子的初婚年龄大约在十三四岁到十六七岁,[1]69“珠”在永元十一年达到适婚年龄,因此简牍CWJ1③:325-1-55前可能记载有建初晚期或元和的年号,“元”就在此时去世。
二、对简牍内容的考释
关于“散用钱给和”也值得讨论,陈伟先生曾认为简牍上“和”的右边不清楚,可能是“私”之误,是说“何”把出卖宅和奴婢的钱化为己有。[2《]说文解字》:“给,相足也。”段玉裁解释道:“足居人下,人必有足而后体全,故引申为完足,相足者,彼不足此足之也。”[4]64《7辞源》对“给”有4种解释:丰足,供应,及,言语便捷。[6]2650陈伟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这些散用钱应该是“何”归为己有,“给”后面可能是“私”,可以解释为“及”。
还有个问题就是“民”的身份与价格问题。罗小华认为,汉代奴婢价格一般不超过3万钱,“民”的价格高达9万5千钱,应该是奴而不是婢。[7]这种推测是合理的,两条简牍的“民”不是同一人。从时间看来,简牍CWJ1③:325-4-25中“何”卖掉“民”应是“元”在世时“纳”出嫁后进行。而简牍CWJ1③:325-1-55的“民”出卖是在“元”去世后清理财产时进行。从奴婢的排列顺序看来,简牍CWJ1③:325-1-55把“民”放在“侍”的后面,表明“民”是在“侍”之后再买的。而前一个“民”则是在买“侍”之前就已有的。“民”作为人名,缺乏性别特征。《说文解字注》:“民,众萌也。萌,古本皆不误,毛本作氓,非。古谓民曰萌,汉人所用不可枚数。今周礼以兴锄利甿,许耒部引以兴锄利萌,愚谓郑本亦作萌,故注云变民言萌,异外内也。萌犹懵懵无知儿也。郑本亦断非甿字。大抵汉人萌字,浅人多改为氓。”[4]627段玉裁很清楚地认识到汉人使用“民”字的普遍,只表示“懵懵无知”的人。虽然先秦奴隶被称为“人民”,但在秦汉时期很少使用。[8]91-92因此,我们不能断定“民”用作人名时有特别的身份或性别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元”去世后整个家庭共有三奴两婢,在买大婢“侍”之前,“元”仅仅把女婢“婴”送给“纳”,没有送任何男奴,因此,“婴”可能的身份是奴婢或媵妾。[8]62-6“3婴”虽然和“纳”的丈夫“世”没有进入婚姻关系,但其服役内容可能包括给予主人性的满足。[9]168赠送“婴”后留下的空缺,可能由“何”卖奴买婢来填补。
三、“脩”和“珠”的住所和身份问题
从简牍看来,“元”是长沙临湘人,娶了零陵郡泉陵人“脩”,“元”在仓梧去世时,女儿“珠”在才四五岁。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元”与“脩”“珠”的居住地问题。这存在两种可能:仓梧或泉陵,如果他们旅居仓梧,[3]1“4脩”和“珠”在“元”去世后又回到“脩”的老家泉陵住了10多年。这种情况可能性小且不太合情理,泉陵只是“脩”的娘家,丈夫“元”死后,“脩”作为已出嫁的女子很难长时间不住在自己婚后的家而住回娘家。因此,“元”与“脩”“珠”可能都住在泉陵。从地理位置看来,苍梧郡与零陵郡相邻,而泉陵既是零陵郡治,[10]49-50,63-64同时也是“脩”婚后的家及娘家所在,他们一家住在泉陵的可能性更大。
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脩”和“珠”是否参加“元”的葬礼?简牍记载,“元”归葬临湘时因为“珠”幼小,加上临湘距离泉陵数百里,路途遥远,“随脩留泉陵”,母女俩似乎没有回临湘参加丧礼。但这种情况很难理解,秦汉时期人们特别看重生死,东汉时期已有“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厚葬风气,葬礼很讲究排场。“元”去世后,不管“脩”是妻还是妾,她和“珠”都应该回临湘参加葬礼,服斩衰。一般说来,汉代如有亲人去世,亲属出游于外者当奔赴(丧),即使是“女子已嫁者,亦归来奔丧”[11]84-85。可能的情况是,母女俩回临湘参加了葬礼,因珠“幼小,随脩留泉陵”,没有留在临湘。我们推测,“元”的女儿“珠”应该可以留在临湘生活,因其年幼,最终和生母“脩”生活在一起。对于年幼的孩子而言,生母的陪伴是至关重要的。女孩的养育更看重血缘关系,相比之下,不仅宫廷中很多皇子的养育因为继承或其他政治原因不得不早早离开生母,而且在普通家庭中,男孩的成长也可能因为继承原因而远离生母,其中也体现了秦汉时期母子情感与父系制度之间的微妙复杂的融合与对抗。[12]202
在“何”检录、分配财产的过程中,“脩”和“珠”全无财产处置能力,且一直保持难以置信的静默,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脩”是泉陵人,且身份较低。[3]12虽然“脩”是“珠”的母亲,但简牍并没有说明“脩”是“元”的妻子,也没有登记“脩”的身份,“脩”可能只是庶妻。秦汉时期流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庶妻多被称为小妻、旁妻、下妻、偏妻、小妇、少妇、外妇等,[8]6“3脩”可能是其中一种。身处家庭的女性中,庶妻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何”在临湘分配“元”的财产,“元”作为一名家境殷实的商人,在泉陵应该留有较多财产,因此“脩”对于临湘的财产分配没有发言权。岳麓书院秦简的“识劫案”与之类似,虽然“识”曾经是“沛”的“隶”,当后来成为“沛”的免妾并生下孩子后,她对于“沛”生前分给了“识”的财产没有分配权。而对于“沛”在世时曾经口头允诺给“识”的“布肆、舍客室”,“沛”去世后由其户后女冤的儿子“义”继承,分异后的“识”也“弗当得”。[13]151-154
“珠”虽是“元”的女儿,但她既没分到财产,也没有成为“元”的继承人。除了因为“珠”远离临湘、尚处年幼外,女儿在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上的弱势地位也是主要因素。在死者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秦汉法律主张死者的“父母和妻子享有高于其他后代的优先权”[14]120。而女儿最终会成为外姓人,因此,在没有户绝的情况下,无论女儿是否出嫁,都不可能成为“户人”。秦汉时期的未成年“户人”全部都是男性充任,也说明了在室女在户主继承上的弱势地位。徐世虹先生指出:户主的继承必须是“同居数”,就是同居且在同一户籍中人。《二年律令·置后律》也规定:“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其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者。”而“珠”既不属于“同居数”,也不属于年长者,因此,“珠”没有达到身份继承的条件。此外,女儿结婚不利于财产保留在本家族内部。因此,“哪怕是未嫁出门、生活在父家的女儿,通常也不可能分到一份土地”[15]168。“元”作为商人,可能没有土地可以分配,但“珠”及母亲“脩”却没有得到任何宅肆和奴婢,这可能与“脩”身份较低且她们跟“何”异居有关。如前所述,“脩”可能是庶妻,母亲的地位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财产继承。她们俩生活在泉陵,可能户籍属于泉陵,因此“何”在临湘的财产分配完全不涉及母女俩。
其实,即使是秦代,出嫁的女儿也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里耶秦简就记载:“卅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爰书:高里士五(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饶,大婢阑、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8-1554)”[16]356-357东汉时作为“户绝”的出嫁女仍可以继承娘家财产。[17]长沙东牌楼出土的《光和六年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记载了户主精宗死后田产纠纷的案例,精宗死后,留下的“田八石种”被同宗人精张(精昔)强占,其外孙李建在成人后,通过诉讼的法律程序,最终得到了精宗所留3/4的田地,“以上广二石种与张,下六石悉畀还建”[18]73。虽然最后是外孙获得了土地,但仍说明出嫁女儿获得娘家财产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简牍提及的“(永元)十五年三月中,脩、珠俱来”,很可能是母女俩去临湘试图分得家产的记载。“来”的地点是临湘,因为五一广场简主要记载的是临湘的案例。“户绝”的出嫁女可以继承娘家财产,因此,10 多年后“脩”和“珠”回临湘分得家产就具有情理上的可能。另一方面,母女俩在泉陵生活了10多年,因为缺乏收入来源,“元”留在泉陵的财产可能被消耗殆尽,母女俩为生活所迫来临湘寻找帮助就有现实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何”在“元”下葬后赶紧检录财产、卖掉住宅和奴婢的原因——尽可能降低生活成本,以保障自己的生活条件。
四、“何”与“纳”的身份问题
检录、购置及分配“元”财产的“何”是何人?是否和“元”住在一起?叶山教授曾推测“何”是这个家庭的旁系尊亲,李华推测“何”是“元”的同居兄弟,而不是“元”的妻子。①参见黎明钊《试析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几枚东汉简牍》、李华《长沙五一广场简所见“元的遗产案”考述》,载黎明钊、马增荣、唐俊峰主编《东汉的法律、行政与社会: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探索》,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2、96页。她认为“元”在世时,作为正妻的“何”既没有“自驾(加)起居”的必要,也没有对“元”财产进行买卖管理的必要。[19]这种推测稍显牵强。据学者研究,东汉时期商品交换异常活跃,不仅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日常用品可以用于商品交换,而且田、宅、奴婢等集市之外的交易买卖也很盛行,还可以进行瓜分。[20]因此,对一个家境殷实但缺乏田产的大家庭而言,拥有几处房产应该不是难事。“元”作为一个专业商人,[21]其商业活动重心不在临湘,但临湘作为“元”的籍贯所在地,他在那里应该留有不少财富,作为正妻的“何”对其进行经营管理也很正常,“元”去世后“何”来检录、处理临湘的财产也合情合理。“脩”作为“珠”的生母,却在“何”分配财产时完全静默,很大可能是“元”在泉陵的家也留有足够多的财产,这些财产“何”也同样因路途遥远等原因无力干涉。
《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22]59新出土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规定的顺序与《二年律令》大致相同:“死代户次:子男、父母、寡、女、孙、耳孙、大父母、同=产=子=父=母=同=产=子=(同产子、同产子父母、父母同产子、同产子)同居者毋(无)此次,而相与同居。”[23]194这明确了户主的继承顺序:第一继承人是其子男,第二继承人是父母,第三继承人是寡妻,第四继承人是女儿,之后才是孙、耳孙、祖父母及“同产子”。滋贺秀三指出:“若夫死亡而无子,则属于夫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要移交于妻之手,这一点是通行于任何时代和地区的中国人普遍性的法意识。”[24]335因此,“何”在继承顺序上应该排在女儿“珠”前面,可以排除“何”不是其子男,也不是其父母,所以“何”应是排在第三位的继承人——“元”的妻子。另外,汉代继承制度的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户主正常死亡,未婚女儿与被继承人虽然是直系血亲,但因其未婚,其财产要随其出嫁转移到夫家,要被他姓所分割,故排在儿子、父母及寡妻之后。这种继承方式兼顾了血亲和财不出户的原则。[25]130此案例中的女儿“珠”在继承顺序上是第四继承人,虽然幼小,其母亲“脩”也在世,但“元”去世后,正妻“何”就获得了“元”在临湘的财产的分配和管理权。应该指出,妻子并没有财产的所有权,只具有中继的性质,因为“在祖先子孙的连锁关系之中,妻本身没有形成独自的一个环节,无非是寡妻代替夫之一环节并守护到底……出于为嗣子考虑的目的,财产权应该立即被明确并委托给妻亲手保持,以便将来作为夫之后继者所立的嗣子继承该财产”[24]335。
简牍中还有个比较重要的人物“纳”,她出嫁时不仅获得了大婢“婴”,还可能与“元”的一孔豉肆有关。“元”去世后,她的儿子“石”又被“占数户下以为子”,因此,“纳”应该也住在临湘,与“元”一家关系密切。“纳”可能与“元”一家有亲戚关系,李华推测“纳”是“元”的同产姐妹,其儿子“石”过继给“元”。[19]98这种推测稍显武断。从简牍的表达习惯看来,我们看到了五一广场简中其他几处都明确标识了“同居”和“同产兄弟”的情况。据统计,简牍共有8处标识了同产兄弟,[5]142,217除两处是指同一对兄弟“同产兄宗、宗弟禹”外,其他如“晨与父宫、同产兄夜、夜弟疑、疑女弟捐;与母妾、同产弟强”,“荣夫荆前与同产兄郎、弟御及知等同居”,“通同产兄育给事府”,“董与父老、母何、同产兄辅、弟农俱居”,“併同产兄肉复盗”,“辄考问宠、汉、知状宠同产兄”等②参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40、168、168、218、224、231页。其中,“疑女弟捐”与夜、晨可能是“同产”,但却没标识,因为同产姐妹要嫁入外姓家的缘故。,都是同产兄弟,有的还是同居关系。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规定:“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置后,毋(无)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无)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简牍中明确有“女同产”的表达方式,且“女同产”与“同产”并存,因此“同产”只表示同产兄弟,而不代表姐妹。“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无)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者。”[23]195可见同产和同居的重要性,而同产也只表示同产兄弟。另外,西汉初年的法律都规定“同产子”可以为后,“纳”如果是“元”的同产姐妹,其儿子“石”就是“同产子”,有继承权利。但现实中“石”却没有继承资格,只能以过继的方式从“世”那里过继过来,因此,“纳”不是“元”的同产姐妹。我们猜测,“纳”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与“元”是同一宗族,其儿子“石”能够“占数户下以为子”,可能因为“纳”或她的丈夫“世”与“元”有亲戚关系。就像《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那样,“石”作为族人宗亲过继给“元”。另一种可能是“纳”与岳麓秦简“识劫案”中的“识”类似,是“元”的“隶”,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因此可以获得大婢等财产(可能包括一孔豉肆)。而与“识劫案”不同的是,此处的“何”是“元”的正妻,而只是免妾而已。
五、“公私”领域下女子的姓氏问题
这个案例中,除了“珠”的前夫“蔡恤”有姓氏外,其他人均以单名出现。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大部分涉及到“私”的场合,或者只涉及一个家庭时,都仅记录人名,而不记录姓。财产分配与户主继承都属于“私”的领域,案例中甚至连“元”也只记单名,说明此案例还停留在“私”的层面,除“蔡恤”外的其他人都与这个家庭有关。只有在涉及到刑事案件及某些具有固定格式且属于“公”领域的信息登记时,才会记录姓名。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在“公”的场合,女子记姓大多以“女子某某自言”的格式出现,如女子张罷自言、女子王刘自言、女子陈谒诣府自言竟解、南乡言女子范荣自言本、女子张基自言本、南乡言女子周复自言须立秋书等,有件文书记载了“知状女子马亲、陈信、王义”的姓名。①参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56、173、176、180、181、184、213页。简牍CWJ1③:291记录了“女子王绥”的牛被劫的案件,[5]139可见在秦汉帝国形成和建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庶民都有姓,即便是女子也是如此,姓已经达到普遍化的程度。[26]88然而,与里耶秦简户籍文书的“只书名,省写姓”不同,[27]虽然五一广场东汉简记载了女子姓名,但在遵从文书简洁的情况下,只书写女子信息,我们无从判断这些女子的姓氏是来自父系,还是来自夫宗。
这批简牍中有一个疑似女子“于”自改姓氏的案例:“会计,于自名户,随兄姓为杨。”整理小组认为,疑“于”是女性,出嫁后随夫姓。自立户后,才恢复本姓,随兄长姓为杨。或“兄”为人名。[5]166据此推测,“珠”在被弃前可能在“公”的场合被称为“蔡珠”,被弃后就恢复父姓。日本的滋贺秀三提出,女子从父姓这是从自然性的意义而言,这种关系从出生直至死亡终身不变。而从社会性的意义来看,女子从夫姓是因为婚姻取得了夫宗的地位。女子姓氏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背离,是女性命中注定的。[24]16从简牍看来,女子姓氏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可能同时存在,这时期的女子既可从夫姓,也可从父姓。
五一广场简中的女子姓氏非常多样,即使同在南乡,也出现了范、周等不同的姓。如果秦汉时期的平民妇女在户籍、司法文书等官方文书上只将夫姓视作唯一的正式姓氏,母、妻等嫁入家门的女性在礼法维度被视为脱离父族而隶属于夫族之人,[28]那么,临湘县人口流动的频繁及汉代“异姓杂居”的程度就可见一斑。实际上,女子的离异、再嫁、立户甚至丈夫的死亡都可能影响到女子的姓氏选择,而绝大多数古代女性都生活在“私”的领域,在家族秩序的支配之下,姓氏主要来自户主,而附在户下的女性及奴婢虽被视为“家人”,[29]却不再记录姓氏。这种记录方式掩盖了女子姓氏的选择变化,导致了我们对女子姓氏的笼统模糊的认识。
六、宗法关系与婚姻关系较量下的家庭生活
秦汉时期的个体家庭都处于宗法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网络中,因此,婚姻关系和父系宗法关系都会影响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该案例看来,个体家庭中母亲地位(主妻、次妻或妾的身份)、父亲去世时孩子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是影响财产继承的重要因素,[30]271此外,孩子性别及出生顺序也会影响继承。
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所有制和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家庭规模也有原来的核心家庭向扩大家庭转变。五一广场简中有不少父母兄弟同居在一起的案例,前面提及的几对同产兄弟多是同居关系,有的还和父母同居在一起。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很流行,对于一些富裕家庭而言,妻妾子女这些重要的家庭成员并不住在一起。这个案例中的正妻和庶妻就住在相隔几百里的不同郡县,汉代流动性较强的商人阶层因为人口流动而造成的籍贯不同的家庭间的通婚可见一斑。[1]49这种不同地区间的远距离通婚能够打破地理条件的隔绝和限制,一方面说明这个家庭有足够的维持两个住处生活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体家庭的分化尤其是一些核心家庭或残缺家庭在应对风险、变化时的脆弱。
然而,在秦和西汉时期一些普通家庭的户籍简牍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正妻和庶妻被登记在一起,走马楼吴简也有不少正妻庶妻登记在一起的记录。可见一般家庭并不具备分户的经济条件。《二年律令》也明确规定立户条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2页。杨振红先生认为,“有田宅,附令人名”中间不应断开,说的是“有田宅却让他人为自己名田宅”的情况,其说可从。参见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3期,第52页。律文中所说的“无户却让他人为自己名田宅”和“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名田宅”都是非法,②杨振红先生认为,这里包含三种非法名有田宅行为的处罚规定:不为户、有田宅却让他人为自己名田宅及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名田宅。参见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3期,第52页。与先生的意见不同,笔者认为“不为户”在此处应是一个前提,汉初有很多种“不为户”的情形,有合法有非法,从律文内容看来,“不为户”与“名田宅”也不是并列关系。因为笔者认为这里应该只包括“有田宅附令人名”和“为人名田宅”两种情况。而为户有田宅才是正常情况,为户无田宅则会根据一定条件配以田宅,保障其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31]106从这个角度而言,经济条件是影响秦汉家庭规模变化的重要因素,案例中的“元”在世时经济条件好,可以提供正妻和庶妻相距遥远且富足的生活。而一旦经济基础不能保障日常生活,就会产生甚至激化各种家庭矛盾,个体家庭中的婚姻关系和大家庭下的宗法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
个体家庭中最为核心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个体家庭中,作为妻或妾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她们作为母亲时则影响更大。而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从父辈到子孙之间一代又一代的强调传承的宗法关系具有重要地位,纠缠和影响着家庭内的婚姻关系。在中国古代这个父系血统决定一切的社会里,妻妾、女儿等女性都是附属品。从“元”的遗产案看来,即使他有女儿“珠”,但因为没有儿子,其户主身份及主要财产,都归占数其户下的“石”继承,而不是其女儿“珠”。个体家庭内部则强调女性的巨大影响,而扩大家庭和宗法家庭的继承和延续更重视男性的作用,两个矛盾的原则导致了个体家庭与父系血缘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中国家庭的每个方面。[15]15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