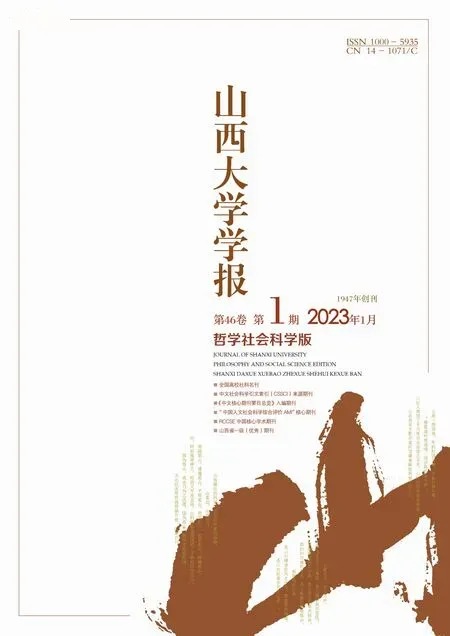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
——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2023-04-06王玉彬
王玉彬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庄子那里,正所谓“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下引《庄子》仅注篇名),语言是人称谓、指示、召唤、接纳万物的基本方式,在人类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天下万物本以“浑沌”为其存在态势,因之而起的语言符号同样也应该呈现“言未始有常”(《齐物论》)之貌。如果语言不能“知止”于此,就会逐渐衍化出在浑沌中凿出秩序、固化价值的“庄语”,这也就是《齐物论》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通过论辩“是非”的方式,“庄语”试图定性乃至重构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从而形成了对外物的限制与宰制。在庄子看来,这种“庄语”恰恰构成了天下脊脊大乱与众人役役相争的缘由。正是为了解决语言因隐于荣华与小成而使人无法合理观物、应物的生存难题,庄子才选择了“不可与庄语”,并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方案——“三言”(寓言、重言与卮言)。通过《寓言》的相关表述来看,“寓言”之必要,在于人们“与己同则应,不以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异于己为非”这一日常的心理与存在结构;“重言”之必要,是因为人们更乐意相信那些“耆艾”也即往圣先贤关于“经纬本末”(即治理之道)的旧有阐述。这样,寓言与重言就是以常人之是非与古今观念为观照而生成的语言策略,意在弱化言说对象的是非对抗心理、因顺言说对象的尊古崇圣心理;与之相应,卮言则是依乎天理、因物为正之言,由之可敞开一个“咸其自取”的生活与意义世界。如果说寓言、重言是一种别有意味的语言形式、独具匠心的语言策略,卮言则是这种形式与策略的内容表达与实践应用。在此意义上,卮言既呈现出了庄子语言观念的核心特征,更与其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换言之,卮言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思体”,承载着庄子关于世道人心的思考。本文之所以关注《齐物论》中的卮言问题,并致力于阐述卮言的齐物旨归,理由主要两点:其一,在语源层面,《寓言》与《天下》关于卮言的说述全部本于《齐物论》;其二,《齐物论》的语言风格、文本内容典型体现了卮言的内涵特征与义理旨归,由此可对之进行更具体而深微地理解。
一、《齐物论》与“卮言”
陈少明认为,“《齐物论》的言述,可以代表《庄子》的风格”[1]。徐圣心也看到,《齐物论》“有许多段落是纯粹的卮言”,因此是“恰当的卮言范例”。[2]36两位先生都看到了《齐物论》在表述风格上的独特性或典型性,徐先生更是将之视为卮言范例。那么,何以说《齐物论》是《庄子》中最具“卮言性”的篇章呢?这一点,可以通过《寓言》《天下》的卮言表述与《齐物论》的材料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来证明。
《寓言》述卮言云: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天下》述卮言云:
以卮言为曼衍。
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
这些与卮言相关的表述多与《齐物论》直接相关,举证如下:
其一,《寓言》“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以及《天下》“以卮言为曼衍”,均取自《齐物论》所谓“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
其二,《寓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一段,与《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用语类似。
其三,《寓言》“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中的“天均”,本于《齐物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一句,近于《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其四,《天下》有所谓“諔诡可观”,陈鼓应注“諔诡”云:“与《齐物论》篇‘吊诡’同”[3]。马其昶注“吊诡”亦云:“‘吊诡’,犹‘諔诡’”[4]19。于省吾云:“经传言不叔,金文通作不吊。叔吊音近字通,后世假叔为吊,遂不知叔之本作吊矣”[5]。由此可知,《天下》之“諔诡”即《齐物论》之“吊诡”“恢恑”。
其五,《齐物论》所谓“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之“化声”,恐即为“卮言”之另名。郭嵩焘释“化声”云:“言随物而变,谓之化声”[6]。张祥龙说:“‘化声’意味着随语境而转化,不受制于固定的观念或对象”[7]。“随物而变”“随语境而转化”之“化声”,也即“因物随变”之“卮言”。马其昶云:“化声者,天籁也”[4]20。以“天籁”释“化声”。吴光明也认为,“不知之知”“参与生命变迁,与之反映共鸣,这叫做‘化声’,叫做‘相待若其不相待’,叫做‘物化’”[8]。倘若此说不误,则《寓言》与《天下》非仅以《齐物论》之“文”释“卮言”,“卮言”本即《齐物论》“化声”之别名。
可见,《寓言》《天下》关于卮言的言说内容,全部取自《齐物论》;这样,本文以《齐物论》为卮言之典范性文本,也便无疑义了。尤需注意的是,卮言所涉《齐物论》之文句,均与“天钧-天倪”之“齐物”要义相关,本为阐“意”之文,《寓言》《天下》将之化用成了释“言”之文,这种“意”与“言”之间的照应与呼应,也可以佐证卮言并非仅仅是一种表意方式或话语策略。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才将庄子的“卮言”与“齐物”结合起来论述,并以“齐物”作为庄子语言观念的宗旨与归宿。
在《庄子“三言”的创用及其后设意义》一书中,徐圣心以《齐物论》为范例分析了庄子之卮言。但是,我们不认可徐先生的这种论断:《齐物论》中的卮言就是那些除却寓言、重言之对话模式的“思想独白”。庄子之卮言,并非仅以“思想独白”的形式呈现,同时也贯注于庄子创设的寓言与重言之中。在《齐物论》之中,“南郭子綦隐几而坐”章、“啮缺问乎王倪”章、“瞿鹊子问乎长梧子”章、“罔两问景”章等都是寓言;“故昔者尧问于舜”章是重言;至于卮言,既包括寓言中南郭子綦之“天籁”说述,啮缺、王倪之“四不知”,长梧子、瞿鹊子之“妄言”“妄听”,也包括重言中“舜”所述之“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还包括寓言、重言之外的思想独白与梦蝶自述。可见,庄子之卮言是贯《齐物论》之始终,甚至是贯《庄子》内篇之始终的。
二、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
对于《齐物论》在言说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特征,杨祖汉与徐圣心均有过细察与详论。杨先生认为,《齐物论》的言说方式有三:互夺双亡,肯定一切;无穷追溯,泯归当下;犹豫仿佛,真俗不二[9]。徐先生认为,《齐物论》的表出形式有六:排比并立;再现复义;对称互涉;对比相消;后设离端;历程旨冥[2]73-79。两位先生对《齐物论》言说风格与表意形式的把握堪称精详,本文所欲阐述者,固与之多有关联,惟所重者不在分析《齐物论》之“文体”特征,而是以卮言为“思体”,并进而讨论此一“思体”之表出方式(“尝试言之”)与聆听方式(“姑妄听之”)所彰示的义理旨归。
先述“尝试言之”的意义。在《齐物论》中,我们常会看到“请尝言之”“尝试言之”“妄言之”这一类型的表述,相关文段有三: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鴞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蔡岳璋认为,“《庄子》文本里头那充满戏剧性口吻的‘尝试言之’、‘尝试论之’、‘予尝为女妄言之’等近似说书口吻般,对于自身言论展现高度保留与宽容态度,既不得已而有所言说,却又时刻与话语自身‘保持距离’的句式用法之中。这也是引发《天下》篇对庄子作出有别于其他诸子之学术定位,其间批评转向的巨大扭力的关键所在”[10]。这种观点既强调了“尝试”所透显的言说的不得已性、容留性,也看到了“尝试”作为庄子之独有语言态度的关键性与风格性,可以说,“尝试言之”即卮言的首要风格。
上引第一段“请尝言之”、第二段“尝试言之”之前,均有论者容易忽略的“虽然”一词。实际上,“虽然”正是尝试性之卮言的立言基点或内在态度。细味两处“虽然”,其间之义理指向有着细微的差别。第一段“虽然,请尝言之”之“虽然”,意指“我之言”与“我之所批判之言”(可称为“彼之言”)是“相与为类”的,两者之间没有实质区别;正因“我之言”与“彼之言”是本质相类的,“我之言”只能“尝试言之”,正因如此,“我之言”与“彼之言”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彼之言”为“断言”,“我之言”为“尝试”,两者隐含的意态可谓悬若天壤。第二段“虽然,尝试言之”之“虽然”,意指“我之言”出乎“吾恶乎知之”之“不知”,即:因为“我”本即处于某种“无知”之境中,所以只能“尝试言之”。同样,第三段中的“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虽未明确道出“虽然”,细味其语脉,亦可知“妄言”亦以不可知之“妙道”为出发点,与第二段之意相同。
可见,卮言之所以是尝试性的,理由有二:一是作为对万物的称谓与召唤,语言必须尊重“万物之化”的本然状态,这种本然状态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的“不知其然”,或者说是“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大宗师》)的“不知之化”;二是语言既为语言,便非“妙道之行”自身,也便缺乏“道行之而成”的“成”所具备的自然完满与天然充盈,必须通过“尝试”去不断凑泊、揭示、贴近之,而无法一言道破、一语中的。
结合《齐物论》上述段落的内容而言,可知“尝试言之”首先是“批判性”的:第一段之“请尝言之”,意在破除对“始”与“无”的无穷追溯;第二段之“尝试言之”,意在拆解对“同是”或“正”之追求;第三段之“妄言之”,意在解悬生死、是非之困扰。这种批判性的言说方式之所以是尝试性的,恰因其所批判的对象在表述中呈现出了缺乏根基的确定性与断言性:对宇宙根源(道体)的确定、对万物同然的确定、对自以为是的确定。在此意义上,庄子的“尝试言之”意在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揭示这些“断言”在本质上的“不确定”或“假定性”:“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所有“断言”,都是具有假定性质的“未定之言”,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自以为是、信以为真、误以为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有走出成心束缚、师心自用而与化游息的可能。
“尝试言之”还进一步体现为“吊诡性”。《齐物论》云:
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在庄子那里,卮言的批判性不仅指向他者之言说方式与立论态度,也指向作为“有言”的卮言自身,以及作为“有言者”的“我”自身。王又如称这种言说方式为“反讽”(irony),也就是“一种以意料之外的自我取消或自我矛盾为特征的表达方式”[11]。长梧子谓瞿鹊子处乎梦境之中,又谓这一判定自身亦为梦中之言;《齐物论》本“有言于此”,然而,“此言”不管与“彼言”有无差异,注定与之“相与为类”,受到语言自身限度的限定:一“言”既出,虽其本质是“未定”的,但却一定会趋向于“既已”与“定型”。可见,尽管卮言因其“尝试性”而体现着与一般语言不同的质素,并有与妙道为行、随万物而化的特征,但终究还是一种“言”而非自然妙道或万化自身。王夫之说:“此欲显其纲宗,而先自破其非一定之论”。[12]卮言的吊诡性,由此“自破”而充分开显。孔令宜认为:“庄子为避免自己的论述也陷入言诠,采取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用‘旋说旋扫’的方式,取消彼端与此端这种逻辑上的二元对立,谓之‘辩证的诡辞’。”[13]实际上,卮言无法完全摆脱言诠,亦无法“取消彼端与此端”之二元对立,正因如此,卮言才只能靠“旋说旋扫”的方式不断地“自我脱冕”——“它藉此来破坏文本被权威化和封闭化,以避免文本之死。为使文本如活物般不断地‘曼衍’下去,就只好让作者主体退位、让作品权威倒塌,一边邀请阅读者加入更多地参与”[14]382-383。总之,卮言既是对“庄语”的批判,亦极力避免自身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庄语”,从而永葆其开放性与流变性。
在庄子那里,卮言的“尝试性”与“吊诡性”并不意味着语言观念的游移不定,而正是出于语言的审慎;并不意味着言说的犹豫不决,而是要为言说留出余裕;并不意味着立论的生涩难通,而是立论圆熟的内在要求。《齐物论》云:“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面对“不知其然”之“妙道之行”与“万物之化”,“知止”实际上就是庄子在“书写的临界点”[10]上的“怵然为戒”。面对这一“临界点”,如果不知“知止”而跨越语言所应持守的界限,就会操起语言之斧而“尝试凿之”,这是“倏忽”般的鲁莽尝试,必定会破坏语言与生命的浑沌余地,并永远失却了再次“相与遇于浑沌之地”的可能。与这种跨界的雄心壮志相反,“尝试言之”体现出的是一种在“批判”与“反身”中的复归姿态,由此,语言便可以“负道而抱物”,既不越界而言“道”,亦不离道而言“物”,而是“在道之中言物”;既为“在道之中言物”,卮言也便成为沟通“道-物”的“中介”,或者说处于“道物之境”中的“人”左右逢源而调适上遂的存在姿态:“它不只说出真理,尤有甚者,它‘在真理中’进行言说,而‘尝试言之’正是一切识别的指认关键。”[10]在此意义上,庄子并不认为以语言为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的人类能够掌握天道、占有万物;人与万物一样,都是于“天道”之中存在的存在者。这样,人的语言与行动也必须“在道之中”,而不能僭居于“道”或“造物者”的位置。
一言以蔽之,以“知止乎其所不知”为精神、生命状态的卮言不是一种既成性的最终“抵达”(“知止”而不“留止”),而是一种回返性的暂且“尝试”——在“知止”不断“回返”,在“回返”中不断“照见”。
三、从“妄言之”到“妄听之”
正所谓“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泛应训》),先秦诸子之书无不体现出浓厚的现实关怀、强烈的应用倾向,因此,这些子书实际上都蕴涵着某些潜在的言说对象与阅读对象,并致力于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化、改变言说对象乃至阅读对象的思维与行动方式。比如,老子之“道德”言说,冀其“甚易知、甚易行”之言可为侯王知、行而能守;孔子之仁义言说,一为教化君主而行德政,二为教化士人而成君子。在此意义上,老子与孔子所阐发之言与文,均可谓为“载道”之“庄语”;既“载道”矣,“庄语”必以“传道-教化”为目的,也即教化听者、改变读者为目的: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第七十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论语·阳货》)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老子以其言为“有宗”也即“有道”之言,故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寄望于侯王知其言、行其言,乃至以其言为法则。子贡、颜回于孔子之言无不悦,不违而述之、事之,亦即听之而从之。可见,老子之所期待、孔子之所追求者,为听其言者之“从其言”。孟子云:“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体现出了更强劲的语言信力与思想信力。
那么,庄子又是如何在卮言的脉络中看待、对待“听者”的呢?《齐物论》载: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
徐圣心认为,这段话表现的是长梧子“先使听者急欲有所得之心稍微松弛,而后才开始其卮言”[2]57。仅以“妄听”为一种聆听卮言的心理准备。实际上,长梧子不仅以“妄言”为瞿鹊子言,亦建议瞿鹊子“妄听”此“妄言”。“妄听”与“妄言”本即不可离分:“妄言”要求“妄听”,“妄听”要求“妄言”,这正是庄子营构出在面对他者、相互交流的时候的“卮言情境”。也就是说,卮言并非仅仅是“妄言者”所道出的内容,而是亦包括“妄听”在内的“语言-思想-存在”姿态。如果说作为“妄言”的卮言反映的是语言面对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知止态度与滑稽色彩,那么,“妄听”摹写出的则是“卮言情境”中的人(不管是言说者,还是聆听者)所应具备的投身倾向与开放姿态。
所谓“妄听之”,首先要“姑妄地听”,“姑妄”故不执着;其次是“虚妄地听”,“虚妄”故不胶固。这与《人间世》孔子为颜回揭示出的“心斋”若合符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与“心”分别指向“成形”与“成心”,“听之以耳”致力于感官化地听到一些什么,“听之以心”致力于理性化地听见一些什么。不管是感官化的听到还是理性化的听见,所听的那些“什么”总是具体的、限定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听”之中得到建构的;与之不同,“听之以气”或“妄听之”并不以“听到一些什么”为意,并不以“我”的建构为意,惟当如此,“听之以耳”与“听之以心”才能归本于其所然与所是,一种在“心斋”之虚境与无境中向“道”而在的存在方式也便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卮言情境”中的“听者”与“言者”共享着“妄”这一既不“庄”不“正”、不“成”不“我”的开放姿态,也便意味着“听者”与“言者”处于某种根柢性的平等与均衡关系之中,从而迥异于“庄语”情境中“言者”与“听者”之间的“主-从”式教化关系。如果说“庄语”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与被迫接受,卮言曼衍出的则是“彼是莫得其耦”的“道枢”之境,“言者”与“听者”正是在此“天钧”境域之中相与相遇、相尊相蕴,由“环中”而观万物之化、明妙道之行的。“言者”与“听者”均可因物化而明独化、因自然而明自由、因地籁而聆天籁,呈现出卮言的开放性与平等性。
赖锡三说:“理想的书写者便是妄言者,而理想的读者则是妄听者,妄言与妄听浑然一体,共同在一‘非实体’、‘虚位化’的文本空间中莫逆于心地遇着,一起参与语言的创造游戏。”[14]在作为“语言游戏-生命游戏”的“卮言情境”中,“妄听”的本质是一种“邀请”:“卮言使听者解义,并同步用功。”[2]67卮言并非坚定而压迫式的“果是”宣教,也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揭示“同是”真理。卮言是“妄言者”对“妄听者”的邀请,一起步入“真理之路”的邀请。这种“真理之路”,也就是庄子所谓“摇荡、恣睢、转徙之途”: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为来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大宗师》)
尧之所“谓”意而子者,为“仁义”,为“是非”;尧之所“资”意而子者,为“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仁义”与“是非”即“庄语”,“躬服仁义而名言是非”即“庄语”对“听者”的单向教化,“必”说明这种教化是一种必然如此的强制性要求。许由认为,尧之“庄语”意味着对意而子之自然生命的刑罚,由之无法步入“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也即无法成就为“真人”并通达“真知”。《说文》云:“妄,乱也。”在此意义上,“妄听”即汩乱或拒绝“必”之强制、必然,而在“遥荡、恣睢、转徙”中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游息。《天下》云:“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与“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的灭裂相比,卮言正所谓“连犿无伤”者也。
四、结语:“卮言”与“齐物”
在庄子那里,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就是在“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因其“在‘妙道之行’中”,卮言并不企图用“言”的方式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因其观照、因顺的是“万物之化”,卮言亦不企图用“言”的方式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在“妙道之行”中观照“万物”之化,卮言必须通过“尝试言之”“妄言之”的方式主动“知止”,才能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寓言》所谓“卮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这是卮言之“齐物”旨归的第一个维度的体现。
除了沟通“道”与“物”,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价值和意义。附着于“辩”、趋向于“名”,是“言隐于荣华”的必经之路,此即“庄语”的生成逻辑;在此意义上,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通达开放中敞开彼此、沟通你我。人与人注定是在“语言”中相遇的,这种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正如《应帝王》中的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卮言亦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性质,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最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是卮言之“齐物”旨归的第二个维度的体现。
总之,卮言乃朝向“无言”之妙道与物化之言,衍生出的是“忘言”之无竟与广莫。“无言”“忘言”并不意味着卮言的不必要,恰恰相反,庄子追求的是“言无言”“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言无言”者,以道之无言而言物之可言之谓也;“与忘言之人言”者,彼此不以卮言为庄语,而可“咸其自取”于“天籁”“莫逆于心”于“无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