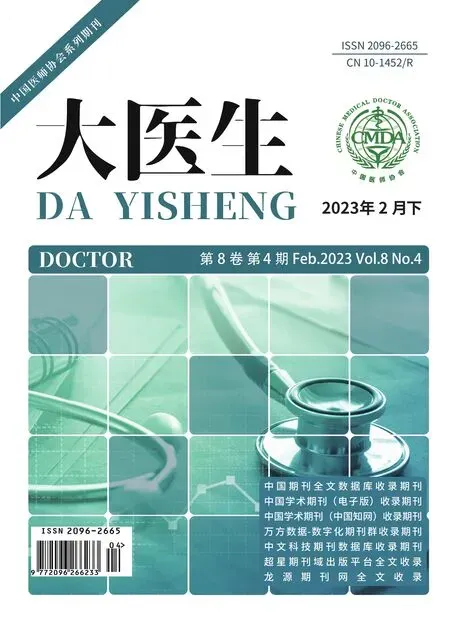伏邪理论指导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药治疗
2023-04-05王格格邱雪莹陈新胜
王格格,邱雪莹,陈新胜
(1.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5;2.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鄂州中医医院消化内科,湖北 鄂州 436000)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主要累及结肠和直肠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间断性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及里急后重等。牟强[1]以60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例开展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常规的西医治疗,加入中医药的治疗,不但能缓减不良作用而且对患者后期身体恢复有极高的价值。现阶段西医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虽在短期内有成效,但溃疡性结肠炎易复发的特点提示对其的治疗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而长期的西医治疗对患者的胃肠道刺激较强,尤其对于体质较差的患者还可能诱发其他并发症,加重病情的复杂性;中医药治疗能够在改善溃疡性结肠炎症状的同时,注重调节脾胃的平衡,其优势显然。而张莉敏等[2]基于伏邪理论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的研究提示,应用中医经典理论“伏邪理论”治疗现代难治病例如溃疡性结肠炎安全有效,值得深究和推广。
“内伤伏气致病”流派代表性传承人朱祥麟教授认为发病病机为湿热毒邪蕴结于结肠。饮食不洁,湿热邪气感而内伏,过期而发病。本文总结溃疡性结肠炎多年诊疗经验,收集溃疡性结肠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相关古今文献、临床病例,拟定特色中药方剂,为其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1 溃疡性结肠炎的传统中医认识
溃疡性结肠炎无具体的中医病名,对其类似临床症状的论述可见于“肠澼”“泄泻”“便血”等多种疾病[3]。最早出现是在《黄帝内经》中关于“肠澼”的描述。如《素问·通评虚实论》中“肠澼便血何如”“肠澼下白沫何如”“肠澼下脓血何如”,后世也将其称为痢疾[4]。《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记载“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入五脏,则脘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5]。”《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6]。”皆表明饮食起居不节,脾胃内伤而易于致病。《诸病源候论》云:“凡痢皆由荣卫不足,肠胃虚弱,冷热之气,乘虚入客于肠间,肠虚则泄,故为痢也。”可见该病发病基础为脾胃大肠虚弱[7]。李永成教授认为溃疡性结肠炎是以湿热瘀等邪为标,脏腑失调为本,标本同病,《温病条辨·湿温》中有:“秽湿着里……气机不宣,久则酿热……秽湿着里,邪阻气分……秽湿着里,脘闷便泄”,湿热之邪互结,热邪易灼伤血络,湿邪性黏趋下,蕴结肠道,久而成毒,脂膜肠络受损,肉腐酿脓,则见带下黏液血便[8]。《证治汇补·痢疾》言:“恶血不行凝滞于内,侵入肠而成痢疾,纯下紫黑恶血。”瘀血是溃疡性结肠炎发病的驱动因素,瘀血日久,客于肠内,易于复发,阳气逐步虚损,血液运行无力,且气血壅滞后致血败肉腐成脓,整个病程迁延难愈[9-11]。《景岳全书·泄泻》有云:“脾弱者,因虚所以易泄,因泻所以愈虚……下必及肾……所以泄泻不愈,必自太阴传于少阴。”脾为后天,肾为先天,脾主运化,将饮食水谷转化为水谷精微,并将其吸收、转输到全身脏腑;肾阳助脾阳吸收、转输精微。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会致脾阳不振,而脾阳若是久久虚弱,又会进一步影响到肾阳,导致肾阳虚衰,故脾肾虚弱是久泻久利的重要病因[12]。
古今医家一致认为溃疡性结肠炎以本虚标实为主要病机特点。国医大师李佃贵教授认为素体脾虚,运化不利,水湿等邪气内生,蕴结于肠,郁热内生,浊毒阻滞气机,最终伤及肠壁脉络而致病[13]。李乾构也认为溃疡性结肠炎以湿热痰瘀为标,以脾虚为本,久而及肾[14]。王长洪亦言脾虚为发病基础,湿热毒邪诱发致病,气滞血瘀等病理产物贯穿整个发病过程[15]。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与环境、饮食、五志等后天因素密不可分,其病位主要在肠,与五脏关系紧密,尤与脾胃为甚,久而及肾[16]。故中医主张“益气健脾,涩肠止泻”的治法[17]。
2 基于伏邪理论认识溃疡性结肠炎
2.1 伏邪理论的内涵伏邪又称伏气,为潜伏而暂不发之邪。最初属于伏邪温病的范畴,即狭义的伏邪,因外邪入体、正气被遏或正气虚弱不能鼓邪外出,使邪气潜藏于脂膜、膜原、肌腠部位,伺机而发[18]。且伏邪非指六淫,专指疠气内伏,邪伏膜原[19]。《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论述,为伏气学说之肇端,指出感寒未及时发病可成为伏邪,潜藏于体内,遇感而发,且发病与否取决于人体正气是否充沛。随着温病学说迅速发展,伏邪不仅局限于伏邪温病,还逐渐扩展到一切体内伏而不即刻发病的邪气,即广义的伏邪。《王氏医存》载:“伏匿诸病,六淫、饮食、诸郁、结痰、瘀血、积气、蓄水、诸虫皆有之”,又进一步提出伏邪不仅局限于外感六淫,还包括内伤杂病,主要为湿热、瘀血、痰浊、内毒等内在的致病因素[20]。总之正气虚损,邪气伏存,正气胜邪,故邪虽伏存而不发,正不敌邪,故发而为病[21]。
2.2 伏邪理论与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性郭富彬等人通过因子分析研究,调查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症状的多元性及高度复杂性,诱发因素的规律性及反复发作的疾病特性,发现传统的单一发病机制很难解释溃疡性结肠炎中医病机,而中医相关“伏邪”理论依据病邪所伏部位和性质的不同,其症状及多重易感性也存在差异,这与溃疡性结肠炎症状多样性及复发的规律性有很高的一致性[22]。杜晓泉教授认为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与湿热之邪所伏部位有关,肠道因层面较深,气血流动慢,故而邪易伏于此[23]。董时洁等通过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血液流变学检测实验研究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液浓度及黏稠度偏高,血液不能充分营养肠道黏膜,导致细胞缺血、缺氧而变性坏死,肠道黏膜组织因此损伤,加之血液黏稠度高使毛细血管因血运不畅而阻塞,血液凝结,血栓形成,肠道黏膜组织坏死,形成溃疡[24]。溃疡性结肠炎始发经治疗后多有湿热之邪未除而藏匿于体内,具有一定的活动性,一旦素体正气虚损,加之感受外邪,则容易复燃,甚至累及他脏[25-26]。黄雅慧教授提出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需根除伏邪,谨防留瘀,同时需扶助正气,正盛邪退,根本上应祛除诱因,预防再发[27]。
2.3 以伏邪理论为指导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2.3.1 健脾燥湿,清热解毒,和血生肌 主证:晨起腹泻,一日多次,日久不愈,黏冻便或夹脓血,腹胀,里急后重,纳谷欠佳,形瘦乏力,口干少饮,舌黯红苔白黄腻,脉濡缓。
方药:朱氏自拟健脾愈疡汤(黄芪15 g,白术10 g,薏苡仁20 g,升麻6 g,黄连5 g,五倍子10 g,地榆15 g,赤石脂20 g,三七粉3 g,木香10 g,白及10 g,甘草9 g)。
按语:溃疡性结肠炎复发活动的关键在于湿热蕴肠,脂膜血络受伤,气血不调,大肠传导失司。湿为阴邪,重浊黏滞,湿与热合,热炽湿郁,充斥三焦。热入湿中,如蜜之黏滞,胶结不解。湿热伏藏,胶结于体内,难以清解,迁延难愈,成为“湿热伏邪”。湿重则阳微,热重则阴竭,致正气耗损,无力驱邪外出,使“湿热伏邪”潜藏于体内,每遇诱因而发。《景岳全书·泄泻》云:“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24]脾虚是湿热伏邪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诱发湿热伏邪反复发作的重要因素,因此,针对湿热伏邪,当补益脾胃之气,合以燥湿,助邪外达。方用黄芪、白术、薏苡仁、升麻补脾益气升清;白术、薏苡仁、黄连燥湿利湿,清热坚肠;木香行气以除后重;三七和血止血;白及活血生肌;地榆活血、凉血、止血;改善结肠阴络血液循行而止血便;五倍子、赤石脂凉血涩肠固下。而黄芪配黄连能治脓便,黄芪配白及去腐愈疡,甘草调和诸药。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甘草具有消炎、抗氧化、抗癌、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作用,在调和全方药效中发挥着卓越的作用[28-29]。
2.3.2 理气活血、化瘀消滞、荡涤浊邪 主证:腹痛即泻,泻后痛缓,日久不愈,腹胀甚,两胁不舒,腹鸣,脓血粘冻,里急后重,纳少嗳气;面目下黯,舌瘀苔白黄,脉弦滑。
方药:膈下逐瘀汤《医林改错》减味(赤芍10 g,当归10 g,川芎10 g,红花10 g,玄胡10 g,五灵脂10 g,乌药10 g,香附10 g,枳壳10 g,甘草6 g)。
按语:邪毒内困既久,肝失疏泄,气机塞滞,久病入络,瘀结于肠,则瘀血与邪毒胶结难解,损伤结肠肌膜,形成溃疡而不愈。故治法应以理气活血、化瘀消滞、荡涤胶浊之邪为主。方用王清任膈下逐瘀汤去桃仁、丹皮。原方治“肾泻”“久泻”“百方不效”者,谓有“瘀血过多”所致。方中香附、乌药、枳壳疏肝理气行滞,当归、川芎、红花、玄胡活血化瘀,尤其五灵脂腥味入络,化瘀血,祛胶浊;合用之使肠道蕴结日久之瘀滞消除,使溃疡能祛瘀生新以愈。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之理。气血调和,脾胃亦健,肠腑通顺,顽疾可渐痊愈。根据相关药理学研究表明,结肠黏膜病理异常的情况通过调气活血中药的治疗后有明显改善,例如方中川芎具有抗炎、改善血液循环、抗血小板凝集等作用[30];香附具有极佳的抗炎镇痛作用[31]。红花能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所诱发的血小板聚集、释放[32]。
2.3.3 补肾温阳,活血复膜 主证:腹泻一日二三次,久不愈,腹痛绵绵,待暖则舒,便多黏冻、少脓血,里急后重,肢末畏冷,尿清长或尿频涩,腰酸,舌黯瘀、少白苔,脉沉细微。
方药:自拟补肾复膜汤(黄芪15 g,补骨脂10 g,肉豆蔻6 g,五味子10 g,淫羊藿15 g,当归10 g,三七粉3 g,儿茶6 g,赤芍10 g,木香6 g,白及10 g,炙甘草6 g)。
按语:湿热伏邪,内伏日久,耗伤脏腑阴阳,至阴阳虚损,气血亏虚,继而出现脾肾阳气俱衰,病程后期形成寒热、虚实交杂之证。方用黄芪大补元气,淫羊藿、补骨脂、五味子补肾温阳,木香行气,当归、赤芍、三七和血消瘀,白及、儿茶和血以复肠膜溃疡,肉蔻温中,炙甘草补中并和诸药。合方有补肾温阳,和血消瘀,修复结肠溃疡以止泻的功用。
2.3.4 清热解毒,通腑存津 主证:突发腹泻,一日数次,脓血黏便,腹痛腹胀,里急后重,并发热,口渴欲饮,甚者心悸,舌红乏津,脉芤数。
方药:金花丸合小承气汤加味(黄连5 g,黄柏15 g,黄芩10 g,栀子10 g,厚朴10 g,枳实10 g,大黄10 g,地榆10 g,金银花10 g,人中黄10 g,天花粉10 g)。
按语:金花丸即黄连解毒汤,具有很强的清热燥湿解毒作用,合小承气汤通因通用。通腑逐邪,加金银花、人中黄增强透热解毒之功,地榆凉血活血止血,花粉清热生津止渴。合用以清解伏于结肠之毒邪,存正气而愈病。若兼心悸神昏者,加服至宝丹。热解症缓后,用芍药汤加减调治。
2.3.5 生肌敛疡,宁络止血 方药:外用苦参五倍灌肠方(苦参30 g,黄连15 g,地榆30 g,白及30 g,五倍子15 g)[33]。每日或二日一剂,以水浓煎,每次取100 mL,温度37~39 ℃,输液瓶装,用导尿管插入,缓慢滴注,控制在60~80 滴/分,1 次/d,7 日为1 疗程。配合内服药,可提高疗效。相关研究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机体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等炎症介质释放会因核因子κB(NF-κB)活性上升而增加,从而引起炎症反应。而苦参等中药灌肠可以下调抑制蛋白α(IκB-α)蛋白水平,降低NF-κB 的活性,抑制TNF-α、IL-6、IL-8 等炎症介质的分泌,减轻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局部炎症反应[34]。
3 临床治验病案
易某,女,56 岁。1998 年4 月26 日初诊。数年前因发热、腹泻、腹痛,中药治疗后热退症缓解,后常腹痛,每日大便3~5 次,量少,糊状,夹黏冻脓血,里急后重,便后腹痛减轻。曾多次查大便,排除痢疾病。结肠镜检查:“结肠黏膜水肿、糜烂、溃疡、出血”,诊断为“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经服多种中西药及成药,时好时发。终未能愈。刻诊脐周及右下腹时痛,痛则欲便,便后腹痛缓解,两胁时胀满,嗳气,大便糊状,夹黏液、脓血、里急后重,面黄晦,舌黯红,热蕴结肠,少白黄苔,脉弦细,腹软,左下腹轻度压痛。
方用膈下逐瘀汤减味,每日内服1 剂。餐前服。另用自拟苦参五倍灌肠方,1 次/d。
1998 年5 月3 日二诊:经1 周治疗,腹痛减轻,胁胀满已除,大便次数每日2~3 次,里急后重,黏液脓血大减。仍用原方去枳壳、红花、玄胡,加蒲黄、白及、薏苡仁,服药7 剂,灌肠5 日。
1998 年5 月10 日三诊:腹痛已消失,大便日一二次,软而成形,无黏液脓血便,肢软,纳谷不香,舌淡黯黯红、苔薄白,脉细。久病脾胃虚弱,乃以异功散加山楂、诃子,五剂善后。年后随访患者症状未复发。
按语:具悉患者病史,结合中医舌脉象等,认为其肝失疏泄,气机塞滞,久病入络,瘀结于肠,则瘀血与邪毒胶结难解,损伤结肠肌膜,形成溃疡而不愈。故治法应用理气活血、化瘀消滞、荡涤胶浊之邪为主,结合患者舌黯红、少白黄苔,脉弦细,脉滑数,辨病为瘕泄病,辨证为气滞血瘀证,肠道气滞,湿热内伏,紧扣湿热伏邪深伏肠络之病机,运用膈下逐瘀汤加减。方中香附、乌药、枳壳疏肝行气导滞,当归、川芎、红花、玄胡活血祛瘀,尤其五灵脂腥味入络,化瘀血,祛胶浊;合用之使肠道蕴结日久之瘀滞消除,使溃疡能祛瘀生新以愈。全方疏肝理气消瘀,促使邪气外出。二诊,考虑患者腹痛减轻,胁胀满已除,故于去枳壳、红花、玄胡,加蒲黄、白及、薏苡仁以滋止血健脾渗湿之功。三诊,腹痛已消失,大便日一二次,软而成形,无黏液脓血便,肢软,纳谷不香,考虑患者病程较长,久病入络,瘀阻络伤,故以异功散加山楂、诃子,益气健脾,行气化滞,补而不滞。本案临证巧妙运用“湿热伏邪”理论。对于湿热伏邪潜藏日久致气滞血瘀从而导致的慢性反复发作的溃疡性结肠炎,辩证选方,加减化裁,补行并施,以防病情进一步发展损伤阴阳气血,体现中医治未病的观念。
4 期待与展望
上述对于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辨证分型标准缺乏统一性,相关研究文献之间缺乏借鉴性;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方面虽取得很大进展,但在实验研究方面仍有欠缺,主要表现在不同证型对药物的选择、药物剂量以及治疗疗程等方面较为模糊,使得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缺乏规范与严谨。因此,今后研究应完善统一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模型及更加科学的药效评价标准将成为此病的研究目标,为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提供更好的研究平台,深入探讨中医药针对不同证型的具体治疗作用机制及靶点。另外,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治疗远期疗效的追踪较少,考虑到这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疾病,应加大对其远期疗效的随访力度,结合临床探索总结适合溃疡性结肠炎的规范化中医外治诊疗方案,以更好地防治溃疡性结肠炎,为临床上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提供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