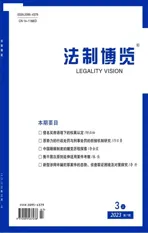《刑事诉讼法》中法官澄清义务实施困境与完善建议
2023-04-05廖黄鹏
廖黄鹏
广东尚尧律师事务所,广东 佛山 528000
所谓法官之澄清义务,其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初来自于德国,也有人将其翻译为法官的职权调查义务。[1]它意味着法官有义务为了获得真相而主动收集证据,查明事实,但其必须在职权范围内展开相关活动。[2]该义务虽然发源于罗马法,但是在现代文明国家中被普遍适用,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它有利于对以往的强职权主义模式进行调和与改良,是对英美法系中当事人主义模式积极学习之成果,能对当事人行使权利更好地提供保障,有利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实现。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规定了法官澄清义务并对其进行了制度设计,但是该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效果不佳,尚存在众多问题,本文对此将一一厘清。
一、刑事诉讼中法官澄清义务的基本内容
刑事诉讼中特别重视还原事实真相,故而法官澄清义务的核心同样为发现实质真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官要依据职权积极主动去查清真相,其中主要涉及四个组成部分。
(一)诉讼关照义务
法官澄清义务中的重要组成之一,是诉讼关照义务,法官需要关照的对象主要为辩方。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法官对其的关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对辩方正当权益尊重和维护;第二是对辩方正当权益积极照顾和协助实现。[3]诉讼关照义务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辩方对自己的正当权利无法实现,也就无法充分为自己辩护,其可能无法充分为自己的诉求举证,那么控辩双方的实质交锋、实质辩论也就无法实现,这不利于事实真相的查明。所以,法官在必要情况下,有义务对辩方提供关照,从而协助辩方更好地进行举证和辩护。
(二)释明权
所谓释明权,其主要针对公诉方。如果公诉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出现了过失,导致技术问题的出现,从而使得诉讼程序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此种情况下法官要对其进行释明,目的是提醒控方其所犯的疏忽,让控方尽快纠正,从而让诉讼程序回归正轨,能够继续进行下去。[4]法官对于公诉方的释明,并非对公诉方的偏袒,更本质的目的是保持诉讼之效率,让诉讼进程不因为一些控方的疏忽大意而受阻。
(三)庭内查证权
所谓庭内查证权,是指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要积极履行职权,去搜集案件相关证据,从而了解案件事实情况。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控辩双方均有所疏忽,没有对应当提供的证据进行提供的时候,法官有必要依据职权对相关证据进行补充,从而更好地呈现真相。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控辩双方的质证不够充分,让一些事实真相还没有更好显露出来的时候,法官也可以主动对相关人员例如证人、被告等进行发问。[5]如此之目的,都是让法官在案件事实真相上形成内心确信。特别是在比较重视庭审辩论的国家,辩论双方对于证据的提供,对于质证问题的选择和对方提问的回复,都会选择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展开,双方都站在自己角度展开相关辩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会在某些真相细节上导致空白地带出现,它不利于法官准确地了解案件相关事实之全貌。此种情况下,法官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发问来确认自己想了解的方面,进一步充分还原事实真相。这恰恰是对当事人辩论制度的一种弥补和修正。
(四)庭外查证权
和庭内查证权不同,前者只是通过对当事人发问等方式来让案件事实更为清晰,或者让相关证据的情况和作用更为明确。庭外调查权却可能是法官依据职权,在休庭期间,自己去对证据进行调查与核实。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现有证据不够充分,或者有了新的案件事实出现等情况。我国对于法官的庭外查证权限制较多,只允许特殊情况下法官自己依据职权主动搜集和核实证据。
二、《刑事诉讼法》规定下我国法官澄清义务履行中存在的困境
我国虽然采纳了法官澄清义务制度,将其规定到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但是该义务在实际履行上存在效果不佳的情况,它的困境主要体现如下:
(一)法官对庭审活动指挥失序
法官澄清义务的落实前提,是法官对于庭审过程能进行良好指挥,把握其节奏,从而在对诉讼活动的引导、管理、控制中合理依据职权调查事实真相。[6]然而制度初衷虽然美好,法官对于庭审的实际指挥控制能力却不能符合对应要求。
学界一般认为,在刑事诉讼庭审进程中,法官有义务对控辩双方积极有序参与庭审进行引导和督促,从而让法官能通过其积极有序参与查明事实真相。如果控辩双方在此过程中出现缠诉、拖延、偏离重点、钻牛角尖,导致诉讼无法有效推进,法官必须及时阻止无关询问和引导两者重新回归到案件的重点,特别是争议点上,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必要情况下,法官必须对诉讼规则进一步说明,或者要求法警行使法庭警察权等。此外,法官还要决定是否允许新的证据、证人在法庭上展示。对此,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进行了一些规定,但是在法庭庭审过程中,法官是否能控制好庭审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经验。许多法官因为观念原因,并不重视对庭审进程的控制、引导和把握,甚至放弃对其驾驭,而消极对待庭审。此种情况下,法官也不可能履行好澄清义务,因为澄清义务从某种程度而言,以法官积极参与、引导和控制庭审进程为前提。
(二)法官诉讼关照缺乏实质
如上所述,依据职权,法官有义务对控辩双方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提供关照支持,从而促使辩方能更好地展示证据、参与质证,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官对辩方的关照帮助并不会导致不公平的出现,因为其关照帮助的目的,仅为辩方对自己应有权益的行使,而没有增加辩方新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对于发问与案件无关的情况,审判长有义务制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如果控辩双方中一方提出,相关证据和案件无关或者存在重复的时候,法庭对此应当审查,异议成立,可以不予准许相关证据在庭审中的展示。
以上规定虽然涉及了法官的诉讼关照义务,但是又没有完全呈现后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针对的是法官对控辩双方的职权,并没有单独照顾到辩方。真正应当为辩方提供的照顾,例如证据的呈现、认定和相关效果等,特别涉及事实呈现的方面,现有立法都没有具体规定,这也表明现有立法对于法官诉讼关照义务方面规定的欠缺,对此也有必要尽快改变。
(三)法官庭外查证权启动条件和行使内容模糊
目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了法官的庭外查证权。《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一条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补充,规定庭外调查所得到的证据要经过庭审质证后,才能成为定案依据。但是,对于庭外查证所得的非关键证据,如果控辩双方无异议,可以直接适用。相比于以往而言,现有规定对于法官庭外查证权的规定已经进一步细化,但是其不足仍然还较为明显。
相关不足主要体现为:首先,庭外查证权的启动条件不明确,它的发动似乎全凭法官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需要具备的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将其表述为“法官对证据存有疑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一条则另外增加了“必要时”,但是两者都未对此进一步细化,例如,法官如何判定证据存疑?以及何时为庭外查证权启动的“必要时”?[7]此外,法官如何进行庭外查证,相关规定也较为欠缺。对此,有的法官会去案发地点进行走访和搜集证据,在法律未进行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是否适合如此深入去查访证据,其是否又会导致法官的“偏见”?都是值得疑虑的。
三、《刑事诉讼法》中法官澄清义务实施困境之完善建议
综上,我国虽然规定了刑事诉讼中法官具有澄清义务,但是法官对该义务的履行效果不佳,该义务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困境,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一)整合和明确法官的庭审指挥权
如上所述,法官履行澄清义务的前提,实际上是法官能对庭审进程合理引导、督促、把握和控制。对此,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定中未过多涉及。故而,有必要在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上予以完善。对此,应当明确规定,在不同环节,如举证环节、质证环节中,法官在何种情况下必须主动介入,进行引导;法官介入以后,相关环节如何进行下去,在此过程中,法官如何行使自己的澄清义务;法官介入和依职权发问下,当事人如何回复。
我们必须知道,对于法官而言,只有法官对于庭审有着良好的控制力,履行澄清义务才有更好的效果。[8]现实中,许多法官对于庭审消极应对,实际上在对案件进行一种“材料审”,不够重视当事人质证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展现。这是因为许多法官的观念还没有扭转过来,也不理解法官澄清义务和法官指挥引导庭审的意义。对此有必要尽快扭转,从而使得法官通过充分介入庭审,充分把握过程,从而最大程度接近案件事实真相,形成内心确信。
(二)拓展法官的关照义务
如上所述,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法官的关照义务较少涉及,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常常地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在法官的澄清义务中,关照义务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庭审效果,关系到当事人在庭审中是否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证据和情况。如果庭审中的当事人,特别是辩方没有充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质证不充分,法官所形成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可能会偏离真相,导致冤假错案出现。我国司法诉讼中存在庭审虚化的情况,而这正是法官怠于行使关照义务的表现。[9]
在关照义务的行使上,法官既要履行消极的关照义务,即保持客观中立,创造平等的庭审氛围,同时也要行使主动的关照义务,在辩方因为一些困难而无法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无法充分展现证据和表达的时候,法官应当介入引导辩方,甚至自己询问证人,从而对证据进行核实,对真相进行澄清。此外,《刑事诉讼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法官针对辩方履行关照义务的时候,必须使得调查结果对辩方有利或者至少维护双方地位平等,而不能在效果上将辩方推入更糟糕的境地。
(三)完善和细化法官的庭外查证权
法官庭外查证权的启动方式和调查方式需要被进一步细化。就启动方式上,要对“证据存疑”和庭外查证启动的“必要性”细化说明。证据存疑,是指法庭上控辩双方展示的证据尚无法揭示案件真相,法官内心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确信结果。此种情况下,法官无法依据现有证据判定案件,而必须继续依据职权获得更多证据。证据存疑的同时,还要考察补全证据的可能方式,在控辩双方都无法继续提供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庭外查证权的启动就具有了必要性。在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法官庭外查证得以启动。
同时也要注意法官对于新证据的搜集,如上所述,一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新的搜集方法,例如去案发地点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从而搜集控辩双方未搜集到的证据。对此,如果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较好效果,也应当通过立法进行明文规定,从而更好地对其规范。但是,所有庭外搜集的证据,必须到庭审中被进一步质证,在庭审中,法官应当说明其采取查证的方式之必要性,以及搜集到的证据的过程,证据的证明力等,然后控辩双方要对此具体展开质证。相关规定是为了防止法官不合理地利用庭外查证权和虚置庭审过程。
四、结语
法官澄清义务是刑事诉讼庭审过程能高质量推进和取得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必要组成,它是大陆法系积极向英美法系学习的结果。我国虽然规定了法官澄清义务,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之内容,从而提升法官澄清义务的履行效果。这对于改变我国庭审虚化、庭审失衡等长期存在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