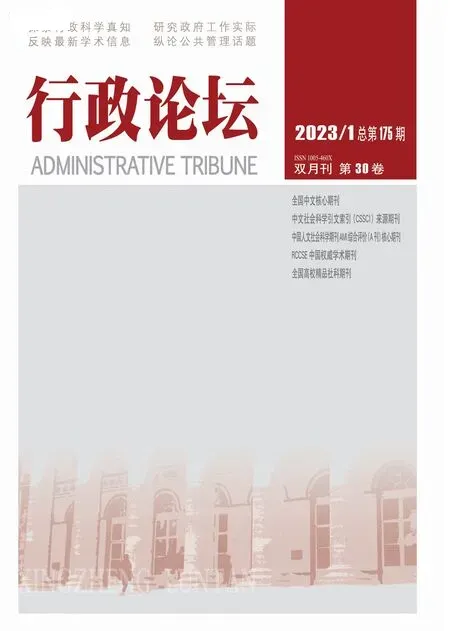协商民主、公共善与辩证行动主义
2023-04-05张宪丽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620
张宪丽(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协商民主日益成为中国当前推动和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本文所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什么?笔者尝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力图对协商民主的本质作较为深入的讨论。首先,从美好生活的角度讨论协商民主的外在目标;其次,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将协商民主的本质定义为公共善,并对其内涵进行讨论;再次,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特性角色概念出发,试图构建一种协商民主过程中的辩证行动主义;最后,在情感和理性二元要素的基础上分析协商民主过程中公共善的扩展原则,并重点从相互承认和移情的过程维度讨论公共善的扩展问题。
一、个体美好生活:协商民主的外在目标
协商民主主要是指协商代表围绕相关议题,通过民主辩论和对等交流等形式,最终达成多数人都相对满意的重叠共识的过程。正如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所指出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其更是一种通过提供有助于参与、交往及表达的条件,从而推动平等公民进行自由讨论的社会与制度框架[1]。协商民主尽管是一个现代词汇,但其内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直接民主实践之中。在古希腊,直接民主就与个体的美好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譬如,亚里士多德就讨论了公共领域(城邦)与个人美好生活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城邦之中,每个个体都应该成为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的政治动物,而城邦的目的则在于促进个人的善德和美好生活[2]。在近代,卢梭较为完整地讨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卢梭看来,公共幸福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3]。
在当代,一些学者也讨论了协商民主与美好生活的关系。譬如,亚瑟·卢丕亚(Arthur Lupia)等学者就论述了协商民主对促进个人美好生活的意义,认为通过聆听大家的陈述,参与者可能更加欣赏多样化的生活世界。同时,协商民主基于共同的目的,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更强大、更广泛的道德、伦理和技术基础,从而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4]。与此相类似,俞可平教授指出:“民生和民主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两个基本保障。”[5]在这里,民生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而民主则是达致美好生活的方式。
整体而言,协商民主的外在目标是要实现每个公民个体的美好生活,然而,这里涉及对美好生活的定义。美好生活在不同时期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物质资源较为稀缺的时代,我们往往可以从物质资源丰富的角度来定义美好生活,而较少关注精神生活的内容,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则需要兼顾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随着丰裕社会的来临,人们越来越关注精神生活的填充。譬如,约翰·加耳布雷思(John Galbraith)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就提出,一个社会除了考虑它的基本目标以外,还有更崇高的任务。那就是它对于幸福和和谐的追求以及如何成功地排除痛苦、紧张、悲哀等[6]。质言之,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很多思想家和学者都论述过精神世界对人的重要意义。譬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悲痛地指出:“上帝死掉了;上帝死于他对世人的同情。”[7]尼采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当时欧洲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的呐喊。泰勒就精神生活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泰勒看来,人们不仅要关注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的物质生活创造,更要关注心灵意义上的精神生活。泰勒更是将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的退场称之为“世界彻底丧失了其精神的外观”[8]29。泰勒将精神世界的丧失称为一种病理学的表现,“能动者本身产生了精神性病理特征”[9]。换言之,精神世界的空虚在现代社会是最为恐怖的事情。精神的空虚意味着自我的丧失,这是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精神病理学现象。在这里,泰勒其实更多的是将“精神”和“道德”联系起来。在泰勒看来,我们如果要克服这种疾病就需要清晰的表达,因为清晰的表达能够让我们重新将我们的强烈评价与道德根源联系起来,这些道德根源使它们有意义并赋予它们力量[10]。
总而言之,协商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围绕公共生活的精神性活动。尽管协商民主会涉及物质利益的分配,但协商民主在其运作过程中更加关注每个个体的精神状态。换言之,精神生活日益成为协商民主所关注的重要面向。精神生活对于协商民主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有利于保证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治理,促进公民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二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则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民主质量,促进国家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美好生活的达成。
二、协商民主的本质:实现一种公共善
美好生活不仅表现为自我对生活的满足感,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公共善的追求。关于公共善的讨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自我之善与公共善的关系方面。在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权利优先于善(个人权利高于公共利益)。换言之,自我之善优先于公共善,而公共善要以正当和正义为前提。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要构筑道德上的善概念,必须借助于正当和正义的原则。”[11]390而在社群主义的学者看来,公共善优先于自我之善(即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12]。譬如,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认为,个人的权利必须以公共善为前提,公共善优先于个人权利。对此,桑德尔提出,国家应该在诸多善的观念之中保持中立[13]224。对于公共善,我们需要发展一种辩证性的认识,在这里所提到的公共善的辩证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平衡性。其具体内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公共善需要在自我之善和社群之善之间达致平衡。自我之善表现出主体性,而社群之善则更多表现出主体间性。公共善首先要通过每个主体的言语和行动而得以展现,这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此同时,公共善还表现为主体在追求自我之善的基础上对社群之善的关照。关于社群之善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用主体间的“友爱”来表达这种社群之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只有相互都抱有善意才是友爱。”[14]桑德尔对社群之善的讨论则比较直接,在桑德尔看来,我们应该关注共同体内部的善,因为共同体主义的价值和彼此的善可以减少人们的互不理解和冲突[13]208。伯纳德·雅克(Bernard Yack)在讨论协商民主中的个体利益与社群利益的关系时也写道:“我们在政治共同体中共同协商并通过倾听的方式来说服彼此,未来的某些措施最好服务于公民彼此共享的目标,即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优势。”[15]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协商民主中关于善的讨论更多地体现在社群层面,即关注社群之善,而过于强调社群之善则可能会压制自我之善,即个体的自主性则可能会在社群中消失。泰勒的讨论力图从社群之善中进一步发现自我之善。泰勒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道德的内容并以一种道德的方式来为共同体做事。在对社群之善讨论的基础上,泰勒希望从道德出发来讨论自我之善。泰勒将善作为道德的根源。这里的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有价值的、高尚的、值得赞赏的种种类型和范畴”[8]134。泰勒极为强调自我之善的独特性和本真性,而其主要通过自我对道德的认同来表现。因为道德是一种内在的声音,它能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正确的、哪些事情是错误的。因此,善在自我对道德的认同中则尤为重要。因为道德不仅仅关乎伦理,而且还涉及善。个人对善的认同主要表现为自我要忠实于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则被称为一种基于道德意识之上的“本真性”理想。
换言之,这里的自我之善与自由主义学者从自我利益出发来界定的自我之善是不同的。自我之善产生于共同体之中。对于协商民主来说,自我对善的认同不是凭空产生和自我创造的,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和协商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如果过于强调自我利益,则很难达成一种社群的整体性。公共善需要兼顾自我之善和社群之善。麦金太尔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一个人的善与那些在人类共同体中和我密切相关的他人的善是统一的。我追求我的善既非我所专有也非你所专有——善不是私有财产。”[16]290简言之,公共善首先要以个人的善为前提,即首先是从自我出发的善,但同时公共善又会表现出一定的社群性,需要在个体之间达成一种社群的整体利益,并且,每个主体则需要与其他主体在公共善方面达到一种基于重叠共识的主体间性。
第二,公共善还要在多元主义利益和基本善之间寻求平衡。社会会被分割为不同的群体,而群体往往会有相对一致的诉求和认知。这样的群体性认知会以某种社会文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善的内容具有某种相对性,即很难对善持有一种绝对普遍的定义。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所提到的协商民主的多元主义则体现了这一点:努力达成元共识(metaconsensus),即相互承认其他参与者持有的不同价值、不同偏好、不同判断和话语的合法性[17]。对于协商民主来说,参与协商民主的主体来自不同的社群,其所在的情境具有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则带来了协商过程中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从这一点上来讲,每个社群或个体在对善的认识方面也呈现出多元主义的特性。在主张同质性的人看来,多元化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冲突。而在主张差异性的人看来,基于某种共同性,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冲突和矛盾。正如艾丽斯·M.杨(Iris Young)所指出的,群体之间并不是吸纳或是排斥的关系,而表现为一种不会导向同质化的交叠和混杂[18]。然而,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仅仅止步于多元主义,那么就有可能会掉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尊重多元主义文化和利益的基础上仍然要努力实现一种跨越文化和族群的基本认识。这种基本认识可以称之为协商民主中的基本善,其主要表现为在多元主义利益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内部的凝聚力和跨越社群的公共性。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学者对基本善都有类似的讨论。譬如,在罗尔斯看来,建立在个人自我价值意义之上的自尊与自信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善[11]382。而泰勒对道德最迫切的要求的讨论也包含了类似基本善的内容,譬如,尊重他人的生命、完整和幸福等[8]11。协商民主中的基本善更多地表现为不依赖于言说者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标准化的存在。
三、协商民主过程中基于特性角色的辩证行动主义
协商民主是一种面向公共善的认知和行动过程。一方面,协商民主是一种认知过程,即我们需要对公共善的定义及其辩证内涵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更加体现出行动主义的特征。协商民主中的公共善更多地表现在行动者的具体活动之中。换言之,协商民主就是一种表现为公共善的行动过程。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集体行动的困难,因为多数大众可能会受限于自身的时间分配或能力等因素,很难充分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同时,多数大众又无法完全由协商代表来表达其利益,而协商代表也无法完全做到将多数大众的利益和诉求反映到协商议题之中,这就使得大众利益的被代表与无法代表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里提出的辩证行动主义就尝试弥补这种紧张关系。
辩证行动主义更加强调一种多数大众与关键少数(协商代表)之间的辩证关系。笔者在这里更为突出关键少数的特殊作用。在麦金太尔那里,特性角色便发挥了关键少数的功能。在这里,笔者借鉴了麦金太尔所论述的特性角色概念,试图从特性角色的身上发现协商代表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所应该发挥的功能。具体来说,辩证行动主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特性角色在辩证行动主义中发挥重要的榜样导向功能。社会学中对角色的讨论比较充分。譬如,社会学家乔治·H·米德(George H·Mead)在讨论角色分类时就提到了以共同体为背景的角色定位。在米德看来,角色代表着对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所被期望的行为,并代表着共同体的价值观[19]。麦金太尔则借用了戏剧隐喻的说法,将这种角色称为特性角色。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一种特性角色被文化的一般成员或其重要部分视为目标。他为他们提供一种文化理想或道德理想……特性角色从道德上使一种社会存在的模式合法化。”[16]37从这一点上来说,特性角色具有一定的榜样导向功能,即通过榜样的象征意义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康德也指出,榜样能给予我们达到类似的良好效果的希望[20]。协商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特性角色,即关键少数的作用。关键少数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榜样功能。正如杰弗里·库尔巴瓦(JeffreyKurebwa)所论述的:协商代表传递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一个拥有这些利益的群体的更广泛的象征意义[21]。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榜样功能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和扩展应该是非强制性的。如果我们对关键少数的榜样内涵进行强制性推动,这实际上与协商民主的自主性内核会发生冲突,然而,如果不将榜样的力量进行扩展,又无法推动社会大众的参与性。因此,我们需要在榜样的扩展过程中思考如何激发大众自主性这一问题,这一点将在文章第四和第五部分专门加以论述。
第二,特性角色在审慎性沟通的基础上开展辩证行动。审慎性沟通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正如尼科洛·库拉托(Nicole Curato)和德雷泽克等学者所指出的:“沟通越慎重,民主就越有效。”[22]这里的审慎性沟通主要表现为两点内容:一是审慎性沟通主要表现为协商代表的专业性。在麦金太尔看来,特性角色的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知识,把理性实施限定在某一合理范围之内。譬如,企业的管理者应该限定在他所认定的事实领域、手段领域和可度量出效率的领域[16]8。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认为,协商代表要对自己所审议的事情有充分的了解,这样其他公民才能被说服[23]。二是审慎性沟通还表现为对协商议题的理性认识。譬如,在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看来,审慎是一种政治美德。当我们试图使用普遍原则或抽象理论去指导政治现实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先深入了解事务的诸多具体情况,同时洞察其底蕴[24]。西蒙·钱伯斯(Simon Chambers)在谈到理想的民主公民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在钱伯斯看来,理想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通情达理、深思熟虑、消息灵通和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25]。特性角色之所以形成榜样的力量,就是因为其在专业性和理性上都表现出与普通社会大众的明显区别。这种专业性和理性可以引导社会大众较为有秩序地参与政治活动。
第三,特性角色的榜样引导要以情境性道德为内容展开。这里要避免走向一种道德普遍主义。尽管在公共生活之中要追求一种公共善,但也要避免一种以公共善之名对个体诉求的压制。因此,我们需要把公共道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便是情境性道德的意义。对于协商代表来说,情境性更多地体现在协商民主过程之中角色存在的时间性方面。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存在的偶然性的论述便体现了这种情境性的特征。在萨特看来,自我在社会当中,不论占据什么样的社会空间,都是偶然为之。正如萨特所指出:“它存在是因为它是纯粹的偶然性。”[26]萨特的这段话某种程度上就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情境性和时间性问题。协商代表是被社群推选出来并代表社群参与协商议题的特性角色。因此,协商代表具有与协商过程相一致的情境性。需要指出的是,协商代表的角色虽然具有情境性,但并不意味着协商代表就可以为所欲为。换言之,具有情境性的角色也要讲求美德。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就提到了道德对于代表的重要性。在密尔看来,代表的职责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还与道德有关[27]。当然,这里的情境性道德不仅表现为前面所提到的善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协商代表要处理好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譬如,腐败的产生就是因为公务人员没有厘清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从而影响了民主的质量和发展。
总之,人们往往会在公共活动中从自我利益出发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情境性道德则更为强调个体在美德前提下的诉求。将情境性道德这一观念引入协商民主过程中,将会有助于整个社会共通感的达成。情境性道德更强调“将他人作为目的”。如果每个个体都力图实现“将他人作为目的”,那么整个社会便更加容易实现共通感,并会帮助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个体更容易去理解他人。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的关键就是要对公共善进行适当的扩展。不仅作为特性角色的协商代表要对公共善进行正确的认识,而且我们每个普通公民都应该维护这种公共善。
四、情感和理性:协商民主过程中公共善的扩展原则
如前所述,协商民主的关键就是要对公共善进行扩展,即从特性角色扩展到每个普通公民。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借助情感的力量。情感有助于激发公民个体的参与主动性。对社群的情感有助于每个公民积极地参与社群的公共事务。公民个体可以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练习将“他人作为目的”。在追求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修辞对情感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活动中加入更多的修辞要素,这样可以激发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因此,这里就需要在政治活动中加入带有情感的语言修辞,这样可以激发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譬如,一些爱国主义活动或是体育赛事都可以激发公民对共同体的情感,这都有助于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很多学者都强调了情感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指出的:“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28]譬如,我们对这一件事情是支持的,对另外一件事情是反对的,这些判断经常都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讨论科层制时非常强调个体要保持价值中立,不要为情感所主导,但麦金太尔却将韦伯称为“情感主义者”。在麦金太尔看来,韦伯并没有否认人的价值立场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16]32-33。尽管研究者往往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归入强调理性的学者行列,但哈贝马斯在《包容他者》一书中讨论了情感的重要性:当我们在考察道德争论的时候,必须把情感反应纳入道德表达范畴之内。这些表明立场的情感潜在地表达出了判断[29]。正如马汀·格里芬(Martyn Griffin)所评价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尽管坚定地将自己置于康德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但两位理论家仍然注重情感的影响。”[30]从这些讨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情感对于个体的行动是尤为重要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正如泰勒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论证可以让某个人用中立的态度去对待世界[8]16。
修辞对于情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对修辞的重要性都进行了讨论。亚理斯多德在其《修辞学》一书中就认为,演说者能够利用修辞,从而对听众的心理产生说服的效力[31]。在瑞安·沃尔特(Ryan Walter)看来,语言修辞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政治竞争中重要的工具[32]。约翰·尼尔(John Neill)也认为,我们最终热爱的不是某样东西,而是其他人的修辞学,既涉及讲话者可信度的自我表现,也涉及对听话者情绪的表达[33]。换言之,那些试图说服我们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人,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把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描绘成对社区其他成员也有好处的事情[15]。需要指出的是,在协商民主过程中,语言修辞固然很重要,但我们同样需要注意修辞的适度性,因为过度的语言修辞可能会给人一种类似“脱口秀”表演的感觉。
当然,对公共善的追求不能完全诉诸情感和修辞,我们仍然需要引入理性的要素。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如果世界为情感所主导,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使用带有情感的语言修辞在公共活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从而让其他人能够支持和认同自己。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情感和修辞对协商判断和共识达成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情感的视角来作决策。麦金太尔肯定了情感在构建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对用情感来操纵他人。在麦金太尔看来,人的行为会受到情感主义的影响,语言也会受到情感的操纵。因为人都有自利性,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种他人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问题[16]29-30。只有在情感和理性的平衡之中,这种从特性角色到普通公民个体的公共善扩展才能以更加有序的方式持续展开。
整体而言,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情感的适度表达;另一方面,也要兼顾理性的价值判断。正如卢丕亚等人所指出的:“协商既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性。”[4]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祛除情感中的极端主义要素和内容,然而,仅仅从理性出发,人们往往会丧失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和理性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在情感和理性的平衡之中,这种从特性角色到普通公民个体的公共善扩展才能以更加有序的方式持续展开。如果每个个体在情感和理性的平衡之中以“将他人作为目的”为目标,那么整个社会便更加容易实现公共善,从而帮助不同社群的个体去理解彼此。
五、在相互承认和移情中实现公共善的扩展
公共善的扩展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承认与被承认的相互承认关系。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每个个体在彼此承认的过程中都可以得到一种被尊重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泰勒所强调的承认政治的内涵。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所强调的“为了承认而斗争”[34]49也会成为协商民主的一个基本动力。这种承认更多地表现为协商主体身份的被承认和权利的被尊重,这是公共善扩展的关键。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是协商代表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最重要的精神世界的满足。正如钱伯斯所指出的:“协商民主不仅表现为避免精英主义政治,同时也表现为平等地尊重每个公民的自治精神。”[35]关于承认对主体的意义,黑格尔、阿克塞尔·霍耐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泰勒等学者都进行过非常多的讨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36]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之所以被确认为存在,是因为它被另外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承认。霍耐特在黑格尔对承认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承认的三种理想的形式,即爱、法律和团结。在霍耐特看来,这三种形式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承认”状态,因为这三种形式相继提供了基本的自信、自尊和自重[34]175。德里达在讨论友爱时也讨论了承认的重要性:“我们无论如何都有追求彼此承认但不求彼此认识的朋友。”[37]
公共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他者的承认和尊重。正如泰勒所指出:“我们应把我们最深层的道德本能,我们有关人类生命应得到尊重的根深蒂固的知觉,当作我们走向世界的模式。”[8]16在泰勒看来,承认和尊重应该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为“日常生活是善良生活的真正核心”[8]23。对公共善的理解,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泰勒认为,种族主义者以某种“背景”来界定种族的优劣。这种界定充满偏见,是对其他种族的一种“扭曲的承认”和缺乏尊重的表现[38]291。而这种扭曲的承认既缺少该有的尊重,也会对他人造成巨大的创伤,最终会让受害者背负一种自我的仇恨[38]291。这种扭曲的承认明显会影响到公共善的扩展。在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特权主义和“一言堂”等问题。譬如,强势一方的观点可能会被作为主流意见而让他人被迫承认,而弱势的一方则只能被动接受,这就会导致协商民主过程中弱势一方不被尊重的问题产生,而不被尊重将可能带来新的冲突。质言之,公共善不能以强制性的方式加以扩展。
整体而言,尊重对于公共善的扩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研究协商民主的很多学者都讨论了这一问题。譬如,亨利·理查德森(Henry Richardson)认为,在协商民主的模式里,人民主权的一大特征表现则在于“明确的人民意志之中存在尊重个体公民表达的承诺”[39]。在这里,人民意志就体现为一种公共善的达成。马克·彭宁顿(Mark Pennington)则从主体平等的视角讨论了尊重的内容,“协商民主就是它使包括穷人和各种被边缘化的群体能够通过平等的协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观点,并受到尊重”[40]。在公共善的扩展构成中,边缘群体的意见需要更多地被倾听。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则从协商程序结束之后的履约方面谈到了尊重的内涵,自由与平等公民之间的协商决策的正当性一旦形成,将会与尊重社会内部与跨社会间的许多道德与文化差异相一致[41]。古特曼的这段文字表明了协商程序中的履约和尊重对于公共善扩展的意义。基莫·格隆伦(Kimmo Grönlund)则重点讨论了尊重对于协商民主的作用:协商过程中的包容、平等、互惠、反思、真诚和尊重等规则可以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42]。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尊重和承认有助于公共善在社会层面被广泛接受,这实际上就是学者们所强调的承认政治的内涵,特别是一些少数群体会为了自己或自身群体的一些特殊利益或文化价值,与多数群体展开深入和充分的协商。在这种协商过程中,少数群体的利益和文化认同得以彰显,那么每个个体便在这样的意义上得到了尊重和被承认,这便是自我之善和社群之善的统一。
公共善的扩展还要达到一种主体间的移情状态。移情对协商民主的意义则在于其可以减少协商过程中的冲突,促进协商共识的达成。公共善需要在每个主体的情境中得以展现,同时每个主体同样需要与其他主体之间达成一种移情的共通感;否则的话,每个个体都会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很难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公共善,那么这样的善便可能会堕落为恶。如果主体缺乏移情,那么则很难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公共善。换言之,只有从移情和共通感的角度出发,更多从他者的角度来思考共同体的利益才能更加接近这种公共善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讲故事和小说对达到移情的状态具有重要的作用。譬如,在艾丽斯·M.杨看来,讲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特定社会情境的人的特殊经历,从而能够让我们真正与他人达到移情的状态[43]。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形式),让读者通过移情的方式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产生情感的共鸣[44]。从整体来看,移情的观点提示我们,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所有的代表都要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尤其是相对强势的一方也要学会从善和移情的角度出发来关照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使协商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能够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进而走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善。
六、结语
协商民主的本质是追求一种公共善,而公共善在根本上体现为自我之善和社群之善、多元主义利益和基本善之间的平衡。如果要实现公共善这一目标,就需要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实践一种辩证行动主义。辩证行动主义首先重视关键少数即特性角色的榜样性力量,通过榜样形成社会道德的标识效应,同时辩证行动主义还要求通过社会大众的正向学习来对公共善进行扩展。对公共善的扩展过程同样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首先要诉诸基于情感的修辞,因为情感和修辞可以激发公众个体对榜样的学习。在某种故事性的情境中,公民的道德意识可以较为容易地被激发。同时,这一过程仍然需要强调理性。基于情感的政治很可能会引向一种过度参与,而理性则有助于我们将情感的表达限定在公民政治的合理框架之内。通过审慎性沟通和情境性道德,关键少数与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辩证法,这有助于公共善在社会层面的达成。在对公共善进行扩展的过程中,基于主体的社会移情极为重要。换言之,社会大众对特性角色的社会学习主动需要被激发出来。在广泛性的社会学习中,正向的公民能量源源不断地产生,这才能成为辩证行动主义在协商民主中应用的实践性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