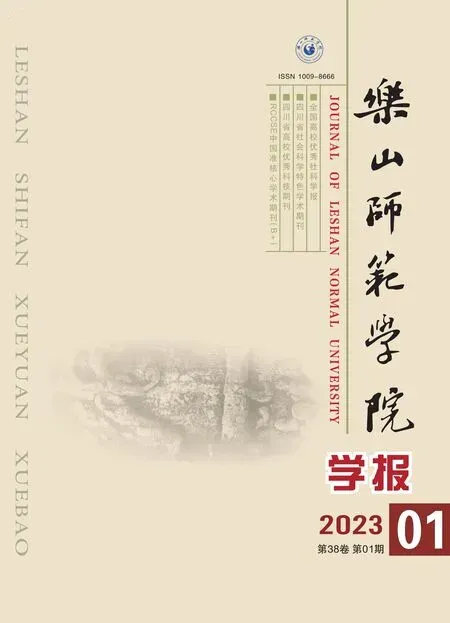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2023-04-05陈夏临
陈夏临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校,福建 福州 35000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哈罗德· 阿克顿(Harold Acton)和美国诗刊编辑哈丽叶·蒙罗(Harriet Monroe)等人,借助文学研究译著《中国现代诗选》(ModernChinesePoetry)与著名诗歌刊物芝加哥《诗刊》(Poetry)等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向西方读者译介林庚(Lin Keng)的中国新诗及其成就,向英语世界打开了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美的新诗鉴赏之路。
近年来,对林庚新诗的研究,不仅关注他在新格律诗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历程,还从新诗批评视角,对林庚格律诗创作历程进行反观。而林庚作为文史研究者的身份,也使更多学人关注其所提出的“盛唐气象”说与其新诗的晚唐风韵间联系,从而发掘林庚新诗寓古于今、复兴传统的古典化创作意识。林庚新诗创作思路,结合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继承与思辩,其新诗格律与语言兼具较强传统性与跳跃性。而阿克顿等西方学者对林庚诗的甄选与翻译,更从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视角,寻觅投射于新诗的中国古韵,并向世界提交了来自中国新诗的个案研究。
一、林庚新诗的创作背景与域外传播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林庚曾受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施蛰存、茅盾、周作人、废名、沈启无、徐耀辰等著名文人提携指点。在1936年冬这“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经徐志摩引荐,林庚成为《世界日报·明珠》文学副刊主编,在1936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三个月间,林庚以《明珠》为新文学启蒙运动阵地,发表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叶公超、朱自清、朱光潜、李长之、沈启无等的大量诗歌与散文作品,创作编辑水平得到初步历练[1]。
在阿克顿编译《中国现代诗选》的1936年,林庚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先是“留校担任朱自清助教,并为闻一多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又应郑振铎之邀,任《文学季刊》编委,并负责新诗一栏的组稿工作”[2]。林庚新诗创作始于1931年,1933年发表第一本诗集《夜》(1933),收录1931年至1933年创作的自由体新诗43首;1934年他辞去清华大学教职专事新诗创作,同年发表第二本诗集《春野与窗》(1934),收录自由体新诗57首;1936年又出版新格律诗58首,结集为第三本诗集《北平情歌》(1936)。林庚新诗被翻译到英语世界,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阿克顿,是向英语世界结集翻译中国新诗之第一人,在首部英译新诗总集,即阿克顿与学生陈世骧(Ch’en Shih-hsiang)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中,林庚新诗被选录19首,分别是WinterMorning(《冬晨》),Daybreak(《破晓》),RedSun(《红日》),TheCountryinSpring(《春野》),MorningMist(《晨光》),Rainywindyevening(《风雨之夕》),Forget(《忘了》),TheRedShadow(《红影》),FifthMonth(《五月》),SpringandAutumn(《春秋》),MemoriesofChildhood(《忆儿时》),Home,SummerRain(《长夏雨中小品》),Night(《夜》),HopelessSorrow(《沉寞》),Autumn(《秋日》),TheHeartinSpring(《春天的心》),ShanghaiRainyNight(《沪之雨夜》),NewYear'sEve(《除夕》)。而阿克顿之所以尤其青睐林庚新诗,恰是被其诗中所述的古典中国意象所震撼。无独有偶,在阿克顿英译林庚诗作同一时期,林庚新诗还被美国著名诗歌刊物、编辑美国芝加哥《诗刊》创立者哈丽叶·蒙罗频繁选录翻译。蒙罗晚年致力于传播中国新诗,《诗刊》遂成最早录用中国新诗的西方刊物。林庚新诗以其诗歌的独特中国古韵与隽永唯美的语言风格,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浮华美国商业社会对中国新文学的诗意想象。
林庚新诗创作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白话诗歌几乎全盘摈弃中国古典诗歌传承的激越洪流中,林庚却另辟蹊径,“他的诗学思想里面有着古与今、新与旧的巨大错位,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逻辑与历史的内在分裂。”[3]在对西方诗歌借鉴、仿效甚至照抄成一时风气的逆境中,林庚毅然站在传统文化审美与古典诗歌继承的客观立场,此举正源于林庚深植于心的“仿古”意识,旨在于新诗中再现“盛唐气象”。“林庚通过自我选择,实现精神上的‘二重’解放,走上新诗自由创造的起点,并找到了新诗现代性追求与皈依传统的契合之路。”但林庚新感觉派新格律诗所突显的“晚唐诗的自然与幽深”,也成为其诗歌被诟病为晦涩与“仿古”的根源[4]。林庚认为,新诗的时代特征,并不在于古今或新旧,“应该是那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盛唐之世,与北宋时期,同为太平盛世,在生活上可谓相差无几,然而唐人解放的情操,崇高的呼唤,与人生旅程的憧憬,在宋代都不可复见;这正是唐宋文艺的分野。我们如果希望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来临,便必须从那错误的思想形式与错误的人生情绪中醒觉。”[5]林庚此论既是对唐宋文学所投射时代精神的剖析,亦是他在新诗创作探索之初,对“诗言志”理想人格的要求。
二、纯粹、古典、史感:阿克顿的林庚新诗品鉴
(一)技法纯粹性
值《中国现代诗选》编译时期的林庚,已经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Night,1933)、《春野与窗》(SpringMeadowandtheWindow,1935)等,在阿克顿的新诗印象中,林庚这些寥寥数行的小诗,却意象极饱满、诗语颇纯粹,首首皆精华。作为现代主义诗人,阿克顿的诗歌创作理论旨在立足传统诗歌创作技法,依古韵创新诗语。阿克顿个人在诗歌创作中,就尝试拼接与借鉴现代主义诗语,试图融合古韵与新语态的唯美诗意,继而以文学传统可依的创新,反映诗歌所依托的社会新环境、折射新语境下的读者审美偏好。因此,为阿克顿所质疑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诗,在求新时摒弃古典诗歌技法,反而无法突破传统诗歌的成就高峰。
为了支持继承文化传统的创作论,阿克顿将时任北京国民学院教师林庚的《论诗歌》(OnPoetry)一文,在《中国现代诗选》作家小传中重点摘录,作为阿克顿偏好新诗古韵的论据。在《论诗歌》中,林庚也提及新诗创作尽弃传统时,诗人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林庚提到,无论古诗还是新诗,皆不能掺杂太多个人观点,需忠实迎合人对自然的体悟。如苏轼《卜算子》的生成过程,类似于以人的视角还原自然。先有诗感,接下来旋即而生出对所咏之物的体认,如王维《山居秋暝》的阐发过程。在诗歌创作技法层面,林庚所持观点是,联通天人与体悟大道并非同类技法,前者是欣赏,后者是还原。而诗人在创作时须二选一,不可因刻意求全而损伤诗意美的表达,因中国诗歌在视角切换、感受还原上,都不允许有太大的跳跃,否则就会使诗歌气脉断裂[6]166。但若从诗歌形式与语言发展来看,林庚认为,无论新诗与古诗,诗歌宗旨并非一味流于形式,而是追求内涵深邃。无论是对自然规律的体悟、还是对自然状态的感受等,林庚认为诗歌素材应始终以自然与天性为宜,过于人文、物质的内容,易造成意象堆砌与过时。
而除了社会环境与诗语革新,林庚认为,诗人是否关注读者,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技巧。“新诗包含的新感觉和新的表达方式”,对从古典诗歌阅读习惯中走出的读者而言“显得尤为陌生,因此也生出拒绝”[6]169。新诗在素材与诗语拼接“创新”上导致的阅读障碍,原出发点是为新诗发展提供形式转换的缓冲时间。“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跳出传统的内容、形式、语言与章法的关系后”,新诗在全新的内容、形式、语言与章法上,“必然会达到一种更广阔、更新颖的关系”[6]169。因此,在借鉴古典诗歌既有成就方面,林庚指出,不能因古典诗歌中可借鉴的养分多,就贪图近便,遵循古诗格律、语法、词汇、典故等的渊博与精深,新诗的出路源于创新。“摹仿是永远也不会让人感到新鲜的”[7]31,向古诗借鉴技法,实是从传统古韵中汲取能量。
(二)诗语古典性
林庚古典诗词与白话新诗兼擅,在新诗创作前,他曾有多年的古诗词创作经验,“1931年在《文学月刊》先后发表《菩萨蛮》等词16首。并开始从旧体诗词转向自由体新诗的创作”[7]369,奠定其新诗的古韵基调。林庚的个人新诗集在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选译林庚作品前就已问世,处女作《夜》(1933)由林庚自费出版[8],该诗集以其古典与唯美风格,深受阿克顿击赏。
林庚“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历史考察来展望新诗发展的前途”,此外,在新诗语言探索上,“通过对汉语语言特点的分析来确定新诗形式的建立所应遵循的原则”[9]。给阿克顿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林庚新诗尽管忠实使用白话文创作,遵从新诗语言应用规范,但古典韵味非常浓烈。阿克顿认为,林庚新诗在意象与意境营建上,都注重对灵感与直觉的“诗意化”还原。林庚则将阿克顿所褒扬的“诗意化”,归结为“唐诗的好处……唐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7]1,即唐诗的超越性表现于其可启发一切时代的人文性。谈及古典诗歌创作的成就,从事历史研究的林庚曾提出“盛唐气象”,此理论后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林庚认为,古体诗歌在唐代已发展到意象巅峰,后世对古体诗歌技巧又进行了精细如发的系统性打磨,故现代人写古体诗,“就算写得再好,也不过怎样像古典诗词而已,不可能有你自己。于是就改写新的现代诗。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很尖锐,也不可能沉醉于古典之中。”[10]21
林庚擅用古诗韵律、节奏、意象和典故写作新诗,他以敏锐的诗感,精准把握古诗词的语言特点。林庚敏锐借鉴古典诗歌在节奏上的跳跃感、省略带来的想象空间、瞬息万变的感受性、自由的模块组合方式、陌生化生活中的感知系统等,让新诗语由飞跃而精炼,因真切而雅致,因朴素而动人。林庚认为,“要寻求一个完美的诗歌形式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为了新诗发展的需要,对此进行不懈的探索、不断的尝试”,而完美的诗歌形式则有助于诗情与诗语的展现[11]2。
阿克顿比较《中国现代诗选》所录新诗中的“古典派”与“现代派”,如林庚和戴望舒的新诗,风格就迥异于闻一多、郭沫若与徐志摩。正如1919年,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对新文学的性质作出的定义,新文学并非“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12]142。新诗人对古诗的继承,使得新诗既革新诗语又传承文化,借力于文学传统在新形态中立住脚跟。
而为阿克顿所质疑甚至反对的是,《新青年》诗人群体等,则更多仰赖西方文化传统,“太匆促地在欧洲和上海‘孵卵’”[13]。而作为“现代派”诗人的林庚,恰认识到文化血脉传承的重要性,而“五四”之后为梁启超等学者所遗憾的“中国文学传统没有史诗”,在林庚恰解释为,中国史诗形成时期,“印度与希腊用的都是拼音字母”,可即时记录口头流传的史传与故事,而中国史诗产生时所使用的甲骨文不便于记录。林庚认为,中国直至文字出现,封建时代的文言记录与白话口语已明显区别开来,官方文字记录的多半是严肃历史[14],从而错失了史诗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窗口期,因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求人类历史发展初期的历史遗迹。
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导言中,以批评对比方式,毫不客气地“戳穿”诸多早期知名新诗人对西方诗的忠实“借鉴”,在形式与语言上不乏照搬,甚至只隔一重译语“造诗”,思维上的懒惰无益新诗成长。阿克顿认为,新诗创作的文化土壤不需通过完全否定古典诗歌来一蹴而就,正如林庚所说,语言作为思维传导工具,创作者要擅于利用古典诗歌语言上的“便宜”。
选取2017年2月~2018年3月在本院耳鼻喉科进行鼻内镜下射频治疗的患者83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1例,女62例,年龄15~68周岁,平均年龄48周岁,高血压患者27例,糖尿患者9例。所有患者的鼻出血部位有所不同。通过检查我们可知,鼻中隔后端出血患者有24例,中甲后端出血患者有23例,中鼻道出血患者有24例,Woodruff静脉丛出患者有13例,下鼻甲前端出血患者有36例,以及嗅裂区出血25例。
林庚的“新感觉诗”在当时中国新诗坛,不属于向西方诗歌忠实借鉴的“商籁体”,或者形式主义的“豆腐干式”。旧瓶装新酒固然缺乏创新精神,因“新酒是用新的生活语言写成的诗,新瓶因此也就必须是符合于这新酒的生活语言”[15]70。俞平伯称林庚诗是天然个人化的文化产物,“所谓‘前期白话诗’固不在话下,即在同辈的伙伴看来也是个异军突起。他不赞成词曲谣歌的老调,他不赞成削足适履去学西洋诗,于是他在诗的意境上,音律上,有过种种的尝试,成就一种清新的风裁。”[10]33林庚信旧体诗时代已逝,“今日的诗坛便只有自由诗在活跃着”[15]68。
(三)诗风历史性
20世纪30年代,废名、林庚、何其芳、卞之琳、金克木、朱英诞、南星等诗人“在重新考察与阐释古典诗传统时”,在古典诗歌中收获了“诗言感觉”,在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与诗语构成中,寻求新诗探索之难题,发现源于传统的“诗感”对新诗创作同具超越时代的启发作用[16]。林庚在30年代的诗歌,正是将唐诗意境与音韵美合一,并非简单摹仿,而是质与象的细腻重组。
阿克顿认为,林庚新诗是继中国古典诗歌后的新生代诗歌典范。但恰是阿克顿所似曾相识的古韵,令当时读者对林庚新诗产生用白话的“新瓶”装古诗词“旧酒”的泥古印象。如林庚《偶得》(《北平情歌》)中的“春愁”“江南岸”“孤云”“游子衣”等意象中的思乡之情,《古城》(《北平情歌》)中“西风”“秋云”“荒城”“断梦”意象中的萧瑟悲感。林庚新诗甚至在体裁上也借鉴古典,而同时期的新诗人亦觉新诗太过“自由”,1923年陆志韦就曾指出,“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陆志韦也进行了新诗格律实验,并将格律体新诗结集为《渡河》。而1926年闻一多所撰《诗的格律》一文,奠定了格律体新诗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7]。林庚在30年代前期开始格律诗探索,《北平情歌》代表其最高成就,经典作品被阿克顿选译[18]。
然而,被阿克顿归于与林庚同类型、传承古典诗歌精髓的新诗人戴望舒,却针对林庚无法完全突破古诗体裁的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檄文,批判林庚不过是拿着白话诗语来填古诗[19]。戴望舒犀利地调侃林庚,“没有带了什么东西给现代诗;反之,旧诗倒是给林庚先生许多帮助。从前人有旧瓶装新酒的话,‘四行诗’的情形倒是新瓶装旧酒了;而这些新瓶实际上也只是经过了一次洗刷的旧瓶而已。”[15]82但林庚的新格律诗,并非简单以白话文为语言素材重蹈古诗路径,更非戴望舒所说“想用白话去发表一点古意而已”[15]79,而是基于文化自信的诗语与格律实验。
林庚主编《明珠》副刊时,主要撰稿人、“京派文学鼻祖”冯文炳(废名)极推崇林庚新诗。冯文炳作为一位看不惯“闹新诗”的传统文人,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实践中,林庚诗作的重要性远胜同时代作品,读林庚诗作,“从此不但知道我们的新诗可以如此,又知道古人的诗可以如彼”,“我读了他的诗,总有一种‘沧海月明’之感,‘玉露凋伤’之感了。我爱这份美丽”,“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是很自然的,同时也是自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15]101-102在新诗语言风格与创作成就上,冯文炳所持观点与阿克顿不谋而合。阿克顿对林庚诗歌的偏爱与盛赞,折射了英语世界诗歌读者与创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审美倾向。林庚新诗被谤的“缺陷”,使其新诗更接近西方人对中国盛唐古韵的印象。在《中国现代诗选》导言中,阿克顿甚至警告新诗人,全盘抛却中国诗歌传统,“忠实”效法西方诗歌,将无法逾越古韵巅峰。
三、还原唯美古韵:阿克顿的林庚新诗翻译策略
(一)悲感与动态的古韵——《夜》
林庚新诗长于复现古典诗歌意境,而《夜》(Night)作为其新诗作品中最能传达悲凉古韵者[10]6,除文字古典美与意象古典化之外,还兼具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动感,凝成融悲感与动态于一体的复古新诗韵。古诗中常见的战争乱离主题,在《夜》一诗中,经由“飞驰和超越”意象的动态再现,构成了一次“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Imagination)之旅[20]。全诗以移动的视角,捕捉几近凝滞的离人之悲与慷慨悲壮的战士之勇。动态是串联悲感的线索,林庚在诗中使用如镜头移动般的动态笔法,串联意象的同时,引导读者走入他精心设计的古典离乱悲情之中。
动态线索在破题句即展开,合于古诗章法之“平起”,同时借写夜色笼罩征战之地,以萧瑟情境为底色,渐次拉开叙述帷幕。首句“夜走近孤寂之乡”,借助将意象拟人化以静衬动,“近”具有持续性,而“夜”的近逼,更使诗境显得紧迫局促。阿克顿的译诗遵从林庚的创作技法,尽量还原诗歌面貌。如译文“Night enters the solitary region”,亦保留拟人化的“夜”,古诗的“起兴”被阿克顿移用于译诗中,以动态化意境,造成启下之势。次句“遂有泪像酒”,带出泪与酒双重意象,并以通感联系二者间相似性,所引发的悲感亦随意境铺陈。阿克顿译此句为“So there are tears like wine”,通过“泪”与“酒”的英文语义,粘合了“night”与“tears”间的逻辑关系,译文风格忠实于原文,虽对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想象力均构成挑战,却保留了“中国味”。
而《夜》的笔法精致之处在于,悲感轻重与动态缓急,形成节奏的正相关。在意象与情感的相关性上,随着意境串联得越发绵密,经由意象组合所阐发的情境与紧张急促的悲愤合流。以“原始人熊熊的火光,在森林中燃烧起来”启下,打开动态的镜头,继而避战者、参战者、烽火、战火、森林、战马,伴随着黑夜与火焰、呜咽与铁蹄,以绵密的意象堆叠,将真实战争的一角撕扯开来。阿克顿译句“The vigorous flames of primitive man. Blaze in the deep woodland”,合用了原作的引申与通感,保留了动态的视角。“原始人”的“火光”,在原诗中借此意象,暗指离人被战争惨况激发的原始悲感,“flames”不仅有“火焰”之意,亦有“强烈感情”之内涵。阿克顿以“blaze”译“燃烧”,巧妙化用“blaze”“熊熊燃烧”本意,从而将表面可见的森林之火与潜在的心灵之火,通过内涵相接的“火”意象合二为一,做到了对原诗意象呈现法的还原。
《夜》的高潮部分,也是动态意象演进为叠加意象的顶峰。这部分的意象如梭般多而不乱,意象不仅绵密且错落叠加,飞驰意象、低喃耳语等同时出场,浓淡相映,如层层尽染的画面。这部分也是林庚此诗最具现代感的部分,他借助变化极快的场景,切换真实可感的画面,将愤激、悲怆的情绪推向巅峰。阿克顿的译诗在这部分也以还原真实现场感为主,在意境呈现上亦延用叠加手法,典型者如“Now is it whisper-time”一句,似将读者带入避战处的同时,“Outside, the clattering of horse's hooves”,又将视线推向外部的战争景象,纷而不乱。收结处,一系列快节奏意象的堆叠象征着热烈、勇敢、胜利,墙内避战者惊慌低语,恰与墙外奔赴沙场的高昂蹄声形成鲜明对比。马蹄“急碎”本不同于“clattering”,阿克顿用后者译“急碎”,旨在以“clattering”在英语语境中的拟声“咔哒”,模拟马蹄铁掌与地面相触的金石声,带出马匹奔腾的现场感[6]112。
《夜》的主题是古诗中常见的战争乱离,结构亦合于古诗的起、承、转、合章法。译诗虽未能全得其精华,但也忠实再现了原诗绵密意象的交织与移动,译诗通过对战乱悲感的动态呈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新诗古韵。
(二)古典与现代的碰撞——《沪之雨夜》
《沪之雨夜》中所呈现的现代诗“惯有的非逻辑关联的跳跃”,“在现代感性将一个旧有典故还原成一种具体的艺术感知过程之时,在诗的逆转所带来的反讽意味和空间张力中”,融合了现代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手法,聚合了现代绘画艺术的超现实主义,突破了中国古诗的章法[21]。虽林庚长于以白话复现古诗意象,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时代主题。如《沪之雨夜》,就是为表达现代文明强势入驻的文化环境下,旧思想与新环境错位所引发的怅惘[10]130。林庚借助古典与现代意象的同步在场,以蒙太奇式的意境重组,反映古典诗思寄生于现代社会的尴尬与迷乱。
该诗将古今意象进行同步拼接,视角如电影镜头般细腻,通过“眼见”与“耳闻”串联意境。主人公虽身处雨夜车涌笛鸣的都市,却心怀古典梦境,他“打着柄杭州的油伞出去”,但现实并不似他眼中所及的“檐间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实景却是雨中的柏油路。主人公继而惊喜于耳闻,巷中阁楼上的“南胡”声传来,但随即他意识到,与“高山流水”不容于柏油路面和汽车鸣笛形成同类复调,古典的“南胡”,却是在演奏着似不关心的“孟姜女寻夫到长城”,古乐器纵使演奏古乐,但也难入古典情境。但如此复杂的情感复现,对身为英语翻译者的阿克顿而言,只能通过细腻诠释“南胡”与“孟姜女”等历史词汇来复现古韵,即增强文本诠释精确性。而阿克顿在翻译用于反衬古韵已逝的现代词汇时,未能做到全然精确。如译诗将“一片柏油路”译为“endless pavement”,即“无尽的长路”,较原诗更具悠远古韵,却忽略林庚此时用“一方”可见的现代文明意象目的,是要在下文“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中,借手操古乐器、却无从再回返的历史遗韵的诗中人,与一片“柏油路”形成反向映衬,译诗与原诗出现了错位。
囿于创作者与翻译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也因林庚诗中运用了大量负载潜台词的意象,为保证读者读到的内容基本与原诗一致,阿克顿对《沪之雨夜》一诗基本采取直译,确保在忠实案本前提下,再现林庚的意象叠加法。如“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句,阿克顿把“似不关心的”译为“A tune of abstract long-forgotten sorrow”,将林庚使用“似不关心”一词所影射的暧昧朦胧的“有意淡忘”,用“像是早已忘却了的”明确用语翻译,忠实了原诗字面意义,却消解了此诗类似蒙太奇手法所锻造的模糊美与复调性。
除意象翻译之难,最难译的是意象中的典故潜藏,而对典故翻译不到位,也是阿克顿译诗逊色原诗、未能传达抚今思昔感的原因。如“檐间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句,阿克顿并未为“雨漏”与“高山流水”作注,反将象征愁绪的“檐间的雨漏”译成“由屋檐而下的瀑布”(“cascadesn from the eaves”),对“高山流水”也只用“高山上的水”(“water from a high mountian”),英文意象搭配古韵全无[6]116。因英语并无“夜漏绵长”“高山流水”等典故,且阿克顿认为过度注释会打断读者阅读节奏,从而扰乱体会诗歌过程,因此译诗保留适度“陌生感”更能彰显中国味。
四、结语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所构筑的古韵,曾给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等西方现代艺术家以创作灵感。而由中国古诗意境所阐发的意象派诗歌对中国诗境的移用,亦跨文化辅养了西方诗歌艺术的高峰。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导言中指出,林庚新诗忠实承袭了唐代诗人的经典意象群,看似将写作范围限定得异常狭小,但经由意象组合与文字处理后,创作技法的灵活运用与对意象的精确把握,使其新诗的简单意象重组呈现出极深邃、细腻的情感,显示出现代派的风格与象征派的气韵。阿克顿总结林庚诗隐晦难译的主因,在于其对新格律诗的探索,阿克顿翻译上的“失误”,与林庚在新诗创作暗藏的创作实验有直接关系。
积极向西方世界引荐中国新诗的先行者阿克顿,在翻译唯美古韵的林庚新诗时,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翻译笔法,立足技法、诗语、题材与意象,忠实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古典“中国诗味”。同时,林庚新诗中所暗藏的盛唐气象,在阿克顿译诗中,被唯美诗语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古典意象,引领西方读者经由诗语走进记忆中的东方诗境。阿克顿致力于复归中国传统、传播唯美古韵《中国现代诗选》,最代表性的林庚译诗,融通了林庚的古典中国诗味与阿克顿的唯美主义西方诗味。林庚译诗既契合了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亦以具有古韵与画意的历史诗境,投射了阿克顿立足中西诗歌艺术交融互鉴的唯美主义“中国梦”。阿克顿对林庚新诗的唯美翻译,使西方世界读者通过对译诗诗境里中国古典印象再认,“重拾”了中国新诗的古韵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