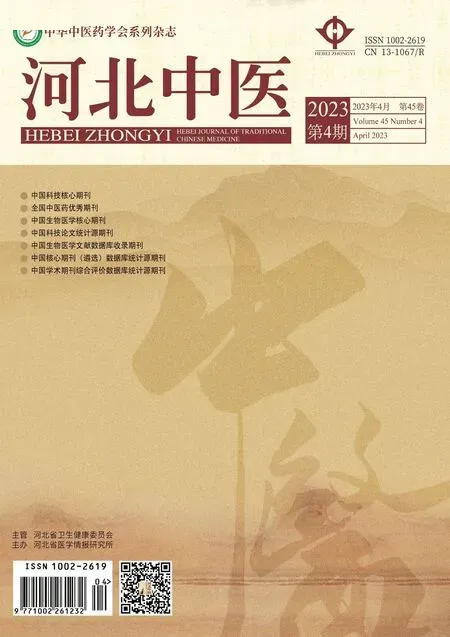李东垣疫病治疗经验解析及当今临床应用※
2023-03-19齐晓凡周计春
方 倩 齐晓凡 周计春
(1.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诊断学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200;2.河北中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河北 石家庄 050090;3.河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医史文献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200)
疫病是外感疫疠邪气所引起的,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易引起大流行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的统称。据中医史料记载,历史上共发生传染病流行不少于500次[1]。虽然直到明代才有第一部治疫专著《温疫论》出现,但中医疫病治疗历史久远,历代医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总结,并创新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庞安时的“寒毒说”、刘完素的“火热论”等学说的创立均与疫病治疗相关。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其生活在战乱灾荒年代,行医数十载,历经疫病治疗,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元史·李杲传》载:“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这里的“伤寒”是广义的伤寒,包括温病和疫病。但在李东垣著书中除大头瘟疫的治疗外,并未言及治疗他疫。我们经梳理文献可知,李东垣当时曾以“内伤说”辨治壬辰疫病,将疫病发热认作为“阴火”。
1 清热解毒合升阳散火治疗大头瘟
李东垣关于大头瘟的治疗情况见载于《东垣试效方·杂方门·时毒治验》,在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李东垣以进纳得官,监济源税,当地出现一场流行病:“时四月,民多疫疠。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李东垣首例治疗的是县丞侄,时医以伤寒之泻热法治疗不效,而求助李东垣。“张县丞侄亦得此病,至五六日,医以承气加蓝根下之,稍缓,翌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缓,终莫能愈,渐至危笃。或曰李明之存心于医,可请治之。遂命诊视,具说其由。”
李东垣认为病在头面,热壅上焦,不当以泻法,“夫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盛,以承气下之,泻胃中之实热,是诛伐无过,殊不知适其所至为故”。于是疏方施治,并获良效。“用黄芩、黄连味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橘红苦平,玄参苦寒,生甘草甘寒,泻火补气以为臣;连翘、黍粘子、薄荷叶苦辛平,板蓝根味苦寒,马勃、白僵蚕味苦平,散肿、消毒、定喘以为佐;新升麻、柴胡苦平,行少阳、阳明二经不得伸,桔梗味辛温,为舟楫,不令下行。共为细末,半用汤调,时时服之,半蜜为圆,噙化之。服尽,良愈”。李东垣感慨“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凡他所有病者,皆书方以贴之,全活甚众。时人皆曰此方天人所制,遂刊于石,以传永久”[2],这也是后来方名中“普济”的来源。
大头瘟疫的病机当为风热疫毒之邪壅于上焦,发于头面,阻于咽喉,与气血搏结,壅滞不畅,而见头面红肿焮痛,目不能开,咽喉不利;风热之邪外郁肌表,正邪相争而见恶寒发热;热毒伤津则舌燥口渴。邪在身半以上,不当以泻下,而应以“火郁发之”的原则,在清热解毒消肿药的基础上,配伍散火之品。方中柴胡、升麻性凉味辛,功擅疏散风热火邪,是李东垣善用风药的体现。连翘、牛蒡子、薄荷、僵蚕气味清轻,辛凉宣泄,并能消肿解毒。全方清降与升散并用,因势利导,共收清热解毒、疏风散邪之功。李东垣清热解毒合升阳散火治疗大头瘟的经验,为后世医家治疗热毒壅于上焦之头面肿毒类疾病提供了治疗思路,此方成为“火郁发之”的代表方剂,受到后世医家关注和发挥,当然也存在一些争议。
原书在方解中无人参,而案后附方中有人参三钱为臣。后世有以为当用人参者,如明·汪机《外科理例·附方》将本方名命为“普济消毒饮”,方药略有不同,保留人参以扶正。清·吴昆《医方考·大头瘟门》亦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用人参以补虚”[3]。持异议者则认为热病中用人参反助邪,明清温病学家多持此论,至清·汪昂《医方集解·泻火剂》所载普济消毒饮,已无人参。回顾验案中张县丞侄乃富贵中人,或无气虚用参之需,故去之。临床中当因人而异,虚则用之,或加黄芪、甘草共同补脾扶正,理同补中益气汤疗时行热病[4]。
至于大黄的使用,虽李东垣认为身半以上之病,以承气下之,是诛罚无过,但方后又云“食后大便硬,加酒煨大黄一钱或二钱以利之”[2]。本证病位高居头面,热壅上焦,明·汪机以清热解毒合升阳散火为主,但若热结明显,亦可加大黄以通下泻热。后世沿用,如《外科理例》载“如大便硬,加大黄(酒煨)一钱或二钱”。清·吴昆《医方考》载“大便秘者加大黄,从其实而泻之,则灶底抽薪之法尔”。
方中牛蒡子辛苦性寒,升浮之中有清降之性,一药两用,兼具疏解风毒和通利二便之功。吴鞠通分三焦诊治温病,其辛凉平剂银翘散之组方即受此影响。“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从普济消毒饮时时清扬法”[5]。方中选用辛凉轻清之品,并强调整煎煮时间要短,“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5]。对温毒的治疗,吴鞠通提出“治法总不能出李东垣普济消毒饮之外”,但对于方中的升麻、柴胡,吴鞠通提出了不同观点。《温病条辨》载“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甚则耳聋,俗名大头瘟、虾蟆温者,普济消毒饮去柴胡、升麻主之”。他认为病本为热在上焦,是“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麻、柴胡这样的升发之品,而且“此方皆系轻药,总走上焦,开天气,肃肺气”,不必再用柴胡、升麻作引经药[5],但这点未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同。
2 以甘温除热法治疗壬辰疫病发热
壬辰年(公元1232年)李东垣以“内伤”辨治发热患者,注重和“伤寒”的辨别,并归之为“阴火”范畴,但结合症状表现和史料记载,李东垣实际所治的是具有脾胃内伤基础的疫病。
2.1 时医误以“伤寒”论治壬辰疫病 据《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记载,壬辰年,元军包围汴京,李杲被困城中,此间经历了一场流行病“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2]。这里的数字虽不是十分确切,但从病情描述可知,发病急骤,发病率高,致死率高,显然是一场“急性、烈性传染病”[6],而不是通常意义的虚劳发热。这与史书记载相符,《金史·卷六四·后妃下》记载“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对这场疫病目前比较流行的是肺鼠疫说[7]。
时医泥于仲景之说,以伤寒论治,反而加重病情。“余在大梁,凡所亲见,有表发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汤、丸及茵陈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2]。这在《脾胃论·序》中被元好问称为“壬辰药祸”[2]。李东垣对这场热病的病因提出质疑,“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2],并结合发病背景,认为“脾胃内伤”是主要原因。“计受病之人,饮食失节,劳役所伤,因而饮食内伤者极多,外伤者间而有之”,“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大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2]。时医“将元气不足之证,便作外伤风寒表实之证,而反泻心肺”,是重绝其表,实实虚虚,致人殒命。
2.2 东垣将疫病发热归之内伤阴火 李东垣受张元素脏腑辨证的影响,尤其重视内伤为病。他在外感和内伤的分辨上积累了大量经验,“中年以来,更事颇多,诸所诊治,坦然不惑”。在壬辰年之前就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详辨内伤外感,书中提出“阴火”的概念,指出“与外感风寒所得之证颇同而理异”[2]。
“阴火”一词为李东垣所创,指内生之火,是相对感邪所致的“阳火”而言。此处“阳”指外感性疾病,“阴”指内伤性疾患。《内外伤辨惑论》对阴火的症状、病因、治疗详加阐述,“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生长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不任风寒,乃生寒热,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2]。《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又记载:“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能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2]在李东垣著作中多处论及“阴火”,总由脾胃内伤,气火失调,或升降失常所致。复杂的“阴火”难以一言以明,但肯定的是,李东垣将具有脾胃内伤壬辰疫病的发热也归之为“阴火”。
对于这场热病,李东垣认为虽有发热,“乃不足之证也”。结合发病背景,认为是脾胃内伤,致元气不足,元气系在上焦,致心肺不足。心主荣,肺主卫,荣卫失守,皮肤间无阳以滋养,不能任风寒也。“内伤饮食,则亦恶风寒”,《内外伤辨惑论》这样描述病人症状,“故脾胃之证,始得之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2]。从症状描述看,与阳明经热证类似,所以有的医生误用白虎汤,以至“旬日必死”。李东垣提出劳役不足之热与阳明实热的辨别,“此证脾胃大虚,元气不足,口鼻中气皆短促而上喘,至日转以后,是阳明得时之际,病必少减。若是外中热之病,必到日晡之际,大作谵语,其热增加,大渴饮水,烦闷不止,其役不足者,皆无此证,尤易分解”[2]。在治疗上,“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2],内伤所得,属不足之证,法当补,不能以伤寒有余之证论治。
壬辰疫病患者有群体脾胃内伤的情况,故治疗上应忌辛温发表和苦寒清热,而是以甘温益气之法治其本,伍用升阳散火之药。《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载“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今立补中益气汤”,“黄芪(劳役病热甚者一钱),甘草(炙以上各五分),人参(去芦)、升麻、柴胡、橘皮、当归身(酒洗)、白术(以上各三分)。上件咀,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早饭后温服。如伤之重者,二服而愈,量轻重治之”[2],这里也是“甘温除大热”一语的出处。
2.3 壬辰治疫,有治疫之实,无治疫之名,影响后世继承 参考历史背景和症状描述,补中益气汤最初所治发热实际是疫病发热,这点后世医家也有阐述。清·王泰林《王旭高医书六种·医方证治汇编歌诀》言:“补中益气汤原为外感中有内伤一种者设,所以补《伤寒》之未及,非补虚方也[8]”。现代医家顾思臻等[9]认为,《内外伤辨惑论》卷上、卷中所载阴火证候群有类于鼠疫初起。张再良[10]也认为,补中益气汤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杂病治疗,但补中益气汤其实是从热病证治中走出来的一张名方。
对于壬辰疫病,李东垣否定外感风寒是正确的,认识到发热患者群体有脾胃内伤情况,这点总结也没有问题,但只从内伤来解释全部病因却又是不全面的。正如范行准所说“所以他把这次汴京大疫属于内伤,在医学史上来说,实是一个罕见的大错误”[11]。但李东垣以甘温除热法在临床上又取得了肯定的疗效,不然不会“以平生已试之效”著书立说,这实际是“方效论错”。对于壬辰疫病的治疗,李东垣书中有治疫之实而无治疫之名,以至于影响了后世对其经验的继承。
李东垣时代研究的是由战乱、饥寒交迫导致饮食劳倦内伤而引起的一系列急性传染病,是在内伤基础上的传染病,是基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传染病。原书黄芪用量非常少,宜于当时脾胃内伤者,而当今临床,中气、大气下陷者,量宜加大。如蔻兰俊等[12]对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使用加味补中益气汤,峻补中气,可明显改善呼吸功能,缩短上机时间,提高脱机率。
2.4 “甘温除热法”解析 气属阳,气为阳之渐,气虚当表现为乏力恶寒。《难经》言“气主煦之”,煦,有温暖之意。“热者”当“寒之”,甘温又怎能除热呢?其实“气虚—发热”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其间还有与气虚相关的其他病机,共同作用而致热,“气虚+其他病机—发热”,如气虚+阴虚、气虚+疫毒、气虚+外感等。“甘温除热”也不应简单理解为用甘温药去除热,而应是“甘温+除热药”,甘温针对气虚,加药针对其他病机。如补中益气汤为“甘温三味+升麻、柴胡”,黄芪、人参、甘草三味甘温补其虚,而升麻、柴胡升阳散火除其热。方后注还有更为复杂的加减:腹中痛者,加白芍;恶热喜寒而腹痛者,更加黄芩。“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水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气浮心乱,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则愈”[2]。
对于甘温除热的配伍,李东垣说:“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既然宜甘寒泻火,大忌苦寒,可方后又加黄芩、黄柏等苦寒药。看上去,似乎相矛盾,其实其本意是忌单用苦寒药,恐伤脾胃,但可以甘温药+苦寒药,合而则成“甘寒药”。另外如补脾胃泻阴火的升阳汤,就是甘温三味+羌活、升麻、苍术+黄芩、黄连、石膏,也是典型的“甘温+除热药”的模式。
单气虚不会致热,单甘温不会除热。气虚发热不是由气虚导致发热简单的线性关系,中间还有可能不只一个的病理环节。如果简单地认为“气虚”可以导致“发热”,那么这一命题是有严重缺陷的,有悖于气的生理,其间一定存在着因虚致虚、因虚致郁、因虚致邪的复杂病理环节[13]。治疗上,也不能用“甘温除热”简单概括内伤热中证的治则。“甘温”用以治劳和损,但不直接除热。基于复杂病机,而应采取“甘温+”的组方模式去理解,以甘温药补其虚,再据相关病机酌加甘寒或苦寒药,共同达到除热的目的。正如黄彩平[14]所言,东垣甘温除热法是有其特定的组方意义的,实际上是甘温补中药与清热祛邪药的组合。
3 东垣治疫经验在当今临床的应用
3.1 普济消毒饮广泛应用,不拘于大头瘟一病 清热解毒与升阳散火并用的李东垣名方普济消毒饮,是“火郁发之”的代表方剂,此方得到后世诸多医家的重视和发挥,为温病学理论和治法的开启与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清·费伯雄《医方论》对其有高度评价:“天行疠气最为酷烈,病在上焦者,于上也,此方清热解毒,祛疠疫之气最为精当。”其以柴胡、升麻等风药疏散火热成为火热证治疗的一大法门,尤其适用于头面、身半以上的热证。目前普济消毒饮已经广泛应用到腮腺炎、扁桃体炎、甲状腺疾病、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皮炎、腮腺炎性睾丸炎、扁平疣、水痘、痤疮、带状疱疹等疾病的诊疗,这说明随着对普济消毒饮的研究,其应用范围得到拓宽,并不局限于古代的“大头瘟”一病[15]。
3.2 甘温除热法可用治外感热证 由于李东垣壬辰治疫,有其实无其名,所以没有得到后世很好地继承发扬。根据李东垣的治疗实况,脾胃内伤基础的疫病发热或外感发热均可依“阴火”辨治。当今临床,有不少医者在实践中有所感悟,从“阴火”论治气虚外感的报道不在少数,包括流感、呼吸道感染、肠炎、尿路感染等,以反复发病,病程较长,慢性病合并感染为多。如徐红日等[16]以益气清瘟解毒合剂(药物组成:炙麻黄、羌活、柴胡、金银花、生石膏、黄芩、生黄芪等)治疗流感,是用甘温除热法治疗外感热病的典型例证。庄爱文等[17]对甘温除热病机也有所认识,提出阴火可由外邪诱发,是内伤与外感的共同结果,但脾胃气虚是本,外邪是标,与单纯外感病截然不同。黄彩平[14]认为,甘温除热法可用于温病兼有脾胃气虚的治疗,认为使用甘温除热法既要有以气分热证为主的表现,又要有脾胃气虚的表现。所以,临床中凡是脾胃内伤基础的外感热证,包括疫病在内,同样能依李东垣“阴火”理论来辨治,莫拘于“内伤”一语,而将甘温除热法排除在外感热证治疗之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亦属中医疫病,当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若患者有明显脾胃内伤表现,则可依内伤热中证辨治。何青等[18]研究发现,采用补中益气汤能明显改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症状,降低炎症指标水平,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正是古方今用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