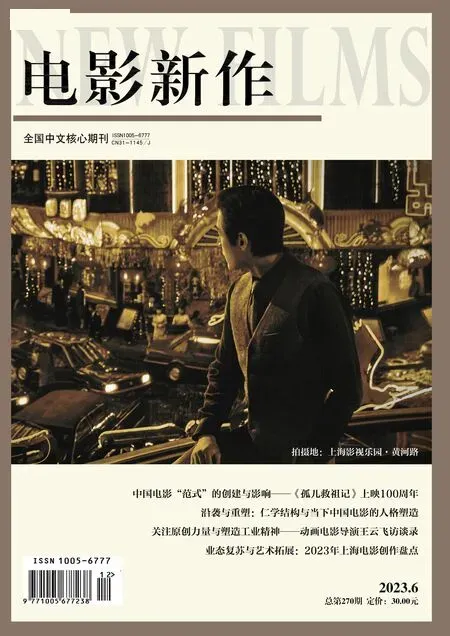创伤与缝合
——论现实题材影视表演的情绪记忆传达
2023-03-18陈思含
陈思含
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众多的战争与无数磨难,战争消耗着人类的生命与文明,苦难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伤在浩劫中逐渐显影,却无法自然痊愈。于是,创伤记忆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逐渐成为文学及艺术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直至现在,无论是战争、灾祸等大事件造成的集体性创伤,还是小到每个家庭中的原生家庭创伤,都在影视作品中常有出现。表演作为电影与电视内容的表现形式,通过作品与观众建立独特的联系,将创伤记忆呈现在银幕之中,不仅表达着作品的思想和情感,还借由情绪记忆的传达,结合观众的精神世界,形成新的意义。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也部分地经历创伤、感受创伤、治愈创伤。
一、创伤记忆的载体:表演中的情绪记忆
“创伤”一词最初源于希腊,意指“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此后在弗洛伊德的推动下,创伤的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步走向心理或精神层面,“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让心灵受到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对于创伤的表达通常会注重描绘角色经历创伤,“在心理、个体记忆、自我认识及其与他人的关系上发生的无法逆转的变化”2,并通过演员对角色情绪记忆的传达,具体化人们对创伤记忆的感知。一般来说,影片通常围绕着两大创伤主题:一种是以自然为施暴者的天灾,如电影《唐山大地震》《大太阳》《海啸奇迹》等,以家庭为视角讲述灾难侵袭时人类的脆弱与渺小,通过对主人公情绪记忆的重现,具象灾害创伤下人们的颠沛和挣扎;另一种则是以人为施暴者的事件,如侵犯、虐待、战争等。此类主题的影视作品往往会聚焦于个体创伤,并以此折射出历史大背景下的人类社会问题。有关战争创伤的影视作品如《南京!南京》《四十九日·祭》,通过再现战争中的分离与死亡、人性的拷问与博弈、信仰崩塌与情感纠葛,回望和反思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民族创伤记忆;如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林恩从战场短暂地休假回家,却发现战场之外的现实生活除了战友几乎无人能够理解他们在战场经历的一切。影片聚焦林恩和战友们在球场庆典中,因格格不入而产生的沉重和焦躁的情绪,隐喻了战争带给当下年轻军人痛苦又迷茫的创伤;又如电影《美丽人生》,用描绘圭多一家人从前的幸福生活对比二战后生活的艰难,用父子之间的真情互动对比集中营内生活的惨烈,展现了主角圭多用善良对抗残暴,用温情回敬现实。战争残酷,他却用爱和生命为孩子创造了一个未被创伤裹挟的童年。

图1.电影《唐山大地震》剧照
如果说影视作品的画面是对创伤记忆的复原,那么表演中的情绪记忆就是创伤的载体。“情绪记忆”作为一个心理学名词,最早可追溯到1984年法国心理学家戴·利伯的《情绪记忆研究》,特指以体验过的情绪、情感为内容的记忆。3在表演艺术中,“情绪记忆”则是斯氏表演体系体验技术中的一块重要拼图。他认为“情绪记忆”是演员体验的内部材料,是情感的燃料。演员自身的情绪记忆也可以作为角色相关联的中介,借由这种人类固有的心理活动过程,在角色的情境中培养、构成不同形象的种子。4从表演创作的角度出发,情绪记忆并不能表现创伤的全部,但因其在表演过程中具备的真实性、共识性与生活性等特点,可以将创伤记忆凝练得更为真切与丰富,传递得更为直观与强烈。演员作为表演的执行者,通过感受和把握角色的情绪记忆,可以更为精准地揭示角色所承载的创伤。
在《唐山大地震》中,演员张静初饰演的方登是一个灾后幸存者。“在灾难中被母亲抛弃”是她一辈子摆脱不掉的创伤经历,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创伤导致的情绪问题。在方登的成年阶段,张静初的表演着重于放大角色身上孤独与割裂的情感状态,强调了角色面对亲密关系时淡漠与疏远的态度。演员通过闪躲的眼神、局促的肢体语言等外部动作的设计,展现了角色对与地震有关的创伤记忆一直在刻意躲避,传递出创伤之下的痛苦与无助的情绪记忆。不论是集体创伤,还是个体创伤,受创者的情绪、记忆、反应等方面都会在创伤经历后产生相类似的应激特征。“记忆侵扰”就是受创者身上最普遍存在的创伤特征之一。创伤记忆往往停留在受创当时,让当事人即使在经历结束之后,仍然会以“闪回”和“梦魇”的方式重新回到受创的时刻,而这种反复的创痛“穿越”就是记忆侵扰。地震带来创伤记忆从未离开过方登,并常常化作梦魇侵袭而来,让她总在睡梦中猝不及防地被拖回地震发生的绝望时刻,被迫重复体验残忍的创伤经历。在噩梦惊醒后的惊恐与不安的爆发与她清醒状态下的冷静、疏离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创伤记忆的沉重,并透过演员的表演体会到灾难对她内心的摧残与折磨。
受创时刻的画面来回闪现,受创时刻的情绪记忆萦绕不去,受创者的历史关系、时空关系和人际关系就会因此处于长期断裂的状态。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李·钱德勒也是一个饱受记忆侵扰的受创者。不同的是,他的创伤经历在现实的挤压下隐藏着更多复杂且压抑的情感。“创伤有可能是由一次偶然的急性事件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一系列生活经历影响,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的。”5李·钱德勒的创伤记忆来自于他在曼彻斯特小镇经历的痛苦——因他的疏忽导致自己三个孩子死于火灾,妻子也因此与他离婚。无法面对创伤的李·钱德勒,选择远走他乡自我放逐,将自己封闭起来。直到哥哥去世,他才不得已回到家乡操办后事。然而,重回曼彻斯特就像是撕开了他从未愈合的伤疤,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过去的碎片中。“闪回和梦魇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受创者创伤记忆的一种提取,并以当时的画面和情绪感受反复、重复地出现,成为一种压抑的经验。”6正如影片中有关过往的画面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曼彻斯特的故人旧物都在提醒着其曾经犯下的过错,唤起他内心痛苦不堪的情绪记忆,让他在逃避现实的同时依然不断叠加着自身的创伤。
李·钱德勒的饰演者卡西·阿弗莱克在影片中的表演是平淡却充满张力的,所呈现出的悲怆与沮丧蕴含着惊人的表达,并用极强的控制以及合理清晰的表演策略,向观众传达出创伤之下角色心中丰富且层次分明的痛苦。呼吸,是他表演过程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创作点。卡西·阿弗莱克对于呼吸的运用没有局限于特定情境的拔高音量或情绪过激时的生理反应,而是成为他外化角色心理活动的一个表演手段。“呼吸本就是演员内心活动的重要依据。只有内心活动充实了,呼吸也就准确了,所有的设计也就合理了。”7影片中,李·钱德勒在独自铲雪时,接到了哥哥去世的报丧电话。面对突发的噩耗,卡西·阿弗莱设计了如下反应:在奋力铲雪的过程中,他短暂地停顿了几秒钟,有些发愣。与此同时,他急切地控制住自己因铲雪所产生的剧烈喘息,认真判断电话里的具体信息。而后,他回话时发出的声音却是微微发颤的,让观众迅速捕捉到那瞬间涌上心头的悲情。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一会儿,他又调整回之前寒冰一样的常态,离开时甚至还有条不紊地取回雪铲。这个细节,立刻将李·钱德勒与开篇在房客面前心神游离、不在状态的样子呼应了起来,契合了他在经历创伤后麻木、淡漠的人物基调。
在医院太平间等待哥哥遗体的那场戏,卡西·阿弗莱克又在表演处理中展现出来自角色的极大克制。这是一种近乎失控、没有从容感的克制。遗体被推出后,他的双手局促到无处安放,时而紧握成拳,时而胡乱地猛抠手指,面部神情则是死一般的煞白与僵硬,这暗示着他短暂的呼吸停滞。在这几秒钟内,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那颗早已被烧成灰烬的心,似乎又短暂地跳动了一下,尽管没有死灰复燃,却依稀闪烁着爱的火苗。卡西·阿弗莱克没有将李·钱德勒的这份触景生情演绎成翻江倒海,而是诠释为一种拧在心里的悲伤。这份悲伤,在李·钱德勒俯身亲吻哥哥时随着眼泪一起涌出。可却又拼命眨眼试图克制泪水的滴落,他用这种方式顽强地拒绝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苦。
“记忆是人类构建并确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8,“人们对于自身的存在和身份的感知都来自于记忆的延续。一旦丧失记忆,自我就无法确认,存在就成为了虚无”。9过去的毁灭性打击破坏了李·钱德勒的记忆,镌刻在大脑、身体和心灵上。创伤理论家库尔克和哈特认为一些受创者在受创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同时生活在创伤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中,并难以将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李·钱德勒也常在记忆侵袭之际,同时穿梭于过去的创伤与现实的悲剧中,让“面前的现实”与“回忆重塑的第二现实”并置于脑海中。影片中李·钱德勒在被律师告知自己要成为侄子的监护人时,毫无预警地闪回到当年的火灾现场,目睹自己醉酒后酿成大祸:三个孩子的尸体被装袋、抬出火场的绝望时刻。在沙发上迷糊睡去之时,他看见已故的女儿出现问:“爸爸,你没有发现我们烧起来了吗?”无常出现的幻觉是旧创伤的新梦魇,现实创伤包裹着历史创伤,而历史创伤催化着现实创伤,李·钱德勒在两个家庭的不幸中被各种绞杀。创伤所承载的情绪记忆如同一剂慢性毒药缓慢侵蚀着李·钱德勒。悔恨和无奈,就像是一团精准定位的乌云,笼罩在这个中年男人的身上,让他变得沉默、木然、歇斯底里。
在不同的时间线里,演员卡西·阿弗莱克运用对比性极强的表演,凸显出人物完全不同的情感色彩。在有关过去与妻子生活的回忆里,无论是与孩子的交流,还是与妻子的欢爱,演员多数形体动作的选择都很奔放,传递出角色关于过去温暖而又热情的情绪记忆。反观现实生活,角色所生活的海边环境以及雪天呼出的冰冷气息,甚至是演员疏离的面部表情,都在提醒着观众角色的内心早已被寒冷的坚冰完全包围。相对极致的一场戏,是创伤发生之后李·钱德勒在警局接受询问的片段。灾难刚刚发生,李·钱德勒神情游离,麻木又迟钝如同一具心神皆无的游魂,似乎还没从巨大的悲伤中反应过来。却在下一秒,他突然发疯一般夺下警察的佩枪,欲求饮弹自尽。这个强有力的举止反差,如同重拳出击一般狠狠砸向观众心头,让观众瞬间强烈地感知到角色内心那结结实实的痛楚,并与角色一起长久地难以接受、无法释怀。过去的李·钱德勒是明烈的,鲁莽而又直接,创伤之后的他只有压抑与麻木,自毁的人生并没有让他获得半分救赎,反而在负罪与悔恨之间无所适从。卡西·阿弗莱克通过呈现李·钱德勒内心隐忍和克制的矛盾冲突,以及自我意识在过去和现实之间的痛苦挣扎,传递出角色的孤独感,让观众在爱与恨、苦与痛的交织中,直击伤痛的抵达,感知这份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二、创伤记忆的呈现:受损个体沉重的情绪记忆表达
将创伤放置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以个体视角出发描绘创伤经历对个人的影响,是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表征创伤的主要方式之一。多数作品通过对创经历的再现和对创伤后果的揭示,唤醒创伤个体难以治愈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往往伴随创伤经历而形成。对于个体创伤来说,沉重的创伤经历会让受创者的自我遭到损坏、内心产生无法逆转的变化。在影视表演过程中,创伤对不同受创个体的影响可以通过对其情绪记忆的再现进行更为复杂和细腻的表达。戴·利伯曾提出,“情绪记忆是过去情感的恢复”。从创伤者的角度出发,“情绪记忆”特指曾在创伤经历中体验过的情绪、情感为内容的记忆。而将情绪记忆延伸到影视表演,可以理解为演员将代入角色后引入的感受、感知以及情绪用不同的表演手段将可视创伤具象为可感创伤传递给观众。
近年来,围绕“身体创伤”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例如影视剧《原生之罪》《她和她的她》《胆小鬼》以及《漫长的季节》等。这类影片中的创伤人物,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拒绝倾诉创伤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创伤的情绪反应中,内疚与羞愧是主要的症状群,持续的内疚与羞愧会让受创者用遮掩的方式处理自己的受创情绪,将创伤经历埋藏在内心深处。在《漫长的季节》中,沈默就是一个极致隐忍的角色。演员用层次分明的表演,叙述着沈默被创伤裹挟的破碎人生,让观众透过她与养父对峙,窥见性侵创伤的原貌:是沈默被皮带抽打时,因疼痛面部暴起的青筋;是养父那句“你早晚死在我手里”的笃定诅咒;是她被扼住咽喉快要窒息时,奋力挤出的惨淡微笑。不论是演员波澜不惊的面部表情、还是节奏平缓的身体语言,甚至是受到伤害时做出的情绪反馈,都呈现出一种极致的淡漠与麻木——那是反复地经历创伤后,沈默近乎病态的情绪缺失。
在该剧的最后一集,由演员张静初饰演的成年沈墨,作为最终揭晓谜底的人物,用短短两三场戏的表演,为沈墨这个角色补足了空白。20年的仇恨、愧疚、痛苦与流离,似乎都写在张静初那张沉默的脸上。在访谈中,张静初提到自己在剧中出现时已到剧集尾声,观众对于沈墨这样一个角色,还是会想知道曾经发生过的巨大创伤对于20年后的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表演需要向观众揭示出沈墨身上那消失的20年所留下的情绪记忆。为此,张静初在表演创作之初就详细地补充了有关沈墨的前史,尽可能地具体化角色的内外部规定情境,让自己更好地置身其中,感受角色内心的恐惧与挣扎。她分析多次遭遇伤害的沈墨在面对侵害者时内心会因过度害怕而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整个人如石化般僵硬。所以成年后的沈墨能够选择再度回去,其实是战胜了内心极大的恐惧,才得以完成复仇。在无法控制的悲惨的人生中,她一直在试图努力夺回自己控制权。由此她定位了成年沈墨的角色性格——压抑和克制,并以此为出发点对角色身上有关创伤的情绪记忆进行了极具张力和压迫感的表现:沈墨所承受的苦难、伤害和愤怒,都压抑于她心中,如一个高压气罐,等待一个爆炸的契机。就表演艺术的特性而言,演员的确无法摆脱自身的情感进行角色塑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体验派艺术的主张者也曾提出,“情绪记忆”是为了强调在角色的情境之下演员内心情感体验的重要意义。演员在表演创作的同时也在心中培养了角色的规定情境,调动情绪记忆与角色的情感世界交相呼应、结构配合之下完成角色的表演。

图2.电影《一念无明》剧照
“在心理学中,记忆被定义为人对过去经验的反应,而‘情绪记忆’则是人们对体验过的情感的反应。‘情绪记忆’是人们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在表演中如何运用这种心理活动并可以帮助演员顺利走进角色的情感世界,是演员心理技术的核心问题。”10作为人的心理活动,“情绪记忆”的触发会使演员沉浸于过去的某种情感体验当中。演员苗苗在影片《芳华》中饰演的何小萍是一个热爱舞蹈却不合群的女孩。她在访谈中讲述与角色有着相类似的成长过程与创伤经历——在艺校被孤立。片中拍摄何小萍在艺校所经历的霸凌创伤,于她而言就是一种触发。她重新体验了曾经的创伤经历,唤醒了过去的情绪记忆,也由此较为真实地表现了何小萍被孤立后的苦涩与难以言语。关于“情绪记忆”的调动,演员常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情绪记忆”在演员首次的表演创作中因其自身的突发性与未知性,会格外强烈和丰富。但随着表演次数的增加,“情绪记忆”本身就会变得暗淡。其自身的不稳定性便成了演员表演创作中的一种障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主张演员的情感是只可引导而不可强制的,心理技术的运用要完全遵守这条原则,否则演员的“情绪记忆”只会被限制而非被启发。也就是说,演员要想接触自己的下意识领域、驾驭灵感,就要找到“刺激物”,进而使记忆复苏。11演员苗苗也提到,何小萍这一角色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角色的层次深度来说,都是一次严格的试炼。在拍摄过程中,为了找到更好的人物状态,导演冯小刚要求其他演员都不能理她,以此为“刺激物”影响她的内心感受,帮助她保持“情绪记忆”的鲜活,将人物的创伤呈现得更为深切和真实。
不同于沈默、何小萍的隐忍,演员金燕玲在其作品《一念无明》和《春潮》中的角色塑造则呈现出受创者对于创伤记忆的另一种情绪表达。两部影片中,金燕玲饰演的角色在不同程度上都选择以激烈的情绪抵抗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创伤。多数情况下,创伤会对受创者造成深远而又复杂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甚至进一步诱发严重的情绪问题。“‘警觉性增高(易激惹)或反应明显改变’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的症状之一,指的是受创者易被激怒、易受到惊吓、对创伤相关的事物有很高的警惕性甚至出现暴力行为。”12其中,愤怒导致的暴力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情绪调节失衡的表现。演员金燕玲在《一念无明》中的表演,便是以极端的愤恨与崩溃隐喻创伤带给角色的疤痕。在片中,由她饰演的母亲,晚年生活落魄又饱受疾病的折磨:丈夫每月寄钱却从不现身,最牵挂的小儿子躲在美国不闻不问。易怒和狂躁是这位母亲的常态,为缓解身理与心理的双重痛苦,她终日用极尽恶毒的诅咒与谩骂将恶劣情绪宣泄在身边唯一的亲人阿东身上,只有沉浸在过去的回忆幻象中才能从痛苦中短暂抽离。影片中,金燕玲用为数不多的几段表演,将颓唐又重病在身的绝望母亲演绎得丝丝入扣。发病时的撕心裂肺,她用激烈到近乎失控的情绪宣泄着来自角色的无尽痛苦;陷入幻想时的喃喃呓语,她那苍老憔悴的面庞却洋溢起少女般幸福的微笑;失禁后的狼狈不堪,她噙着泪的双眼满是无法自理难堪。她又凭两句《姑娘十八似花轿》的幽唱、三言受父亲宠溺的回忆,向观众道出角色的创伤郁结——数年前一段阶级不对等的失败婚姻。如此,观众如亲身经历般走入角色身处的绝望地狱之中,切身感受到她所背负的创伤记忆。她让人跟着歇斯底里,让人亲见阿东失手弑母的痛感,让人感受亲人之间的爱极与恨极,以及生而为人的深深孤独。
同样,《春潮》中由她饰演的姥姥纪明岚,也被失败的婚姻烙下创伤,并通过“强烈、重复的倾诉”应对难以排解的痛苦。创伤对该角色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她对家庭几乎狂热的控制——要和女儿争夺外孙女的爱和忠诚,犹如当年和前夫争夺女儿的爱和忠诚一样。在片中,纪明岚常常以锋芒毕露的姿态出现,不仅强势能干,还乐于在居委会热心组织老年合唱团活动。可在外待人热情的她,在家却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对家人乱发脾气,对女儿郭建波更是有着源源不断地抱怨、苛责、乃至恶毒的诅咒。在“纪明岚”一角的表演创作中,金燕玲用幽怨的眼神、跋扈的态度、愤懑的情绪与酸楚的语气将角色喋喋不休的数落演绎到极致。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提出的“强迫性重复”是指一个人固执不断地重复某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活动,或反复重温某些痛苦的经历和体验。这种强迫性重复不但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也经常在家庭里产生代际传递。在《春潮》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几代母女之间的强迫性重复,“创伤的代际传递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父母、个体自身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的‘易感性’上”。13这些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产生影响。作为创伤的共同亲历者,女儿郭健波和外孙女郭婉婷都表现出“拒绝倾诉”的隐忍顺从就是创伤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表征。
演员郝蕾饰演的郭建波是被软禁的女儿和母亲,从原生家庭代际的创伤让她与矛盾共生。她一边顺从着母亲无止尽的谩骂,一边用各种方式消极抵抗;她痛恨着母亲,却又渴望着母爱;作为记者,她直面现实社会的负面信息;同时,她对人生的阴暗面抱以维持现状的退缩。郝蕾的表演细致刻画了郭建波对母亲的无声反抗,用压抑和心痛映射角色隐忍之下暗流涌动的叛逆和爆发。正如与母亲的冲突中,她没有用激烈的言语回击,而是紧紧握住仙人掌,以此宣泄内心的痛苦。她反复地揉捏伤口,任凭鲜血流出,如仙人掌般用长满刺抵抗着来自外界的绝望。影片最后郭建波的独白,是她在片中唯一一次将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无法言说的创伤向观众摊开。站在病房的窗口,身后是昏迷不醒、终于安静的母亲,眼前是繁华热闹的街景,演员郝蕾用毫无生气的语言诉说着一个个激烈痛苦的创伤时刻,愈平静,愈痛苦,与创伤本身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这份异样的平静中,观众终于看到了郭建波内心深处的伤痛,感受到她痛苦的情绪记忆。
三、创伤记忆的缝合:情绪记忆的述说与重建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的功能性之一在于让读者和作者的压抑得到补偿或变相满足,文艺作品如梦一般不仅是欲望的化装,也是一种弥补。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创作,在心理创伤的治愈机制中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这种治愈不仅存在于创作者与作品中,也存在于被作品影响的观众中。创伤记忆作为人类记忆残酷的部分,借由影视作品的创作和放映,将其复杂又特殊的精神属性外化为可感、可视,并通过一遍遍被观看、被解读,形成如同心理治疗的暴露疗法一般治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影视表演所带来的情绪记忆在观众与影视作品之间架起一座共情的桥梁,用共情完成创伤的述说,从而达到缝合的目的。
“与他人分享创伤经历,是重建生命意义感的先决条件。”14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肖认为,“从创伤复原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也就是说能够将创伤切实地向某位或者某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15在电影《绿皮书》中,主人公谢利就通过与托尼的创伤叙述,得以部分地治愈创伤。作为第二代黑人中产阶级,谢利虽没有直接的创伤经历,但“种族歧视”导致的创伤仍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创伤记忆镌刻在他脑海深处,并破坏了他与社会之间的正常联结,这种僵局直到巡演途中白人司机托尼的出现与陪伴才得以打破。为避免当创伤记忆侵袭,痛苦的再次发生,谢利主动向托尼谈及家庭,包括只有着极少往来的弟弟,并在托尼的引导下道出创伤的核心——关于自己和家庭亲密关系破裂的情绪记忆。相较于宏大的种族隔离,这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隔离,才是真正的隔离。

图3.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然而叙述创伤的过程并不容易,创伤的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漫长过程,可能经历倒退和重复。为躲避创伤带来的痛苦,谢利已习惯于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孤傲默然的伪装者,以此来遮掩自己与外部关系的断绝。对他而言,述说创伤经历无异于再次体验创伤事件中的痛苦情绪。正如开鲁斯所说:“创伤一旦发生就永远无法完全从记忆中抹去,但我们总会竭尽全力修复创伤经历在心灵中留下的裂隙,只有这样才能重建患者与外界的联系,重塑患者积极的自我。”16当他双眼含泪,嘶吼着向托尼讲述自己承受无人理解又无人理睬困境时的孤独,以及独自消化外界彬彬有礼之下的种族暴力时,发自内心的窘迫与愤怒。他那包裹结实的伤口才被彻底撕开,关于伤痛的情绪记忆得以释放。也在这时,谢利的创伤才真正找到了被疗愈的可能。在影片的最后,谢利与托尼对待彼此的态度发生改变,这是谢利自我意识得以匡正的最好体现。尽管创伤记忆为谢利带来的伤痛不可能彻底抹去,但他通过对情绪记忆的述说与重建,逐渐实现了个体意识的完整形态,与他人建立了联系,重归正常生活。可见,记忆与叙述是受创者重塑自我的关键因素。叙述可以为受创者“提供一个重塑自我、重构意识形态主体以及重新评估过去的平台,它能够帮助创伤经历者缓解症状,最终治愈创伤”。叙述给予了受创者治愈创伤的契机,通过重现创伤经历、重建创伤记忆,达到重塑自我的目的。
缝合创伤的前提是正视创伤,并以此来探寻治愈的通道。法国精神病学家贾内特认为,创伤记忆是固定的,不仅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回忆,也不受意识的主动控制。受创者需要将创伤经历叙述出来,才能使创伤经历融入正常的记忆中去,使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相融合。电影《地久天长》中,成年沈浩向老年的耀军和丽云的坦白与诉罪,就是他对创伤记忆的一种直面。隐瞒了20年的真相伴随了他的整个成长阶段,沦为他心中无形的负担。正如沈浩所言:“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他用坦白将创伤中的情绪记忆述说,在丽云夫妇最大的善意与宽容中,试着重建自我,求得一丝治愈。相比之下,母亲海燕的创伤记忆显得更为复杂与沉重。年轻时为完成计划生育的指标,她对丽云打胎致其终身不育。儿子沈浩又意外导致丽云失去另一个儿子刘星。面对耀军与丽云的丧子之痛,她用“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的谎言掩盖事实,却在后续的人生中都背负起痛苦的创伤枷锁。在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她呢喃忏悔“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时,她声嘶力竭的临终自责“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从创伤的折磨中解脱。
耀军、丽云、海燕等角色跌宕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影片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从中国80年代初跨越到21世纪初,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将角色的个体创伤与时代背景互为交融,刻画出一代群像。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角色在时代变迁下所经历的复杂纠葛的个中情感,以及被时间缓慢治愈的创伤,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真实诉说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于观众来说,这也有着更为切身与强烈的的情感共鸣。由此,影片在情感的述说与重建中传递出更深刻的意义: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创伤,如今终于得以言说,得以治愈。
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提出,“受伤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一般需要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描述出来,并设法回到该事件中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该事件的理解,最后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实生活中,重建与周围环境的安全机制。”17对此,库尔克也提出,如果能在原始的记忆画面中做一些变动,就能逐渐减少创伤记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并且给他们将来的生活带来希望。18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主人公贾晓玲就通过重返过去,“修改”创伤经历,重建安全机制,以此弥补母亲情感上的缺憾,实现了修复自我的创伤缝合。该片的情节虽为虚构,但演员贾玲在表演过程中的细腻丰富的情感表达,却真切地唤起了观众内心深处对于亲情的记忆。角色在影片中依托情节进行治愈,贾玲的表演却借助于情绪记忆的传达,让观众因共情于角色,形成自我认同情感的再现,同步实现观众的自我的治愈。
“一个人可能通过艺术创作或者梦境展现出被压抑或遗忘的一些表现和特征,以释放情感上的压力,消除创伤症结。”19从观演关系出发,表演也可以看作是叙述创伤的途径之一。这对于具有心理创伤的艺术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较好的走出创伤和排解压力的治愈方式。演员作为受创者,用表演创作的方式诉说创伤事件,直面创伤对自我的伤害,并借由影视作品袒露出私密的创伤体验,以此达到超越恐惧和痛苦,回归自我认同。贾玲以演员、导演的双重身份,通过对影片的艺术创作,部分地治愈了生命中的创伤。一方面,真实的创伤经历赋予了影片真实的创作背景、为角色提供了更为复杂深刻的情绪记忆素材,使表演所传达的情绪记忆更为细腻和具体;另一方面,用自我的创伤经历进行艺术的再创作、重构生命故事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仅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建过去,与自我和解的治愈过程。
结语
“创伤”作为一个现代性话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如影随形,并在当下,越来越多地成为众多现实主义影视题材的创作母题。创伤记忆并非不可表征,影像作为一种记录的手段,通过呈现这一动作与观众的精神世界相连接,承担起呼唤记忆、治愈创伤的责任。而影视表演所传达情绪记忆,就如同一份可感知的证词。一方面,它见证着创伤的存在,借由其共情性予以创伤记忆最为感性地表达。另一方面,它又具备着复原的力量,用对集体或个体创伤记忆的回应,寻找着可知可感可诉的治愈通道。
【注释】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周颖.创伤视角下石黑一雄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3 钱国英.情绪记忆的特点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2.
4 保尔·艾达罗夫.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概念“情绪记忆”(下)[J].陈世雄译.福建艺术,2022(9).
5 朱迪恩·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30.
6 毕苏羽.呈现与治愈:阿伦·雷乃电影中创伤记忆的视觉化表达[J].当代电影,2022(7).
7 舒宗文.浅析戏剧表演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J].当代戏剧,2023(6).
8 尚必武.创伤·记忆·叙述疗法——评莫里森新作《慈悲》[J].国外文学,2011(3).
9 张德明.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刘金.“情绪记忆”辨析——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李·斯特拉斯伯格[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23(03).
11同10.
12邓明昱.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研究新进展(DSM-5 新标准)[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05).
13谷音.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阿根廷“肮脏战争”小说,[J].外国文学,2020(2).
14同5.
15 Shay,Jonathan.Achilles in Vietnam:Combat Trauma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M].NewYork:Touch -stone,1994.
16 Cathy,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2016.
17张渝婕,吴晓梅.“普通人”的追寻之旅——创伤理论视角下解读电影《绿皮书》[J].名作欣赏.2022(7).
18周颖.创伤视角下石黑一雄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19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