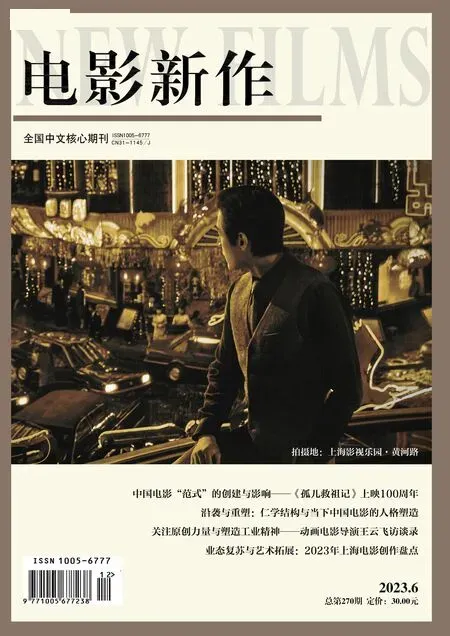“忆”中演“意”:论当代影视表演的身体修辞与文化运作
2023-03-18尹相洁
尹相洁
20世纪20年代,库里肖夫将影像表意的理论观照聚焦于剪辑的语法,莫兹尤辛的表演成为走入观众心理的意义符码,指涉了演员身体在影像发展历史中被遮蔽的境况。随后,美国的方法派表演接续斯氏体系中基于舞台身体开发的解放训练,带领演员从挖掘剧作文本转向“心理现实主义”的自身感知,成为好莱坞明星表演大获成功的关键。从对身体的单向开发发展到对演员官能心理感知力的综合训练,这一更适用于银幕和镜头的表演训练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去戏剧化”的争议浪潮中进入我国,被表演人才培养和主流创作群体奉为圭臬。进入新世纪,伴随计算机合成技术的发展和流媒体影响力的扩大,以感知连结个体与外界的影视表演身体不可避免地在某些类型作品中成为一种图解式的视觉形象,导致作品评分两极化现象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影视作品往往率先引起公众对演员表演和银幕内外演员身体的极大兴趣,最终在口碑与票房或收视率的反馈中达成“完美收官”。问题在于:在观演关系的变动中表演如何对审美主体产生吸引力?在审美主体选择与接受表演的过程中映射出怎样的现实经验?在客观条件不断更进的情况下,表演主体在传统方法和现代技艺的耦合中怎样实现对身体表演范式的差异化处理?
在以詹姆斯·纳雷摩尔为代表的表演修辞表述中,表演修辞是形成表演风格的重要元素,“电影表演的修辞控制着演员的外在形式、表演空间的相对位置以及他们同观众的交流形式”1,文章以当代影视表演身体的修辞共性与视觉表征为文本,钩深索隐当代影视表演外在形态、观演审美主体与身体话语的联动,试图论证两者的互动规律及其潜在的象征性,探讨影视表演超脱于叙事框架和影像整体性限制而作为话语枢纽、媒介文本并走向认知领域的修辞价值所在。
一、显影:当代影视表演中的身体
从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身体是各派理论讨论的热点。“在一个技术迅速扩展的社会中,人的身体体现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方面的这些宏观变化产生的后果是,人类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2在文学身体理论中,身体被认为是“现代性维度上感性体验的首要载体”3,这与莫里斯·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是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是世界的枢纽”异曲同工。“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4显然,作为表演主体的身体并非孤立的语义核心,同时也是处于复杂意义网络中的、影视表演和文化相互影响关系中的身体。学者厉震林提出中国电影表演学派的三大标志性概念,即诗意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体验学派”表演方法和“中和性”表演哲学。其中,诗意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作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表演调性,是由影戏表演、纪实表演和写意表演融汇而成,“既非板块型也非组合型,而是浑然一体,融和天成,在现实主义表演结构之中流淌或淡或浓的诗情”5,由此出发,将身体置于现实主义表演结构之中,可以发现,身体形态在隐形中提供了自足的意蕴图示,在显形中则强化了身体的能动性与多维性,达成表现式的非连贯性在场以及与观众的双向互动。可以说,当代影视表演中身体的显形与隐形共同构成了身体修辞的丰富含义。
(一)隐形身体:话语修辞与戏剧表演
隐形身体表现在身体意识和经验在表演中的投射,指向“体验学派”的表演方法和民族表演美学形态的融合。在表演中,人物的身体以及由身体延伸出去的语言、动作、行动等往往由于与日常生活过于熟悉而被人忽略,成为隐形身体的外在表征方式,并且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场域中存在细微的代际变异,本质上仍是一种戏剧式的演绎方式。
论及其成因,首先是表演历史的理论潮流与创作本体选择偏向的背离。20世纪80年代,电影界经历了“丢掉戏剧的拐杖”的理论热潮,强调“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与之共生的电影表演同样经历了“去戏剧化”的理论扫荡,然而相较于前者在实践创作中推陈出新的影像演变,表演界“去戏剧化”的言论中虽不乏“去表演化”“零度表演”“电影演员活道具论”等言论的发声,在实践创作中的现实情况却与理论主张相背离。电影导演在演员选择时普遍邀请戏剧演员出演电影,戏剧演员逐渐演变为电影表演的主要群体,戏剧技巧极大提升了电影表演的艺术表现力。以第四代导演张暖忻的《青春祭》以及主演李凤绪、冯远征为例,影片展现出了对电影语言的先锋探索,以一种地理空间的自然写实主义和内心独白贯穿全片,使人联想到法国左岸派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而两位主演则贡献了准确、隐形的身体表演。李凤绪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中饰演九姑娘。1985年李凤绪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在读期间参演《青春祭》。李凤绪饰演的女主角李纯在下乡到傣乡插队落户时,破落松垮的外在装扮与傣族姑娘漂亮的筒裙、婀娜的身姿格格不入,到她自发的穿上床单改造的筒裙之后,成了一位“傣族姑娘”,同时也隐喻了女主人公心理转变的萌芽。男主角冯远征则是地道的话剧演员,1985年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在《青春祭》中饰演一位知青。在影片中演员身体的表演以争端的形式展开,柔弱白净的男性青年身体通过与粗犷黝黑的傣族男人的冲突与互殴,成为放大的戏剧效果。其次是纪实表演的深化与演员表演主体性的丧失。影视表演进入第五代电影人的银幕美学实践后,纪实表演在电影人声势浩大的银幕美学突围中深化为“日常”的部分,表演身体在逐渐庞杂和多元的视听技巧构成的、高复合型的影像表达面前淡化至次要地位。以《黄土地》和《老井》为例,村民身体对主人公身体的挟持,表现为沟壑纵横的沉默面庞与重复无止尽的仪式化行动,比如“求雨”“婚礼”抑或是“打井”“迁移”。此处的隐形身体外在表征为时间维度和伦理维度,一方面沟壑纵横的沉默面庞是村民的身体和由身体延伸出去的姿势在特定时刻的固定,因此在《黄土地》中,村民身体的动作和姿势指向“沉默的黄土地”和古老中国;另一方面村民身体和主人公“我”的身体之间是无法斩断的民族情感,银幕之外的审美主体在此意义上获得在场,与“我”视点重合,三者一同建构了一种舞台化的观演关系。欧文戈夫曼认为表演是一种“安排”,“将一个客体的人变成一个人们可以围观而不会让他们感到反感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行为能引起观众的兴趣”。6因此,影片中的群体性表演身体成为朝向镜头的“安排”。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陈述更为明显的指向观演关系:“电影表演是一个剧场性的首语重复,一种为观众布置观看演出场面的物理性安排。”7
总体来说,隐形表演身体在影像整体的叙事框架中易被固化为话语符号,并在观看与接受中获得文化、历史、象征的意味。演员身体成为影片表意的元部件之一,与画框、声音、色彩等意义符码一道置于各自适当的扮演位置。在后续的影像发展与文化转向过程中,隐形身体被推向台前。需要强调的是,影视表演发展中身体的显形并非外在表征对隐形的取代,也不是身体的外在表演框架的单向度嬗变,而是突出一种以区别于其他银幕隐在表演的身体显形,来引起观众的吸引力关注,其与隐形身体的关系是一种敞开的关联性存在。

图1.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二)显形身体:从图像到意象
显形身体表现在身体作为表演主体的能动性与多维性,具有表现现实主义表演特点。在表演中,指向偶发式的影戏表演与再现式的写意表演,演员通过突出展示、模仿表现或非连贯性的身体在场实现与观众的双向互动。
首先,最为突出的显形身体是奇观电影中作为“视觉图像”的身体。在当代电影从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的“文化转向”中,表演不再倾向于塑造“角色”、建构情境,而是将身体的服务重心转向视觉快感和吸引力生产。换言之,作为“视觉图像”的身体的显形具有商品化意味。新世纪以来的影视表演发展中,受通俗文化影响,大批合拍片以多样分化的类型表演范式出现,在中国香港动作片、枪战片、武侠片中显形的动作化身体与暴力化身体持续活跃于影坛,而台湾地区的偶像剧中的表演身体则伴随流媒体平台的选秀机制与粉丝经济的萌生,散佚在当代都市言情剧、古装偶像剧以及仙侠剧中承担消费社会的视觉要求。劳拉·穆尔维给出了这一身体奇观的修辞范畴,即“被凝视的身体”以及“按欲望剪裁的幻觉”8,在性别的表意中,显形身体作为视觉图像走向精神层面——思维图像。
其次,出于对已有身体的模仿,通过重复、拼贴进入表现现实时刻的显形身体。奇观化影视表演向主流的进阶试图以类型为加持,妄图在机械复制中实现情感的价值认同,因而演员身体在表演中往往外化为特定立体的视觉意象使身体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如具有意指的动作、神情、停滞等。“戏剧性电影总是鼓励一种隐蔽的表演方式,即不表演的表演,结果使得那种带有明显表演痕迹的、需要较高表演技巧的表演形成鲜明的表演特色和风格。”9这一方式大多用于历史题材影视表演或传记片中对领袖人物或公众人物的模仿与再创。在日常化和生活化的表演场景中本该隐形的表演身体主动通过依赖于现实互动的意象选择引发关注。诸如众多影视演员对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的身体表演是通过模仿口音、站姿、相似的外形来实现。2021年播出的《觉醒年代》中,饰演青年毛泽东的演员侯京健在表演演讲或抒发胸臆时使用向下甩手的身体动作,这一具带有文化共性和社会记忆的视觉意象足以让荧屏前的观众注意到表演存在的时刻:演员身体在“挥斥方遒”,成为詹姆斯·纳雷摩尔所言的“表演中的表演”。
再次,打破表演连贯性表达的显形身体。与对视觉意象的复制效果类似,打破连贯性表演的显形身体也可视之为“表演中的表演”。此类身体多显现于反派人物和喜剧表演当中。以反派人物为例,作为正反二元对立的邪恶一面,势必要以撒谎、伪装等表演形态来掩盖作恶。身体处理此类表演时需要使观众注意其神情或行为的前后矛盾,因此打破表演连贯性的方式之一是在同一镜头或同一叙事时间内呈现两幅面孔,即演员身体的分裂化处理。比如,《狂飙》中的高启盛在面对哥哥时表现出睿智、早熟但乖巧听话的矛盾面孔,转而在哥哥视线之外的同一叙事画面中面对镜头掏出了自制的手枪,露出了冷血、残忍的另一面。于是我们看到这一显形身体前后的割裂和生成机制源自对亲人的保全与妥协……此类表演作为视觉意象在接下来的叙事进程中不断叠加,直到高启盛在高启强面前最后使用这一“伪装”来表现和掩饰自己即将替对方“牺牲”的结局,这一表演片段在荧屏之外引起广泛热议。现实经验表明,作为显形身体的反派表演对观众的吸引力往往高于正面人物。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与复制固定的视觉意象达成的“表演中的表演”不同,打破表演连贯性瞬间的显形身体具有区别于在场其他偶发性表演的剧场性。“所谓剧场指的是在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中,演员的语言、动作的程式等呈现的偏离生活正常状态的艺术假定性特征。”演员通过前后矛盾或一体两面的身体显形实现“表演中的表演”时,恰好是身体偏离生活正常状态的艺术假定性的时刻,银幕的隔离使表演的剧场形成面对观众的单向度的情景穿透,从而增强了演员身体的在场感,身体的私人表达就此进入公共领域,成功“暴露了电影和社会生活营造统一主体幻象的全过程”。10
不难看出,身体的显影在当代影视表演发展中呈现出修辞意义上的某种共性,隐形身体往往是服务影片意义内核的话语符码,而与作为“视觉图像”的显形身体相比,进入视觉意象并搭建起剧场空间的显形身体表演片段回归了叙事与人物的重心,也回归了古典舞台的自然主义趋向的表演方法。不仅如此,“意象使表演从叙事性转向情感性,或者说是从时间性转向空间性,并触及美学以及人文性。它的造型价值,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表演既不脱离具象的固有形质,又超越而赋予主体的意绪。”11换言之,当代影视表演的身体显影在意象搭建中成为表演修辞的组合文本,产生超出当前叙事框架的多义性,这也是引发审美主体的注意力转移的潜在成因。
二、潜在:意象与记忆的表演序列
那么,身体修辞如何参与当代影视表演的运作?答案是记忆。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强调了记忆的身体维度,“记忆由于不断的操演而成为身体的一种习惯时,过去的记忆就在身体上得到了体现。”12在表演中,记忆被重提也被重塑,身体成为记忆的历史制造所,成为诺拉的“记忆之场”。13郑君里认为,“意象”是演员进入“规定情境”前的一座桥梁,而“藏在我们心中的与角色间接或直接有关的经验、记忆、想象”是进入陌生情境的“熟路”。14由此可见,在当代影视表演中,身体作为具象实体的记忆,通过仪式和习惯的体化联结带有视觉原型的文化意象,成为适用于当代影视表演的修辞文本。接下来,笔者通过截取当下引起关注的作品《狂飙》中具有代表性的表演文本进行分析,试图说明身体修辞在表演内部的运作与多义性。
2023年上半年公布的央八黄金档首播剧榜单中,反黑刑侦剧《狂飙》收视率排名第一,其中由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在2023年抖音阅读量过亿角色中位居榜单最高位。在剧中,张颂文将外显的身体表演与内化的习惯性有机结合,在仪式化的日常行为中体化为“底层的抗争”,形成表演文本在银幕内外对个体记忆的互文与意指。以剧中吃猪脚面的表演片段为例,首先是2001年高启强与安欣吃猪脚面的整段表演文本,以身体的显影和动作的节奏变化为节点,可以将这段表演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吃面开始前,两人坐在桌前,高启强越过调料罐用纸巾把安欣面前的桌子仔细擦干净后才擦自己面前的桌子,随后以同样的行为逻辑为安欣擦筷子。此举显示出作为“卖鱼佬”,面对曾帮助自己的警察时特有的殷切与讨好。在角色的对话中,高启强得知弟弟高启盛被带走审讯,因此加快吃面速度,外侧正反打的近景过肩镜头中可以发现演员的眼神处理始终向下,眼神和加速的吃面动作都在含混敷衍安欣的试探。随后,高启强得知唐小龙也被带走审讯,此时吃完一碗面的高启强稍作停顿,又抬头询问安欣能否再要一碗。此处,张颂文以目光的停顿和动作节奏的转变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并露出看似不好意思的憨厚笑容。
第二部分,在等第二碗面上桌的过程中,安欣开始以审讯的问话方式与高启强交谈,而高启强回话时的动作与神情都呈现出收放自如的稳定感。“审讯”随着第二碗面上桌而结束,高启强看着猪脚面露出了与之前要面时略有不同的笑容——这次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此处,演员对微笑处理的细微差异使我们意识到,刚刚接受审讯时的人物表现出的收放自如是一场身体紧绷的伪装,也就是詹姆斯·纳雷摩尔的“表演中的表演”,表演的身体在此时显形。接下来,高启强开始慢吞吞地讲述“三兄妹与猪脚面的故事”,演员在讲述时眼神向下,看着面却没有吃面。
第三部分,已经意识到高启强在“表演”的安欣站起,高启强的视线跟随安欣的动作,在抬起头的同时向上抬眼,做出整体向上的身体姿态处理,使表演与擦桌子、吃面和讲述故事时的状态形成差异,眼神意味着人物希望得到互动的心理,这种表演技巧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两人的对话关系从第一部分的友好试探,第二部分接受审讯与主动表述,最终来到了对峙与分崩离析的阶段。安欣给出最后一分钟的坦白时间,在下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高启强抬眼看向安欣背后墙上供奉的财神像,回话时眼神向下再次回避了安欣的视线并开始吃第二碗面。在手表提示音响起、面碗被夺时,高启强表现出了抵抗的姿势甚至越过桌子最后夹了几根面条,抬手、仰头由上至下的将面放入口中,并用手抹了把嘴。这个带有挑衅意义的粗鲁举动,意味着高启强开始解除伪装,坦然面对并接受自己身份的转变,并且期望能在与安欣的关系中掌握自主权。
在这段表演文本中,张颂文的身体看似起伏变化的无序状态,一会殷切讨好,一会老实无辜,一会又粗鲁无礼。然而,直到观众视线跟随安欣走出面馆,张颂文以一种自得的松弛姿态摸着肚子,我们意识到,高启强看似被动,但实际上已经掌控了这次吃面与安欣对峙的主动权和危机公关的主动权,表演中无序的身体恰恰是以有序的设计达成的。用詹姆斯·纳雷摩尔的话来说,“这种卓越的自然主义表演效果包含了某种以有序来表现无序的才能”。15最后,高启强说出“安欣,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你个东西”时,作为一个底层的卖鱼商贩,作为个体的抗争在这场表演中赢得了胜利。
剧中,与上述表演文本的互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26集高启强与高启盛吃猪脚面的表演片段。从习惯行为上来看,这两个表演片段在以下几点有所重复:一是要求吃猪脚面的仪式化行为。二是都试图以第二碗猪脚面拖延时间。三是在吃面过程中都讲述了“三兄妹与猪脚面的故事”。四是人物在剧中都处于罪行即将暴露的时刻,要掌握主动权进行“破局”。在纪念式的仪式层面,高启盛与高启强对“猪脚面”故事的讲述指向了两者共享的底层记忆,高启盛在危急时刻的“自爆式破局”则明确涉指高启强的社会地位的“进阶”,因此前后两个表演文本具有仪式重现特征。在身体修辞层面,张颂文和苏小玎共同贡献了卓越的自然主义表演,都以打破连贯性表达的表现法则来实现了“表演中的表演”。表演身体的显形在不同的时间跨度由于高启强位置的颠倒而指向了伦理维度,成为两段表演文本的区别所在。在伪装暴露的时刻,2001年还是卖鱼的高启强的抗争胜利是以走出面馆的身体自由为标志,而高启盛个体抗争的胜利是以身死为标志。换言之,高启盛之死既是个体掌握主动权的抗争胜利,又是在同一表演文本中高启强丧失主动权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表演文本与整部剧所演绎的高启强的底层个体抗争史的叙事框架存在互文关系,甚至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种身体的修辞代替,如高启盛之死在此处产生了对高启强命运的预知和表象的作用。演员在表演时通过外显的身体与下意识对于主动权的习惯性掌控进行结合,在与高启盛饰演者苏小玎产生镜像的互文表演中,高启盛作为高启强抗争的代偿身体走向了死亡。由此,高启强的个体进阶均以服从规则而死去的部分主体意识为代价。前文中死去的是良知与道德,后文中死去的是伦理精神的寄托对象。
另外,张颂文对失去部分主体意识的高启强的表演处理,形成表演文本在银幕之外对底层群体抗争经历的互文与意指。“根据福柯的看法,对于绞刑架(或是任何一种公开展现的惩罚)最有效果的使用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可被许多人观看的景观来呈现。”16在叙事意义上,高启强分裂为两个被现场的警察们围观的角色,角色A是面对弟弟死亡而回归震惊与无措的哥哥,角色B是在场内其他人面前大义灭亲且迎来权力进阶的高启强。演员在表演中以迂回的、节制的肌肉失控与无意识的生理反应,在此处与A角色和B角色都保持了距离。我们首先在表演中看到了由于“震惊”而肌肉失控导致的身体的失序——动作重复、分不清楚方向、想要坐到凳子上却趔趄着打翻了桌子、语无伦次、漏洞百出。在失序的间隙里,张颂文以一种神经质似的条件反射形式频繁将视线投向躺在地上的高启盛,表现在特写镜头中,视点则落在银幕之外。这种穿插设计截至在跌倒被扶起后,张颂文看似轻松地环顾四周林立的“观众”,对由震惊而产生的失控进行了辩护和伪装。

图2.电影《满江红》剧照
总的来说,在记忆与意象的表演运作序列中,叙事层面的底层小人物看似通过抗争掌握了话语权,实则获得了“惩罚”,成为被观看的景观,走向一个被规训的罪恶伪善的身体空壳。在表演层面,通过对被惩罚的身体的有序展示,权力的机制在叙事象征框架的内部得到再现和强化,而演员表演对角色与叙事保持的距离,即有序的设计建立的外化失序的视觉表征,呈现出“一方面被操纵被利用,另一方面表现反抗和干扰”的身体,“那种有反抗有需求,被社会化了的,而且抵制与社会趋同的身躯,它虽然丧失了一定的权力,但充满颠覆的力量”17,从而生成超出叙事象征框架的多义性和文化讯息,与社会文化记忆形成互文与意指。
可见,身体修辞在表演文本内部的运作具有联结和表意作用。在“记忆-意象”的文化运作中,演员在“记忆”中演绎“意象”,“文化从抽象的精神走向可见的人体”18,当代影视表演被引向更为开阔、开放、自主的认知空间。如果我们以身体修辞为话语枢纽,那么表演文本之间的修辞互文,表演文本与整体叙事框架的互文,以及表演文本与银幕之外的互文则说明身体修辞所联结和运作下的当代影视表演文本正作为意义转换的媒介物。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19当代影视表演的意义生成过程也是对现实认知的重塑过程。
三、延拓:当代影视表演的意义生成
依托于视频制作软件的更迭简化与推广使用以及流媒体平台大数据的弹幕交互与即时反馈,当代观众在观演过程中可以任意把一个表演动作剥离为独立存在,或自行重新拼贴,将演员身体以及身体的表演运作解构为修辞文本,用以结构新的“表演文本”,从而生成新的表意,譬如伴随偶像表演和粉丝经济衍生的“cp剪辑”,抑或是影视解说类视频。不得不说,这种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思维展现了观演关系的新型互动。在当代影视表演的意义生成过程中,观众对“文本”的审美认同行为指向对表演修辞的主观认知,也指向当代社会人们不断追求新颖和动态的深层文化逻辑。
首先,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对表演文本奇观审美图示的麻痹化与文化的转向因果相续。回顾影像发展史,在20世纪10年代的特殊历史节点,电影脱离了早期先锋派纯粹的奇观展示,被好莱坞流水线制作的叙事逻辑收编。然而伴随视觉文化时代到来,人们对“新奇和轰动”不断追求,奇观影像重回影视文化的主导形态,并内化到表演当中,表演成为身体显形的“视觉图像”,不再以叙事表意为重心。然“新奇总被更新奇的东西所取代,不断地攫取视觉快感资源又不断地失望”。20马歇尔·麦克卢汉将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与人类的生活经验直接相关,“正是因为持续不断地接受日常使用的技术,所以在我们自身这些形象的关系中,我们才进入了潜意识中知觉和麻木的那喀索斯角色”。21在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观演关系发展中,观众正成为表演的“伺服系统”而对机械复制的“惊奇”逐渐麻木,既无法停止对视觉快感的追求又陷入审美的“陌生化”之中,因“美”的随处可见而无法感知美的存在。这一注意力的悖论状态被乔纳森·克拉里视为“ 知觉的悬置 ”,“主体处于一种既是关注又是关注缺席或延搁的状态中,一方面对于某个吸引力碎片全神贯注,一方面又不断受到竞争性吸引力打扰、震惊而无法全神贯注。”22对此,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一种艺术类别中,历史进程行至某个结点,总会分流出两条道路:一条去往叙事,一条指向媒介本身。”23
作为意义转换的媒介物,当下影视表演正成为一种带有震惊体验的媒介新奇,将深层的文化逻辑以表演的方式直观地再现,从而使表演的修辞性进入审美认知领域。有学者指出:“修辞性认知是以一种思维联想的方式对现实予以模仿并再现”。24在2023年上半年的票房数据中,《满江红》《流浪地球2》位居前二,其中《满江红》以近46亿元位列年度票房冠军。两部影片在题材和类型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指向历史文化,后者指向未来想象。但两部影片对表演的处理存在许多共同点,足以证明身体修辞在运作中对现实认知的联结效果。
从表演层面来看,两部影片都显示出表演在“记忆-意象”运作序列中的再现现实认知的表意作用。其一,两部影片都存在历史与文化记忆层面的原型话语,即“英雄”原型。英雄蕴含了国人久经传颂的民间文化记忆,表现为世俗道德所推崇的“忠义之士”。可以说,“英雄”这一原型话语自带古典主义精神。结合叙事,两部影片塑造的是一个或多个“末日英雄”,如《满江红》“锄奸迷局”中的人物群像,以及《流浪地球2》中的刘培强和图恒宇。在这里,“末日英雄”是一个由个体牵涉集体无意识与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当他抵达神话循环的最低点时,他将经历极致的痛苦并得到报偿。这种胜利可以用英雄与世界神母的交合(神圣婚姻),得到创世之父的认可(向父亲赎罪)以及他自己的神圣化(神化)来呈现。”25在影片中,“末日英雄”的“神化”时刻均以自我的牺牲来达成。因此,末日英雄的胜利并无世俗意义上的有效报偿。不仅如此,从整体原型来看,对“英雄之旅”结局的打破,是将英雄回归到集体和日常的趋向,已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英雄原型。其二,演员对“末日英雄”的典型演绎是以自然主义的戏剧式表演方法展现的,在表现现实的时刻正是身体显形的时刻,身体的修辞表意因此成为剧场性的立体化的视觉意象。《满江红》的张大“刻字”和《流浪地球2》的图恒宇完成最终水下任务的一场“神化”时刻都是如此。其三,表演文本均以表现现实的手法再现“现实认知”,影视表演意义的生成最终达成对记忆的重提与重塑,从而在审美认知层面产生“新奇”体验。《满江红》的表演过程既是对岳飞精忠报国这一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寓言文本的直观再现,也是对岳飞死后《满江红》历史化过程的联想式再现,可被视为“记忆的碎片”被重提的契机。《流浪地球2》则是作为《流浪地球1》的前传出场,以直观再现的形式回答了《流浪地球1》中饱受诟病的“流浪地球计划”的产生问题,这是对已有记忆的重塑与延伸。在当下,伴随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数字化传播机制,记住一切成为可能,然而,“历史的加速度”却导致了生活记忆与历史的断裂。《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表演实现了从原型话语导向现实认知的意义生成过程,在身体修辞重提记忆,表演修辞重塑记忆的时刻完成对断裂和忘却的“历史记忆”认知的“陌生化”的反拨。更进一步,已然实现对现实认知再现与重塑的当代影视表演文本正延伸为一种修辞性认知,由此,当代影视表演主体的修辞逻辑得以走向一种认知的修辞。
综上种种,可见当代影视表演意义的生成是一个修辞化的运作过程。影视表演修辞的迭变和大众审美认知的循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项,而是一个彼此环绕的立体螺旋。在动态演变过程中,身体的显形与隐形共同构成了身体修辞的开放的关联性特质。通过联结“记忆-意象”的文化运作序列,身体修辞将当代影视表演超脱于叙事文本,作为话语枢纽、媒介文本并走向认知领域。当代影视表演的经验表明,带领作品走向公共领域的表演固然有赖于身体对记忆、经验、想象的表现与回应,以及对新兴技术和传统表演方法的深化与耦合,但从表演主体所蕴含的修辞逻辑来看,更重要的是创设一条从原型话语通往现实认知的动态意义渠道,以实现对大众观演审美图式的“陌生化”反拨。
【注释】
1 詹姆斯·纳雷摩尔,谢小红.电影表演的修辞[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1):43.
2[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等译.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8.
3 李凤亮,孔锐才.身体修辞学——文学身体理论的批判与重建[J].天津社会科学,2006(06):90.
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16.
5 厉震林.从历史到现实:构建中国电影表演学派话语体系[J].电影艺术,2020(03):84.
6 谢小红.詹姆斯·纳雷摩尔的电影表演本质论[J].电影艺术,2015(02):126.
7 同6.
8 张红军.电影与新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2.
9 同6.
10 詹姆斯·纳雷摩尔,表达的连贯性和表演中的表演[J].谢小红译.电影艺术,2011(03):95.
11厉震林.意象表演的中国电影本土类型及其美学分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10):62.
12钱力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J].社会学研究,2015,30(06):221.
13[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曹丹红,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8.
14郑君里.角色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63.
15同1,49.
16[英]帕特里克·富尔赖.电影理论新发展[M].李二仕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社,2004:92.
17同16,104.
18[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精神[M].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6.
19[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1.
20 周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J].哲学研究,2001(10):68.
21同19,62.
22[美]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M].沈语冰,贺玉高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10.
23罗雯.被驯化的奇观:VR电影的吸引力与叙事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8):50.
24王雪璞.影像意义的修辞化运作——从电影表演谈起[J].当代电影,2023(04):42.
25[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M].朱侃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