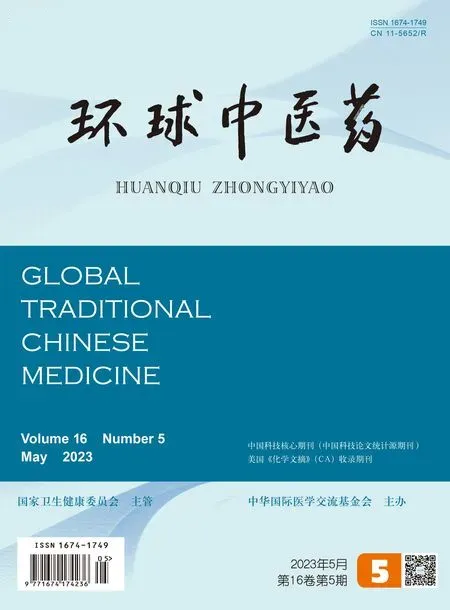基于《临证指南医案》浅析叶天士治疗脾胃病气味配伍应用
2023-03-17刘宪克宋素花
刘宪克 宋素花
叶天士为清代温病学派创立者,其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临证最擅温病时疫痧痘,亦精于内科、妇科、幼科等。叶天士内科尤其擅长脾胃病,其在吸收借鉴李东垣治疗脾胃病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脾胃分治的理论,对脾胃病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对药物气味配伍规律的应用极富特色。笔者通过梳理《临证指南医案》相关案例,不揣鄙陋,总结归纳叶氏治疗脾胃病常用药物气味配伍规律。
1 气味配伍内涵
气味理论最早载于《神农本草经》序录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气味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包括四气“寒热温凉”和五味“酸苦甘辛咸”。“七情”是药物配伍最基本的方式,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七种情况,方剂配伍除了七情配伍之外,一般还有君臣佐使配伍、气味配伍、升降浮沉配伍等。程昭寰等[1]认为方和药最好的结合点是气味配伍,因为有些药经配伍后失其性而减效,而有些药经配伍后而全其性而增效。气味配伍理论最早出自《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明确提出了气味配伍之间的关系,为后世研究气味配伍理论奠定了基础。
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提出:“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说明张仲景已经开始尝试用气味配伍治疗疾病。至金元时期,气味配伍理论越来越受到医家的重视,其中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一书中提到气味配伍制方之法,如“湿制法: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明清时期,张景岳亦提出“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用纯气者,用其动而能行;用纯味者,用其静而能守”,他认为气能行,味能守,气味之间的合理配伍可纠人体气血阴阳之偏性,气味配伍理论逐渐流传开来。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疟》中说:“黄帝论病,本乎四气,其论药方,推气味。”明确指出气味配伍在方剂中的重要作用,将气味配伍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2 脾胃亏虚,甘以补之
甘入脾土,甘味药具有补益和中的功效,叶天士亦言:“甘补药者,气温煦,味甘甜也。”甘药能温煦人体之脾气。因此,叶天士治疗脾胃病,首重甘药,或甘温补气,或辛甘化阳,或酸甘化阴,药物气味配伍的多元化有利于脾胃病的精细化治疗。
2.1甘温益气
《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言“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药能补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亦言“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甘药具有补益的功效,温药能健运,可增强甘补之效,甘温相济,相得益彰[2]。饮食劳倦、思虑易伤脾胃之气,宜用甘温之品,补脾益胃,温运中焦。李东垣受《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理论的启发,重视养护中焦脾胃,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
叶天士提出“脾胃分治”的论断,较之东垣理论更进一步。其中对于脾气虚所致脾升清之功能失常,叶天士常遵东垣甘温益气升提之法,如选用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类,如《临证指南医案·脾胃》王五十案,平素有痰饮,脾阳衰微,“最详东垣,当升降法中求之。人参、白术、羌活、防风、生益智、广皮、炙草、木瓜”[3]121。而对于脾胃气血化生不足证,则用六君子汤、归脾汤、小建中汤等甘温守补之剂,正如叶天士所言“虚热宜用温补,药取味甘气温,温养气血,令其复元”,如炙甘草、益智仁、人参、白术、枣仁等甘温之属。
2.2辛甘化阳
“辛甘化阳”的理论于《黄帝内经》中首次出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提出“气味辛甘发散为阳”,即味辛甘能补阳气。辛味药能通阳;而甘味药能补气,两组气味相伍,即成辛甘化阳法。
叶天士亦言:“遇寒腹痛,用当归桂枝汤,辛甘化阳,以和营卫”,寒入中焦,伤脾胃之阳,即用辛味之药,合甘味之药,多入血分,温通阳气而治[4]。辛味能走窜,正合叶天士“脾阳宜动”的论断,弥补前人不足,选药如辛味之生姜、桂枝、附子等温阳散寒之品,配伍甘味之当归、大枣、炙甘草、黄芪等益气和中之品,即补阳散寒药与益气补虚药同用,以达温中阳之效,如《临证指南医案·脾胃》宣三五案,因饥饿导致脾络虚损,“当养中焦之营,甘以缓之,是其治法:归建中汤”[3]122。脾胃阳虚为由外感寒邪所侵,阳气不得伸扬,或由他脏累及脾胃阳气,阳虚不能温煦机体,须辛甘配伍以扶脾胃之阳。
叶天士在桂枝汤的应用中就提出“辛甘理阳”与“辛甘理营”的治疗理论[5],拓展了辛甘气味配伍的临床使用。桂枝汤由辛甘之桂枝、甘草、生姜与酸甘之芍药、甘草、大枣两组气味配伍组成。辛甘配伍所对应的证为卫阳虚,酸甘配伍所对应的证为营阴虚。临证需要根据对应证灵活化裁,如《临证指南医案·痞》沈二四案:“精气内损……食减中痞……议辛甘理阳可效。”[3]156方用桂枝汤去芍加茯苓。又《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顾五一案:“营虚胃痛,进以辛甘。”[3]382方用桂枝汤去芍加归苓。此两案均为脾胃虚寒,故去芍药,正所谓“辛甘宜加,酸甘宜减”。
2.3酸甘养阴
酸甘化阴是将酸味药与甘味药相合,增强养阴生津之效。酸味药能敛肝养阴,甘味药能补脾生阴,酸甘配伍,即“酸先入肝,甘先入脾”之特性,一敛一柔,增强养阴生津之效,相辅相成,故酸甘养阴法有助于脾胃养阴生津与补肝阴以制肝用之效,肝脾胃同调。
叶天士认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变之所”,脾胃病多责之于肝。酸甘养阴较甘寒养阴增强了养阴之效,可在临床中根据阴伤轻重灵活运用。叶天士提到:“阴虚……胃口弱极,六味苦味未宜,用甘酸化阴法。”正如《临证指南医案·噎膈反胃》苏五四案,饱食伤胃,“五味中喜食酸甘,肝阴胃汁……酸甘两济其阴:乌梅、人参、鲜生地、阿胶、麦冬汁、生白芍”[3]159。而针对单纯胃阴虚证,叶天士提到“胃为阳土,宜凉宜润”,胃主受纳,喜润恶燥,以通降为和,胃阴虚则虚火内生,叶天士倡养胃阴之说,宜用甘寒之品清热生津、润养胃阴以达“胃腑以通为用”,正符合胃之生理特性[6],叶天士常选益胃汤、沙参麦冬汤等甘寒之剂,其药如麦冬汁、鲜生地、梨汁、鲜藕汁、蔗汁、荸荠汁等甘寒之品,乃因甘寒合法,滋而不腻,寒而不伤阴,清补脾胃是也[7]。
众所周知,脾胃喜甘味,若仅仅使用甘味药,不能尽其药性,若能从临床出发,将甘味与其他药味相合使用,可最大程度发挥甘补之效,且将药味合理配伍,可以减少药物的使用以合“药简力专”的中医理论。
3 气机不调,苦以降之
苦味药具有泄热降气之效,胃以通降为本,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苦能通降气机。脾胃病中肝乘脾胃占绝大多数,苦辛通降法治疗肝郁胃腑不通,配以酸苦泄热,舒肝、柔肝、降气、通气同治。
3.1苦辛通降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阳明之复, 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首次提出调理中焦辛温药和苦寒药同用。辛开与苦降两组气味在作用上相互配合,相互照应,用之得当,则阴阳相和,疾病乃愈[8]。《素问·藏气法时论篇》亦言“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即苦能燥湿,且辛味药有醒脾之功,所以辛苦相伍有醒脾燥湿之用[9]。
苦辛通降法可使一身气机流动,腑以通为补,叶天士谓其“阳明辛热宣通”“胃阳不旺,浊阴内生”,治以采用辛温苦降法,辛可升可发可行可散,苦能降能通能泄,合而用之,宣湿祛浊,升降气机,通调寒热。不再仅仅使用升麻、柴胡、苏子、赭石、牡蛎等具有升降作用的药物,而是用苦辛气味配伍药物,治疗简单灵活,且对人体伤害最小。叶天士亦明确提到“苦降能驱热除湿,辛通能开气宣浊”,并据此运用辛温行气苦降之品,辛味药常用半夏、干姜、香附、草果等开气宣浊之品;苦味药常用黄芩、黄连、枳实、杏仁等驱热除湿之类,说明湿热证与脾胃升降气机关系紧密,故苦辛通降法能开气机、降浊气[10],正如《临证指南医案·痞》周案,外感暑湿又加动怒伤肝致呕吐蛔虫,“议以开痞方法。泻心汤去参、甘,加枳实、白芍”[3]154。半夏泻心汤为张仲景所创立苦辛通降之代表方,将辛热药与苦寒药相伍,二者相反相成,平衡阴阳。此案,叶天士变通泻心汤,较之原方宣通气机之力更强,以达“胃以通为补”之意。
叶天士调治中焦气机常化裁半夏泻心汤,该方由苦寒之黄芩、黄连和辛温之半夏、干姜和甘温之人参、甘草、大枣三组气味配伍而成。若湿郁中焦,胃气不虚,则去掉甘温之药;若痞塞严重,则加重辛开或苦寒之品,宣畅中上二焦,如枳实、杏仁等类,或又佐以甘渗之品如茯苓、泽泻等渗湿通利下焦,并据此制订出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甘草大枣加枳实生姜方、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甘草大枣加枳实杏仁茯苓泽泻方等,实乃叶天士活用经方之典范。
3.2酸苦泄热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酸苦涌泄为阴。”即味酸苦能泄热降气。张仲景最早将酸苦泄热法应用于临床,如乌梅丸、黄连阿胶汤等。
叶天士进一步发挥,在其《临证指南医案》“木乘土篇”有大量应用此法的医案[11],不再像仲景局限某一经病的治疗,而将其拓展到脾胃病的治疗。叶天士认为“肝木横逆,胃土必伤”,胃土患病,宜从肝来论治。他提到:“冲阳上犯,治以镇逆,佐以酸苦泄热。”酸苦多泄厥阴之热,俾肝降则胃复。叶天士亦言“胃被肝乘,法当补胃,但胃属腑阳,凡六腑以通为补,黄连味苦能降”“芍药酸寒,能泄土中木乘,又能和阴止痛,梅占先春,花发最早,得少阳生气,非酸敛之收药,得连楝苦寒,内经所谓酸苦泄热也”,正如《临证指南医案·呕吐》钱三七案,呕吐食不下,头胀胃脘郁闭,“议用苦辛降逆,酸苦泄热。不加嗔怒,胃和可愈。川连、半夏、姜汁、川楝子皮、乌梅、广皮白”[3]165。
苦味药有泄热,燥湿、存阴的功效,若与酸味药配伍,则增强泄热存阴之效;若与辛味药相合,则增强宣通气机与祛湿之力,脾胃病为寒热错杂多见,辛开苦降法寒热相调,为中医“和法”的典型应用。
4 脾胃湿阻,芳淡祛湿
湿邪阻遏脾胃气机,芳香药具有上宣之效,淡渗具有下利之效,药性和缓,芳香药与淡渗药不仅具有化湿之效,同时一上一下兼具调畅脾胃气机之功,可谓一石二鸟。
4.1芳香化湿
《素问·金匮真言论篇》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臭香。”脾病气味为香,故香味可入脾土。
叶天士在临床中屡次证实了芳香健胃悦脾的作用,并提出了“芳香逐秽,以疏中宫”的论点。他亦提到“土爱暖而喜芳香”,若中焦湿邪内伏,脾不健运,清阳不升,多选用如省头草、麦仁、陈皮、藿香、肉豆蔻等芳香之药祛湿宣中宫,因芳香药通过其芳香之性斡旋中焦气机并醒脾化湿,此乃脾胃纳运相调是也,正如《临证指南医案·脾胃》云某二四案,愈后胃气未复,“不饥少纳,姑与清养。鲜省头草三钱,白大麦仁五钱,新会皮一钱,陈半夏曲一钱,川斛三钱,乌梅五分”[3]118。
4.2淡渗利湿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湿淫所胜……以淡泄之”,运用淡味药渗利湿邪。叶天士亦言“淡渗通泄气分”“淡渗消其湿热”。淡味药不仅渗泄湿邪,亦可通泄气分以宣畅气机。《温热论》亦提到:“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湿邪秽浊易窃踞中焦,有碍脾胃气机运行之虞。叶天士在临床治疗脾胃湿热证,多以芳香化湿与淡渗利湿相合运用。常用芳香化湿之品如藿香(梗)、佩兰、白蔻仁等,淡渗利湿通泄之药如茯苓、薏苡仁、泽泻、猪苓、通草、滑石等[12]。芳香化湿与淡渗利湿同用,可增强祛湿效果,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泄泻》杨案,湿伤脾胃,“小便不利,大便溏泄,补脾法中,佐以淡渗,分其阴阳。熟术、茯苓、象牙屑、泽泻、苡仁、广皮、白芍”[3]306。
叶天士治湿倡分消三焦法,变通麻杏苡甘汤,去掉麻黄,用苦温之杏仁开宣上焦以化湿,用甘淡之薏苡仁、茯苓等淡渗下焦以利湿,加白蔻仁、藿香等芳香之类温燥中焦以化湿,正如《温热论》云:“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
淡味药和芳香药都可祛湿,可用于湿温初起,或是在补脾胃的同时加上淡味或芳香药,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若脾湿严重则可配辛开苦降之法,增强通宣祛湿之力。
5 寒伤胃络,辛以通络
辛味药具有宣通之效,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的观点,络病为久病不愈入络导致,非辛之走窜而不能达,再配伍活血药,以逐络病之瘀。叶天士由辛润通络衍生出辛香、辛温通络等配伍规律,可谓量体裁衣,体现了中医辨证之精微的特色。
5.1辛润通络
辛润通络即以辛味药与润燥通络药相合而成,治以气血瘀滞兼有化燥伤阴的络脉病证。辛可宣通气机,润可逐瘀润燥通络。
叶天士指出“宜通血络润补,勿投燥热劫液”,治疗脾胃病重养胃阴,因“胃喜濡润”是也。叶天士认为辛味药与润燥通络之品相互配伍,既可“通”又可“润”,通而不伤正,润而不壅滞。常选桂枝、干姜、葱管等辛开类,配合当归、桃仁等润燥通络类,以达辛不破气、润不滋腻之功[13],正如《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高案,胃痛久而不愈,胃络瘀痹,“治在血分。血络瘀痹。桃仁、当归、桂枝、茯神、远志、炙草”[3]384。
5.2辛香通络
辛香通络由性味辛香走窜之品配以活血通络药组成,用于治疗寒气入络或气血瘀滞的络脉病证。辛香走窜,可宣通经隧之壅滞,配以活血药可通络消瘀,共成辛香通络法。
《临证指南医案》总结出“病久入络,久病频发之恙,必伤及络,乃聚血之所,久病必瘀闭”的络病病理特点,根据“腑病当以通为用”的理论,对胃之络病而言则应以“通络”为其治疗原则,故叶天士提出“攻坚垒,佐以辛香,是络病大旨”等治络病之法,即用辛香走窜之药开络病之郁,常选药如桂枝、高良姜、丁香、小茴香、香附等辛香走窜之品,配伍延胡索、五灵脂、蒲黄等活血通络药,辛香入络,祛瘀逐痹。如《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汪五七案,胃痛入络,谷食减少,“姑与辛通法。甜桂枝八分,延胡索一钱,半夏一钱,茯苓三钱,良姜一钱,蜜水煮生姜一钱半”[3]382。脾胃病久治不愈邪气易入络,导致胃络瘀滞,但凡“病在络脉,痛甚于下,浊结有形”之癥瘕,“瘀血积于胃络”之胃痛,均可运用辛香通络法[14]。
5.3辛温通络
辛温通络指由辛温 (热) 药配以活血化瘀药治疗寒湿凝滞所致的络脉郁闭证。非温则寒邪不散,非通则瘀血不除,故以辛温之药入血络荡涤寒湿[15]。
叶天士以“寒痰浊气凝遏,辛温定法”为寒湿入络之治疗大法,常用吴茱萸、高良姜、川乌、川椒等辛温(热)通络之药,配以蒲黄、五灵脂、血竭、莪术、三棱等活血化瘀之品,正如《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吴三七案,呕吐吐涎沫,胃痛时发,久病入络,“议通胃阳,兼制木侮。淡吴萸、良姜、半夏、延胡、炮川乌、茯苓、蒲黄”[3]379。胃腑以通为补,最忌不通,寒湿入胃络,寒湿胶着难解,非辛热之品不能达。
叶天士变通旋覆花汤,创立辛润通络之气味配伍,其中当归、桃仁等为活血润燥之品与辛味药组成辛润通络法,为络病的治疗开创了新的思路,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辛温通络、辛香通络等络病治法。一般胃脘痛为脾胃病中较严重的一种,多为久病不愈,寒入血络,可根据络病从轻到重分别采用辛润通络、辛香通络、辛温通络之法,辨证用药更精准。
辛味药具有行气活血的功效,辛味药与不同性味的药相合在脾胃病中产生的效能不同,若与甘味药相伍则可补脾阳;若与苦味药相合,则可通气燥湿;若与活血药相合,则将辛味药通络之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6 小结
叶天士熟谙经典,以《内经》药物气味理论及气味与脏腑、病证关系为门径,精研常用方剂尤其是经方所寓之法并灵活变通应用于脾胃病的临床辨治中。其创新性提出的“辛甘理阳”“辛甘理营”“辛润通络”“苦辛开泄湿热”“甘寒滋阴生津”“酸甘化阴”“酸苦泄热”等气味配伍诸法与理论,对后世临床辨治脾胃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