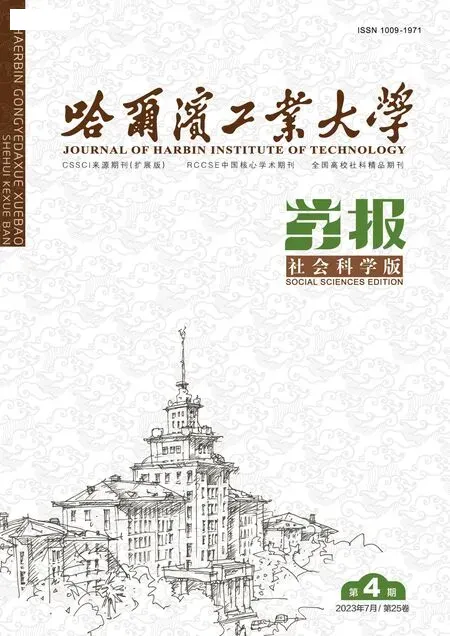《左传》灾害书写的共生文化思想
2023-03-17唐梵凌
唐梵凌
(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6)
引 言
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疫灾从另一个维度将生态环境问题全方位突显了出来,并吁求探求其根本的解决之道。 当世人类要能真正走出疫灾场域[1]化的“人类世危机”[2],需要史鉴的智慧。 中国不仅具有数千年文明史,更有数千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3]的存在智慧,这源于“我国灾害之多, 罕有其匹”[4]的历史。 《左传》这部鲁国史,从公元前722 年到公元前468 年这254年中,其丰年记载仅两次,即《桓公三年》“有年”和《宣公三年》书“大有年”①在古代,丰收意为五谷皆熟,“有年”就是五谷皆熟,丰收;“大有年”,就是五谷大熟,指大丰收。,但对重大灾害的记载和书写却有114 次之多。 《左传》对灾害的书写,融进了古人对灾害的存在论思考,体现“自然、社会、人”共生存在的思想和文化精神。 这一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共生存在的思想和文化精神应成为当世人类如何与自然相处的智慧。 但《左传》记载的环境生态智慧,却至今未得很好的挖掘。 CNKI 数据库显示,抉发《左传》中生态环境智慧的专门文献仅四篇,即《从〈左传〉“雩礼”看春秋时期的生态变化》(王春阳,2004)、《〈左传〉生态环境思想解读》(李飞、严耕,2010)、《〈左传〉,用一株兰花发出生态警示》(刘隆有,2012)和《〈春秋左传〉灾害书写初探》(李伟,2014),均没有涉及《左传》灾害书写对“自然、社会、人”的共生存在思考,而“自然、社会、人”的共生存在思想则是《左传》丰富的生态环境智慧的精髓。抉发古人思考“人与天调”的生存问题所形成的“自然、社会、人”的共生存在思想,或可为当世生态环境的生境重建②有关于“环境生境”和“生境重建”的系统思考,可参见唐代兴《气候失律的伦理》(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恢复气候的路径》(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和《环境治理学探索》(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提供其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
一、《左传》书写灾害的共生视野和文化原则
《左传》记载灾害时,对“灾害”一语有严格界定:“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左传·宣公十六年》,以下皆只写卷名)成周城里的讲武临观之所着火了,但由于是人为造成的“害”,只能称“人火”,不能称“灾”。“人火”之所以非“灾”而是“害”,是因为它与自然无关,所违背的不是自然律,而是存在安全的社会律;“灾”却是自然使然造成的害或人违背自然的律法造成的害。 仅自然使然言,“‘灾’和‘害’分别指涉不同事物:灾,指造成对人(类)的伤害的自然现象或事件;害,指特定的自然现象或事件产生、爆发造成对人的伤害,影响了人的安全存在和有序生活。 从自然观,灾与害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因为自然运动不存在害或非害的问题,将某些自然运动现象定义为‘灾’并继而将其视为‘害’,是人的主观作为:在人看来,自然界启动自调节方式造成的环境变化,无意地给人类造成了安全存在的阻碍或有序生活的困难,就既是‘灾’,也是‘害’。”[5]《左传》所书的“灾害”,不仅是如上意义的,而且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形成其书写“灾害”不可违背的原则或不逾越的章法,以突出自然、社会、人的共生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讲,《左传》对“灾”“害”的辨别和对“灾害”书写所遵循的“时失则书”、“不时则书”和“无灾不书”的基本原则,贯穿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相共生的思想。
(一)时失则书
《经》: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 (《隐公九年》)
《传》: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 书,时失也。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平地尺为大雪。(《隐公九年》)
史官书写所发生的事以备后鉴,涉及自然现象时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记录异动自然现象不能无巨细,一定要选择。 一旦涉及选择,就需要确定其鉴别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凡由节候或天时不正引发的自然灾害,必书。 它由“书始也”明确规定:孔颖达疏“书,时失也”,即“夏之正月,微阳始出未可震雷,既震雷,又不当大雨雪,故皆为时失。”[6]1734这里的“时失”,不仅指节候不得其正,更指天时不正常。 由此,能够入书于史的自然现象,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凡是有违节候天时的异动自然现象,可入书于史。 比如非震雷时节的阳春三月,却震雷滚滚,这种自然现象是违反时节的;又比如阳春三月,应该是“雨霏霏”时节却下大雨雪,这种自然现象体现天时不正常。
在古人看来,凡是违反节候和天时的自然现象,都是反常异动现象。 其实,自然界出现违反节候和天时的异动现象,只是自然世界自我调节运动,很属正常,只有当这种有违节候和天时的自然运动造成了对人间生活的严重干扰,比如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财物损害,或威胁人的生存安全等危害时,它就变成了人类生活之灾,就需要记载入史。 比如所书之“霖”,久雨:“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6]1734古人言“大雪”,也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即平地积雪深尺者,乃“大雪”,这种尺深的大雪如降于春三月,自然是时失,所以要书之。 由此不难看出“失时则书”原则,对“书写”做了两个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规定:第一,所书写的对象必须是违反节候或天时的异动现象;第二,这一违反节候或天时的异动现象,一定给人和人间社会造成了实际的危害。 合言之,只有当引发或造成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之共生存在的生境状态遭受干扰或破坏的“失时”现象,才是史书要记载的“灾害”。
(二)不时则书
夏,城郎,书,不时也。 (《隐公九年》)
秋,大雩,书,不时也。 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 过则书。(《桓公五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因节候不正或天时不正造成的“时失”现象,都指自然自我调节其失律的运动造成人类生存不适应的反应,《左传》将这种难以适应的异动自然现象和由此造成的损害、危害称之为灾害。 与此相反,《左传》所总结出来的“不时”现象,却是指人类生存过程中因为不遵守自然的律法并有违自然规律所造成的灾害、灾祸。
《左传》记载了“不时”的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违时。 在完全受制于气候和地理环境来从事农业种植为生的古代,违时是指有违农时,妨碍生产,由此造成意外的损失或相关灾害。 比如,周历的夏季实是农人忙于耕种的春季,鲁隐公却征调民力修筑郎城,史官书之“不时也”,以为后鉴,因为春播秋收之时征调民力既有逆农忙节时,也违自然规律,往往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灾害。
第二种现象是过时,即错过时节。 违时,是指该为当为之事时却不为,以此错过最佳为时而造成意外的破坏人与自然或社会与环境共生的后果。 相反,错时,是指在不当为之时为当为之事,以此造成人与自然或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存在关系的颠倒。 比如祭祀山川自然,自有时节:求雨祭祀应在入夏之初,如行秋祭则是过时;烝祭应该在夏历十月举行,如前提到夏历五月就是错其时。 因为四季之祭,表达其敬畏和感恩自然的诚意不同,呈现出来的与自然的关联亦有时节的区别:进入春季,昆虫惊动行郊祭以祈谷;进入夏季,角亢二宿出现行雩祭以祈雨;进入秋季,寒气降临行尝祭以祈泽后,入冬之后,昆虫蛰伏行烝祭以报祖恩。 凡错过时节而行祭,既有违自然规律,更是丧失赤诚的敬畏和感恩之心。 在浅表的唯物质论层面,人们可将古代的祭祀视为迷信,但万物皆存在于自然世界里,人类作为自然之子,也与自然血肉相联,正如马克思所讲,“人(和动物一样),依赖于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范围也就越广阔。”[7]另一方面,“自然的历史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过程,历史的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创造过程,二者统一于人类发展的历史。”[8]人向自然生成和自然向人生成的相向敞开,就是自然与人的同一性。 “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9]人是依赖于自然而存在,人获取生存的全部资源都由自然提供,人必须敬畏自然和感恩自然,就是遵时节守律令而得生生。 人敬畏和感恩自然,既需要神圣的仪式,更要有固定的时节,这样才体现至诚之心和挚诚之情。 敬畏和感恩自然的非时节化,必然导致随意性;而随意性的行为始终体现私我的重要和根本,将所敬畏和感恩的对象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形成表面敬畏和感恩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的行为在本质上体现人与自然的貌合神离。 在敬畏和感恩方面都可以貌合神离地“过”,那还有什么不可以任意地作为呢? 其结果必然形成违时悖律而窘迫其生。 这是《左传》将其“过时”视为是“灾”而书之的根本原因。
“不时则书”原则中之“时”,既有时间意义的“得时”或“恰到好处”之义,更有空间意义的“限度”或“边界”之义。 “不时”,是指既违背了人与自然或社会与环境共生之恰到好处的“得时”法则,也违背了人与自然或环境与社会共生的边界与限度法则,所以必然造成灾害,所以,《左传》为警示后来者而不得不书。
(三)无灾不书
整体观之,“时失则书”和“不时则书”分别从灾害形成的原因论,可看成是灾害书写的条件原则或分原则;“无灾不书”则是从灾害造成结果论,可看成是灾害书写的后果原则,亦可理解为灾害书写的总原则。 因而,“无灾不书”的正面表述是“有灾必书”。 “有灾必书”之“灾”,首先由“时失”所界定,即凡是节候不正和天时不正所造成的一切形式的自然灾害,都要书;其次由“不时”所界定,即凡是人为地违背时节和规律的行为所造成的无论来自于自然方面的灾害、灾祸,还是来自于社会方面的灾害、灾祸,都应该书。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僖公三年》)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襄公元年》)
秋,有蜚,为灾也。 凡物,不为灾,不书。(《庄公二十九年》)
从僖公二年十月到三年五月,一直不雨,虽然干旱的时间如此之长,但因为没有造成灾害,也不能称之为“旱”。 “蜚”,是一种吃稻花的小飞虫,即蜚盘虫,它在二百多年春秋史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襄公元年,因为没有造成灾害,所以不予记载;另一次出现在庄公二十九年,因为造成了灾害,所以被记载。
二、《左传》书写灾害的共生存在宗旨
《左传》共书写了114 件灾害事件,不仅表明春秋时灾害爆发的状况,更蕴含古人将灾害入史的根本考虑或鉴后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比如已有学者通过灾害的分类学探讨来揭示《左传》书写灾害的基本思想。 李飞和严耕合撰的《〈左传〉生态环境思想解读》将《左传》所书的灾害事件分成雨水和冰雹、干旱、病虫、地震和异常五类[10];李伟《〈春秋左传〉灾害书写初探》将其划分为气候灾害、昆虫灾害、地理灾害、牵连灾害和战争带来的灾害五大类十七小类, 并予以归类分析[11]。 学者们对灾害做类分体现出来的差异,源于所选择的类分标准和依据不同,故而其探讨重心和目标指向也不同,比如前者对灾害的类分,意在于探讨春秋时期环境生态的变化以及古人的应对之策,并以此呈现生态思想在春秋的萌芽和其生态思想的当世意义。 后者对同样的灾害事件予以不同的类分,意在于探讨《左传》书写灾害的背景、方法及其蕴意。 本文从探讨《左传》书写灾害的“时失则书”、“不时则书”和“无灾不书”所展示的共生视野和文化原则入手,来揭示《左传》书写灾害的共生存在之思想文化宗旨,即合时地存在和居安思危地生存。
(一)合时地存在
《左传》书写灾害的共生存在之首要思想文化宗旨,是合时地存在。 它主要通过灾害书写的原则呈现出来。 《左传》书写灾害的三大原则,贯穿一个“时”字。 如前所述,这个“时”字既表节候,更表天时。 节候与天时,二者本是一个“东西”,即自然运动的规律,更抽象地讲,是自然运动所依据的法则、律令,或以此所显现出来的天道。
节候是自然运动的规律、法则、律令或者说天道的微观(具体)呈现,因为“节候”作为一纪年概念,指以年为计量单位的自然运动节奏,被历法描述为春夏秋冬四季及更具体的二十四节气。 《左传》里用以表灾害书写的“时失”和“不时”,都是指自然的异动(所引发的灾害)都源于不合节候:不合节候,就是不合纪年的四季节奏及其节气,简言之,就是不合时;反之,合时便是合律,也是合道合理。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曰旱,不为灾也。 (《僖公三年》)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秋,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 凡天灾,有币,无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庄公二十五年》)
僖公三年春季无雨,直到夏六月才下雨,正是“久旱逢甘霖”,所以正合时,没有造成灾害。 庄公二十五年,夏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秋天发生大火。 应对这两起自然灾害,采取击鼓、用牺牲来祭祀社神甚至城门门神,都属于违礼、不合礼的行为。 对于古人言,不合礼之实质,是既不合时,也不合律、不合道。
《左传》书写灾害的合时的思想,实质上是合自然律、合天道规律的思想。 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灾异方面,而且在其它生活方面也要求合时。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 书,不时也。 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庄公二十九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従,乃免牲。 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 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従也。”(《襄公七年》)
庄公二十九年春季新造马厩之所以不合时,是因为万物生养运动均要遵从自然规律,符合天道运行法则。 马是“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的牲畜。 所谓“日中”,指春分和秋分,春分时节,百草始繁,马应牧于垌野;秋分时节,农事始藏,水寒草枯,马皆还厩。 所以,春“新作延厩”,不仅不时,而且违时。 这个时,具体讲是季节、节候,大而言之,是气候周期性变换运动形成地球气候,产生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律,本质上是天宇运动的律法,或者说天道。
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律所呈现出来的律法和天道,也是时,是节候的抽象形态,即天时。 与节候不同,天时是自然运动的规律、法则、律令或者说天道的宏观(或曰抽象)呈现,因为天时是一个天文学描述,指以天(宇宙)为描述对象来展示天体(星系)运动的节奏,它被历法描述为天体(星系)运行的轨迹、轨道,在《左传》里,不少有关于星系有规律的正常运行或逆规律运动的探讨,并将其正反运动作为依据来讨论邦正国安,应该如何来正人君得失。
在《左传》里“天时”之“天”,实指自然,它具象为气候变换运动;“天时”之“时”,实指自然规律、法则、律令或天道,具体到气候运动就是其变换的周期性,即气候周期性变换运动实是自然规律、法则、律令或天道运作的具体状态和进程。 天时,是指天道运作有时,自然运动合律,具象为气候周期性变换,而气候的周期性变换运动则具体呈现为历法、节侯、节气。 所以,天时所强调者仍然是一个“时”字,灾害生发于天时不正,实指自然运行不合时,具体地讲,就是气候丧失周期性变换运动规律。 从根本讲,一切形式和形态的环境灾害,都与气候失律相关;而气候的失律,不仅是失序,本质上是失时[12]22-60。
(二)居安思危地生存
《左传》将灾害入史,是要以为后人鉴。 《左传》通过书写灾害从两个根本的方面以为后鉴:一是希望通过灾害书写而引导后人能够合时地存在,即遵自然律法和循天道地存在。 二是希望通过灾害书写而警示后人学会居安思危地生存。
《书》曰:“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襄公十一年》)
居住于安定、安全的环境里,要时刻想到危机的来临。 对于人来讲,其安全和安定的环境,当然指人所组成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但其土壤却是自然环境,是自然。 存在于自然世界中,暂时没有危险、危机,并不等于一直没有危险、危机,相反,一切相对安定、安全的自然环境始终潜伏着危机和危险,避免其危机、危险降临的根本生存姿态,就是居安思危。 合时地存在意识,是居安思危的认知前提。 当具备合时地存在的认识,居安思危的的首要方面就是认知自然,认知环境,掌握自然运行及其变化的规律。 这方面的努力方式,就是对气象的监测与预报。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平秩南为,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厥民隩,鸟兽鹬毛。 (《尚书·尧典》)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 而书,礼也。 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僖公五年》)
古代没有气象学,也没有气候局这样的社会机构,但却有专门负责监测气象变化和天象运动的官职。 《尧典》中的羲和、羲仲、和仲、和叔就是尧所任命的天官,专门负责观测四方天象、制定历法、掌握气象变化来构建秩序、规范生活、引导生产。 对气象的监测和对天象的认知与了解,不仅有专职于事,而且至于春秋,观测气象变化和天象运动,也成为邦国君主所亲之事:僖公五年周历正月初一冬至日,鲁僖公行太庙告朔并处理完政事后,登观台遥望云气变化。 这是因为凡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以及立春立夏和立秋立冬之日,要特别记载云气变化,以为可能发生的灾害做准备。
二十八年春,无冰。 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 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 蛇乘龙。 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 玄枵,虚中也。 枵,秏名也。 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襄公二十八年》)
古人之观测气象变化和天象运动来预测人间灾祸及年成丰匮,因为气候的周期性变换运动始终直接影响地温和气温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影响地域性的生物种群、群落的繁衍生息,更影响到地域性存在的人的群居化生产、生活。 从根本讲,气候的周期性变换运动,实际上是地球与宇宙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虽然有规律,但要受到三个天文因素的影响。 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地球轨道偏心率的变化、地球轨道所描绘出来的平面有关的地球两极轴倾斜的变化以及二分点的前行(岁差,précession)[13]。 在这三个要素中,对气候周期性变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地球轨道运行所形成的偏心率,这源于地球本身的椭圆体结构,即地球的轨道与并非圆形的椭圆之间所形成的偏心率,“会在圆(偏心率为零)到6%之间变化……偏心率的变化使得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也随之改变。”[14]这种改变将产生两种结果状态:如果地球轨道是圆形的,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就远,地球表面接收到的能量将会减少,气候就由此趋冷;反之,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越近,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量将会增多,气候亦因此趋于变暖。[12]26古人虽没有今天的科学知识,但却基于经验而建立起一套朴素的认知地球与宇宙互动变化规律及其发现天象反常变化的机制,他们根据具体的地域状况来划分宇宙星系中的星宿,将宇宙星系运动中星宿指派给地域化生存的邦国,使之互为对应,然后将该天区发生的天象运动的异常变化作为对应地域化生存的吉凶预兆。这就是襄公二十八年夏历春,鲁大夫梓慎根据本该结冰而无冰的地域气候,反推其对应的天象变化,然后以其无冰相应的变化天象来推测宋、郑二国必有饥荒。 因为夏历春,正是隆冬。隆冬无冰,却是地温暖,地温暖源于地球与宇宙互动过程中太阳距离地球近所致,由于冬暖无冰,既使土壤中害虫得以存活,又导致大地干燥,既影响耕种,也影响种植的作物不能健壮生长,生产自然减产,饥荒不可避免。
大雨雹。 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 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 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 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 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 火出而毕赋。 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 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 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不出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 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 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 雹之为灾,谁能御之?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昭公四年》)
在古人看来,地球与宇宙互动,既形成天象的有序运动,也因为地球的偏心率等天文因素而影响天象的异常运动,但无论是有序运动还是异常运动,都表现为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或非周期性变化,这就是可为人们观测到的气象变化,并可能根据气象变化的规律或异常来应对生存,即既可根据气象变化的规律性态势来安排生产、政务和生活,也可根据气象变化的异常性态势来预防性安排生产、政务和生活,以避免灾害或灾害发生,尽可能减少灾害。 这就是鲁正卿执政大夫季武子与其家臣申丰关于雹灾是否可防御的问答:雹灾,甚至所有“时不”(节候不正和天象不正)产生的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 但几乎所有的自然之灾都可通过预防而使之将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可以化灾为利[15]。 申丰就雹灾大谈何以能化而用之的道理:化灾为用,灾就变成了利;缺乏化灾为用的想法、意愿和行动努力,所有的灾都是害,甚至可以使之成为大害。
然而,《左传》通过记载季武子与家臣之间的应对,其意旨所归并不在于化灾为用,而是表达“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的思想: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了,既可怕,也不可怕。 这怕与不怕,取决于人君:人君狂妄自持,私欲滋彰,任何自然灾害对于民和邦国来讲,都是不堪承受的灾难。 反之,人君勤勉邦政,心系民生,必为邦为民而居安思危。 人君一旦以居安思危为基本政务,就会“思则有备”,并做到“有备无患”,一切自然之灾都可化而为用以利民利邦,所以虽有灾(雹),不仅不为灾,而且有可能成为邦国之幸和民—人之福。
夏,大旱。 公欲焚巫兀。 臧文仲曰:“非旱备也。 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 巫兀何为? 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従之。 是岁也,饥而不害。 (《僖公二十一年》)
三、《左传》灾害书写的共生存在精神
《左传》书写灾害,不是为灾害而书写灾害,而是通过对灾害的书写,以资引发后人对“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思考。 因而,《左传》对灾害的书写,呈现较为系统的“共生存在”[16]之思想文化精神主要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一)人与自然共生的存在精神
过程论哲学家怀特海在其《科学与近代世界》指出,“西方世界现在遭受着前面三代人有局限的伦理观之苦果……存在两个灾祸:一是对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真实利害关系的忽视;另一是忽视环境内在价值的惯习,而这一价值的重要性在考虑终极目标时是必须权衡的。”[17]怀特海揭示工业社会进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直接的动力机制是物质幸福无限论和自然资源无限论观念,但最后的根源却是人类自我狂妄地淡忘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18]。 但在古代中国,人与天调、天人相生的共同体思想[19]却已得到明显的确立,《左传》通过对灾害的书写阐发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共生存在精神。
晋人谋去故绛。 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 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 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従教,十世之利也。 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 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成公六年》)
晋人计划迁都,众大臣皆曰应将都城迁入郇、瑕二氏居住的地方,理由是那里的封地肥沃富饶,又靠近盐池,有充沛的资源可开发和利用,这既对邦国有利,更能让国君享乐。 唯有新中军将兼仆大夫韩献子反对,其理由有二:迁都的目的,不是有利于开采资源,更不是满足国君当然也包括国人的享乐。 一是要有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实现人的居住与环境共生,因为环境的生生,自然的丰盈,才是邦国长治久安的土壤;二是要有利于引导和教化国民利用厚生,因为“国饶,则民骄佚。 近宝,公室乃贫”。 晋景公最后采纳了韩献子的建议而迁都新田,是因为韩献子的人与自然相生的思想,得到了晋景公的认同。 人与自然共生存在的思想灵魂是利用厚生,因而,利用厚生精神构成人与自然共生存在的本质精神,它在事实上构成春秋时代安邦治国的共识精神。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 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従郑伯以劳诸柤。 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 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 见子产,以马四匹。 见子大叔,以马二匹。 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刈,不抽屋,不强丐。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慁宾。 往来如是。 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昭公六年》)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 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 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 乱政亟行,所以败也。 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 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襄公五年》)
《昭公六年》记载楚公子弃疾为使晋国,路经郑。 郑之三卿子皮、子产、子太叔伴随郑简公在柤地慰劳弃疾,子皮、子产、子太叔皆断言弃疾必将成为楚王,其依据是弃疾懂礼仪,但最为根本的却是弃疾强力推行的这一政令,即“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刈,不抽屋,不强丐。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该政令严格规定采伐有时、有度:有时,指只能在规定的季节采伐;有度,指只能在规定的地域采伐,不能随便放牧、割草、砍柴、伐树。 在自然资源并不匮乏的春秋,弃疾的如此政令,不能用自然资源的保护观念来解释,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环境共生存在的边界约束的思想,这一边界约束思想的精神本质却是节制地存在,其节制存在精神的具备才使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环境相共生的边界约束成为可能。
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共生的边界约束思想和节制精神,并不是弃疾等贤者才有的思想,应该是春秋时代比较普遍的思想。 昭公十六年,郑国大旱,郑君派大夫屠击、祝款、竖柎去桑山祈雨,此三子却为祈雨而砍伐了桑山林木,执政大夫以此“夺之官邑”,理由是“有事于山,蓻山林也。 而斩其木,其罪大矣”(《昭公十六年》)。 天降雨有时,以天地相生为前提。 郑国三大夫因祈雨而砍伐树林的行为,根本不涉及“适时、适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10]的问题,而是破坏了天地相生和人与天调的存在生境,天地相生和人与天调的生境一旦被破坏,人与自然共生的存在根基被拔起,所以这种祈雨伐林的行为“其罪大矣”。
其实,通过《左传》对灾害的书写可以感受到春秋时期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共生思想所张扬出来的以边界约束和利用厚生为实质内涵和根本的共生存在精神,实际上深入人心。 隐公五年(即公元前718 年),鲁隐公准备到鱼台观渔人捕鱼以为乐,被臧僖伯所劝阻:“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隐公五年》)指出狩猎行为本身具有对人与自然共生的环境生境的破坏,虽然狩猎这种自古而来的娱乐方式不可取消,但一定要有时、有度,使自然与生物之间保持生生之态。 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书之“非其地”也,批评周王狩猎逾越天子之地,既不合礼制,更违背狩猎合时合度的原则,孔颖达疏之曰:“则狩于禚、搜于红及比蒲昌间,皆非常地,故书地也。 田狩之地,须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狭,唯在山泽之间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诸侯必于其封内择隙地而为之。”(《桓公三年》)联系僖公三十三年“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 是其诸国各有常狩之处,违其常处,则犯害民物。”(《僖公三十三年》)均强调狩猎必须遵时守度,因为这是地球上生物生息繁殖的保障,生物繁衍生生不息,才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前提。
(二)人与人、邦与邦互济的共生文化精神
综上,《左传》的灾害书写所呈现出来的以利用厚生和边界约束为本质规定和基本内涵的共生存在精神,不仅仅体现人与自然的维度,也体现在人与人、人与邦、邦与邦之间,拓展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精神,即人与人、人与邦、邦与邦之间邦难互济的共生文化精神,它最集中地体现赈灾、援灾方面:
秋,宋大水。 公使吊焉。”(《庄公十一年》)
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 (《定公五年》)
宋国发生洪灾,鲁庄公派使者去吊灾,反映邦国与邦国之“贺福吊灾”的外交礼仪,这种“以吊礼哀祸灾。”(《周礼·大宗伯》)的礼节背后,是大家同存在于一块土地上,灾福共生。 正是这一质朴的共生文化思想,才使当蔡国被楚国包围,民人处于饥困状态,鲁国为之输送粮食,以周济蔡之急难。 并将这种吊灾济难的共生存在思想上升到礼的层面,就形成一种共生存在的礼文化,即礼尚往来的互济文化。 这种以礼尚往来为行为方式、以互济生存为本质诉求的共生存在文化最终通过制度予以定型:“冬,饥。 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庄公二十八年》)生活于春秋晚期有大思想家孔子所言“周监于二代”之“礼”,实际上是天子共主为诸侯邦国制定的一套共守的共生存在的礼文化规范制度,赈灾、济灾被纳入礼的范畴,或者说将邦与邦之间赈灾、济灾纳入“礼”的范畴予以考量,这恰恰是《左传》书写灾害的共生存在思想的另一个维度的体现。
邦与邦之间赈灾、济灾合礼,意在强调三个方面的共生文化诉求:第一,一邦发生灾难,向邻邦告籴,是合邦国之礼的文化精神的;第二,向他邦予以吊灾慰问,也是合邦国之礼的文化精神的;第三,他邦告籴,予以赈济,亦是合邦国之礼的文化精神。 此“三合礼”的文化精神揭示两个方面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共生存在思想: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的邦国不仅在文化、文明、血缘上是天下一家,而且每个邦国都生活存在同一个地球上,存在于具体的地域共同体[19]中,因而,第一,一邦有难,应该众邦相援,这是春秋华夏的邦际文化精神的呈现;第二,同情理解和救济危难的生存精神,这是春秋时代华夏共生共存的普世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得以生成、传播、共享、共运的源头活水,却是人与自然相共生存在的思想和限度存在与生存节制的精神。
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 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 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 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 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 退曰:“君其悔是哉!”(《僖公十四年》)
泰国发生饥荒而乞籴于晋,而晋君拒绝赈灾,却遭到大夫庆郑的激烈反对,指出“幸灾不仁”“何以守国”? 揭示“弃信背邻,患孰恤之? 无信患作,失授必毙”。 庆郑将哀灾、吊灾、济灾上升到邦国的自守层面来讨论,揭示一个道理:“为了自保,为了享受幸福,与一些具有与他同样的欲望、同样厌恶的人同住在社会中。 因为道德学将向他指明,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它将向他证明,在所有的东西中,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20]邦国是由人组成,没有人,何来邦国? 济他邦之民,亦是保本邦之民未来无虞,更是强本邦之生始终无患。 因为天道循环,生老病死、灾祸福荫,均不可测,今日他邦之灾,亦或己邦未来之难。 所以今济他邦灾民,亦是为本邦之民未来避灾支付了一份保险。
(三)人、社会、自然共生的限度生存精神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桓公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 魏子莅政。 ……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 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 (《定公元年》)
桓公七年,鲁桓公为便于围猎,放火焚烧咸丘,逼野兽外逃。 《左传》记录此事,意在批评鲁桓公违反狩猎之“时”“度”原则,揭露人的任性的自由将带来灾难和危机。 任性的自由,既可在人君身上发生,也可在人臣以至于任何人身上表现。鲁定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初七,晋大夫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主持为周天子筑城,但他却将差事交给韩简子和原寿过,自己跑到大陆打猎,并为获取猎物而焚烧草木。 任性的自由,之可以在人身上泛滥,是因为人自身缺乏节制的意识和品质,缺乏人与自然共生的限度生存思想和精神。 正是这种限度生存的思想和精神的缺乏,才引来《左传》的特别关注,书此二事入史,以警示后人引以为鉴。
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邦与邦的共生思想,落实到行为上,就是节制和限度,而节制和限度的生存本质却是相对自由,或曰有限的自由而非任性的自由,构成人的限度生存的内在规定。 以有限的自由为本质规定的节制和限度之于邦国治理,必落实为两个基本方面,即整理田制和军训,前者的基本任务是“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后者的基本任务是“庀赋,数甲兵”和“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襄公二十五年》)并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有序执行和维护。《左传》认为,邦国治理要真做到有节制和有限度,关键在于邦君必须远离任性的自由而具备克己的自由,这要求邦君应有很强的节制能力和限度品质。 邦君要具备很强的节制能力和限度生存品质精神,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能力的具备:
一是邦君应具备明真假、辨善恶、知美丑的能力,这种能力却源于人与自然共生思想的滋养和觉醒。 《左传》记载齐景公弃盅惑行善治,则是这方面的最好说明: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生疥疮并患疟疾,一年未得痊愈。 众诸侯派史来问候,宠臣梁丘据和裔款盅惑齐景公不敬鬼神之罪名杀祝、史,来向诸侯使者解释何以不得痊愈的原因。 晏婴指出此种做法万万不可的理由:“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盐蜃,祈望守之。 县鄙之人,入従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 承嗣大夫,强易其贿。 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 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 私欲养求,不给则应。 民人苦病,夫妇皆诅。 祝有益也,诅亦有损。 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 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齐景公“悦”晏婴之言,“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昭公二十年》)
二是邦君应具备很强的内自省的能力。 鲁庄公十一年,宋国发大水,鲁庄公派遣使臣前去吊灾:“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宋国闵公却深为自责对来使说:“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宋闵公认为宋遭遇特大的洪灾,表面看是天时不正,实际上是自己及治域下的邦民对上天不敬,这种不敬表现为对环境的任性和对自然的无度。 所以,宋闵公深自责以求天恕。 鲁国大夫听到此言大为感叹道:“宋其兴乎。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 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庄公十一年》)
内自省的意识,是节制和限度生存的心理动力;内自省的能力,是节制和限度生存的主体保障。 不管是邦君,还是人臣或者个体生存者,内自省的意识和能力生成的原动力机制,却是共生存在的意愿和思想,没有共生存在的意愿和思想,只具独生的欲求和渴望,无论如何不能自生出节制意识和限度生存的能力。
(四)崇天遵道守律:人与自然共生的思想文化精神依据
以限度生存和节制为基本内涵的共生思想之在春秋形成,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因素的激励:一是自然环境破坏引发人们居安思危。 因为武王灭商封建周,天下一统,生活安定,人口持续增长,各个邦国出台各种政策奖励“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普天之下扩大耕地,开发资源,环境自然遭遇破坏。 比如周成王时期,楚国“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跋渉山林,以事天子。”楚国的发展自然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推动对土地的扩张,同时更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无限度开发、利用,比如楚之云梦犀兕麋鹿、以及楚之江汉的鱼鳖鼋鼍等富饶资源,源源不断地开发为中原诸国利用,形成“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襄公二十六年》)二是人口增长,资源耗竭,必然带动战争,包括中原与四夷之间的战争和诸侯之间的争夺战争。 尤其是西周末以降至于春秋,战争在邦国之间常态化,造成了环境资源的大消耗和自然生态的大破坏。 三是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亦推动社会性的资源开发和环境破坏。
既成昏,晏子受礼。 叔向従之宴,相与语。 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 齐其为陈氏矣! 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 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 釜十则钟。 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 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 山木如市,弗加于山。 鱼盐蜃蛤,弗加于海。 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 国之诸市,屦贱踊贵。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昭公三年》)
《左传》记载叔向与晏子谈论齐晋邦国兴衰,意在揭示邦国兴衰与人君是否节制和有度息息关联。 邦君对权力无节制,必带动财富占有和挥霍的无限度,宫室骄奢淫逸盛行,必然将国家引向无节制的征伐和资源掠夺,最终造成国力衰退,百姓疲惫,道路上饿殍相望,民人怨恨。
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唤醒社会生存及其发展的节制意识和限度思想,节制意识和限度思想的社会性形成,促发遵天循道思想的产生。 这一遵天循道思想通过“礼”得到系统的表达: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 ……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従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 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 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昭公二十五年》)
子大叔与赵简子论礼,将作为人间规训体系的“礼”,上升到其存在论依据层面来认知,指出人间必循之礼的存在论本质,却是“天地之经”。“天地之经”之中的“天地”,即是宇宙和地球;因而,其“天地之经”就是宇宙与地球共生运行的规律、律法、道。 人间社会所循其礼,实是崇(或曰“畏”)天循道守律。 所以,表面看,礼不过是一种构建社会秩序的文化,但本质上却是自然律令和天道法则对人间社会的规训方式。
基于这一崇天循道守律的共生思想,大叔与和医论“礼”,从单纯地解释自然灾害转移到关系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的生变关系的阐述:“晋侯求医于秦。 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 是谓:近女室,疾如蛊。 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良巨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 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 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 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昭公元年》)天地生生被具体地表述为六气的阴阳互动和协调,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成灾;具体到人的身体,过则为疾。 因而,礼,成为“人、社会、自然”共生存在的生生之序,遵礼守礼行礼的生存本质,就是天地共生,人与天调[22]。这是《左传》书写灾害以鉴后世的根本智慧和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