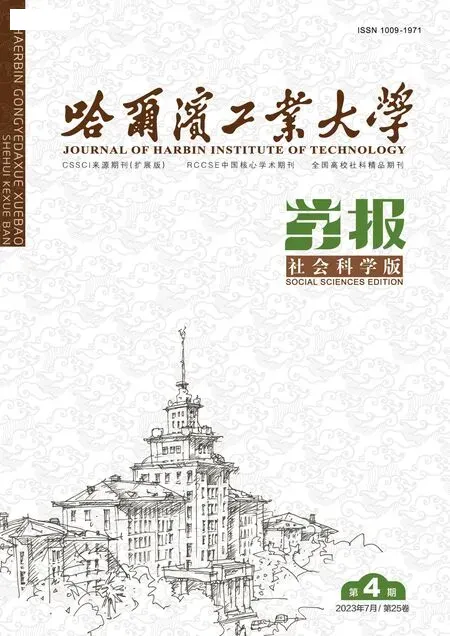女性主义术语的概念演变与汉译历程
2023-03-17栾荷莎
栾荷莎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自清末开始进入中国语境并获得广泛传播,对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乃至现代化进程起到过切实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极为深远。 但迄今为止,女性主义的某些核心术语的汉译并未实现标准化,并存在诸多争议。 “由于术语生长或形成的语境参数较为复杂,加之其跨文化旅行过程中必然遭遇到的语言文化冲突,术语的翻译并非易事,其意义与价值自然也不简单。”[1]女性主义术语在西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与广阔的外延,其概念在历时上具有演进性,在共时上呈现多样性。 而其汉译术语跨越了语际与文化后则呈现出变异性与复杂性。 基于此,本文从话语生成的角度梳理女性主义核心术语的概念演变与汉译流变,揭示中国语境对女性主义术语的吸收、排斥、融合、反思与再创造,以期为总结术语跨文化传播规律,构建女性主义及性别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带来助益与启示。
一、从“女子主义”到“女性主义”权力内涵的“波浪式”传承与接受
(一)“Feminism”概念与名称在西方语境下的发生与历史沿革
英文“feminism”和法文“féminisme”的出现皆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其成为女性主义术语之前,已经存在尚未精准表述出来的观念,后来发展成为“女权”概念。 而先于“女权”概念出现的是“人权”概念。 “人权概念是17、18 世纪一些西方国家学者在若干宣言和法律文件中提出的,提出时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和历史局限性。”[2]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就堂而皇之地把妇女权利排除在外。 为此,Olympe de Gouges 于1791 年发表了《妇女与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妇女权利”(即法文“droits des femmes”,英文“women’s rights”)或曰“女权”的概念与名称就此确立下来。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陆续兴起妇女运动,初期的基本诉求是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因而“妇女权利”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术语。
进入19 世纪末与20 世纪初,由于陆续出现的“妇女权利”“男女平权”“妇女参政运动”等术语不再能涵盖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中发展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需要新的术语来表述更加丰富的内涵, 英文“ feminism” 与法文“féminisme”走进公共话语,成为彼时的新术语。根据法国学者的研究,法文中的“féminisme”一词于1872 年首次出现在法国作家小仲马的笔下,它最初是指使男人女性化的一种病理,1882 年开始具有反抗性别不平等的意义[3]。 英文中的“femi⁃nism”一词于19 世纪80 年代首次出现,并经历了与法语语境类似的概念嬗变。 “只有当一个词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下来之后,才能成为大家接受与认可的‘概念’。”[4]“Feminism”就是一个典型:随着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反对两性不平等”的意义被反复使用,最终成为这一领域的核心术语。
由此可见,概念后于观念而产生,并随着观念的转变与丰富而不断完善。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核心术语的概念的演化,与社会发展及时代变迁密不可分。 正如有学者指出:“词是产生概念的土壤与支撑,其历史应该先于概念。同时,定义表达或者指称的历史也不可能先于被定义的、被称名的、被指称的东西。”[5]479-480在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feminism” 获得了“反对两性不平等”的概念;反过来也可以说,“反对两性不平等”的概念选择了“feminism”这一名称。 为一个研究对象命名,能使之获得一个独立的名分,并在此名分之下集结多种信息,成为联结所有相关对象的重要一环。 获得名分之后的“女性主义”概念就是如此,它在发展过程中增添了诸多内涵:在19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的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中获得了“普遍主义”的内涵;在20世纪60-70 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获得了“差异主义”的内涵;在20 世纪末又获得了后现代主义“消解二元论”的内涵。 这些内涵有时互相矛盾并彼此竞争,形成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广阔场域。 如今,“女性主义” 早已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概念场、一个术语系统,它的次一层级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等。 “女性主义”术语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促使女性从性别无意识走向性别自觉,终结了过去女性在父权话语系统中的文化失语现象,为女性抗争提供了丰富的话语武器,并成为各种女性主义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最终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女性处境与性别文化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的深刻变革。
(二) 从“女子主义”到“女权主义”的权力内涵之强化
“一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术语外译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特点、民族心理特点、语言观念和与源语民族的相互联系和文化交流。”[6]64“Feminism”一词自进入中国语境以来,先后产生了多个汉译术语:“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弗弥捏士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这一汉译演变历程充分体现了百年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变迁以及与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女性主义术语的汉译是在清末中国遭遇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维新人士从西方思想文化中汲取“天赋人权”的概念,主张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 在此后接连发生的革命运动中,女性问题自始至终都是重要议题,而中国的女权运动也成为国际女权运动的重要一环。 中国语境移植了许多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其中“女权”一词成为核心术语。 一般认为,“女权”一词来自现代日语。 日本比中国更早接受西方文化,中国从日本转借来很多西方概念。 日本学者须藤瑞代指出,“民权”“人权”“女权”这三个词首先出现在日文里,然后才出现在中文里;日文中的“女权”一词最早见于1881 年井上勤翻译的斯宾塞的《女权真论》,汉语中的“女权”首次出现在1900 年《清译报》刊发的《男女交际论》一文[7]。 而复旦大学陈雁则认为,“女权”一词是多词源的:从日文转借,直接从英语翻译,以及中国学者对“男女平权”一词的使用,并建议把这一术语看作是东洋与西洋文化交叉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翻译与重译的过程[8]106。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进入一个女权高涨的时代,它深受西方女权运动影响,同时也在鼓舞着后者。 中国社会各界频繁使用“女权”一词来反抗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性别秩序,呼吁男女平权,主张赋予女性以政治权、经济权、受教育权与婚姻自主权,甚至爆发了多次妇女参政运动。 这场旷日持久的女权运动虽然最终未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权与妇女解放,但在各个层面均取得显著成效,极大地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
早在20 世纪20 年代,“feminism”通常被译为“女子主义”和“妇女主义”。 1933 年,中国辞书第一次同时收录英文“feminism”、 法文“féminisme” 和德文“feminismus” ,并音译为“弗弥捏士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它与“女子主义”“妇女主义”三个汉译术语各自出现在报刊上,直到1937 年《最近汉英大辞典》把“feminism”翻译成“女权主义”才相对获得统一。 这表明:“词汇对于社会文化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和共变性,外译术语的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发展而变化,有的概念更加确切,有的被淘汰,有的由新术语所代替。”[6]66“弗弥捏士姆”因为不符合汉语习惯而早早消失;而“女子”与“妇女”这两个词承载着传统女性的形象与价值,于是“女子主义”与“妇女主义”也逐渐不再被提及。 “女权主义”一词虽然出现最迟,却流传最为久远:一方面,“女权主义”让人联想到“女权”是这一核心术语的派生词,而“女权主义者”是其另一个派生词,这样,这三个汉译词之间的关系甚至比在源语中显得更加圆融自洽;另一方面,“女权主义”具有强烈的争夺政治权力的意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时期包括妇女参政议政在内的女权运动对于权利与权力的诉求。
由此不难看出,外译词漂洋过海落户于本土,有一个顺应社会发展、符合民族接受心理的适应过程,其中,与源语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文化交流为其扎根生存提供了有益的滋养。 适应的过程,是固本的过程,抑或是淘汰的过程,而决定其生命力旺盛与否的是概念内涵的适应社会价值所在。
(三)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权力内涵之式微
20 世纪50-70 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 期间“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代替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从公共话语中消失。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一直主张吸纳女权主义者,用“妇女解放”一类的话语取代“女权主义”;后来,“女权主义”逐渐被看作是“西方的”和“资产阶级的”,最终走向负面意义。 进入80 年代,中西方文化交流重启,女性主义话语复苏,“feminism”的汉译又经历了新的嬗变。 受台湾地区译法的影响,“女性主义”一词开始在中国大陆广泛使用[8]110-111。 从此,尽管“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并存于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之中,但“女性主义”大有取代“女权主义”之势。
“Feminism”由译为“女权主义”逐渐过渡到“女性主义”,反映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其权力内涵式微而差异主义思想重占上风的趋势。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在经历了20 世纪60-70 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后,女性问题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争取政治权力的意味逐渐淡化。 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前期,以波伏娃为代表的普遍主义思想把女人从“生来低等”的屈辱中解放出来,但却抹杀了女性的特殊性并导致其“雄性化”;因而在这次浪潮的中后期,主张重新发掘女性气质的差异主义思想抬头,号召把过去被视作低等的女性特征转变成优势。 虽然中西方交流渠道曾长期受阻,但中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轨迹具有重合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便通过立法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并且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大量女性走出家庭,通过参与社会劳动与公共事务逐渐实现自我赋权,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与普遍主义同构。 改革开放后,既往“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被认为是以牺牲女性特质为代价,事实上造成了对女性的另一种压迫,因此,中国女性需要回归女性身份。 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女性早已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无需再多谈争取权利。 因此,在对过去30 年妇女解放的反思中,在传统两性道德的回归中,同时也在消费主义对“女人味”的鼓吹下,性别差异观念卷土重来,“做女人, 做优质女人”成为时代话语。 词语及词义的发展变化无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甚至折射出社会生活变化的细枝末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较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从字面上隐去了对权利与权力的伸张,并且有一种差异主义的内涵,因而该译法出现的频率变得更高。
“女性主义”这一名称被学界再三确认。 在1992 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译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前言中,编者张京媛阐述了“feminism”的翻译问题,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分别对应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为女性的基本权利而奋斗,虽然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但因为已经是后现代理论时期,并且此书收录的论文也以后现代主义为主,所以她倾向于使用“女性主义”一词[9]。 自该书问世之后,“女性主义”成为学界公认的比较标准的译法。 翻译家郑克鲁在2011 年版全译本《第二性》的后记中特别提到,他在面对“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选择时也曾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后者,原因同张京媛相似:在二战之前,女权运动主要是争取同男人一样的权利,因此用“女权主义”更适合;而战后新一轮女性主义浪潮不再局限于要求政治权利,用“女性主义”来翻译“féminisme”更妥当[10]。
然而,“女权主义”一词并未就此被淘汰。 首先,“女权主义”在大众话语中流传下来,近来有复燃之势。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女权主义”比“女性主义”的传播历史更久远,已经形成使用惯性;另一方面,“女权主义”听起来更激进、更有攻击性,给人一种一群强势女性要统治男性的观感,这种冲击力强的词语很容易获得广泛的传播。 其次,个别学者倾向于使用“女权主义”旨在传承历史。 比较典型的是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她主攻的中国近现代女权运动史正是普遍使用术语“女权”和“女权主义”的时代。 对王政而言,21 世纪的中国女性仍然在享受中国女权运动史的馈赠,使用“女权主义”一词才能更好地继承这一宝贵遗产[11]。
总之,一定时代的思想文化在选择核心术语,核心术语也在尽可能地、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尽管“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有各自的侧重点与局限性,但是,沿着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考察,“feminism”的汉译以其内涵的演变为标志,经历了一个“波浪式”传承与接受过程。 “女权主义”似乎是政治的、历史的,倾向于对权利或权力的伸张,但今日略显狭隘。 而“女性主义”看起来更温和、更学术,但也有可能重新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需要指出的是,“feminism”在当下也遭遇了解构,因为它预设了男女两个对立性别,没有给其他性别提供空间。 因此,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后半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术语“gender”开始盛行。
二、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研究
1975 年,美国学者Gayle Rubin 首次提出“gender”这一概念。 21 世纪,“gender”已成为国际社会推动性别平等与发展的重要概念。 在西方语言文化中,“sex”指生理性别,强调男女在解剖学与生理学上的差异;而“gender”侧重男女在特定社会的文化角色与性别身份认同。 如果说过去的“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等术语是一种原则及阐述,那么“社会性别”则成为这些原则与阐述的底层逻辑。
1995 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为迎接这次盛会,中国学界译介了大量相关著述;世妇会之后,译介与研究热度仍不减。“gender”作为性别研究的基本概念被引进到中国语境并传播开来。 有关“gender”以及与此相关的“sex”和“sexuality”的汉译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值得作一番探讨。
1998 年王政与杜芳琴在《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一书中首次把“gender”译为“社会性别”,此称名就此在学界得到了广泛接受。 显然,之所以译为“社会性别”,是因为“gender”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加上“社会”未尝不可。 中国女性学创始人李小江则认为,中文的“性别”一词同时包括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12]。 李小江立足中国本土文化,注重性别差异,建议不要完全抛弃生理既定。 在她看来,“女权主义”是政治的,而“性别研究”是学术的;从“女权主义”发展到“性别研究”是学术的进步,但却是政治的倒退[13]。 实质上,“王政关注如何将西方的理论、概念完整地引进中国,用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李小江则致力于本土文化的挖掘与重建,在运用西方话语时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14]二者殊途同归,无论是“洋为中用”、为我服务,还是绝不照搬照抄、坚定自信,都旨在把概念内涵的阐释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西方“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性别研究”的政治意涵反而在不断增强,以致于被西方多国极右翼势力视作洪水猛兽而加以打压。 愈是如此,我们愈是要从概念阐释的基础做起,以勇于构建的学术自觉,提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内涵、新表述。
此外,作为性别研究的一个新分支, “性存在”(即英文的“sexuality”,法文的“sexualité”)是性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核心概念。 “如同社会性别一样,性存在是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视角和‘整合性的工具’,是一种‘涵盖性的术语’。”[15]“性存在包括性的生物存在、性的心理存在、性的社会存在三个子系统,三个系统是相互影响与作用并构成性存在这个整体。”[16]正因为“sexuality”的外延广阔,其汉译可谓多种多样,各有侧重:“性”“性欲”“性心理”“性经验”“全性”“性存在”,等等。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法国哲学家福科的性存在史开山之作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的标题汉译:1989 年版取名《性史》;2015 年版取名《性经验史》;而近些年相关领域学者称之为《性存在史》。 显然,“性”“性欲”“性心理”“性经验”等译法都压缩了“sexuality”的外延;“全性”的译法虽然试图涵盖全面,但略显生硬。 性学专家潘绥铭提出的“性存在”是近些年学界比较认可的汉译。
由此可见,对外来词汇的吸收也有一个阐释、比较、鉴别、认同与接受的过程。 把握差异,对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才有所助益。
三、无处不在的“男权”
“Feminism”有多个对立项:“patriarchy”“pa⁃triarchism”“masculinism”与“male chauvinism”。通常,“patriarchy”被译为“父权制”;“patriarch⁃ism”被译为“父权主义”;“masculinism”被译为“男性主义”;“male chauvinism”被译为“男性沙文主义”或“男权主义”。 这四个术语的汉译虽然不存在更多的争议,但中西方语境所流通的术语及概念并不一一对等,从中可以看出术语及其概念的西方输出与中国接受之间的参差。
在西方语境下,这四个术语的概念既重合又互补。 其一,“patriarchy”是一个相对古老的词语,经历过一番内涵的演变。 它来源于古希腊词汇“pater”(父亲)与“archie”(来源和指挥)的组合,最初意为“父亲的权威”[17]142;摩根(Lewis Morgan)和巴霍芬(Johann Bachofen)把“patriarch⁃y”等同于史前社会取代了母权的父权;这一意义被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和倍倍尔(August Bebel) 接续使用,一直延续到20 世纪70 年代[17]142;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美国学者Kate Millett 在其著作《性政治》(1971)中赋予“patriarchy”以当代女性主义意义,指涉女性主义应与之抗争的整个制度,该术语随即进入当时的女性主义话语[17]143。 “Patriarchy”具有两方面特征:它指代一种体制,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或心理状态;西方女性主义者们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等起来,认为女性的屈从地位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后果之一[17]143-144。 其二,“patriarchism”的意义内涵依附于“patriarchy”。 两者之间的区别为:“patriarchy”指一种社会制度;而“patriarchism”指父权制的品质。 其三,如前所述,“masculinism”最初是指使女性男性化的一种病理。 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masculinism”曾指代男性统治的捍卫者。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词在法语、英语和德语中都十分罕见且含义不稳定。 20 世纪80 年代,“masculinism”恢复使用,是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反动。 进入21 世纪,该术语变得普及,是对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回应[18];在“保守革命”的全球背景下,它是一种表达,认为女性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颠覆了权力关系并让男人们感到混乱和恐慌[18]。 其四,“male chau⁃vinism”是指男性优于女性的信念,尤其是在工作场合。
中国语境最常使用的是“父权”与“男权”这两个存在已久的术语来作为“女性主义”的对立项。 它们比“女权”稍晚一些出现。 “中国知网”上最早以“父权”为主题的中文论文是1934 年发表的《家族演化之理论》一文,作者杨堃主要阐释西方学者有关家庭的理论,其中多次提及“父权”“父权说”和“父权家庭”。 而以“男权”为主题的论文则要更晚些年才出现。 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男权”一词少有被提及。 1995 年之后,“男权”一词的使用激增,大有赶超“父权”之势。 人们每逢提到“男权”时,想到的大多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而提到“父权”时,会想到家庭中的一种权力关系。 “对选择术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般认识,而不是概念”[5]479。 大众已然习惯于把“男权”视作“女权”的对立术语,因为“男权”一词更简单易懂,更容易制造两性对立,也更具煽动性。 而“父权”一词主要出现在专业研究领域,被用来指涉建立在父系基础上的一整套压迫制度,规避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 相比之下,“mascu⁃linism”的汉译术语“男性主义”与“male chauvin⁃ism”对应的“男性沙文主义”近些年才进入中国语境,但使用频次并不高。 并且在多数语篇中,它们被当做“男权”的替换词,少有体现出源语中的内涵,也没有像在源语中那样形成互补。 可见,在中国语境下,“男权”一词几乎无处不在,遮蔽了“女性主义”的其他对立项。
总之,对立术语的称名也是其内涵的体现。“父权”“男权”及其派生的一系列概念作为“女性主义”核心术语的外延,为“女性主义”的汉译流变的考察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女性主义汉译流变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女性主义核心术语的概念演变与汉译流变为我们构筑了一幅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图景与现实生机,它揭示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跨文化传播的自身逻辑,为我们在国际话语场域发出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带来相应的启示。
(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洋为中用、辩证取舍
女性主义虽然发端于西方,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为汉译女性主义术语增添了新的内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国的概念内涵与话语表达。因此,我们不可能被动地接受或僵化地使用西方术语及其概念,而是充分发挥主体认知与创新能力。 特别是在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的态势下,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国家对于特定概念拥有解释的垄断霸权并借机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以此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 有学者指出:“我们应基于中国独特传统和现实语境,基于中国自身历史和现实规定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包括西方术语在内的原有概念范畴进行再定义、再解释、再表达”[19],即“洋为中用,辩证取舍”。 之所以如此,旨在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而是从术语概念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波浪起伏过程以及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活跃度、认同度、接受度方面作以考察,既要考察其在源语中的历史演变,又要将其纳入中国语境,从而在全面把握其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完整准确地做出“自主”的阐释。 更好地实现洋为中用,必须辩证取舍、辩证扬弃,这是洋为中用的先决条件。 为实现“中用”,必须“自主”,唯有“自主”,亦才能更好地实现“中用”,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尽管核心术语作为自主知识体系中最基础、最基本的单元,但是,由其核心地位所决定,使之成为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性支撑。 从女性主义核心术语“中国化”的历程来看,它的内涵阐释立足于中国实际,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见微知著,既全面反映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又让术语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内涵、新阐释。 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译目标及其传播效果,奥秘在于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所谓守正,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及其道路,恪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谓创新,在守正中寻求新的突破,赋予时代新的理念、内涵与境界。守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伦理品格、思维习惯与接受心理;创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对守正的创造性丰富与发展。
(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放眼世界、融通中外
梳理自清末以来包括女性研究及性别研究在内的中国女性主义的内涵阐释,为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概念,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和实践,也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其概念、范畴和理论内涵,应放眼世界、融通中外。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为中国学者的学术造诣与学术贡献,它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主体与要件;中国话语能否与世界畅达地沟通与交流,至关重要的是能否融通中外。 它不仅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伟大实践,还是与世界认知的契合与对接,它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融会贯通。 因此,放眼世界、融通中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传播中国话语体系说来,既是价值取向、价值旨归,又是实现的途径与举措;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 愈是让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与世界相融相通,愈加有助于世界不同国家与民族观察中国、解码中国、信赖中国。
综上所述,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是我们对待西方女性主义核心术语这一舶来品应持有的科学态度,它体现为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体现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核心术语并融入中国实践,传播中国价值与中国经验,以满足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探求,它以中国特色为标识;放眼世界、融通中外,旨在对接世界认知,以核心术语阐释为未来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