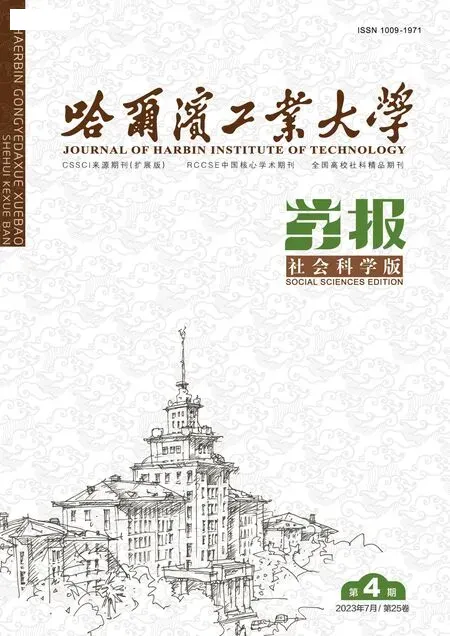朱天文:女性主义的书写与后世俗思考
2023-03-17刘晓宇
刘晓宇,田 泥
(1.北京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台湾女性主义书写场域中,朱天文无疑备受瞩目。 她惯以在眷村、台北、乌托邦神话世界的虚实空间和新世纪前后的历史流荡中表达女性存在,主题涉及都市时空变迁,也涵盖大陆移民群体的国族记忆。 朱天文的写作在整体上绵延为一个现代系统:传说时代(1972—1981)—都市时代(1982—1987)—世纪末时代(1988—1990)—荒人时代(1994 年至今),内在主题也始终悬置出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空间,作家笔下的女性主体则完全负载了这一思考。 她们从仙风道骨的诗经时代走来,经历新世纪物的繁杂、话语迷惘,在未来世界颠沛流离,最终选择转身面向来处寻求慰藉,这也是许多论者所谈及的朱天文写作中“返身过去”的怀旧心态,还有“背向未来”的反现代意识。
朱天文在《明天过后》一文中,借《戏梦人生》中李天禄用台语说的“也要神,也要人”表达了对现世神性信仰遭遇祛魅的哀恸,有论者将此表达为作家的时间焦虑和对未来的消极态度。 朱天文确也在《废墟里的新天使》中阐释了自己后期书写的转向:“不要从好的旧东西着手,而要从新的坏东西着手”[1],她的观念轨迹深刻烙印下本雅明“历史天使”的形象[2]43-44,在“进步的风暴”中裹挟着满是质疑的历史回望。 “进步的风暴”描绘的是现代理性世界的世俗化进程,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世俗世界的造就依靠“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3]79,即在关于世界的解释机制中剔除超自然神力的部分,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3]80,如此,正像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中强调的,世俗化过程会使人在工具理性的压抑下走向主体焦虑[4]。 通过书写世俗世界中的时空压抑,来具体呈现现代性主体危机是朱天文写作的重要议题之一,但她的写作超越了客观呈现,而通往救赎之道。 诚如哈贝马斯从新世纪之初就开始不断思考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并突破世俗主义立场,发现了后世俗(post-secular)世界中宗教、感受、直觉等超验力量的复苏,及其向现代自由、民主、理性、制度发起的挑战,朱天文在写作中也敏锐捕捉到哈贝马斯意义上后世俗时代的来临,因而在家学师承的规训与叛逃欲望的撕裂中,她于惯常的世俗性写作,尤其是在关于女性的议题中,探寻救赎的可能性:在“光晕”尽失的现代“废墟”中,实现“碎片”的去蔽;面朝原初世界的诗意与想象中的神性,去追寻某种缺场力量的复归,而这种复归正印证了哈贝马斯在《后世俗社会的注释》中对“后世俗社会”的预言,即原先被世俗化驱赶到私人领域的宗教性正在悄然复兴,并以多元形态介入公共生活的“共鸣板”[5]。 这些潜在于朱天文阶段性写作议题中,通过世俗性物像书写不断询唤某种超验力量的方式,成为她抵抗现代性的一条有效路径,并具体地绵延于她女性主义思考的始终,这个过程反过来也促使朱天文走上后世俗女性主义的革命之路,为我们解读朱天文的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一、传说时代:同构叙事中的“被压抑物”
朱天文的写作源起于对张爱玲的模仿。 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以书写陆港都市传奇中的女性原罪而著名。 在朱天文特殊的成长经历里,有过青春期的尴尬与不安,还遭遇过特立独行的偶像经验。 无疑,张爱玲个人主义的乖张性格和古典荒凉的美学格调,就深刻栽植于她的精神底色,更重要的是,还指引她密切开掘现代都市中的种种世俗性问题。 虽然朱天文在世纪之初写下了《叛逃张爱玲》,表达出对偶像“影响的焦虑”,但也正因为张爱玲,朱天文的写作基因里才葆有了叛逆的特质,使她不断索求自我主体意识的建立以及消解他者的影响,这种源自早年的焦虑意识,作为一种拉康意义上的“被压抑物”深埋于朱天文写作的潜层,同时也促使朱天文超越张爱玲式的对女性世俗阵痛的冷静陈列,而持续触及到更绵远的女性救赎理想。
在朱天文的早期写作中,张爱玲的深刻影响表现在题材选择与女性造型方面。 她在《淡江记》回忆三三社团时透露,传说时代的写作基于半自叙传式的青春记忆,人物原型大都被艺术化处理为耽于幻想的高蹈绝尘女子,具有“樱子的烂漫无禁忌”[6]的诗意,疏离于凡俗世界。 这源于作者冷静内省的叙述策略,通过内置“看”与“被看”结构,制造自我与他者的观看距离。 同时,叙述者“我”的声音的嵌入,不断自我询问,与外界展开对话,不仅令其文本混有冷眼疏离的质感,也使得她笔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有迹可循。
写于1972 年《仍然在殷勤地闪耀着》中的主人公李,特立独行,不服规训,是朱天文少女时代的“理想自我”的显形,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违规冲动,累积了她后期的写作爆裂。 20 世纪70 年代,悸动的台湾正在接受国民党伊甸园西化教育,新思潮不断涌现,这样的后殖民环境是“我”发生裂变的动因。 而西式文化刺激下的新女性想象,引发了朱天文青春期内心的冲突——“我”敏感、自卑,受传统禁忌羁绊,于是“充满着崇拜英雄的童心爱慕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学她”[7]。 对自我的僭越源于对他者的想象,如“固执坚毅的希腊武士”的新女性李,为“我”提供了一个构想自我的心理活动力场,在拉康的“想象界”中,它“规定了一种对自身的无尽追寻,一个为了支撑其统一性的虚构而合并越来越多的复制与相似之情形的过程。”[8]这种合并与模仿行为促使他异之物与自我的统一,也正是不断认知到自身内部的他异性——“小他者(the other)”的存在,造成了自我的发现。 朱天文早期的青春写作中,人物关系和叙事模式基本都采用相同的“传统-现代”的对照结构,如《俪人行》中的丹凤和尤可玉、《陌上花》中的嘉宝和如星。 在互为参照的女性形象组合中,朱天文一方面无限向往着代表先进文明的异他性,但同时也在“小他者”的反衬中,回观自身,并在现代焦虑意识的挤压中,向传统文化回切,从中汲取精神养分,走向自我主体身份的历史审视,随之,“历史天使”所表征的历史主体也在此显影。
女性自我的建立,不仅超越了对“理想自我”的盲目爱慕,也开始把批判的视野投射于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the Other)”之上——宏大的社会制度与现代环境,这是女性主体作为“大他者(the Other)”评判者身份的正式确立,进一步提出对自身所经验的整体象征秩序的质疑。 比如,“我”作为敏锐的观察者,在面对同学张淑华的死亡事件时,以局外人的视角,冷辣地审视这场由众人“贫乏而做假的哀伤”与“贩卖”故事发起的同情表演。 《怎一个愁字了得》是内置了“女性—男性”“幼年—成人”“学生—老师”三层权力关系的成长叙事。 惠兰对老师爱恋的陨落,归因于老师的世俗肉身的被发现,惠兰深感“失去了一件东西”[9],象征了传统父权世界霸权的全面陷落,朱天文也在质疑现代权力结构中,发展出具有自省能力的女性主体。 《乔太守新记》标志着朱天文逐步超越个人写作,面向更阔大的社会作出敏锐反应,开始反思女性与时代的关联。 莎莎被先进文明的化身季慕云携领,在西方思想浪潮中追新逐异,同时又耽于象征原始生命力的成宇的健全灵肉,显示出“历史天使”的矛盾姿态。 朱天文最终让莎莎选择逃离现代化,回归健全人性世界,展现了“背向未来”的美学选择。 这也正式昭示了朱天文女性主义话语生成于被“被压抑物”激化的逃离世俗的欲望,与对现代性的批判紧密关联。
为表达对现代的叛逃,朱天文采用了同构的美学叙事策略,即在女性形象与命运的表达上,倾向将女性主体静置于一个架空的、消除了时间概念的纯美学空间,以此消解女性与诸多现代性议题的本质关联。 如《剪春萝》里对疯癫女人阿足的书写,作家避免言说其苦难命运及根源,而是在诗意审美空间的晕染中,逐步涂抹掉历史化的印记,传达出女性与更神远灵性世界的关联。 《青青子衿》里工读生碧娟,以自洁的心灵强力躲避凌乱的社会万象,退守于想象世界来获得“干净了许多”[10]的自足感。 而在小说《思想起》和《春风吹又生》中,赵德春、余刚这样的男性都被塑造为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中失败的革命教条者,而大学教师黄蕴芝和赵德春之妻林启秀这两位女性,则超然于历史主潮之外,被美学之力抽离出历史时间的表达,由此造成小说叙事的两重造境:一重是革命现实的紧迫感,一重是美学真空的松弛感。在同样是革命背景的小说《腊梅三弄》里,何郁雯和梅仪等待着参加左翼革命的沈洁明的归来,她们处于革命历史的边缘,怀着淡然、怅惘的情愫,被悬置在悲而不伤的美学空间。 然而,书写女性遗世独立的高蹈品质和以美学为主导的自由意志,并非作家在刻意规避权力话语的表现;她们在历史与革命中谦卑地退守,恪守古典性别秩序中的男尊女卑,也不是孱弱的个人主义审美方式。朱天文通过建构男性革命叙述空间与女性纯粹美学空间的二元对立,是以复魅的女性神性元素,来抵抗男性象征的历史秩序与现代叙事。 且唯有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朱天文放弃了营造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的历史主义观念,而倾向于本雅明强调“对过去的独特体验”的历史观,即个体挣脱“当下”时间的束缚,嵌入某一时刻自我的“独特体验”。 对朱天文来说,这种将女性力量放逐在美学范畴的写作实验,构制出一个精致的、努力消除“当下”时刻霸权的传说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现代的方式。 可以看到,传说时代的女性不仅远离革命、政治、历史,甚至也远离成长本身,如“十七岁就好”[11]的丹凤,“兴亡与沧桑在她身上都不落下痕迹”[12]的嘉宝,纤毫间都隐现出逃逸时间追捕的、作家未言明的神性意味。 这种古典小说的传奇笔法和对“女体”的印象式书写,也进一步丰润了对女性的神性想象。
朱天文传说时代的女性写作,从思考自我对“小他者”的“想象性认同”,到寻求自我在“大他者”的“符号性认同”中去发展,最终试图走向去认同、去焦虑、去历史化的自由境地,参与到纯美学建构上。 在文本叙事内部与作家人生经验之间,显现出微妙的同构关系,这鲜明地指向隐藏在朱天文初期写作意识中的“被压抑物”。 她在现代性的规训与女性天赋的内省力量之间激烈地跌宕,在本雅明时间“单子”意义上,以不断“跃入”古典美学的某一审美时刻的方式,来弥合内心对奔逐现代性的失落。 朱天文拒绝将女性主体融入既定的社会符号场域,去接受既定身份“询唤”,而是步步退守,无限留恋未有“历史幻境”的世俗化之前的历史时期,回归神性美学范畴。 而这也注定了朱天文的女性主义书写从传说时代始就注定了后期的探寻方向,此后每一阶段的书写都是“被压抑物”幽灵不断“回到未来”的现身。
二、都市时代:世俗废墟中由癫狂到神性
在都市阶段,朱天文开始关注从青春的伊甸园跌入现代的女性生存,在世俗废墟与都市幽闭场——包含婚姻、道德、身份政治、话语禁忌等现代理性制造出的多重隐形制度空间,女性身体与感知的碎片化,诸如源于疼痛的敏感、安全感零弱、噩梦意识、身份焦虑、人格裂变、主体性缺失、疯癫与文明的悖论等,都成为此阶段写作的共同符码。
朱天文清楚地意识到都市以其多种形态的制度性力量,造成了女性生存的艰难和心灵囚禁。正如《画眉记》的开篇是一段由喧嚣街道向室内近景的长镜头推移,呈现出空间的狭隘化与物的无序,视点继续推移到禁闭于室内的年轻女人关关身上,形成“街道—室内”“婚前-婚后”的嵌套隐喻结构。 现实婚姻让“火烧似刚烈”[13]的关关“步下云阶,一阶一阶沉入了凡尘”[14],禁足于密闭空间,周身充塞着都市的琐屑和不安。 于是,她选择以跳楼的方式出逃。 《最蓝的蓝》里的女学生周荔亭,为生计在舞厅“蓝烟赤焰的横流里”跳五龙凤,被发现后也选择了自杀。 死亡作为她的出逃方式,是对周遭“凝视”的反抗和对自身双重身份焦虑的终结,“硫磺里浮升起的一朵白莲花”的女性圣像才得以永铸。 这种“疯癫/死亡”的叙事结构延续到《伊甸不再》:素兰以三个名字、三重身份漂泊在“都市—眷村”“现实—回忆”“荧幕—现实”之间,身份分裂而无法整合自我,最终内部崩解而自杀。 “像野芒叶会割人见血”的素兰由于过早领略了世间的“灰凉决裂”,企图逃离原生家庭的累赘和困苦的眷村生活;她的都市身份是艺人甄梨,为寻找一个可安放自我的位置而介入了导演乔樵的婚姻,但失爱的结局让她陷入了更危险的失根状态;荧屏角色侠女戚双红是她现实处境的隐喻,终究遁入空门。 从《伊甸不再》开始,朱天文变得愈发“凌厉辣挞”,但她依旧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神学信仰和审美理想,追求“无立足境,方是干净”超脱的诗意境界,来抵抗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内心飘零,为现代女性身心困境寻找新的生路。 如果说女性主义经典《阁楼上的疯女人》借简·爱潜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反抗父权的潜在欲望的化身——伯莎的“疯癫”典型,提供了一种旨在“颠覆”的女性诗学典范,她象征了愤怒、毁灭的黑暗力量,那么朱天文女性写作中的“癫狂”则更倾向于一种存在主义的状态描述,终结“癫狂”的方式是内向的自我毁灭——毁灭现代性别秩序中女性既有的身份标签,以此收获平静的美学力量并超越死亡本身,这似乎在“疯女人”的天使与魔鬼的两个维度之外找到一条更接近神性的救赎路径。 在这之后,朱天文继续强化女性神启的超拔品质,甚至以男性启蒙者的角色出场,显示出对父权的睥睨。
《安安的假期》讲述了一个疯女人与幼女之间心神契合、无言会通的故事,作品情节淡化、突出了寒子花所象征的纯澈心灵的悠远诗意。 富于意味的是,整个故事发生在男孩安安的“凝视”下,在他的视角中,成年男性世界的不堪,跟疯女人与幼女这对奇妙组合所构成的超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诗性力量被愈加凸显出来,即女性已不再是传统男性视野中被想象的客体,而被理念化为某种超越世俗性的精神力量。 由此,朱天文笔下的女性升华为更完足的精神性和个体力量的神性载体。 比如电影文学底本《风柜来的人》里的女孩唐秋杏,就扮演了男性的启蒙者角色,她不断催生着问题青年阿清偶发的英雄梦:原本“无所事事和浪费生命”[15]的乡下青年阿清,在步入城市后更加孤独、迷茫,但面对灯火通明的喧嚣夜市和大河呜咽,阿清突然萌生出“想要创造一个亮光光的世界给她,他站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捍卫她”[16]85的愿望;最后秋杏选择独自面对生活苦难而离开,阿清接受了二次启蒙,他开始反思自我:你将来要干什么?”虽“其去未知”[16]88,但获得了彻底觉醒。 《最想念的季节》的表现议题更加世俗化,故事的缘起是廖香妹“为孩子寻找一个合法姓氏”,这是典型的父权社会逻辑下的事件,但她在自主选择的契约婚姻中,表现得落落大方、豁达通透,逐渐让男人沦陷。 朱天文高度赞美廖香妹的生存哲学:游走于社会准则边缘,追求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状态。 不同于前期书写女性在世俗社会中的失根、飘零、无法获得自我统一性以致疯癫的生存状态,廖香妹兼具神性品质与世俗肉身,能够自我圆融,收获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桃树人家有事》中的孟太太,不同于早期因婚姻而选择跳楼的关关,她在婚姻中由琉璃少女逐步被打磨成一个滚厚结实、干练世故的女强人,与孟先生隐瞒婚史、嗜牌成性、自恃清高的卑琐形象形成对比,朱天文笔下的女性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真正成长。
在都市环境下以女性为载体的神性力量出现并挑战着诸种世俗常态,这一主题的成熟表现在《炎夏之都》。 朱天文反向书写了作为男性的吕聪智,他是如何在都市禁锢中寻找自我救赎的现实题材的。 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依凭三个女性的力量获得慰藉:回忆中初恋燕妮“二十岁的身体”给他“活着”的感觉;妻子德美怀孕时坚韧的母性“像榕树伸出的须和气根,扎在他的生活之中”[17]229;特殊职业情人叶则是他逃避现实的港湾,在叶的“凝视”中,“他像是把心底一样珍贵的玉器豁啷啷弃掷于地,碎了满地破片”[17]231,男性的脆弱和萎琐在女性面前被暴露无遗。 一方面,这三个女性在不同的方面为男性提供了想象性的滋补,填充了他麻痹空虚的灵魂内壳,吕聪智也不断反刍“多年以前所爱的人的那句话,有身体好好”[17]232,追忆着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投射载体的过去时代;另一方面,更深的叙事结构则表达了女性的“反凝视”主题,集中表现在叶与吕聪智出场的“对视”情节,男性在世俗肉身欲望的泥淖中渴求被救赎,与女性的神性光辉相遇,相形见绌,彻底败下阵来。 而来自“二十岁”燕妮的永恒回望、德美强力的母性关照,则都代表了女性不受现代理性限制的恒定神性,成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有效回应。
都市时期的朱天文曾明确自己的小说创作以世俗为脚本,写活生生的现实与人:“人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18],但不同于铺写阴暗的琐碎人生的新写实写作,她强调“罪愆的救赎、化蝶的变身”和“向一切无奈无聊无知告别的启蒙”[19]的成长问题。 她清晰地认识到“世俗主义实际上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和将她们排除在理性公民身份和政治的公共范畴以外”[20]43,而在书写中不断发掘女性作为一种超验力量”,在现代伦理与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命题,同时强调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崛起,对现代的反叛就在于在俗世社会中引渡、移栽世俗精神性,以走向更神圣的空间或界面,书写女性由“癫狂者”到“神启者”的身份进化,以此尝试突破世俗社会的重重桎梏。
三、世纪末时代:世俗物象与“灵晕”复生
朱天文的世纪末书写冲动,源起于长期颠沛于世俗世界所产生的深远焦虑,延续了对都市空间的直感,而进一步蔓生出寻求救赎之道的诸多思考。此阶段的文本杂糅了两个看似矛盾的主题,却具有鲜明的过渡性:一方面,以《炎夏之都》文末那句“有身体好好”为起点,极尽身体欲望和官能世界的世俗性表达与物象摹写,尤其书写了一群以“浪掷青春”为务的混哥混妹们在世纪末时代的群魔乱舞,笔法也相应愈发华丽奢靡,以此衬托出世俗世界的繁杂;另一方面,朱天文强化了对感性、知觉、灵性等的形而上思考,用以修复世俗世界日益支离破碎的经验,形成以现实人生为底本的高度浪漫化的寓言体、传奇体文本,其中女性主体被抽象化为一种象征、符码,负载着易感沧桑的“老灵魂”们对青春、理想、乌托邦世界的追寻,促成了“灵晕”的复生,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之道。
对女性的符码化表达集中体现于诗化小说《柴师父》。 女孩作为男性视野中的一种印象:“等待女孩像料峭春寒里等待一棵颤抖泣开的杏花”,“等待女孩像等待一块绿洲”,“等待女孩像等待知悦的乡音”,“等待女孩像等待青春复活”[21]1-4,女孩凝练了年老的柴师父对时间、政治、命运的想象,也深挖出一场悲壮的身体与记忆危机。 这种高度精神化的幻影以实体的触感留存于柴师父的记忆:“四十年过去了,他枯细然而柔劲修白极其敏锐的手指触摸到女孩凉软的胸乳时,肚底抽起一丝凌厉颤动”[21]1,女孩的身体触感带他在“死的,活的,神鬼,拥挤占据着同样的空间与时间”里穿梭,窥见一生。 通过女性肉体感通的灵媒,男性的每一个“当下”得以通往“对过去的独特体验”。 本雅明认为每一个“当下”都是个体直面“废墟”的“危险关头”,如此,个体为自己赢得了立于“废墟”之上吁求救赎的契机,“当下”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从因果链条中挣脱出来的“过去”同样是曾经充满救赎潜能的“当下”——“过去”以其“废墟”的面目燃起了“希望之火”。 朱天文的世纪末书写以超验感知力为匕首,集中扼杀了现代的线性时间想象,传达出强烈的“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启示论味道:“过去的每时每刻都将变成‘今日法庭上的证词’。 那一天便是最后审判日”[2]39,末日审判同时也是迎接救赎的时刻。 但与本雅明不同的是,朱天文将末日神性的期许降临于女性主体:在《尼罗河儿女》中体现为普通女孩林晓阳的古英雄幻梦与宗教互文书写,绑定渺小自我与尼罗河伟力的后裔、古埃及曼菲士王妃的神话叙事;在《带我去吧,月光》中更体现为向东方女性之神“蚕神螺祖”的精神朝圣,召唤女性内部原始阴性之力的重现与救赎。 朱天文肯定了水泥丛林的世俗化过程制造了艾略特式的人的荒原化,同时以宗教信仰的重现及其传道者——女性,作为唯一的末世救赎之道。
《世纪末的华丽》叙写的末日神话将后世俗女性主义思考呈现到极致。 在满覆轻质化建筑的现代台北,“巫女”米亚和老段的禁忌之恋充满了安息香、花草茶、干燥花草味道和各式印象派画作的颜色,过分的耽美营造出一个密不透风、渴求纾解的物质空间,这正寓意着“被幽禁”的现代理性世界的本相。 朱天文充当了从时间深处走来的“忧郁寓言家”,娓娓讲述了服饰及以此为想象载体的女性权利的历史轮替。 米亚对物质的迷恋、对旖旎官能世界的崇拜并非是作家批判性的核心——与其说作家再现了人的精神沉沦与现代世俗性之间的复杂黏附、搏弈关系,倒不如说是作家在揭示种种物质视觉表征背后的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以此为女性最终叛逃世俗化进程的爆破力量做铺写。 文中,米亚以现代世俗化肉身不断触碰着古老的寓言、禁忌、神谕议题,躲避男权世界的危险和失根而萎的孤独。 文末,她呐喊出自己的女性主义宣言:“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22]。 对“嗅觉和颜色的记忆”的强调,正暗示了本雅明所提出的“当代危机”中的典型症候——“灵晕的凋萎”,而这一“灵晕”正是感知、对象与生存方式互相嵌入而形成的一种人类存在形态,它以丰富的个体感知能力为基础,当然也与历史性有深刻关联。 与本雅明略微不同的是,朱天文强调这种感知能力的纯粹内在性与性别的分野,只有女性才具备以睥睨视角或独语的旁视——神学的、美学的主体观念来抵御世俗世界的神性能力。 她悄然解构着作为西方现代性本质的世俗化过程——与宗教的分离而出现的历史主义启蒙;于后世俗世界中,展现神灵、超验因素的复魅,嫁接在诸种典型的世俗场景中,宗教精神性萦绕着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等终极问题叙述而展开。 同时,朱天文下沉到真实的世俗世界,正如米亚从容流转于各种身份之间,不卑不亢地做一名游离态的物质狂欢者,极致地展现了后世俗社会的世俗性维度:“为了能够谈论一个‘后世俗’社会,首先这个社会必须已经处于‘世俗’状态之中”[23],而所谓的“世俗性”必然“以内在的、工具理性的、功能主义的与实用的世俗理性作为支撑”[24]。 可以说,朱天文的女性主义思考撬动了新世纪的一个重大命题:物质的、进步的现代启蒙效能中,某种神性的滋长,表象上追求很在地的物质性,其背后则是有信仰因子的精神性支撑。 正如布拉伊多蒂的质问:“‘我们’——女性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环境主义者,等等有多世俗? ——真的如此吗?”[20]45
在朱天文的世纪末写作中,对现代物质性的极力繁写,深刻展现了后世俗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世俗特性本身;但另一方面,神话叙事、宗教互文俯拾皆是,从神学和神话中发掘出超验式的自然,有意将世俗社会中女性的救赎引入一个复魅世界,试图在世俗启迪中呼唤重现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以此作为对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反拨,表达了后世俗的批判性所在,二者实则并不矛盾。 而“尼罗河儿女”“蚕神螺祖”的后人、巫女米亚——这些标注了“历史天使”形象的女性主体,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开放、游走、被撕裂,从“在世俗物质世界上嬉戏”到“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我”[25],领受“唤醒死者、弥合破碎”[26]的天职,以忧郁的寓言家心灵吟咏死亡田园诗——“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呼唤悠远的古代性”[27],在此在的碎片化废墟的“当下”呼唤彼在的永恒理想,深情召唤着业已失落的“灵晕”复生。
四、荒人时代:“历史弥留之际”的后世俗希望
从《荒人手记》开始,女性的历史主体被高度抽象为“阴性体”,表征为灵与肉二元分裂的混杂存在,成为一个美学符号、一种伦理学的理念化象征。 在物质密集、无秩序、轻飘飘的失根时代,人破碎成畸零的游离拼接态:“我”是“一朵阴性的灵魂装在阳性身躯里”,“我们的阴性气质,爱实感,爱体格,爱色相”[28]90-91,“我们”是“放野在社会边缘的逐色之徒”,是世纪末“被欲海情渊腌渍透了的木乃伊”[29],“未败于社会制裁之前先败于自己内心的荒原”[28]109。 朱天文以新写作实验大胆表现了后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作为违规者的“我”——无祖国、无父姓、无意义的存在,以及包括性别话语在内的一切现代宏大叙事趋于消解的历史境况,这恰恰就是弗雷德里希·尼采在反思现代性时指出的“没有人格,没有意志,对‘爱’的无能”[30]的问题。 现代性统治下濒危的身体感知与记忆能力,极度理性所致的内心荒芜与精神狂狷,让朱天文义无反顾地表达出对父权时代的背弃,并以“逐色者”的身份面向远古神母时代的大地女神信仰——作为种族记忆和集体大梦而被崇拜的“好看,被取悦,好难取悦的,神秘莫测的阴性体”[28]87——虔敬朝拜并明确道出她所追寻的“所谓神性,亦即阴性”[28]89。 朱天文预言在去性别化的无性爱时代,世俗肉欲与物质性会凋零,而精神性的爱的传奇将会成为后世俗社会的救赎希望。 她向“原初性”时代致敬,提出以“柔性生态主义对抗刚性物质主义”[28]113,历史的转捩必将趋向母性社会,而破碎的现代人最终将以母性独有的官能:气味、颜色,实现灵与肉的合一。
荒人时代是世纪转换的“后色情时代”,女性主体化身为巫,执掌神谕,通感原初世界。 朱天文终于抵达终其一生写作孜孜以求的对人的存在和人类发展的总体反思,如荒人在手记中如是写道:
神话揭示出隐情,自然创生女人,女人创生男人,然而男人开造了历史。 是的,历史,男人于是根据他的意思写下了人类的故事。写下了女人是他身体的一根肋骨做成,更写下了女人啃食知识禁果遭神谴责的原罪。 可依我来看,倒是男人偷吃了知识的禁果罢。是他,开创二元对立的。 是他,开始抽象思维的。 他观察,他分析,他解说。 他建造出一个与自然匹敌又相异的系统,是如此与自然异体质的东西呀,男神篡取了女神的位置。 女神的震怒,遂成了人类的原罪。 记住啊,最后的女神说,有过一个时代,你独自徜徉,开怀大笑,坦腹沐浴……女神背转身走入了神话的终止里,让位于社会秩序登场。 女神的哀怅,成了我们失去不返的伊甸园。[28]89-90
“历史”“知识的禁果”“二元对立”“抽象思维”“观察、分析、解说”,这些在马克思·韦伯看来的工具理性,造就了现代社会:“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31]。那个极速扩张的世俗世界曾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支柱,号称“追求平等的人类解放和通过理性进行统治”[20]43。 然而技术主义发展到极致则加速了视听节奏与新旧更迭,施行了对人文主义的疯狂扫荡,被巫称之为E 族、雅帝族的新人类代际叠新,物质与效率成为终极追求,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和本雅明的“机械复制”对废墟碎片的层累作用成为世俗化的恶果。 现代的工具理性、商品经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祛魅”成功,也造成了时间快速滑入“历史的弥留之际”。 但是不同于马克思的“革命性”——关涉将“当下”转化为现世解放的世俗形式,朱天文采用了与本雅明类同的“救赎性”策略,为“当下”赋予神学意味上的救赎潜能。 她不仅是荒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还是于物之繁华与现代文明中望见神谕的巫女。 在既往美学乌托邦的建构中植入“赋魅”策略,对世俗化的批判与救赎借女性主义的革命赋能,而诉诸于神性的、超验的阴性力量和世俗精神性就是朱天文超越于世俗化之上的一条信仰朝圣之路。
检索当代女性主义发展,最主要的叙述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实践而存在的,以女性经验为中心,为性别平等的目标服务。 这种自由主义(以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为典型)以“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主张保护个人权利,信任科学,信任目的论进步,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之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合作。 与以上平等女性主义者不同的是差异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和男子在“本质主义”上的不同,根因于自然生物属性的不同。 因此在后一种女性主义中,女性越过了世俗化的程式与禁忌,彻底摆脱父权制的意识形态限制而具备激进的革命内涵。 如阿尔卡-阿罗拉所证明的那样,女性主义虽与宗教或灵性没有先验的关系,但与世俗化息息相关,因此性别问题必然与信仰自由密切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朱天文新世纪后的写作更加关注世俗化过程中的信仰因子,本质上暗合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后世俗演进,这也体现出朱天文女性主义思考的先锋性和深刻性。
结 语
纵向梳理朱天文四个阶段的写作,她的女性写作产生于现代性强力之下的“被压抑物的回归”,又在世俗化进程中由癫狂发展出对神性的召唤,由此形成她写作中独特的后世俗二元结构:世俗性与神性的交杂议题。 可以看出,她的女性主义由美学乌托邦建构通往后世俗思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一个逆向求索的连贯闭环。从诗经里来、到神话中去,虽在师承的转身过程中偶尔犹疑顿足,但她女性身份中天然的内在冲动和困囿于现实的焦虑,作为“被压抑物”始终存在并不断驱使她强烈地寻求世俗化中的救赎新径。不可忽视的是,虽然朱天文女性主义话语本质上生成于逃离世俗的欲望和对现代性的批判,且成像和表征为不同时段的写作议题,使她的女性主义写作无疑充满了革命强力与反抗后劲;但她所依托的现阶段后世俗理论内部本身又矛盾重重,尤其是去世俗化的神学皈依使得内在于后人文思想中的平等、解放等世俗诉求难以自处。 尽管如此,朱天文的后世俗女性主义书写,询唤女性内部原初阴性之神力的重现,以及提倡柔性的生态主义等,为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话语重新肇始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尤其是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更指向了女性版的创世纪,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解构父性神话学传统和父权支配性逻辑的文化策略,或许这可为我们继续研究后世俗女性主义问题提供有效的想象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