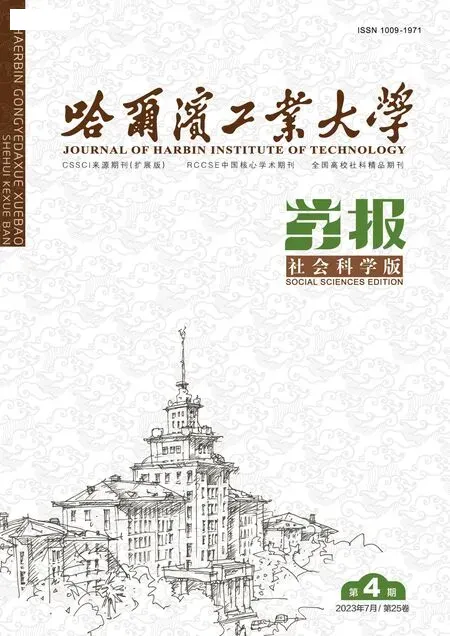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2023-03-17任竞泽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史料极为丰富,撮举几例,如:“诗文各体原出五经”,“文章根本皆在六经”,“文章体制,省简而繁,分化之迹,较然可识”,“谈艺者固当沿流溯源,要不可执著根本之同,而忽略枝叶之异”,“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文体递变,此体可以代兴”。 在《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中国文学小史》等著作篇章中,经典论断在在可见。 我们在全面检阅辑录、分类阐述散见在所有著作中的文体史观念史料的基础上,从文体源流论、文体发展观、唐宋诗体论三个方面梳理并构建其文体史观念体系,其中所体现的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一、诗文各体,原出五经:文体源流论
文体源流论是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观念体系的基本理论,主要包含两方面内蕴:一个是“文体源出五经”,近于文体发生学的文学本源论,一个是“原始以表末”,属于文体流变观的文体研究方法。 关于前者,钱钟书围绕《文心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元典,从学术史的视域全面梳理了“文原五经”说的源流演变;关于后者,钱钟书则借鉴刘勰这一文体研究方法,对众多文体形态、文体范畴和文体现象诸如七体、连珠、僮约、官箴、评点、小说、骈文、设论体、八股文、破体论、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进行推源溯流,这也是其重要学术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一)诗文各体“原出五经”
“文源五经”说的实质是“文体源出五经”论,其代表就是《文心雕龙·宗经》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后者明显受前者的影响而稍作变化和调整。 钱钟书在此命题的推源溯流时,对二者都有提及并更为重视,因未出全篇,我们录于下,以见大概: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 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1]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2]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以《文心雕龙》《宗经》为核心,一方面从文体继承上的“推源”入手,指出西晋陆机《文赋》已发其绪,所谓“陆机《文赋》‘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陆机盖已发《文心雕龙·宗经》之绪”,并进一步向前追溯到建安王粲,所谓“《全后汉文》卷九一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虽云‘遂训《六经》’,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圣文殊致’,初非缘词章说法,‘文学’所指甚广,乃今语之‘文教’”,但是从近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出发,认为王粲还不属于“词章”“文学”的文体源流,而陆机却已经符合并真正启发了《文心雕龙》之文学意义上的“文体源出五经”论:“机《赋》始专为文词而求诸《经》,刘勰《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大畅厥旨。 《征圣》曰:‘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曰:‘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 鲜克宗经。 …… 文章奥府, 群言之祖。’”[3]1182另一方面,从文体影响下的“溯流”展开,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北朝的颜之推,上面引文很直观地说明了这一影响,钱钟书也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角度,将颜之推与王粲对比,所谓“王粲之《志》只道‘励德树声’尔。 若《颜氏家训·文章》论诗文各体‘原出五经’,则庶几道‘建言修辞’者”。 其后论其对唐宋杜甫、韩愈、王质、辛弃疾的影响[3]1182。
可以看出,钱钟书最大的贡献是,将刘勰影响下的颜之推“文章者,原出五经”论,明确地界定为“文体源出五经”论,即“若《颜氏家训·文章》论诗文各体‘原出五经’”。 其重要性在于,以刘勰、颜之推为代表的“文原五经”或者说“文章源出五经”论,一向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上的文学本源论,虽然钱钟书也未能摆脱从文学和非文学的视域进行探讨,但其“诗文各体‘原出五经’”论却成为现代文体学上的首位提出者,近年一些文体学者也有这样的理论认识,如吴承学等云:“古人提出‘文本于经’除了为文体溯源之外,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夹杂着宗经或者尊体的理论目的。”[4]
(二)“原始以表末”文体发展观的个案研究
《文心雕龙》上编二十篇文体论每篇都以“原释选敷”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研究方法进行论述,这也成为古今文体形态或文体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中“原始以表末”更是传统学术“溯流别”的典型方法,也使得二十篇文体论中的每一篇都堪称一部简明的分体文学史或者说文体通史,钱钟书对诸多文体形态也大体或详尽或简约地运用这一文体研究方法,较为详尽的有七体、连珠体、八股文、以文为诗等。
1.“七体”文体源流
钱钟书以“枚乘创体”的赋体《七发》为核心,通过对晚清章学诚痛诋萧统对“七体”命名的沿承考证,即“释名以彰义”,平步青对“七”体文体源头为枚乘创体的确认,即“原始”,及其历来总集收录“作《七》者”不可胜举,说明“七体”创作的繁荣,进而通过“名实之辩”,指出宋明以来诸如华镇、夏完淳等“尚有名不标《七》”“而实属《七》林者”,“更难烛照数计”。 这一切一方面体现了“七体”的自身文学史和文体史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两千年来“七体”形成了固定的文体创作规范,即“敷理以举统”。 历代作者大都遵循“体制为先”的“辨体”原则,故而如洪迈所云“规放太切,了无新意”,总体不能够破体创新,其中唯有“柳子厚《晋问》用其体,而超然独立机杼”,也就是《晋问》既能够在遵守“七体”文体规范的基础上,即“用其体”,又能够打破名称上的束缚并在题材风格上破格出新,呈现出“破体”的文体创新价值,即所谓“洵所谓‘文成破体’”,承认“拟议变化,一篇跳出耳”[3]904,跳出固有的保守的文体窠臼,这属于“选文以定篇”的经典化过程。 此外,还通过章学诚所载进一步“原始”追溯《楚辞》《大招》才为“《七林》之所启也”,并在枚乘“七发”之命名方法上也推源到《招魂》《大招》,无疑是一种“释名”以彰义。 对此,钱钟书也同样中西汇通,运用中西比较文体学,以见“西土名作如密尔敦《乐园复得》”“又与二《招》、《七》林同类”[3]637,可谓纵横捭阖。
2.“连珠体”文体源流
一方面着眼于“敷理以举统”,在引用“连珠体”史上著名的傅玄《连珠·序》所论连珠应该具有的文体规范,即“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进而补充说明“班固、扬雄、潘勖、蔡邕、曹丕、王粲所作此体”大多不符合文体规范,即“每伤直达,不甚假喻”,同时既对傅玄所肯定的班固“最得其体”提出异议,又指出傅玄所未知晓的陆机《演连珠》才真正“得体”,即“庶足当‘喻美文丽’之目”。 另一方面,着眼于“破体”,指出梁武帝所作《连珠》未能辨体尊体,“全乖《连珠》制构”,并推测这是梁武帝以“帝皇”身份故意为表率,开连珠破体的风气之先,“自朕作古”,那么这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文成破体”,进而以现存梁武帝《连珠》三首为证说明都符合文体规范,不像这一篇为“破体”之作[3]1135。
之后进一步引证明清学者诸如杨慎、梁玉绳、尚镕、何焯、叶树藩关于“连珠体”文体源流的大量文体史料,梳理出“连珠”体源于先秦战国诸子如韩非子,到了东汉班固、扬雄等共同创作才让这一文体名称和规范得以定型,即所谓“盖诸子中常有其体,后汉作者本而整齐藻绘,别标门类,遂成‘连珠’”云云。 再进一步,又追溯到春秋名家邓析子为最早的“连珠之草创”,其后遍数历代诸如汉初刘安《淮南子》、西晋葛洪《抱朴子》、北朝北齐刘昼《刘子》、唐末五代谭峭《化书》等,最后指出,晚清张之洞《连珠诗》之不得体,即“非傅玄所谓‘假喻违指’之体”,近代翻译家严复用“连珠”翻译“三段论法”也不符合其文体本义[3]1136。可见,仅从“七体”和“连珠”,便自看出钱钟书对刘勰“原释选敷”文体研究方法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
3.八股文文体演变
这是继七体、连珠之外较为详尽周全的。 八股文又名八比文、四书文、时文,盛行于明清。 钱钟书在申明其主要源于骈文、四六及其对偶对仗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引述清代骈文派领袖汪中、阮元之论而出以己见。 如《谈艺录》从八股文之文体特征的不同角度进行文体源流追溯:一是先引阮元之论,从八比、对仗的语言特征上追溯到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即“《两都赋》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语公卿二比,即开明人八比之先路”。 二是从排偶的角度,笼统地溯于唐宋四六,即“是四书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为文之正统”。 三是从唐宋四六的角度,对唐宋具体作家作品的追溯,唐代如初唐四杰的杨炯,所谓“暨乎初唐四杰,对比遂多;杨盈川集中,其制尤伙”,中唐柳宗元,引证汪随山“谓柳子厚《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张公墓志铭》中骈体长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二比”云云。 关于宋代,引述宋明谢伋《四六谈麈》、孙梅《四六丛话》,溯至北宋宣和及南宋汪彦章,所谓“谢伋《四六谈麈》谓宣和多用全文长句为对,前人无此格;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三论汪彦章四六,非隔句对不能,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古意寖失。”四是从文体形态角度追溯至唐宋“表”体与唐代律赋,所谓“《四库提要》明胡松编《唐宋元明表》条云:‘自明代二场用表,而表遂变为时文。 久而伪体杂出,或参以长联,如王世贞所作,一联多至十余句,如四书文之二小比。’言尤明切。 皆可与阮汪说印证,惜均未及盈川。 至于唐以后律赋开篇,尤与八股破题了无二致。”五是从八股文“代言”“代圣贤立言”的表现手法上,追溯至南宋初年杨万里,所谓“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 董思白《论文九诀》之五曰‘代’是也。 宋人四书文自出议论,代古人语气似始于杨诚斋。 及明太祖乃规定代古人语气之例。”六是从“代圣立言”和“揣摩孔孟情事”的文体创作心理角度,对八股文大加赞赏,这与五四以来一边倒的严厉批判截然不同,所谓“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皆不足道耳。”七是与上一则“揣摩孔孟情事”关联,从代言摹古的表现手法上,遍引明清诸如徐渭、吴乔、袁枚、焦竑等名家之论,将八股文与元明戏曲文体进行比附对照,说明“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所谓“徐青藤《南词叙录》论邵文明《香囊记》,即斥其以时文为南曲,然尚指词藻而言。 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二论八股文为俗体,代人说话,比之元人杂剧。 袁随园《小仓山房尺牍》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一书,说八股通曲之意甚明。 焦理堂《易余龠录》卷十七以八股与元曲比附,尤引据翔实。 张诗龄《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谓生平举业得力《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 亦其证也。 此类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名曰Prosopopoeia,学僮皆须习为之。 亦以拟摹古人身份,得其口吻,为最难事。”[5]32-33将“八股文”的文学性体现的淋漓尽致,完全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僵化封建的面目中解脱出来,赋予“八股文”以新的生命,并与西方“罗马修辞”加以比照,可以说最能体现钱钟书融古今中西于一体的通达文体观了。
4.“以文为诗”之破体源流
“以文为诗”的破体论内蕴极为丰富,其中以虚字、语助这种文法为诗是其最基本的理论内涵。以此为核心,针对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渊源和文体源流,钱钟书用详实的文献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陶渊明的源头意义。 关于正面的肯定的角度,他从“诗用虚字”和“诗用语助”的“以文字为诗”的文体史角度着眼,通过“自汉末魏晋南朝至唐人遍举”,除了诗骚乐府等篇章之外,历代诗人诗作包括杨恽、曹操、蔡文姬、徐干、陶渊明、沈约、刘绘、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元结、韩愈、元稹、白居易等,最后的落脚点在于,指出陶渊明才是韩愈“以文为诗”的直接文体源头,即所谓“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渊明者”“渊明《止酒》一首,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云云[5]73。 在梳理虚字语助类“以文为诗”的破体源流史中,引用南朝梁刘勰、宋何汶、蔡宽夫、清蒋超伯等经典文论、诗话、诗选加以佐证,同时结合具体作品,颇为详尽,令人信服。
此外,钱钟书对诸如骈体文源流、小说源流、“评点”批评文体之源流、设论体源流、“堆垛物名”的“柏梁体”源流、三句转韵体源流、十二月启源流、山水游记源流、《长笛赋》源流、《僮约》体源流、司空图《诗品》源流等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篇幅关系,不再赘论。
综上所述,钱钟书在文体源流论上,以文体形态个案研究为主,兼顾重要的批评文体和经典的文体命题。 而文体形态选择上,则一方面注重不为人所关注的陌生文体形态诸如七体、连珠、八股文、三句转韵体、僮约体等,尽管新时期以来这些文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钱钟书无疑是较早进行关注并影响了后来研究。 另一方面,即便是柏梁体、启体、游记等常见的文体,钱钟书也主要关注其中的某一类偏僻陌生的文体形态,诸如“堆垛物名”之于柏梁体、十二月之于启体、山水之于游记体等等,这或许对著名文体学者吴承学先生的文体形态研究多选择陌生文体不无影响。
二、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文体发展观
如果说在文体源流论上,钱钟书还主要是对某一文体形态或文体命题进行客观地、平平地梳理、考证和描述,用实例和证据说话,那么,他的诸如“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之类的文体史论或者说文体发展观,则更多寻绎和挖掘背后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因素对文体发展的影响,这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的文学史观有相通之处。
(一)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
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 文体史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发展史。 关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背景因素及其必然趋势,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进行了深刻总结,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云云,而钱钟书则借用同时稍后的梁元帝萧绎所谓“夫时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及其西方“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顾同时风气所扇、一人手笔所出,复因题因类而异”,这两则论断都明确与“体”相关,明显是文学史视域下的文体史批评。
关于前者,钱钟书引用梁元帝《内典碑铭集林序》之“夫时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3]1398,显然,萧绎之论应该是在刘勰影响下形成的:其中,“夫时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 有版本“时代”作“世代”,这与刘勰“时序”篇所谓“文理”“推移”“世代”“与世”“文质”“质文”等,可谓如出一辙,只是“属词之体或异”更为突出明了,用具体清晰的文体体格之“体”代替了模糊宽泛的文学文章之“文”,也进一步说明了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密不可分。
关于后者,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引用西方相似文体史理论,即“诗、文、书、画”各类“艺事之体”都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同,涉及“同时风气”的时代风格、“一人手笔”的个人风格,这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篇的“以时而论”和“以人而论”殊无二致,并称“复因题因类而异”,也即因题材内容和体类分类而不同。 再以古体、今体之时代文体之别和“奏记”体类因“敕定”的限定而具有必用“今体”的文体规范,提出了“时异其体”和“类异其体”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体史理论。 进而以曹丕《典论·论文》之“本同末异”“四科不同”的文体理论来佐证和诠释何为“类异其体”,在主张遵守各自文体规范的辨体论基础上,然后从反面的诸如“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的“破体”形式来对举说明,层层递进,让人叹服,同时提出刘勰所谓“参体”就是“破体”的见解,无疑是研究刘勰文体论之范畴“参体”的一个独特视角[6]888-891。
同样,钱钟书《管锥编》增订所谓“观者不当以文体古今之变”“即人是‘古时’而诗书是‘近体’也”“即与世推移”“祝词何写以隶书”“疏文何行以骈体”云云,如此融合了辨体、破体的文体史观,则是对刘勰“与世推移”文学史观的引申和拓展[3]49。
此外,文学发展观上的复古与革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也是历代文学史的核心问题,尤其唐宋明清以来的文学史可以说就是在这一辩证关系中曲折前进的。 批评史家论及时,大多着眼于宽泛的“文”“文学”“文章”或者具体的诗、文、词文体等,钱钟书则更多关注历代文论史料中不为人所注意的从“文体”角度言说的文献,诸如“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蚪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则于文体复古早持异议”等,往往立足于文体革新,诸如苏绰、李谔的欲革文弊、上书正文体,韩柳的古文运动之古体变革今体,穆修、柳开奋然以起衰革敝自任,及夫欧阳修斐然为之先,王安石、苏洵、苏轼卓尔为之后,乃能蔚成风会,取徐铉、杨亿之体而代焉,梅尧臣的改革诗体,等等。历来文学批评史上的文学复古与革新问题,在这里都成了文体复古与革新的文体史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体革新成功与否的原因,钱钟书认为与帝王提倡无关,即“初无待于君上之提倡、谈士之劝掖也”[3]1551-1553,这与刘勰“时序”篇认为“帝王好尚”是影响文学盛衰的重要因素不同。
(二)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
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经典文学史论域,其内蕴实则是“一代有一代之文体”的文体史问题。 这一命题以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最为著名,堪称是这一论题的集大成和总结者。 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7]王国维这一借鉴西方进化论而形成的文学史观,其文体发展观体现在:“文体之间始终存在以新代旧的竞争法则,旧体自成习套,唯有创新文体......王国维沿着‘兴、盛、衰’的逻辑,指出了文体间和某文体自身的演变规律。”[8]
对此,钱钟书遍引元明清历代学者,诸如:元代虞集,明代叶子奇、李开先、李贽、袁宏道,清代孔尚任、焦广期等七家文献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中虞集所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关于气数”,最与王国维相似,而“亦关于气数”则更具刘勰“时序”篇以来的文学史理论色彩。
其中,每一代之“绝艺”、“文学”及文体最能补王国维之“所不足”,如元明虞集、叶子奇、李开先前后相承,都秉持“绝艺”的学术史视域,其中宋之道学理学为其共同之处,叶子奇补以晋字书法,其实这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而实际上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的关系问题[9]。 自李贽之后明清诸家就大体从“文学”“文体”的角度来变异补充了,最可注意的是,除了孔尚任,其他明清学者李贽、袁宏道、焦广期等都把举业诗文八股文列入其中,并放在文体史的发展中给予极高的评价[5]352,这相当于王国维以“近代文学”的眼光来列举一代之文体,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具学术研究价值和文体史意义。
(三)文体递变,此体可以代兴
“文体递变”是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以上历代文体发展规律进行总结而得出的重要文体史观念,并在此题目纲领之下,反复纵横,引证大量文体文献并出之己意,如剥笋般层层递进,洋洋洒洒,堪称其文体史观念最为集中且体系宏大之论。
与上文一脉相承,钱钟书进一步引述金刘祁、明曹安、七子、胡应麟相似言论来证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和“文体递变”是一个与朝代气运盛衰兴亡相辅相成的文体史规律,其中胡应麟所谓“宋人词胜而诗亡矣,元人曲胜而词亦亡矣”更为准确[5]27-28。 当然,这种文体的盛衰兴亡规律,并不是绝对的一种文体替代另一种文体的简单物理模式,而是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即所谓“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5]28-29。
接下来,钱钟书认为文体的发展和革新,其实就是一种“以文为诗”类的“破体”和“变体”,这与保守的“体制为先”“辨体”论正相对立,即所谓“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这种“破体”可以扩充诗文境域,即“盖皆深有识于文章演变之原”[5]28-31,进一步,钱钟书结合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点,所谓“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指出“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谓某体限于某朝”则不可,其原因正如“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或试其技于词曲”及其“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 唐诗遂能胜唐文耶。 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所以,文体史的嬗变规律是“未尝谓此体可以代兴”以及“后体盛而无以自存,前体未遁而能不亡”[5]28-31。
钱钟书在文体发展观上也同样运用中西比较文体学方法,借用西方“釆生物学家物竞天演之说”,“以为文体沿革”,所谓“所撰《文体演变论》中论文体推陈出新诸例,如说教文体亡而后抒情诗体作,戏剧体衰而后小说体兴,与理堂所谓此体亡而遁入彼体云云,犹笙磬之同音矣”[5]36,可以说是以上观点的一个很好总结。
三、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宋诗体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自南宋以来便引发广泛争议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命题,也是当今古代文学领域引起学者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话题。 某种意义上说,元明清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争鸣都是在其笼罩下进行的,其实质则是关于“唐宋诗体之争”的文体史和文体批评史问题,也即钱钟书所总结的“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之论断。 所谓“朝代之别”,这正是传统上固化的普遍的文学史和批评史观念,而“体格性分之殊”则体现了钱钟书敏锐鲜明的文体史和文体批评史学术视野。 所以,尽管如钱钟书所云“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且历代相关诗学文献浩如烟海,不过如钱钟书这样完全从文体史视域进行集中观照和总结者却极为少见,这对于“唐宋诗之争”研究视角的转变、文学史和批评史的重写及其古代文体理论批评体系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诗分唐宋”这类以文体史代替文学史划分的观点反复申说,所谓“力持异议,颇不乏人”,我们分开来看,层层剥笋,以见大概。
(一)“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脗合”
针对“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这种“乃谈艺者之常言”的按朝代更替和世代变迁的普遍文学史观念,钱钟书认为历代就有“力持异议”的人。 如元末明初苏伯衡批驳元“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是因为他的“始音、正音、遗响”诗体分类三分法未能按照盛衰正变的时代发展规律也即文学史观念来划分,所谓“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云云的“文体史观念”。 针对苏伯衡的观点,钱钟书也“力持异议”,认同杨士弘的文体史观,所谓“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脗合”[5]1-2,这也与刘勰“时序”篇以来的治乱盛衰文学史观针锋相对,揭橥其鲜明的文体史观,这于当下学界的文体史编纂及研究的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二)“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文体的两个基本内涵分别是“体裁”和“风格”。 钱钟书上文先论“体裁”,接下来就以“风格”和“体格性分”的文体史观来反对四唐朝代之别的文学史观。 钱钟书通过引证清康熙年间姜西溟驳斥钱谦益而提出的“四唐不可以作诗者之年月论”,明确提出初盛中晚的四唐之分并不是按照“年月”“世代”划分的文学史观,即“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而是一种“风格之分”的文体史观,在这里“文体”指“风格之分”或者说“体格性分之殊”,所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5]2,这样就把其四唐“文体史观”的理论内蕴明晰地呈现出来。
(三)“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
通过中西文体学比较方法,钱钟书借德国席勒“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谓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更为明确。 这里的“体制”表层含义似乎是上文第一则的“体裁”,但是根据席勒所云“真朴出自然”与“刻露见心思”的“德”“巧”之义,则更倾向于体格风格内涵[5]3。
接下来的三则也同样是着眼于“诗体”之风格体格性分之义包括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来进行唐宋诗之辨,也即从诗体史的角度来看唐宋诗之争这一向来的诗史论争。
(四)“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 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钱钟书所谓“丰神情韵”和“筋骨思理”是一种以“人体之喻”来辨析唐宋诗“诗体风格”的文体史观念,而“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 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云云,则更是明确了唐宋诗之争不是着眼于唐宋朝代之别的文学史观念。 当然,像所有文论观点的提出都以详实的文献证据为基础一样,关于“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一为现当代文学史、批评史学者所熟知并频频引用的经典论断,钱钟书也以严羽和杨万里的相关观点为证,但是其刻意而发的“文体史”观念的良苦用心却往往为人所轻忽,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5]2。
(五)“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 关于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上复古主义的宗唐学唐和宗宋学宋之分歧,在此理论意义上,钱钟书引证清初叶燮所谓“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之论,认为这与每个人的气质禀性不同有关,且同一个人也因年事岁月增长及少年与晚年性格个性的变迁,在宗唐宗宋上选择适于自己禀赋气质的诗体风格和类型,也即“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 并且客观上一个人“由唐转宋”诗风的转变与其一生少年与晚年不同时期的仕宦思想变迁息息相关,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体选择,对此钱钟书以明代复古派“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为例,其前期的诗学主张就是提倡“诗必盛唐”,但晚年《续稿》之作却转向“宗宋”“用宋”,并再举清初钱谦益以及近代湖籍诗人陈锐(抱碧)、程颂万(十发)三人亦晚年“由唐转宋”的学诗作诗经历为佐证[5]3。
(六)“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
在论唐宋诗之争源流的基础上,即“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引用“戴昺《答妄论唐宋诗体者》”并驳斥其“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观点,认为“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说明“格调”即风格体格,“诗体”与诗人的性情性格密不可分;“格调”即“诗体”,唐宋诗之争就是戴昺所谓“妄论唐宋诗体者”,尽管观点相悖,但不影响说明二者的关系为“唐宋诗体之争”。 进而引证叶燮关于“前七子”李攀龙和何景明的“读唐书”与“入宋调”之论,最后得出又一个经典的唐宋诗体之争的论断,即“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也进一步说明唐宋诗体之争主要是“气质之殊”,也即为诗人禀赋气质性格个性关联的风格体格之不同。 同时进行中西文体学比较,引述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的“精神”和德国谈艺者的文体“形态”及其“作家才情”来说明这一“气质”“气禀”的文体风格含义[5]5。
(七)“随园论诗,深非分朝代、划时期之说”
通过引述潘德舆称道袁枚所谓“随园论诗,深非分朝代、划时期之说”之论,反复“重言申明”所谓“则似唐宋诗胜元明诗也”“则不仅分别时期,抑且谓宋元迈出唐人也”“则似谓唐诗胜宋诗也”“可据以分宋唐”“则似谓唐诗胜宋诗也”“则亦以唐诗为胜宋元也”“则宋、元、中晚唐又后来居上也”云云,以见唐宋诗之争的高下优劣之争,并不是“分朝代、划时期”的文学史之争,而是体裁风格的唐宋诗之诗体之争[5]214-217。
(八)“宋人好唐诗”,“且唐与宋奚辨”;“宋人率而唐人练,宋人浅而唐人深也”“宋人之诗乎,唐人之诗乎”
钱钟书引述明代何乔远、曾异前所列之论,以驳严羽以来唐宋诗之争中的唐诗胜宋诗之论,借徐叔亨驳斥宋人“浅率”而唐诗“深练”的朝代之别也即唐宋之辨,进而推尊“宋诗”,抬高宋诗的文学史和文体史地位,这也是钱钟书在唐宋诗之争的基本观点[5]472。
(九)“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
关于唐宋诗之争,钱钟书所论主要是为了推尊宋诗,推尊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以文为诗”,但是又主张辩证地看待宋诗,认为宋诗具有“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这是“以文为诗”的文体特征,并指出“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进一步说明“唐宋诗之争”主要是“诗体”之辨,而且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是前后沿承的关系[10]7。
(十)“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不像之处恰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前面提到,唐宋诗之争是关于宗唐宗宋的文学创作师法对象问题,其中也包括宋人学习唐人之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发展观,也就是钱钟书引证并肯定皎然《诗式》中“复古通变体”的文体复古革新问题,所谓“认为‘通变’比‘复古’来得重要而且比较稳当”,并提出了“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这一为现当代文学史家所频频引用的经典论断,这实际上是清代蒋士铨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尴尬境地,进而说明宋人在唐诗这座高峰面前,学习继承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代表形成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生新瘦硬风格,也就是“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学唐诗而不像唐诗”,“不像之处恰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10]10-12。
(十一)“诗莫丑于宋人”,“诗之衰,至宋元而极矣”
钱钟书通过历数金人王若虚、清初吴伟业、屈大均等推崇宋文而贬低宋诗的观点,诸如“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诗之衰,至宋元而极矣”“诗莫丑于宋人”等,进而提出反对意见,推尊宋诗并抬高其诗史和文体史地位[5]612。
(十二)“文章体制,省简而繁,分化之迹,较然可识”,“谈艺者固当沿流溯源,要不可执著根本之同,而忽略枝叶之异”,“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
钱钟书的文学史观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有集中体现,而文中更多是用文体史观来反映他的文学史观。 例如通过宋诗之“以文为诗”的“严于辨体之证”,说明“惟其辨别文体与诗体,故曰‘以文为诗’”,进而说明这种“以文为诗”的破体变革,正是文章体制“分化之迹”和“沿流溯源”的文体发展规律。 同时进行中西文体学比较,以“吾国”之“文”与“西方”之“verse”对比,提出“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唐诗和宋诗因时代风气不同,故而唐诗诗体“风格”“体格”也“面目”各异,也因此“须各还其本来面目”,不可“削足适屦,以求统定于一尊”[6]95,这才是研究唐宋诗之争的正确学理路径。
总之,“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11]。 近四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硕,论文多达六十余篇,而钱钟书作为这一论争的理论总结者和新时期以来研究的启蒙者,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结 语
综上所述,钱钟书的文体史观有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对待普遍认同并形成共识的传统文学史观念诸如“文原五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宋诗之争”等经典命题,因其从文体学的角度切入而显得别开生面,体现了鲜明的文体意识,这对于将文学史与文体史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其二,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 无论是对于系列陌生文体形态个案研究的“原始表末”,还是对一些文体理论经典命题的推源溯流,都能够旁征博引而出以己意,并且很多文体文献都是稀见偏僻和众所忽略的珍缺史料,至今也还为现当代文体学者和文学史家所忽略,令人唏嘘,希望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和后续研究。
其三,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 钱钟书对待传统的文论范畴和文体观念往往能够别具手眼,于经见处出以新意,但总是辩证看待而不会截然否决。 掇拾几例,如“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脗合”“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等,所谓“固当”“非仅”“多以”“非必如”“不必尽”“要不可”“非曰必出”“特举大概而言”“是大幸也是大不幸”云云,可以管窥钱钟书的文体通变观。
其四,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 钱钟书的这一文体通变观及其学术方法论,就如党圣元先生所云:“在文化发展观方面,钱氏是一个‘通变’论者,主张古今、中西融会贯通,反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打通’古今、中西以及人文学科各科之间的樊篱,融通观之,既是钱学方法论的特点之一,也是钱氏的研思目标,所以具有观念和方法两方面的开创性意义。”[12]文体史上的古今沿流溯源往往从先秦两汉至明清近代乃至民国现代,史料证据信手拈来,在在可见。 至于中西融通比较上,本文统计一下,共十一处,包括英国密尔敦《乐园复得》之类“七体”、意大利罗马修辞教学Prosopopoeia 以类八股文代言之体等等,可以说都是其文学通变观及其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再如林玮生也认为钱钟书关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共同诗心”,“让人认识到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文论在交叉阐发中存在的‘同构性’”[13]。
要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在古代向当代文体学研究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链条作用和启示意义。 文体学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引人瞩目的学术增长点,而作为文体学的一极,虽然文体史具有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兼容并包的学科属性,但是并未引起文体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希望通过对钱钟书文体史观念的初步研究,将中国古代文体史研究推向深入,为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树立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