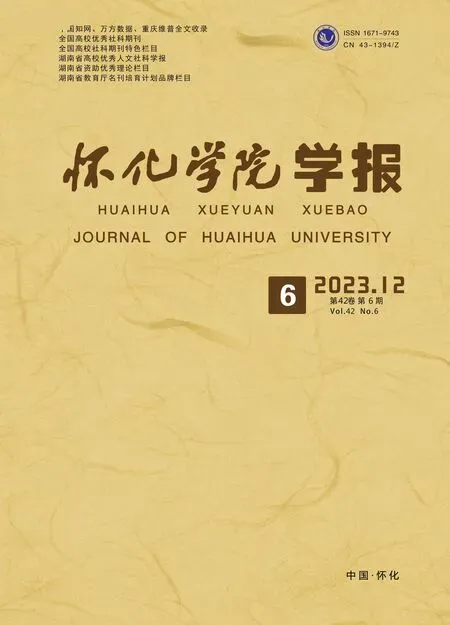从行先蚕礼论唐前期皇权沉浮
2023-03-15卢玉玮贾发义
卢玉玮, 贾发义
(山西大学,山西太原 030006)
先蚕礼作为皇后所主持的国家最高祀典,彰显了皇家对农桑的重视。据《通典》记载,唐代的先蚕之礼集中于肃宗之前,尤以高宗、玄宗两朝为盛。肃宗之后,因鲜少有皇帝在生前册立皇后①,故再无皇后行先蚕礼的记载。先蚕礼的举行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愿景,但有时这一祀典的举行也与皇权的沉浮有关。高宗时期,武后曾多次亲祀先蚕,其背后另有内涵,不能将之一概论为统治者祈求物丰民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禅位于太子李显,史称“神龙政变”,此虽迫使武则天提前还政于李氏,但其他有权势的女性不愿就此远离朝堂回归于深宫内苑,武则天虽退出政治舞台,但是政治权力并未全部聚集于皇帝手中。在多方势力的干涉下,中宗的皇权愈发卑弱,韦后一党借机炮制祥瑞之兆,为自己造势,可见这一时期皇帝权威之脆弱性。延和元年(712)八月,睿宗禅位于太子,此后如何摆脱武周时代的阴霾以及女性政治所带来的挑战成为玄宗无法回避的问题。先天二年(713)三月,玄宗就恢复了搁置已久的先蚕礼,数月之后玄宗通过先天政变翦除太平公主一党,这场权力之争以玄宗的胜利而告终。消灭太平公主等政敌只是玄宗重塑皇权的一个起始环节,如何彻底否认女性政治存在的合法性更是玄宗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王皇后于开元二年(714)和开元七年(719)再度行先蚕礼,如此频繁的举行先蚕礼,或可被视为玄宗试图收官武周以来的女主政治,从礼制上终结武周以来的乱象。
学界有关唐前期政局研究的成果颇多,主要以高宗②、玄宗③两朝为研究重点。但是鲜有学者以“先蚕礼”④为中心进行论述。本文试图以唐前期皇后行先蚕礼为中心,分析高宗数次举行先蚕礼背后的内涵,追溯中宗时期韦后是如何通过献《桑条歌》来扩大自己权势的,并探讨玄宗如何利用先蚕礼重塑李唐皇权。
一、先蚕礼源流及初唐行仪
先蚕礼始于周朝,史籍对周王后、诸侯夫人行先蚕礼有着详细的记载:“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1]汉代也继承了这一礼制,只是关于先蚕地点发生变化,从原先于北郊先蚕变为“蚕于东郊”[2]。东汉之后战火频仍,但史籍中依然保存了部分政权先蚕礼的运作流程以及皇后行先蚕的记录:
“魏文帝黄初七年,皇后蚕于北郊,依周典也。晋武帝太康六年,蚕于西郊。……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蚕所,设兆域,置大殿,又立蚕观。北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外。……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六宫三妃、三、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少牢亲进,祭奠先蚕西陵氏神。礼毕,降坛,令二嫔为亚献终献,因以躬桑。隋制,先蚕坛,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币,祭先蚕于坛上,用一献之礼。”[3]
魏晋以来各政权对此礼的保存为后世先蚕礼奠定了基础。及至唐代,“皇后以季春吉巳享先蚕,遂以亲蚕”[4]。贞观元年(627)长孙皇后便首次行先蚕礼,《资治通鉴》载:“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5]彼时距离玄武门事变还不足一年,太宗刚经历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内忧虽解,但仍有外患。武德九年(626)颉利可汗率兵直逼长安,在太宗的主导下唐与突厥缔结“渭水之盟”,突厥退兵,但此事仍令人心有余悸。因此无论是为了巩固皇权还是为了维稳政局、安定民心,太宗都亟须进行皇位以及王朝合法性的构建,而“古代国家祭祀的仪式性表演能够建构人们的合法性信仰”[6]。长孙皇后与太宗感情深厚,是太宗成就贞观之治不可或缺的伴侣,因此由长孙皇后来主持这场仪式性表演并无不妥。在人为的推动下,先蚕礼作为一个重要政治符号重现,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诉求通过举行仪式得以彰显。数年之后,贞观九年(635)三月,“文德皇后率内外命妇,有事于先蚕”[7],长孙皇后虽两度率命妇行先蚕礼,但先蚕礼在贞观年间尚未正式列入国家高级祀典的范畴,高宗即位后对国家祭礼进行了调整,先蚕礼的等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武后行先蚕礼——高宗权威的自证
《唐会要》记载:“永徽三年三月七日,制以先蚕为中祀。后不祭,则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农。”[8]所谓中祀,即仅次于大祀的国家高级典礼。永徽年间高宗将先蚕礼列为中祀,可见对先蚕礼的重视。吊诡的是,史籍均无王皇后行先蚕礼的蛛丝马迹,此事也许是高宗有意为之,结合同年七月立陈王忠为太子一事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9]
《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并未有异,但是从两唐书的记载中可见立陈王为太子一事颇为曲折,《旧唐书·燕王忠传》载:
“时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10]
《新唐书·燕王忠传》载:
“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11]
以上三份文本还原了高宗立陈王忠为太子的过程:王皇后与其舅父柳奭谋立陈王忠为太子,当王皇后向高宗提出请求时,此事很可能遭到了高宗的拒绝,所以才会有之后柳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联合请立陈王忠为太子。可以佐证此论的正是史料中所用的“固请”“继请”等词。“先行前来说服皇帝的人都遭到皇帝的拒绝,所以才有大人物们陆续出场。正是因为皇帝坚持拒绝,所以才有大臣们‘继请’和‘固请’”。[12]王皇后虽如愿立陈王忠为太子,但这件事也暴露了一个足以令她日后陷入险境的问题:她与高宗并非政治盟友,甚至可能存在对立关系。这件事发生在以先蚕礼为中祀之后,但是之后几年史籍中也并无王皇后行先蚕礼的只言片语,似乎可以说明高宗并不希望王皇后参与先蚕礼或者说他不希望留下王皇后与先蚕礼有关的记载。
显庆元年(656)三月,武后首次行先蚕礼于北郊。《文献通考》载:“显庆元年三月,皇后有事于先蚕。总章二年三月,皇后亲祠先蚕。咸亨五年三月,皇后亲祠先蚕。上元二年三月,天后亲祠先蚕。”[13]高宗一朝先后四次行先蚕礼,可见先蚕礼在这一时期颇受重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显庆元年(656)是高宗在位的第八年,先蚕礼为何会在此时举行,难道仅仅是因为高宗对武后的情感吗?若将视野置于永徽时期政局,或许能窥见一二。
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离世前,“引无忌与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遗令辅政”[14],由此确定了高宗执政之初的政治模式。但是“这种遗令托孤往往只是老皇帝一厢情愿,新皇帝和这些老皇帝所信托的顾命重臣一般多无历史渊源,未必乐意接受这种监护式辅政”[15]。况且高宗即位时正值青年,已非需要监护的稚子。永徽六年(655)“废王立武”之后,两位辅政之臣也先后被清除出权力中枢。旧史在提及高宗执政的三十余年时,格外注重永徽时期的统治,这与永徽时期重臣辅政的政治模式有很大关系,《新唐书·长孙无忌传》为永徽政局冠以“永徽之政”的名号:
“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气。帝亦宾礼老陈,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也。既二后废立计不合,奸臣阴图,帝暗于听受,卒以屠覆,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16]
《新唐书》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失势视为“贞观风气”的终结,此后大权尽归于武氏。《资治通鉴》在提及永徽时期的政风时也曾言:“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17]史家关于“永徽之政”的说法不啻为将永徽时期所取得的成果视为贞观之治的遗产,而这种叙述模式事实上也是在暗示长孙无忌倒台以后,唐高宗的政治成就实在乏善可陈,永徽之后的数年执政只是在为武则天掌权进行铺垫。孟宪实指出:“高度评价永徽时期,其实质意义是从一个角度对显庆此后的政治进行了否定。”[18]对于高宗而言,当托孤辅政的政治模式结束,为了防止彼方势力反扑,他必须采取诸多手段来巩固权力,“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将权力仪式化,借以宣扬皇帝的权威”[19]。正如大卫·科泽所说:“权力神圣化的逻辑结果就是统治者的神圣化,即统治者既不依靠武力更不依靠幻象,而是以赋予他的超自然力量进行统治。”[20]由此可知为何自显庆元年(656)始,高宗对先蚕礼的举行乐此不疲。
上元二年(675)武则天最后一次行先蚕礼,史载:“三月丁巳,天后亲蚕于邙山之阳。”[21]这次先蚕活动“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22],远远突破了皇后应该享有的规格。此举不禁让人回想起麟德二年(665)四月,高宗曾经“讲武于邙山之阳。”[23]有学者认为,武则天在邙山行先蚕礼是为了显示自己与高宗平起平坐的地位[24]。此时高宗虽常年苦于风眩之症,但尚未病入膏肓。此举恰恰证明了高宗与武则天二人在政治上的配合,“高宗将武则天视为其皇权的延伸,甚至提高到充当皇帝政治代言人的角色”。[25]武则天并无外戚与勋臣的协助,她能重回宫廷乃至被册立为皇后都源于高宗的支持。若言永徽时期高宗与王皇后在政治上已然分途,那么武则天与高宗则是同处一个阵营的盟友。先蚕礼本就是皇后率领命妇所进行的国家高级祀典,此举能令武皇后身份合法化,武则天权威的塑造又何尝不是高宗皇帝权威的自证?换言之,“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是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而政治权力也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强制,而是力图呈现为一种合法合理的运用”。[26]高宗之所以会大肆利用先蚕礼,除了看重先蚕礼所承担的政治功能,还因为诸礼之中唯有这一祀典能够在促使皇后权力名正言顺的同时巩固皇帝权威。但是先蚕礼若要取得如此成效存在一个前提,即皇帝与皇后务必为政治同盟。一旦帝、后二人出现分歧或者皇帝势弱、皇后强势,那么先蚕礼就不会发挥维护皇权的作用而是变成皇后结党营私的工具,中宗与韦后就是例证。
三、献《桑条歌》——皇权羸弱的产物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武周王朝终结,“后武周时代”⑤拉开了帷幕。张柬之等五人因功封王,显赫一时。然而翌年,五人获罪被贬以致客死异乡。张柬之等人有此下场,与武三思等政敌的攻讦不无关系,但是中宗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敬晖被贬的诏书可看出中宗对五人的态度:“晖等因兴甲兵,划除妖孽,朕录其劳效,备极宠劳。自谓勋高一时,遂欲权倾四海,擅作威福,轻侮国章,悖道弃义,莫斯之甚。”[27]这充分说明了中宗对五人未能审时度势、收敛锋芒的强烈不满。五王贬官赐死只是中宗为抑制五人权势的最后一击,复位初期,“中宗首先仿效其父高宗当年引武则天参政以打击元老重臣的办法,也引韦皇后、上官昭容等干练的后妃参预朝政,借以限制外朝相权”[28]。但是中宗在朝中没有可托付的亲信,因此在罢黜五王之后,中宗的皇权并未因此有所加强,直接受益者反而是韦武一党。中宗本想效仿高宗抬高皇后地位以强化皇权,但是韦后与武后当年所面临的环境实在是大相径庭。武后之所以能得高宗青睐结为盟友,除了个人感情外,主要缘于她在朝中并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而韦后与中宗并非亲密的政治伴侣,韦后自身也有称帝的野心,并且与武三思、上官婉儿等人过从甚密。神龙元年(705)五月,上官婉儿就曾劝说韦后“袭则天故事”[29],虽未立刻改朝换代,但韦后也在积极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假手韦、武除去五王之后,中宗“再无可以凭借的政治势力,因而无法改变皇权卑弱的状态,只能听任韦武摆布”[28]。
神龙元年十一月,在中宗的支持下,群臣曾为韦后上尊号“顺天皇后”。但彼时中宗复位不久,曾经大权旁落的经历如芒刺背,对五王拥立之功也颇为忌惮,正如他的尊号“应天”是顺应天意,此时帝、后同上尊号表明中宗急于证明其皇位之合法性,但这助长了韦后的权势。神龙三年(707)八月,中宗再加尊号,随后宗楚客“率领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30]。此次帝、后加尊号恰好为节愍太子发动政变后的一个月,因此绝非巧合。景龙元年(707)太子李重俊因谋逆被诛,此事与韦后一党长期以来对李重俊的打压有直接关系。《旧唐书》载:“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31]李重俊起兵后先杀武三思父子而后直入宫禁“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32]。这场政变以太子被杀告终,而其政敌武三思父子二人虽死却仍获追封,韦后也于次月再与中宗同加尊号。韦后上尊号虽也经由中宗首肯,但此时,上尊号的意义更多是利于己身,而非利于中宗集中皇权。景龙政变之后,韦后逐渐开始大肆制造自己的“祥瑞故事”。景龙二年(708)“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33]同月,迦叶志忠上表进《桑条歌》十二篇,在皇后行先蚕礼时所用音乐的问题上借题发挥,来迎合韦后神化自我的企图:
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五行六合之内,齐首蹀足。应四时八节之会,歌舞同欢。岂与夫箫韶九成,百兽献舞。同年而语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为盛。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34]
迦叶志忠提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等帝未受天命之前,天下百姓皆传唱歌谣,这种将前代英主与当今圣上并列以美化帝王的方式并不罕见。但显然,迦叶志忠上言的根本缘由是为了迎合韦后而非中宗,否则也无须提及则天皇后。迦叶志忠将永徽时期民间传唱“桑条韦、女时韦”[35]等民谣与韦氏受命封后相结合其意昭然若揭。“在中国古代,祥瑞、音乐、歌谣等事务本质上属于政治,它们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也是特定时代变革的预兆,常常被用来预言以及证明政治权力变更的合法性,而韦后以祥瑞、音乐、歌谣为自己受命大造舆论,其称帝的政治野心可见一斑。”[36]这种舆论造势远远高于皇后行先蚕礼本身能带来的功效,皇后本就为先蚕祀典的主持者,如今传出韦氏封后前民间就有此歌谣,更可体现韦氏“顺天皇后”乃是顺承天意。
即便韦后从未正式主持过先蚕礼也无关痛痒,因为她已经通过对“桑条韦”大做文章,以一种看似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高宗时代曾为帝、后两人巩固权威的先蚕礼,如今与民间歌谣一同成为韦后扩大势力的工具。正如先蚕礼曾经被高宗用作自证其权威的工具,这一礼制在不同的帝王手中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宗因皇权卑弱为韦后谋私提供了可能,待到强势君主主政,先蚕礼便会再度成为维护皇权的礼制。
四、重行先蚕礼——玄宗抵制女主政治
先天元年(713)“三月辛巳,皇后亲蚕,自嗣圣、光宅以来,废阙此礼,至是重行”。[37]此时玄宗即位不过半载却急于恢复一个已被废止数十年的典礼,此举实在令人疑惑。但若仔细思量唐隆政变之后盘根错节的政治局势,也许可以诠释玄宗此时恢复先蚕礼有何内涵。
景云元年(710)七月,相王受禅登基。唐隆政变之后,政局看似再度恢复平稳,但政变只是对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的清算,而并未影响女性的政治话语权。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姑侄二人在政变时虽为同盟,但此时早已势如水火。太平公主多次散布流言中伤李隆基,企图更立太子,史载:“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38]《资治通鉴》还记载太平公主曾在太子身边安插眼线以监视太子的举动:“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39]而睿宗作为天子,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与宋璟向睿宗秘密进言,请求将太平公主迁于东都以安东宫,而睿宗却认为:“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虑。”[40]睿宗的一番话似乎对太平公主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保持中立态度。
对于睿宗这种游移的态度,李锦绣认为:“睿宗看似依违于太平与太子之间,实际上,睿宗是使二人两相牵制。隆基因有太平而储位不稳,太平因有太子而不能像其母一样取兄而代之。”[41]从史料来看,这番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延和元年(712)七月,睿宗决定传位于太子时的一席话也体现出他心中城府:“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犹亲巡守,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42]睿宗此语说明他只是让出皇帝之位,却不想将权力完全让出。正因如此在禅位之后,“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43],这种做法难免让玄宗有掣肘之感。而太平公主倚仗着睿宗,“连结将相,专谋异计。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44]玄宗皇位合法性来源于睿宗的禅让,所以相比于上皇不愿放权,太平公主结党擅权更让玄宗无法忍受。
先天二年(713)三月在玄宗的授意之下,王皇后行先蚕礼。这一举措显然不可能是因为重视农桑,而是玄宗长期以来对太平公主等强势女性在政治上过度插手的不满与反击。此时行先蚕礼无疑是玄宗想整饬女性过度干政的政治乱象,尽可能地缩小上层女性参政的范围,也是玄宗这一新兴政权希冀“透过符号展现出它比前任更具优越性,或通过复兴更为古老的政治象征建立自身的认同和合法性”。[45]先天二年(713)七月,姑侄二人矛盾彻底爆发,玄宗发动政变,“这一次政变是玄宗登向权力巅峰的惊险一跃,它终结了自武后开始的女眷政治,也决定了此后的历史走向,其意义之重大毋庸置疑”[46]。政变成功之后睿宗彻底放权,玄宗下制:“朕承累圣之鸿源,荷重光之积庆。昔因多难,时属构屯,宝位深堕地之危,神器有缀旒之惧。”[47]可见其与太平公主一党斗争之不易,而“多难”的源头在玄宗看来当然是武周以来女性过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为了避免再出现皇权式微的险象,玄宗利用礼法对上层女性的政治身份进行限制,“开元二年正月辛巳,皇后亲蚕”[48]。数年之后,开元七年(719),“季春吉巳,享先蚕于西郊”[49]。开元年间两次举行先蚕礼意味着玄宗迫切需要终结武周以来女性执政的状况。先蚕礼其实无异于一场政治表演,“正如语言符号的意义依赖于谁对它的运用一样,合法性象征符号虽然只是一般的‘所指’,但一旦它被谁运用、操作或表演,其意义‘所指’,谁就成为制度的‘所指’,成为制度的合法性叙事的指向”,[50]玄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提升李唐权威,将上层女性规范于新的政治框架中。
先蚕礼为祭祀蚕神之礼,彰显了国家对农桑的重视。贞观元年(627),为了皇位以及王朝合法性的构建,长孙皇后行先蚕礼,这一礼制作为一个重要政治符号得以重现。但此时先蚕礼尚未被正式列入国家祭祀系统,直到永徽三年(652)先蚕礼才被提升为中祀。高宗时代,先蚕礼俨然是权力仪式化的重要环节。“废王立武”之后,武后多次行先蚕礼,其背后暗含高宗欲通过此举自证权威,因此这不仅是武则天权威的塑造,也是高宗皇权仪式化的重要一步。中宗时期,皇权羸弱,韦后通过制造祥瑞、授意其党羽献《桑条歌》十二篇神化自身以进行政治角逐。玄宗即位之后恢复了搁置已久的先蚕礼,此举说明玄宗试图依托先蚕礼纠正上层女性自武周以来过度参与政治的状况,从礼制上终结武周以来的政局,让女性发挥原本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
注释:
①自玄宗废王皇后之后,唐代皇帝在生时立后者,唯有肃宗、德宗(昭德皇后于封后当天去世)、昭宗三人。学界关于唐帝王生前未立皇后的讨论集中于玄宗、宪宗二人。黄永年先生认为玄宗正是出于对后妃干政有着清醒认识所以在废黜王皇后之后,不论是宠幸武惠妃还是杨贵妃,都不愿再授其皇后权柄,见黄永年“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燕京学报辑刊》,2003 年第15 期。李文才指出玄宗废黜王皇后之后不立皇后是出于防范后妃干政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政治行为,并提出防范后妃干政才是宪宗不立皇后的根本原因,见李文才“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2 期。黄永年先生也在《唐史十二讲》一书中也指出,懿安太后未能在宪宗朝成为皇后更多还是从政治上考虑,见黄永年《唐史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7 年。可见唐后期多数皇帝未能在生前立后与忌惮后妃干政一事有直接关系。
②高宗朝政局一直为学界研究之重点,故此处只简要梳理。参见:李鸿宾,梁民“唐高宗武后东巡及其政治的转化”,《理论学刊》,1992 年第2 期;孟宪实“论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事”,《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2 期;李琰“唐高宗乾封封禅与其权力回拢——以武则天降禅亚献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6 期;吴丽娱“试论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文史》,2016 年第1 期;李永“唐高宗、武则天政局与大明宫的重建与塑造”,《中华文史论从》,2019 年第3 期,等等。
③余海涛认为开元之初唐玄宗开始了以革除武周、重建女性与政治关系、神化李唐为中心的开元革新运动,见余海涛“后武周时代女性政治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周其力探讨了自中宗以来李旦政治势力的消长以及禅位前后与玄宗之间的政治矛盾,见周其力“唐睿宗政治势力的消长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李锦绣提出睿宗、玄宗父子在唐隆政变成功后即已产生矛盾,太平公主在与玄宗的斗争中实际上也有睿宗的支持,见李锦绣“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原学》第3 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年,第161-179 页。唐雯认为玄宗与睿宗即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就有着激烈的政治较量,政变成功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的权力,见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3 期。此外,唐雯还通过墓志资料探讨了先天政变前夕太平公主与玄宗对北衙禁军统领权的争夺,见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中华文史论从》,2014 年第4 期。
④学界有关先蚕礼的研究多集中于清代,唐代先蚕礼的研究成果较少,参见:宗宇对历代皇室后妃亲蚕历史和先蚕礼仪进行了追溯,虽涉及唐代,但并非其研究重点,见宗宇“先蚕礼制历史与文化初探”,《艺术百家》,2012 年第S2 期。范芷萌梳理了唐代先蚕礼的举行仪式,认为先蚕礼常被干政欲望强的女性用来扩大自身政治势力,是政治角逐中的有力工具,见范芷萌“唐代先蚕礼探析”,《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 年第4 期。
⑤余海涛在“后武周时代女性政治研究”一文中将后武周时代界定为具有武周时代特征且武周时代的影响还持续存在的一段历史时期。文中认为后武周时代起自神龙元年(705)的神龙政变,止于开元十三年(725)的开元封禅。参见余海涛“后武周时代女性政治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