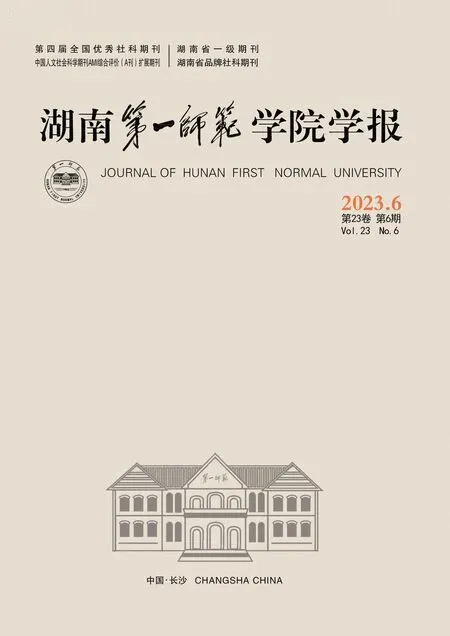接受与流播:韩国潇湘八景诗中的“恨别思归”
2023-03-14文偲荇
韩 燕,文偲荇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一、韩国对潇湘八景与“恨别思归”情感的接受
“潇湘八景”原指分布在湖南湘江至洞庭湖沿岸的八处胜景,后因其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八个主题被历代无数文人墨客用于文学与绘画创作中,便逐渐成为融合人文精神及美学情感的文学主题。提及“潇湘”,便使人联想到其清幽、朦胧、浪漫、忧郁的文学色彩。我国的潇湘八景诗画在北宋晚期通过使团传入朝鲜半岛,此后,在绘画创作和文学审美方面引起众多韩国文人画士的追捧和效仿,掀起一阵阵创作热潮。
早期的潇湘文学中的湘妃传说和屈原的左迁流寓文学就十分契合地展现了“恨别思归”思想情感的始源。而潇湘文学中的离恨思乡之情也不断地被发展延续,最终形成了“恨别思归”情感雏形。它脱离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成为各种文学、艺术乃至情境的代名词,随着潇湘八景文学艺术的东传,其中蕴含的“恨别思归”情感主题也开始通过具体的作品为实物载体被韩国文人接受。探究韩国文人对我国潇湘八景文化与“恨别思归”情感接受的原因,具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文化与汉文学的盛行。中韩毗邻而居,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尤其是在七世纪后期新罗借助唐朝力量统一后,朝鲜半岛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得以快速发展,中韩之间的交流联系也空前密切。当时的亲密关系不仅表现为唐宋时期两国大量进行商品交易、物物交换,还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礼制及文化的学习。如新罗时期,韩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将官制改为与中国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模式相似的制度,仿效唐制设立了国学和读书三品科,将《论语》《孝经》《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毛诗》《文选》等汉学经典作为考试科目选拔官吏[1]849-1019,仿汉制,将汉学经典作为官方教材的政府行为,在当时的韩国社会掀起了狂热追捧汉风汉学的新潮流。在这种“请章服从唐制”的浓郁氛围下,韩国几乎事事皆与汉风看齐,大至庆州黄龙寺、芬皇寺的建筑风格,小至新罗妇女的衣服头饰等,无不仿自长安遗风,带有深厚的唐风余韵[2]。而汉文学之风在韩国社会的影响同样源远流长,宋朝时,不仅有官方直接向高丽王室赠书的传统,还存在着更为活跃的民间书籍交流现象。不少穿梭于两国之间的民间商人通过挟带走私的方式将题材更为多样的汉文书籍私下运往高丽,狂热的“慕陶”与“学苏”等仿汉文学思潮也成了当时韩国文坛的新风尚标,由此创作而出的汉文作品一度成为两班文人争相追捧、热烈讨论的焦点话题。高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的潇湘八景诗画也是当时韩国文人效仿与追捧的对象。由此,从君主到平民阶层,从文学到艺术、建筑等各方题材和领域,中国的潇湘八景文化在韩国盛行了约700 年之久。
其次是动荡时局对文学思潮的影响。高丽毅宗年间,武臣发动政变罢黜毅宗,这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武臣之乱”的开端。“武臣之乱”的出现与高丽一直以来重文轻武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样的制度下,武臣们常年积压的不满在某一个时刻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在这次政变中,武臣们喊着“凡戴文冠者,虽胥吏,杀无遗种”[3]329的口号,使用武力清洗了当时的文官群体,改变了由韩国两班贵族们所主导的社会阶层结构,同时也彻底颠覆了原来以文臣为核心的“文尊武卑”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样貌。于是,众文臣受制于武臣统治的高压,政治抱负无处施展,一度面临着被打压到需要远遁于丛林之间来避祸的地步,进取仕途的远大志向亦随着社会动荡而冷却。此时,传入的潇湘八景文学就恰好点燃了韩国受迫害的文人们隐藏在心底最真实的“恨别”之意。“草屋半依垂柳岸,板桥横断白苹汀。日斜愈觉江山胜,万顷红浮数点青。”[4]397高丽时期诗人李仁老诗中描绘的美景映照下的自然山水,显得比平时更加美丽动人,而天下江山在诗人的眼中便同于此情此景。一句“愈觉江山胜”暗自吐露出了诗人对国家的真挚热爱,诗人潜藏在这份爱国之心下的“望归”与“离恨”之情,通过“以乐景写哀情”的方式呼之欲出。李仁老这首作于武臣之乱时的小诗饱含着诗人的不舍之情,低落而不舍,十分契合他作为“海左七贤派”被迫隐遁山水但仍旧不免思念家国、牵挂社稷的“恨别思归”忧愁心绪。
最后是韩国本土文学中的“恨别”与“思归”。韩国古时期的歌谣《黄鸟歌》和《箜篌引》是最早表达类似“恨别思归”情感的诗词作品,《黄鸟歌》讲述了因王妃禾姬与稚姬争宠,稚姬怒而返家,琉璃明王策马而追,却没能追回爱妃,只能在树下看着黄鸟,感叹道:“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5]178故事中的琉璃明王身为一国之君,却仍然未能平息妃妾之争,最终导致心爱之人稚姬的离去。琉璃明王感受到与爱人分离痛苦,又看到黄鸟成双成对,自己却只能孤身一人。这分离和寂寥之恨的交织,便是韩国古代诗歌中最初展现出的“恨别”情。而另一篇《箜篌引》中“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6]讲述船夫溺毙后和妻子天各一方的“死别”故事,与《黄鸟歌》中琉璃明王与稚姬的“生离”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它们都充盈着凄美哀伤的情绪,都叙述了爱人间不同的“恨别”方式。而高丽歌谣《郑瓜亭曲》则表达了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与离恨。《高丽史·乐志》中记载道:
《郑瓜亭》,内侍郎中郑叙所作也。叙,自号瓜亭,联昏外戚,有宠于仁宗。及毅宗即位,放归其乡东莱,曰:“‘今日之行,迫于朝议也,不久当召还。’叙在东莱日久,召命不至,乃抚琴而歌之,词极凄婉。”[7]
《郑瓜亭曲》以第一人称独白体的抒情手法,表现了郑叙迫于朝议被流放,苦等起复,却久等不至的郁郁心情。所著歌谣中虽有“恨别”之意,却未有恨的字眼,只流露出对“郎君”深沉的情意,是明显的“恋君”情结。因此,《郑瓜亭曲》看似是对夫妻间“恨别”情感的描写,但实际上是借用了夫妻之间“恨别”的情感外衣揭示君臣关系中的“思归”心情。被贬的文人想要君王重新信任自己,而不被奸人左右的想法,恰似闺阁女子在祈求已经移情别恋的情郎回心转意。所以,将君主比作情郎,对君王的规劝就变为对情郎的不舍和“恋君”之意。因而以“恨别”为基底,在文学作品中再引出对丈夫、君王产生的恋君“思归”的情感共鸣,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也是早期韩国古典文学中“思归”情感的表现。
综上所述,潇湘八景与“恨别思归”的情感之所以能够被韩国文人所接受,一方面是由于本土文学中早早孕育出了类似“恨别”与“思归”的情感,并受到了汉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在政局动荡的历史环境下,韩国文人由于仕途不顺、境遇坎坷,恰好与潇湘“恨别思归”情感产生了共鸣从而受容了它。
二、韩国潇湘八景诗歌中的“恨别思归”情感内涵
我国的潇湘八景与“恨别思归”情感东传朝鲜半岛之后,在韩国潇湘八景诗创作中一开始仍然保留了“二妃”与“屈原”的人物意象,用以表达与原始“恨别思归”相同的思想情感。后来随着“恨别思归”逐渐融入与发展,韩国文人将羁旅思乡之情与规劝统治者的愿望,化合为表达自身渴求贤君的“仕途之望”的象征含义,最终形成了“二妃情恨”、“屈子余怨”和“仕途远望”三种具有韩国本土色彩的“恨别思归”情感,来分别表达忠君、规训和入仕的思想。
(一)二妃情恨与忠君思想
二妃思念虞舜,一路追随至楚地却只落得个与爱人阴阳相隔的结局。分离的思念与天人永别的痛苦都化作泪水,洒在路旁的竹子上,成为永恒的痕迹,“湘妃竹”由此得名。朝鲜前期诗人洪彦弼也不免发出“湘君一夜悲难胜,斑竹千年色不刊”[8]216的感叹。不同于一般情况下将“湘君”对应为舜帝的解释,此处的“湘君”指代的娥皇、女英二妃。这是由于韩国文人沿用汉代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中“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的历史认知。而“湘君一夜悲难胜”写出了二妃因一夜之间与丈夫的生离死别而引起的巨大心境变化,诗人洪彦弼也以“一夜”和“千年”的时间对照来形容,体现出短时间内物是人非的反差所造成的强烈悲凉感。但即使如此,斑竹的翠绿却可以千年不改,正如二妃对舜不变的忠贞与爱意,能够永存于“竹上斑痕”之中,也象征着作为臣子的作者对君王永恒的忠贞之心坚如磐石,读来无不令人动容。
二妃失去挚爱夫君的痛苦和从此天人永隔的情与恨,与韩国古代诗人苦于贤君难觅、伯乐难求的境况一般,都蜿蜒着“绵绵无穷尽”的情义。因此,韩国潇湘八景诗中引用“二妃”的人物意象时,多数情况下都会以“二妃”自比,以女性视角将对丈夫的忠贞思念之情比作文人对君主的“恋君”之心,委婉地表达自身永怀赤诚忠心的感情。因而韩国潇湘八景诗中对二妃意象主题应用的发展也不只停留在歌颂或惋惜二妃与舜帝的凄美爱情上,而多有借用二妃对爱情的忠贞来表示臣子对君王的忠贞之意,从而顺应当时韩国文人的实际需要。于是,“二妃”意象所象征着的忠贞、恋君之意,就形成了韩国潇湘八景诗中的第一重“恨别思归”之心。如朝鲜王朝后期诗人权相一的《潇湘夜雨》写“千古皇英离别泪,苍梧山色望皆疑”[9],明面上说的是二妃与舜帝的别离,实际上则是诗人将自己比作了皇英,离开君主后自怜自哀的暗喻。诗人所处的朝鲜王朝后期经过连续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社会变得愈加动荡不安,思想也开始向注重现实生活和向往道仙思想等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分化。因而权相一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了上古传说中二妃和舜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于圣君的向往,诗人渴望远离痛苦尘世但却又心怀儒教式忠君思想,最终只能转而寄托于道教仙境神话。这种利用富有感染力的抒情意象来对君主表忠心的方式,与我国的古代“闺怨诗”体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群在外力影响下抱负难施,渴望得到重用却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通过对男女之情的借喻来抒发真实心声,既有文学的含蓄美又具有明显的效用性。
(二)屈子余怨与规训思想
朝鲜前期诗人林忆龄认为屈原即使死去,化为一缕幽魂,也是“今古有沈魂,天阴鬼语纷”[10]126的英灵。其《潇湘夜雨》诗作中的“屈原”,就往往象征着古往今来,许多与他一般郁郁不得志的贬谪文人,他们的怨情即使在鬼界也会引起纷纷议论。林忆龄同样对遭受朝堂不公境遇表示不满,因此借屈原之口来表达自身深切的文人之恨。诗人林忆龄另一首题为《潇湘夜雨》的诗又写屈原:“鱼腹葬忠魂,千秋向国纷。江深招不得,天水合无痕。”[10]126屈原投江,苦于江水深深而被后人招魂不得,忠君报国之人的魂灵只能够沉寂在水底,不得安息,诗人的心中对于这一现状也难免流下眼泪,同时也体现诗人在怀念凭吊屈原之时,透露出因物伤其类而产生的遗恨。再有,高丽文人李齐贤在以《潇湘夜雨》为题的潇湘八景诗中写道:“二女湘江泪,三闾楚泽吟。白云千载恨沉沉,沧海未为深。”[11]109夜雨寒冷,勾起诗人深藏心底的乡愁。正是有着内蕴相似的“怨别”之情为基底,官场沉浮已久的李齐贤才能在思及二妃和屈原的故事时,仿佛能切身体会到其中的分离之痛、思君之苦,为之长久地叹息,同时文人心间含蓄而幽深的“恨别思归”之意,也油然而生。
屈原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对故土的热爱,是他身上最为闪光的精神特征。他的人生虽然充斥着悲剧色彩,但在其身上所体现的纯洁的人性和崇高的节义精神,则收获了韩国文人的追捧和高度评价。韩国文人、政客们在诗文中多以屈原自比,不仅抒发了自身在武臣之乱中压抑而痛苦的郁郁心情,更体现了其向往与屈子一般宁折不弯的文人傲气与风骨。林忆龄《潇湘夜雨》诗中写“谁招去国魂,千里不禁纷。忽返三更响,孤襟带血痕”[10]126,认为屈原随故国逝去的魂魄绵延不绝,哪怕是在半夜三更梦回时,也仿佛能看见穿着带血痕单襟的魂魄,诉说着对故国的思念。其中情感之强烈,仿若亲眼可见文人们的字字血泪。而韩国文人不仅喜爱歌颂屈原的爱国大义,同样也会借用屈原含冤遭贬的经历,委婉地诉说自己的心意。因而,在这类情况下被创作出的韩国潇湘八景诗歌,往往带有借屈原作为忠义之臣的人物意象来唤醒君主的强烈目的。韩国文人借由诗中塑造出的屈原含冤被贬的忠臣形象,来告诫君主不要像千百年前屈原的君主一样受到奸臣小人的蒙蔽,而错误地贬谪或是流放像屈原一样真正忠心的臣子。在结束了高丽王朝后期至朝鲜王朝初期的武臣之乱后,为了防止乱政再现,韩国文人以屈原为例来警醒君主在新朝必不能重蹈前朝覆辙而发出规劝和勉励。
(三)仕途远望与入仕思想
高丽文人陈澕言“除却骑驴孟浩然,个中诗思无人识”[12]283,认为自己身有才华却无人赏识,即使外表已洗去铅华、归隐于山林之间,心灵却始终没能真正体会到梅妻鹤子般的隐逸境界,获得灵魂上的超然与共鸣,只能与远去已久的古人孟浩然遥遥神交,悲鸣“个中诗思无人识”的寂寥遗憾之感。而高丽时期诗人千峰的《潇湘夜雨》亦云:“一夜湘江雨,三秋楚客心。”[13]38其中“一夜”对“三秋”,两个极端时间的长短对照,体现出诗人的心境变化之大。诗人可能也面临似“楚客”一般被驱逐流放而无比煎熬的时刻,原本只是在湘江地带下了一夜的雨,体感却像是已经过去了三个秋季。遥远的朝堂冥冥之中仿佛也象征着光明仕途的远去。
韩国文人虽身处美丽的山水田园间,心绪却徘徊不定、渴望回归,是因为他们受儒教思想影响至深。自古以来,他们深受儒家入世观熏陶,将自己的诗文作品当作一种入仕的表达,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视作毕生的愿望。例如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影响下,韩国在朝鲜时期的汉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归”意象,就是当时文人深切渴望回归仕途的鲜明表征。朝鲜前期徐居正的《四佳集》也透露出与陶渊明深有共鸣的“归去来”情结,但存在一些差别。陶渊明的“归去来”是中国古代潇湘地区原始“恨别思归”情感的体现,即因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将山水田园看作最终的归宿。“离别”和“归去”表达了陶公对俗世及官场的失望和厌恶,是“不带走一丝云彩”的极简与轻松。而徐居正虽然接受了“归去来”的意旨,却认为“功成者退,亦四佳之隐义也”。徐居正的“归去来”是希望“功成身退”的圆满,认为要为君为民建立一番功业,成就功名后退隐山林才是“归去来”的要义[14]97。这点非常符合古代朝鲜民族一贯追求的积极入仕、弘益人间的观念。由此可见,韩国所盛行的“恨别思归”情感在入仕思想的渗透下,也有了更为强烈的功利性改变。
三、“恨别思归”情感在韩国的流变
作为潇湘文学的集大成者——“潇湘八景”文学在远传朝鲜半岛后,其受容作品中不仅包含着对“恨别思归”的多种阐释与吸收,而且凭借文学作品和文化意象发展的相辅相成,韩国潇湘八景诗文学的发展也给“恨别思归”情感带来了新的生机。韩国文人在充分吸收和继承其内涵的基础之上,对于“恨别”与“思归”的内涵也分别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和扩充。相比较于原“恨别思归”情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多被用来表述离愁别恨、羁旅思乡的抒情含义来说,韩国潇湘八景诗文学中的“恨别思归”被更集中地应用在规劝统治者、借古讽今、表忠心以及毛遂自荐等政治方面的含义之上。由此可见,韩国潇湘八景诗在对“恨别思归”情感的运用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恨别”情感蕴涵的变化
“二妃”和“屈原”作为中国古代的人物意象,在韩国文人的创作之中仍旧最大程度上保留着与人物故事息息相关的情感色彩。所以,二妃传说之中的“恨别”与屈原故事中的“怨别”,在流入朝鲜半岛后,一开始仍然被作为吐露国仇家恨、情爱别离相关情绪的固有文学意象被应用在文学实践活动当中。然而随着潇湘八景文化在韩国的日益发展,“二妃”和“屈原”人物意象所具有“恨别”与“怨别”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二妃”和“屈原”意象分别是生发自舜帝和二妃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和满含冤屈被流放的忠臣义士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共同情绪底色是灰暗的、消极的,充满着绝望厌世的氛围,强调“恨”的情绪表现。所以古代中国文学中使用“二妃”和“屈原”人物意象的作品,大多都表达了想要脱离肮脏尘世独善其身的出世愿望。但是,韩国对于“二妃”和“屈原”意象的接受和继承,则去除了其中的想要“遗世独立、独善其身”的含义。这是因为韩国文人士大夫受儒教思想的影响颇深,“入世”则是他们实现自我理想与自我价值唯一通路,原始的“二妃”与“屈原”意象中包含的“出世”观念与之截然相反,自然很难受到韩国文人的认可。他们即使有“恨”的情绪,也不会像庄子的《逍遥游》一般向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三无”超脱境界,怨恨世间繁务束缚住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将“恨”指向了祸国殃民的“奸臣”和“暴政”,以及痛恨自己无法拥有改变现状的机会。在对于“恨别”的理解上,韩国文人也更爱强调“别离”之意。这是因为何时能够重返朝堂、重新回到能够建功立业的地方,才是韩国文人更加看重的结果和目的。因而“恨别”情感在朝鲜半岛上所产生的“恨”的对象的变化以及由“恨”转向“别”的叙述重心的改变,体现了两国文人在目的性和情绪底色上的区别。
(二)“思归”情感内涵的扩充
“思归”同样生发自潇湘谪迁文学,时常作为“恨别”思想的伴生情感而出现。比起拘束于二妃、舜帝、屈原等固定的人物意象表达出的单一情感来说,“思归”本就包括了一定的“恨别”情感基础。加上韩国不同情境下的衍生,“思归”情感的内涵被扩充得更加复杂丰富。如朝鲜前期文人李承召《潇湘夜雨》的“舟中多少远游客,尽向灯前说古乡”[15]461一句写尽远游之愁,表现出了诗人的“思归”之心。诗句表面平静的情绪下掩盖着强烈的思乡愁绪,使得其中隐藏许久的“恨别”之情也在字里行间中慢慢地展露出来,最后一览无余。而这首诗中“恨别思归”的情绪互相交织,正是思归情感愈来愈能包孕“恨别”情感的体现。“有别才有归,有恨才是情”,思归的情感天然建立在“恨别”的基础之上,但当它作为“恨别”的衍生和迭代生成了“恨别思归”的复合情感时,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强的生命力。
“思归”内蕴也体现在对“归处”的定义范围的变化上。在中国原始的潇湘文学中所描述的“思归”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一些理想的世外洞天和梦中仙乡里。这些“归处”虽美轮美奂,但都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如陶渊明所勾勒出的“世外桃源”和“山水乐园”就是这类理想化却遥不可及的“归处”写照。而在韩国潇湘八景诗中,新描绘的“思归”之处则变得十分简单而具体。韩国文人们的理想归处就是一个山河平定、百姓安康的太平盛世。对于入世颇深的韩国文人来说,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朝堂和睦清明的模样才是向往的“归处”所在,正如高丽诗人李奎报在《平沙落雁》一诗中写:“赖有汀边木笔花,最宜文字落横斜。低飞欲下沙州戏,待汝传书有几家。”[16]197李奎报在这首诗中用朴素的白描技法描绘了天地间随处可见的一副自然景象,再借用“鸿雁传书”的典故传达了一丝乡愁的情绪,便是在诉说希望能像典故中的苏武一样尽快回到故土的怀抱,结束动乱飘零的现状,回归平静安宁生活的愿景。这首诗不仅表现出了一个正统儒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表达了诗人向往归处的所思所想。
(三)“恨别思归”情感衍生出的现实意义
“恨别思归”作为潇湘文学产出的原始情感,自然和湖南地区多山多水、潮湿荒僻的地理环境有所关联,如刘禹锡《潇湘神二首》中“湘水流,湘水流,九嶷云物至今愁”一句表面上看是在描述湘水奔流不止的场面,但诗中将湘水和“愁”字结合在一起,就不免让人联想到神话中湘妃的眼泪就如同这绵延不绝的湘水,仿佛在诉说作者因被贬远游而同样百转千回的愁绪。戴叔伦的《过三闾庙》中云:“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诗中把沅江和湘江水量丰富而长流不尽的模样,比喻成屈原所背负似江海般深沉的忧怨冤屈。诗人在为屈原打抱不平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的深切悲悯和“恨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人对“潇湘”书写的创作习惯多以抒情的视角来表达自己仕途不遇的“恨别”情感。流传至朝鲜半岛后,“恨别思归”的复合式情感在韩国潇湘八景诗歌中被应用得更为广泛,除单纯抒情,更具有政治功利性的现实意义。
同样,高丽文人李齐贤在《潇湘夜雨》中,道:“惊回楚客三更梦,分与湘妃万古愁。”[17]595诗人以“楚客”的远游客身份自居,离乡背井的远走又使得他染上了与二妃同样因千里跋涉而产生的愁思。诗人好似在“恨别思归”的情感漩涡里一直徘徊,可其中潜藏的不安愁绪,体现了诗人既不清楚“前路”在何地,也无法把握住“君”已离自己远去的结局。即使在梦里也缠绵思归,梦醒时分却无法改变身在天涯远地的处境。于是作者写下这首诗,并将自己希望早日回归的愿望寄托其中。此时的诗作便开始具有了向君主陈情、希望早日归还的实用性意义。因而在韩国潇湘八景诗作中,从一开始单纯引入潇湘“恨别”的情感因素,到逐渐转变为由表面写“恨别”实际表“思归”目的的迁移,最终发展为内涵更为丰富、情感包蕴更为多样的“恨别思归”组合。“恨别思归”的叙述重心在朝鲜半岛随着运用方式的改变和政治现实需求的变化,呈现出的一种由强调抒情的“恨别”转向强调具有政治功能的“思归”的情感变化。
四、结语
湖南地区自古以来阴雨连绵的气候和潮湿险僻的地理环境,再融入二妃传说、屈原故事的文学意象群,潇湘大地上生发出的文学早早奠定了忧伤悲愁的抒情基调,塑造出“恨别思归”的潇湘原始情感。而韩国潇湘八景诗自古受汉文学影响,又有本土传统文学中已有类似情感的基础,加上对同样仕途不顺、境遇尴尬的文人的共情,对“恨别思归”的情感进行受容后,变化出了新的情感意蕴和运用形式。其中,以“二妃情恨”“屈子余怨”和“仕途之望”三类作为韩国潇湘八景诗歌中体现了“恨别思归”情感的主要部分,分别体现了忠君、规训和入仕的韩国潇湘八景诗的主题思想。韩国潇湘八景诗歌不仅改变和扩充了“恨别思归”的情感内涵,也变化了原本的叙述重心,增添了“恨别思归”情感的现实意义,即着重强调“思归”与强化诗歌文学的现实功能性。
潇湘文学“恨别思归”情感在韩国潇湘八景诗歌中的接受与流变,可称为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典型例子之一。潇湘八景文化对韩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恰好证明了我国传统文化流传海外,受到异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同时在韩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适应性,这展示了中韩两国良好的文化交融,体现了韩国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