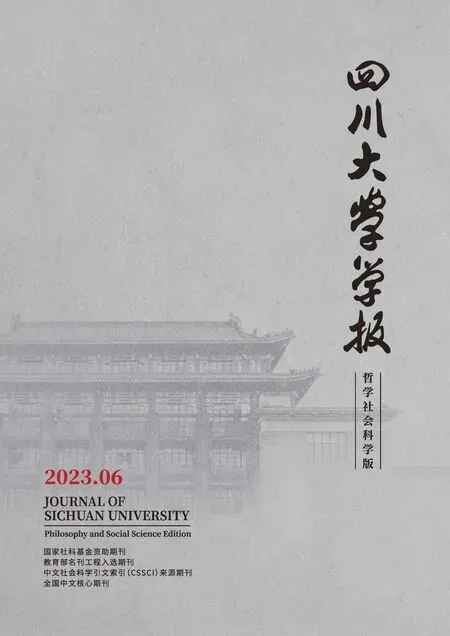川汉铁路宜昌工程与四川保路风潮
2023-03-13徐跃,高龙
徐 跃,高 龙
由川汉铁路国有问题而引发的四川保路风潮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要认识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和演变,必然要关注川省川汉铁路的路线规划和工程修建。目前学界对于川路的选线和施工问题还未有比较细致的梳理,对于川路宜昌工程以及驻宜公司与四川保路风潮的关系也缺乏较为深入的论述。(1)关于四川保路运动史的学术梳理,可参见苏全有、邹宝刚:《近三十年来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综述——纪念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近些年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Xiaowei Zheng,The Politics of Righ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鲜于浩:《四川保路运动再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与本文论旨较为相关的论著还有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晓东:《股东维权与政府夺权之争——保路运动中的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事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黄权生:《清末宜昌川汉铁路建设原委及李稷勋考》,《长江文明》2013年第1期等。上举研究对川路宜昌路事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钩沉,但在具体史事细节和脉络上仍存在着不少遗漏或缺失(如选线争议、施工困境等),对于宜昌路事与1911年四川路潮的关系、宜昌路绅与成都保路绅民之间的关系更是缺乏细致深入的梳理和论述,为本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留下了空间。这与宜昌路工作为川路公司唯一之开工路段(驻宜总理也是公司三大总理之一(2)川路公司于1907年奏改商办后,“援湘路三总理故事,奏任胡峻为驻省总理,丁忧道员阆中费道纯为驻宜总理,乔树枏为驻京总理,用三总理名义,组织总公司于成都”。三总理互不统属,各有职责。不久后,费道纯去世,邮传部参议李稷勋(四川秀山人)于1909年被公司奏派为驻宜总理。参见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文》,《交通丛报》1922年第86期,第5页。)的地位是不够相称的,也不利于我们以路工、路事为切入点来认识清末的路策、路潮。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厘清川路宜昌夔州(万县)路线的划定、开工与困境,探讨宜昌路工迟滞问题与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关系,进而考察国有政策出台后宜昌、成都两地川绅路事主张的分歧以及驻宜总理李稷勋任免风波的发生,并以之为线索来揭示四川保路风潮的发展和激化,以期深化学界对于清末川汉铁路史和路事风潮史的相关认知。
一、川路路线的划定与先修宜万的争议
甲午战败之后,清王朝统治危机加深,在华列强竞相划分势力范围、攘夺中国铁路利权。1903年,新任川督锡良奏请四川铁路应“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1904年初,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是指四川成都至湖北汉口的铁路,以之定名反映了锡良意在开通内陆四川、勾连京汉铁路的雄心,而相应路线的规划、勘测与施工等事宜也成为此后多方人士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
川汉铁路贯穿两省,路线绵长,需要适当划分路段以落实相应筹划。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为铁路事宜上书锡良,主张将川汉铁路分为汉口至宜昌、宜昌至重庆、重庆至成都三段,并建议先修宜重路段。(4)《留学东京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上川督锡制军书》,《新民丛报》1904年第9号,第3页。另有内地川人发文指出,川汉路线应分为汉口至宜昌、宜昌至夔州、夔州至重庆、重庆至成都四段,应当先修宜夔路段。(5)《与四川同乡诸君子论宜速修川汉铁路并续修川藏川滇川陕各路书》,《申报》1904年10月5日,第1版。1905年初,锡良与两湖总督张之洞联衔奏陈川汉路事,认为“水陆之险,皆在川鄂接壤之区,应从宜昌开工,先能修至万县”。(6)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0页。在上述诸人的认知中,湖北宜昌成为川汉铁路选线和施工的关键地点。宜昌是进出四川的要道之一,将之纳入路线规划自无不可。但严谨的铁路选线却需要勘测对比多条路线以作备用方案,川汉铁路未经实勘就取道宜昌明显有些“先入为主”和“想当然”,此举对之后川路路线的划定和开工造成了严重干扰。
川汉路线意拟取道之宜昌、夔州(及其辖境万县)位于川、鄂交界地带,需要由两省官绅共同筹议以划定相应权限及负责路段。川路公司总办胡峻曾为此前往湖北协商,他在致锡良的电文中指出:“川汉铁路分境各修,湖北留学生多持此议;而正绅有识者知鄂难筹款,颇不以分界为然。窃谓宜路不通,即成万路成,无大利益,是宜夔一段非修不可。”(7)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02册,第534页。然而宜夔一段“皆系连山大岭,险峻非常,……工作极艰,费用极巨”。其时鄂省刚刚赎回粤汉铁路,“所应分任赎路造路之款,已属不资”,自是难以兼修川汉路段。而在锡良看来,川省铁路“非从宜昌修起,则川民疑惧,谓鄂境不修,则川路无用,……且川路运机运料,非由宜昌入手,则转输不便,川路亦将无可施工”。多方考量协调之后,锡良、张之洞奏准将“宜昌以上鄂路暂归川省代修”,待宜万路线修成25年后,准许鄂省“备价赎回”。(8)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59-260页。
川省“代修”鄂路之议牵涉两省民众的切身利益,看似明晰的权责划分带来了诸多问题和争议。湖北留洋学生“龂龂以省界所在,即权利所关”,对“代修”一议抱有意见。部分川绅也是愤愤不平:宜夔工程艰难、需款甚巨,“川人竭蹶以图其始,鄂人安坐而收其成,准理揆情,宁为平允”?(9)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259、445页。关于川汉铁路路线划分所带来的川、鄂省际纠纷的研究,可参见潘崇:《清末铁路建设与多方势力的路事博弈——基于锡良筹办川汉铁路的讨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川籍京官杜德舆更是在奏文中批评“越境争修,失计己极”,“以七八千万之母财,置诸十余年不得一利之路,稍有知识者,可直断其永远不能开工。即令贸然开工,势将坐废半途”。(10)《度支部主事杜德舆为川汉铁路事呈都察院代奏折(三续)》,《申报》1907年10月14日,第10版。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则在于,由于勘路工程师迟迟未能聘定,以上选线、分段和“代修”方案基本立论于推想之上,根本未经过实勘和论证。川官王廷佐即为此禀请川督重新审定路线,认为川汉路线应“以江北厅经两路口、大竹、东乡、太平而至汉中,再经兴安、老河口出襄阳达汉口为上策”(即陇襄线)。(11)《川汉铁路审定轨线》,《申报》1907年10月22日,第5版。川汉铁路取道宜夔(宜万)本就有待商榷,而所谓从宜昌开工则更是依托于一些未经推敲的认知,如“四川铁路,不达于宜昌而与航路接续,则为废物”,等等。(12)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445页。这种“成见”不免要与后续的路线实勘情况产生偏差,由此引发了先修宜万路线还是先修成渝路线的争论。
1906年,川路公司聘定胡栋朝、陆耀廷为工程师以勘测成渝、渝万、宜万三段路线。1907年夏,川路勘线任务初步完成,但胡、陆二人对于先修何段却是各有主张。胡栋朝提出应先修成渝路线、从成都开工,而陆耀廷则主张从宜昌开工、先修宜万路线。两说各有凭据、僵持不下,川路公司乃于1907年秋“邀集在省各属股东,并电请东京、北京及重庆商会决议施工次第”,其后根据各处复电“以多数决定由宜昌开工”。(1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372页。然而此次在省会议“既非股东总会,又非办事人全体会”,(14)《川路开工成渝宜万两线孰先之利害得失比较论》,《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书》,出版信息不详,第13页。“日本虽有改进会(即川汉铁路改进会)覆电先修宜万,然其事实未尝谋及全体”。(15)《乡人公告书》,《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书》,第3页。因此这一“多数决定”非但没有一锤定音,反而引起了涉事各方持续的论争和辩难。
胡栋朝、陆耀廷以工程师的身份最早展开了关于先修成渝还是先修宜万的争论。胡栋朝在1907年末发表《四川川汉铁路宜先修成渝说》,从“工程之难易、风气之开通、人心之向背、资本之多寡、利息之有无”等方面立论,指出川路“当以成渝一段先修,以其需费少而成功速”且可以带来诸多便利。(16)胡栋朝:《四川川汉铁路宜先修成渝说》,《广益丛报》1907年第25期。而陆耀廷则在其后发布《川汉铁路宜昌开工论》,认为入川路途艰险、铁路所需“重器”难以运输、必须先修宜昌以便转运,声称“先修成渝虽有百利,不敌一害;先修宜万虽云百难,犹获一易”。(17)陆耀廷:《川汉铁路宜昌开工论》,《北洋法政学报》1908年第82册,第2、3、5页。
工程师的相关言说是各方参议路事的重要参考,与胡、陆之争相呼应,川人也渐次划分出对垒的阵营。以重庆商会、川汉铁路改进会为代表的部分川人支持从宜昌开工,认为先修宜万便于“四川接触于中原,变僻陋之乡而成交通之域”,便于川省货物外销和商业发展,便于铁路器械转运并节省运费,等等。而四川留日同乡会则反对其议,并对以上各理由提出反驳:川路公司初创而宜万工程艰巨,“一有顿跌则旋归瓦解,冀交通者适以阻交通”;四川工商业尚不发达,“一旦骤开门户,洋货麕集,外商络绎,势必排挤四川之生产家而压倒之”;等等。同乡会认为重庆商会仅侧重于从“商旅”上立论,未能兼顾全川之“危亡”与“利害”。(18)《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书》,无页码。对于川汉铁路改进会,同乡会更是发布《四川同乡会宣布川汉铁路改进会罪状书》进行讨伐,指证改进会干事蒲殿俊等人隐匿电文,“不经多数决议而私自擅覆”。(19)《四川同乡会宣布川汉铁路改进会罪状书(续前)》,《大公报》1908年8月30日,第6版。
为辨明先修成渝的立场,四川留日同乡会专门发布《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谨告全蜀父老》一文,分别从“铁道之性质”“资本之单薄”“工程之便易”“营业之效果”“路权之保护”等方面提出理据,号召川人“力排先修宜万之说,毅然定计首从成渝动工”。(20)《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书》,无页码。四川铁道协会在《乡人公告书》中支持其说,声明“路线未实测之先,无人不主先修宜万,以其利交通而便搬运也。暨工事实测后而道路之奇险与工事之巨艰加以款项之奇绌,遂成不得不先修成渝之势”。该文还从“水运争利之有无”“工事实施之难易”“资本销费之多寡”“沿途贸易之荣枯”等方面论证川路取道宜万远不如取道陇襄,提议“不妨先修成渝以为实测陇襄地步”。(21)《乡人公告书》,《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书》,第7-10页。
不难看出,先修宜万的理据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多质疑,部分川人甚至从根本上对宜万路线的选择提出了否定。但川路从宜昌划定及施工乃锡良、张之洞在实勘之前就已审定的方案(陇襄线被排除在外),其后更是得到了继任川督赵尔巽的支持,(22)陆耀廷:《川汉铁路宜昌开工论》,《北洋法政学报》1908年第82册,第2页。故而川路公司最终还是奏准先修宜万并从宜昌开工。其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川路公司在勘测不全面、论证不充分、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贸然开工,且“冒险盲进”(2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37页。地去修建工程艰巨、需款浩大的宜万路线。川路宜昌工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其迟滞延误直接为清廷干路国有、借债修路等举措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二、宜昌路工的困境与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
1909年秋,川路公司在宜昌开工,但其准备并不充足,开工仪式也略显草率,各省“传为笑柄”,川人“激成公愤”。(24)《川汉铁路公司留京股东致董事局函》,《申报》1910年3月28日,第2张第2版。川籍京官随即作书登报,揭发川路公司“开工之真相及其内幕之黑暗”。(25)《四川川汉铁路开工之真相及其内幕之黑暗并改良之方法》,《广益丛报》1910年第2期。外媒趁机讥讽道:“川路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现在居然开工,中国前途叵测,环球列强均当留意。”(26)《李稷勋读中外各报感言》,《广益丛报》1910年第12期。而这还只是开端,其后便是一直存在着的且不易克服的施工难题和舆论困境。
宜万路线“沿线层峦叠嶂,山脉伟大绵长,皆由西北横亘东南,至江岸屹然而止。应穿隧道及山沟、桥梁,险工林立,皆为吾国前此铁路所未有”。(27)《李稷勋读中外各报感言》,《广益丛报》1910年第12期。根据工程师胡栋朝的勘测和估计,川路全段以宜万“工程最难,平均核计每里需款三万七千余两,约五年工竣”,共需银三千二百余万两。(28)胡栋朝:《四川川汉铁路宜先修成渝说》,《广益丛报》1907年第25期。四川留日学生在考察对比世界上其他铁路“难工”后指出,“宜万间数百里中穿山腰应为隧道线者”甚多甚长,全段竣工所需的时间及款额将远超胡栋朝的预估。(29)《川路开工成渝宜万两线孰先之利害得失比较论》,《为川汉铁路先修成渝告全蜀父老书》,第17页。而川路公司所筹股银直至1911年也仅有一千多万两,缺口极大,根本难以支撑宜万路工的完成。
此外,川路公司在湖北宜昌施工属于跨省作业,需要协调和处理多地官绅民众的关系。如公司在宜昌购地时“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30)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43页。既影响了开工工期,也遗留下诸多隐患。1909年,川路驻宜公司购地设局,“内有车站码头,并不特别给价,且广基址窖界居奇。种种不公允之处,各业户皆不心服,屡经具禀鄂督及京师铁路公所”。(31)《川汉铁路购地之纠葛》,《大公报》1909年11月2日,第9版。1910年,旅京鄂人又因驻宜公司“有强争民房、圈占地亩、设立弹压公所用刑取供各情节,特发函诘问”。(32)《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7月2日,第1张第5版。公司购地施工屡起省际风波,为后续工程的进行增添了不少阻力。
宜昌开工不久后,川路驻宜公司总理李稷勋就在报纸上直言宜万路工之不易:“工程艰险,进行线千盘万折,未能十分迅速。……沿路桥工机料,重者动数千万斤,断难以人力转运,必甲段通轨而后乙段之桥乃可运料安设。且山中夏涨时,溪壑纵横,人踪断绝,工事尤滞。”在清廷日益关注铁路建设和“国有铁路主义”渐次盛行的情况下,李稷勋担忧宜昌路工“中道或有磋跌”时清廷会“起而干涉”:“盖人民之财力能力果能胜此巨任,政府固应维持;若财力不充,能力不济,而外侵内哄,此攻彼击,纠纷无已。恐政府轸怀路事,未便坐视其扰扰而长此缄默也。”(33)《李稷勋读中外各报感言》,《广益丛报》1910年第12期。
李稷勋本以为“使所筹股本,每年确有三百万之收入”,则以上各种疑难便会“冰消雪释”,(34)《李稷勋读中外各报感言》,《广益丛报》1910年第12期。然而川路公司的股款情况却不容乐观。四川咨议局议员陈洪泽在1909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公司的收款问题:川路股款以租股为大宗,年收银约二百万两;“现连年水旱偏灾,加以坐扣息银,现只能收净银一百二十三万矣。年短一年,后必入不敷出,何以接济工程”。(35)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第476页。川路旅京股东会在1910年初也对公司的路款路工问题提出质疑:“公司股本原自不丰,又经当局诸人累年糜耗,存放之号迭次倒塌。现在所储不过千万,仅恃租股,来源亦枯,……其果能以川人之资金成此大功乎?”(36)《川汉铁路公司留京股东致董事局函(再续)》,《申报》1910年3月31日,第2张第2版。不久后,川路驻沪经理施典章亏倒股银二百余万两的“上海倒款案”爆发,公司的股款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川绅胡骏感慨道:“川民之膏血,以供一二无经验、无担保之人之滥收滥用,若之何其可,……可见川路之能成与否,已在漂缈虚无之间,……终必至于归官办,借外债而后已。”(37)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413页。
川路公司经营不善,宜万工程修建困难,一应任事路绅自然是饱受非难。“川路开办以来,攻击之风几成积习。未开工则责以不能开工,既开工则复多方责难。种种浮言,当事者竟无一而可。既足以摇惑群情,即深恐妨碍路事”。(38)《果足弭川汉之浮言乎》,《申报》1910年6月14日,第1张第5版。川路取道宜昌、先修宜万本就伴随着诸多争议,开工之后各种“浮言”和“责难”更是此起彼伏。这不仅阻碍了公司的运营和施工,也反过来加深了川绅之间在路事上的分歧。
宜万路工既然举步维艰,改修成渝之说再度浮出水面。1910年,湖北前布政使李岷琛(四川安县人)、现布政使王乃徵(四川中江人)等发文揭露宜万路工存在着巨大隐患:“舍成渝先宜万,千余里深山穷谷,工费数倍,路成尤无以养。……以川费先修鄂境,川人不知有路,股款既罄,人必灰心。”(39)《川路开设银行之建议》,《申报》1910年8月20日,第1张后幅第3版。1910年末,川路公司召开第二届股东大会,正式提出改修成渝一案。会场上主张改修成渝者“最占势力”,“凡有反对之研究,不待毕词出已哗噪相逐,以是畏其气焰者皆裹足不至”。由于此种开会情形过于“离奇”,最终未能成议。(40)《铁路股东会之聚散》,《蜀报》1910年第6期。其后,董事会又向川督赵尔巽及驻宜总理李稷勋提议“兼筑宜万、成渝两线”,往复函电商议后未能获准。(41)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文》,《交通丛报》1922年第86期,第7页。但众多川人和股东已是不再看好、甚至是不再支持宜万路线的修筑,宜昌路工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在上述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宜昌路工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相当有限。至1911年,宜工分段开工者“计由宜昌至归州(即今秭归)线长二百八十余里”,然而建成“通车运料者”却只有三十余里。(42)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9页。时论对之批评道:川路建成如此之短而耗银却达三百万两之多,“以此比例推之,若至重庆必应费去数亿两无疑。且宜万一线何时可以告终,其他之部分此后何时可以开通,皆在不可知之数”。(43)《川汉铁路果有此现象乎》,《申报》1911年3月25日,第1张后幅第2版。川路若想全段建成,似乎仅有收归官办、借债修筑之一途。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川汉等路,不欲筑造则已,苟欲全工告竣,则非借外债不可。然此事亦宜待时而行,以免操之过急,激出意外之变端。”(44)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15页。国家借债筑路一议已在清廷高层的酝酿之中。
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抨击川、鄂等省商办铁路靡费倒款、“溃败延误”,指责川路宜归工段“不知何年方能告竣”,奏请将干路收归国有,由国家从速修筑。(4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13-114页。邮传部复议该奏时指出,各省商办铁路“苟能随时集款,随时兴工,则六七年来,亦必已有成就”;然而各商办公司却是不足以“副其责成,以致路工濡滞,耗费浩繁”。盛宣怀支持干路国有,外务部、度支部大臣与之“意见相同”。(46)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16页。5月9日,清廷下旨指出各省铁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47)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18页。有鉴于“宜昌以上山路崎岖,非用专门洋工程司(师)不能妥速”的情况,盛宣怀在接续张之洞议定四国两湖铁路借款合同时,特意“将宜昌至夔州难工约六百里,抵补截去之汉荆枝路”,“以赴干路速成之宗旨”。盛宣怀进而议定聘请美国工程师承修宜夔路段,“因其惯造山路,可望速成”。(48)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28、160页。川路宜昌路工的困顿迟滞作为一大因素,直接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以及借债修路举动的出台。(49)其实各省商办铁路问题重重,促成清廷干路国有政策出台之原因不止一端。路工建设迟滞问题之外至少还有股款亏蚀问题、士绅分歧争斗问题、租股扰累民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石长信奏亟宜明定干路为国有折》中都有提及,参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13-114页。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原议之两湖铁路借款草约所包含的乃鄂省川汉铁路,并非宜昌以上川省承修之川汉铁路。但由于两省川汉铁路名目“相混”,故而“鱼目混珍、张冠李戴之事比来已数见而不鲜”。(50)《成都来电》,《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1907年第4期,第106页。湖北川汉铁路借款的消息总是会牵连到川省川汉铁路,每每激起川人的反感和抗议。张之洞在1909年筹议借债修筑鄂省川汉铁路时,川人郭成爽等即认为“川路借英、法、德款,全蜀垂危”,号召同乡诸公“速开大会商量一切,速电京外同乡及川督力争”。另有川人发布《声讨卖路之檄文》,抨击借款筑路无异于“卖吾民之铁道以断送吾民之生命”,呼吁川人反对湖北借款、保护川汉路权。这些情形可以说是1911年保路风潮的预演,也强化了川人本已存在的“保路”观念。而盛宣怀所签订的四国铁路借款合同却赫然把川路宜夔一段划入到借债修筑的范围之内,这不免会引起川人的不满和反对:“四国借款,本无川路在内。若牵连及我川人,尤当拼死力争。”(51)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00-502、564页。四川保路风潮的大幕正是在此一部分背景和心理之下拉开。
三、成、宜川绅分歧与路事风潮的演进
清廷干路国有政策于1911年5月9日颁布后,各地川人纷纷发布文电抒发意见。驻宜总理李稷勋于5月15日致电成都总公司道:“川路既欲收回,则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仅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52)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25页。李稷勋不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也不否认争路的必要性,主张收回公司办路用款。成都《蜀报》主笔邓孝可在发文揭出“四川路工之险峻如彼,人民之贫瘠如此,罄我川人仰事俯蓄之资,将不能成吾川之铁路”的情况后,表示“吾川必欲争川路商办,甚无味也”,提议收回路款兴办川省实业。(53)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3-345页。李、邓二人的见解有些相似,颇能反映此期川人“都欲保全款项”的一般心理,(54)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69页。成都、宜昌两地川绅还未有明显的分歧。
5月22日,清廷下旨停止川省铁路租股的征收。租股为川路股款之大宗,一旦停收,则“釜底抽薪,商路生命已绝”,宜昌路工的后续资金成为一大难题。而此时宜工各处却是危机四伏:“工役数逾四万,人类繁杂,良莠不齐。自闻收回国有之命,谣言四起,各包工异常惶骇,……湖北人心,尤为汹惧。如此重大改革事件,政府既未先期通告,一切毫无准备;设因此滋生他变,勋万难当此重咎。”故而身为实际负责人的李稷勋不得不致力于维持宜昌路工的稳定以及妥善归置公司的各类资产,并一再致电成都寻求解决方案。成都总公司在复电中指出:“尊处工程自不能停,但当如何截止预算造报,以备他日与官府交涉,极乞酌裁。”(5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65、600、577页。6月3日,李稷勋致电总公司和四川咨议局,声明宜昌路工危险重重,决议先将“本路用款及工程成绩”上报并将6月之后的工程用款改为另册登记,请求成都方面速谋对策,派人接收。(56)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63-164页。
李稷勋查报宜昌账款、意拟移交路工的做法与此期拒绝收路查账的成都士绅的主张相凿枘。总公司于6月6日致电李稷勋道:“现在省各界合力争请暂缓接收,与尊处不无冲突。公意以工程人众,猝闻有美国勘修之说,恐酿事变,诚为至虑。护院亦洞悉情形,已拟向部磋商。”李稷勋在复电中指出,川路若不及时接收,公司须再垫现款,“所以急催接收者,为爱惜现款计,恐政府未必即来接也”。(57)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65页。总公司则在回电中表示:“路归国有,认否尚待大会。然款系商股,宜先停支以俟解决。”(58)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78页。李稷勋不认同此议,其在复电中争辩道:“顷催接收,正为惜款。尊意认否尚待大会,路(工)不交,款何能止?一旦停工,则成绩糜烂。若政府不认接收,前款从何取偿?”(59)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66页。川路成、宜公司在路工接收和路款处置问题上开始产生裂隙。
6月14日,四国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邓孝可、罗纶(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等阅后大为不满,随即发文抨击该合同丧权“卖路”。(60)邓孝可在《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一文中指出:“记者处分川路案,发端即论借款是否以路抵押?即非作抵是否与路有关?今直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外,更以两湖财政作抵。”参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86页。罗纶等又联名签注驳斥四国借款合同称:“此合同成立,不啻断送该路也。”参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17页。四川的舆论风向为之一变,反对借款合同、要求争路保路的呼声占据了上风。(61)具体论述可参见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212-213页。6月17日,总公司致电宜昌传达成都各界会议的决议:“本路工程,万不能停”,“非公司办事员,不能擅将股款拨付接收”,“另设机关,力争合同”。(62)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737页。会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并提出“破约保路”的宗旨,成都的保路风潮日益高涨。6月19日,总公司致电李稷勋,声明“同志会宗旨,力争合同,不仅争路争款”,(6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98页。以同志会宗旨否定了李稷勋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建议。而李稷勋对之则持保留意见,表示“路固当争,设争竟无效,则最后归宿,收款尤为切要”。(64)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738页。
成、宜公司意见不一,路事纷争不决,李稷勋在告知总公司后于6月底晋京,意拟“与同乡京官、议员切商对付方法,并晤端大臣(即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陈说一切”。(6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744页。川路公司迟迟未有定策,在宜股东“益滋疑虑,深恐路一停修,股款无着,咸向公司管理诸人需索原缴股本”,宜昌公司以铁路收归国有为由进行推脱。“众股东见公司一味推卸,不胜忿怒,即将管理诸人殴辱一番,并将器具、房间全行撤毁,……风潮甚烈,难以和平了结”。宜昌当地警察、军队前往弹压后,股东们更加愤激,“各回乡村纠聚农民二千余人,执械抗拒,殴毙兵士二十余名”。(66)《宜昌因路殴毙兵士之风潮》,《大公报》1911年7月6日,第2-3版。宜归各工段工人担忧停工失业,亦是蠢动不安。“工徒数千人结党成群,肆行劫掠。宜万一带如清滩镇一处,抢案十余起;并盘踞路旁,意图暴动,……恃众抗拒,凶悍异常”。(67)《宜昌扰乱之情形》,《大公报》1911年7月8日,第6版。宜昌官军难以应付,只得禀请鄂督派兵援助。府城人心惶惶,并因之停市。
宜昌工程动摇、乱事频出,川路驻宜董事局(下简称宜局)不得不作出应对,于是向成都股东会、总公司提出了保款附股、专修宜归的方案。宜局在电文中指出,川路租股停征,路款难以为继,“就成、渝、汉、沪现有存款,不过约敷两年之用。即令朝廷降心相从,仍归商办,设或款项不济,半途中止,其危险不堪设想”。宜局认为成都路绅“未可徒以空言争论”,应该注重保全款项和维护路工,建议将川路股票、资产等交由清廷接收并换领国家铁路股票,将现存路款用于专修宜归一段。“如此于股东应享利益,可免无失,且宜归纯用川款兴筑,尤足为川人留一纪念”。李稷勋也“甚愿以现存租股认办宜归”,表示要“设法运动”成都总公司。(68)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22-223、227页。
总公司对宜昌路绅的争款保工建议不以为然:“除争废约外,无可着手。盖以合同不废,川款即全行争回,而此后狙公政策,实难保险。”(69)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776页。7月30日,成都召开川路特别股东大会准备会。该会声明“惟争路乃可拒约,不争路并难保款”,拟议提回公司在宜昌、汉口等地的存款。该会在提案中解释道:“此法骤闻之,必有以吸现银过多,必惹起市面恐慌为疑者。不知我既欲达此重要目的,则以外任生何等危险,皆不必顾。且市面果有摇动,政府棘手无策,则争路目的或有可达之一日。”总公司董事局随即提出停止宜昌路工案,认为“宜工先时本无预算,近且乘此忙乱,耗费巨资。……宜工不修,应停止,即修亦应暂停”。股东会对之表示认可:“不修诚不善,然不修与外人修比较,则不修转较修善。我争回后,充其量不过路无力修,然此一块干净土,尚吾国子孙万世所有。”(70)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45-246、248页。
宜昌“本川中商务之外府,操商权者皆系蜀人”;(71)《川路滴滴血(十)》,《申报》1911年9月30日,第1张第5版。该地作为川路施工路段之所在,还聚集了公司花费巨资所购置的大量工料器械。成都特别股东会的提款停工方案将会恶化宜昌(路工)本就动荡不安的局势,也会给在宜川人(股东)和驻宜公司带来“池鱼之殃”。这种忽视宜昌路工现状、不计代价及后果的激进决策非但不能平息成、宜公司之间的争执,反而进一步加大双方的裂隙。
在宜昌路绅眼中,成都保路绅民“未悉路事之利害,及股本之难易”,其争路活动“不从融合政策,筹备股本着手,又牵及于拒债破约,是既违反其已宣布之政策,又欲变更其四国已批准之合同,陈义愈高,阻碍愈大”。而在成都方面看来,宜昌路绅不遵从总公司及股东会的相关决议,其保款主张更是“于路事国情,尚未明了”:“我川路既已失去夔关以下,譬如门户藩篱被人侵越,其危险为何如?亡川以亡国,均在于此,凡有普通常识者,均能反驳之。”(72)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68、818页。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分歧直接导致了李稷勋任免风波的发生,进一步推动了四川保路风潮的高涨和激化。
四、李稷勋任免风波与保路风潮的激化
1911年8月5日,川路特别股东会开幕并决议力争川路为商办。8月8日,邮传部下发咨文(“部咨”):“该路既收归国有,应俟将从前支出各款妥定归结办法。……所有宜归路工用人、用款,应责成该京卿(即李稷勋)悉心主持。……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呈报本部及督办大臣査核。”此文转到成都后引起轩然大波,“群哗路款并送,纷电责成”。总公司在当日即致电宜昌董事局,指责宜工“事权暗移,路款并送”,要求宜局董事“联合川人诘李”。四川咨议局则致电李稷勋称:“路已归官,非复川有,公已为官派总办,非复公司总理。”8月10日,股东会上呈川督赵尔丰代奏电文,弹劾盛宣怀“与一分公司总理私相授受,取接收路工之实,而阳避其名,并强据公司现款”,指控李稷勋私自“达部交涉”“专擅害公”,奏请将李稷勋予以免职。(7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4-258、261页。这便是保路风潮中聚讼一时的盛宣怀“弊通”李稷勋“夺路劫款”案。
为厘清此案根由,此处有必要先辨明李稷勋是否有权“达部交涉”。《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续订章程》规定,公司总、副理由“公司呈请四川总督奏派”,公司重要事务(包括任免总理)需禀请川督(转商邮传部)办理。这就导致“公司对于行政官府之关系,杂官权之作用,失商办之性质”,(74)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324-325、330页。为接下来股东会“奏免”李稷勋失败埋下了伏笔。川路公司原定的“总、副理制”在1908年演变为“三总理制”,三总理互不统属、各有职责。李稷勋本为邮传部参议,于1909年被前川督赵尔巽奏派为驻宜总理,主要负责该地的路工和招股事宜。从李稷勋的职权和官身来说,他是能够前往邮传部商讨川路宜工事宜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敢于光明正大地将其晋京行程告知成都总公司。
而李稷勋是否致使公司“事权暗移,路款并送”也需要在上述情形下予以判定。李稷勋本是邮传部属官,其总理一职也是由邮传部核准派定,“部咨”责成他主持宜昌路工实属正常。总公司对此其实异议不大,“尤为众指责者”主要在于“将办理情形随时呈报督办大臣”一节。(7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38页。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乃清廷为了将干路收归国有而添设的官职,在各省铁路交接期间,其职权颇为含混;李稷勋若向其随时呈报确实有“事权暗移”之嫌。但此项罪责的认定却需要后续查有实据,此时“部咨”刚下,相关事实尚未发生。准此再作申论,“路已归官”“路款并送”的指控也很难站得住脚。李稷勋曾将宜昌路工6月以来之用款特意改为另册登记,若成都路绅争路成功,那么宜夔路段就仍归公司承修,支用公司款项自无不可;若成都路绅争路失败、川路收归国有,账款另册登记也便于厘清权限以作为“认还川款之根据”。盛宣怀在致端方、瑞澂(两湖总督)的电文中曾说明道:宜昌路工邮传部尚未接收,“界限不清,又不能动支部款,故不得不饬令仍就川款应付,统侯接收时一并核结”。(76)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62页。可见,“部咨”之办法乃是宜夔归属未定之时维持宜昌工程的权宜之计,其后续如何办理仍有待进一步商议。
成都保路士绅因“部咨”一事而对李稷勋、盛宣怀大张挞伐,相关举动颇给人一种捕风捉影、张皇其事的感觉,其所反映的正是当时保路风潮的高涨和激化。因为在路事主张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成都路绅对宜昌公司的成见越来越深,股东会在8月7日就已决议取消驻宜董事冉崇根、杨用楫的董事资格。“部咨”下发的次日(8月9日),股东会又开会讨论对付李稷勋之办法并提出“最好方法不如暗杀”:“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全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要知吾川人之誓杀此二贼,非吾川人杀也,实法律杀之也。”(77)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35页。成都的保路风潮日益高涨,参与其中的保路绅民也是愈发敏感和激进。“保路”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使用“激烈手段”以推进“保路”、排斥异己越来越成为一种风习。(78)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四川保路同志会交涉部部长罗纶在8月9日时曾表态称,代奏参劾盛宣怀、李稷勋一事太难,意拟另商办法;“当时激成众怒,谓纶如畏葸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参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36页。
李稷勋饱受攻击、难安于位,遂于8月10日致电总公司道:“公等既主保路,势难停工。……如不接收,则承办洋商必起交涉,栈租月息,所费不赀。……总之,主争路则不能止款,主保款应速交路,不难两言而决。至勋奉文暂行经理,公等如有所疑,应请趁大会速举总理来宜,以便交卸。”(79)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38页。李稷勋随后又致电盛宣怀道:“现在路仍川有,勋仍商办总理,并非官派总办,不知何以遂滋乡人之疑。……至前与宜董事及公司同人所致股东会文电,不过为保全股本原额。……不料与会众意见相违,遂牵合两事,因疑致误。纷电诘责,屡经声辩,终不见谅,只得辞职。”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李稷勋仍是心系宜昌路工,但无奈只得自请辞职,股东会随即决议选举他人接任驻宜总理。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李稷勋乃川督“奏派之人,该会岂能擅行举换?似此无理取闹,必酿事端”。盛宣怀认同其意,认为宜昌路工正面临交接,若“骤易生手”,恐怕工段工人会蠢动不安,已成工程也将蒙受损失。盛宣怀、端方在一番考量之后,决议仍由李稷勋担任驻宜总理。瑞澂为维护宜昌治安起见,也决定“非留李姚琴(即李稷勋)不可”。端方在8月17日致电盛宣怀、载泽(度支部尚书)表态道:“既主留李,实是正办。惟此言一发,即系与川人决裂,必须内外通筹,坚持定见,一线到底。”(80)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61-264页。
其时股东会弹劾盛宣怀、李稷勋的奏文已由清廷下发,端方、盛宣怀等乃借此机会向清廷辩白并奏请留用李稷勋。端方、瑞澂致电内阁称,“部咨”委派李稷勋其实是“因顾全路事与绥靖地方起见,……乃川人计无所逞,辄指李稷勋专擅害公,妄议辞退”,奏请“明降谕旨,特派李稷勋仍行留办路工”。盛宣怀也上奏辩驳股东会的一应弹劾,指责股东会“任意开除奏派之总理”,认为“现值官商交接之间,若任令更新换旧,恐经手工程款项,必多推诿掩饰;而鄂督所虑谣言四起,有碍治安,亦所难免”,奏请转饬李稷勋“仍驻宜归,暂管路事”。(81)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69-271页。
8月19日,清廷同意了盛宣怀、端方的相关奏议,谕令川督赵尔丰转饬李稷勋仍驻宜昌管理路工,并命赵尔丰于成都“严行弹压,务任滋生事端”。(82)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82页。李稷勋被改为“钦派”意味着邮传部与股东会的“决裂”,8月24日“电文宣布,遂激成罢市之举”。(8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80页。在既有认知中,成都罢市被视为保路风潮突破“文明争路”并走向激进的标志性事件。(84)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256页。但从以上论述可知,股东会在“部咨”下发后就威胁对李稷勋进行暗杀,早已突破“文明争路”的范围。换言之,李稷勋任免风波的发生已导致成都的保路风潮走向激进化,成都罢市其实是此前风潮激化的一个显著后果;而这一后果又反过来助推了当时已经激化的风潮,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引线。
罢市之后,成都的保路活动更加激进且难以遏制,股东会随后又决议不纳正粮、不纳捐输。9月3日,股东会成立办事处以作“实行抗粮抗租之机关”。(8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932页。9月5日,有人在股东会会场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些举动无疑恶化了成都官场和保路绅民之间的关系。9月7日,赵尔丰逮捕罗纶、邓孝可等保路绅首,酿成枪杀平民的“成都血案”。保路同志军、革命党人等揭竿而起,路事最终演变成乱事,四川陷入乱局之中。(86)关于此段史事的研究和论述,可参见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265-300页。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8日,革命党人于宜昌举行起义。宜昌路工本就动荡不安,此时更是风雨飘摇。“鄂军猝兴,列城响应,烽埃翳天;工餫梗阻,徒夫兽骇,浸构凶害,……道路纷纭,哗言路工且变,中西商旅,一日数惊,妇稚流离,联艑东下”。11月,李稷勋在宜昌商会、宜昌军政府的帮助和震慑之下,决定停止宜归工程并解散各工段工人、包工,计耗费银币111万元(包工工价)、铜币1494万枚(工人工钱)。“路工停辍,役夫云散,工材亿千,沦于榛莽”。辛亥鼎革后,川绅决定将川路让归国有并与交通部签订收路偿款协议。1913年,交通部委派工程师前往宜昌“勘估工料,清核用款”并进行正式接收,四川商办川汉铁路驻宜公司随即撤销。(87)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文》,《交通丛报》1922年第86期,第1、2、9页。
五、结 论
川汉铁路的筹建深受锡良、张之洞、赵尔巽等督臣意志的影响,川路公司的选线和施工其实是一场以宜昌为题眼、以宜夔为主线的“命题作文”。这不仅导致了川汉全线由川省“独任其难”(88)周询:《蜀海丛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165页。情况的发生,还致使川路公司在勘线及论证不充分的局面下贸然开工,宜昌路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路线艰险、施工困难、舆论指责、股款亏短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宜工建设举步维艰、进退两难,所取得的成绩相当有限。再加之轰动一时的“上海倒款案”的发生,川路建设“溃败延误”已经成为难以遮掩的事实。这引起了朝野人士对既有铁路政策的反思,也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借债修路等举措的出台。在盛宣怀等清廷高层的主持下,已显成效、有望速成的国家借债修路策略取代了问题频出、工程迟滞的各省商办铁路方案。(89)关于此期清廷铁路政策转变及其与各省商办铁路建设、列强干涉铁路借款之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清廷干路国有的一应举措推出后,成都、宜昌两地川绅在路事处置上的分歧愈发明显。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万工程的艰难情状和工段的动荡形势,越来越注重维持宜昌路工的稳定和妥善归置公司的各类资产,其后又提出了保全路款、维持宜工的应对方案;而邓孝可、罗纶等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四国借款合同丧权卖路,随即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其后更是不计后果地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宜工的反对方案。这些矛盾致使成都路绅对宜昌路绅的成见越来越深,解任免职、威胁暗杀等手段相继被提出,保路风潮走向激进化。李稷勋任免风波诱发成都罢市之后,成都的保路风潮更加不可遏制,“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挽回矣”。(90)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338页。在成、宜分歧的助推之下,路事风潮最终走向决裂,(91)四川路潮走向决裂的原因相当复杂,如清廷处置失当、赵尔丰操之过急、罢市后局势逐渐失控、成都官民矛盾加剧、革命党人趁机活动,等等,既有研究对此多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两地公司均陷于乱局和动荡之中。
从宜昌路事来反观四川路潮,我们可以对成都的保路活动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路潮激荡和分歧显现之时,成都总公司、股东会的保路士绅总是从路权(可能)丧失的角度来“定性”相关的人、事、物并对之进行抗议和讨伐,具体的铁路事务时常被置于陪衬地位;他们并不真切了解宜昌路工的困境和现状,在宜归工程动摇、公司资产受损的情况下也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处置方案。“但日闻诸公之力争,不闻诸公之办法”,(92)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304页。路事风潮难以平息,路工危局也无从解决,川路建设“溃败延误”、宜昌工段资财耗散的恶果只能由广大川人和股东承担。
既有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由于深受“保路”话语及立场的影响,比较侧重于对成都的保路活动及其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论述,对宜昌路绅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主张则鲜有深入的讨论和正面的评价。(93)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246-256页;鲜于浩:《四川保路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鲜于浩:《四川保路运动再研究》,第170-192页。一些以清廷举措为切入点的研究虽对之有所纠偏,但仍旧分享着清廷(高官)举措失当、“官逼民反”的认知逻辑,仍是潜藏着“厚”成都路潮、“薄”宜昌路事的认知倾向。(94)此类研究可参见陈廷湘:《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苏全有:《论清末的干路国有政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杨猛:《“路事”与“乱事”:载泽与辛亥年干路国有风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这些“偏视”忽略了宜昌路工的复杂情状,也未能注意到工程资产、工人生计、地方治安等因素对相关任事官绅的路事决策所造成的影响。路事本身研究的不足将不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与之相关联的路政、路策和路潮,(95)如既有研究基于章程条文的解读,普遍认为川路租股征收遍及四川农村社会各个阶层。但笔者经过史料考证和数据分析发现,租股的实际征收范围其实相当有限。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四川保路运动中民众的动员和参与问题。参见高龙:《川汉铁路租股征收问题新探》,《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而宜昌路工相关史事的揭出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清末川汉铁路的路事变迁和路潮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