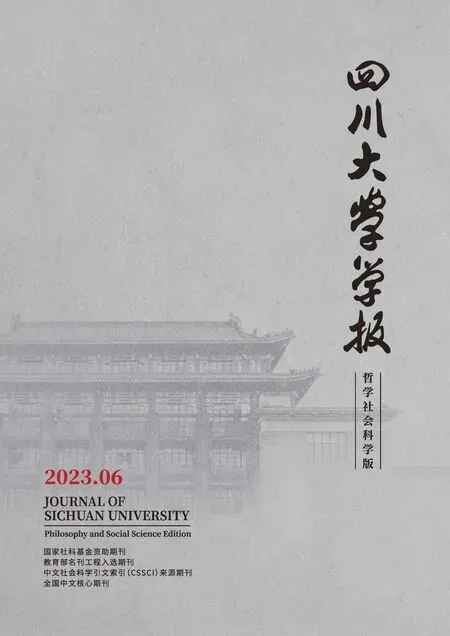“谁来继承英格兰?”:《霍华德庄园》中的记忆冲突与传承
2023-03-13王欣
王 欣
《霍华德庄园》(HowardsEnd,1910)是英国爱德华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被美国文学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誉为“一部毫无疑问的经典之作”。(1)Lionel Trilling,E. M. Forster,New York:New Directions,1943,p.114.《霍华德庄园》中的乡村庄园作为英国记忆场域的讨论是该小说研究的一个焦点。司代普(J. H. Stape)认为,“霍华德庄园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英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中心,是稳定的,与流动的、无根的现代化城市伦敦相对立”。(2)J. H. Stape,“Picturing the Self as Other:Howards End as Psychobiography,”in Alistair M. Duckworth,ed.,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 &Boston:Bedford Books,1997,p.339.德尔巴-加兰特(J. Delbaere-Garant)则认为霍华德庄园“最终成了一个不同阶级、文化与历史的融合物,为英国的未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J. Delbaere-Garant,“‘Who Shall Inherit Engl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Howards End,Parade's End 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English Studies,vol.50,no.1-6(1969),p.101.除了伦敦与霍华德庄园之外,埃文斯(Walter Evans)发现,小说中“奥尼顿也是英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的代表,也是理解小说的一个关键因素”。(4)Walter Evans,“Forster's Howards End,” The Explicator,vol.36,no.3(1978),pp.36-37.另有一些学者将《霍华德庄园》中的场所与物品所承载的记忆及象征意义与维多利亚时期出现的“怀旧商品化”(Commodified Nostalgia)现象联系起来。如道尔(T. Douglas Doyle)指出,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编织与做针线活”(sewing and weaving)的行为,与小说的记忆主题有深刻的内在关联。(5)T. Douglas Doyle,“Forster's Howards End,” The Explicator,vol.52,no.4(1994),pp.226-228.国内学者何宁分析指出,“福斯特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通过两次‘照片事件’展示出两位主人公伦纳德·巴斯特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所面对的社会身份边缘化的危机”。(6)何宁:《福斯特与〈霍华德庄园〉中的照片》,《读书》2021年第5期。以上学者都从怀旧和记忆的角度分析,但是并没有揭示小说中记忆危机与记忆传承的问题,而后者恰是理解《霍华德庄园》的一个重要方面。
《霍华德庄园》深刻地反映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爱德华时代世纪交替中文化记忆面临的危机和传承问题。特里林认为霍华德庄园的传承,是一个“谁来继承英格兰”(Who shall inherit England?)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文化记忆问题,即:“英格兰将选择什么来传承?什么会被它选择作为遗产?物质还是精神?身体还是灵魂?”(7)Elizabeth J. Hodge,“The Mysteries of Eleusis at Howards End:Germ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a Mythology for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13,no.1(2006),p.50.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给出的答案是“唯有联结”(only connect)。小说将原本对立冲突的各阶层重新联结为一个象征性整体,建构霍华德庄园这一英国传统记忆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 or the Realm of Memory),以重建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聚力。
一、“英格兰现状”和记忆传承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霍华德庄园》应该被作为英格兰现状小说(a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来阅读。19世纪中叶,批评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最先意识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困惑和反常,提出了“英格兰现状”问题。卡莱尔指出,“社会财富增加,旧的社会方法已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时代病了,混乱不堪”。卡莱尔在其1839年的论文《宪章主义》中,回顾了“法国革命”中产业工人强有力的政治表达所引发的日益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威胁,他认为这一警告对英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以上引文参见安妮特·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司各特到肖伯纳》下,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97、96、99页。卡莱尔的观念深深影响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批重要作家,如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莫里斯(William Morris)、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他们“设法将一个正在裂变的思想体系凝聚在一起,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知识界竭尽全力的目标。就当时的性质而言,这是一个解说和理论上的冲突、科学和经济上的自信、社会和精神上的悲观主义、深刻意识到进步的不可避免、深深的焦虑不安的时代”。(9)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84页。这些作家创作描绘英格兰现状小说,探索了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背后社会道德沦丧、宗教信仰式微,以及工人阶级低工资、失业、罢工等社会问题,反映出对英格兰未来走向和发展的焦虑。
在此文学传统和背景下,《霍华德庄园》所聚焦的“谁来继承霍华德庄园”的问题,其象征意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里林认为,“这本小说的情节如大多数英国小说一样,是关于财产继承的问题,也就是‘谁来继承英格兰’的问题”,而小说结尾伦纳德和海伦的孩子成为霍华德庄园的下一任继承者,预示着一个无阶层划分的英国社会即将到来。(10)Trilling,E. M. Forster,p.118.对于这一点,有研究者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样一种阶层间的融合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因为伦纳德的死亡和亨利·威尔科克斯的衰老,这个孩子实际上属于施莱格尔姐妹所属的那个阶层”。(11)Thomas Churchill,“Place and Personality in Howards End,” 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vol.5,no.1(1962),p.72.也有研究者持相同意见,认为小说具备现实主义本质,福斯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所有可能的最好的品质与价值观念的英国继承者,以确保英国伟大传统的延续与活力”。(12)Peter Widdowson,“Howards End:Fiction as History,”in Duckworth,ed.,E. M. Forster,p.364.也就是说,谁来继承霍华德庄园的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关于英国记忆继承的问题。因而,小说中的霍华德庄园人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这部小说是否成功地完成了其卷首格言所宣称的“唯有联结”的任务,一直以来都是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13)关于这方面讨论的相关梳理与总结,参见Leslie White,“Vital Disconnection in Howards En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vol.51,no.1(2005),pp.43,57-58.
小说中,作为霍华德庄园继承候选人的玛格丽特和威尔科克斯父子,代表着19世纪英国两种不同的记忆。施莱格尔姐妹祖上留有遗产,积极参加上流社会的文化活动,注重人际关系、个人情感、想象力与内在的精神生活,代表着浪漫主义的文化记忆。而威尔科克斯父子则是工具理性和金钱物质的拥戴者,他们讲究实用,追求金钱的最大功效,通过精确计算功利来达到目的,代表着工业资本记忆。小说开篇提到的“威尔科克斯风波”所反映的正是这两种文化记忆的冲突。在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尔科克斯一家以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方式相遇后,海伦在写给姐姐玛格丽特的信中说,“威尔科克斯一家的活力让她着迷,在她的脑海里形成了众多美丽的画面,而她则积极予以回应”。其结果是海伦与保罗很快坠入了爱河,又以更快的速度分道扬镳,因为保罗还要去尼日利亚干一番事业,而海伦明显不符合他选择妻子的标准。这次风波对施莱格尔姐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亲情关系在那里并不是最重要的。在那里,爱情意味着婚姻财产的授予,而死亡就意味着缴纳遗产税。”(14)以上引文参见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巫和雄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2页。施莱格尔姐妹文雅的行为举止、优雅的生活趣味和文化标准,和威尔科克斯父子粗鲁冒失的作风、拓展海外生意的冲动及锱铢必较的生意头脑形成了对比。海伦与威尔科克斯家人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到爱德华时代社会转型期间,浪漫主义的文化记忆和工业文明的文化记忆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带来的情感生活中的失望、混乱和挫败感。
19世纪,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和殖民地赚取了巨大利润,成为世界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然而,机器时代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精神的充裕,而是如西方研究者所言:“进步已经让我们所有的精神如此的枯萎。”(15)Philippe Roger,The American Enemy:A Story of French Anti-Americanism,trans. Sharon Bow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62.小说中即以玛格丽特的感知表达了这种精神上的危机:“这个世界的灵魂是经济,最深的深渊不是没有爱,而是没有金钱。”当金钱变成了新的、世俗的“上帝”,经济原则与金融体系变成了新的道德准则,以此为指导的人际关系就成为一种物质交换关系,如玛格丽特所说,“我们的思想是拥有六百镑的人的思想,我们说的话也是拥有六百镑的人的话”。(16)以上引文参见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15、44页。尽管玛格丽特的沙龙中充斥着文学与音乐、女性权益、民主平等、社会责任等议题的讨论,但这种浪漫主义者对理性、秩序和想象力的倡导,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和人的异化,也无法让施莱格尔姐妹摆脱由伦敦拆迁带来的“游牧生活”的不安。浪漫主义的温情掩盖不了物质主义的冷酷无情,这种冲突割裂了跨阶层之间的交往,小说中的下层人士伦纳德就处于这种理想和现实割裂的状态。伦纳德是一个有着较高艺术修养的人物形象,他不仅研读斯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卢卡斯(Edward V. Lucas)的文学作品,他的“夜间荒野漫游”更是展现了19世纪末期的“自我关注、自我怀疑、爱情的捉摸不定、旅行的自由”,(17)阿瑟·休克拉夫(Arthur Huph Clough,1819-1861)的《旅行之爱》(Amours de Voyage,1858)中,以旅行见闻和自我分析讨论了19世纪英国人热衷的旅行给情操方面带来的影响。详见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第661页。而他的音乐爱好也使他有机会接近施莱格尔姐妹。但文学艺术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窘迫,对于施莱格尔姐妹的信任反而使伦纳德丢了工作,和海伦的私情也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施莱格尔姐妹对伦敦居所不定的不安,威尔科克斯父子时时在灵魂深处感到的罪恶,伦纳德对世界不断下坠乃至崩溃的感受,都隐喻着维多利亚时代中表面的优雅平和、繁荣进取下,社会内部情感结构中各个阶层深刻的分裂。不论是充满紧张气氛的家庭关系,还是社会成员明显不安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都显示出各阶层的人们与稳固安宁的传统之间存在着记忆的断裂。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是具有自由思想还是持保守思想的维多利亚人,不安感都日渐增强。尽管19世纪英国的国际声望和经济力量已为世界所关注,但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经济增长率的停滞、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激烈改变、海上霸权受到德国海军扩张的挑战等社会现状,也成为公众不安的来源。就如同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多佛海滩,声称他听到了“信念的海洋的‘忧郁、慢慢退却的吼声’”(18)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第654页。一样,这种对英国未来走向的不安感是无法避免的。卡莱尔的所谓英格兰现状问题正在指向一种不确定的未来。
二、伦敦城市和霍华德庄园
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科技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物质层面的繁荣与精神层面的危机共同构筑了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面貌,形成了不同往昔的突出特征。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指出:“同那些曾认为他生活其中的世界是处于逝去了的黄金时代与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之间的(一个持久不变的中间阶段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19)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2页。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伦敦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中心。《霍华德庄园》将伦敦所具有的庞大的非人的力量与盲目的、变动无常的本质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个伦敦有着不断流动与变化的城市景观,居住在这里的主要人物都“居无定所”,不是等待着搬家就是正在搬家,或者是被迫“流离失所”。玛格丽特讨厌伦敦的变动无常,更厌恶随之而来的颠沛流离的感觉:
这个城市本身也在不断变迁,……这个著名的大楼拔地而起,那个建筑则难逃拆除的厄运。今天改造了白厅街,明天就要轮到摄政街了。月复一月,路上的汽油味儿越来越浓,街道越来越难通过,人们越来越难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呼吸越来越困难,蓝天越来越少见。(20)以上引文参见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79-80、106页。
通过她的感受,我们可以获得对当时伦敦人居处不安和彼此疏离的深刻感知。
《霍华德庄园》中所描绘的伦敦城市中的居无定所,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流动,而是圈地运动和济贫税造成的社会流浪。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失去土地的人们不断涌向城市,日益扩张的城市如同巨兽,逐渐吞没了英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记忆。由于传统的文化被工业革命引起的变化破坏,如英国研究者所言:“我们已失去的是体现活文化的有机群体。民谣、民间舞蹈、科茨沃德山区的村舍、手工艺制品说明了一种生活艺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规则,有格调,涉及了社会艺术、交往原则,以及从远古继承而来的对自然环境和季节交替的适应能力。”(21)F. R.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Westport,CT:Greenwood,1933,pp.1-2.工业化的结果是劳动者失去了劳动的乐趣,工作只是为了谋生,传统的乡村生活丰富多样的生活节奏消失了,代之以单调、平和、机械的城市生活模式。乡村文化记忆的消失导致了个人心理的困惑和疾病,进而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指出的,“心理学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22)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序言”,第1页。小说中的施莱格尔姐妹生活在商业发达的伦敦城市中,尽管这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但她们感觉“吸进口中的空气冰如硬币,……到处弥漫着粗俗的气息”。而且“城市的面目有点狰狞,越来越狭窄的街道就像矿下坑道一般逼仄。……情绪的低落让内心感受到愈发悲哀的黑暗,反过来又让情绪愈发低落”。(23)以上引文参见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271、83页。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个体,无力去关注未知的、无功利性的世界,精神和情感趋于麻木,逐渐丧失正确看待自我和批评社会现状的能力。
与伦敦代表着对传统文化记忆的破坏相反,霍华德庄园作为传统乡村文化与贵族文化的中心,所代表的是传统的“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24)参见Judith Weissman,“Howard End:Gasoline and Goddesses,”in Duckworth,ed.,E. M. Forster,p.440.而其实质是“对一种以固定的、互惠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秩序的美化”。(25)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1页。小说通过霍华德庄园附近村民对它的评价,展现了这种英国传统的道德经济:“这家人特别仁义,老霍华德夫人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也不会把人家饿着肚子打发走。那个时候,他们的土地上从来没有树过‘外人免进,违者严惩’的牌子,而是客气地说‘请勿进入’。”作为霍华德庄园真正的拥有者,威尔科克斯家的女主人露丝的形象与众不同:
她拖着长裙不声不响地穿过草坪,款款而来,手里还捏着一把草。她跟两个年轻人以及他们的汽车似乎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她只属于这房子,属于笼罩其上的那棵树。大家都知道,她崇尚过往,而这过往将特有的智慧加持到她的身上——大家把这智慧不太贴切地叫做贵族气质。(26)以上引文参见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125、20页。
作为小说中第三种文化记忆的象征,露丝身上明显表征着英国乡村田园文化记忆。她出场时手里捏着一把草,不禁令人联想到诗人华玆华斯的《露西组诗》中所描绘的英国田野形象:“你晨光展现的,/你夜幕遮掩的,/是露西游憩的林园;/露西,她最后一眼望见的,/是你那青碧的草原。”(27)《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从中也可以看出,露丝的形象是对古希腊依洛西斯神话(Eleusinian Mysteries)中代表土地与庄稼的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的化用。在古希腊的依洛西斯神庙祭祀中,德墨忒尔的崇拜者就是手执着“在寂静中收割的一穗谷子”。(28)Edith Hamilton,Mythology, New York and Scarborough:New American Library,1969,p.48.因此可以说,手握青草的露丝,实质上是土地和英国传统乡村文明的象征。
露丝和她所拥有的霍华德庄园代表着一种更加稳定和有机的乡村生活记忆,而作者福斯特对霍华德庄园(乡村宅院)和露丝(宅院主人)的青睐,则意在建构黏合社会各阶层的稳定的文化象征结构。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Struktur),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它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29)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霍华德庄园》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不同角度的冲突与联系,阶级的对立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往往交织在一起,但最终这些冲突都通过霍华德庄园所建构的共同的回忆、经历和情感而逐渐趋同。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似乎在去往或者说寻找霍华德庄园的路上,而当他们最终抵达的时候,所有的伤痛似乎都会得到抚慰,所有的冲突也会得到化解。首先到达霍华德庄园的是玛格丽特和海伦,原本以为这将是一次不愉快甚至是最后的会面,但是霍华德庄园里面被重新安置的施莱格尔家的旧家具勾起了两个姐妹共同的回忆——椅子上一处污渍,使她们回忆起童年的趣事,并深刻地认识到她们“彼此不可能被分开,因为她们的爱根植于共性的东西”。(30)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297页。而所谓“共性的东西”很明显就是共同的记忆及其附着的情感与经历。之后,查尔斯和伦纳德两人之间爆发了剧烈而短暂的冲突,造成伦纳德死于刺伤引发的心脏病,查尔斯也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而被捕,导致其父威尔科克斯精神崩溃,最终来到霍华德庄园在玛格丽特这里找到了安慰。从露丝来到伦敦寻找到她精神上的女儿玛格丽特,到她逝去后将霍华德庄园留给玛格丽特继承,最终海伦的孩子入住庄园,成为继承人,霍华德庄园继承人之间在整体上形成了诞生-死亡-重生的记忆联结。
三、记忆之场与记忆联结
《霍华德庄园》中所描述的所有相互对立冲突的元素,其本质上都可以说是不同的文化记忆之间的对立冲突。记忆是一种选择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通过各种记忆的矛盾冲突而形成记忆交织的凝聚点,即将某一记忆图像置于其他形象之上,成为特定共同体内获得公众认同的最终选择。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中的霍华德庄园正是福斯特试图建构的一个拥有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聚力的记忆之场。有研究者将“记忆之场”定义为“任何经由人类的意志或时间的打磨,已经成为其所在社群的纪念性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实体”,(31)Pierre Nora,“From Lieux de memoire to Realms of Memory,” in Lawrence D. Kritzman,ed.,Realms of Memor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ⅹⅶ.认为虽然“记忆之场作为一种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但是其核心在于象征性,归根结底是象征性使一个‘场所’成为‘记忆之场’”。(32)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29页。因此,霍华德庄园的真正价值也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种记忆的联结与重组,而更在于它还提供了一个英国记忆传承的象征。
霍华德庄园的拥有者露丝的形象与其说是一种久远的神话象征,不如说是以她为表征的这个田园神话记忆给现代英国带来了精神慰藉。西塞罗曾对古希腊罗马神话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些神话让我们的性格甜蜜,让我们的习惯柔和;它们让我们从野蛮的状态进化到真正的人性。它们不仅给我们展示了愉悦生活的方式,而且教诲了我们如何带着更好的希望死去。”(33)转引自Hamilton,Mythology, p.48.而霍华德庄园也正是以其特有的英国乡村神话传奇,展示了文化记忆中大地女神和土地的联系。如小说描绘庄园中栽种着英国古老的山榆树,(34)山榆树长期作为“英国”的隐喻出现,如盖斯凯尔夫人的《露丝》(Elizabeth Gaskell,Ruth,Global Grey Ebooks,2018,p.38);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George Eliot, Felix Holt:The Radical,Free Classic eBooks,p.8);及哈代的《一双蓝眼睛》(Thomas Hardy, A Pair of Blue Ey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中都有相关的意象。“那棵树的树干上嵌了几颗猪的牙齿,离地面大概有四英尺的高度,是很久以前乡下人嵌上去的,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嚼一块树皮就能治好牙疼。现在这些牙齿几乎被树皮覆盖住了,也没人再理会这棵树”。(35)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97页。这里的猪牙故事是和希腊神话相联系的。在希腊神话中,美少年安东尼斯(Adonis)是从树中诞生的,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和冥界的王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都爱上了他,宙斯判决让安东尼斯秋冬季节与冥后在一起,春夏季节则与爱神共处。在一次狩猎中,安东尼斯被野猪的獠牙刺伤流血而死,化为了血红色的银莲花。(36)参见Hamilton,Mythology, pp.90-91.霍华德庄园山榆树中的猪牙,作为神话和乡土的记忆之锚,成为死亡和再生的象征;如同小说中伦纳德最后被刺伤而死于心脏病,他的儿子却成为庄园的最后继承人,证明霍华德庄园作为继承英国文化记忆的“场所”,本身具有神奇的愈合力量。
作为英国传统文化的“记忆之场”,霍华德庄园发挥了福斯特所言“唯有联结”的作用。威廉斯指出:“围绕着定居的观念发展出了一种真正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依赖于许多真切而持久的情感:对那些我们生长于其间的人们的认同感;对我们最初生活于斯和最先学会用眼去看的那个地方,那片景色的眷恋之情。”(37)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121页。作为霍华德庄园的继承人,玛格丽特第一次造访霍华德庄园时,她就感受到了霍华德庄园所承载的英国传统文化记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从容领略人生,一切尽在掌握,一眼看清人生的短暂和青春的永恒,并将两者联系起来——毫无痛苦地联结起来,直到所有人都情同手足,那就是这些英格兰农场了。”(38)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266页。霍华德庄园具有神奇的治愈能力,能够让疏离的现代人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温情。当施莱格尔一家的房子租约到期而不得不搬离伦敦,他们把所有的家具、书籍和生活物品全部都打包运到了霍华德庄园。在这里,那些三十年来都没感受过阳光的可爱的小椅背被晒得挺热乎的,不仅如此,霍华德庄园还恢复了被遗忘的家庭温暖,使矛盾的文化记忆共同建筑在英国共享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上,成为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科克斯父子认同的记忆之场。
文化记忆是一个不断被选择和阐释的过程。社会发展、历史变化和阶级利益等都会影响我们如何定义过去,如何传承价值。“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39)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35页。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露丝对事物所做的判断依靠直觉,然而她本能地对土地存有温情,本能地抵制威尔科克斯家族那种坚不可摧但庸俗无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福斯特投射了他对‘以前的英国’的种种想象”。(40)纳海:《寻找英伦的神话:〈霍华德庄园〉中的“英国问题”和国民性》,《外国文学》2017年第4期。露丝选择玛格丽特作为霍华德庄园的继承人,正是看到了玛格丽特身上既具备英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又能够引导工业资产阶级的进取方向。从词源来看,“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指涉着“hog warden”(“看猪人”)或“guardian of the home”,从象征意义来看,其所指的是“家的守护者”。作为霍华德庄园的继承者和守护者,玛格丽特清楚地意识到金钱和灵魂之间的矛盾,看到都市生活的不确定和乡村生活的安宁之间的反差,所以她赋予自身的任务就是建起一座“彩虹之桥,把我们内心的平淡与激情联结起来。没有这座桥梁,我们就是毫无意义的碎片,一半是僧侣一半是野兽”。(41)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18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玛格丽特成为“家的守护者”,而霍华德庄园也成了施莱格尔姐妹、威尔科克斯先生、海伦和伦纳德的儿子的家园。三种文化记忆通过霍华德庄园的联结,形成一个稳定的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具有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集力的“记忆之场”。在这个意义上,福斯特也回答了英国未来将继承什么、谁来继承的问题。
结 语
乌特卡(Elizabeth Outka)指出,“福斯特对霍华德庄园空间上的重新组织实际上是对于空间所承载的时间(包括记忆与历史)的重新组织,以此重新建构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从而将人、物与场所联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42)Elizabeth Outka,“Buying Time:Howards End and Commodified Nostalgia,” NOVEL:A Forum on Fiction,vol.36,no.3(2003),pp.330-350.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科克斯父子的冲突、伦纳德的沦丧反映了英国19世纪以来各种社会问题,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现状小说对英国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思考;同时,伦敦城市和霍华德庄园之间的对立,也展现了现代与传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情感的困惑和记忆的断裂。福斯特在小说中对传统记忆的继承问题提出了“唯有联结”的断语,他通过文学的表现力,以霍华德庄园为记忆之场,寻找记忆之锚,建构了过去和现在、城市和乡村、阶级冲突之间的联系。如德尔巴-加兰特所指出的那样,霍华德庄园“最终成为了一个不同阶级、文化与历史的融合物,为英国的未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3)Delbaere-Garant,“‘Who Shall Inherit Engl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Howards End,Parade's End 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p.101.尽管小说充满作者主观性的想象和希望,但霍华德庄园所承袭的英国传统文化记忆和所象征的英国“记忆之场”,却通过承认差异并且认同差异,让生活在其中的浪漫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可以和谐共处,让原本冲突的各阶级可以重新找到各自的位置,使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们预期的那样去发展”。(44)E. M.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第336页。小说的结局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与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霍华德庄园》展现了爱德华时代对改变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阴郁态度的尝试。